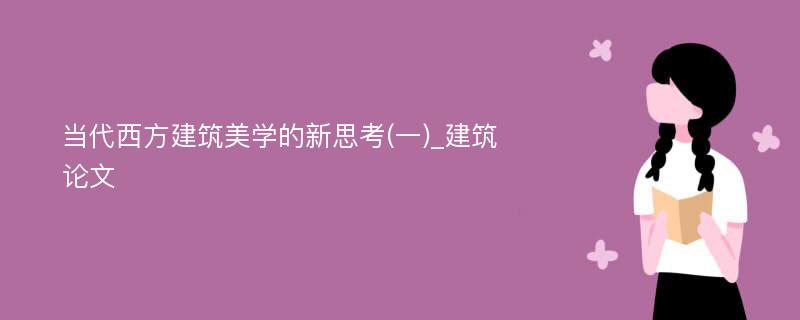
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新思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美学论文,当代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思维的变化。这是一种富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变化。我们知道,现代建筑的审美思维,基本上局限于总体性思维、线型思维、理性思维这种固定的、僵死的框框之中,很难突破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束缚。然而,在当代,在西方当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和推动下,当代建筑审美思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它完全摆脱了总体性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思维的惯性,迈向了一种更富有当代性的新思维之途。
美国学者詹姆逊曾经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作过如下描述:
当代的理论,也即后现代主义理论排斥我所谓思想领域里颇有影响的四种深层模式;有关本质和现象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和虚假意认的辩证思维模式正是这样一种深层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从表面进入深层的阅读和理解,实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言而喻,当今的理论对这一深层的攻击最为激烈。第二种有影响的深层模式自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和分析模式,这一模式对梦的表层和潜在的各个层次和压抑进行分析,显然这种心理分析在当代思维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同样受到当代理论激烈的攻击,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那本书就对心理分析模式作过诋毁,特别是米歇尔·福柯在他那本著名的《性的历史》中提出彻底丢弃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观念。第三种在西方有影响的深层模式是存在主义的模式和它关于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它也是当代理论攻击的一个目标。最后一种深层模式是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它包含指符和意符两个层次。但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们实质上用这种理论来反对它自身,提出对索绪尔二元体系的批判,当代理论(即后结构主义理论)普遍采取这一立场。综上所述,当代理论要做的一切……只是在浅表玩弄指符、对立、本文的力和材料等概念,它不再要求关于稳定的真理的老观念,只是玩弄文字表面的游戏。[1]
虽然詹姆逊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演讲有它特有的语境,并且他对后现代主义(指文化上的——作者注)的批判也有过激之处,但是,即使在今天,他对当时的西方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对当下西方的艺术理论,对西方的建筑美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因为他至少总结出了当代理论思维的两大特征,非理性思维和非总体性思维。这是詹姆逊通过第一种思维模式和第四种思维模式总结出来的。
由于詹姆逊的这篇演讲出现于十几年以前,加上他所论述的,是文化和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在参考他的论点的同时,当然必须从建筑美学的实际出发,因为我们探讨的毕竟是建筑美学自身的思维特征问题。
一、非总体性思维
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霸权和纯净主义美学基本上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压迫性总体化”(阿多诺语)来调控和引导建筑的美学走向的。当文丘里、菲利普·约翰逊等人起而挑战这种“压迫性总体化”,当反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领域日益变得蓬蓬勃勃的时候,现代主义的大一统格局很快就被打破,总体性受到重挫。不幸的是,当后现代主义建筑大量涌现时,建筑师们很快就预感到,他们很可能会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从一种处境跳入另一种处境”(注:雅斯贝尔斯说:“因为实存是处境中的一种存在,所以我永远不能逃出处境,除非我又跳入另一处境。”雅斯贝尔斯《哲学》,转引自徐崇温编《存在主义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4页。)一样,从一种总体性跌进另一种总体性。这种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美学革命,是当代建筑师和美学家最不愿意看到,最不能接受的,因此,从反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直至当今出现的各种新建筑观念,无不把抵抗总体性、追求差异性作为预防和驱逐任何形式的美学专制妖魅的旗帜。(注:所以沃·威尔什说:“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现实和知识结构的统一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再有效。”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让—弗·利奥塔等著,赵一凡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阿多诺(Theodor W·Adoeno,德国哲学家)(注:T.W.阿多诺(1903~1969),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否定的辩证法》,《齐克果:美学的建构》,《美学理论》等。)说,“人类的解放决不意味着成为一种总体性”(注:参见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5页。)。为了在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进行沟通和了解,确实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应该遵循同一种总体性。对审美,具体地说,对艺术和建筑来说,总体性通常只能是一种惰性力量,甚至可以说,它是创造性最可怕的敌人。
总体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周期性病态发作的惯性力量。当艺术上的一种总体性遭到致命打击之时,往往正是另一种总体性悄悄出笼之际。所以阿多诺认为,如果艺术始终是激进的,它就始终是保守的,强化与支配性精神相分离的幻觉,“它在实践上的无效以及与没有减轻的灾难的同谋关系就显然是痛苦的”。它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如果艺术绕开贬黜历史的逻辑,那么它必定要为这个自由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难以符合历史逻辑的再生产。(注:参见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阿多诺对逃离总体性一直持一种矛盾、怀疑甚至是悲观的态度。他曾说过,我们可以忽视总体性,但总体性却并不忽视我们。仿佛总体性是一种如影随形、神出鬼没、无法摆脱的东西。在他看来,逃离总体性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因为你在对抗总体性时,“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可是,大多数建筑师并不同意阿多诺的观点,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建筑师的关注力、知觉和选择的能力,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自主性和捕捉与表现自我差异性的能力,以图逃离总体性的陷阱。
被菲利普·朱迪狄欧(Philip Jodidio)誉为思想型建筑师的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说过:“建筑与其遵从技术或风格的统一,不如让它向场所的非理性开放。它应该抵制标准化的同一性倾向……新的建筑必须这样构成:它既与跨文化的连续性适配,同时也与个人环境和社区的诗意表现适配”(注:Philip Jodidio:New Forms:Architecture in the 1990s,Taschen,1997年,第76页。)。霍尔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总体化,他心中理想的建筑,是既合乎个人生存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境遇,又具有某种异质性因素的建筑。
摩弗西斯事务所的主将汤姆·梅恩一向以特立独行而著称,他虽然没有像屈米和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注:美国青年建筑师和有影响的建筑评论家。著有Exquisite Corpse:Writing On Buildings(London,1991)等。)那样,呼唤丑陋的建筑,但他对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忽视几乎与他对建筑结构和空间的重视一样出名。他对拼贴式的、虚假的后现代主义怀着深深的厌恶,对80年代流行一时的虚假的多元论更是不屑一顾。他曾说,“今天,我们有可能评价我们多元世界里共同的价值系统,在这个世界,现实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因而终究也是不可知的。冒险已经成为我们的操作原则……今日建筑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关于一个建筑师是否可以摆脱内在于我们环境的、腐蚀我们的自主性、自我意识甚至个人心智的心理和社会的势力而独立行动的问题。”(注:Tom Mayne.Connected Isolation.Peter Noever(editor).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 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New Modernism.Munich:Prestel,1991年。)梅恩和他的其他合作者们一样,极为重视艺术创造的个人性和独立性。在他们看来,个体不应该受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影响,不应该受制于宏观理性,而应该听从自我的纯粹创造使命的指引,走“小叙述”也即个人化道路。只有这样,建筑才能摆脱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怪圈。同设计维也纳Z银行的G.多米尼希(Gunther Domenig)一样,蓝天组的沃尔夫·普瑞克斯(Wolf Prix)显然也把建筑当作了一种叙述性和表情性艺术。他真诚地希望建筑师的设计能够和作家们的创作一样,充分构拟、揭示和表现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说:“我们应该寻找一种足以反映我们世界和社会的多样性的复杂性。交错组合和开放的建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怂恿使用者去占据空间”(注:Wolf Prix.On the Edge.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 & Maggie Toy (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唯有语言艺术能够自如地描绘、揭示和诠释心灵、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常识普瑞克斯当然知道。但是,他和许多当代建筑师一样,急切地希望建筑能够超越自身的极限,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同总体性抗衡,所以难免对建筑的叙述性和表情性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许。
比起普瑞克斯,迈克尔·索尔金属于那种思想激进、敢说敢干的、富有青春气息的建筑师类型。他的建筑主张往往带有强烈的达达主义式的叛逆色彩。他说:“……应该让建筑出来为无理性的幻想申辩……建筑师应该是最开放的,可以和任何人或任何有意愿达到极佳效果的事物结合。你要想成为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爱你的所有的孩子,尤其要尊重他们的差异性。让我们设计怪异的、拉伯雷(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讽刺作家和科学家。其讽刺作品风格怪异,滑稽突梯。《巨人传》为其代表作。)式的、疯狂的建筑吧……这是新生的模式也是乌托邦,是对理性的官方风格的一种快乐的戏拟。我喜欢那种具有反讽风格的建筑”(注:索尔金的这段文字讲到,建筑师应该是可以和任何愿意达到性高潮的人结合的性放纵者,引者对这段文字作了意译。见Peter Noever(editor).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 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New Modernism.Munich:Prestel,1991年,第119页。)。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建筑师在考虑建筑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个性从那种“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救出来,如何充分发展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把大叙述和小叙述对立起来,把总体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把同一性和异质性对立起来,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自我的创造的思维特征,不仅是建筑领域,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利奥塔就曾以嘲弄的语气说过:
在争取宽松和普遍的倦慵感的状况下,我们居然听到一种祈望回到恐惧感的咕噜,渴望让幻想成为真实而去把握现实的幻想。
我对此的回答是: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和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Diane Ghirardo说:“后现代主义在这些领域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如拒绝统一的世界观……在二十世纪早期,当现代化力量倾向于消除乡土的、宗教的和种族的差异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却明显强调这些差异性并将其推向显著位置,而它曾一度被现代主义这一占主流的文化推向边缘。也许,最好的例证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对种族和男女平等的研究的热忱,这些研究者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希望人们能够倾听从前不可能听到的呼声。”参见Diane Ghirardo:Architecture After Modernism.Thames and Hudson,1996年,第7页。)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他们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写道: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那些构筑世界)的砖块业已土崩瓦解……我们不再相信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再相信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德勒兹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书中指出:
……理论并不要求总体化,它只是一种实现繁多化的工具,并且将其自身繁多化……总体化是权力的本性……而理论从本质上讲是反对权力的。(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福柯说:
(必须)把政治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subvision)和建构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也许当今的任务不是去揭示我们之所是,而是去拒绝我们之所是。(注:福柯.主体与权力.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向统一的整体开战”的思想,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差异理论,福柯的恢复被总体性压抑的自主话语和知识的思想,甚至还有德里达的解构哲学,都具有一种极为明显的反社会、反主流文化的倾向。虽然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很少关注某一具体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情境,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毫无疑问地揭示了并影响了作为最具有大众性的文化情境之一的建筑及其观念。当代建筑审美思维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把总体性作为自己打击和颠覆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当代流行的反总体文化和哲学。
建筑创作的变革,从来都是以审美思维的变革为先导的。没有对建筑的审美思维惯性的超越,就不可能实现建筑创作的美学超越。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确认非总体思维的合法性,从理论上说,的确不失为一种逃离总体化或公式化陷阱的美学策略;从实践来说,它也确实已经(并且必然还将)对当代建筑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但是,非总体性思维或者说差异性思维往往会把建筑师引向另一个极端:畸形的个性或噱头式个性。如果说建筑是一门艺术,那么,它是一门极其昂贵的、实用的、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艺术,并且是一门比较脆弱的艺术。极端的、病态的差异性不仅不会给建筑带来个性,不仅不会给建筑创造美和实用性,而且往往会葬送建筑本身。
二、混沌—非线型思维
非此即彼的线型逻辑虽然已经随着现代主义美学的隐没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建筑师的抵制,但是,那种执著于简单明了的确定性和秩序性的思维定式,依然严重地干扰着建筑师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才能的发挥。建筑意象被引向单一性和简单化的文化情境之中。当混沌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时候,西方学术界包括建筑界普遍感到他们固有的思维范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牛顿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受到沉重打击。因为混沌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使人们相信,机械论的思维范式已经终结,宇宙比牛顿、达尔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想象的更富有创造性、更自由、更开放和更具有自组织性。建筑师们普遍意识到,当代科学的发展必将带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传统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和封闭的审美意识只能成为艺术创造之“蔽”。去“蔽”才能存真,去“蔽”才能求新。而去“蔽”,首先就要向固有的思维方式挑战,向现存的建筑观念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混沌学就成了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寻求设计突破和理论突破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在这里我必须对混沌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混沌,即英文chaos,是一种研究复杂的非线型(nonlinearity)力学规律的理论。詹姆斯·格莱克说:“混沌是这样一种思想,它使所有这些科学家们信服大家都是同一个合资企业的成员。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或数学家,他们相信简单的决定论的系统可以滋生复杂性;相信对传统数学来说过于复杂的系统仍然可以遵从简单规律;还有,不论他们的特殊领域如何,相信大家的任务都是去理解复杂性本身。”(注:詹姆斯·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321页。)混沌使人们注意到,简单可以包孕复杂性,复杂也可以遵从简单的规律;在一般人看来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两种(或几种)东西,却往往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或依存关系。混沌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伦兹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的题目“可预言性: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所揭示的蝴蝶效应就是对这种非线型现象(或称为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的最佳注脚。
混沌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人们从机械的宇宙论转变到有机主义新视野。机械论使人们相信,宇宙是静止的、独立的、有着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受决定论支配;时间和空间是线型的、同质的、独立的、局部的;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而有机主义使人们相信,宇宙是变化的、进化的、普遍联系的;时空是不可分的,是非线型的、异质的、相互关联的、非局部的,不受决定论支配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两种世界观,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前者以一种僵化的线型思维为特征,把我们的世界描述成一个稳定、规则、有秩序的并且受决定论控制的世界;后者则以一种非线型思维为特征,把我们的世界描绘成一个变化的、不规则的、混沌的、不受决定论控制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混沌理论建构了一种正反合的思维方式:认为我们世界是以一种混沌和有序的深度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为非线型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是混沌(无序)和秩序的深层结合,是随机性和确定性的结合,是不可预测性和可预测性的结合,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深层结合。非线型系统之所以有自组织性、自协调性、自发性和自相似性,正在于它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和辩证律。混沌学研究者法默说:混沌,“从哲学水平上说,使我吃惊之处在于这是定义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是可以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调和起来的一种形式。系统是决定论的,但是,你说不出来它下一步要干什么。同时,我总觉得在世界上,在生命和理智中出现的种种重要的问题必然与组织的形成有关……”又说,“这里是一枚有正反面的硬币,一面是有序,其中冒出随机性来,仅仅一步之差,另一面是随机,其中又隐含着有序。”(注:参见詹姆斯·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64页。)混沌学正是这样,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人们的思维进入到一个多维的、多元的、可预见性、可调节的、富有弹性的开放宇宙。
有趣的是,首先并不是建筑想要借助于混沌理论,相反,是混沌理论先来找建筑的茬。詹姆斯·格莱克指出:
对于尺度现象的了解必须来自人类视野的同一种扩展,这种扩展曾经消灭了早期关于自相似性的天真想法。到了20世纪后期,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形象以过去不能设想的方式进入每一个人的经验。人们看到了星系和原子的照片。人们无须再像莱布尼茨那样去想象微观和巨观尺度上的宇宙是什么样子,显微镜和望远镜已经把这些形象变成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只要思想上有从经验中寻求类比的渴望,对大小世界的新的比较就是必然的,而且有些比较是卓有成效的。
热衷于分形几何学的科学家们常常注意到,在他们的新的数学审美观与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文化变化之间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并存性。他们觉得自己正从整个文化中吸取某种内在的热情。对于曼德勃罗来说,欧几里德感受性在数学之外的集中体现就是包豪斯的建筑风格。它也可以同样地由艾伯斯的彩色方块绘画表现出来——宽舒整齐、线条简练、几何化。几何化——这个词代表着它几千年来原有的意义。所谓几何化的建筑是由那些用很少几个数就可以描述的简单形状即直线和圆构成的。几何化建筑和绘画的风尚来了又去了。建筑师们不再设计纽约岛上一度被人们不断叫好和模仿的方块摩天楼。(注:参见詹姆斯·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混沌学理论家,比如曼德勃罗和他的追随者们,从自己的专业的角度对建筑中流行的线型性几何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建筑创作的关键在于,建筑师是否以大自然组织自身的方式或人类认识自身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来认识和表现建筑的本质。从事非线型科学研究的德国物理学家爱伦堡曾经这样问道:“为什么一棵被狂风摧弯的秃树在冬天晚空的背景上现出的轮廓给人以美感,而不管建筑师如何努力,任何一座综合大学高楼的相应轮廓则不然?在我看来,答案来自对动力系统的新的看法,即使这样说还有些推测的性质,我们的美感是由有序和无序的和谐配置诱发的,正像云霞、树木、山脉、雪晶或雪花这些天然对象一样。所有这些物体的形状都是凝成物理形式的动力过程,它们的典型之处就是有序与无序的特定组合。”(注:参见詹姆斯·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混沌学家基本上认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秩序感是粗俗的、简单的、乏味的。同时,他们对建筑师固有的尺度感也提出了质疑。他们首先向人为万物的尺度这一传统观念发起攻击。曼德勃罗就认为,令人满意的艺术没有特定尺度,因为它含有一切尺寸的要素。曼德勃罗指出,作为那种方块摩天楼的对立面的巴黎的艺术宫,它的群雕和怪兽,突角和侧柱,布满旋涡花纹的拱壁以及配有檐沟齿饰的飞檐,都没有尺度,因为它具有每一种尺度。观察者从任何距离望去都可以看到某种赏心悦目的细部。当你走进时,它的构造就在变化,展现出新的结构元素。(注:参见詹姆斯·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27页。)
很显然,混沌学家对建筑尤其是当代建筑的不留情面的问难,使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陷入了某种窘迫状态,(注:70年代末,日本建筑师曾对如何认识混沌学感到不知所措,一度予以抵制,但很快就把混沌学方法运用于建筑设计中。参见Contemporary Japanese Architects,Taschen,1994年,第37页。)然而,混沌学所蕴涵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传统思维的颠覆力,在使建筑师因陈旧的思维定式深感汗颜无地的同时,不能不对这种振聋发聩理论心悦诚服,并且迅速开始寻求去“蔽”求新的路径。
最早接受混沌理论并且把非线型设计引入建筑设计的,是几位活跃的日本建筑师。
出版过《混沌与机器》(1988)的筱原一男,从80年代起,就一直把“进步的混乱”(progressive anarchy)和“零度机器”(zero-degree machine)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所谓“进步的混乱”,实际上是指一种合乎时代发展的、以非线型设计为中心的美学理念,这种理念摒弃肤浅的秩序与和谐,追求高科技的“笨拙”和美丽的“混乱”;“零度机器”则表明筱原一男不是重复现代主义的机器美学,而恰恰是对这种美学的解构和颠覆,以取消意义的方式使之在建筑中获得新的意义。筱原一男说:“这种无意义的机器可能会在建筑中承载新的意义”。(注:Botond Bognar:Japanese Architecture,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Inc.1990年,第31页。)筱原一男喜欢在建筑中运用当代高科技飞行器的意象,然而,这种意象往往是片段的、似是而非的。筱原一男总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机的甚至仿佛是即兴的方式把这种意象同一些异质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在一种令人意外的意象组合中传达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所蕴涵的特有的意义。筱原一男像一位从不采用写作大纲的小说家,直到故事写完,自己才知道结局原来如此,于是,自己就和读者或观众一道,为这个意外的、偶然的结局唏嘘、感叹或惊奇。
一向被人视为保守派的桢文彦对混沌学也情有独钟。他的螺旋大厦(Spiral Building,1985)不仅采用了分形维度,更采用了多种异质元素的拼贴和混合。桢文彦解释说:“我的螺旋大厦隐喻城市意象:一种主动将自身献出,供人切成碎片的环境,然而,正是从这种肢解中,它获得了生命。”(注:Contemporary Japanese Architects,Taschen,1994年,第38页。)桢文彦显然想以建筑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构拟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像许多混沌学追随者一样,桢文彦虽然似乎把建筑师的业务拓展到哲学家或文学家的范围,然而这丝毫没有损害建筑本身的形式意义和功能意义。因为在这里,混乱与秩序并存,片段性与整体性同在,在一种雅化的秩序原则(a refined principle of order)的统帅下,混沌赋予建筑一种深奥的美,一种有张力的美,甚至还有一种隐嘲的美(以混沌反对混沌一度成为日本建筑界的一种时髦)。这也正是原广司、高松伸等建筑师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使混沌思维贯穿于自己的设计中的一大原因。
虽然欧洲建筑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观察到日本建筑中的第二因素的过剩,即由广告牌、招贴、陈列、霓虹灯构成的混声合唱和异质的立体装配中,感受到某种富有审美意义的混沌特性,并对混沌学产生兴趣的,但是,他们对混沌的理解,最终还是回到了非线型的轨道上。
亚历山大·托尼斯,里亚纳·勒芬赫和理查德·戴曼德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混沌似乎一再成为建筑辩论的中心。仿佛我们又回到了60年代初我们的起点,回到了建筑被宣称进入了一种混沌状况的时期”(注:Alexander Tzons,Liane Lefaivre,Richard Diamond:Architecture in North American Since 1960,Thames &Hudson LTD.,London,1995年。)。
在西方,对混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把自己的那套非线型思维方式推而广之的,仍然是普瑞克斯(Wolf Prix)、屈米、埃森曼这样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建筑师。
“开放建筑”的倡导者普瑞克斯说:
建筑的平安无恙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永远不再存在。“开放建筑”(open architecture)意味着自觉和开放的精神。事实上,从20世纪初到90年代的建筑历史可以解释为一条从封闭空间通往开放空间的道路。从愿望上说,我们愿意建立一种没有目标的结构以便让它们可以被自由运用。结果,在我们的建筑中,没有围合空间,它们是组合的和开放的。复杂性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寻找一条足以反映世界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性……(注:Wolf Prix.On the Edge.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Maggie Toy(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
作为著名的设计事务所蓝天组的代言人,普瑞克斯把他们的设计理念——“开放建筑”定位于一种“边缘性”意义之上,使之包含了一切不受局限的、可以充分发挥或选择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恰恰又是建立在构拟我们“世界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之上。其实,这种充分尊重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并依据客观现实重构和模拟这种展示非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空间的精神,也正体现了混沌理论的精神。普瑞克斯是否真正接触过混沌理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理论在客观上真正体现了混沌学某些精髓性的东西。
屈米与普瑞克斯不同,他是混沌理论的热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许多场合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形式和功能之间,结构和经济之间,形式和程序(program)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线型的因果联系,重要是要用“一致与叠加、置换与替代的新概念”,还有混沌的思想,来取代它们。(注: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Maggie Toy(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第21页。)他认为,在建筑设计中,任何追求和谐、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动机都是于事无补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当代建筑师需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穿插与对抗,是各种建筑构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混合。他明确指出:
如果……“所有类型互相混合,经常替代,各种体裁互相混淆”是我们时代的新方向,那么,这倒可能……对建筑的普遍的更新大为有利。如果建筑既是概念的,又是经验的,既是空间的,又是使用的,既是结构的,又是表层意象的(非等级的),那么,建筑就不再分出这样一些类别,而是将这些类别合并为前所未有的方案(program)和空间的混合体。“交叉方案”(cross-program-ming)、“跨方案”(transprogramming)、“非方案”(disprogramming),这些概念代表项目之间的移位和相互混合。
……
建筑的定义不可能是形式,或墙体,而只能是各种异质的和不协调因素的结合。(注:Bernard Tschumi.Event Architecture,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Maggie Toy(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
屈米讨厌一切稳定的、确定的、静态的和无变化、无眼光的设计。他宣称,冲突胜过合成,片段胜过统一,疯狂的游戏胜过谨慎的安排。屈米不仅以一套非线型思路来规约单体建筑(如他的成名作巴黎拉维莱特公园,1982~1991),而且还把一种非确定性的混沌思想贯穿于他的城市美学之中。他热切希望设计一种可以对发展新的社会形式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文化的和艺术的“语境”,而摒弃那种只是着眼于过去或现在的、不包括任何预见性的僵死的环境。他对等级明确的传统城市极为不满——它们往往以寺庙、教堂、宫殿等为中心;对现代主义的城市同样怀有深深的敌意,因为现代主义也通过严格的分区,把城市空间分成工作空间,生活空间,服务场所等。屈米希望他的城市在形式上是反简洁的、无等级的,在价值上是非传统的。他不希望以一种决定论来限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当代城市应该给人提供无限的自由和可能性。这与他在《事件建筑》中所张扬的那种建筑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屈米的思想中心,说到底,就是要建构一种混沌建筑,一种以非线型形式构造、以混沌思想定义的建筑。
对埃森曼来说,混沌的思想和解构观念已经融合为一体。我们很难断定,到底是因为混沌的思想还是因为解构哲学,导致了埃森曼对建筑意义的解构。比如埃森曼对住宅的居住性的解构和对展览中心的展览性的解构,作为对人类思维惯性和确定性的挑战,既合乎解构哲学的目的性,同时也合乎混沌学的目的性。但是,当埃森曼在谈及住宅10号时,对传统建筑尺度观的挑战,却毫无疑问来源于混沌思维。埃森曼说:“五个世纪以来,人体尺度一直是建筑的基准,但是,由于现代技术、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发展,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作为始源的存在这种最高抽象概念,可能再也保持不住了……”(注: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Maggie Toy(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第20页。)“虽然弗罗伊德对无意识的揭示早已使这种天真的人类中心说的观点失去了合理性,但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今天的建筑中依然存在。关于存在和起源的争论对人类中心说的问题至关重要。为了在建筑中实现对人的这种环境的某种反应,这个计划提出一种力图避开人类中心说关于存在和起源的组织原则的话语。”(注: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时间种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173~174页。)埃森曼后来设计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这种观念,如东京大剧院(Tokyo Opera House,1986),加州长岛大学生艺术博物馆(University Art Museum,1988),夸迪奥拉住宅(Guardiola House,1989)等。尤其是坎纳乔城市广场(Cannaregio Town Square)和夸迪奥拉住宅。前者通过三种按比例递减(或递增)尺度的对比,既解构了人为万物的尺度的传统预设,同时也强调了埃森曼一贯强调的建筑的自主性和建筑尺度的自我相关性;后者则是埃森曼对“作为始源存在”的人的最极端的拒绝,这个立方体结构,三面为实墙,一面有窗,可以被视为“容器和被装载”,或者多少可以被定义为存在于“自然与理性之间,逻辑与混沌之间”的“场所与非场所”。
勃罗特彭特认为,埃森曼有三种排列(scaling)方法:一是“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既有过去,可以在羊皮纸上阅读的过去,当然有现在,而且还有一种未来的潜势);二是“梯归”(recursivity)(采用一种双极对立,如功能/形式,结构/经济,内/外,用多极意义进行叠加);三是“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相似性重复)。(注:Andreas Papadakis,Geoffrey Broadbent&Maggie Toy (Editor):Free Spirit in Architec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年,第20页。)勃罗特彭特所说的这三种方法,无一不与当代混沌学思维相关。如第一种方法揭示了混沌理论所包含的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之间的矛盾性;第二种方法反映了混沌理论中所包含的系统的相关性;第三种方法不用说,更明显地表现出非线型思维的主要特征。詹姆逊早已注意到埃森曼的排列方法的渊源,他指出,“我认为埃森曼的特殊的、新的历史性,应该理解为对这种直接的形式问题的一种反应:以这种方式看,它不是一种风格的选择或装饰,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紧接着出现的行动。他首先把这称作‘排列’(scaling),这个词可能源于曼德尔布洛特(即曼德勃罗——引者)和无序理论(即混沌理论——引者)。按照这种理论,无限扩大和缩减肯定重复‘完全相同’的、基本的不规则和反常性,但我觉得,正是作为最富当代性的科学,那种‘促动因素’才可任意选择。事实上,排列会取得某种更基本的、更具形式的东西:就是说,从格式塔中去掉多重解读的楔子,将共时性力量的行列(格子)投射到大量历时性的轴线之上”。(注: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时间的种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詹克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三座建筑,即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埃森曼的阿诺诺夫艺术中心,李伯斯金柏林博物馆,均为非线型建筑。(注:AD,10/9/97.)因为这些建筑不仅仅采用了电脑辅助设计,更主要是采用了混沌思维方法,那种非逻辑的逻辑序列,非秩序的混沌的秩序,既表现了对建筑自主性的充分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建筑与历史的、现实的对应关系。
不过,最能反映混沌思维的成功范例,应该是艾西顿·雷加特·麦克杜加尔(Ashton Raggatt Mcdougall)的墨尔本(Melbourne)的多层大厦(Story Hall)。这个工程以分形学为基础,以两种花砖作为象素手段,通过一种视觉拟态,在自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绝妙的融合。在这里,既规则又混乱的分形,组成一个自支撑、自生成的视觉拟态场所,成为新古典主义建筑之间的一个既怪异又新颖、既简单又复杂的和谐空间。在这里,我们无法用普遍的逻辑推理和线型思维解读设计者的意图。因为这里不存在任何点、线、面的关系,只有一种由不规则的曲线、不规则体块和色块组成的大杂烩。正是这个大杂烩,正是这个无设计的设计,在自我呈示的同时也赋予周围的环境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要寻找一种混沌学或非线型的最佳图解,这个设计也许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混沌思维为当代建筑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也赋予建筑师一种更加自由的创造精神。在秩序与混乱、静止与运动、确定与变化这样一些对立项之间,建筑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选择,甚至双极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线型思维方式在这里已经没有立锥之地;建筑师的设计将不再囿于任何固定的框框,而是以自然生物(厥叶的茎线分布)、生命构成(如DNA结构图)和自然现象(如山、闪电的形式)等为灵感触媒,创造出更灵活、更富有有机性和更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生存空间。
混沌思维从根本上动摇了机械主义宇宙观和人类中心说,因此,它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混沌思维揭示了建筑乃至整个艺术创作的新规律,也大大拓宽了建筑和艺术创作的疆域,因此,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价值;混沌思维把系统之间和系统之外的一切元素视为相互依存的关系项,认为生命与生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都具有某种相关性和依赖性,因此,它体现了一种生态智慧。
黑川纪章说:“借助于海森堡的量子力学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分形几何学正暗示着某种新秩序的可能性。在自然现象中显然存在着分形秩序,由于其复杂性以前被拒绝接受。位于秩序和混沌之间的中间领域的分形几何学是生命本身的原则。生命时代的建筑将在分形几何学的基础上发展。”(注:转引自郑时龄、薛密编译.黑川纪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黑川纪章的观点,代表了老一代建筑师对混沌非线型思维的无比重视,对未来的富有生命意义的建筑的期许。
混沌思维给当代建筑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的确给当代建筑面貌带来了新的变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混沌思维(有机论)作为机械论模式的对立面,受到当代建筑师的重视,但是,如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机械论模式在建筑中仍然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种认为思维是一种单一反应的过程而非复杂作用的过程的观点,那种认为思维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思维简单地取代另一种思维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本身也是与混沌思维相违背的。
混沌非线型思维对拓宽建筑师的创作观念,开阔建筑师的创作视野,乃至于对城市规划和建筑意象创造、空间安排等,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那种不顾建筑的环境、经济和技术的限制,想当然地生搬硬套混沌—非线型理论的建筑设计,那种为“混沌而混沌”的建筑设计,是应该受到坚决抵制的。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这样的设计担心。因为这种设计是不可能找到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未完待续)
标签:建筑论文; 美学论文; 当代建筑论文; 建筑美学论文; 混沌现象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阿多诺论文; 混沌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