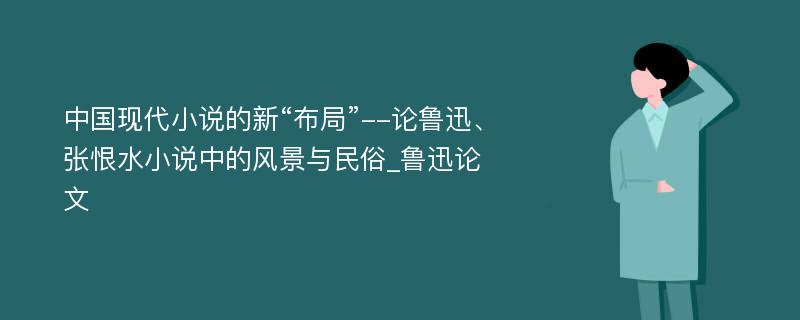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版图”——从鲁迅、张恨水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与民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鲁迅论文,现代小说论文,版图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6-0038-08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6.006 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指出,中国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风景描画,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旧的文人多是不出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1](P540)胡适很自然地把风景叙事和小说的叙述模式联系起来,这为现代小说的结构艺术建立了新的范式。事实上,人们所认识的自然和所看到的自然,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而是被人们“加工”了的人化的自然。换言之,传统风景和现代风景的区别不在于对自然风景的观察,而是观察风景背后的特殊感受。观察现代风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观察风景本身,而是寻找更高一层的意义,风景只不过是这意义中的图景而已。因此,现代小说中提出的“作为风景之风景”问题,是在人们对风景的认识中,通过文学的想象所看到的风景,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对象的风景自身的问题。有画意的风景才会有韵味,才会有研究价值。这样的“画面结构”是鲁迅和张恨水小说都常用的一种结构方式。所谓小说的“画面结构”指“以景物、场面为主体的画面式情节单元的组合”[2](P75)。 如果说,鲁迅和张恨水对外国小说的题材和形式有所借鉴的话,那么二人对外国小说创作艺术手法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二人以对生活中的具体场景的描写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全貌,从而弥补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不足。在鲁迅小说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较突出的作品有《风波》《示众》《头发的故事》等。这里的场景虽然是生活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场景,但是深刻地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画面。与鲁迅的作品相比,张恨水对生活场景的描写更立体化、全面化。如《小西天》《燕归来》《北雁南飞》《满江红》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生活风格。其次,二人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二人大胆吸收了外国文学中的第三人称心理活动的手法,丰富了塑造人物的表现方法。这种结构特色,从不同方面显示了鲁迅和张恨水小说的非凡魅力,因此有必要分析其小说的深刻思想和艺术效果。 五四现代作家对个体的审美观和主体意识的重视,凸显了现代风景叙事的主要特征。与传统小说中的由说话人所描述的风景叙事,平面式的故事情节所不同的是,个人的经验和实地的观察使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开创了一个具有深层结构的风景叙事模式。也就是说,传统自然观中的那种“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超越和隐喻式的田园山水概念,在现代人眼里以客体存在的方式而成为现实人生的组成部分。“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3](P100)如诗如画的风景描写,在展示着作者文字功底的同时,也影响着作品的审美和意境。虽然表面看来其在作品中占的容量不大,但是在文中起到的实际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景物描写在揭示社会背景、烘托人物心情、渲染场面气氛、展现人物的活动空间以及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泛读鲁迅的小说,我们很少能找出大段的自然景物描写。他常常用简单的描述,创造出人物活动的客观场景。正如美国小说理论家利昂·塞米利安所说:“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它是通过人物活动而展现出来的一个事件,是生动而直接的一段情节或一个场面。场景是小说中富有戏剧性的成分,是一个不间断的正在进行的行动。”[4](P6)鲁迅向来不为描写景物而描写景物,也不为歌颂风花雪月多用笔墨,而是以最简洁的笔法奠定作品的感情基调,并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有力地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 有趣的是,在鲁迅的小说中,风景叙写从叙事者本身的多种感触中表现出来,叙事者不仅用视觉,而且通过听觉或嗅觉等各方面来把握风景。作为诗人的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展出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诗意画面。如《药》的开头和结尾中写出了鲁迅对生命的独特感悟,构成了一幅“安特莱夫的阴冷”的画面: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5](P463,471,472) 这就是叙事者以敏锐的视觉和听觉来描述对黎明前黑暗的某种悲哀、恐惧、绝望的复杂心理,同时也达到揭示当时时代背景的目的。在《故乡》中,对严冬雪寒的故乡风景的叙写,凸现了叙事者所看见的天气的“隐晦与苍黄”,这隐喻着鲁迅对精神故乡的失落和生命轮回的幻灭感。《在酒楼上》的“我”从这座酒楼的窗外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种画面令他感到“惊异”: 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6](P25) 在小说整体令人感到阴冷、压抑、悲凉的气氛下,突然出现这样的“亮”景,带着强烈的震撼力。这让读者看到世俗的吕纬甫在“几乎无事”的平常人生的悲剧里寻找心灵的归宿,而“我”的漂泊是对世俗的一种颠覆。这幅画卷也蕴含着作者面对生命无奈的伤痛,对世俗无法抗拒的悲哀,从中看穿了“我”愈来愈难以脱离这宿命式的轨道。这正是代表着鲁迅式的往返质疑。虽然“景”有限,但“意”无穷。《铸剑》是在“三·一八”惨案的背景下写的一篇表现复仇主题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一副“骇人”的景象: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7](P435) 鲁迅在这个铸就复仇宝剑的奇异想象中,营造出梦幻、诡异的气氛,表现出对生命意识升华的歌颂。鲁迅从感情上对“复仇”无疑是十分倾心的。在20年代与北洋军阀的对峙中,他写了一系列作品,如《这样的战士》《无常》和《铸剑》等都渗透了作者对复仇的复杂态度。上述的几幅图画虽然表现的内容和主题各不相同,但是包含着一些共同特征:运用阴冷、恐怖的意象和景象,通过鲜明色彩的对比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风格独特而寓意深刻的生动画面,这些超现实的场景更加凸显出鲁迅的矛盾复杂的内心,而这又无法以传统的简单的现实主义笔法表现出来。鲁迅所关注的是蕴含自然景物的社会,而带有社会蕴含的自然景物又映射到人物心理上。他用暗灰色的景物描写来透视整个社会的枯寂,这与人物的暗淡心理相协调,从而将物景、心境、世景三者达到有机的统一。《呐喊》的宗旨是先写出某种现实社会的灰暗,这给人物活动场景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氛围,从而激发人们要正视社会,与其“呐喊”主题相一致。《彷徨》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则更多的是以自然景物冷色来衬托人物迷惘的心境,反映出人物在彷徨之后无家可归的悲剧人生。鲁迅借用景物描写,一方面达到了对中国现代社会批判的目的,另一方面丰富了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深度。当然,在鲁迅作品中除了带有现代色彩的画面之外还有些具有传统色彩的画卷。如《故乡》里对于少年闰土的刻画,富有乡土气息的连环画色彩: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8](P502) 这里没有了以往的黑暗、沉闷和恐怖,而是充满着无限的童趣,像传统诗歌里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丽境界。作者的多种感觉参与风景叙写,在小说文本中起到了两种作用。首先,显示出鲁迅的个性特征,鲁迅在词汇色彩的选择上多用克制性的冷色调,以辞约义丰而取胜。他对白描技法有这样精彩的概括:“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小说的自然景物描写正是这种白描技法的典范。他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乡镇的自然景观,不刻意粉饰“太平”,不刻意描绘风花雪月,不故意卖弄描绘技巧。这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乃至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深化都有强烈的影响,也给我们留下了更自然、朴实、真切的生活画面。其次,突出了叙事者在文本中的作用。叙事者通过自己的感官把风景推到了小说叙述的前台,也把自己置于叙述的“漩涡”之中。这不仅拉开了小说与艺术的审美距离,也意味着叙事者用观感风景的方式观感自己。这种距离通常是以自我分裂和疏离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在《故乡》中,叙事者通过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之间的隔阂来完成对故乡和老年闰土的疏离,从而反思知识者的虚妄;在《祝福》中,叙事者通过庸众的同谋者——自我的隔膜来完成对知识分子的质疑。这里,叙事者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却疏离了自我,形成了风景叙写结构上的隐喻关系。叶世祥也评论道:“《故乡》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即它不像古典小说中的第一人称‘说书人’那样置身于自己叙述的故事之外,而是在自己叙述的故事之内担当角色,结尾处有关‘路’的议论非但不给人从外部强硬塞入的感觉,反而对塑造或理解那个徘徊于十字路口的辛苦辗转的归乡者形象大有裨益。”[9](P114)词汇的色彩和叙事者的主观色彩具有审美意义的晦涩和含混,这恰恰符合五四时代的浪漫特征,使鲁迅成为现代抒情小说的先驱。这种特征,可以从其散文诗集《野草》中找到更合适的根据。鲁迅小说的这些不同风格的画面无论是采取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描绘的都是鲁迅最真实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真挚的思想,作者只能被称为“画匠”而不是“诗人与画家的结合”。这也是鲁迅作品“诗意”画卷的真正美丽所在。 而张恨水对传统章回小说的创造性改造中对于风景描写也有自己独特的处理。 传统章回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常常被视为“多余”的。因为传统小说以“讲故事”为中心,注重故事的情节。而大段的景物描写被认为阻碍故事的进展,打断读者的好奇。这种观念使传统章回小说仍然保留着“说书人的腔调”,难免脱离程式化的故事模式。古代长篇小说的成书过程往往是集体编写,写景则更多代表了集体。《三国演义》经历了由历史到民间传说,经过众人之手最后再借一个人的名字创作出历史演义的过程,《水浒传》和《西游记》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由于集体的创作,就容易流于空洞,也显出简略。“在写景方面,旧小说往往不太注意,其实这和故事发展是很有关的。其次关于写人物的外在动作和内在思想过程方面,旧小说也写得太差,有的是粗枝大叶地写寥寥几笔点缀一下就完了,尤其是思想过程写得更少。”[10](P49~59)即使在《红楼梦》中,真正景物描写也比较少。近代刘鹗的《老残游记》作为一部重视景物描写的作品,但是自身并没有多少独立的审美意义。总体来说,在新文学之前,风景描写及场景描写在中国小说中还是缺乏独立价值。随着文人的文化程度逐渐提高,作者开始赋予小说人物更多自己的情感,对外界景物的观察更为敏感。文人写作带给景物描写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韵文的减少,更主要是情与景的结合,意境的产生。章回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较多的受到“说书”这种民间形式的影响,因而早期章回小说景物描写较少,且多以诗词赋的形式呈现。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题材的世俗化以及文人参与程度加深,写景渐渐增多。在传统章回小说中插入景物描写并非从张恨水那里开始,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景物描写的重视和自觉发挥以及运用的方式远远超越了前人。并且,张恨水小说的情节设计与艺术结构非常精妙,他除了选取能揭示社会问题的典型环境和复杂性格的人物之外,还充分利用民俗传承来的结构故事,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充满独创性的故事情节,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这种智慧来自于外国小说、翻译文学带来的一些新的技法和五四新文学的启发。张恨水曾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以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11](P133)。 张恨水小说的景物描写,也非单纯意义上的风景,作者注意的是浓郁的情感氛围。这种艺术构思更加突出他对描写对象的总体感受,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场面以及故事情节等都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基本是同体的。这才使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保持着某种相应的情感形态,仿佛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感情融入到对象之中。在《春明外史》中,为了表达杨杏园和妓女梨云的感情挫折,作者多用自然景物来增加抒情成分。梨云因病过世,心情沉痛的杨杏园送灵柩出城,张恨水通过雪景营造一种凄凉的环境氛围的同时,处处不忘文人本色,描写景物刻意追求“诗化”的效果,借此突出人物的心理变化: 街上电线杆上的电线,呜呜地响,天色黑沉沉的,已经刮起风来。街上行人稀少,空荡荡的,清道夫泼在地上的水,和土冻了起来,又光又滑。杨杏园在车里伸头一望,云黑成一片,天都低下来,一点日色没有,却有一阵乌鸦从头飞过去。 这时,天越发暗得紧了,半空飘飘荡荡,已经下起雪来了。这义地本在永定门外,在一片旷地的中央。灵柩走出外城来,一到旷野,雪更下得大。杨杏园从车里往外一看,早些日子留下的残血,东一片,西一块,兀自未消,加上这一阵大雪,路上又铺成一片白,路边苇塘子里,收拾未尽的败芦被风一吹,又被雪一打,只是发出那种瑟瑟的响声。这大雪里,路上哪有一个人走路?静悄悄的,惟有那班抬灵柩的杠夫,足下踏着积雪之声一阵一阵的可听。[12](P351) 与风景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功能的风俗描写,也同样在作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其中,许多优秀的民俗文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风俗描写也可以说是景物描写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充分体现人物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物的性格,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色彩。我们可以通过鲁迅的小说《风波》《祝福》《故乡》等看到江南农村的风俗民情,可以在《阿Q正传》《孤独者》《明天》《药》《离婚》《社戏》《长明灯》等作品展现的民俗事象中获得崭新的审美感受。从乡村社会的习俗管制(如乡村议事、制裁、调节等),到人生仪礼的民族形式(如吊丧、殡仪和送葬等);从婚姻的民俗形式(如买卖婚、离婚等),到岁时节日的民族形式(如农事节日、祭祀节日和庆贺节日等);从迷信的民俗形态(如祭祀类迷信、禁忌类习俗等),到游艺的民俗活动(如社戏、押牌宝等),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民俗,非常丰富多彩。所以,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浙东风俗民俗画。[13]鲁迅小说所吸取的故乡绍兴的民间文化精神,主要包括以绍兴为原型的城市S城、以他的外婆家为代表的平桥村和情景化的“鲁镇”环境,还有绍兴的茶馆和酒店的文化特性。《呐喊》《彷徨》的25篇小说中有11篇以绍兴为创作背景。小说中的许多环境不是直接按实际存在的对象来描述,而是通过鲁迅的想象,将这些典型环境在细节上加以净化,突出人物的故事和其不同命运,赋予了震撼心灵的艺术感染力: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14](P457) 这段文字表现了鲁迅故乡绍兴文化特有的温馨,通过特有的意象和氛围再现了穿长衫的人可以休闲享受地域饮食的某种幸福感。可以说,这种典型细节的描述进一步提高了整篇小说的生活景象。《祝福》《风波》《明天》《社戏》均以“鲁镇”为典型环境,这里,鲁迅有意使“鲁镇”的绍兴民间文化添加了新的意义与社会功能。“鲁镇”这个意象明显打破了古老文化原初的平静,强化了不同人物的人生蕴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鲁迅在《祝福》中具体描述“抢亲”的阴郁气氛,这显示了绍兴“抢寡妇成风”的恶习: 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15](P12) 这种使人感到压抑、郁闷的文化环境,令人恐惧而绝望的民俗图景往往阻止了个人性格的正常发展,本来应当争取自我幸福权利的个人一旦面对传统文化的强大势力,立刻就以自我贬低的方式逃避现实矛盾,这无疑是旧习俗中的一种病态文化心理。除了婚抢习俗之外,在《孤独者》中可以看到葬礼仪式的描写。失去亲人痛苦中的魏连殳,心里蔑视陈腐的“重孝”表演,但他在内心苦闷的压迫中更显出玩世不恭的态度。鲁迅在民俗事象的背景下突出了人物无能为力的内心矛盾。另外,民间信仰在中国社会中压抑人性而导致的人生痛苦,基本表现在《药》《长明灯》《阿Q正传》等作品里。鲁迅小说中民俗事象的表述的价值和目标在于使得人们正确地发现人的价值。 张恨水也将民俗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民俗文化的描写。由于张恨水先后在北京、南京、安徽、重庆、西安等不同城市生活过,因此其小说的民俗风格,既有北方特色,又有南方特色,体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在《金粉世家》中这样描写春节的活动: 人生的岁月,如流水地一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儿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可是一走上街去,花爆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得忙一忙。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觉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而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停,反觉消闲些啦。这日是农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16](P1) 在张恨水的小说与散文中,经常看到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除夕、春节等节日的描述。这些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是陈陈相因的民族的力量,也全面影响着各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张恨水不仅关注自然景物和风俗描写,也非常关注人物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作者所涉及的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比如说服装、饮食、建筑以及婚丧嫁娶等,这就折射出一幅上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世俗民情的图卷。《现代青年》的周氏父子离开故乡潜山到安庆见地主孔大善人(孔大有)时,作者这样描写城乡人的不同服饰: 到了一个客厅里,只觉得那屋子里陈设像平常在图画里看到的那样富丽,脚下踏着的地皮,也是软绵绵的,低头看时,才知道地上也铺了厚被单子一样的东西。转过了客厅,旁边有一间房,一张横桌子边,有一张圆桌,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位四十上下的先生,他口里衔了一根比指头还粗的黄色香烟,微昂着头,看了人进来。他穿了一件蓝绸长衫,由里面向外卷着袖口,露出里面小衣的袖子。他胖胖的一张圆脸,两腮上的肉,向鼻子边直接拥上来,浓眉倒配着小眼睛;笑起来,鼻子边两道沟纹,眼睛合成一条缝,倒真个有些像庙门口那大肚罗汉。[17](P45) 从作者对农民周世良和地主孔大有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人物的生活环境制约着个体的思维方式。同时,作者用心描述南北方人的不同饮食习惯,也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春明外史》的杨杏园和何剑尘请了一个日本客人板井吃北京烤鸭,作者较细致地描写了北京人的吃法: 三人一同出来,坐了门口停的汽车,一路到华乐园看戏之后,就到鲜鱼口一家烤鸭店去吃晚饭,走上楼,便在一间雅座里坐了。板井笑道:“到北京来了这么久,样样都试过了,只有这烤鸭子店,还没有到过,今天还是初次呢。”杨杏园道:“一个吃羊肉,一个吃烤鸭,这是非常的吃法。外国人到敝国来,那是值得研究的。”不一会儿工夫,只见那伙计提着一块雪白的东西前来。及至他进屋,方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钳了毛的死鸭,最奇怪的,鸭子身上的毛虽没有了,那一层皮,却丝毫没有损伤,光滑如油。板井看着,倒是有些趣味。那伙计手上有一只钩,钩着鸭嘴,他便提得高高的给三人看。板井笑着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何剑尘笑道:“这是一个规矩,吃烤鸭子,主顾是有审查权利的。其实主顾倒不一定要审查,不过他们有这样一个例子,必经客人看了答应以后才去做出来。犹如贵公司打合同,必经两方签字一道手续一般。”接上,另外一个伙计,用一只木托盘,托着一只完全的烤鸭,放在屋外的桌子上。板井在屋子里向外望,见那鸭子,兀自热气腾腾的。随后又来了一个伙计,同先前送鸭子的那个人,各自拿着一把刀,将那鸭子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放在碟子里,放满了一碟子,然后才送进来。板井这才明白原来是当面割下,表示整个儿的鸭子,都已送来了之意。[18] 张恨水对居住环境的描写也非常细致,他的小说甚至成为民国时期的民居资料。他在《金粉世家》和《天上人间》中这样描写北京的豪宅: 在这大门口,一片四方的敞地,四柱落地,一字架楼,朱漆大门。门楼下对峙着两个号房。到了这里,又是一个敞大院落,迎面首立一排西式高楼,楼底又有一个门房。进了这重门,两面抄手游廊,绕着一幢楼房。那后面一个大厅,门窗一律是朱漆的,鲜红夺目。大厅上一座平台,平台之后,一座四角飞檐的红楼。这所屋子周围,栽着一半柏树,一半杨柳,红绿相映,十分灿烂。就在这里,杨柳荫中,东西闪出两扇月亮门。进了东边的月亮门,堆山也似的一架葡萄,掩着上面一个白墙绿漆的船厅,船厅外面小走廊,围着大小盆景,环肥燕瘦,深红浅紫,把一所船厅,簇拥作万花丛。[16](P70) 这客厅里的陈设,异常别致,四周墙壁,都是由黄绫子裱糊的。此外,所有沙发椅套,帐帷,也用的是缎子,足下的地毯,按着桌椅的部分,配了有花纹。屋子正中,安放圆桌的地方,地毯上盘着五条龙,簇拥着一个球,这桌子六个脚,恰好都放在这球上。其余的陈设,都是以黄色为主。靠着客厅的东边,开着一个雕花月亮门,门边垂着黄色的纱帐,在纱幔这边,看纱幔那边,也是一个客厅,里面家具,全换了中国的紫檀木仿古雕花式的,也可以见一种那伟大的规模。[19](P63) 张恨水对建筑的描写,除了豪宅之外,也有对具有平民色彩的北京德胜门胡同风景的描写。这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展现了当时生活的千姿百态,令人耳目一新: 走到茶馆前,那茶馆正立在护城河北岸,后面是一带黄土墙的矮屋,大门正对着河,是一所凉棚。这凉棚是四根歪木头柱子撑起来的,上面横七竖八,用木棍、木条、木板搭了一个架子,架子上稀稀的盖了一些破烂的芦席。凉棚底下,不见什么桌椅,小的低的,算是板凳。那茶棚隔壁,土墙弯进去一个小犄角,正是小露天茅厕,墙里一条浅土沟由里向外,直下护城河,还流着臭水,这一种脏象,简直不堪入目,更不要说是鼻子里嗅着那种气味了。 ……又过了两户人家,那四号门牌,倒是一所大门,里面空荡荡的一所大院子,周围列着黄土矮屋。大门口,左边斜靠着一只三尺高的粪桶,右边一辆独轮车子,架着两只腰形柳条篮,原是装粪用的。这时虽没有装粪在内,可是篮子上糊满了粪汁,成千上万的苍蝇,在车前车后飞舞。[19](P111~113) 在张恨水的民俗描写中,除了衣食住行的描写,还有不同阶层的各种娱乐活动,如看戏、听戏、唱戏、逛妓院、上茶馆、吸鸦片、逛公园、结社吟诗、说笑话、猜谜等。在《金粉世家》中特别写出金府纨绔子弟们请戏子来家里唱戏的情节;在《啼笑因缘》中,写了平民的娱乐场“天桥”、先农坛、什刹海和北海等风俗景观。张恨水的诸多作品,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京尘幻影录》《夜深沉》《天上人间》等都描写了当时北京的生活景象。他的作品不像有些描写北京的小说,描绘历史过往中的非现代的古都,而是展现了那个实实在在在当下存在的城市。所以,“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之属,虽不无京味,却也并不具备京味小说的审美特征——这里又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不同旨趣,令人感到京味小说作为风格现象其审美尺度的严肃性。”[20](P20)甚至,张恨水为全面反映急剧变革的时代,描述了一系列封建社会末期的传统婚丧嫁娶之俗。在《金粉世家》中描写贵族之家的各种礼节文化,如客来上茶和相见时的引见、抱拳、握手、道福等;在《现代青年》中描写平民之家的子女周计春和菊芬定亲的过程,这种场景非常符合各阶层人们的风俗习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这是社会生活的典型场景。因此我们不能把民俗简单理解为“日常世界”,也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包括各种劳作的经验,对亲友的情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愿望等[21]。 可以看出,张恨水通过民俗事象增加了生活的乐趣,也启发了他以人的灵魂、现代观念对自我、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观照,深刻思索乡土中国群众的个性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才能获得更全面、自由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看,鲁迅和张恨水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这种所谓“艺术化”了的民俗,实际上渲染了小说的情感氛围,增加了生活的“真实感”,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环境的典型化,进而突出社会主题。《小西天》是以西安一家名为“小西天”的旅馆为背景,描写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城乡的不同特色。旅馆里本来住着各种各样的人群,如妓女、生意人、知识分子、劳动者等,这增加了浓郁的“民间”色彩。小说开头描述潼关到西安的黄土公路上,坐在德国汽车上的几个人对开发西安的希望,这些自然景观的描写折射出了人物的不同个性: 潼西公路,由潼关县的西关外,开始向西发展。在平原上,远远看到一丛黄雾,卷起两三丈高,滚滚向西而去,这便是在路上飞跑的汽车卷起来的路面浮土。路上的尘土,终日的卷着雾飞腾起来,那便是暗暗的告诉我们,由东方来的汽车,一天比一天加多。这些车子,有美国来的,有德国来的,也有法国或其他国来的。车子上所载的人,虽然百分之九十九是同胞,但都是载进口的货。国货差不多和人成了反比例,是百分之一二。那些货大概是日本来的,英国来的,或者美国、俄国来的。总而言之,十分之八九,是外国来的。这种趋势,和潼西公路展长了那段西兰公路,将来还要展长一段兰迪公路一样,是有加无已的。[22](P1) 上述的描写,进一步揭示陕西的开发,来自外国资本或买办资本对民族经济的压迫。这样的背景,增强了整个作品所描写的社会风情。这是一幅让人既爱又恨的悲苦图画,作者有意让读者看到民族衰败的耻辱。可以说,这种论述显示着张恨水自身的生活感受。 对于民俗事象的描写,使张恨水的现代“长篇章回体”小说内容广泛、情趣典雅、意蕴深长。特别是以景物营造某种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理的表现是西方现代小说惯用的艺术技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所欠缺的部分。张恨水改良的章回体小说,广泛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着力刻画了中国某些地域独有的民俗生活,显示出当时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张恨水在小说中对民间风俗的描写,也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民俗文化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无疑扩展了小说艺术领域的表现手法。 由此可见,与早期小说对背景式的自然风景的叙写和风俗描写相比,鲁迅、张恨水对小说文本中场景式的自然风景的开掘,一方面改掉早期片断式叙写的局限,表现出创作技法的成熟;一方面增强了景物、风俗叙写自身的叙事功能,而且这种叙写使得叙事者的观察和景物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审美距离,产生了景物叙写的写实感、生动感。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再现的艺术,它侧重于作家对外在现实的客观描写,作家往往以叙事者的角度来叙述他人的生活,依据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去叙写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二人一直认为“民”在演绎着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动态不拘的世界,是一个需要平等对话的世界,也是一个需要感受的充满地域性的世界。于是二人现代小说中的叙写,可以说是在对传统的浪漫式的反叛中完成的。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上的混杂性质,决定了中国“不会再有纯粹的原来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也不会再有纯粹的原来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23](P10)当然,这反而有利于对作家创作中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至于风景、民俗叙写,鲁迅和张恨水共同关注着叙事者本身的内心感受、主观体验,他们在对孤独、烦闷、凄凉等自我内向性的关注以及对人们精神状态的审视中,关照外在世界,即发现自然风景与内在世界的互相映照。二人的小说将景物叙写成功地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版图”,为后来的风景、风俗叙写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总而言之,由于二人的思想感情、文化修养以及对待传统与西方、借鉴和反叛的态度不同,或者倾向“西化”,或者“存留旧小说上的一些基调与笔法”。鲁迅和张恨水分别作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大家,其作品中对风景和民俗等的书写体现了严肃文学和俗文学在小说创作中的雅俗取向。雅俗的真正界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雅文学中也有对于民间风俗、人情的大力刻写,比如20年代鲁迅、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的乡土小说,而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对民俗的关注是通俗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却也有大量对于传统士大夫生活场景、审美情趣的抒写。可见雅与俗的分界不在于其作品中的抒写内容,也不能单纯由雅俗来看待鲁迅和张恨水的异质性。雅与俗作为一种风格因素,更多的是共存于二人的小说中,如果说鲁迅更多的是想寻求借助民间风土来建立新文学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张恨水则是由雅入俗,成为新文学想要贴近民间的一个绝佳的范例。标签:鲁迅论文; 张恨水论文; 风景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故乡论文; 金粉世家论文; 风波论文; 祝福论文; 景物描写论文; 鲁迅公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