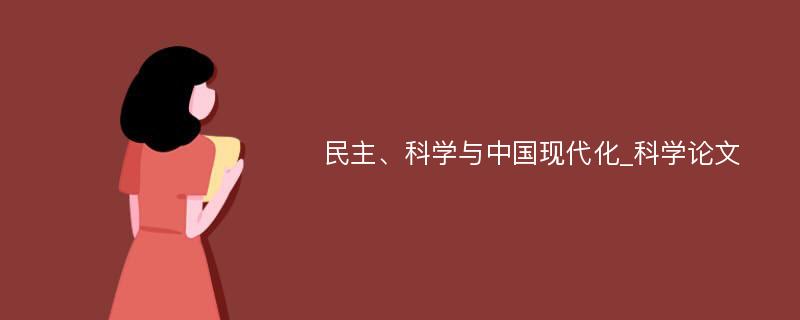
民主、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1999)04—0005—0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精神,揭开了中国文化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新纪元,至今仍是指引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旗帜。
作为“五四”新思潮核心观念的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而是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新观念。儒家经典如《尚书》、《左传》之类书中,也曾有过“民主”字样,(注:例如《尚书·多方》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因而成汤便“代夏作民主”。)但所指乃是民之主,是君主或帝王,与今之民主完全背道而驰。至于科学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则未之前闻。直到19世纪中叶,列强以舰炮轰开古老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方由西方逐渐输入民主与科学的新观念。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都曾介绍宣传过西学的民权与科学;而以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成绩最著。他不仅认为“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注:严复:《法意》按语。)而且提出过“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卓越论断。(注:严复:《原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不仅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和实践的先例。
然而,民主与科学观念,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程度不同地打了折扣。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未脱封建传统文化的藩篱。康梁辈自幼深受封建教育的熏陶,维新运动并未超越洋务派张之洞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路。梁启超便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叙》。)严复亦深信“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也”。(注: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康有为虽然借儒家经典为幌子宣传西学,但开口圣人,闭口孔子,后来则径直尊孔子为教主。而他们对于西学的了解,除严复外,主要依靠当时同文馆、上海制造局及外国教士所译的西书。梁启超说自己“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按:指翻译者),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而康有为也是“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他们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自然难以深切。故梁启超后来总结说:“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烈,固宜然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革命党人的代表孙中山,曾周游欧美三十年,对西方民主科学的了解较维新派深切得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贡献也更大。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气味,如《国粹学报》及神州国光社、南社中人,大多是民族主义的种族革命论者,又都是国粹保存论者。孙中山也说自己“于圣贤六经之旨”,“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并把“泰西治国之规”与中国古代的“唐虞”相提并论,谓其“深得三代之遗风”。(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到他晚年重新讲解三民主义时,更多夸赞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复古保守倾向更有明显表露。(注:参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五、六讲。)
其二是忽视个人自由。严复所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观点,对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表述非常准确而深刻,可惜在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维新派宣扬民权,却并不看重个人的自由。例如梁启超从其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出发,虽然也宣传过自由,却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甚至说如果以个人自由为自由,“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孙中山同样以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讲他的民权,竟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所以成为一片散沙;“由于中国人的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因此自由“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这类的说法甚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观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大都留学欧美或日本,大量甚或直接阅读西方著作,亲身体验西方民主、自由及科学昌明的伟大成就,或目睹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维新的巨大变化,因而对于民主与科学崇信的诚笃,了解的深切,显然继承而又远远超越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
首先,用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价值重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特征。陈独秀指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他批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及后来的一些人,把古代中国的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传统观念看作现代民主精神的论调,指出前者是“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与西方“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持的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态度,从价值体系上作整体性否定,与局部性肯定其优秀成分并给予历史的适当评价,二者辩证统一;因而主张分清“国粹”和“国渣”,(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在大力批判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整理国故”和正确评价旧文化优秀成分的工作。故说“五四”是整体性反传统则可,说其“全盘反传统”则有悖于历史的真相。
其次是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和最重要的现代性品格。陈独秀曾指出宗法制度有四大恶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正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的长期统治与传统文化长期熏染之下,中国人只是为人子,为人臣,驯养出一种服从的、奴隶的子民意识,“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注:鲁迅:《灯下漫笔》。)“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则以现代人的意识取代子民意识,大声疾呼人的解放,为个性的自由发展,为思想言论自由而斗争。他们强调“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注:陈独秀:《人生真义》。)而“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养成个人独立自由的人格;如果“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便“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这些见解正是对严复所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继承与深化,又是对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忽视个人自由的反拨,从而达到了以个人自由为民主政治之根本的现代民主观念的高度。
其三是对于“科学”,维新派基本上还限于“器”与“用”,革命党人多视为各种专门的实用科学或“实业”,而“五四”先驱者则在具体实用科学之上,更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陈独秀曾指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精神文明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他们与李石曾都认为“中国人种种邪说迷信”,“当科学真理扫荡之”(注:陈独秀:《基督教与迷信鬼神》。)。鲁迅也认为,医治中国人思想上“昏乱病”的药,“就是‘科学’一味”。(注:鲁迅:《随感录·三十八》。)他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脑子里没有科学思想,而国粹的医、卜、星、相、扶乩等种种迷信风行,故强调科学的精神、态度与方法。而胡适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治学的各种论著,都是围绕着“方法”打转的:“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强调“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李大钊也说:“所谓科学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二为重据”,“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注: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五四”先驱者所强调的科学精神、态度与方法,实际上关涉到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止于具体实用的科学技术层面。
总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虽然理解上还有某些缺点或不充分,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高张着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具有揭开并指引中国迈向现代化新纪元的深远历史意义。
回顾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艰难曲折而又伟大辉煌的历程,凡是继承并发挥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时候,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胜利;而违背民主与科学精神,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创造性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因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此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违背民主原则的家长式作风和背离科学精神的教条主义路线,都给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民主与科学精神继续有所发展,但非民主与反民主和非科学与反科学的倾向也不断滋长,家长式个人专制发展成个人迷信,阶级斗争扩大化,侵犯个人合法民主权利,浮夸风等等,起初虽然未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未能及时纠正,以至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为全面反民主反科学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人们从反民主反科学的个人迷信和僵化教条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我国现代史上继“五四”和延安整风以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新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正朝着富强、民主、自由、幸福的现代化目标阔步前进。
我们在朝现代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还会有困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方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创造精神,克服困难,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角度看,当前需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民主与集中,既对立又应统一,这中间便容易发生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按理民主应该是基础,是集中的前提,离开了民主这个基础来讲集中,必定是盲目的集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势必酿成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广大群众要发扬民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自然也不应排拒或反对集中;干部和领导往往强调集中,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但如果离开了民主,这样的“上级”往往是胡涂的,错误的,甚至形成个人专制。而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民主监督,正是当前腐败现象普遍严重的症结所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正为各地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例所证实了吗?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加强法制,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也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适度的集中,限制过分的集中。
二是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保证个体的自由。我们提倡集体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绝不应忽视个人的自由选择之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在他看来,“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而“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注: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个人是构成社会的原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和灵魂。一个社会有没有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就看这个社会的个人有没有自由选择之权,有没有自由发展之权。如果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讲个人服从社会,压制个性,企图把一切人放在一个模子里铸造,不让他自由发展,那样铸造出来的只会是思想僵化、没有任何创造活力的庸才甚至奴才;而一群庸才或奴才,是绝对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三要全面理解科学,正确处理人的科学精神与物的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是人类的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德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指的是系统的、有条理的、真实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 自18世纪后期起,“Wissenschaft”这一学术观念引起了德国大学的改革及随后的扩展,法学、历史和哲学学科提供的学科设置模式,很快就被自然科学所采用,随后又为世界各大学所仿效。在中国,陈独秀于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便提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也肯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类;邓小平也于1977年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注: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然而在我国还是存在一种轻视甚至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这大约与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理解片面有关系。针对“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四个现代化的罪恶行径,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和创造精神,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卓越论断,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有些人甚至某些领导人便据此而错误地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生产力,借以贬低社会科学。殊不知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背后必定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离开了人的科学精神、态度和方法,就绝不可能有物的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发明。即使从外国输入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同时,一再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说,物的科学技术固然很重要,舍此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人的科学精神尤其重要,否则,不仅物的科技搞不上去,其他一切工作也做不好。而人的科学精神的培养,非研究和宣传社会科学不可,其中自然也包括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而重视和发展社会科学,重视人的科学精神,实在是发展物的科学技术的根本性条件,是治国建国的根本方略。
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我们应更高地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沿着“五四”先驱者所开辟的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勇猛前行。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梁启超论文; 孙中山论文; 陈独秀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