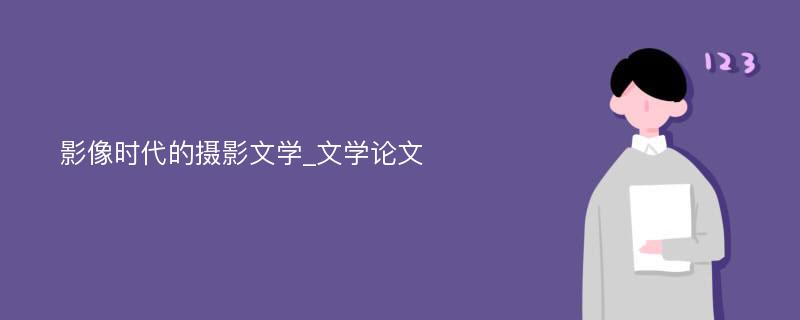
影像时代的摄影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像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过去的时代,文学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人人崇仰珍爱的缪斯女神。巴尔扎克、曹雪芹,人们无不津津乐道,今日的文学已然衰落,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学被抛离了中心,日益边缘化了。
曾经十分尊贵的摄影和摄影艺术也衰落了,今天它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成人手中听凭摆弄的“傻瓜”,甚至世界摄影大奖也授予了一位从未把摄影当做艺术的人。昨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禁不住怀疑,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动态的视像已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你的画面定格,于是你便完成了一幅作品。那么,摄影究竟还能走多远?
两种曾经十分辉煌的艺术形式似乎已度过了它们的颠峰期,正在垂头丧气地走向衰落。
似曾相识燕归来。迷惘中发生了一次“后”时代跨门类跨学科的联姻:衰落的摄影+衰落的文学,于是艺术诞生了一种新亚类:摄影文字。也许这并不能说就是对衰落的文学的拯救,也不能说就是对衰落的摄影的振兴,但它却是创意时代里一次隆重的“推出”,一次辉煌的策划和一次郑重的许诺。
摄影与文学,一次新的“粒子”对撞,它产生新的巨大的能量。这是一次再设计,是1+1大于2的大手笔。两种衰落的艺术形式,因了新的契机而焕发了勃勃的生命力。“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它打破了艺术门类固有的藩篱,融汇两种艺术形式的精粹,它开拓出艺术的又一块疆域,栽种下一片蓬勃的次生林带。
二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发生了文化的“转向”,文化的转向中最为抢眼的景观是视觉影像的“转向”。今日的视觉影像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它已经“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了文化的大片领地。不管是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还是电影《大话西游》,不管是流行歌曲MTV,还是电视报道美国轰炸阿富汗塔里班,不管是城市白领们翻阅的时尚杂志,还是打工仔喜欢的卡通读物,不管是触目皆是的街头广告,还是热浪叠起的居室装修,我们都离不开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图像的时代。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这种发展的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指出: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参见《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
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了,人们更加关注视觉文化事件。在当今西方世界,正是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产生了后现代文化,所以,一些专家断言: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
今天的视觉文化或者可视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它就是一种现实:人们如今就生活在视觉文化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成了区分当下与过去的分水岭。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
然而视觉图像的兴盛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突然间一窝蜂地在屏幕上重演最为古老的图像机制,似乎人们回到了人类童年的岩画或象形文字的时代。不,不是的。视觉图像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当代最重大的世界性文化事件,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这种转向以当代高新技术: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行模拟器、电脑动画、数码摄影摄像、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为平台,在各种艺术电影、电视、绘画、摄影、摄像、广告以及娱乐、游戏、日常生活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新的视觉图像文明。
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向原始时代的象形文字和阴山岩画的回归,不是向传统的摹仿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而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构、体制、话语、身体和构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当代现实。
在今天,观看行为(观看、注视、浏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观看将逐步建构它的观看史,发掘观看的深度,养成会观看的观看者。从观看《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太空景观、塞尚风景画中那闪烁多变的兰色和绿色,从观看柏林墙坍塌的实况转播,直到9·11帝国大厦的轰然坍塌所带来的感受,都发掘和形塑着今日的观看。而基于单纯的文本性的模式恐怕已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了。
重要的是,尽管图像表征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它现在已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从整体上理解影像,它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的筹划,也是其结果。影像不是现实世界的补充或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及过程。图像以它特有的形式,诸如信息或宣传资料,广告或直接的娱乐消费,成为主导的社会生活的现存模式。它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化模式,是建构当下生活的主要材料。
视觉文化的兴起不单纯依赖图像,而是依赖当今世界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摄影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借壳上市”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三
的确,当代世界是个视像逐渐成为巨无霸的世界,人们已经离不开视觉图像。但是,视觉文化的兴盛并不等于摄影文学的兴盛。作为一种交叉类型或边缘体裁,它的兴盛取决于它的创新,取决于它文本间、文类间、学科间的交叉的特性。
摄影文学的文本是图像与语言构成的双重文本。此中存在着两种文本间的交错、溶浸、对话与交融。它拥有跨越两种文本的独特的文本间性。摄影文学又是电子媒质与印刷媒质的多重媒质的交集、互补、叠合与创生,它拥有跨越两种文类两种学科两种媒质的独有的文类间性、学科间性和多媒质性。
文学文本以言语为媒介,它的形象的显现是间接的。它没有视觉媒介的那种形象的直观功能,它的实现必须经过创作阶段从形象到语言、接受阶段从语言到形象的两次二度转换。但却正因为此,它发展出了描述、叙事等超越时间空间的巨大表现力。它以想象与幻想为手段,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茫茫宇宙,滚滚红尘,文学均能驰聘意象的神骏,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语言文本具有超凡的叙事性。叙述,只有文学的叙述,才使我们更生动更真切地理解世界。文学文本又具有极为强烈直接的情感性。“诗缘情而绮靡”,由于语言所负载的声音,文学最容易“以情动人”,抒情成了文学最突出的功能。
文学在视觉图像上的感受的间接性带来了阅读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也留下了体味、阐释的广阔空间,留下了文学意境、韵味得以实现的广阔空间。
与文学的语言文本不同,摄影将一切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的形象。这种图像文本拥有文学文本所没有的视像的直观性、具象性,具有强烈的再现性、真实性和造型性。它长于再现,拙于表现,长于展示,拙于叙事。它只能通过照相机后面的眼睛,去选择最富意味的瞬间,将时间与空间凝冻在静态的固定的胶片上。
比不上语言文本作为时间艺术的历时性特征,图像文本以两维的平面空间切断时间之维,往往只能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展示自然、社会和人生。面对一个历时的过程,它发明了“蒙太奇”,来断断续续地连缀历史,它把照片装订成册,于是便把过去打包,将幻想显影,将记忆定格,将希望与憧憬制作成“过去未来时”的卡片。这样,静止的照片就把每个人记忆深处的那些“特殊时刻”转变成为一件能够被保存下来的物品,把历史制成断片。
作为最大众化的公共介质之一,图像又不同于文字,它拥有文学语言难以达到的普遍可传达的特征,它无需语言的长期习得和专门训练,更没有不同语言甚至方言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都可以用图像来进行交流。图像是一切文化间的“硬通货”。
今天,在我们这个拼贴的时代,两种曾经是那样相隔遥远的门类,在现代技术中结合了,它们打破了原有的边界,生产出摄影文学的优势:平面的(准立体)的空间式的构图与线形的时间的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想象的丰富与直观的惊叹结合起来了;语言的抽象性与图像的具象性结合起来了。两种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文类、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媒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创生发展出惟属于它的新的性质。凤凰在这里“涅”。
这种新的性质既吸取了文学的语言文本的优长如自由的叙事性,强烈直达的情感性,想象的丰富创造性,表现的主体性及深长的韵味,又发挥了图像文本的直观性、具象性,再现的真实性与造型性,特别是直接的普遍可传达性质。它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同在,是再现性与表现性的合题,是语言媒质与图像媒质的交互共生。
这种文本间的结合创造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有可能。它依托于摄影技术的普遍化,依托于电子技术、传播手段与印刷方式的划时代革命。
当然,新的双重文本由于它的幼稚不成熟,粗糙不精致,由于它没有成熟的文本规范,没有既成的接受积淀和读者期待,因而它暂时明显不如成熟的单介质文本,它的多介质的综合文本的特征还没有充分显现。
但它具有明显的成长性。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最早的象形文字恰恰是象形与指意的结合,人类从直观的图像出发,走向了抽象的文字,而当抽象的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最高的)阶段,而技术与能力又达到相应程度时,人们就力图打破和超越文字的局限,回到图像,准确地说,回到文字的图像。因为,严格地说,今日的图像也是一种语言。从发展逻辑来说,这是从抽象到更高的具体。
四
摄影文学未来的兴盛和发展同样取决于它的文体、形式、结构的成熟、完善和可创造性,取决于它的这种构成形态能否创造出属于它自己的经典范例,取决于这些经典范例能否获得广大观众的广泛认可,并最终赢得一个稳定、长期的观众——读者共同体。
毫无疑问,摄影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艺术或者说艺术性应该成为摄影文学的灵魂。摄影与文学联姻,是摄影回归艺术本位的一次艰苦的努力。在光与影、线与形、色彩与质感的交错和融合的后面,是像外之像、景外之景,是寻求实现一种意味,是创造一个境界。它在传递外在形象、形式中,更传递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想象和情感,一种阐释与理念。
摄影文学的成熟需要自觉的文体观念和文体创新。它融合了诗、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的某些特征,融汇为一,成为新质。文体创新首先在于摄影小说。图像与语言的深度结合,笨拙的摄影小说因其简洁、直观和独有的叙事方式而在这个信息高度冗余的现实中赢得一席之地。这种崭新的叙事方式,有其独特和新颖之处。
摄影散文、摄影随笔以及摄影报告也许是最富生命力的亚样式。它与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相互契合的。是与像旅游这类当代人最普遍的综合文化形式非常匹配的艺术样式。
摄影诗是更富艺术性的摄影文学亚样式。它先天地拥有“诗画同一”“情景交融”的特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了它最准确的脚注。
美的影像(自然与艺术)+诗(诗情、诗事、诗叙述、诗文化)+运动(参与、过程、体验)+对生活的思索、命名与发掘(像外之像,韵外之致)=摄影文学?
实现它需要实验。
摄影文学又是一种复数文本。它是一种“可写的文本”,是召唤所有读、观者来共同参与创作的文本。从欣赏和接受来说,摄影文学拉长了我们感受摄影作品的长度,它攫住你的眼波,让你在这里留驻,徘徊,以至让你流连忘返。它虏获你的心神,让你在这里徜徉,回荡,引你浮想联翩。它给光与色带来了节奏和乐音,先前的独白于是变成了对唱,进而变成了艺术的交响。它赋予线与形以情节和故事,瞬间于是成为复数,光点相连,相机成了叙事者,摄影于是找到了另一种永恒。
五
过去我们总是说,摄影是对生活的记录,是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社会的。但是现代社会,虚拟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它是一种“超级的真实”。在9·11之前的纽约帝国大厦,为观看虚拟纽约兜风而排的长队,要比乘电梯去望台看真景的队列长多了。今天,人们可以在拉斯维加斯的“纽约饭店”,观看色彩诱人的整个纽约景观,欣赏那座已成废墟的帝国大厦。而拉斯维加斯的巴黎饭店据说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它创生了一座虚拟的巴黎,模仿那座流光溢彩之城中许多著名而美妙的形象和景观。人们照样趋之若鹜,甚至多次去过巴黎的人。在当代,人们有时候对这种仿真的生活比真实的东西更加迷恋和沉醉。
读图时代的摄影文学不再仅仅是对生活的反映,对自然的再现,对时代的记录。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实现,一种观念的投射和一种主体思维的筹划。它总是要在图像之后说些什么。
而今天的摄影文学则是一种“仿真”的“超现实”的策划。20世纪80
年代早期,舍瑞·莱文(Sherrie Levine)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后现代摄影师,曾通过征用别人拍摄的照片对摄影的本真性提出质疑。现在,对摄影再现真实的理论的否定,已成了像《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和那些更声名显赫的出版物谈论通俗文化的一个主要话题。摄影照片几乎不再成为真实的事实的证据。辛普森的律师常常驳斥某一张真实的照片是伪造的——单独一张照片已无法代表真相,而辛普森则据此逃脱法律的惩罚。同样,那些真实的新闻事件与人们看得特别痴迷的电视连续剧没什么区别。
在当今的世界,真实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被颠覆着。
六
作为一种“直观的符号”,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或几本相册,人们通过相册储存一份生命,珍藏一份记忆,他要把整个世界——他的世界装订成册存入脑中。
摄影文学的再兴,就源于这种摄影的普遍性与普及性。苏珊·桑塔格说,“我们每个人都与照片发生着关系,并迷醉于这种带有审美意味的消费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成了在照片中纵欲的伪君子,摄影成了一种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的确,当今的摄影成了一种极普通的生活内容。随着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的、精神的、艺术的、心理的和更具个体性的需求日益上涨,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一日三餐,大鱼大肉,而希望获得更高的精神享受。于是,旅游、阅读、观赏、娱乐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
摄影文学的生命恰在于它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创造者消费者借助视觉技术从中寻求信息、意义或快乐。
作为创造者,那是我的作品,我的创作。由对生活的记录到对生活的咀嚼、体味,从对生活的体味到对生活的思考与创造,从外部进入内部,从对象变为主体,从被动接受变成对生活的主动投射与筹划。当你看到自己创作的作品,你会油然产生一种母亲对待孩子般的亲近感。那是我的情感、我的智慧、我的意志、我的精神创造力的对象化成果,那就是我,我的生命演进的轨迹,我在那里看到我自己,“在对象身上反观自身”,看到我的无穷潜能的开发与释放,看到人的感觉的全面解放,看到人的生命的无限趋近于完美的实现过程。
那是一种生活本身,是必需,是必备。它已成为一种仪式,一种程序。比如出行或旅游,谁能不带一架相机呢?我们行走在路上,大道通天,我们追寻着精神的和物质的“道”,就带一架相机吧,让你用文学的眼睛去摄取生命和生活。在路上“看”并“做”。
所以,今天摄影文学的成功或兴盛正在于它可能成长为一种真正广泛参与的大众文化样式。在于大众由看到做的变革。
专业的摄影,专业的文学都已经创造了太多的经典,太多的辉煌,与之相对的,是通俗的大众的摄影文学。就让曾经高贵的摄影和文学“下嫁”给大众吧,面对数码时代网络时代的大哥大、大姐大如电视、电影、互联网,摄影与文学这对没落的贵族,在联姻中获得了转世重生的最好机遇,获得了溶入新的时代生活,成为吸引普遍参与的大众介质的机缘。
摄影文学的生命在于不断的否定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