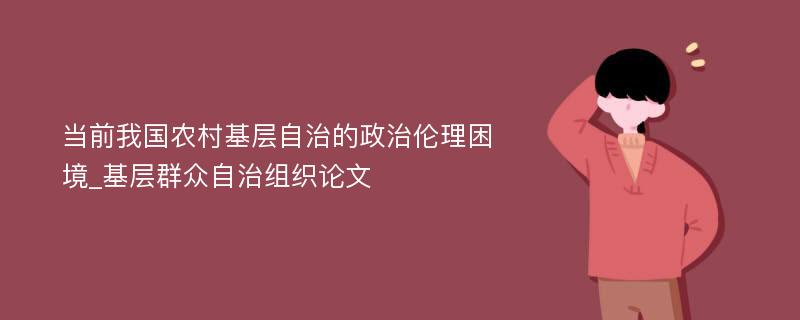
目前中国农村基层自治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困境论文,农村基层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9)11-0037-05
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乡村社会,农村基层自治被认为是农村民主生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然而,在二十余年的农村基层自治实践中,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困局。事实告诉我们,村级自治组织、村干部与村民在农村选举与自治活动中,并非时时刻刻都能做出恰当的行为选择,往往面临着在伦理层面上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涉及人们如何有意、无意地为价值观和价值原则排序。它既是实践问题,也是伦理问题。这就是农村基层自治的伦理困境,困境的核心点就是价值排序,形式是行为选择。事实上,农村自治组织自身的性质及其职能定位,都与行政组织存在相似之处,区别主要在于自治组织的“行政性”更多地受限于“自治性”。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有关的行政伦理学理论可以适用于农村自治伦理。由于组织面临的伦理困境与组织中个体面临的伦理困境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前者具有影响后者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本质特征,组织的行为总要通过组织中的个体来实施,个体的职务行为就代表、体现了组织行为,因此,通过考察后者,可以预测或管窥前者的一般特征。笔者主要通过对个体行为与价值选择的考察,从而更加明晰地呈现农村基层自治的种种伦理困境。
一、角色困境:自治组织双重身份的纠缠
角色不是恒定的,在不同的语境中,每个人都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
在特定的情形下,我们所体验到的特定角色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或者是互相排斥的。一般说来,我们不是仅仅体验价值观本身,而是体验在价值观支配下的角色冲突。就农村基层自治而言,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被自己、上级政府、村民等赋予了多重的角色期待:上级政府期待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扮演政府代理机构的角色,承担起延伸国家行政权力的功能;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自然期望其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公正行使村民自治权。而村干部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在组织中、在家庭中以及在整个村子里又分别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在内心对自己也有着不同的行为期望,比如期望做一个无私的干部,期望做一个好家长等。但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角色之间可能存在天然的冲突与矛盾,支配这种矛盾的正是个体的价值取向。当自治组织和组织中个人的角色扮演,与自己、上级政府、村民的期待不同或冲突时,伦理困境就产生了。
[案例一]2004年7月5日下午4时许,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天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谭中伟被发现死亡。出事地点在村党支部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瓶甲氨磷剧毒农药。
谭中伟留下遗书一封,内容如下:“望党委政府把天华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今后村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确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同时希望天华父老乡亲,团结一致谋发展。领导、父老乡亲、亲人,对不起大家。没有想到,荣升之时,却成了离别之时。”
谭中伟是天华村第一名由村民海选产生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2004年5月1日上任,终年28岁。据死者同事和村民介绍,曾在部队荣立三等功的退役军人谭中伟为人随和,实在肯干,做事讲究亲力亲为,多为群众着想。
“他们把我骂得要死,把我逼到崖上,怎么得了”。7月2日中午两点多,开完镇党政领导督阵的村现场办公会后回家,谭中伟愁眉不展。这次会议与谭中伟的死有莫大干系,已是天华村人尽皆知的事。据村上知情村民和党员反映,谭中伟此次会议上被上级领导重点批评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先伟公司购地需其签字,谭中伟没有答应;二是天华村民从2002年以来的上访最近发展到远赴北京,谭中伟制止劝阻不得力。
“这块土地是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人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是前任村支书张海泉的主意。张书记跑了,现在要新上任的谭中伟认账,这怎么行?没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谁敢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谭中伟不签这个字是对的”。天华村一位老党员振振有辞。
“他上任60多天,责任却有五六年之重,老问题复杂,新问题压头。要解决老问题比登泰山还难,要解决新问题面对现实,他陷入了深渊,不能自拔。在这残酷考验中,精神全面崩溃,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唤起全体村民团结起来”。天华村老党员替谭中伟上书说。(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4-08/19/content_1825211.htm)
案例中的征地争端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社会问题,但放在农村基层自治的语境中,则凸显出自治组织及个人所面临的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政府代理人与村民代言者之间冲突的伦理困境。按照库珀的说法,“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1]。镇政府期望村主任完成基层政府交给的行政任务,村民则把权力与信任交给谭中伟,所希望的当然是村主任能够维护村民共同利益,这两者构成了“村官”谭中伟所承担的客观责任。村主任是民选“村官”,谭中伟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由村民塑造的,村民通过选举的形式将权力委托给他及他领导的村民委员会,以行使自治权,因此,谭中伟理应直接对全体村民负责,忠诚于村民利益;基层政府是村民自治运动的推动者,它与村庄自治组织的关系在法律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谭中伟理应接受镇政府对村庄事务的业务指导,况且他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对党的忠诚与服从理念将支配着他坚定地贯彻上级命令,但是他应该忠诚于镇党委、镇政府吗?也许个人的道德良知会告诉他,应该忠诚于全体选民。这时,忠诚于选民利益是谭中伟所承担的主观责任。如果他更倾向于忠诚上级政府,那么执行上级政府的命令就是他承担的主观责任。不管谭最终忠诚于谁,都会造成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之间存在的现实对立。每一种角色所激起的根植于价值观的义务感影响着他的行为,价值观的相互排斥使谭中伟体验着两种角色的冲突。在冲突面前,他难以做出恰当的选择,以至于在困境中走向自我毁灭。
案例中的镇党政领导期望谭中伟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落实镇政府既定的征地签字并劝阻上访者;村民因为普遍不同意卖地,则希望谭中伟能够支持他们的想法,希望谭中伟能代表村民表达这一诉求。拒绝前者,会失去基层政府的支持;拒绝后者,会失去村民的信任。征地争端使得村民委员会和村主任面临顾此失彼的危险。不得不说,正是征地问题凸显了农村自治组织在身份性质上的认同困惑。自治性是村庄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但自治是由政府拉动的,并被纳入国家制度体系,因此,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乡一级政府。事实上的乡村关系,并非如同法律上所界定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被视为国家政权体系中的终点,但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履行着村庄自治“政府”的权力与职能,即所谓的“乡政村治”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政府的行政功能由村级的基层自治组织得以延伸和拓展至乡村的各个角落。无论从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村庄自治组织都摆脱不了行政化惯性的轨道。在体现“自治性”本质的同时,它又被打上了行政性规划的烙印,双重身份的纠结表明了两种相反的村庄自治发展理念与发展要求。如此,村民委员会及其管理者“既要扮演完成国家和政府任务的‘代理人’角色,更要扮演管理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当家人’角色”[2]。这两种角色的非相容性造成了村庄自治中的伦理困境。
二、利益困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利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且有一种自利的倾向,它促使人对资源和条件进行改造和占有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欲望。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诉求的人们,易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即利益集团。相对于公共利益而言,个人利益与小团体利益都属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就是社会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共同利益,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各种主体间部分利益相同、相一致的方面。公共利益存在于个体寻求其私人利益的努力之中,但它又不是私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如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必然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我们知道,公共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寻求公共利益,而公共组织成员又不能自动地超出他们私人的特殊的利益,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体,我们也同样不能自动地做到这一点。在村庄自治的特定范围内,村民集体利益就是农村自治组织所要追求的公共利益。村干部作为自治组织的成员,不断寻求并促进村庄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职业道德的要求;同时作为独立的个体和承担着家庭角色的社会人,他们也会有追逐私人利益以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要与欲望的必然性,这当然也是伦理规则所允许的合理行为。当追逐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目标出现不一致时,便构成了行为主体在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当然,我们所说的“利益”不尽然是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权力、情感、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等也都属于利益的范畴,只是经济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当村干部有机会利用村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时,他们该何去何从?优先公共的“善”,还是优先个人的“善”呢?
[案例二]四川省仪陇县五福镇筏子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主任、原专职会计三人相互配合,侵占村公路建设资金买手机,后又以买摩托车为名再次把手伸向公款。最终,三人被仪陇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刑。
唐远海、唐本兴、唐大辉分别是仪陇县五福镇筏子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主任、原专职会计。2001年至2003年期间,三人以村干部身份主持筏子村村民集资和向上级争取资金修建村级公路。唐远海负责审批各项支出,唐本兴兼出纳掌握支出,唐大辉管账、做账。2002年夏季的一天,三人共谋后,分别用公款购买手机一部,同时还给五福镇驻筏子村干部、下派干部二人分别购买价值2000元的手机各一部。同年冬季的一天,三人再次共谋后,以买摩托车为由,每人拿走公款各2000元。
2003年4月,眼见有大量支出无法报账,三人商议决定涂改工程购货发票虚增支出,共虚增支出104700元,以掩盖共同侵占集体资金17300元的行为和抵消不能入账的支出。(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7-11/18/content_7105549.htm)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村干部侵占公共利益的案例,但也许我们应该尝试将其放入当代中国社会大背景和农村自治制度的小背景中予以考察。乡、村干部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身份——乡镇干部是国家干部,其生活资源基本仰仗国家供给;村干部除掌握一定的权力以外,与普通村民没有什么根本性差别,仍然是农民,必须靠自己及村级自治组织来解决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因此,村干部最初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上级的差别,因而也就具有虽然是初步却是明确的对于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意识。王思斌曾经提出一种与此相类似的“边际人”理论,即村干部的基本身份仍是农民。他指出,“村干部处在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和农村社区自治系统的中介位置,既是这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点,又是这两个系统利益冲突的触发点”[4]。当村干部自认为他们所获取的生活资源已难以满足个人和整个家庭的需要时,他们就会将视线转向村庄公共财产和公共收益,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村民的信任,逐步侵蚀公共利益。这是一种个人生存优先的价值排序。案例中的唐某三人正是这种典型人物。修建村级公路,进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原本是为村民谋福利,为村民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作为村庄的“公共”管理人,唐某三人主持这一事务是他们在履行公共角色所赋予的义务与客观责任,此时的他们俨然是公共利益的追求者和守护者。然而,在公路建设款项管理中,他们监守自盗,私自挪用、占有集体资金购买手机,为个人获取经济利益,这与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角色相去甚远。他们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选择上,甚至缺乏必要的伦理思考,就进行了不合理的、不负责任的行为选择。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乏唐远海、唐本兴、唐大辉这样的村干部。
三、权力困境:行政权与自治权对立
农村的自治权不是农民所固有的,而是来自于主权国家的赋予。从法律体系的特点来看,中国在推动农村基层自治时采取的更像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治权界定的方式,即自治机关和自治主体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但同时自治机关有义务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因此,如何处理好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两种权力的互动集中体现在乡村关系上。一种情形是,由于政府的力量强力介入乡村社会,农村基层组织已经完成了权力的转变,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政府的管理和基层党支部的直接领导机制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实践中的乡村关系“行政化”了。另一种情形是,一些村民委员会主任不能正确认识和行使自治权,往往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支持,与乡镇政府发生冲突,这实际上又陷入“过度自治化”的泥潭[5]。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体现出村庄自治主体在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博弈中所做出的不合理行为选择。如果认定行政权优先于自治权,则强势的行政力量将严重挤压村庄自治的自由空间,自治很可能沦为行政的附庸,徒有其表;如果认定自治权优先于行政权,则行政力量很可能丧失在村庄治理上的话语权,甚至走向“乡政”与“村治”的对抗。虽然“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对立并不是非此即彼、势如水火,但是要维持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脆弱的均衡状态,尺度把握的难度相当大。在两种权力的对立与博弈中,村民自治主体很难作出负责任的选择,于是便造成了权力的困境。
另外,自治权与政党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拥有对政治的绝对领导权,且与各级政府共同分享政治权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党政二元权力结构”。对村庄而言,政党领导权是国家行政权某种意义上的延伸。这种二元结构在农村基层表现为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并存。由于两者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四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极易导致权力的对立与责任的冲突,尤其是在实行“一肩挑”体制的村庄。当两种权力的话语指向不一致时,村干部究竟是应该履行党内责任、服从国家权力,还是遵从村民意志、坚持自治权?
[案例三]浙江瑞安莘塍办事处某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李道原,因失去村民信任被罢免村主任职务,但在启动罢免程序过程中,莘塍办事处党委却逆民意而行,批复同意吸收李道原为中共预备党员。村民不解:一个失去村民信任被罢免的村主任,党组织为何却发展其入党?而党委负责人反诘道:被罢免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治安处罚,《党章》哪一条规定被罢免的村主任不可以入党?
莘塍办事处党委为何如此不惜与民意对抗,顶着内外压力,冒着民众上访的政治风险,力挺一个已经被罢免的落魄村主任?村民又为何对一个被罢免的村主任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如此介意,不断上访要求上级取消其党员资格,难道仅仅是情感上受不了这种藐视吗?
我们首先来看看村主任李道原是如何被罢免的。据报道称:李道原在村主任位置上有多起违背村民意愿、损害村民利益的违规操作行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件是,李未经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集体研究同意,违反广大村民意愿,私自出让本村土地0.255公顷给一家服装公司盖厂房,后来又公然违背村民委员会决定,在瑞安市国土资源局的补偿标准文书上私自出具“村民对此无异议”的证明。显然,私自出让土地建厂房并私自出具“村民对此无异议”的证明,这确实置村民于非常不利的博弈位置,损害了村民利益,村民当然有理由罢免这样的村主任。
作为村民选出的父母官,李为何会做出这种违背村民意愿的卖地行为,仅仅是为自己牟取私利吗?从利益格局看,其中带着明显的上级政府意志——私自卖地建服装厂,虽然对村民不利,但对上级政府却是大大的政绩,引来厂家投资,既能增加地方税收,又能提升地方GDP;私自在政府补偿标准文书上出具“村民对此无异议”证明,虽然损害了村民利益,却让上级政府留下了更多的卖地收入,占了更多卖地的便宜。显然,村主任李道原是在有意无意地贯彻着某种来自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据新华网: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7/11/content_7483295.htm)
从农村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察觉到:党员标准争议只是表象上的冲突,背后隐藏着非常激烈的权力博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不是科层制意义上的上下等级关系,在村务上实行村民自治,但乡镇政府又不甘心村民自治带来的权力失落和利益失却,于是借着李道原这个村主任,对本该自治的村务进行权力渗透和干预。在面对行政权的强势介入时,村主任李某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是服从于上级政府的政治权力,以牺牲村民利益、践踏自治权的代价获得上级政府的赏识。作为自治主体之一的村民委员会在李某的主导下倒向了公共权力,但作为另一自治主体的村民,他们是村民自治的中坚力量,当然会拒绝这种损害自身利益的村主任,于是对其进行了依法罢免,并做出了坚守自治权、对抗政治介入的行为选择。在这种情形下,村民和他们的权力代理者之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而上级政府又不会“亏待”听从自身意志的人,选择了以“党员身份”对被罢免的李某进行补偿,同时也是在借机对抗村民自治的利益诉求,还在力挺李道原的行为中传播一种“村长要听上级话”的价值观。于是,在这样的权力对垒下,双方在“李道原能否入党”这个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对抗。两种权力的博弈、三方行为的差异,“村官”与村民有着不同的政治考虑与价值排序。
四、道德困境:以德服人与以财服人难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道德伦理型社会,农村是传统道德最后的堡垒。带有传统乡村“自治态”色彩的农村基层自治,最初选举的村庄当家人大多是公信力强、道德高尚的“贤人”,凭借有目共睹的个人品行,他们在管理村庄公共事务、调解民间纠纷时具有较强的道德说服力,能够公正、公平处事,安分守己做“官”。这种选举偏好主要是基于当时农村社会混乱无序的基本状态,最初也适应了农村基层自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将此模式称之为“贤人治村”。渐渐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使得农村也出现了剧烈的变迁,市场化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产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经济的发展鼓舞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泛滥,对财富的膜拜开始充斥村民的内心。如此,村民的选举偏好逐渐由“贤人”向“富人”倾斜。这些“先富能人”土生土长在农村,但又基本脱离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属于新型农民群体。由此,农村实现了从“贤人治村”向“富人治村”的转变。农民所希冀的“富人治村”,无非是期待致富能力强的“先富”者能够带动全体村民走向共同富裕,至少是村民普遍得到实惠。富人和贤人一样也是“能人”,由于卓越的经济才干,他们在乡土社会中也具备一定的权威,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富人是否应该也是贤人呢?富人担任“村官”所赖以服众的资源是他们的财力、势力,还是他们的道德公信力?以财服人与以德服人,形成了富人“村官”潜在的两种路径选择。
[案例四]王文选,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村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因给村民发放1332万元“人头钱”而被称为“天价村官”。
王文选今年50岁,乡镇企业家、劳模,创办多家实体企业,在韩城家喻户晓。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他说自己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时,他承诺: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10000元,“5年后的龙门新村将户户住单元房,家家有小汽车,人均收入2万元”。“为了让村民更快致富,如果我当选,垫资分配三年的两万元,让大家拿钱挣钱”。当选次日,2008年12月16日,王文选提前兑现竞选承诺,村民按人头领到了存单。
王文选在韩城有一个焦化企业,并出任西安某造纸企业董事长。当选村主任之后,他辞去西安企业董事长职务,回到韩城专门管理焦化集团。王文选表示将腾出一半的时间做好村中的工作。他打算以自己的企业作为依托,发展村办企业。(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12/15/content_10506774.htm)
近年,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乃至亿万富豪竞选村干部的事例已屡见不鲜,伴随其中的词汇往往是“天价村官”。一个小小“村官”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值得这些富人付出“天价”争着去“买”?“天价”当上“村官”后,他们会不会为收回“投入”而变本加厉地掠夺村庄财产?虽然是选后发钱,但是王文选仍有贿选之嫌。因为一个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往往能够左右选民的选举意向。分发“人头钱”,这对于村民来说是再实惠不过的承诺了。凭借王文选企业家的身份和雄厚财力,可以轻易赢得村民的选票,所以无论是先发钱还是后发钱,他都摆脱不了贿选的嫌疑。至于王文选为村民承诺的村庄美好理想,以及他个人声称的助民致富、造福家乡的竞选动机,现时期均难以取信于民。龙门村的村民把票投给了王文选,这究竟是不是理性的选择,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如此,王文选的当选明显带有较为浓重的“以财服人”的色彩。
富人争当“村官”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民服务、助民致富,在造福家乡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另一种是为私人企业发展谋求更大空间,为个人谋利。前一种取向,将为富人“村官”争取到更多的正面道德评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树立起较强的道德公信力,建立在道德资源上的个人权威也会愈加牢固。后一种取向,也许会为富人带来更多的财富,但个人财产的增长未必会伴随着村民福利的增加,如此,富人“村官”的个人权威能不能得到村民的认同?以财势作为资源凭借,恐怕“村官”会异化为村霸。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诸多事实表明,富人“村官”大多数倾向于倚仗财力、势力来树立起个人权威,甚至凭借财力、势力乃至武力做出非道德的行为选择。一些村庄存在着干部贪污腐败、乡村恶霸横行、官匪勾结严重、贿选不断出现、结党营私盛行等现象。很明显,这些“村官”缺乏的已经不仅仅是必要的伦理思考了,更缺乏的是作为村庄公共管理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农村传统道德的沦丧已经造成了权威道德体系的缺位。在市场化、世俗化、信息化的大潮面前,“向隅而泣”的道德又因价值观的分崩离析而呈现出分散化、多元化的互相冲突的趋势。日渐式微的道德难以产生效力,道德失范现象在村庄政治中悄悄地蔓延。
[收稿日期]2009-08-02
标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 村庄规划论文; 农村论文;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