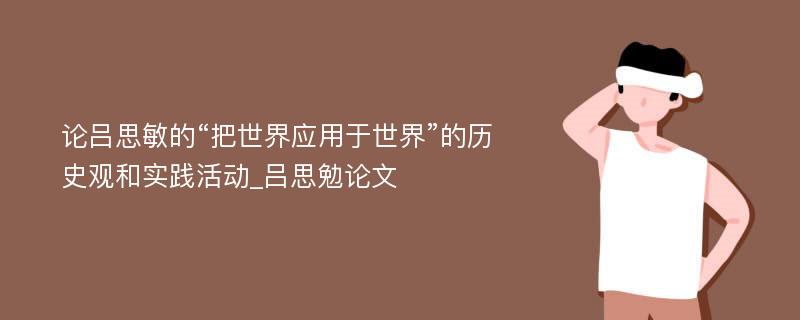
论吕思勉“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与实践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史学论文,实践活动论文,论吕思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4-0492-04
吕思勉先生的煌煌八百余万言巨著,在他生前未能给他带来显赫的声名,但在他逝后 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注:严耕望在他的《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文中 指出,吕氏史学博通周密而不够深密,其史料多取材于正史,鲜有其它史料和新史料, 吕思勉本人又长期枯守于上海光华大学,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与当时作为学术中心的 北平无声气相通,这些便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严耕望将之与陈寅恪、钱 穆、陈垣并立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5页)。) 。今天,我们在考察新史学的发展轨迹时,不能忘记这位前辈史学家的开创之功。先生 不仅留下了“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严耕望语)的丰厚史学遗产,而且他的“经世 致用”的史学观念,他的“为当世效实用,寄希望于未来”的良好愿望,也是我们后学 的典范。本文拟由此入手,谈一谈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活动。
一
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丰富多彩。他在23岁立志治史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正续《古文辞类纂》、三通、二 十四史、《日知录》及《廿二史札记》等书,具有了相当的目录学知识、小学与经学的 基础、文学的修养和史学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尤其是清 代朴学基础上的[1]。然而,吕思勉不仅仅是乾嘉考据学的传人,更是新史学的开创者 之一。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史学界也不例外。梁启超发出了 “史界革命”的最初呐喊:“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当时“史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摈弃旧史学琐碎和脱离实际的弊病,恢复顾炎 武等人提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关注现实时政,让史学真正做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 。吕思勉受其影响,他后来自述道,“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 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 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自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如果说康有为给他以 世界观的熏陶的话,那么,在具体论事,高唱经世致用方面,他则私淑于梁启超,“染 任公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2]。
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前进,吕思勉自己也讲:“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了一个从古未有的 新局面。”他以兼收并蓄的气度,随时代而进,自觉地融西学入国学。西学为中国传统 学术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方法、审视角度与研究手段,具有相应的互补性。吕思勉认为, “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向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瀛海 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3]。吕思勉意识到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对于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性。他说:“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 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 他在研读吴理(C.L.Wolly)的《考古发掘方法论》时指出:“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 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相当的了 解,称赞黑格尔发挥了历史进化论的见解[4]。令吕思勉最感兴趣的是社会学,他对于 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名著都有过深入研究,并指 出:“能明乎社会学,则研治历史,若探骊而得珠。”“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 以历史证明社会学的公例,二者如辅车之相依也。”[5]“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 社会学。”[4]吕思勉对于西学的自觉的吸纳,尤其是对社会学超乎寻常的关注,扩大 了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的理论空间,并使他超越了前人,成为新史学大师。
1930年前后,吕思勉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他后来所讲的思想的第三期变 化:服膺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2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 并开始赞同唯物史观的“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的理论,指出:“这一观 点,无论受到怎样的非难,它总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注:1920年,吕思勉所写的《 沈游通信》、《南归杂记》以及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题为《士之阶级》的讲演会 上,都曾提及这一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事证之,可 见其说之确者甚多,大抵抹杀别种原因则非,然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他还具体分 析了唯物史观遭人非难的原因,这里不再赘述(张耕华《史学大师吕思勉》,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对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 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晤,马君劝予读马 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颇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报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 道,及其致之之道,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6]吕思勉觉得,对马列主 义深入了解后,就发现唯物史观与其治史当经世致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史学观点,不 仅冲突甚少,甚至还有众多的契合之处,可逐步解决他以往思想上的问题,比如,他以 前认为“超阶级之观点”,“亦不过两阶级可以勉强相安”,“而即此区区,仍有人亡 政息之惧。今知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且其改革可以彻底,世界乃真能走 向大同”。又云“旧时之见解,爱国爱民族易与大同之义相龃龉,得马列主义,乃可以 平行不悖”。对于社会改革,“至巨公(即王莽——笔者注)失败后,言改革者,不敢作 根本之图,乃皆欲从改良个人入手。玄学时代已然,承之以佛学而益甚。宋儒虽辟佛, 于此见解,亦未改变。然历史事实,证明此路实为绝路。故今日之社会主义,实使人类 之行动,转变以新方向也”[6]。这一思想转变,对他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以1940年 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为例,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学术文化, 以后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莫不如此。他后 来所写的读史札记,社会经济方面的条目相当多,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 比较特别的[7]。可以说,马列主义使得吕思勉的“经世致用”史观的理论,更趋于成 熟和完整。
二
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史学观的最主要特征是:研究学问,“为当世效实用”。他 强烈反对那种为学问而学问,或“著书皆为稻梁谋”的学者。他说:“小时所遇读书人 ,其识见容或迂陋可笑,然其志则颇大,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若以身家之 计为言,则人皆笑之矣。今也不然,读书者几皆以得一职求衣食为当然。”[8]他叹息 近来讲旧学、讲社会科学者,经世致用讲得太少,实则从反面表达了自己的治学宗旨。 他认为,研究学问从根子上讲,是研究现实问题,因为只有现实的一切才是学术研究的 基础,研究学问并不是学术的归宿,而应是为社会改革服务的起点。他说:“大凡一个 读书人,对于现实社会,总觉得不满足,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对于现状觉得不满, 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 ,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 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 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9]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最大的 愿望便是矫正社会病态,臻于郅治。他认为,研究学问看上去与社会改革无关,其实不 然,要进行社会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还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适当的 手段,就是从学问研究中、尤其是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所以,“学问之事,原不限 于读书。向者士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在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 书者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 当世效实用”[6]。显然,读书者的任务是将书本上的东西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如此 ,则书本所载,与阅历所得,合于一身,才是真正的学问。明晓此理,则阅历所及,皆 为学问,自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10]。
讴歌进化,寄希望于未来,是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史观的又一特征。早在20世纪2 0年代,他就曾揭橥:“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的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想。 ”[11]后又说:“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变迁的,读了历史,才知道人类历史进化的道理 ……若真正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不能阻了, 所以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12]考察整个历史,他认为,世界无一息 不变,后世总比前世要好,因而在社会新旧冲突中,“新的大概是合理的,因为旧的动 摇了,然后新的会发生,而旧的所以要动摇,即由于其不合理”[13]。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意识到历史环境的变化,是渐变与突变的统一,是“风化”与“山崩”的统一。由 此,他得出结论,我中华民族在外辱的刺激下,只有不断地磨砺自我,实施彻底的改革 ,方能自强。“迨乎近世,世界大通,西力东侵,我国与相异的欧洲文化接触,不得不 起彻底的大变化,这是中国所遇到的旷古未有的变局,也正是我民族革新的机会。”[1 4]他大半个世纪的教学与著作过程,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外国侵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 ,但他对于民族自强,一直“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他“讴歌进化,鼓舞信心,竭 精殚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诚可谓鞠躬尽瘁焉”[15]。在《吕著中国通史》的最后 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中,他揭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用“ 大器晚成”来预祝中国的前途光明。他说:“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 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 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15]
三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 以才能自诩,不满足于书斋空谈,都希望直接入世任事,一展平生所学,以实现“兼济 天下”的生平抱负。不过,现实的残酷往往将这些美丽的肥皂泡打得粉碎,在屡屡遭受 碰壁的现实面前,他们只好收拾起“兼济天下”的入世面孔,打出不与浊世合流的“独 善其身”的出世旗号。对此,吕思勉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自忖自己不适合做官,对 于当时的政界风气也看不惯,所以最终选择了治学和教书的道路。他曾评价康有为、梁 启超、章太炎“都是长于计划,短于任事的”,“不脱书生本色”[16],这也同样可以 看作是对自己真实的写照。他说自己“与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做幕 僚而不可做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6]。因而,他总是写文章、发议 论、提倡议,希望以自己的呐喊推动社会变革。
吕思勉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倡议社会改革的时论性文章,它们都触及到了社会的症结 ,如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文官考试宜严》(1912)、《论社会之根本变革》(1919)、 《救济米荒之一策》(1920)、《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1928)、《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 》(1935)、《改良盐法刍议》(1940)、《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 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194 5)、《论美国助我练兵宜缓行》(1946)、《论外蒙古问题》、《如何根治贪污》(1947) 等;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有:《禁奢议》(1935)、《吃饭的革命》(1936)、《上海风气 》、《向慈善家进一言》(1940)、《生活的规范》(1941)、《妇女就业和持家的讨论》 (1944)、《吕思勉谈派报问题》(1946)、《致叶圣陶、周建人建议便利汉字分部书》、 《日报版式印数诤议》、《书店印行完全书目议》(1952)、《致<解放日报>再议报纸发 行书》(1953)等;涉及教育方面的有:《小学教授国语宜用俗语说》(1909)、《全国初 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义》(1910)、《职业教育之真际》(1918)、《反对推 行手头字提倡制定草书》(1935)、《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1937)、《学校与考试》 、《青年的教育问题》、《青年修养》、《国文教学质疑》(1941)、《论中学国文教科 书》(1945)、《学制刍议》、《如何培养广大的群众的读书兴趣》、《读书的方法》、 《读书与现实》(1946)等[10]。这些文章或言时弊、或抒民困、或倡革新,虽不脱书生 本色,但一个抱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我们以吕 思勉先生最关注的几件事作为实例,来具体阐述:
(一)学校的建设与改革。先生将毕生的精力付于教学与著述,虽没有参与行政工作, 但他对于学校的建设与改革,是极其关心的。1927年、1928年,针对兴办学校及改革社 会,他两次上书光华大学,提出“足兵足食”的战备建议。他预言“以今日中国之处境 ,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8],学校与社会的各项举措,均应立足于斯。为此,他 建议学校行政当局:将学校的学生军推行校外,“使人民皆有当兵之技,平时即豫为成 军之备而已”;在学校所在的法华镇建立社仓,“平时借贷于民”,“战时资为军粮” ,并提倡人们多食杂粮及寒食,节省做饭时间;奖励人民多藏军械,“一旦有事,皆国 家之用也”(注:第一次《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刊于《光华大学周刊》第一卷五、六 期上,第二次未刊出。1928年两信合刊于《小雅》杂志,取名为《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 》,编者在前言中讲,其原理“各地方、各团体,皆可师其意而行之”,“书中计划, 眼光远大而切近易行,无锡钱君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良非过誉”(张耕华:《 史学大师吕思勉》,第75页)。)。
(二)“吃饭的革命”。先生认为,中国人花在饮食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 ,很有改革的必要。他主张多办公共食堂,多吃寒食和杂粮,这样就可以使妇女从繁重 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节奏。这种思想,后来愈 发成熟。1936年,光华大学计划添建一新食堂,吕思勉先生便在校务会议上提议,新建 食堂应与公厨改革一起推行,他在校务会议上做了演讲,并写成《吃饭的革命》一文, 详细地介绍了公厨改革的原则,并对公厨的规模、人员安排、财务开支、卫生标准等, 做了具体的设计。他还希望这种改革由学校开始,渐次普及社会。
(三)教学改革。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提 倡启发学生自学,反对照本宣科,生灌硬塞。他在沈阳高师的做法是,“预科国文五小 时,第一至第三学期以两小时讲范文,令学生自看,问乃答之,不能问,然后告之。第 四学期,以两小时命题作文,其余三小时,悉听学生自行研究,欲读何书,即读何书, 如有意思自欲发表,即于此时间内写论文札记等。三小时之自由读书,教员不加干涉, 听其愿读何书,即读何书”[15]。1940年,在无锡国专(沪校)讲学时,也采用先由学生 提出若干要求讲授的问题,由他选择其中一二讲授,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点疑难的 方法,使学生能深入理解[15]。吕思勉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学术大家,他们 回忆起在先生门下求学经历时,都对此方法赞誉有加(注:如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 诚之先生》、王玉祥《怀念吕诚之先生》、庄葳《记吕思勉先生》、叶百丰《忆诚之先 生》、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方德修《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诲》、陈楚祥 《崇高的师表》等文章,对此均有涉及(以上文章均见于《蒿庐问学记》)。)。客观地 讲,这些言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对后世也鲜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言行 的效果本身可能并不重要,关键是,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的理论本身和他的实践精 神,对于现代的学者而言,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和纪念他 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2-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