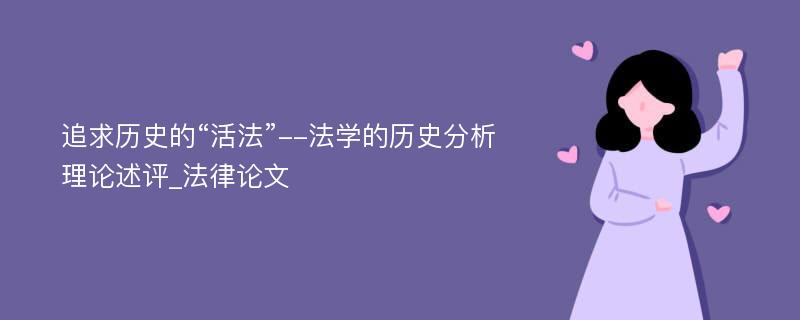
追寻历史的“活法”——法律的历史分析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述评论文,活法论文,理论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主要探究法律的起源和历史沿革,以及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背景,揭示当前法律的制约因素及路径依赖,乃至为当下的法律提供权威的规则渊源。它的兴起与18世纪自然法观念及体系论思想的衰落、弘扬历史和人的个性的浪漫主义思潮的繁荣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从学科建制看,在欧陆国家,法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当时的法学几乎是以萨维尼的历史法学为中心建构的。萨维尼同时提出了“体系”和“历史”两种方法,而“体系”又以“历史”为基础。这对德国法学乃至英美法学的影响都极其深远。(注:Mathias Reimann,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Legal Science.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31,1990.)在萨维尼时代,法律历史分析正式成为与分析法学、自然法学并列的一个学派。由此可见其在法学史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流派的基本观念与方法、理论谱系、意义和局限等方面的分析,对该理论做一评述。惟该流派枝蔓甚多,资料庞杂,笔者绠短汲深,恐谬误纰漏多有,尚祈同仁教正。
一、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基本观念与方法
(一)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基本观念
1.法律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法律历史分析理论首先假定,法律的历史是连续的。首先,这一假定为实现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目的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如果法律的历史不是连续的,该理论就无法达成它的现实目的,即为当前的法律规则及未来的法律变革提供传统的、历史的依据。其次,这假定昭示了该理论的法律观。大多数法律历史分析理论都隐含或者明示:法律是对生活在某一地域、某一文化共同体的人类群体生活经验的总结和表述。它表述的即使不是民族整体的生活规则,也是一个群体的主要和核心的生活规则。因为这种共同生活不会突然裂变、停顿,所以,表达这种生活的法律也是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不会突然中断,而能够保持连续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观念与古代的循环论历史观完全对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观诞生前的主流历史观念几乎都是这种循环论(如尼采所谓的“永恒轮回观”)。这体现在古希腊的“自然”与“历史”观念的对立、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和赫拉克利特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中。中国古代也有认为盛世都在过去的观念(如孔子“郁郁夫文哉,吾从周”的崇古情绪)以及治乱循环观念(如“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朝代更替)。法律连续发展观念表明,历史是前进的,并不是往复的永恒轮回,治乱循环。它与基督教历史哲学中的创世观念一致:上帝创世使人的活动不再是对希腊观念中至高无上的“自然”的单纯模仿,而是作为一种创造活动,参与到上帝关于人类社会进程的整个计划中。事实上,基督教的末世论也必须克服希腊的循环史观,否则就无法完成基督的救赎。(注:上帝创世时,既创造了人和自然界,也创造了时间。参见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三联书店,2002年);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卷11。西方现代性的宗旨之一就是世俗化,但它又引入了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正如康德所言,这一观念必然假定历史“终结”,各种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与基督教历史观念不同之处在于,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中的法律仅仅是对人类历史和当下鲜活的现实生活的表达,法律史也是纯粹的世俗历史。
法律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法律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或是简单的和机械的重复,如果是这样,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种连续性中也包含了变化,甚至不排除突变的可能,但这种变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已有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制约下应变的结果。
2.法律发展的历史相对性。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假定的历史相对性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种理性主义(伴随着乐观主义),它的直接渊源是基督教神学中的“神恩”和“天意”。基督的“化身”和十字架事件把世俗历史纳入到神的历史中。这样,历史终将会把人类引向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而且,历史是朝向未来的、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和千禧年主义的。在这一进程中,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逻辑还统治了历史,历史只是对逻辑的演绎。在这一点上,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又完全不同。
如果说普遍主义的历史是抽象的、有特定目的历史,那么,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中的历史则是具体的、无特定目的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法则优于理论规则。正因为取消了历史的终结目的和方向,历史就由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经验组成,这些活动与经验又没有被一种超验的目的所组织和综合,所以,历史没有优劣之分,历史的发展线条也是多重的。法律都是从历史产生的,是对民族生活的描述,也就没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别,更无所谓进步与落后。借用尼采的话说,法律是“超善恶”的。而且,法律是一个历史范畴,没有超越历史之外的法律真理;不存在永恒有效的法律,而只存在发挥实际效用的法律。
3.法律是一个有机体。大多数法律历史分析理论都隐含了这种假定:法律是一个有机体。如萨维尼的历史方法之一就是“有机方法”。(注:Hans-Ulrich Stue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Duncker & Humblot,1978,s.27.)这一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就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而言,法律虽然体现为独立的规则,但它也反映了各种社会因素,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产物。第二,法律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类似。法律本身和人类一样,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是有生命的连续体。在任何阶段,法律都不是孤立的,仅仅指向当下;法律不能仅仅由理性单独创造,而必须在当下(包含了历史的)的具体经验中寻找法律的渊源。
这种观念使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分析法学和哲学法学区分开了。分析法学假定的法律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金字塔体系;自然法学假定法律中存在终极的、可以被认识(或者被启示)的目的和理想,法律的价值种类和体系是固定的;法律历史分析理论设想的法律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与社会生活同步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各不相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四海皆同的规则体系,法律不是自足自洽的,而是与时俱变的。
法律是一个有机体的观念与苏格兰启蒙传统中的复杂系统观念紧密联系,它也常常与法律的民族性观念一道构成法律中的神秘主义。
4.法律与民族性紧密相关。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假定,法律体现的是民族生活,它直接来自于民族的生活经验、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这是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最核心的观念。萨维尼精辟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年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征,其为一定的民族所特有,如同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注: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7页。)而萨维尼将法律等同于“民族精神”更明确地表明了法律与民族性的关联。普通法学者也强调这一点。如黑尔(Matthew Hale)认为,“普通法本身不仅仅是公平、优秀的法律,而且它独特地适用于英国政府以及民族的性情。同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运用,普通法已经与英国人的民族气质结合起来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英联邦的章程与法律。”(注:Sir Matthew Hale,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30.)很明显,黑尔把普通法归为适合英国民族特制的法律的观点,与托克维尔对“民情”的强调异曲同工。
依此,法律一直留存于人们的集体记忆和传统中,始终根植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民众的心灵或各种典籍等历史文本。正如霍姆斯所说,法律好比一面魔镜,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看到过去的人的生活。如果法律因为时间而湮没,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就会因为失去分析对象而成为无源之水。
法律是民族性体现的观念常与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其他假设一起,催生出法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二)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基本方法
法律的历史方法首先使用的当然是历史分析方法,如对典章制度的钩沉引幽、训诂等方法。这里仅介绍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其他重要方法。
1.归纳。与分析法学和哲学法学(在德国学理上,与历史法学派对立的法学流派)使用的方法相比,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最有特色的方法就是归纳方法。分析法学主要分析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和制度,重点是对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如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语义、逻辑和概念的考察。哲学法学研究法律的各种超验因素,如法律的神学、哲学基础、法律规则中的各种理想价值等。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并没有预先假定一个理想的、终极的法律乌托邦,它必须从零散的法律史中归纳、提炼出法律的发展过程和规则。它偏好分析的也是民族的习惯法,而不是国家的实定法。可见,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归纳方法与哲学法学的演绎方法完全对立,所以在德国法学史上,历史法学派是直接作为哲学法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
法律的历史分析从法律史中归纳出法律的一般规则时,常常会走向历史分析方法的反面。如萨维尼最终投身于体系化的、理性化的方法,抛弃了历史方法。这既体现了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归纳力比多”,也反映了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方法的局限性。波斯纳指出的麻痹的历史感和进步的历史感,以及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提到的运用历史的限度问题,都表明了这一点。
2.移情。从法学史上看,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是与浪漫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就来自于赫尔德奠定的历史主义观,而赫氏的这种观念又直接催生了德国的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传统。德国精神科学的一些核心要素,如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李凯尔特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两分,基本上是以历史科学为基础的。其后,这种方法经过新康德主义和韦伯等人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萨维尼认为,研究法学仅仅依靠单纯的逻辑方法还不够,必须借助“直观”的方法来弥补概念逻辑推理的不足,(注:Helmut Coing,Gesammelte Autsaetze zu Rechtsgeschichte Rechtsphilosophie und Zivilrecht:1946—1975,Band 1,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178 ff.)而直观则是精神科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思路极大地影响了耶林,并最终促成“利益法学派”的形成。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发掘的是在历史中实际运作的法律,移情、体验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若不采取这种方法,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以前的法律,就很可能比较出现在的法律与以往的法律之间的优劣。因此,它要求法学家把自己置于法律产生的特定历史情景中,在法律得以发挥作用的各种复杂社会因素中,发掘法律本身以及法律存在的正当性。法律的历史并非是由宏大事件构成,法学家要致力于发现的,乃是以往拓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当时是鲜活的法律,它们通过涓滴细碎的日常方式表现出来,构成当时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有生命力,也是因为其不是外在于人们生活的,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见,法律的历史分析针对的并不仅仅是研究对事件、往昔的编年史或者记录的历史,而且是一种联系、解释或者说明往昔的方式的历史。(注:参见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3.语境方法。语境方法的首要假设是任何制度的正当性都是历史的。永恒的、普适的正当性是人们刻意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自然的、历史的。“任何具体的制度本身都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合法性,都必须服务人类的、特别是当代人的需要,这才是任何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根据。”(注: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其次,语境论的方法假设,产生和变革法律制度的直接动力不是理性创造或者神启,而是社会的现实需求。霍姆斯指出:“远古时代人的习俗、信仰和需求使一条规则或者准则得以建立。随后的数个世纪,这些习惯、信仰和需求早已湮灭,而规则却依然如故。制定规则的原因早已被遗忘……人们思考、解释政策,并使之与目前的情境调适,于是,新发现的原因就适用于这些规则……旧形式接受了新内容……。”(注:Holmes,Common Law.Boston:Little and Brown Company,1948,p.5.)而且,霍姆斯对各种时期的责任形式的考察,也表明法律制度演变的动力是社会的需求,它是社会逐渐演化的结果,而不是理性创造的结果。
语境论也与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关于历史相对性假设联系在一起。因为历史是相对的,所以任何制度在历史中几乎都有其合理性,在当时几乎都是正当的。但这种合理性和正当性只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不能跨越时空界限。如果不运用语境方法,假设法律是线形发展的、法律规则可以横空出世,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就会失去现实意义。因为法律的历史就不可能对当下的法律发展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法律的历史分析就完全成为一种纯粹知识上的探求。
在操作上,语境论的方法首先要求,在对法律进行历史分析时,除研究法律文本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文本的语境和脉络。也就是说,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不但要分析法律制度本身,还要分析与法律制度相关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观念史等,从而将历史分析真正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其次,法律历史分析理论还应总结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为与现在和将来没有确定的事件相比,历史是人们经历了的,当然更具有借鉴价值。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就非常强调历史分析对当下的借鉴价值。(注:参见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同样,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也很强调历史分析对当下的作用,历史分析不是最终的目的,它不但应恢复历史中法律的原貌,还应给今天的法律提供启示和借鉴。这是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作为学科的法制史学的区别所在。所以,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常常会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法律,如梅因、布赖斯(James Bryce)等学者所做的那样。因而,豪斯华斯(William Holdsworth)在评价梅因时曾指出,梅因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结合了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注:Richard A.Cosgrove,Scholars of the Law:English Jurisprudence from Blackstone to Har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130.)
二、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理论谱系
埃利希指出,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和注释法学派。17—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大学者们都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历史和哲学的法学家。英国法学家从福蒂斯丘(Fortescue)开始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布莱克斯通则是历史分析的大师。(注:Eugen Ehrlich,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of Law,translated by Walter L.Moll,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oce Pou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4.)这里遴选部分重要的思想家,分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论述。
(一)大陆法国家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理论谱系
1.维柯。维柯对历史学的意义在于,他反对笛卡尔的几何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提出了“新科学”。它其实就是摆脱了自然科学权威,并将历史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科学。维柯在其早期作品《当代研究方法论》(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中,就开始思考现代方法与古代方法的优劣。他认为,现代方法提供的工具是“哲学批判”和以笛卡尔主义的逻辑为代表的“几何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产生了自然科学的探究方式以及艺术生产方式。而古代方法则是一种“主题的艺术”,即用想象和记忆来组织演说,使其雄辩、动人且有说服力。维柯认为,现代方法过于强调了几何学方法,没有认识到学习过程的展示、说服力和愉悦。(注:Vico,On the Study Methods of Our Time,Elio Gianturco(tran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维柯认为,笛卡尔的方法不能适用于感觉和心理科学,以及其他不能量化的研究。维柯虽然也从“天意”出发研究历史进程,但他关注的不是奥古斯丁式的历史哲学,而是从人类的语言、神话和传说中寻找历史的踪迹。维柯对诗性智慧的强调,影响了狄尔泰、马克思、柯林武德和布赖斯等人,并直接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精神科学的源头。
维柯1694年获得民法和教会法学位。他不仅贯彻了自己的方法论,对罗马法研究做出独有的贡献,而且还提出法律历史分析的基础理论。维柯指出,人对于他所在的民族的制度和法律的记忆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正是因为有这些法律和制度,一个民族的人们才得以被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民族,(注:参见维柯《新科学》(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3页。)正是法律和制度把他们联系在他们的社会里。(注:参见维柯《新科学》(上)第118页。)维柯的这些观点与后来德国的历史法学派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2.孟德斯鸠。从法学学术分科来看,孟德斯鸠基本上是被作为法社会学的先驱看待的,其实他对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也做了很大的贡献。《论法的精神》与《罗马盛衰原因论》探究的都是决定国家政制的一般性因素。“法的精神”是一般的精神,包括了支配人类的诸种因素,即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原则、先例、风俗、习惯等。(注: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5页。)
从法学方法论角度看,孟德斯鸠的贡献在于他平衡了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与维柯将历史归于“天意”不同的是,孟德斯鸠凸现了人的理性创造力,人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是有能动性的。因此,普遍的法律体现的是人类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情境下的特殊适用。
孟德斯鸠对法律一般精神和规律的考察并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建立在考察各民族的历史条件、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论法的精神》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法律的历史和现实制约因素的分析。这使他与自然法学派拉开了距离。此外,孟德斯鸠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他驳斥了霍布斯假设的自然状态,认为霍布斯只是把社会建立后的事情加在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身上,(注: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4页。)换言之,这种假定是非历史的。
孟德斯鸠对“法的精神”的考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他对法的精神的界定包括了法律是一种有机体的观念。涂尔干指出,孟德斯鸠是将法律作为社会的一个生命来看待的。法律“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因素或器官。除非我们努力了解它们如何合作及适应,我们不可能认识它们的功能。”(注:参见涂尔干《孟德斯鸠和卢梭》(李鲁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页。)孟德斯鸠还认为,立法者的主要美德是节制。“他强调了为统治术所要求的深思熟虑的技巧——他需要决定用什么样的法律;需要理解构成法的精神的诸关系之间和这些关系与每个社会复杂的细节的联系。”(注:参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4页。)他非常强调习俗对法律的制约作用,认为风俗和习惯是一国的一般制度。立法者不能用法律改变习惯,而只能通过提倡其他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来改变。因为各族人民对自己习惯总是恋恋不舍的,用暴力取消习惯的做法行不通。(注: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305—311页。)孟氏对法律的一般精神和习惯制约力量的强调,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很近似。
3.萨维尼。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真正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进入法学殿堂,始于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法学史一般都将萨维尼作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注:Ehrlich,op.cit.,p.16;Paul Vinogradoff,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Batoche Books Limited,2002,p.107.)在德国,历史法学始于康德哲学对自然法假定的批判以及对实践知识与理性知识、伦理规则与法律规则、应然规则与实然规则的区分。它的直接动力来自于19世纪初期对科学性的追求。历史法学派有关历史的思想来自于赫尔德。德国法学中的历史学派可以追溯到18世纪。被伯林称为第一位历史社会学家的德国律师默泽尔(Justus Moeser)认为,一切制度都有自己“当地的理由”,不可能被普遍适用。他因此反对伏尔泰对路易十四时的法律著名的批判:从法国此地到彼地,要像换驴一样更换法律。他认为,这恰恰表明,当时的法律建立在不间断的、古老的习俗上,保持了丰富的多样性,避免了强求一致带来的专制。(注:参见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5页;Otto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rnest Barker,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translator’s introduction,liii。)
通常所说的历史法学派诞生于哥廷根大学。普特(Puetter)在他的演讲和著作中最早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揭示法律。但历史法学派的真正创始人是普特的门生胡果(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对历史法学派的评价针对的就是胡果)。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民族生活才能够被理解,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和表现形式。(注:参见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0页。)真正为历史法学派在历史学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是胡果最得意的门生、日耳曼派的代表人物爱希霍恩(K.F.Eichhorn)。他在1808年出版了《德意志法律与制度的历史》。他将法律描绘成从一切影响民族生活的因素中产生制度,并追溯了不同时代的法律观念与制度的联系,揭示了它们演变的连续性。古奇这样评价他:“在法学家中,没有人能这样有力地唤醒与培养民族精神,即使在历史学家中也是少数。”(注:同上,第132—133页。)
历史法学派的深远影响是由萨维尼获得的,尤其是他与蒂博1814年就制定德国民法典问题的论战,使历史法学派成为当时法学中的一颗璀璨明星。萨维尼也被视为法学界的牛顿或者达尔文:“他通过对法律现象的理解,发现了一个现象的世界——就像牛顿那样。……萨维尼把文艺复兴的阳光带进了法学。”(注:Sir John MacDonell and Edward Manson(eds.),Great Jurists of the World.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68,p.586.)但萨维尼并不反对法典化,他主要担心如果当时制定法典,会把目前不太成熟的法律科学固定下来,从而阻碍法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注:Karl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8.Auf.C.H.Beck,1997,s.65.)
萨维尼对历史法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法律诉诸于民族的共同生活与精神,并通过“民族精神”这一简短有力的术语,以及诸如法律与语言的关系等论证使历史法学派的主张不胫而走。后来,萨维尼的弟子普赫达(G.F.Puchta)在1887年的《作为权利科学的法理学大纲:法学百科全书》中也使用了“国民性和大众性”、“共同意识”、“民族精神”等术语。但是,他们使用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人类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萨维尼的学术实践与其学术主张之间的反差极大:他没有发掘真正属于日耳曼人的习惯法,而是毕生沉醉于对罗马法的研究。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罗马法在中世纪没有被湮没,而是以各种形式留存在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生活中。(注:Carl von Savigny,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Law During the Middle Ages.tr.by E.Cathcart,Hyperion Press,Inc.1979.)而且,这种罗马法并不是经中世纪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加工后的罗马法,也不是经过实践改造后的罗马法,而是原典罗马法。萨维尼因此遭到了很多批评。(注:Ehrilich,op.cit,pp.17—18;Vinogradoff,op.cit,107 ff.)萨维尼的这种做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根源。(注:参见拙文《萨维尼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从历史法学派形成机理角度的考察》,《清华法学》第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真正坚持历史法学派主张的是爱希霍恩、基尔克等“日耳曼主义者”,而不是萨维尼等“罗马法主义者”。
在19世纪中期,随着罗马法的研究大功告成,加之受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历史法学派完全走向了其反面。萨维尼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美化历史,而在于探究实证法最根本的原则。一旦发现了这些原则,历史研究就终结。普赫达发展了萨维尼的体系方法,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体系,并由此构建了概念法学,认为体系不但是接受性的,也是生产性的,从既有原理中可以推演出新的法律规则,可以无视概念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同时,他也发展了萨维尼关于学者法的观点,强调学者法对于习惯法的优先地位。耶林早期也倡导“自然—历史方法”,要求将法学从罗马法的实体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概念法学以特殊的自然形式。(注:Mathias Reimann,op.cit.)到这一时期,历史法学派逐渐衰落了。
4.基尔克。在德国的历史法学派传统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基尔克。汉语学界最为熟悉的是他的法人有机体说,即认为法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体,与自然人一样具有生命力。(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实际上基尔克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作为历史法学派中日耳曼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成果对法学和政治学都有重大影响。而且,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德国才没有通过温德夏德主持的纯粹罗马法式的民法典。
基尔克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中世纪日耳曼法中的团体的研究——四卷本的《德意志团体法研究》(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他的出发点是反对罗马法上的法人拟制理论,并建立新的社会理论和社区理论。(注:Fredrik Hallis,Corporate Person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138 ff.)基尔克不仅论证了法人有机体说的合理性,也论证了日耳曼组织体法的精髓——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重视的是邻里、同伴和合作关系,关注的是集体人格和共同体精神。这是与罗马法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精神质素,也是罗马法的解毒药。与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结的萨维尼类似,基尔克梦想的是创造一个浪漫主义的、体现日耳曼集体主义与互爱精神的共同体乌托邦。梅特兰盛赞基尔克的法人学说,认为基尔克的新理论“在哲学上是真实的,在科学上是合理的,法典与判决中都已暗示了这一点。它在实践中是便利的,历史上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一理论确实是属于德国的,而且可能为德国的民族性所独有……”(注:O.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translated & introduced by FW.Mait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0,p.xxv.)
基尔克有关中世纪的政治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古代希腊与罗马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的精髓都是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它们都包含了一些共和理念,如人民主权、反对独裁等。到中世纪,国家、社会与教会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关系。中世纪的思想家并不将社会看成是追求各自目的的个人的集合。相反,他们认为,被统治者是身体,而国家机关则是头。头思考,身体则行动,社会秩序相当和谐。而社会是“一身两头”,“两头”即教会与国家。两个“头”之间的斗争以及这种身体的隐喻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基尔克的核心观点是,希腊—罗马法是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世界,而基督教则是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源头。(注:Ibid.,p.xxvii.)基尔克对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分析的基调,是努力发掘日耳曼传统中的共同体和社群思想,重新建立德国的政治秩序。他的团体人格论其实是与社会契约论相对应的思路,可以开创出另一种国家权力合法性和个人权利正当性的逻辑。
(二)英美国家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理论谱系
1.从布莱克斯通到黑尔:普通法心智。普通法的兴起通常被看作是王权扩大、中央权力集中的产物,(注:Sir F.Pollck & F.W.Main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2[nd],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其实普通法的形成主要是自然演进的结果。王权并没有破坏普通法,相反还保持了普通法的一贯性,维持了世代口耳相传的习惯法传统。按照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普通法是久远的、超越记忆的,而且是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的。这种观念的学术表达就是“普通法心智”。在学术史上,无论是格兰维尔(Glanvill)、布莱克斯通、福蒂斯丘、戴维斯(John Davies)、柯克还是黑尔,都非常强调习惯法的优越性。
著名法律史家波洛克表达了这种观念:
如果法律是习惯的观念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法律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以适应人民生活中的每种新经验。这样,过于探求法律本质的理论似乎都无法走向历史观念。但事实是,坚持法律是习惯的普通法的法律人,却相信普通法以及宪法,恰恰一直就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的,它们是超越了记忆的: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古老,或者是因为它们是遥远的、虚构的立法者的作品,而是因为从准确的法律意义上说,其起源是超越记忆的。正因为此,最早关于普通法的历史记载是找不到的。(注: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Reissue with a Retrospe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6.)
正因如此,格雷教授在为黑尔的《英国法律史》所作的长篇导言中将英国法律史的内容分为隐含的和外显的两部分。隐含的传统其实就是对法律的态度、观念与意识。(注:M.Hale,op.cit,p.xi.)从普通法的经典著作看,普通法理论契合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基本观念。普通法的经典理论也蕴含了法律是“有机体”的观念,即普通法是自发生长的,而不是人为创造的。大陆法系的立法理性是一种主权理性,普通法理性则主要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理性。普通法的权威和智慧不是来自于人为的理性和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于历史和传统,来自于对日常生活和历史的表述;不是来自于对真理和正义的阐述,而是来自于其历史深度以及它与国民认同感的联系。普通法是对日常经验的理性规制过程和反思过程的产物。柯克说“法律的生命是理性”,这种理性是指“通过长期学习、观察和经验得到的人为的完美理性”。(注:Gerald J.Postema,Some Roots of our Notion of Precedent.In Laurence Goldstein(ed.),Precedent in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p.18—19.)可见,普通法的理性是司法理性而不是立法理性,是实践理性而不是推理理性。正因为如此,英美法才一直有法律不是被制定的,而是被发现的观念。
普通法的这种观念使英国的政治和法律较为稳定和平和,也是英国成为近代自由宪政典范的原因之一。格兰维尔、布莱克斯通等人都认为,不成文法产生于司法判决和权贵的同意(这是远因),但是其权威却来自于国王(这是近因)。(注:J.W.Tubbs,The Common Law Mind: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onception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87.)直到17世纪,柯克、培根也明确指出,司法判决并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证据和根据。(注:Ibid.,p.182.)其后,黑尔还明确指出,司法判决仅仅约束诉讼当事人,它们不是法律,因为只有国王和议会才有权力制定法律。(注:Hale,op.cit.,p.182.)但是,普通法的这种效力并没有影响普通法的力量,国王和议会不能随意更改普通法。如福蒂斯丘在《论法律的本质》(De Natura Legis Naturae)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获得人民的同意,英王不能随意改变法律,因为他的统治既来源于王权,也来源于政体。英国是一个政治的和王权的国度。习惯法的存在和改变直接体现了人民的合意。而且,普通法是最好的法律,因为它来自于远古,如果不是最好的话,早就被废除了。(注:Tubbs,op.cit.,pp.54—55.)福氏的本意和布莱克斯通其实是一样的,即指出了王权的边界(通过区分王权和政治权力),从立法权力的角度控制国王权力。这表明了法律的历史对于现实的深远意义;它使普通法成了捍卫自由和权利的力量。正如格雷教授指出的那样,柯克及其同代人把法律从一门手艺转化成了一门自由的艺术。(注:Hale,op.cit.,editor’s introduction,p.xii.)
另一方面,普通法的这种历史观既使法律保持稳定性,又使国家的政制保持连续性。洛克林认为,英国宪制的法律形式体现着一种中世纪的秩序,英国公法领域中也保留着一种基本上属于前现代的世界观。(注:参见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1—63页。)这就是普通法心智对宪政的意义所在。
2.梅因。在英美法学界,梅因可谓第一个明确使用历史法学方法并为历史法学在英美赢得声誉的法学家。梅因批评了布莱克斯通对道德论证的依赖及对自然法理论的诉求,还指责边沁和奥斯汀对法的本质的思考缺乏历史维度。他认为,法律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边沁和奥斯汀的理论本身也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注:Richard A.Cosgrove,Scholars of the Law:English Jurisprudence from Blackstone to Har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p.119—121.)1861年,梅因出版了其名著《古代法》,阐述了他的历史法学方法。不过,从学术史上看,梅因的主要贡献是他从印度归来后对乡村社区、早期的制度、现代习惯以及古代法的研究。梅因明显受到萨维尼的影响,这在他的《古代法》中有充分体现。(注:Paul Vinogradoff,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Batoche Books Limited,2002,pp.115—116.)
梅因在该书中既提出了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基本方法(如比较方法、历史社会学方法等),又从事了法律历史分析的具体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书中,梅因将卢梭作为其主要的学术对手,因为自然状态恰恰破坏了经验性的历史调查。(注:Ibid.,p.125.)他认为,自然法虽然“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地接近于它的希望”,而且“并不完全是幻想的产物”,但它和自然状态的假设一样,是“历史方法”的劲敌。(注: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章。)他对自然状态的批判,主要是运用其娴熟的罗马法知识(梅因是牛津大学的民法教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状态假定的非历史性。
3.梅特兰。在梅因之后,英国复兴法律历史分析方法的人是英国法律史学的奠基人物——梅特兰。
梅特兰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将英国法视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中发现法律的意义。梅特兰研究法律史一直有其自身的强烈关切,即探究自由与平等的起源和发展。1884年,他在档案馆发现了英国法律史的大量材料,这让他痴迷不已,认为他发现了英国13世纪的真实生活画卷。而托克维尔曾暗示,这些领域正是英国政治结构中最独特和最重要的。这为讨论他一直关心的问题提供了资料来源。(注:Alan Macfarlane,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Visions from the West and East.London:Palgrave,2002,ch.1.)在《爱德华一世时代以前的英国法律史》一书中,梅特兰将英国法律与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揭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用以说明英国自由整体上的发展。英国制度的核心——法律仅仅是他发现英国社会各种不同的领域的发展的一个主线索而已。因为在他看来,法律史是说明政治史、经济史的最好证据。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时代错误”,梅特兰的处理方式可谓是“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他认为,撰写历史应同时向后看和向前看。他追求的是“想象性重构”。在这一点上,他与柯林武德、克洛齐等人的历史观念类似。梅特兰还坚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分析英国法。他本人对德国法、法国法和罗马法都有深刻的研究,这使他能够总结出英国法的独特性。
尤值一提的是梅特兰关于历史连续性的观点。从孟德斯鸠以来,英国政治的连续性就广为人知。梅特兰的英国法律史研究也没有明确表达过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有重大的革命,相反,他认为,英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早在13世纪就已经确定了。到亨利二世1271年去世时,在法律的形式性、简洁性和确定性方面,英国法就已经是现代的了。(注:Sir F.Pollck & F.W.Maintland,op.cit.,p.47.)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梅特兰也坚持了这种观点,比如他选取了1307—1833年这几百年的时段来分析普通法的诉讼格式。他认为这一时期虽然长,但不能再细分为更小的时段。(注:F.W.Maitland,The Forms of Action at Common Law,URL=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maitland-formsofaction.html.)他还认为,当时英国国会制度、法院法等都可以在爱德华统治时期找到其历史渊源。1066年的诺曼征服也没有对英国法产生多大的影响:“确实,如果我们理解1066年后每年的历史,那么,对诺曼征服对法律是否产生了任何重大的影响,我们都会长时间怀疑不已。在英国的诺曼人数量并不多。国王威廉也不想将任何外来的法典强加于其臣民身上。”(注:Ibid.,p.79.)“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威廉不想废除英国法而代之以诺曼法。相反,他命令,所有英国人都适用爱德华国王的法律,即古老的英国法……”(注:Ibid.,p.88.)从梅特兰的其他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梅特兰始终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此外,梅特兰一直强调英国法的日耳曼渊源。他认为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日耳曼法。他与孟德斯鸠一样,都神往“日耳曼森林”的自由政制。梅特兰翻译过萨维尼论罗马法的著作,但没有完成;他翻译了基尔克论团体法著作的一部分,定名为《中世纪的政治理论》。他受基尔克的法人实在说影响很深。他写了数篇关于法人的论文,(注:如“The Unincorporated Body”、“The Crown as Corporation”、“The Corporation Sole”。)赞成基尔克的观点,并贯彻了他对自由的思考。
这样,英国法律史传统12世纪经过格兰维尔、13世纪的布莱克顿、15世纪的利特勒顿(Littleton)、17世纪的柯克、18世纪布莱克斯通、19世纪的梅特兰,始终弦歌不辍。
4.美国的“历史法学派”。在同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法学方法。所以拉班(D.V.Rabban)将美国赞成历史法学派观点的学者归结为美国的“历史法学派”。(注:David M.Rabban,The American School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URL=http://www.utexas.edu/law/news/colloquium/papers/Rabbanpaper.Doc.)
受梅因的影响,霍姆斯的《普通法》基本上是对法律进行历史分析的著作。霍姆斯认为:“法律包含着一个民族数个世纪的发展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仅仅视为数学教科书里的定理和推论。为了知道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以及它未来的趋势。”(注:Holmes,op.cit.,p.1.)而且,法律的历史对于法律的现在也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无论何时,从根本上说,法律都几乎与当时被认为便利的东西相符;但是,其形式与机制,以及能够产生人们期望的结果的程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过去……”(注:Ibid.,p.1.)
波斯纳指出,萨维尼工作的目的在于,他相信古老的法律原则在今天是有用的,他的任务也在于发现这些规则。而霍姆斯的兴趣则在于变化本身,在于古老的原则如何演进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的现代法。(注:参见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第203页。)这主要是因为,霍姆斯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萨维尼实际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在普通法国家,法律理论与历史具有天然的姻亲关系。拉班的考察表明,在美国,很多反对自然法和分析法学的学者都采用历史法学派的方法。他们提出“法律要运作良好就必须回应国民意识,满足国民的需要”;法律是由“民族的历史和制度、生活方式、习俗和宗教塑造的,简单地说,是由民族生活塑造的”。(注:David M.Rabban,op.cit.)萨维尼对美国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莱曼指出,萨维尼曾经是很多美国学者模仿的对象。(注:Ibid.)与蒂堡和萨维尼1814年的关于制定民法典的论战相似,在19世纪末菲尔德(Field)等人揭橥的纽约制定民法典的运动中,卡特(Cater)反对制定民法典的理由几乎与萨维尼的理由相同。(注:D.D.Field,Reasons for Codification;James Cater,The Proposed Codification of Our Common Law.In John Honnold(ed.),The Life of the Law.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4,113 ff.)
5.赫斯特与霍维茨。美国内战前的法律史是美国法律史学的重点和热点领域。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学者是J·威拉德·赫斯特和默顿·J.霍维茨。
赫斯特是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时报》称其为“美国法律史学泰斗”。他对美国法律史研究的不朽贡献更被誉为“赫斯特革命”。他将法律从“内史”转化成了“外史”,即研究法律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注:参见韩铁《走出黑盒子:美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赫斯特革命”》,《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在赫斯特手里,以往单纯关注典章制度的法律史学变成了法律的历史社会学。
赫斯特的代表作《法律与19世纪美国自由的条件》分为三部分:“能量的释放”、“对环境的控制”以及“权力的均衡。”其中以“能量释放说”最为有名。他认为,19世纪美国法律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一个组织性原则是“最大限度保护和促进个人创造性能量的释放”。(注:J.Willard Hurst,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6.)要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就必须捍卫私法自治原则,同时建立有利于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程序和制度。第二,动员社会资源来形成和控制给人更多选择自由和更少限制的环境。(注:Ibid.,p.6.)在1870年以后,随着大工业、金融业的迅速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加,美国法律从强调释放能量和控制环境转向了保持权力均衡。这里的权力均衡不再是美国立宪时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在整个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的权力均衡,尤其是限制私人权力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注:Ibid.,71 ff.)
从方法论上看,赫斯特的研究属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但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在史料上,他广泛挖掘了法律机关的各种文件,如法庭报道、立法机关文件、州议会的法律汇编以及执行部门的文件。赫斯特的结论虽然相当抽象,但其关注点依然是日常生活的经验。
1970年代后,美国最有名的法律史家是霍维茨。其代表作品是《美国法的变迁:1780—1960》。霍维茨采取微观分析方法,抛弃了整体史观、目的史观的假设,剖析了美国私法变迁的各种复杂、深厚的社会条件。作为批判法学的代表之一,他详尽地揭示了美国私法演变过程中的各种争斗、妥协和平衡。他通过对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利益分析,暗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代价主要是由社会中最无力的人承担的。他指出,美国法官的法律观在1780—182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把法律看作是产生于习惯和自然法的永恒不变的原则,而看成是可以促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该书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在美国亟需发展经济的时期,美国何以没有通过财税制度,而是通过法律制度来推动经济发展?其二,美国法官是如何变革普通法制度,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的?(注:参见霍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谢鸿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霍维茨分析的主要是私法。他使用的材料也主要是各州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对成文法的关注很少。另外,他几乎没有涉及联邦立法与联邦的作用。
在赫斯特和霍维茨时代,美国流行的是进步史学和一致论史学。前者的核心理论是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后者则认为美国的改革是在共同价值和法律框架内保守地进行的。赫斯特和霍维茨事实上都不赞成这两派的观点,并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两种史学提出了挑战。
三、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一)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理论意义
从政治哲学与法哲学角度看,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的纯粹道德/规范分析对立,为法学理论提供了历史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维度,使法律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和生活基础上,这体现了萨维尼的名言,其实法律并不存在,法律就是我们的生活。
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对古典社会契约论的冲击也很大。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作家,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假定存在一个自然状态,并由此出发论证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论证方式与“君权神授”的论证逻辑是一样的,不过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个人主义、世俗化和法律形式主义)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已。罗尔斯也只是修改了社会契约的逻辑前提,并从这一原点建构其正义理论。
对契约论最严厉的批判历来就是它的非历史性。这不仅仅体现在自然状态子虚乌有,更关键的是,这一假定存在明显的反历史倾向:因为契约论假定的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要订立社会契约,必须具备相应的权利观念、自由意思以及政府合法性观念。而这些都是政治和法律的产物,绝非野蛮人所能具有。可见,契约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得出特定结论而编造的历史—政治神话。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中假定的则是具体的、有机的国家。它反对抽象国家与法律,反对没有历史的国家与法律,认为这种国家是机械的、抽象的、没有“人影”的。例如,在社会建制方面,萨维尼明确反对启蒙思想家忽略国家和民族本身,而在国家和民族之外依据抽象的自然原则来构建社会的乌托邦观念。这种从历史的角度观照下的国家与法律,基本上摆脱了自然法的纠缠,在国家和法律的建制中,就可以用切实的行动代替虚幻的空想。
此外,自然法学和社会契约论与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则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背谬的是,在历史上,这种法律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经对自由主义政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英国和德国都如此。
这里还需要提及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法律文化多元化的关系。法律渊源单一论以及价值观一元论的社会生物学基础是,人类内在有渴求秩序、权威和统一规范的愿望。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要求通过大一统的国家法律,既实现和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实现人类在最重大事务上的价值统一。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强调人的具体归属感,这一思想渊源自维柯、赫尔德,后来又为伯林等人所继承。在法律中,它强调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和民间性,强调法律的真正渊源不是来自于立法者的理性,而是来自于民众的具体实践。它认为各民族、各地方的人们都可以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博弈出适合特定人们需求的规则,形成自发秩序。因此它赞成的是多元法律文化。可见,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法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种君临其他价值之上的绝对价值,各种可能相互冲突、抵牾的价值并行不悖,各种价值不可能同时实现,此种价值的实现可能伤害到彼种价值。
最后,单纯从法学方法论角度看,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揭示了法律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对于比较法的研究大有助益。它要求比较法的“比较”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范的比较上,还要深入研究制约法律规范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因素。这对国内法律研究也同样适用。
(二)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实践意义
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它对法律制度的历史约束条件的分析以及通过历史分析给今天的法律提供启示。它把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所简化的法律制度与法律实际运作之间的复杂因果链条展现出来了。波斯纳说:“法律是所有专业中最有历史取向的学科。”(注: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第149页。)但法律历史分析理论并不是要走向先祖崇拜,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揭示法律创新的界限和约束条件,为法律变革奠定基础。
在这一点上,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法律社会学方法有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分析的是历史上的制度,后者分析的是现实中的制度。
法律历史分析理论除了给我们带来历史材料外,还可以揭示我们想当然的制度背后的因素,改变我们的陈腐观念,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福柯对近代以降的刑罚改革研究,以及经济学史学家格瑞夫(Greif)对中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中法律的功能替代物的研究颇有代表性。(注:参见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88页。)福柯运用谱系学方法,揭示了监狱起源的真正原因,也揭示了各种“非话语实践中的权力机制”,来“对抗整体性话语”。(注: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edited by Colin Gord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83.)这种对制度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往往给我们以知识上的震惊,可以改变舒茨(A.Schutz)所谓的自然态度。格瑞夫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历史制度,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即寻找功能替代物并分析它的局限性,说明最后何以会被法律制度所取代。
最后以习惯为例来说明。在现代社会中,联系法律与历史的主要制度是习惯。而法律历史分析理论最能够揭示习惯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现代社会法律的两个发展趋势是:其一,法律数量也越来越多,可谓如“凝脂之密,秋荼之繁”。但在繁复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立法者的理性处处捉襟见肘,很难充裕自如。其二,现代法律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律几乎成了法律专业精英的禁脔,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大陆法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除广泛运用法律基本原则外,就是扩大法律渊源,适用习惯与法理。对习惯的尊崇体现了法律对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生活的珍视。习惯作为人类适应社会生活的智慧的结晶,会通过一代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得以薪火相传,并作为成员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人类社会平和、安定的源泉之一。现代法律对习惯的态度以事功精神为指导思想,习惯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它的实用价值。法律既规定习惯的法源地位,又限制习惯的法律效力。这既使法律(主要是私法)在法源上外接于社会习惯,扩展了法律的现实渊源,又使习惯被控制在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框架内。
(三)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局限性
对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历史法学派的批评。历史法学派遭受的最严厉的批判是它“无视人的取向”。在历史法学派的图景中,行为人是没有意义的。(注:参见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庞德法律理论的研究和批判》,《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历史法学派是否忽视了个人的能动性这一问题,至少对萨维尼等人而言,回答是否定的。在有关民族精神的问题上,萨维尼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坚持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法学家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或喉舌,法律其实是经由法学家而发展变化的。这至少为法学家在法律进程中的能动性打开了一个缺口。历史法学派最后经过萨维尼和普赫达发展为概念法学派也表明了这一点。
萨维尼和普赫达的主张无疑矫枉过正。我们可以从历史法学派与苏格兰启蒙传统的比较中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因为哈奇逊(Francis Hutcheson)、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等人关于社会演进的自发秩序的观点就认为他们忽视了个人的能动性,这种结论是欠妥的。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必须从历史中求得其合法性,因为行动者受历史的制约,历史对当前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制约结构,不是人的能动性可以完全改变的。与结构功能主义一样,历史法学派的观点确实更适合解释静态的结构,而不太适合解释动态的变革。但是,历史法学派守成的观点并没有排斥变迁。关键在于,它与各种激进主义理解的变迁的来源和动力不一样。变迁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法学派也承认这一点。历史法学派的主流观点认为,变迁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理性的创造或个人的天才,而是源于集体的博弈和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就是说,创造者是匿名的人。在法律的变革方面,它反对在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和欠缺审慎考量的情况下突然立法。它坚持法律变化的动因不能是外在强迫,而必须是来自于生活实践的内在变革需要。可见,历史法学派完全将法律的变革交给了生活本身,它只反对暴风骤雨式的法律革命,而不反对法律变革本身。原因之一,正如法谚所揭示的那样:“疑难案件生恶法”。在变革问题上,历史法学派好比是一个成熟的人,而变法模式则是冲动的年轻人。
四、结语: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与中国法律
中国自清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采取的一直是“变法”传统。虽然沈家本等人坚持会通中西、双向开放的文化立场,但“会通”的结果,大抵是中国法律文化屈从于强势的西方法律文化。有学者指出,“改革是绝对不能伤民心、败民风、悖民权的。”对于文化,必须“固本”,唯有“文化中国”得以保持,“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才可能建立起来。(注:参见夏勇《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5页。)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着眼点就是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国民”和“民族”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对民族神话、传说、民歌、民俗的探源一样,其主要目的是寻找法律中的“民情”。它强调法律的连续性和对传统的继承,而且这种继承不一定是“抽象的继承”(冯友兰语),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是直接的、具体的继承。
时下学界对中国法律废除亲亲相隐制度、禁放烟花爆竹、禁乞等规定的讨论都表明,法律不能违背人性的要求,也不能剥夺人们的习惯权利。法律历史分析理论的训诫就是,法律文化、语言、文字、风俗等,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标志之一,也是将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法律改革是必要的,但至少不能使我们丧失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改革者必须尊重社会本身的需要,相信人民的判断能力。“人民也具备自己做判断、做抉择的主体资格。这个资格是由天赋予的。”(注:夏勇:《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第3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应尊重历史、传统和习俗,是不是人民应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呢?
标签:法律论文; 萨维尼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 论法的精神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政治与法律论文; 维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