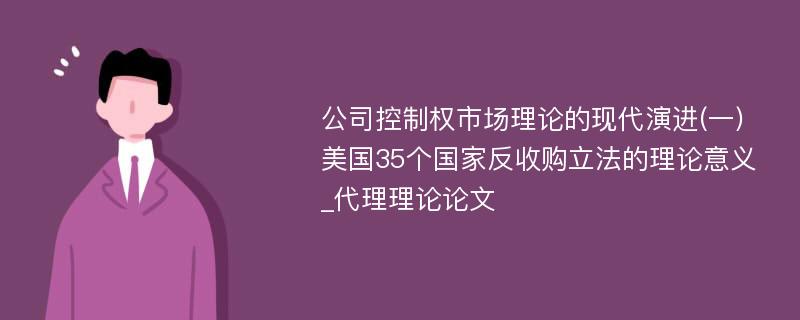
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现代演变(上)——美国三十五个州反收购立法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控制权论文,美国论文,意义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部分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流理论
一
从伯利-米因斯命题出发,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伯利和米因斯,1932;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法玛和詹森,1983)。在这一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中,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总是希望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管理公司。但是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而且代理人本身又有道德风险问题(霍姆斯特姆,1979,1982),因此,股东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控制机制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公司的控制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前者主要指公司管理者内部竞争、董事会的构成和大股东的监督等(威斯顿、郑光和侯格,1996);后者则指代理投票权竞争(Proxy Contest)、要约收购(Tender Offers)或兼并(Mergers)以及直接购入股票(Direct Share Purchase)(曼尼,1965)。(注:关于要约收购和兼并,詹森曾说明如下,要约收购乃直接向股东购入部分或全部股票,毋须征得公司管理者或董事会的同意;兼并则需通过与管理者协商,经董事会同意,再交股东大会批准。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2页。)詹森后来把公司控制机制按照公司经营中的四种“控制力量”重新分为:资本市场、法律/政治/法规制度、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及以董事会为主的内部控制机制。(詹森,1993),但詹森的分类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曼尼划分的内部和外部的框架里。而无论是以董事会构成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机制还是以代理投票权竞争、收购(要约收购或兼并)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机制,都会造成管理者相互之间争夺对公司资源的管理权,由此构成曼尼所称的公司控制权市场(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注:曼尼本人在其经典性的论文“兼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里实际上没有给定“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定义,他只是大致上说:“争夺公司的控制权有若干机制,其中三种最基本的方法为代理投票权竞争、直接购买股票和兼并,”以及“大量的兼并或许是该特定市场成功运转的结果。”见曼尼:兼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载《政治经济学刊》1965年,第73卷,第112—114页。詹森和鲁巴克后来给出了一个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定义。詹森和鲁巴克的定义如下:“我们将公司控制权市场(通常也被称作收购市场)看成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管理团队在其中互相争夺公司资源管理权的市场。”见詹森和鲁巴克:“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587页。)由于在委托代理关系里,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就体现在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上,所以曼尼提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公司的管理效率与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一种高度正相关关系,”(注:见曼尼:“兼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载《政治经济学刊》1965年,第73卷,第112页。)正如曼尼自己所说:“股票价格反映了管理的效率……除了证券市场,我们没有任何衡量管理效率的客观标准。”(注:见曼尼:“兼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载《政治经济学刊》1965年,第73卷,第113页。)因此,自曼尼之后,西方学术界就沿着曼尼的思路以“内部—外部控制机制”为分析线路,以“股票市场价格—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主线来建构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框架,并由此形成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主流学派。
二
从理论文献上看,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主流观点出现于六十年代中,从七十年代末起渐次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在八十年代最为盛行,成为最有影响的财务理论学派之一。主流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当时在罗切斯特大学(后转到哈佛大学)的詹森、麻省理工学院的鲁巴克、芝加哥大学的多德、哈佛大学的阿思奎斯和姆林思以及密执安大学的布雷德利。其中,詹森从1976年与麦克林合写出“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这些结构”的经典文献,为代理学说奠定理论分析框架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又相继发表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1983年)、“收购:传说与科学”(1984年)、“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公司理财与收购”(1986年)、“收购:它们的原因和结果”(1988年)、“公司经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利分配”(1988年)以及“褪色的公众公司”(1989年)“现代工业的进化、退出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失败”(1993年)等一系列鼓吹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观点的文章,被誉为是主流理论“最主要倡导者”。“他的论点与‘收购于股东有利’的主题一样颇多争议。”(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编者按),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09页。)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共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在由公司各种内外部控制机制构成的控制权市场上,无论是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还是外部控制机制中的代理投票权竞争机制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有收购才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控制机制。
重视公司控制的外部机制,轻视公司控制的内部机制,这一思维始终贯穿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的分析中。主流学派的这一主张沿自曼尼的观点,早先曼尼曾说过:“在许多场合下,看起来收购是三种公司控制方法里最为有效的一种。”(注:见曼尼:“兼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载《政治经济学刊》1965年,第73卷,第119页。)后来詹森把曼尼的观点进一步加以演化,早先詹森就发挥就:“让职业管理者按股东利益行事的内部控制机制,其运行过程太难以捉摸,也难以观察。”(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9页。)1993年,贵为美国财务学会主席的詹森又提出,在资本市场、法律/政治/法规制度、产品和生产因素市场以及内部控制制度这四种控制机制中,法律/政治/法规制度被詹森认定是“太迟钝”,产品和生产因素市场又反应“太慢”,而内部控制制度“从根本上失败了”,如此一来,在詹森眼中就只有资本市场这种公司外部控制机制了。(詹森,1993)所以,詹森在他的主席致辞里甚至给出了“现代工业的进化、退出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失败”的题目。在列举了通用汽车、IBM、通用电气、通用动力、通用矿业等大公司的失败事例后,詹森信誓旦旦地说“过去二十年表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在应付(技术、政治、法规和经济等因素,特别是缓慢增长和退出的要求上)变化的效率方面是失败的。”(注:詹森是从公司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与资本支出的生产效率两大方面来衡量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效率,然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为什么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会失败呢?詹森画龙点睛地指出原因在于处于内部控制机制核心的公司董事会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见詹森:“现代工业的进化、退出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失败”,载《财务学刊》1993年,第48卷,第831—8862页及附录。)
既然主流理论认定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失败了,那么公司外部控制机制的作用又如何呢?在公司外部控制的两大机制中,主流理论又进一步淡化掉代理投票权竞争机制所起的作用。代理投票权被认为是“介于董事会解聘管理人员和其它公司外部收购之间的一种惩戒行为。”(注:见多德和华纳:“论公司治理:关于代理投票权竞争的一项诠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405页。)当董事会无法对管理者施加压力时,反对派就会利用代理投票权竞争机制来试图更换现有的董事会,从而更换管理者。代理投票权竞争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代理投票权的征集,在代理投票权竞争中,股东被要求在两组互相“敌对”的董事候选人当中作出抉择,而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拥戴者会想方设法,四处征求股东的支持。对于不出席股东选举大会的股东,反对者和拥戴者则会征求其代理投票权的授权。二是表决制度,在美国公司里存在两类主要的表决制度,简单多数投票制和累积投票制,前者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分别开来逐个进行表决,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寡入选。该方法有利于持有过半数股权的股东控制公司的董事会;累积投票制则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一次性进行表决,候选人按照总得票数决定是否当选,所以,该投票制可以保护少数股权人的利益。不过,在公司控制权主流理论里,代理投票权竞争就被主流理论的代表人物如曼尼等认定为是“最为昂贵、最具不确定性和最少使用的一种办法。”(曼尼,1965)与曼尼同时期的另一位主流学派的早期人物伯利也曾很深刻地指出,代理投票权竞争只是“两大权力巨人(反对派和拥戴派)之间十足的勾心斗角”,两边都只是为了争夺公司的董事席位,而公司的现金流量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并没有关系。反之,一旦公司现有的董事或管理者动用公司资源卷入代理投票权竞争,代理投票权竞争反而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所以伯利嘲笑说,所谓代理投票权竞争会提高效率只是“一幅完全幻想出来的图画。”(注:见伯利:“公司体制的现代职能”,载《哥伦比亚法律评论》1962年,第62卷,第438页。)主流理论对代理投票权竞争所持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后来同样得到了法律经济学派主要领袖人物波斯纳的支持,波斯纳批评说:“公司法的传统学者过于强调公司民主而忽视了公司管理中的市场。由没有取得实质性所有权地位的个人进行的代理竞争非常近似于政治民主程序,但它是一种最不可行的接管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严重的外在性问题:这样的个人如何才能以伴有破产风险的利润补偿其竞争成本呢?”(注: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38页。)在曼尼和伯利之后,许多主流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多德、华纳、布雷德利等人都沿袭曼尼的这一思想。他们认为代理投票权竞争虽然代表公司资源在不同管理者之间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不会增加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多德和华纳曾提出一份实证分析报告证实曼尼的看法。在多德和华纳的报告里,在分析了从1962年7月至1978年1月间的九十六起代理投票权竞争案件后,他们发现“围绕代理投票权竞争日,公司股票确实出现积极的、显著的表现”,不过,这种表现仅仅只是“暂时的”,多德和华纳的结论与曼尼的观点是一致的。(注:见多德和华纳:“论公司治理:关于代理投票权竞争的一项诠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401—438页。曼尼的观点表述在他另一篇不太出名的文章里,见曼尼:“现代公司的‘严厉批判’”,载《哥伦比亚法律评论》1962年,第62卷,第399—432页。)詹森和鲁巴克虽然也注意到:“由于兼并和代理投票权竞争都会转移对公司资产的控制,因此要是公司资产能被放到更好的用途上,则很有可能代理投票权竞争的公告将与股东权益价值的增加相联系起来。”(注:见詹森和鲁巴克:“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621页。)但是,詹森和鲁巴克还是认定“就全部收益来说,这种(价值)修正的幅度相对的小。”(注:见詹森和鲁巴克:“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622页。)从这一逻辑出发,在他们的经典论文里,詹森和鲁巴克对代理投票权竞争也仅是轻描淡写,表明了主流理论对代理投票权竞争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上所起作用的轻视。
美国证券管理与交易委员会(SEC)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对代理投票权竞争机制的运用历来也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1935年,美国SEC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4条款下增订了代理投票权条款,即所谓的LA条款,该条款从信息披露和表决程序两方面对代理投票权的运用作出规定。1938年,美国SEC就代理投票权条款进行第一次修订,对投票权法则和投票人行为做出直接限制。1938年修正案的核心是要求代理投票权竞争中必须使用代理投票权申明书(即表14A),申明书里开列出代理投票权竞争中必须予以披露的十四项信息。之后,美国SEC从40年代到80年代里又对代理投票权条款反复修补,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内容涉及到代理投票权的时间(1940年)、程序(1947年)、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1956年)和信息披露(1982年)等等方面,由此可见,过去数十年间,无论是学术界从理论上,还是美国SEC从实践上对代理投票权竞争于管理者的控制作用上都是持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难怪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庞德很不客气地批评说:“过去三十五年来,关于代理投票权的法规体系禁止了信息沟通、协调及非正式的行为……因此,这种体系不仅无法解决投票程序中的集体选择问题,而且为通过市场自然力量来解决问题制造了障碍。”(注:见庞德:“代理投票权与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载《财务经济学刊》1991年,第29卷,第279—280页。)
这样一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流理论就一步一步地将曼尼笔下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框架的分析焦点集中到了公司收购问题上来。
第二,外来者对公司的收购非但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实际上还会给收购双方股东带来巨大的财富。
上述这段话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主流学派的领袖人物詹森的原话,(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0页。)也是主流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强所有者,弱管理者,这历来是主流学派对待公司收购的一贯态度。按照詹森的看法,现代公司虽然可以被看成是由各种平等的相关利益者所组成的,(注:这一观点也是詹森和麦克林在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詹森和麦克林指出:“公司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一种法律构造,它是一个通过契约关系框架把冲突各方引向平衡的复杂过程的中心。”见詹森和麦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这些结构”,载《财务经济学刊》1976年第3卷,第83页。)但股东是现代公司最重要的成员,他与其他相关利益者不能被平等看待。因为股东是公司剩余风险的承担者,他们当然要享有控制权,(注:詹森:“象所有的组织一样,公司将控制权赋予承担剩余风险的人,……由于股东要保证公司与组成人员的契约关系,他们要承担剩余风险……作为剩余风险的承担者,股东掌握公司的控制权。”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09—111页。)股东把这种控股权委托给董事会或管理者,自然是希望董事会或管理者能够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而董事会和管理者也必须要负担对股东的信托责任。詹森指出:“接受了这一假设,那么,当收购能够提高被收购公司所拥有股票的价值时,它在道理上就说得通了。”(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09页。)詹森不仅认为这样的论点在逻辑上说得通,他还接着说了一大通。詹森提出,有三点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收购会给公司带来好处。首先,詹森指出,股票价格是衡量收购对公司影响的最好方法,对于卷入收购事件的公司,无论是收购方公司还是被收购方公司的股票价格都会得到超乎寻常的提高。詹森举例说,围绕收购事件发生日,对于要约收购来说,收购方公司股票的超常收益率可达到30%,被收购方公司可分享到4%的超常收益率;而对于兼并而言,收购方公司股票的超常收益率为20%,被收购方公司股票价格虽然没能产生超常收益率,但也没有出现低于零的现象。(注:见詹森和鲁巴克:“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587页。同一份表还出现在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2页上。)詹森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如多德和鲁巴克以要约收购为分析原点,通过对1973—1976年间发生的172次典型要约收购事件的分析,他们证实,无论要约收购成功与否,在要约收购事件前的十二个月里,收购方公司的股东能获得相当显著的正收益率,而被收购方公司在事件发生日也都能从要约收购事件中获得相当大的超常收益率。前者为11.66%(收购成功)和8.44%(收购不成功),后者分别为20.58%和18.96%。(注:实际上,在多德和鲁巴克的文章发表之前,早期曼德尔科(1974)、艾略特(1976)和兰蒂格(1978)都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据说结论“自相矛盾”,既“不一致,也不可靠”,而且方法“很可疑”。见多德和鲁巴克:“要约收购和股东收益:一项实证分析”,载《财务经济学刊》1977年,第5卷,第368—369页。)多德本人三年后又提出另一份实证分析报告,这篇文章主要以兼并事件为研究对象,样本包括71次成功的兼并和80次不成功的兼并。多德发现,不管以后兼并是否成功,兼并方案的公布都能给被兼并方的股东带来超过13%的超常收益率,而在整个兼并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带给被兼并方股东的平均超常收益率更是高达33.96%。(注:见多德:“兼并方案、管理层的处置和股东财富”,载《财务经济学刊》1980年,第8卷,第135页。)多德且还明确指出:“这些超常收益率是兼并方案带来的直接结果,并不意味这些公司在兼并前表现出色。”(注:见多德:“兼并方案、管理层的处置和股东财富”,载《财务经济学刊》1980年,第8卷,第134页。)但是与前次和鲁巴克合写的文章不一样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多德发现兼并方股东从兼并方案实施过程中所得到的收益率却小于零,分别为-7.22%(兼并成功)和-5.5%(兼并不成功)。这一点连多德本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不能怪多德“迷惑不解”,认定被兼并方能够从兼并中得到相当的收益虽说是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的一致看法,主流观点有分歧的地方主要出现在关于兼并方是否能够得到收益这一问题上,(注:这一争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证明到底公司间的收购行为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以及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早先的一些学者就如曼德尔克、艾尔特等人就在该问题上争论过。例如曼德尔克认为收购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没有人能够获得超常收益率(曼德尔克,1974)。以后阿思奎斯(1983)、鲁巴克(1983)也持相同的看法。特别是鲁巴克,他在1982年和1983年连续发表了两份对两起轰动一时的收购案件的个案研究报告,在杜邦公司与西格姆公司和莫比尔公司争夺收购科诺壳公司一案里,杜邦公司虽然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从收购中得到的超常收益率却是-9.9%(约相当于七亿八千万美元),相反,西格姆公司和莫比尔公司股票的同期超常收益率反倒分别是+1.13%和-3.05%。在城市服务公司、西方石油、米萨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之间复杂的多角收购中,凡是被收购方都能实现正的超常收益率,如城市服务公司被收购后其超常收益率达12.5%(约相当于三亿五千万美元),而收购方公司,无论成功与否,超常收益率都不理想,如同为发起收购方,西方石油公司为最终胜利者,但其超常收益率实际上几近于零,海湾石油公司中途退出收购竞争行列,不过当初它宣布参与收购时便出现高达-17.6%的超常收益率(相当于损失十一亿美元的权益价值)。(注:见鲁巴克:“科诺壳收购案与股东收益率”,载《斯隆管理评论》,1982年冬季号,第13—33页以及“城市服务公司收购案:一项案例研究”,载《财务学刊》1983年,第38卷,第319—329页。)阿思奎斯对从1962年7月到1976年12月间211家成功被收购的公司和91家被收购不成功的公司做深入分析,他发现在被收购前480个交易日里所有这些公司都只能实现负超常收益率,但当公告被收购时,“目标公司的超常收益率极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注:见阿思奎斯:“兼并要价、不确定性和股东收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64页。)但是艾尔特(1976)发现兼并方是可以实现显著的超常收益率。库默和霍夫梅斯特(1978)、布雷德利(1980)、杰里尔和布雷德利(1980)以及爱克伯(1983a,1983b)也大都持这种看法。(注:这批学者所得到的数据分别为库默和霍夫梅斯特,+5.2%、布雷德利,+4.36%、杰里尔和布雷德利,+6.66%,爱克伯(1983a),+0.07%、爱克伯(1983b),+1.58%。见詹森和鲁巴克:“公司控制权市场:科学证据”,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592—593页表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阿思奎斯、布鲁勒和姆林斯指出:关键在于“兼并方股东没有收益可能仅仅只是反映出(多德等人)没能准确地衡量兼并的收益。”(注:见阿思奎斯、布鲁勒和姆林斯:“兼并方公司从兼并中得到的收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122页。)他们三人认为,必须要在控制住诸如收购方公司的规模、兼并的成功与否以及兼并发生的时间等因素后,才能准确地衡量兼并的收益,他们举例说,从过去兼并历史来看,在1969年美国联邦政府反收购立法前后,兼并发生的次数呈明显不平均分布。如果考虑到这些控制因素的话,按照阿思奎斯、布鲁勒和姆林斯对1963—1979年间数十起兼并案件的分析,“尽管在我们的样本里,平均超常收益率仅为+2.8%,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收购方公司从兼并中同样获利。”(注:见阿思奎斯、布鲁勒和姆林斯:“兼并方公司从兼并中得到的收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138页。据阿思奎斯、布鲁勒和姆林斯估计,+2.8%为1969年后(即联邦政府反收购立法前)的平均超常收益率,而在1969年之前,平均超常收益率还要再高出+2.6%。)其次,詹森认为,巨额的收购价格仅仅只是表示财富从收购方公司向被收购方公司的转移,被收购方公司仍然可以动用这笔资金来兴建新的工厂、购买新的设备或从事新的研究开发。钱并没有象反收购者所批评的那样“被浪费掉了”。收购中唯一消耗的资源是支付给律师、会计师、咨询人员和投资银行等的费用。这笔费用,据詹森估计,总数不及0.7%,(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3页。)远不能与收购所能带来的利益相提并论。第三,詹森争辩说,收购所带来的利益不是因为收购后所产生的垄断局面,而是得益于收购后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协同效应。詹森指出:“股票价格的有利变动显示收购后各方的总盈利能力提高了,有证据表明,这种盈利能力不是来自于市场份额的收购,而只能是来自于公司生产能力的提高。”(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3页。)詹森在这里所说的证据大抵上指的是主流理论的另外数位代表性人物如布雷德利、金和鲁巴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为什么收购会给收购双方带来超常收益率,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解释,协同效应假设和信息效应假设。协高效应假设认为,要约收购实际上反映收购方公司企图通过获取被收购方公司的控制权来利用被收购方公司的某些特定资源的行为,象规模经营、改善生产技术、增加市场份额、资产再配置等等,因此收购是一种提高价值的协同战略行为:信息效应假设则认为,被收购方公司股票价格的提高完全是因为收购过程中所包含的新的信息所致,这类新信息要么让市场认识到先前对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定价纯属“估价过低”,(布雷德利、德赛和金戏称为“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么让被收购公司管理者认识到应该要落实更有效率的管理行为(布雷德利、德赛和金戏称为“黔驴技穷”)。无论是协同效应假设还是信息效应假设皆认为,成功的收购对被收购方公司的股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协同效应假设强调只有当控股权真正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公司,被收购方公司的股东财富才会有实质上的增加,失败的收购不可能让被收购方公司的股东得到永久性的好处;反之,信息效应假设认为,即使收购方案被推翻,被收购方公司的股东仍然能够得到显著的超常收益率。布雷德利、德塞和金在一篇广受推崇的论文里曾就这两个假设做过实证检验。他们分析了1963—1980年间206家涉及收购事件公司(其中112家为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格行为,他们发现在成功的收购和不成功的收购之间,被收购方公司股票因收购行为所产生的超常收益率差异是“令人吃惊”的。(注:见布雷德利、德赛和金:“公司间要约收购背后的基本原理:信息效应或协同效应”,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183—206页。)鲁巴克在对杜邦公司收购科诺壳公司一案做了详细的分析后也得出结论说:“象杜邦公司—科诺壳公司兼并案里从垂直兼并中所得到的收益可能就是(公司股票)再估价的根源”(注:见鲁巴克:“科诺壳收购案与股东收益率”,载《斯隆管理评论》1982年冬季号,第22页。)
第三,长期来看,任何主张干预和限制恶意收购的主张结果可能会削弱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的形式,并导致人类福利的降低。
这段话也是詹森的原话。(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20页。)是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所发表的那篇长文的结束语。詹森争辩说,传说收购会导致更多的工厂被关闭,更多的工人被遣送回家,更多的管理者被解聘,但“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证据。”(注:见詹森:“收购:传说与科学”,载《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11—12月份,第114页。)他进一步指出,即使传说是正确的,也不应该限制或禁止收购,因为那样做才会阻碍新技术的采用,丧失潜在的规模经营效率,从而产生真正的社会成本,在总体上降低人类社会经济福利。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也称帕累托最优)原则历来是西方经济学家用于判别经济活动的标准。詹森要是没有守住这条防线,他就无法为收购做更多的辩解。不过,在这方面,詹森确实是拿不出什么证据。倒是哈佛大学的阿思奎斯和密执安大学的金为他提供了一份很有力的实证数据。阿思奎斯和金批评说,多德等人的研究只是从股东个人福利的角度出发,只看到收购给股东所带来的财富变动,而没有考虑到公司其他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能(多德等人)所报告的正超常收益率是以其他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注:见阿思奎斯和金:“兼并要价对当事公司证券持有人的影响”,载《财务学刊》1982年,第36卷,第1209页。)他们两人解释说,兼并本身也是公司的一项投资,公司的股东同样存在通过兼并增加公司现金流量的动机,当然兼并自身也提高了公司的风险,而公司的风险也要债权人一起来承担,所以,公司股东可能获得的超常收益是以提高公司债权人的风险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所得到的超常收益率正是转移了债权人的财富。那么,兼并到底会不会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产生财富的转移呢?阿思奎斯和金对五十家涉及兼并事件的公司展开分析,他们报告说,在兼并方案公布后,被兼并方公司债券和兼并方公司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0.495%和-0.178%。“这些结果证实兼并方案公布的结果并不会导致债券持有人财富状况太大的变化。”(注:见阿思奎斯和金:“兼并要价对当事公司证券持有人的影响”,载《财务学刊》1982年,第36卷,第1222页。)所以,阿思奎斯和金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们没有哪一项检验能提供证据说卷入兼并的债券持有人在兼并中有所得或有所失。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之间存在财富转移的现象。”(注:阿思奎斯和金:“兼并要价对当事公司证券持有人的影响”,载《财务学刊》1982年,第36卷,第1226页。)“仔细考查证券持有人的收益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假设,即债券持有人总体平均上没有获得正的或负的超常收益率。”(注:阿思奎斯和金:“兼并要价对当事公司证券持有人的影响”,载《财务学刊》1982年,第36卷,第1227页。)“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说兼并不会对债券持有人产生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之间也没有显而易见的财富转移现象。”(注:阿思奎斯和金:“兼并要价对当事公司证券持有人的影响”,载《财务学刊》1982年,第36卷,第1227页。在另一篇自己单独写就的文章里,阿思奎斯同样表达相同的观点,阿思奎斯说:“这份研究表明被收购方公司和收购方公司的债券持有人从兼并中既没有得到好处,也没有得到坏处。这也表示股东的收益不是转移了债券持有人财富的结果,显而易见地是真实收益的结果。”见阿思奎斯:“兼并要价、不确定性和股东收益”,载《财务经济学刊》1983年,第11卷,第82页。)显然,阿思奎斯和金比多德等人看高了一层,他们既考虑到股东的收益,又照顾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益问题。而且他们的结论又同样坚定地支持了詹森等主流观点。
三
在以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为代表的美国三十五个州反收购立法之前,上述代表性观点不容置疑地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流理论。必须指出的是,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之所以盛行一时,另一方面仍是因为它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格罗斯曼、哈特以及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现代企业理论、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等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上的各种备选诠释和论证。(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学术界有多项定义,我们这里采用的是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的《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埃格特森的《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的提法。埃格特森在他所著的书里第11页有段话说得最为清楚。埃格特森说:“这一流派目前仍没有正式广泛的名称,尽管对于这一领域的各种研究被贴上诸如产权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新产业组织理论、新比较经济体制或法与经济学等各种各样的标签。我们将这一流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内容繁复庞杂、博大精深,举凡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收购要价、免费搭车问题和企业理论”、威廉姆森的“作为一种反托拉斯辩护理由的经济效益:福利权衡”、“现代公司:起源、进化和特征”以及斯蒂格勒的“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等文献都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注:听听斯蒂格勒的名言就不难想见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兼并是如何的钟爱,又是如何强调其重要性:“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见斯蒂格勒:“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载《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3页。)现代公司控制权市场主流理论的另一大理论基础是以波斯纳法官为领袖人物的法律经济学中的保守主义法律经济学理论。虽然“经济学被不断广泛地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即法律经济学的复兴是“20世纪后25年”的事(注: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第三版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页。),但由于该学派不只是仅仅停留在法学和经济学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理论研究上,而且是深刻改变了法学家、律师和法官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机制运行效率判断的传统行为哲学,因此,法律经济学迅速地“引起不断增长的学术兴趣和实践兴趣,使文献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发展”(注: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第三版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页。)。法律经济学有两大分支,一是由波斯纳为权威的保守主义观点,另一支是以艾克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两大角色—股东和管理者的争斗中,以波斯纳法官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法律经济学家坚定地站到了股东的一边。波斯纳曾这样解释过他的立场,股东与债权人在公司收益的获取上是“存在着差异”,股东的权益“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理人员如何认真将企业收入的适当份额分配给股东……息息相关,”股东比债权人更容易因为管理者的“不忠诚”而受到损害,所以,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的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足以促使股东保护措施。而反收购的“辩护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注: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35—539页。)甚至当“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这西方经济学两大原则在公司收购中出现矛盾时,波斯纳也宁愿放弃“帕累托最优”的传统原则,转而采取“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保护股东利益。(注:按照波斯纳的看法,法官制定法律(普通法)的依据既可以是帕累托最优原则,也可以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原则,两者是可以互相取舍的,所以他用了“或”这样一个词。波斯纳进一步指出,如果法律给公司收购的有效运用既设置了障碍,而且又降低了公司合并的效率,那么,法律就是“不幸的”。他还认为法官制定法律的依据应该法律是否是“一种能造成有效率(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908—909页。)所以,麦乐怡把波斯纳称为“最为突出的保守主义者”。(注:麦乐怡嘲笑说,按照波斯纳对“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理解,波斯纳还认为奴隶制度是可以许可的,因为对奴隶制度的分析应当基于效率性而不是基于道德。”见麦乐怡:《法与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页。)当然如果从深层次思想上分析,那么,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思维角度鼓吹公司收购,其中最本质上的理由仍是在于公司收购的精神符合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称保守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未完待续)
标签:代理理论论文; 企业控制权论文; 反收购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美国州论文; 要约收购论文; 詹森论文; 经济学论文; 股票论文; 美国公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