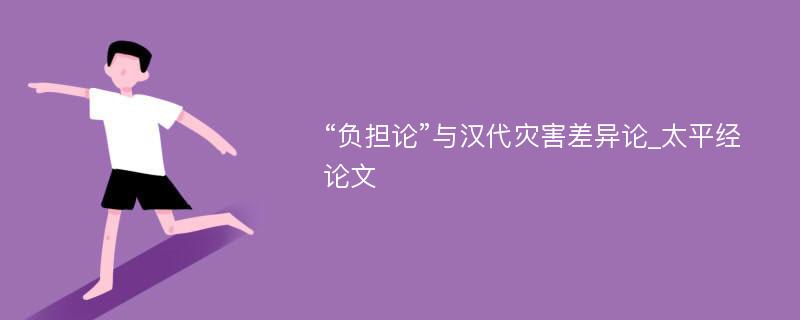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承负说论文,灾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B9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2—0029—08
“承负说”作为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提出的一种基础理论几乎贯穿于整部书中,《太平经》的理想即是“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1](p57)。因此要论及《太平经》便无法对“承负说”予以忽视。有学者很早就意识到“承负说”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道教立教的理论根据”[2](p120),这就指出了“承负说”在《太平经》中的地位。然而,由于“承负说”仅见于《太平经》中,这一仿佛昙花一现即消失的理论,使学界对其思想渊源充满了迷茫,先后出现几种不无矛盾的观点。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承负说”是在《易·文言·坤卦》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认为这种观点“为中土典籍所不尝有”,怀疑它是“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创造[3]。然而后来胡适在一封致杨联陞的信(1952年2月7日)中曾谈到:“‘负’与‘承负’、与‘报’的观念绝不相同,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指出‘负’与‘承负’与《易·文言》的‘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的话也没有关系。”[4](p156,157) 遗憾的是胡适对此并没有作进一步探讨。再一种观点是基于考古发现而来,即认为云梦秦简《日书》中的“负”及东汉镇墓文中的“重复”实际上即是“承负”,“承负说”应是缘起于秦汉时的一种解谪方术[5]。以上意见对正确认识“承负说”无疑均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承负说”的阐释仍然不够深刻,因为仅从思想传承上来说明并不能完全认识问题的本质,还有待于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察。与当时绝大部分著作相同,《太平经》首先是一部救世之书,作为《太平经》的基础理论,“承负说”固然有着某种思想渊源,但它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矛盾的产物,其出现与汉代灾异论盛行及其具有极大颠覆性息息相关,抛开这一点来谈论对“承负说”的认识是不完整的。笔者拟从灾异论的角度对“承负说”作进一步阐述。
《太平经》原始文本问题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经》(即于吉的《太平清领书》)成书于东汉中后期,其后散佚,至明英宗编撰《正统道藏》时本经仅余七十七卷存世。另外唐末道士闾丘方远有《太平经钞》十卷,纂辑《太平经圣君密旨》一卷,其中也保存有《太平经》部分原始内容。今人王明在以上三者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其他典籍中所注所引的《太平经》文字,并详加校勘、考证,撰成《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了一百七十卷内容的原貌①。本文所依据的基本版本即为《合校》。然而,敦煌写本《太平经》残卷的发现证明《太平经》中掺杂有后人的东西,而“承负”说出于汉代则基本无争议,故引文以《合校》为准。
一“承负说”与上古报应思想
“承负”一词首见于《太平经》,其具体含义有多种,这一现象曾被许多学者注意到,如汤一介[7](p366)、陈焜[8]等。日本学者的新近研究为神冢淑子在其《六朝道教思想的研究》(创文社,1999年)中进行的相关讨论。总的来看,“承负”的主要含义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意义上的善恶报应,这是“承负”的基本含义;第二类主要是基于政治层面而言的,是《太平经》对两汉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提升与扩展。先说第一类。
中国上古时期即有自己的善恶报应思想,如《尚书·商书·伊讯》、《国语·周语》、《韩非子·安危》等文献均有善福恶祸一类思想的内容。表面上看,这种思想与佛教的善恶报应非常相似,实则不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印度佛教善恶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业力’,中土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上天’、‘上帝’,说的是‘上帝无常,作善降祥’,‘天道赏善罚淫’。这种报应的力量,一种是自力,一种是他力,一种是内力,一种是外力。”[9] 此言颇是。佛教的善恶观与其业报轮回说紧密相连,而上述中国的善恶报应是一种与天人感应论紧密相关的思想,它认为人为善或为恶会招致上帝或天同类的报应,其差异性很明显。除此之外,中国上古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善恶报应思想,最早见于《易·文言·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10](p167) 这种思想在为善可以得福、为恶可以致祸的传统认识之上,进一步提出祸福可以积累,甚至可以为子孙所继承的观点,与佛教报应论的差异更为明显。这种善恶报应思想可能在战国时已经流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前四篇佚书抄本,唐兰先生认为即《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黄帝四经》,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公元前4世纪[11]。其《称》篇中有多处与《易》中相似的言语,如“天有环(还)刑,反受其央(殃)”[12](p91)、“有宗将兴,如伐于□。有宗将坏,如伐于山。贞良而亡,先人余央(殃);商(猖)阙(獗)而栝(活),先人之连(烈)”[12](p92) 等。其中后两句又见于刘向《说苑·谈丛》篇,其文作“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余烈”[13](p387)。据此,学者认为,“《谈丛》一篇系采自当时流行在社会上各种典籍中的‘警句’而成,上引自当出乎《称》篇”[5]。这种判断是可信的。相似的思想又见于王充《论衡·感类篇》:“阴阳不和,灾变发起,或时先世遗咎。”[14](p786) 同书《辨祟篇》还有:“我有所犯,抵触县官,罗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遗殃。”[14](p1011,1012) 题为西汉刘向撰的《列仙传》亦云:“河间王患瘕,买药服之,下蛇十余头。问药意,俗云:‘王瘕乃六世余殃下堕,即非王所招也。’”[15](p76) 另外,有学者认为东汉时形成一种严格的死生二元对立的招魂葬法,这种葬法的目的是为解除死者可能殃及生人这一灾厄,东汉镇墓文材料中称这种灾厄为“重复”之谪。此“重复”之法实由先秦时期的“复”发展而来,它们都是建立在死者魂灵神化而为鬼作祟于生人的观念基础上,这一观念与《太平经》中的“承负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5]。应当说,以上均为理解“承负说”提供了启发意义。
西汉后期至东汉,由于社会不稳定,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在现实中往往会使人感到困惑,行善不得善、行恶不得恶,甚至行善得恶、行恶得善的现象时而发生,这样势必造成社会混乱:“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1](p22) 《太平经》试图对现实中的善恶错乱现象进行解释,于是提出了“承负”的理论,在《解师策书诀》中明确解释了承负的含义:“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为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1](p70) 类似的观点还见于书中多处。笔者以为,这是“承负”最基本的含义,书中其他所有概念的延伸均是据此而来。“承负说”认为为善为恶的个人行为不仅对个人本身产生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将传及子孙后代:“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1](p22) 可以看出,承负与前所述《易·文言·坤卦》之思想确实有着相当的渊源关系。魏晋之际,承负思想得到继承与发扬,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有这样的记载,人身上有司过之神,人每犯一罪司命则夺其算纪,“若算纪未尽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诸横夺人财物者,或计其妻子家口以当填之,以致死丧,但不即至耳。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终遭水火劫盗”[16](p126)。此类看法在其他道经中也比较常见。
有必要指出,承负的这种含义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命定说”不可混淆。战国出现的“命定说”至汉代时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以“三命说”影响比较大。《孟子·尽心上》云:“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注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日随命。”[17](p879) 王充《论衡·命义篇》对此有详细解释:“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日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14](p49,50) “三命说”同样是传统善恶报应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但其与“承负”则绝不相同。命定说在《太平经》中亦有所反映,如《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曰:“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不能为贵也。”当真人问天师道是否可以学时,天师说:“有天命者,可学之必得大度,中贤学之,亦可得大寿,下愚为之,可得小寿。”[1](p289) 这类话对于传教是很不利的,这或许是《太平经》成书于多人之手、造成观点驳杂矛盾的结果。《太平经》既然想成为一服救世良药,其基础理论“承负说”便须是一种普世的解释系统,“承负说”中便不能有“命定说”的容身之处。《太平经》中有“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1](p22) 之语,这正是对“命定论”的否定。由此看来,那种认为承负与命定说“都是建立在命定论的命运观之上”[5] 的看法似有不妥。
二“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道德说教并非“承负说”的最终目的,以上善恶报应思想仅是《太平经》“为百姓解承负之过”而开的一服药方。通观《太平经》,“承负”的第二种含义格外引人注目,此即“为帝王解承负之厄”,是一服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处方药。它试图对汉代社会危机出现之根本原因提出一套新的解释系统,而这套解释系统与当时盛行的灾异论具有重大关联。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汉代的灾异论。
关于祥瑞与灾异为政治兴败之征兆的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即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慨(《论语·子罕》)。至《吕氏春秋》这种思想得到系统阐释,其《应同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18](P677) 于是它罗列了黄帝、禹、汤及文王时出现的种种瑞兆。祥瑞现,圣人或治世出,相反,若有灾异之事发生,则预示了社会的某种变乱。如《春秋》中的灾异现象特别丰富,汉代京房曾云:“《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19](p3162) 荀子特别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20](p313) 汉兴,这类灾异思想被继承,陆贾《新语·明诫》云:“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晲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21](p155) 因此当出现日食时,吕后以为这是上天谴告自己专权,“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22](p404) 三年后又连续出现两次日食,文帝立即下诏,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22](p422)
在汉代之前,灾异思想多与星占学联系在一起,其时出现的天象灾异并非仅仅针对国君,亦未必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但有一种趋势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渐趋明显,“如果‘天变’——即上天因人事黑暗而以呈示星占凶兆发出警告——发生,帝王或国君就应勇于自责,主动承担责任”[23](p208),正所谓“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18](p479)。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汉代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作用与先秦古籍中重、黎“绝地天通”的神话极其相似。对“绝地天通”一事杨向奎先生指出:“那就是说,人向天有什么请求向黎去说,黎再通过重向天请求……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24](p164)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可以说是一句彻底的“绝地天通”之宣言,既然天子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唯一资格,那么作为交通手段之一的灾异祥瑞现象便只能是针对皇帝一人。至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来,这种思想被整理成一套严密而有系统的理论——“灾异谴告说”,并逐渐成为汉代的正统神学思想。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9](p2498)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25](p318,319) 董仲舒大大强化了灾异与皇帝的关系,“通过把皇帝的统治与天联系起来,董仲舒重新建立了据称在周代诸王与天之间存在的一种纽带;就帝国统一之前不久的诸侯国国王而言,他们则没有,也不能要求取得这种纽带。奇异的或令人厌恶的事件,例如日蚀月蚀、地震或彗星的出现,就成为对皇帝的一种警告。”[26](p760) 顾颉刚先生亦言:“在这一点上汉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们毕竟有比商、周进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来整理灾异的现象,使它在幻想中成为一种极有系统的学问。”[27](p25) 既然灾异皆因皇帝而起,“皇帝应该很快地认识到这个警告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他有效地做到这点,他将结束混乱或不平衡,和弥补缺乏和谐的状况。”[26](p759)
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每当有非常态的社会或自然现象——灾异——发生,便意味着皇帝在某方面存在问题需要反省或改正,随之而来的便是皇帝下罪己诏、策免大臣、诏举贤良、整顿吏治、大赦天下等一系列措施。在汉代,这种现象特别突出,诸位皇帝先后发布了多达58次的罪己求言诏书(西汉28次: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次:光武4、明3、章3、和4、殇1、安5、顺4、质1、桓5),试图以此消弭天子与上天之间的紧张关系[28]。然而灾异论是一把双刃剑。在汉代前期,由于社会状况比较稳定,灾异论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自检行为对社会的稳定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措施亦能够较好地收拢民心。然而当社会处于失控的边缘,大量正常自然现象亦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灾异。如顾颉刚先生所言:“但试想,汉的疆域多大;这样大的地方,地文上不当有些变态吗?这种事,武帝时何尝没有;只是那时的社会正沉醉在祯祥的空气里,大家不提罢了。”[27](p27) 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民众对现存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乃至完全否定。新近研究成果业已证明,灾异论确实对汉代政治秩序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灾异论导致的是对现实生活和世界的不可靠性和终末性的认识,它在政治思维中的反映,就是对汉代国运的怀疑和相应而来的诸如‘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成顺天命’的思想”[29][30](p86~121)。灾异告诉世人刘汉的国运要走到尽头了,大规模的原始道教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书·李寻传》记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或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19](p3192) 可见,“更命”是灾异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此之时,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提出种种医治乱世之良方妙药,《太平经》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应当注意,《太平经》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有本质的区别,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讨论。需要强调的是,《太平经》首先是一部救世之书。倘若将早期道教仅仅看作为宗教,便斩断了认识历史真实的关键视角② 《太平经》的作者深刻认识到灾异论对社会的巨大破坏性,适时地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承负说”第二种含义是针对灾异论有感而发。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行善或行恶均可以传承给后代,那么推广开来,国家之“灾异”是否必定是时君失道之结果呢?显然,《太平经》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对社会危机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试举几例:
凡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养,悉失其纲纪,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令誊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故此书直为是出也。(《试文书大信法》)[1](p54,55)
本道常正,不邪伪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师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养之正道,遂相效学,后生者日益剧,其故为此。积久传相教,俱不得其实,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灾变万种兴起,不可胜纪,此所由来者积久复久。愚人无知,反以过时君,以责时人,曾不重被冤结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虽有万人之德,独能如是何?……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虽然,非下古人过也,由承负之厄会也。(《五事解承负法》)[1](p59,60,61)
中古以来,多失治之纲纪,遂相承负,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实由君臣民失计,不知深思念,善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处深隐,四远冤结,实闭不通,治不得天心,灾变怪异,委积而不除。(《三合相通诀》)[1](p151)
非常明显,“承负说”继承了先秦时期颇为流行的历史倒退论,即上古、中古、下古由治而乱,然而先圣们并未对此有详细解释,《太平经》的作者首次赋予了这种历史观一种独特的阐释:它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1](p70)。“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1](p61)。由于小失得不到纠正,集腋成裘,长此以往,各类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从而造成最终的社会危机。可以看出,《太平经》在这里推广了“承负”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先人的过失同样也会承负给后代,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因此不能让帝王一人承担罪责,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1](p124),但现实是“百姓适知责天,不知深自责也”[1](p125)。
此外,《太平经》的作者还列举了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承负现象,《五事解承负诀》集中讨论了这种泛化了的承负理论。一是人为天地“承负”:“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元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其下根不坚持地,而为大风雨所伤,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南山有毒气,其山不善闭藏,春南风与风气俱行,乃蔽日月,天下彼其咎,伤死者积众多。”[1](p58,59) 这些论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承负”为天地万物共有之性质,既增强了“承负说”的说服力,又大了承负对象的外延。与前面普通信众与帝王的承负相一致,诸如此类的承负均具有逆向思维的方式,在向以前追溯的过程中找出时下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承负”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确实有着相似的思维逻辑,而与灾异论截然不同。
尽管《太平经》提出社会承负观,但是“承负,,并没有否定灾异思想本身,灾异思想于《太平经》中随处可见。“承负说”的意义在于对两汉灾异论、主要是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的重要修正:首先它打破了仅仅帝王对灾异负责的特权,指出所有人包括死去的先人均对时下的社会问题负有责任,这就大大缓解了皇权的政治压力,使其统治合法性与灾异说并行不悖。汉代非议“灾异谴告说”者不仅《太平经》一家,著名思想家王充即是其一,但王充的批判思想是以元气论为基础,与“承负说”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其次,既然灾异非帝王一人造成并对此负责,解铃仍需系铃人,要解决承负必须“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1](p191)。由此,使得《太平经》顺理成章地提出一整套全方位的社会改良措施,“承负说”为上自帝王、下自布衣普遍接受《太平经》准备了理论前提。由此而言,《太平经》所说的“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之言确是发自肺腑,“承负说”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地位确实不容怀疑。
由于种种原因,《太平经》之理论并未被东汉政府所采纳,因而其改良措施亦无法得到大规模实施。然而无法否认,“承负说”将会产生两重社会功能的理论意义确实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三《太平经》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及张角、张鲁
西汉后期,更命之说甚炽,早期道教尤甚。前引《汉书·李寻传》曾言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扬汉家终结说。甘忠可将此具有巨大颠覆思想的经书传与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人,引起中垒校尉刘向的注意,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将其下狱致死。夏贺良等人遂私下秘密传授。哀帝立,夏贺良得李寻相助待诏黄门,数次受到哀帝接见,反复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19](p3192) 然而夏贺良之“更命说”与甘忠可等相比已作了重大妥协,即更命不更人,皇帝照做,仅将年号等形式因素变更一下即可。哀帝信以为真,上演了一出与先秦燕王哙禅位于相国子之如出一辙的政治闹剧。哀帝于建平二年改元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亦改以百二十为度,大赦天下,以更受命于天。哀帝改制诏书云:
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9](p3193)
然而不久,夏贺良即因“欲妄变政事”而被诛杀。自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至哀帝改元,其思想根源皆在于“更命说”,认为若要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皇帝必须更受命,否则社会将走向崩溃,这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核心思想。哀帝改制诏书及事后所下诏书亦可佐证夏贺良所言。很明显,哀帝接受了甘忠可的思想,认为若不更命则自己无以自新、无以续存,天理难容,只有“改元易号”才能使“百姓获福”、“永安国家”。“更命说”毫无疑问是灾异论发展的结果。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提倡的这种“更命说”与《太平经》的“承负说”在思想主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更命说”认为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必须由更受命才能化解矛盾③;而“承负说”则认为社会矛盾是由来已久所有人的罪过承负的结果,必须所有人负责。也许两书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太平经》抛弃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更命说”,而代之以看起来颇为“温顺”的“承负说”,如此,其所受到的政府待遇就迥然有别。《后汉书·襄楷列传》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31](p1084) 宫崇献上《太平清领书》后,虽然未被政府采用,但仅仅被称为“妖妄不经”,也即不合儒家经典,还是受到重视被政府所收藏。至桓帝即位,襄楷再次进献《太平清领书》,并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31](p1081)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桓帝接受了《太平清领书》,但亦未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检索相关史料,灵帝在位时尽管因灾异频繁裁撤高官,然而却未发布任何罪己诏书,这在汉代皇帝中极为反常④ 以上两次献书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献书者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绝不是偶然的,更非帝王个人喜好或汉代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所能解释得了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之主旨在于更命行太平,而《太平经》之主旨在于承命行太平,其要义之改弦更张,其中“承负说”起了根本性的作用。⑤ 如此,“更命说”在理论上已被釜底抽薪。明了此义,汉廷对《太平清领书》之宽容以及部分朝廷要员最初对原始道教之包庇的原因可多一重视角来理解,同时张角与张鲁之本质不同亦使人豁然开朗。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记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31](p2299) 又《孝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31](p348) 由此可见,张角骨子里装着更命说,与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对《后汉书·襄楷列传》所言“张角颇有其书焉”(即《太平清领书》)之语不能过于相信,这一点学者早有清醒认识。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称:“张角的太平道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采用《太平经》的基本思想……太平道抛弃了《太平经》的和平改革路线,实行了暴力革命的路线。”[32](p35) 再如杨寄林所言:“从整体看,它(指《太平经》)并未给张角及其徒众部众提供批判的武器。张角及其徒众部众为了进行武器的批判,只是于己有用地择取了本经中动人心弦的几个关键字眼和极大公平均平、疗疾方术等实质性的内容,而对本经所极力宣示的断金兵、禁盗贼、大顺好生、使火君转危为安等训条,则是彻底否定悉予抛弃的。这在根本立场上同本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从反面证明它(指太平道)和《太平经》在本质问题上是分道扬镳的。”[33](p129)
与张角相比,张鲁受《太平经》的影响更深。虽然同为早期道教,但张鲁终其一生未有如张角般激烈的更命主张,更无革命性行动,这一点在他投降曹操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据《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挥师征汉中,至阳平时张鲁便欲举汉中投降,后为其弟卫所阻。及至阳平陷落,张鲁部下欲焚烧宝货仓库。张鲁又阻之,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31](p2437)。张鲁的投降及曹魏对待张鲁的态度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张鲁的宗教持温和态度这一点不可忽视,仅仅将此看作是《后汉书》对张鲁的溢美之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今人的研究表明,张鲁五斗米道的思想与《太平经》有密切关系,“其祷祝符箓,以及它统治汉、川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很多都和《太平经》的主张相似”[2](p148)。不仅如此,五斗米道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与《太平经》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渊源关系,饶宗颐先生对此有深刻见解:“《想尔》此注,大部分即以《太平经》解《老子》,故与韩非以来说《老》者,截然异趣。”[34](p90) 《想尔注》多处主张维护皇权,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句注曰:“狂或(惑)之人,图欲篡弑,天必煞(杀)之,不可为也。”“其不得已”句注曰:“国不可一日无君……非天下所任,不可妄庶几也。”“承负说”在《想尔注》中亦有反映,如“其事好还”句注曰:“以兵定事,伤煞(杀)不应度,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是谓微明”句注曰:“故诫知止足,令人于世间裁自如,便思施惠散财除殃,不敢多求。”这都是承负的第一层含义。再如“化如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句注曰:“失正变得耶(邪),耶(邪)改得正。今王者法道,民悉从正,斋正而止,不可复变,变为耶(邪)矣。观其将变,道便镇制之。检以无名之朴,教诫见也。王者亦当法道镇制之,而不能制者,世俗悉变为耶(邪)矣,下古世是也。”[34] 这段内容与“承负说”对历史三段论的解释颇为相似。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太平经》对张鲁的政治行为确实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承负说”渊源有自,但作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思想,它是针对汉代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一套原创性理论。它的产生受到汉代灾异论的重大影响,并对灾异论做出重要修正。一方面,“承负说”提出了一套改进了的善恶报应思想,为其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另一方面,“承负说”又为风雨飘摇中的东汉王朝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危机解释理论,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因此,“承负说”确属《太平经》的基础理论,是《太平经》原始文本之基本内容。更早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更命”,至《太平清领书》中“更命”已经被改造成了“承负”。“承负说”与“更命说”的政治倾向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太平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没有被汉帝国所接受,然而它仍然受到汉朝宫廷的温和处理,这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呈上后当事人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张鲁政权对《太平经》的真正吸收,使他与张角在思想观念和行为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区别,这也是他的政治结局较张角不同的重要原因。《太平经》绝不仅仅是一部宗教运动著作,它提出的政治理论有着很强的针砭时弊的特点,因而在汉代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它对汉代历史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⑥
(本文受到恩师姜生先生悉心指点,日本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俊先生亦仔细阅读了文章原稿,作了详细批注,并提供了日本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 除王明外,日本学者对《太平经》的版本问题研究较多,如吉冈义丰的《道教与佛教》、福井康顺等监修的《道教》以及前田繁树的《初期道教经典的形成》等对此均有专门讨论。《道教》认为:“现行本中大概是既有反映汉代思想的文章,也有元代以后增入的文章。”[6](p93)
② 关于《太平经》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说是农民起义的经典,有的说是宗教著作,有的说是政治著作,全面一点的认为它是一部宗教政治著作。实质上,所谓“宗教”、“政治”等今人之学术体系甚至概念本身均系西方舶来品,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异性,用这些理论进行研究必然会有相当的弊端。以《太平经》为例,尽管该书在汉代之后仅为道教所有,但在汉代它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治世典籍,其理论绝非一个道教便可容纳得了的。
③ 对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革命思想日本学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太平清领书》)简称《太平经》是更往后的事,形成之初称为《太平清领书》。这是为了同西汉末甘忠可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相区别。甘忠可之书含有可为王莽篡位所利用的内容。”[6](p91,92) 实际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的“更命说”不仅仅为王莽所利用,张角等均为其实践者。
④ 现有资料表明,后汉诸帝没有发布罪己诏书的仅有冲帝、灵帝与献帝三位,其中冲帝两岁即位,三岁驾崩,献帝即位时已不能控制朝政,只有灵帝在位时间较长(168~189年)。
⑤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道教组织均无意建立一个农民政权或道教领导的政权,甚至连起义后的张角也是如此,如著名汉学家康德谟(Max Kaltenmark)即这样认为(“The Ideology of the T'ai P'ing ching”,in H.Welch & A.Seidel,eds.,Facets of Tao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这类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过分注重于道教组织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彼此的异质性,正如张角与张鲁的区别一样。
⑥ 如恩师姜生先生在其《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29] 一文中首次提出汉代末世论说,认为两汉时期出现的终末论意识与运动本自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另外在姜生先生与汤伟侠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第八章对此亦有详细讨论[30]。由于笔者在本文中提出《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与《太平清领书》核心思想相异的观点,因而对“承负说”与末世论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这对研究汉代政治社会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