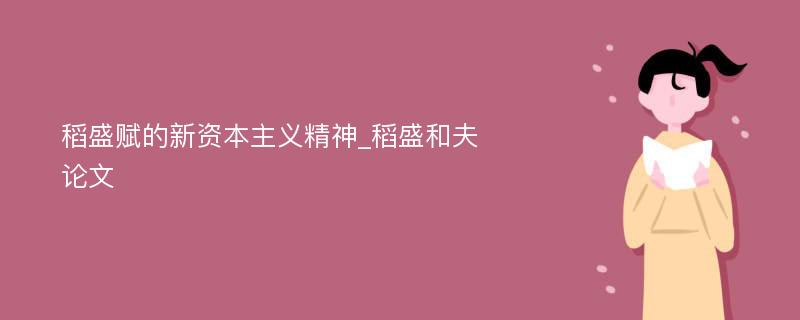
稻盛和夫的新资本主义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探求资本主义新精神,力主改造现在的资本主义,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时所具有的伦理。
稻盛和夫说,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当然,经营者追求利润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追求和利用利润。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赚钱成了唯一目的,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无节制的经营活动,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稻盛和夫以其博大的胸怀和使命感著书立说,意在唤醒人类的理性和智慧,阻止人类文明的崩溃。在《回归哲学》中,稻盛和夫阐述了他的“回归”思想主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倡导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平衡,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形成良性循环,即共生循环思想。其二,倡导道德、伦理回归,要注重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的教育,建立伦理的、道德的资本主义。其一笔者已有行文论及,其二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领域。
稻盛和夫在《回归哲学》中写道,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所提倡的以耶稣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勃兴时代,就存在过基于严格伦理观的资本主义。但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这种耶稣教式的严格的伦理观逐渐淡薄了,本来有利于社会的资本主义,最后变成了只是为了赚钱的资本主义。所以,可以考虑先“返回到其原点”,然后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比初期时更好的“新资本主义”。只是还原还不会有进步,从颓废的现在返回到原点,当然只是暂时恢复基本形态,然后要向“新资本主义”前进。[1](P19)稻盛和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令人思考的问题。那么,“原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通过返回“原点”的途径能否消除现在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呢?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被誉为经典名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原点”时期宗教伦理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韦伯认为:耶稣教蕴育着资本主义精神。而谋利、获取、尽可能多地赚钱,这种冲动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冲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贪得无厌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新教伦理所规范的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缓冲人类的不合理的冲动。”[2](P15)当然,资本主义与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不断获得新的利润。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不能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注定要消亡的。韦伯把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的精神归功于新教所唤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把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克尽职守的美德也归功于禁欲主义新教所倡导的伦理。新教徒崇尚进取和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认为把时间损失在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时,也是要受道德谴责的,不劳者不得食,如果一个能工作的人行乞,那就不仅犯了懒惰之罪,而且违背了新教徒的仁爱天责。
所谓的新教,是16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新教反对封建天主教会内的贪污、腐化,要求建立廉俭教会,主张灵魂得救要靠个人的虔诚信仰,不需教士的监督和干预。受新教影响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受天主教影响的南欧、东欧的资本主义则发展缓慢。新教伦理具有抑制世俗欲望冲动的一面,主张合理地追求利润,那种为了获利而获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然而,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西欧、北美地区,也是最先不受新教伦理约束的,贪婪地追求利润、无情地谋取财富。这种类似的现象在东方的日本也发生了,尽管在时间上要晚得多。
稻盛和夫在《回归哲学》中说,日本江户时代有着土农工商的阶级制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属于最低层的阶级。可是,江户中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说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话:经商并不是卑劣的行为,获取利润是很好的事,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商人获取利润和武士领取俸禄完全一样,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鼓励商人对商业行为要有信心,要进行高尚的商业竞争,正直地经商、堂堂正正地经商。这就是商人应当具有的伦理观,即商人之道。稻盛和夫认为,和欧洲以耶稣教伦理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初期资本主义一样,在江户时期,日本商业资本发生的时代,也有比现在更严格的伦理观。“但这种伦理现在已基本丧失了,不能不令人感到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在伦理方面的贫乏。”[3](P21)如果当时的资本主义精神一直延续下来,今天日本的泡沫经济、政界及金融领域的不正常事件就不会发生。那么,上述资本主义伦理变迁的现象如何解释呢。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把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变异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矛盾性。贝尔的这一重要研究始于韦伯和桑巴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方面宣扬了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同时对奢华懒惰的风气严加惩戒。贝尔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发的阶段便潜伏着“禁欲主义伦理”与“贪婪攫取性的矛盾”。“贝尔把这两方面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并研究和追索它们演变的轨迹。”[3](P13)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种力量纠缠难分,相互制约。禁欲主义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性格,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育了他们的冒险精神,雄心勃勃挺进新疆域。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新教伦理抑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禁欲主义强调精神价值观,摈弃肉体享受,提倡节俭和忘我,严格遵守苛刻的纪律。为了完成使命,为了克制自我和征服他人,就要动员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力量。清教徒生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聚敛财富,他们从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中往往无所得,只不过为了证明自己得到拯救。稻盛和夫所说的“原点”,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时期。后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另一面,经济冲动力所驱使的贪婪攫取性脱离了宗教道德伦理的规范,贪婪的私欲便象脱了缰的野马无所约束了。贝尔说,当新教伦理被资本主义抛弃之后,剩下的便是贪欲、享乐了。贪婪攫取则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性。令人深思的是,在20世纪末期,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的儒教伦理主张仁义、诚信,新中国更是倡导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然而资本主义阴暗面的种种现象,在中国的现今社会也纷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这种怪现象,也许归根结底源于人性的多重性。在古代中国,关于人性就有人之初“性善说”、“性恶说”、“白板说”。人性是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差异。历史上某个时期的道德形态,比如清教徒的伦理观,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能否完全再现呢。稻盛和夫也曾经说过,以前支撑宗教信奉者价值观的是宗教信仰,现在宗教的影响力衰微了,强大的基督教在欧美已大大衰退,日本已有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冠婚葬祭的仪式。宗教已没有力量重建伦理观,所以我们不能再依靠宗教。
稻盛和夫之所以主张先返回“原点”,意在重建资本主义伦理。他对现在商业道德的危机深感担忧,批评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只顾赚钱而不考虑社会效益。稻盛和夫经常对学习他经营之道的青年企业家说,企业追求利润决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追求利润,如何运用利润,仅仅为了一己私利的企业终将被社会所淘汰。稻盛和夫把“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作贡献”作为公司的经营理念;把“与社会和谐共存,与世界和谐共存,与自然和谐共存”作为公司的经营思想。稻盛和夫在决定建立日本第二电讯电话公司前,自己不断反思“动机是否善”、“有没有私心”。在确认参与电讯行业,有利于打破国营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电讯事业的局面,并能使广大民众得到快捷、低价通讯的实惠,便毅然做出决断,现在第二电讯电话公司已进入世界500强大企业的行列。稻盛和夫的公司还投资生产环保产品,如太阳能汽车设备等,为保护地球环境作贡献。稻盛和夫还十分热心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1984年,他从自己的私人财产中拿出200亿日元,设立稻盛财团,并以这笔基金创立了“京都奖”,1997年,又捐献出210亿日元,做为“京教奖”的运营基金。“京都奖”是国际性大奖,一年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从基础科学、尖端技术、社会科学与艺术三大领域中评选出3位当年对社会最有贡献的人加以奖励,其金额为每人5000万日元,现在“京都奖”在世界科学文化界的声誉已越来越高。稻盛和夫以自己实践活动在实现自己的经营理念。
同时,稻盛和夫呼吁大企业要实行自律。他在《新日本·新经营》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主张。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原理为基础,但是,要正当地发挥这个原理,每个经济主体特别是大企业须要适当地控制自己。“某些大企业及企业集团,在达到超级化和垄断化时,其力量在特定条件下,足以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4](P55)他们往往只为了本集团利益决定经营方向,而不考虑大众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超级化和垄断化是决不受欢迎的。还有些超级大企业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毫无节制地向新领域扩张,在市场中排挤中小企业,这势必造成巨树之下众草难生的局面。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不能自恃力量强大而与大众利益及社会的发展方向相悖,要善于和社会和谐共存。
稻盛和夫认为,企业应从封闭走向开放,对社会公开信息,公正经营。企业必须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确保透明度,以便使企业的经营为社会所明了。不至于被滥用于谋取部分人的利益;不至于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企业要把经营财务状况定期向社会公布,这被称作分段信息公开展示。在欧美,这种作法作为保护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手段,已普遍形成制度并规定下来。这对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标签:稻盛和夫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