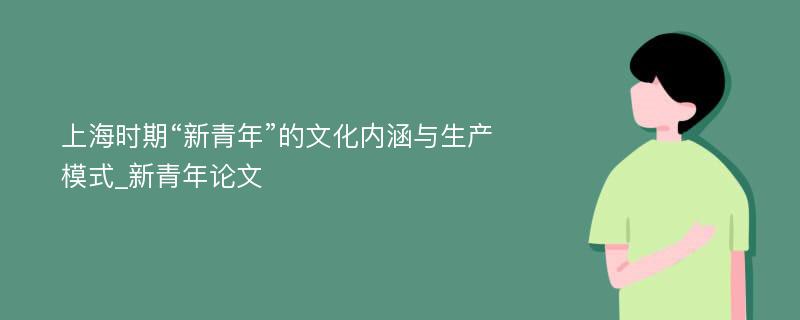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文化蕴涵及生产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生产方式论文,上海论文,新青年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85-04
1917年2月,陈独秀携带创办不到两年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人们热衷探讨的对象。人们探究它反传统的社会语境及现代性文化资源,剖析它的同人分裂所隐喻的中国现代性冲突,颂扬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价值。但是,人们对《新青年》北京时期的如此热衷及专注,是否会遮掩它上海时期那段并不辉煌的初创历史?这种遮掩是否会导致人们对《新青年》认识的偏差?毕竟,《新青年》在上海时期与北京时期的不同阶段,蕴涵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它最初命名为《青年杂志》的历史机缘及文化资源是什么?陈独秀创办这份刊物的原初宗旨是什么?还有,相对于《新青年》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的社会生产模式,《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社会生存策略是什么?这些研究可以呈现《新青年》上海时期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问题。
在《新青年》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常提及的是《新青年》的更名问题,而很少关注它创刊伊始的“命名”问题,即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这份杂志的刊名,以及它所隐喻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众所周知,陈独秀1915年创办这份杂志比较仓促。1914年7月,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去了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初夏,他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得知家中妻子病重、家计难以为继,便匆忙赶回上海料理家事。就在这次归国的船上,他萌生了创办杂志的愿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①。陈独秀回到家中便和汪孟邹商谈创办杂志之事,最后商定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于1915年9月出刊,定名为《青年杂志》。抛开陈独秀创办杂志的动因不论,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杂志的刊名?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的上海报界,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很少,以“少年”、“童子”、“学生”为刊名的反倒常见。那么,陈独秀使用它作为刊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晚清时期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他1902年春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回国后在安庆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不久,又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人组织“中国青年会”。十几年以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是否忆起往昔的革命激情,由此选取“青年”作为杂志的名称,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在《青年杂志》刊行的第二年,上海青年会认为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刊物名称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一事件为我们认识《青年杂志》的“命名”因由,提供了一条思考的方向及途径。回顾近代出版史可知,上海1903年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取名为《童子世界》,商务印书馆1911年发行、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即是说,在20世纪初,凡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陈独秀以“青年”作为自己杂志的刊名,如果不是缘于他早年的革命激情记忆,就是对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的附会。
基督教青年会1840年代产生于英国,目标是改善资本主义社会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不久,法国、北美、澳大利亚、德国等仿效英国青年会,各自在本国成立了相同的青年组织,尤其是在北美,青年会的发展最迅速、影响也最大。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建立,1895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会所,1896年又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青年会机构——中国学塾基督幼教会,该会1912年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要从事教育、体育、宗教宣传、社会服务、童子事业、学生工作等事项,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日趋本土化,更加关注中国的社会平等、劳工待遇、女子解放等社会问题,因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产生很大思想影响。据统计,全国青年会、市会到1922年已达到40处,会员有53800人:各类学校中的青年会有200处,会员24100人。基督教青年会重视个人德育的修养,强调个人应该服务社会,担任青年会干事的余日章就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③
陈独秀创办刊物之时,选择跟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相似刊名的主要动因,可能是迫于北洋军阀政府“报律”的压力。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袁世凯北洋政权的确立及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压迫,北洋政府颁布实施的“报律”摈弃《临时约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不断禁锢社会进步报刊的话语及生存空间。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一度发展迅速,新创办的报纸达500种左右,“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北京的报纸减少到20种左右,上海减少到5种,汉口减少到2种。1913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也从4200万份减少到3900万份”④。面对北洋政府的压迫,当时有人主张报纸应该挂上“洋旗”,有人主张应把报纸迁到租界。可以说,利用外国租界逃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成为当时出版业的无奈选择。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政府报律的滋扰,利用外国教会刊物的名称来伪装自己的杂志,以图刊物能够长远存在,这应是《青年杂志》如此命名的现实考虑吧。
《青年杂志》对基督教会刊物的附会,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隐喻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性文化“发生”的历史影响。我们知道,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指出,“本志之作,欲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他在揭起“义学革命”大旗时,又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义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总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希望启蒙个人“伦理的觉悟”,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重建。这种“伦理革命”的思想方式,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个人尽其所有、竭其所能为社会服务的道德主张,不仅具有极其相似性而且也相当普遍。李大钊就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⑤胡适也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的基础。”⑥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民族国家的重建,必须以个人伦理觉悟为前提。这种重视个体伦理的思想启蒙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在五四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与基督教的文化关系可能最为密切。从1915年至1924年的10年间,他发表一系列评论基督教的文章,并因主张输入基督教而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关注。他在1915年为《绛纱记》作序时,认为基督教不否定现世界,且主张神爱人类,在解释死亡与爱这两大生命问题时比佛教妥帖、易施。他1916年又指出,基督教比儒教有价值,其“信徒制行之清洁”为其他宗教无法相比。总之,陈独秀认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其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即使人类崇尚的科学观念也不曾破坏它,而且将来也不能破坏它。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推行基督教,说:“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不能否认,陈独秀在这时期也有过“非宗教”的言论,但他服膺基督教的教义而仅否定它的“教会”。
无论如何,陈独秀选择“青年”作为杂志刊名,并确立“伦理的觉悟”为办刊宗旨,其间蕴涵的基督教影响绝对不容忽视。然而,陈独秀没有把《青年杂志》办成基督教青年会性质的刊物,他所要宣传的是自由、平等等现代“人权”学说,以此对抗、颠覆近代盛行的民族国家主义观念。
上海草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常被人们视为性质定位模糊的刊物,不仅没有超越当时上海报刊的藩篱,而且没有显示“文艺复兴”的革新面貌。然而,陈独秀在更改《青年杂志》刊名时,没有废弃杂志原来的刊名,只是在“青年”前添加一个“新”字,以示与青年会刊物的区别。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代新文化思潮在晚清后已纷纷涌入国内,到《青年杂志》更名的1916年9月,“新”所象征的外来现代性思潮,作为招徕读者的刊名似乎已失去广告性。那么,陈独秀仍然选择它又意味着什么?
1915年之前的陈独秀,最耀眼的社会角色是近代“革命党”。他从“民前”的反满到“民后”的“护国”,始终希望建立“共和制”国家。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袁世凯的专权及北洋政府的腐败,中国政治与社会道德呈现堕落趋势。此时,保守派迷恋于立宪,激进派热衷于革命,而陈独秀则转向了思想启蒙。在《青年杂志》更名的时候,陈独秀虽没有彻底脱离革命党人气质,但却拥有了不同于时代的新思想,这或许就隐喻在《青年杂志》更名的“新”字中。
我们知道,晚清革命以来民族国家主义成为近代文化主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个体性的国民视为民族精神的承担者及象征。随着民国初年社会道德及国家政治的腐败,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批判国民道德及其文化传统。梁启超主张利用“家族主义”再造国民道德,以激发国民“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资产阶级革命者集中在《甲寅》周围,进行“民族国家”思想的社会宣传,相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根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问题,而整体目标的解决也就是个人的现实要求的达成”⑦。总之,民族国家主义成为晚清民初的思想潮流,人们把它视为个人必须效忠的历史对象。
陈独秀在日本协助编辑《甲寅》的时候,他就萌生了现代“人权”的新观念。他认为,国家应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机关,人民热爱的应是能够保障个人权利与个人幸福的国家,并非仅是盲目的、愚昧的国家崇拜。陈独秀标举现代个人权利的观念,引起了当时读者的纷纷抗议,但得到《甲寅》主编章士钊的同情及支持。创办《青年杂志》后,陈独秀更加努力宣传这种新思想,并指出现代的科学观念、人权观念是它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们现在多把科学、民主看成《新青年》的两个思想革命旗帜,然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海时期标举的“人权”,并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民主”,它更多强调个人的本位主义,强调个人是所有社会存在及价值的前提。因此,《青年杂志》更换刊名后增添的“新”字,实质象征着陈独秀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转型,即由晚清兴起的民族国家主义向现代个人主义的历史蜕变。
这时期,陈独秀强调的“人权”主要指人的自主权,即现代个人的自由权利及解放。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成人以往,自非努力,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转向个人主义,谋求个人权利的自由及解放,颠覆的不仅是晚清盛行的民族国家主义,而且波及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青年杂志》希望“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由此,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关注妇女解放、青年修养、体育问题、孔教问题及文学问题等,实际上都隐喻陈独秀对现代个人“伦理的觉悟”的迫切渴望。它虽然给人留下混杂或刊物定位模糊的印象,但模糊的背后却蕴涵着清晰的、一致的文化追求,即对现代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渴求。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历史,蕴涵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关联,象征着民族国家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历史蜕变,还沾染着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社会逻辑。与《新青年》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的社会生产模式不同,上海时期的《新青年》依靠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这对刊物的宗旨及性质产生了某些遮蔽。
《新青年》诞生于上海,上海的商业文化是它生存的社会语境。1915年前后,上海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拥有重要的出版社、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健全的发行网络。上海出版业的商业化,一方面聚集了许多文化生产者;另一方面使个人生计与出版物、商业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有学者指出,上海当时的报刊市场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仁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基本属于同人刊物,它“凭借的是‘知识’(‘科学’、‘民主’思想等)资本,靠的是‘舆论’(‘打倒’、‘否定’、‘整体’解决的逆向思维等)的穿透力,走的是一条‘信息化’(‘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的路径”⑧,然而,它从第2卷起商业气息愈来愈浓,不仅以“陈独秀先生主撰”为标榜,而且以“且得当代名流之助”为招徕。这些商业性宣传,主要受杂志第1卷销售状况不佳之逼迫。杂志销售情况不理想,不仅给益群书局带来经济压力,而且危及杂志生存和陈独秀个人生活,终使《新青年》以商业化进行宣传,以便获得读者青睐与增加订数。
不仅如此,《新青年》迫于市场压力,还刻意向读者暗示它与《甲寅》的关系,借助《甲寅》的社会公信度进行宣传。《新青年》第2卷1号上登载来信说,“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该期还刊出“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叶挺”的来信,称赞陈独秀“足下孤诣,略见于《甲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新青年》第3卷3号又刊登“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的来信,说:“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当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然不料续《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这些或真实或虚拟的读者来信,传达着《新青年》乃“名刊之后”的信息,目的是为了招徕读者、推销杂志。
种种迹象表明,《新青年》虽属于同人性质的刊物,但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制约,迫使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必须正视它的社会力量,必须依靠它而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压力,可能使陈独秀把杂志读者定位为都市知识青年阶层。众所周知,从清末废除科举到“五四”前夕,新学堂十几年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业吸纳他们。从《新青年》通信栏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很多中小知识分子因经济条件不能继续深造,他们在竞争激烈的都市又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心里充满着社会和人生的焦虑及绝望。这种焦虑状况使他们易受激进思想影响,作为老革命党的陈独秀自然能窥视到其中潜藏的历史力量,所以,凡是知识青年关注的新知识、社会现实问题,《新青年》都给予悉心解答,这不仅是对知识青年的社会关怀,而且是巩固读者市场的“营销”策略。
总之,《新青年》的上海时期,由于受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语境影响,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图生存,使《新青年》逐渐染上商业化刊物的气息,刊物的宗旨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埋下了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终使陈独秀割断与益群书局的关系,摆脱了书局对《新青年》编辑宗旨的束缚及干扰。《新青年》上海时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北洋政府对报界的压迫,中国现代性发生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关系,又可从中发现陈独秀及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转型,以及都市资本主义对刊物生产方式及性质的影响。这些不仅形成《新青年》的“上海特征”,而且呈现了中国现代性文化产生所遭遇的诸多历史问题。
注释: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②参见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2页。
③参见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页。
④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0页。
⑤《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⑥《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8页。
⑦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标签: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上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甲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