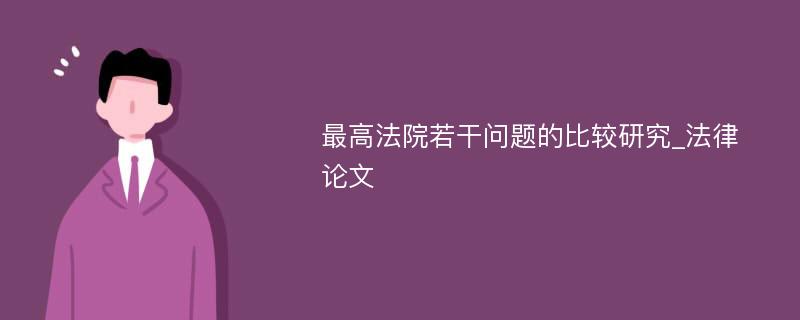
最高法院若干问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高法院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高法院,是一个国家制度体系中独立行使司法权并居于司法体系最高位阶的司法系统,具有终极的国家审判职能和强大的社会控制功能,它通常为一个国家的宪法、司法习惯和法律文化所界定并成为一国政治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高法院首先是一个国家机构,一个权力系统。从历史与社会的视野、法的文化传统及民众对司法的公共认知赋予之这样的意义:最高法院天然是个司法系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开放系统。最高法院引领整个司法系统,实施司法权力,实践司法使命,形成自治的主体,并“在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在系统与环境之间发生着相互作用”(阿尔蒙德语)。
从结构一功能主义出发,最高法院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最高法院在一个国家政治结构中的特定地位;二是最高法院在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特定功能;三是最高法院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因此,一个国家界定最高法院,首先是强调其作为一个政治性机构,是一国中央政府权力体系中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行使国家立法职能的立法机关及实施国家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区别,联邦制国家的各州最高法院在此也得到区分。其次是强调其在一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位阶,将其区别于低级别的法院。大部分国家的宪法直接规定了最高法院及其职权,但在有的国家,最高法院则指实际上发挥最高法院作用和意义的机构。例如,英国上议院和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这一点在学者Becker所定义的法院原型和法院概念中得到认同。(注:Theodore Becker,Comparative Judicial Politics:The PoliticalFunctioning of Courts,Chicago:Rand McNally & Company,1970.)总体而言,诸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英国上议院、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国宪法委员会、日本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以及中国最高法院等等,都是上述意义上的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也是一个制度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涵括了最高法院的制度创设、角色与功能定位、权力与结构安排、人员与机构设置及资源配置、运作的程序与理念等等方面的内容,也因此赋予了最高法院概念的丰富蕴涵和重大意义。有鉴于此,下文拟就目前尚乏研究的最高法院基本制度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最高法院的地位与功能
在现代法治国家,最高法院是独立的政治主体、也是最高的司法主体。按照分权原理,最高法院通常是一个国家政府权力体系中独立履行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在实际运作上,最高法院的地位呈现结构和特征差异。在采取三权分立制衡的国家,最高法院独立且制衡着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美国最高法院即是典型;在强调议会和民选权力机关主权至上的国家,最高法院则是执行议会立法或者对民选权力机关负责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例如,中国最高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谷口安平认为,“司法作为维持政治及社会体系的一个基本支点发挥着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注:[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那么,最高法院则作为司法的最高支点发挥着一种“原生产功能”,因为,最高法院是最高的司法主体,有着司法终审权、统一司法权、最高司法权以及对整个司法系统信息和资源的统一配置与处理的功能。
最高法院地位的彰显有赖于最高法院功能的活化。最高法院具有两种基本功能:政治性功能、司法性功能。
首先,最高法院的政治性功能表现为权力制约功能和公共政策形成功能。近现代宪政国家的一项核心原则——司法独立的根本动因就在于制约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民主需求以及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治理的公正需求,因此最高法院政治功能的要义便在于权力制约和形成社会公共政策。
最高法院的权力制约功能主要是通过司法审查机制而生效。从政治制度架构的层面上,司法审查实质上是一种分权制衡的机制,它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来平衡、制约议会的立法权和政府的行政权,以防止其膨胀和滥用。显然,“当违宪审查权交诸法院行使时,法院的地位便大大提升,如果说法院的传统地位仅是纠纷解决机关,那么违宪审查功能便使法院上升为政治机构,且获得一种对行政、立法机关特别是对立法机关的俯视地位,因为仅仅依据宪法来审查法律,便使得以司法为准则的法院获得一种在传统体制下难以想象的地位。”(注: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在这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和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违宪审查的功能尤为典型。
最高法院的另一种政治性功能是公共政策形成功能。这关乎法官尤其最高法院法官是如何参与政治和发展法律的问题,即在现有的权力空间内,最高法院如何形成政策从而参与对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控制,以及如何发展法律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它体现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配置与运作中的角色与意义定位,也是最高法院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政治性功能与社会性地位的显著象征。所谓公共政策,在本质上属于旨在解决或处理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政府行为,它表示在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目标,反映政策联盟期望的社会结果,也反映决策者认为可以用来取得这些结果的手段。在政治学理论中,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往往被视为特定政治实体的最高权威或权威机关的专有权力。(注: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随着“政治司法化”(Vallinder)历程的推进,“法院和法官开始制定或逐渐掌握公共政策形成,而非司法的决策范围也逐渐由司法规则和程序所掌握”。(注:C.Tate & T.Wallinder,The Global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New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在现代法治社会,最高法院的权力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高度尊重,最高法院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法官总是制定政策,这是由于他们有义务处理社会问题;一些法官十分热切地制定新政策”。(注:[美]亨利·R·格林科:《美国法律中的司法决策》,载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此种司法政策被认为是“对个体和组织都能产生直接的物质性或象征性利益的决定”,包括“结构性政策”和“分配性政策”(Salisbury、Heinz)。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不仅通过具体案件审判和抽象规则制定的传统方式来发挥,更主要的是通过违宪审查来实现。一方面,在传统上,“法院把制定公共政策作为审判案件的必然产物”,(注:[英]W·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页。)“即便法官固守判案的老方式,他们也通过维持现状的方式制定决策。不论司法判例的具体内容如何,法官都在制定政策。”(注:[美]亨利·R·格林科:《美国法律中的司法决策》,载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方面,随着近现代宪政主义实践机制和方式的演进,违宪审查已逐渐成为最高法院公共决策功能的最主要生成机制。美国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尤为显著,“在美国,诸如少数民族的平等待遇,对堕胎的法律限制,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宣告的法律,而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支配的”(注:[美]杰弗里·C·哈泽德:《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司法部门在美国政府机制中发挥其核心作用的基础,而司法部门的作用是美国法治的基础,这是美国成功的秘密所在”。(注:[美]托马斯·L·弗雷德曼:《外交事务:荣誉勋章》,载《纽约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5日,第39页。)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违宪审查及宪法诉愿制度,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公共政策形成相当典型,“宪法法院的一个个判决,催生了人们对宪法和基本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以前就根本没存在过”(注: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美]路易斯·享金、阿尔伯特·丁·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赵晓力、强世功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4页。);相反,中国最高法院由于违宪审查功能的暂缺而在公共决策方面相对微弱。事实表明,具有违宪审查功能的宪法型法院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通常要比普通司法型最高法院强。
其次,最高法院的司法性功能包括纠纷解决功能、法制统一功能。
“争议的解决是司法体系的首要职能”,而“法院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设立的机构”,(注:[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纠纷解决和司法裁判是司法职能天然的最本质含义,最高法院的司法性功能首先是纠纷解决功能。所谓纠纷解决功能,即一套定纷止争机制的功效及价值,其意旨在对个案进行公正的司法处理,实现司法对社会冲突和民间纠纷的最终解决的理想。尽管有些宪法法院也从立法审查的角度对立法的妥当性进行事前、事中或事后的审查,而与一般的纠纷处理相区别;但对立法适当性所存在争议的解决,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所以,当社会的冲突积累到务必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化解和排除的时候,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便随着社会自身进化而形成,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同样生成。当然,对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的应用,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实际做法。例如,印度最高法院对纠纷解决抱持充分积极的姿态,强调最高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初审功能;而德国联邦法院则主要发挥在刑、民案件上诉审中的纠纷解决功能。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主要演化为对典型案件尤其是宪法性案件的解决。而在日本,最高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仍然相当发达。中国最高法院的纠纷解决主要针对刑事死刑复核案件、重大疑难民事经济案件。一般而言,当今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通过上诉审的方式,而初审权的行使则不多见。可以认为,一国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的行使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它在该国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往往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的过分发挥则会消减其他功能的实现程度。当然,各国最高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不但有强弱之别,而且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有区别,如美国最高法院的纠纷解决钎对法律适用问题,而中国最高法院实施纠纷解决功能则要涉及事实认定问题。
显然,个案处理过程的功能是多元的,基于最高法院终极和统一的运作理念,纠纷解决过程实际上也与法制统一功能息息相关。最高法院即使形式上承担着解决纠纷的职责,其实质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因而法制统一功能是最高法院的另一项重要司法性功能。在近现代法治进程中,法律的精神和司法的理念已提升到关乎社会进步、国家存亡的高度,最高法院也因此被普遍定位成法治国家推行法制统一的主角。作为一国最高位阶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具有司法资源和信息方面等诸多优势,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预设了法制统一的使命。必须指出,作为司法政策的统一推行者,最高法院法制统一功能的实践形式也是多样的,总体而言,实践方式大致有三:判例拘束式、司法解释式和判决撤销式。所谓判例拘束式,即通过判例制度及其遵循先例的司法习惯来实现法制统一,美国最高法院是典型。而中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带有显著的法制统一功能,也就是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及设定司法解释在整体司法实践中的普遍拘束力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所谓判决撤销式,则是通过最高法院上诉审判权的行使对有悖于法制统一的下级法院判决作出具有终极裁判力的撤销裁判,目前法国的最高法院便以此方式运作。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最高法院的具体形态,以主要功能为基准,大致存在三种基本的最高法院类型。一种是普通司法型最高法院,它以解决纠纷的普通司法功能为首要功能,当前,中国等部分国家的最高法院就属此种类型。最高法院的另一种类型即是宪法型最高法院,它以违宪审查为主的宪法性功能为主要功能,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为典型。在德国,宪法法院是专门创设以实施违宪审查、监督宪法实施、保护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机构,据统计,从1951年以来,宪法法院已处理50000余件宪法性案件,近年来差不多每年3000件,当中主要是宪法诉愿,并曾有两次对政党违宪进行审查,宪法法院在德国的政治民主生活中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发挥重大意义;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这种宪法型最高法院的国家就已达到37个,而90年代以来其数量又有增长,如东欧各国大都建立了宪法法院。还有一种则是综合型最高法院,既履行纠纷解决的普通司法功能,又实施违宪审查的宪法性功能,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最高法院属于此种类型,据不完全统计,(注:[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仅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便有64个国家赋予普通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的功能。在其中,有的以宪法性功能为显著,如美国最高法院;有的则偏重司法性功能,如日本最高法院。
二、最高法院的组织体系
最高法院组织体系,首先是最高法院的系统结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最高法院的审判组织模式问题,第三个层面是最高法院的业务机构设置问题。
最高法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系统构造在不同国家有差异,大致存在单一制最高法院系统与多元制最高法院系统两种基本结构。所谓单一制最高法院系统,即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系统由单独一个最高法院机构构成,由其实施最高法院职权和功能。目前大部分国家诸如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最高法院系统都是单一制结构。例如,日本宪法第81条直接创设和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唯一终审法院地位及其违宪审查和统一解释法令的功能。多元制最高法院系统结构,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系统由多个最高法院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之间有专业分工与权力分配,在各自管辖权力范围内履行特定的最高法院职能。德国就是这种最高法院结构的典型,联邦德国的最高法院系统包括6个子系统:宪法法院、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政法院、社会法院、劳工法院,每个子系统之间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各自在法定的受理案件管辖范围内行使最高的司法终审权。其中,宪法法院专门受理宪法性案件,履行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的职能,维护宪法的实施和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在具体司法过程中涉及法律合宪性问题时,应当先行将案件移送宪法法院作违宪审查,而宪法法院则一般不干预案件具体处理。最高法院的系统结构与一个国家特定的政制体系、法律文化及司法习惯密切相关。整体而言,多元制结构最高法院的功能分化程度相对显著,单一制结构最高法院的功能则呈现多样性。当然,两种结构的最高法院系统在权力运作和功能发挥上存在诸多差别。
最高法院的审判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庭模式(分配模式)和全体模式(参与模式)。所谓“分庭模式”,是指最高法院根据法律专业、管辖区域、司法习惯或者具体需要等特定的标准分别设置和组成若干审判庭,由特定的审判庭行使审判职权。它强调最高法院内部以庭为基本单位对案件的分配机制及审判任务的有序处理,因此也称“分配模式”。当前推行分庭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法国和中国等。“设立专门审判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法院内部机构的划分,使案件分流从而在整体上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并且,通过依案件性质对案件分流以强化司法的专门化程度。”(注:Edward Mcwhinney,Superme Courts and Judicial Law-Making:Constitutional Tribunals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6.)联邦德国普通最高法院平均每7名法官编为一组,设立了5个刑事法庭和12个民事法庭,分别处理各类刑事、民事等案件。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分设2个庭,即第一庭和第二庭,每个法庭由8名法官组成,其中包括3名联邦法官和5名具有一定任期的定期任职法官(Richter auf zeit),2个法庭的地位和审判权力平等,各自独立运作,案件审理数量大致相当,主要在案件管辖范围方面有所差别;当然,根据《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第14条第2项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某个法庭如果暂时负担过重,联邦宪法法院的联合庭则可另作决议,对2个庭的管辖权进行变更。”在法国,普通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设有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分别受理民事、刑事案件。中国最高法院则主要依照案件专业划分为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所谓“全体模式”,是指最高法院的审判组织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组成和参与,最终的判决或意见由全体法官共同作出。此种模式凸显了法官在最高法院案件处理机制中的参与性,因而又称“参与模式”,美国最高法院审判权的运作就是一个典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审理案件时,原则上由全体大法官参加,至少有6位大法官出席才能开庭审理,有学者将此种审判组织称为“一个合议庭”。(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如果分庭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大众司法”样式及相应分工问题,那么全体模式体现的则是一种“精英司法模式”及司法一体化,这只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制度为高度精英型的国家才可能。需要指出,最高法院在主要采取一种模式的同时,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采用另一模式,从而实际上构成一种混合模式。这主要是推行分庭模式的国家,根据案件的特定情况和需要而决定具体审判组织形式:一般实行分庭模式,特殊情况下则实行全体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最高法院审判组织是由全体法官组成的大法庭和各有5名最高法院法官构成的3个小法庭。大法庭审判法定法官人数为9名,小法庭为3名。理论上,日本最高法院以大法庭行使审判权为原则,尤其对于法令违宪问题案件的判定必须由全体最高法院法官组成大法庭并且有8名以上的法官意见一致来作出。在日常司法中,小法庭行使审判权也极为常见。在司法资源分配和案件处理效率方面,这种大法庭的全体模式和小法庭的分庭模式并存具有相得益彰的司法效果。同样,德国联邦法院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也设置了1个民事案件大法庭、1个刑事案件大法庭和1个联合大法庭,以处理各刑庭之间、各民庭之间、刑民庭之间有意见分歧的案件。
除了审判组织和法官,最高法院的机构设置还涉及一些管理型、辅助性机构以及临时性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法官助理),这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行政人员约百余人,分别担任法律助理、技术助理、法律研究、计划、教育培训、人事管理、会计、统计、数据库等工作,以保障法院系统的正常运转。联邦最高法院每位大法官通常可以拥有3至4名法律助理、2名秘书和1名行政助理,这些助理具有较高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往往是会计、计划、统计、档案、计算机、图书管理、速记、公共信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设有法官助理,主要职责是审阅卷宗材料,查阅相关法律条文、案例、有关学术观点等资料,向法官提出参考性意见,开庭时旁听,起草判决书等。在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每人配备秘书长官1名;另设调查官,对民事、家事和少年案件有关审判的事实进行调查;还设速记官和庭吏,分别负责审判重大、特定案件的速记和开庭事务处理、法庭秩序维护及协助司法文书送达。当然,日本最高法院在机构设置方面的特色是事务总局:根据裁判所法第13条,最高法院事务总局掌管最高法院的庶务。它主要处理与司法行政有关的事务:辅助法官会议决议事项的执行;编辑、整理、刊行判例集及其他审判参考资料;处理有关法院职员人事事项;为制定规则作准备;等等。在法国,据统计,最高法院除去法官84人以外,还有其他法院职员共约78人:协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的调查法官37人、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调查官18人、检察官23人。显然,一个国家最高法院在审判组织以外的机构设置,关系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案件审判的高效率问题,而最高法院司法审判组织与行政性、服务型事务机构的分离对于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经济非常必要。具体而言,是否设置、如何设置最高法院的行政性机构以及人员的多少,首先都与最高法院的行政管理功能的状况有关。如果最高法院具备广泛的行政管理功能,包括对下级法院的管理活动,则势必要求更多的管理人员。日本最高法院事务总局人员达数百人之多,就与日本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行使统一行政管理权有关。其次,这也与最高法院本身工作的负担及法官的多少有关。一般而言,法官越多,案件处理量越大,则行政人员越多。印度最高法院行政人员就明显因此而多于美国最高法院。
从总体上讲,最高法院的组织体系事实上与一国法院的设置乃至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有密切关系。美国和法国最高法院组织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基于国家权力配置的不同最终决定了两者法院设置上的重大差异,在这里,涉及到不同国家权力配置中对司法权及最高法院的价值与角色的初始预设问题。在美国政制的“原初设计者”那里,司法权被想象为独立自治的国家权力,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注:[美]汉密尔顿、杰尹、麦迪进:《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至392页。)最高法院被认为有精英型法官所组成的对美国联邦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最高司法机构,所以,少量的法官和精简的机构设置便成为当然。然而,在法国政制“原初设计者”的概念中,法院的公正性是有疑义的,法国大革命前普遍的司法腐败,保守、反动司法对立法与行政的进步的干预,使得公民对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持有强烈的不信任乃至警惕的立场,于是法国并不授予普通司法优越地位。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司法权不得干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原则。所以,普通最高法院功能的有限性、作用发挥方式的有限性乃至随着时代变化而新出现的行政法院、宪法委员会多个机构并存的最高法院体系便理所当然。
三、最高法院的法官制度
最高法院法官制度,包括法官体系与结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保障制度等。当今各国的法官体系大致呈现为两种基本样式:精英型法官体系和职业型法官体系。精英型法官体系以法官的精英化为首要结构特征,表现为法官数量和质量的少而精,法官选拔的高标准、法官优秀的职业能力和法律素养以及超然的职业伦理、法官的优质待遇和职业保障,等等。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最高法院法官体系就带有显著的精英化特征。在日本,最高法院共有15位法官,其中院长1名,从法官总体知识架构可发现法官的精英性:法官出身5人、律师出身5人、学者和实际经验者(学者、检察官、行政官等出身)5人。根据法律规定,在15位法官的构成中,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必须达到10人,其他5人为“见识高又具有法律素养者”。(注:董璠舆:《日本司法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英国上议院的最高司法权主要由上议院中被称为“贵族法官”的法律议员行使(必须曾担任15年以上出庭律师或具有曾任高等法院法官2年以上的资历),其上诉案件的审理由10名法律议员、以及曾经担任高级司法职务的上议员和上诉法院常任法官参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9位大法官组成,即1名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史上,法官的精英化特征尤为显著:1790年成立联邦最高法院时,华盛顿总统委任了以约翰·杰伊为首的6名法官;1807年增加到7名;1834年增加到9名;在林肯总统位任职时曾增加到10名;1869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1937年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为对付联邦最高法院中的保守势力,决定再增加6名法官,但终究没有成功;时至今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仍然固定为9位。美国最高法院一贯以来抱持法官精英化原则,大法官法兰克福特曾言,最高法院大法官除了必须是获得法律职业博士和经验丰富的律师,最重要的还应具备:哲学家、历史学家、预言家的品质。(注: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毋庸置疑,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这块土地上最令人崇敬的法官”。(注:[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精英型法官体系具有诸多共性:首先,法官选拔机制实质上是将律师精英和法学家精英转化为法官精英的一个过程机制,它们大多从经验丰富的律师和优秀法学家中选拔法官;所以,亚里士多德将法官视为“活生生的正义”(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8页。)的概念在精英型法官体系中可谓得到最为贴切的诠释。其次,其精英型司法机制塑造和张扬了精英法官形象,美国最高法院法官9人,日本最高法院法官15人,英国上议院法律议员加上常任法官人数最多时也仅有30余人,在这些国度,“以法官为中心的职业化传统已经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界最优秀的分子”,(注:郭成伟:《外国法系精神》,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其中不乏崇高的法官形象:创立违宪审查制的马歇尔(John Marshall)、倡导少数意见的詹森(William Johnson)、致力于黑人平等的哈兰(John M.Harlan)、被誉为“美国良知的象征”的霍姆斯(Oliver W.Holmes)、被推崇为注释法学泰斗的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n)、被尊奉为“民众的法学家”的布兰岱(Louis D.Brandeis)、为司法注入新生命的沃伦(Earl Warren)、被奉为“法秩序的守护神”的伯格(Warren E.Burger)、被敬奉为“自由之神”的道格拉斯(Willain O.Douglas),等等。从一定意义上可谓,精英的司法造就了精英的法官,精英的法官营造了精英的司法。
相对而言,职业型法官体系,则以法官的职业化、公务员化为特征,法官的精英化程度较低,法官人员较多,法官的选拔、任免、晋升、考核、奖惩程序与公务员管理特征有相似性。德国、法国的法官制度就带明显的职业化特征。法国最高法院现行法官84人,绝大部分法官是法律专业毕业生或者公务员考试合格者,经由国立法官学院培养并经司法部门实习之后就开始了法官职业。根据法国的法官等级制度和晋升制度,最高法院法官通常从下级法院中逐级晋升而来。同样,联邦德国最高法院任职的法官,大部分也是从下级法院尤其是上诉法院的法官中逐级选调上来的,其晋升标准是工作经历和成绩,虽然德国最高法院可以直接任命杰出的律师或大学教授来担任法官,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注:周道鸾:《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在职业型法官体系,法官的精英个性容易受到模糊,正如梅里曼所言,“执行一个重要而基本上非创造性职能的文官,……法官的名字几乎被遗忘殆尽,其现今的续任者们也都差不多在默默无闻地工作”。(注:[英]格伦敦:《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法官遴选制度是最高法院法官制度的另一重要方面,关键在于法官的遴选标准和程序。
首先,是法官遴选的标准问题。几乎所有国家最高法院法官遴选都有一个司法技术性标准,该标准往往被量化为法学学历、司法资格、司法经验、法官业绩,等等,因为,“除非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的法律家,常人是难以具备司法所要求的特殊的技术理性”。(注: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在美国,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必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法律职业博士学位;第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从事律师行业若干年。在英国,要成为大法官以及上议院常任法官,则必须通过律师考试,从事律师职业,并进入英国四大律师公会(林肯、内殿、格林和中殿律师公会)接受传统的法律思维和技巧的训练;而且,必须是已经任职15年以上的出庭律师或者有曾任高等法院法官2年以上的资历。(注:周道鸾:《外国法院组织和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必须“学识渊博,具有法律素养”;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接受司法进修所培训2年;并曾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或法官累计时间达到10年以上,或曾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法官、简易法院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大学法学教授、副教授累计时间达到20年以上。(注:方立新:《西方五国司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在德国,根据法官法规定,普通法院系统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必须具备:第一,通过大学法律专业考试,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第二,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并通过由国家司法人员培训中心的职业培训;之后按照其法官晋升制度,达到相当程度的工作时间和成绩才能最终晋升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官,则必须具备被任命为高级法官的资格;或者是曾在联邦最高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社会法院、联邦财政法院以及联邦劳动法院任职的法官,同时任职时间达到3年以上。在法国,充当最高法院法官则必须完成4年法律大学课程学习毕业,并进入国立法官学院通过为期31个月的专业培训,在此基础上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之后经过法官工作经历和业绩的积累才能逐级晋升为最高法院法官。
当然,上述标准仅是基本标准,对最高法院法官的实际标准要求远超于此。美国法官汉德认为,“对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宪法的问题的(最高法院)法官来说,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需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蒙田、拉伯雷、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全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注:[美]亨利·J·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可见,最高法院的独特使命对法官的遴选标准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除了技术理性,职业伦理也是最高法院法官遴选的一个必要标准。在英国,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一般要考虑其个人品行,包括道德素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在美国,是否具有良好的品德操守也是被遴选为最高法院法官所必须被考虑的,有学者将之归纳为“法官候选人的品德操守,应是令人无可指责,……起码不能让人说三道四”。(注:甄树青:《法官遴选制度比较研究》,《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另外法官遴选标准还有一个生理性指标,诸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条第1项的规定,被选任为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必须年满40岁。
所以,对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选标准是所有法院中最高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整体上是最为优秀的法官群体。
其次,是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选程序,主要在法官的提名主体和决定主体上呈现差异。目前,基本上均采取提名制,主要有行政提名、司法提名和委员会提名三种具体提名方式;有立法机构决定、行政机构决定和司法机构决定三种决定方式。
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和批准。当然,在该法官遴选程序中,除总统和参议院,司法部、美国律师协会和政党的影响因素很大。在候选人选名单确定及审查中,司法部要参照其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对每一人选的背景和社会活动进行了解和分析;参议院士要由其下设的司法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召开针对每一人选的听证会,征求各方面意见;美国律师协会则在正式提名程序之前以“评级”的方式考核每一人选的素质,在6到8周之内将考核的结果报送司法部长。当然,党派利益也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遴选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政治上的选择”(富莱彻语)。
在德国,根据1951年《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联邦普通最高法院和各专业最高法院法官,由联邦司法部长担任主席的法官挑选委员会(由16名联邦议院议员和16名各州司法部门的代表组成的“32人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决定新任法官和晋升法官的人选)依法官选举法选举,并由联邦总统任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均由联邦议会选择,联邦众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分别选择联邦宪法法院两个法庭中的四名法官,并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4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4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代表众议院选择。(注: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同样,法国最高法院法官由法国最高司法委员会(协助总统实行司法监督的机构,由总统任主席,司法部长任当然副主席,以及总统依照法院组织法任命的其它10名委员组成)提名,法国总统根据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建议案任命。
在日本,根据法院法的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由天皇基于内阁的提名而任命,其余的14名法官由内阁任命,并接受天皇的认证。(注:龚刃韧:《现代日本司法透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通常,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先由最高法院事务总局制作出原案并提交给首席法官,再由首席法官向内阁总理大臣推荐,内阁最终有权决定是否任命最高法院提出的推荐人。(注:[日]小岛武司:《现代审判法》,三岭书房1987年版,第71页。)日本针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设置了国民审查制度,根据1947年《最高法院法官国民审查法》第2条规定,每名法官在被任命后第一次进行的众议员选举时,接受国民审查。所谓国民审查,是指通过国民投票的方式对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信任以及决定是否给予罢免。但至今日本并未发生过最高法院法官在任命后因国民审查而被罢免的情形。
显然,由专业机构或人士在严格审查后提名,在提名后经过审查再决定,且往往在整个过程中乃至事后都向社会公开化,允许社会尤其法界讨论批评的作法,如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参议院任命托马斯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的听证风波,是最高法院法官任命不同于其他法院法官的鲜明特色。当然,这既与人们对最高法院法官的高标准要求有关,往往也与最高法院法官事关国家未来而引发党派之争有关。
最高法院法院制度的又一项重要方面是法官保障制度,包括法官任期、法官待遇、法官晋升、法官培训等保障法官职业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各方面制度。
在法官的任期方面,目前主要有终身制和任期制两种,但基本上均倾向于从任期的长久维护上着力保障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而对法官的弹劾、罢免和辞职方面考虑较为慎重。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在“良好行为”的前提下,法官除非因违法犯罪受弹劾或者自动辞职,其职务是终身的,工作也是终身的。因此,70岁乃至80多岁的大法官比比皆是。法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法官实行终身制,法官在任期内,非因可弹劾之罪并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撤换或者强令退休。英国法官也是终身任职,只要其行为端正,法官职位就受到法律保护,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的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女王予以免职。日本宪法和法律规定,法官任期10年并可以连任,并规定最高法院法官达到法定年龄70岁时退休,同时,法官除因身心故障法院不能执行职务,或受国会弹劾裁判,或国民审查中被罢免,或由于渎职经裁判以外,不能违反其意愿进行罢免、转官、转院、停止职务和减少报酬。
当前,法官的待遇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法官待遇制度日益为各国的司法改革所关注。据有关统计,(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1988年至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年薪为110000美元,首席大法官年薪为115000美元;而从1993年至1995年,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年薪分别高达164100和171500美元。并且,美国法官的工资由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任职期间薪金不得减少,总统和国会都不得降低法官的工资数目和水平。在日本,宪法和《法官工资法》对法官的工资待遇也作了明确规定。以1990年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的收入为例,最高法院院长的月工资收入为1892000日元,达到内阁总理或国会两院议长的同等工资水平;最高法院法官则为1379000日元,相当于内阁部长的工资水平。(注:周道鸾:《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法官工资法》还规定,在法官任职期间,工资不得减额。显然,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之大法官的工资与高阶位政府官员看齐应是国外的主流作法。
总体而言,最高法院的法官制度在不同国家既存在显著共性,又存在重要差异。就其差异的原因而论,主要与对司法的尊重度、司法的政治功能、最高法院的政治地位等因素相关,也与不同国家的司法历史和法律传统有关。在这方面,美国与法国的对比就相当明显,归结到一点就是,具有司法优越的历史与社会资源的国度,其法官制度尤其最高法院法官制度就较为精英化。同时,法官制度的这种差异也反过来会影响最高法院的运作,例如,在精英型最高法院法官体系的国度,最高法院的庭审模式就倾向于采用全体式,而在职业型最高法院法官体系的国家,其审判几乎都通过分庭模式来运作。这种差异还直接影响最高法院功能的实际运行,例如,精英型法官体系的国度,其最高法院着重于统一法制、政策形成等宏观功能的把握;在职业型法官体系的最高法院,其纠纷解决功能能够较为充分的行使。
四、最高法院的权力体系
最高法院权力体系主要涵括审判性权力、立法性权力和管理性权力及其运作模式。最高法院的审判性权力是指其通过审判的方式解决个案纠纷的权力,它是司法权的最基本含义和表现形式,包括初审权、上诉审判权等。从当今各国最高法院审判权的表现形态来看,上诉审判权是最高法院审判权的最主要表现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最高法院几乎成为一切国家最重要的“上诉法院”;尽管多数国家最高法院同时拥有初审和上诉审的管辖权,但初审权实际上大都较少行使;而在有些国家,最高法院就不具备初审权。例如,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拥有初审权和上诉管辖权,在少数情况下,它也直接受理一些属于其初审管辖权范围内的案件。但事实上,美国建国以来最高法院仅仅动用其初审管辖权大约165次,1970年马塞诸塞州对印度支那战争违宪提起的初审诉讼就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拒绝受理。到目前为止,美国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能是上诉管辖,案件通过确认令、上诉状和调卷令三种主要途径上诉到最高法院。(注:[美]亨利·亚伯拉罕:《美国法院的双重体制》,载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享有初审权,可以对一些重大案件进行初审,而联邦财税法院就只有上诉管辖权,仅审理涉讼金额不低于1000马克的案件的法律方面的上诉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则既是初审法院,也是终审法院。在中国,最高法院享有初审权、上诉审管辖权和审判监督权,最高法院的初审权主要集中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疑难、重大、典型案件,但在实践中极少甚至基本不行使;目前,最高法院主要受理来自各省高级法院初审案件的上诉,同时,其审判监督权力较为强大,颇具特色。
显然,上诉审管辖权是各国最高法院的最主要审判权力,但在上诉审权力运作方面各国有特征差异,主要是在法律审与事实审、书面审与开庭审等方面的区分。从一般诉讼原理及司法技术理性出发,上诉审首先应当是法律审,正如有学者指出,“上诉应当优先针对法律问题的观点已有长期的历史,现在正成为不言而喻的。”当前大部分国家最高法院上诉审采取法律审,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就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裁判;英国上议院上诉程序只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的上诉案件。当然,在有些国家,最高法院上诉审程序也采取事实审,诸如中国。另外,最高法院上诉审程序在采取书面审与开庭审、公开审与秘密审方面,没有必然的区别,一般是宪法型最高法院可能采取书面审,而普通司法型最高法院则基于诉讼公正和诉讼经济的考虑而选择特定的审理方式。
最高法院的立法性权力主要指法律形成权和规则制定权。一方面,最高法院通过对案件的审判履行法官“造法”的功能,从而实质上进行司法立法,这在英美法系国家就很显著;而在成文法传统国家,最高法院这种司法立法功能也逐渐显示出增强的倾向。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过“抽象司法行为”来制定程序规则、证据规则等,从而进行直接的司法立法。
美国最高法院在规则制定和法律形成方面的权力相当显著。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美国,先例拘束制度使得法官“造法”成为最高法院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和事实,而对司法先例的严格遵循成为一种司法“惯习”,(注:[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86页。)这便使最高法院判例的形成本身就演化为一个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而“国会之所以将制定民事诉讼规则等的权力授予联邦最高法院行使,主要的考虑是这些规则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由最高法院在终结联邦各级法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这些规则,最为有利”,(注: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于是,程序规则的制定权便归属最高法院。
日本最高法院规则制定权及其运作程序较有特色。日本宪法第77条第1款确立了最高法院就诉讼程序、律师、法院内部规章以及司法事务处理等事项的规则(最高法院规则)制定权。据此,日本最高法院规则制定权的范围为:关于诉讼程序事项;关于律师的事项;关于法院内部规制的事项;以及关于司法事务处理的事项。确立最高法院规则制定权的根据一般认为是为了强化司法权独立的保障,也因为由明了诉讼实际情况的法院来随机应变地就诉讼程序等事项的规则进行立、改、废是合目的的。最高法院规则由最高法院的法官会议议定。作为制定规则的咨询机关,最高法院设置了四种最高法院规则制定咨询委员会:民事规则制定咨询委员会、刑事规则制定咨询委员会、家庭规则制定咨询委员会以及一般规则制定咨询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最高法院从法官、律师、检察官、有关机关的职员、学者中任命25名以内的委员组成。其宗旨在于充实强化司法权的自主性,尊重裁判程序的专业技术性,便于裁判程序的有效运作。日本最高法院于1947年制定了《最高法院裁判事务处理规则》,1948年制定了《下级法院事务处理规则》和《日本刑事诉讼规则》,1952年制定了《法院旁听规则》等。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最高法院,其立法性权力相对要弱。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传统有关,诸如,议会立法权力至上,在德国,“联邦议院是德国的最高政治机构,它在所有立法事项方面是所有的和唯一的代议机构,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在联邦议院大厦的界限之内行使权力”(注:Kay Haibronner & Hans Peter Hummel,"Constitutional Law",in WernerF.Ebke Matthew W.Finkin,ed.Introduction to German Law(1996).);成文法传统浓厚,在法国,“最高法院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才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法院,不让它偏离法律条文”(注:[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等等。
然而,必须指出,随着司法的现代化,最高法院的司法立法权能日益得到激发。在最高法院的权力机制中,“法官造法已从一个具体问题转变为一个规范性问题,问题不再在于法官是否造法,而是法官造法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所根据的价值是什么。”(注:Edward Mcwhinney,Superme Courts and Judicial Law-Making:Constitutional Tribunals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6.)法官造法,实际上成为具体司法中尤其是最高法院自然而然享有和存在的一项重要立法性司法权力。近现代政治理念从分权原理出发,特别强调三权分立中司法权的制衡作用,“人们似乎觉得,不论最高法院有多少缺点,它始终是我们的制度中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宪法法令的最独立、最不带感情色彩和最值得信任的守护人”(大法官杰克逊语)。从传统到现代之法治历程看,司法过程的性质“不是发现,而是创造”,(卡多佐语),(注: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166~167.)尤其是英美法系对法官“造法”一直抱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普通法发展到今天,大多数的法学者和律师都已倾向于认为,法律不再是以先于或外在于司法判决而存在之独立体;他们不再认为法官所作的只是从取之不尽的法律规则中作选择而已,而是共同承认了法官的造法事实,并在理论上也主张法官应该造法”。(注:Friedmann.W,Legal,Philosophy and Judicial Law-Making,61 Col.L.R.821(1961),P830.)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法典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法官造法和最高法院规则制定的空间,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典并未使法律成为一潭死水,相反的,法官们把握时机,通过创造性地解释发展了法律。在某些领域,大陆法系的法官没有守株待兔地坐等立法的变更,而是成功地将法典的抽象性条款灵活的运用到了新的社会条件之中”(注:Peter Stein,Legal Institutions--The Development of DisputeSettlement,1984,P103.);而且,最高法院“实质上通过法律救济和诉讼形式创立了新的法律权利和新的法律”。(注: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最高法院的管理性权力主要表现在对司法资源的配置和司法信息的处理;诸如法官的人事调控,法官考核与培训,法院财政安排等。它是为了确保法院系统的顺利运转并有效发挥功能,确保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和司法效率而进行事务管理的权限。就范围而言,最高法院的管理性权力包括其对最高法院系统本身的横向行政权力和其对整个司法系统的纵向行政权力。应当指出,各国的最高法院都有相当之行政管理权力,但又有差异,且在历史上往往有一个发展与变化过程。例如,在英国,上议院议长同时也是全国司法部门的首脑,负责推荐法官人选,指导其他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任命各巡回区的司法行政长官,定期召集司法行政长官会议,决定法官的增补、调配和司法财务事项,等等。(注:[德]丹尼尔·J·门多:《德国上诉法官:职业模式兼与美英的比较》,载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虽然首要是行使法官职能,但同时也是个司法管理者,作为最高法院的代表,不仅处理全联邦法院系统的行政事务,而且处理最高法院自身的行政事务。一方面,首席大法官首先是美国司法委员会的领导,而这一委员会是联邦司法体系的政策制定者。首席大法官也是联邦司法中心的主席,该中心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培训以及再教育法官。首席大法官还管理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财政预算及数据统计等事项。另一方面,首席大法官还是“最高法院大厦的建筑师”,最高法院的行政人员都受其管理。有人发现,在伯格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常常亲自处理杂务,诸如购买装饰油画、种花、调查法庭房间的灯光等等,实际上,首席大法官每周约77小时的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用于非司法活动。(注:Susan Low Bloch & G.Krattenmaker,Supreme Court Politics:The Institution and Its Procedures,West Publishing,INC,1994.)
从管理性权力角度,当今各国最高法院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强影响型最高法院和弱影响型两种。相对而言,强影响型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权力较大。例如,司法行政权在日本就显得尤为突出,战后,日本在设置最高法院的过程中,曾经围绕司法行政权的归属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结果是,司法行政权从内阁(行政部门)转移到最高法院,日本最高法院被赋予了广泛的管理性权限:第一,关于下级审法官的人事行政事务,包括下级法院法官的调动、晋升均由最高法院决定。第二,关于法院组织构成等运营管理方面的事项。第三,关于厅舍等法院各种物质设施管理方面的事项。第四,关于会计、预算、报酬等财务管理事项。为此,日本最高法院专门设立了事务总局这一机构来协助法官会议、最高法院院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注:[日]园部逸夫:《今日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课题和展望——最高法院院长矢口洪-访谈录》。)
与强影响型最高法院不同的是,弱影响型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较为有限。例如中国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无论在法官人事还是在法院财政方面,无论从制度上的功能创设还是从实际上的影响,都相当有限。从最高法院行政性功能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来看,司法行政权及其功能主要被定位为对最高法院司法性功能和政治性功能实现的日常性、辅助性、服务性功能;同时,从司法系统内部的纵向考察,最高法院的行政性权力则倾向于一种宏观控制和政策导向。
五、最高法院的案件处理机制
案件处理机制,指最高法院在审判权运作过程关于案件的选择、分配、审理、裁判等方面的程序和规则,主要包括最高法院案件选择机制、案件审理机制以及案件判决机制。其中,对于最高法院司法运作具有先决性影响的是案件选择机制。
最高法院高踞司法系统最高位阶,但是,如若最高法院对所有案件都主张司法管辖权,则严重有损司法理性。现代司法要求最高法院有选择地进行司法管辖,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律都规定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和管辖范围。现代司法发展也要求,“最高法院对提交给它的案件的审判价值予以审查,在实质上行使自由裁量权,由其自己决定对哪些案件进行审判。”(注:Susan Low Bloch & Thomas G.Krattenmaker,Supreme Court Politics:The Institution and Its Procedures.West Publishing,INC,1994.)实际上,不少国家都把是否受理案件作为最高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由其自主决定,从而与强制受理的上诉审和初审相区别。这就关系最高法院案件选择机制的存在意义了。因为,最高法院案件选择机制实质上是最高法院对司法资源配置及其运作的过程,也是对司法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这个机制的运转过程,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最高法院对审判价值、司法意义、以及司法权运作所抱持的主观姿态。当然,案件选择机制还受诸多客观因素所塑造,各国的选择机制因而呈现差异,如美国和德国最高法院就在案件选择机制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为,“德国最高法院案件选择程序主要施行法律标准,而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选择似乎更具有政策导向性。”(注:Ralf Rogowski & Homas Gawron,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Comparison:The U.S.Supreme Court and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Berghahn Books,2002.)实际上,案件选择一直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运作和审判管辖问题上的焦点。“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从数千件案件中只选择了很少一部分进行审理,所以在它倾向于对哪种案件、争议、当事人的选择方面,最高法院所公布的意见中就发出了很强的信号”,“最高法院拥有一套决定受理案件的实质性标准”。(注:Susan Low Bloch & G.Krattenmaker,Ralf Rogowski & Homas Gawron,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Comparison:The U.S.Supreme Court and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Berghahn Books,2002.)
美国最高法院在案件选择方面具备丁一套较为成熟和良好的机制及经验。在美国,最高法院每年收到6000多个案件,而审理的不足150件,案件选择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滤掉大部分案件不予复审,而案件审理机制的主要使命则是极力彰显所选择案件的审判价值。而“选择案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随后的判决过程”(赫尔曼语)。美国最高法院案件选择机制,部分基于法律的设定,比如法律对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力范围的设定(如对两个或以上的州之间的争议享有初审而排他的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就发挥了分配案件的作用。同时,调卷令程序机制在美国最高法院案件选择机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据统计,联邦最高法院在1953年院期,收到1302个申诉,复审115个案件;1963年院期,收到2294个申诉,复审142个案件;1973年院期,收到3943个申诉,复审142个案件;1983年院期,收到4201个申诉,复审180个案件;40年间申诉增加了4倍多,而受理的数量却基本没有增加,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调卷令程序机制。(注:Susan Low Bloch & Thomas G.Krattenmaker,Ralf Rogowski & Homas Gawron,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Comparison:The U.S.Supreme Court and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Berghahn Books,2002.)当然,在美国最高法院案件选择中,法官的经验也是一个影响因素,“通常一个案件是否值得复审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确定的规则问题”(哈兰语),有学者就指出,“最高法院对所有案件进行监测,这使它找到其司法权力运作的目标,使它具有何时何地有必要运用这种权力的直觉。”而诸如涉及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民权问题、法律发展问题等便是最高法院案件选择过程通常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日本,最高法院的案件选择和决策过程也常常被置于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大环境下加以考虑,和美国一样,“两国最高法院都形成并始终运用可以充分确认通往最高法院的有规律的方便途径及制度程序,但同时它们也都发现运用严格的案件选择程序来消除鸡毛蒜皮的案件或迅速处理案件的必要性”,“研究职员(Chosakn)在日本最高法院的案件选择机制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注:John R.Schmidhauser,Comparative Judicial System:Challenging Frontiers i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ButterWorkths,1987.)
在案件审理和判决机制方面,最高法院往往区别于地方各级法院。就案件审理机制而言,最高法院一般具有不同于下级法院初审和上诉审的特征:首先,它不是以庭审为中心的机制。尽管可能也有庭审,但实际上案件处理的重心阶段,在于庭审之外的思考、讨论与论争、妥协阶段。这在美国最高法院表现就很充分。其次,它的庭审具有不充分性、象征性。一方面,最高法院庭审往往不具有对抗性,法官职权色彩浓厚。在美国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往往打断双方的陈述,而直接与律师进行口头的问答,且这种问答有可能带有质问性。(注:John R.Schmidhauser,Comparative Judicial System:Challenging Frontiers i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ButterWorkths,1987.)而在德国联邦法院,甚至有时候一方律师不出庭。另一方面,庭审往往较为短暂,美国最高法院庭审口头辩论的标准时间为1个小时,笔者在德国看到过联邦法院仅用20分钟审理案件。就案件判决机制而言,最高法院也与各级法院往往有别,表现为,首先,判决一定要制作判决书,在判决的形式要素方面不同于某些下级法院的初审判决;其次,判决书的形成往往要精推细敲,反复思考,在判定的规范性和说理的充分性上有着更高的要求;再次,判决有可能存在意见冲突,往往有反对意见或附随意见,以美国最高法院为典型,充分表现出判决机制本身的民主特征;最后,为达到判决往往有一个妥协过程,这与最高法院判决利益的多元性和司法对社会利益分配和权衡的客观要求有关。
必须指出,最高法院案件处理机制的特征与几个因素相关:首先是最高法院功能的特殊性,最高法院的个案纠纷解决功能相对于其统一法制和政策形成的功能的价值有限性,决定了最高法院的受案范围和解决案件的独特模式;其次是最高法院地位的独特性,最高法院高踞于整个司法系统的顶端,又是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政治性机构,它在案件的安排和处理方面自然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显要性。同时,最高法院的案件处理机制和模式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治理理念及其司法对社会整合理路的一个映射。
六、最高法院的发展与改革
最高法院发展与改革日益成为各国司法改革以至政制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最高法院也提出了加强自身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涵括了制度建设、功能健全、组织体系优化、法官制度完善、权力机制、运作程序改革诸多层面的课题渐渐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世界范围内最高法院改革和发展呈现的若干趋势,也应为中国最高法院改革所借鉴。
其一,最高法院宪政功能的强化。最高法院宪政功能的健全成为近代特别是现代最高法院发展的主题之一,宪政功能在二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表现尤为显著。这主要表现在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功能的获得和推行,最高法院在各国宪政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因此,”宪政型最高法院”的建构成为当今法治国家建设最高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一个目标。它要求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功能,监督宪法实施,保障民众的基本宪法权利,推动宪法司法化,实现最高法院的宪政价值。中国最高法院是否以及如何进行违宪审查值得思考。
实际上,中国最高法院2001年(第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就从实质上提出了这个深刻的宪法问题: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能否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与受教育权纠纷一案因此被赋予深远的宪政意义:开创法院保护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宪法司法化的先河。(注: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以此为契机,学界热列呼吁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当前,孙志刚案更是引发了强烈的违宪审查启动风波。在中国,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功能的创没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违宪审查已不是一个应否创制,而是如何创制的问题。基于我国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当前,我国应当建构“宪政型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笔者以为,适应我国国情的这种制度模式应当是司法型最高法院与宪法型最高法院双重违宪审查主体的一种互动机制。(注:关于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参见左卫民、谢进杰:《历史、模式与理念:最高法院违宪审查论》一文。)
其二,最高法院司法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基本趋势是最高法院的传统功能——司法功能随着“法院制度现代化”(注: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的演进,其纠纷解决功能也逐渐演化为主要是针对典型、疑难、重大个案的纠纷解决,而最高法院在判例形成、法制统一、司法政策形成等“抽象司法行为”的宏观层面功能得以彰显。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性功能和行政性权力分开设置而运作,最高法院的行政性权力聚焦于法官的职业素质培训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上也成主流。对于中国最高法院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可能需要淡化个案纠纷解决功能,强化法制统一功能。其方式也需要改革,如判例功能是否强化就需要思考。同时,是否与如何淡化目前过多过大的行政性权力,如不必要的内部机构,又强化在中国国情下所需的宏观权力,如是否及如何管理下级法院的资源乃至负责部分人事问题就值得思考。
笔者认为,中国最高法院司法的现代化有赖于最高法院功能的分化与优化。首先,最高法院纠纷解决功能应该弱化,严格限制在对典型、疑难和重大上诉案件的解决上,主要行使上诉管辖权,取消最高法院初审制度。其次,最高法院的法制统一功能应当强化,主要通过规则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实现。再次,最高法院的政策形成功能应当逐渐凸显,发挥最高法院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方面的影响。同时,最高法院的功能优化有待于其在程序化、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的规范和加强,如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就可考虑借鉴立法程序模式而公开化、民主化与科学化。
其三,最高法院精简化、精英化。最高法院的机构设置直接影响了司法运作的模式,从有益于司法运作的角度出发,最高法院应精简化,注重司法审判机构和司法业务服务型机构设置的科学性。从现实与发展看,最高法院法官制度的法官精英化正是趋势。中国最高法院的改革关键之一可能在于如何改革法官制度,精简法官数量,如何选拔与吸收最优秀的法界精英组成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当然,是否以及如何构建标准,创制程序,都值得思考。
具体而言,最高法院的精简化一方面在法院内部机构的精简化方面。最高法院的审判部门、管理型机构与服务型机构的设置应当从重要性和必要程度考虑。另一方面,在法官精英化建设方面,全国性法官职业水平的强化是一个趋势,但法官体系的建构应当分具体情况考虑,最高法院精英型法,官体系和下级法院职业型法官体系的双重结构建设应当是中国法官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中长期目标,中国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应当控制为50至100人之间,并重点在法官选拔上作改革,最高法院法官结构应当充分融合优秀学者、律师、检察官、政府官员和法官的知识构成。
其四,最高法院改革的过程性。最高法院改革和建设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有确定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及相应步骤和措施,根据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二战后乃至20世纪90年代,各国设置并运作宪政性最高法院的成功经验便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中国最高法院的发展与改革也有一个过程性,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设定及相应努力过程。同时,针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最高法院的发展与改革也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违宪审查模式便可因中国立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与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而有差异,又如,是否设置最高法院分院以控制行政与地区差异、限制不当司法如过多复核死刑便值得思考。
总之,由于高踞司法系统的最高位阶,最高法院自身的改革对整个司法改革会发生引导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积极、稳步展开的改革,是可以此带动整个司法系统建设和司法改革的有序展开。在这一点上,中国最高法院的发展与改革也应当如此。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违宪审查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美国大法官论文; 法院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 司法部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