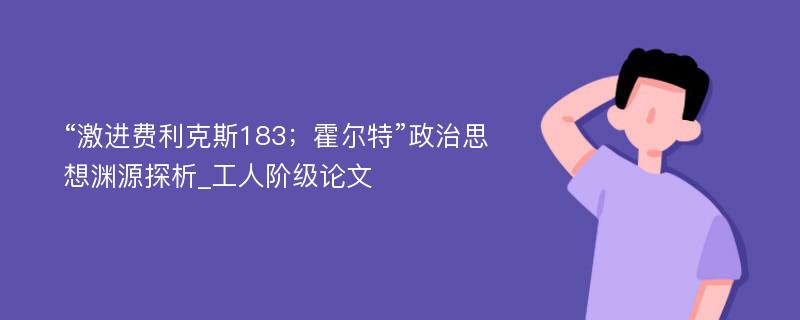
《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183;霍尔特》政治思想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尔论文,激进论文,主义者论文,政治思想论文,菲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乔治·爱略特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霍尔特》(后文简称《激》)的政治主题,部分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小说。F.R.利维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该小说的重点是特兰姆森夫人深刻动人的悲剧,其余情节几不足取。①然而,由于这部小说将1832年英国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前后的社会状况作为主题,并用特雷比马格纳地区议员选举和工人暴乱作为重要的情节支撑,它依然被普遍认为是爱略特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说。② 小说第三章写道:“特雷比马格纳地区的社会变化主要是公共事务,而历史主要牵涉到少数男性和女性的私人空间;但没有一种私人生活不是由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③所谓“广大的社会生活”即作为民主时代表征的政治选举,它带来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困惑:政治经济改革、阶级之争、道德改革等等。保琳·纳斯特曾指出,“第一章一开始就宣告小说专注于令人难忘的1832年,那一年颁布了第一次改革法案。而且这部小说写于1865年3月至1866年5月,这是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前夕争论最激烈的日子。《菲力克斯·霍尔特》是对时政的一次最直接的尝试”④。在讨论小说的政治思想时,评论界往往将爱略特对时政的回应集中在菲力克斯的激进主义上,普遍认为他的激进主义存在于道德层面。纳斯特认为,“这本爱略特最公认的政治小说悖论性地缺乏对政治的兴趣。它的政治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政治”⑤。南希·亨利也认为,“爱略特在狭义上理解政治,她着力描写菲力克斯生活的历史环境,是为了表现政治是检验道德伦理的手段”⑥。这类评论承袭了从伦理学角度解读爱略特小说的批评传统,没有充分揭示《激》在政治思想史层面的价值和内涵。此外,关于主人公之一哈罗德·特兰姆森政治立场的评论更是寥寥,往往将他定性为道德上的自利者,将他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一笔带过。 依笔者之见,小说题目中的“激进主义”一词正是理解爱略特政治思想的突破点。哈罗德与菲力克斯的激进主义不仅反映了英国社会两次改革法案期间的政治风云,也体现了爱略特深邃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描写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生活的《罗慕拉》不同,《激》不但涉及19世纪英国社会的民主改革进程,也表明爱略特的政治思想更具中产阶级倾向,她对民主改革、阶级冲突、激进主义的看法存在着不平衡与相悖之处。本文拟从“激进主义”的定义入手,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现实为参照,通过解析民主气氛下哈罗德和菲力克斯分别代表的两种激进主义的内涵,对该小说再现的政治思想进行探源。 一、哈罗德·特兰姆森: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据雷蒙·威廉斯考证,radical的拉丁文词根为radicalis,意思是“根本的、彻底的”;“激进主义者”常被用来指激进的改革分子,他们提倡的通常是影响较为深远、较为激进的改革。⑦英国辉格派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于1797年首次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激进主义者”这个称谓,倡导进行一场赋予所有男性选举权的“激进改革”,故激进主义者也常被用来指称所有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人。⑧ 按照上述定义,哈罗德·特兰姆森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一名激进主义者。他竞选的最终目的是“进入议会”(Felix:100)。但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哈罗德的激进主义存在两大疑点:其一,他身为乡绅,完全可以利用托利派的政治身份参选,那么他为何要表明自己是激进主义者?其二,他倡导的激进改革是为了赋予所有男性选举权吗?换言之,他是一位彻底的激进主义者吗?阿诺德·科托认为,哈罗德的政治立场体现了统治阶级在民主大潮中的畏惧心理。⑨然而,仔细探究哈罗德的政治身份,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激进主义立场非但不是源于恐惧心理,反而恰恰反映了经济改革背景下贵族与中产阶级结合后的新男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参与和热烈诉求。在小说第七章,叙述者指出了哈罗德暧昧的性格特点:“他同时沉醉于反抗和顺从……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由理论划分,而是沿着一个早年性情和回忆所决定的不规则之字形展开。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定,那就是某一天重新成为真正的英国人。这使他形成了关于英国政治和社会情况的所有决定。”(Felix:102)这段引文的点睛之笔是“反抗和顺从”,这种性格特点既源于哈罗德的早年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和人生目标。 哈罗德回国第一天,就宣布自己是激进主义者。特兰姆森夫人警告哈罗德,说他“应忠实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更别说推翻自己的阶级”(Felix:35)。虽然在英国政治传统中乡绅阶级历来是支持皇权与教权的托利派⑩,但哈罗德的回答却充满了对过去的憎恨:“他[哥哥]总算死了,可怜的人。我一直以为会花更多的钱买一处英国房产。我一直想成为一个英国人,暴打在伊顿痛打过我的那几个勋爵。”(Felix:16)话虽不多,却包含三层意思:哈罗德终于因为兄长去世而继承了特兰姆森庄园;早年他因为没有继承权而受到其他贵族的羞辱,现在是报复的时候了;最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应该拥有财产。在哈罗德眼里,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羞辱实际上都是围绕财产权展开的。如今他不但继承了特兰姆森庄园,而且早已发迹,1832年从土耳其港口城市士麦那回到英国时,他的财产已接近15万英镑(see Felix:98)。 在某种程度上,从东方经商回来的哈罗德已抛弃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意愿是顺应国家经济条件要求的每一个变化,他对那些马车上有爵位的人愤怒而不屑……更尊敬那些没有徽章却有极大影响力的人,这些影响力通过国家常识和大众日益增加的自我权利主张而达成,这是一种迫切的要求。他自己就要成为这样的人。”(Felix:102)此处“无徽章却有极大影响力的人”指的是工业革命中冉冉上升的中产阶级。哈罗德虽身为上层乡绅,他的个人经历、财产来源和世界观却属于新时代,他的归来给处于封建制度下的特兰姆森庄园带来了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效率、经济和人际关系。作为英格兰社会的象征,特兰姆森庄园拥有复杂的过去、急速变化的现在和因哈罗德继承而不再确定的未来。庄园所有权的转变正是社会变革的一场隐喻,而变革的根源则来自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政治资本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 事实上,从准备创作《激》开始,爱略特就一直努力熟悉1832年改革法案背后的经济背景。1865年,她在信中写道:“我近来最常读的就是穆勒的书。”(11)她反复阅读的正是J.S.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爱略特在小说笔记中不仅摘录了《政治经济学》中“论收入”的脚注,如“从1751年起,劳工收入情况得到明显改善,虽然和季节有一定关系,却也已持续了一代人之久”,还从1833年议会农业报告中摘抄了许多数据,如“耕地租金每英亩40至60先令;放牧区35至45先令;劳工收入每周10先令”(12)。这些数据和小说情节看似关系不大,但说明爱略特已意识到英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与政治改革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小说完成后,爱略特还特意加上了前言部分(see “Genesis”:579)。在前言中,一派乡村风味的老英格兰与深受社会经济影响的新英格兰形成了强烈对比:“土地被矿井涂黑、纺织机发出的格格响声传遍小村庄……工业城市的气息……弥漫在四周的乡村,空气中满是躁动。”(Felix:4)叙述者将读者视线带入一个变革中的社会空间:1832年左右,工业革命高歌猛进,它打破了贵族阶级的垄断地位,崛起的工商业主,即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小说第三章进一步展开了工业革命与封建社会的冲突:“特雷比马格纳以前是个受人尊敬的集镇,贸易只与当地乡绅利益有紧密联系,现在煤矿和制造业使它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后者直接与全国的大流通体系相联系。”(Felix:42)小城首先修了运河,接着建了矿,随后又被外来人变成一处时髦的温泉城。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而中产阶级则承担着工业化进程的领导责任。 随着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突飞猛进,他们在政治民主中也开始崭露头角。1832年,英国政坛最重要的争论是:“历史悠久、风景如画却有名无实的老选区是否应当保留?或者应当废除以使强硬的中产阶级取得选举权?”(13)当时,伯克的托利主义已经死亡,整个托利派的领导权掌握在兰开夏郡一位制造商的儿子罗伯特·皮尔手里,这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托利派不但支持选举改革,还希望对整个社会制度做出谨慎而彻底的改革。(14)最终,第一次改革法案于1832年获得通过,作为英国代议制向工业化倾斜的重大进程,它使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大城市获得下议院席位,将选举权第一次扩展到中产阶级。(15)“改革者们胜利了:他们走向哪车轮就转向哪。”(Felix:44)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攀升,罗杰·金这样评论:“在1832年和1867年两次改革法案之间,中产阶级在法律和机构变化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16) 哈罗德顺应潮流选择了激进主义立场,他不仅在离国期间一直关注英国政治走向,而且决意把竞选作为从经济市场到政治市场的一种实际投资:“改革是多数人的意愿。潮流一定会走向改革和激进主义。”(Felix:95)他“最强烈的目标就是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进入议会,成为北罗姆郡在各个方面都举足轻重的人物”(Felix:100)。19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激进主义者的别名。1820年左右,人们常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议会中的辉格党人和激进分子(详见《关》:263)。由于哈罗德的终极目的在于“举足轻重”,因此他的政治选择是通过竞选进入下议院,而不是依据传统利用自己的贵族身份进入上议院。沃特·白芝浩在《英国宪法》里曾对上下议院的不同性质提出深刻见解。他认为,宪法由“高贵”和“有效”两部分组成。高贵部分的代表是女王和上议院,他们是旧时代的象征,没有多少实权;而有效部分,即中产阶级,则通过远距离的操控实施权力。(17)白芝浩继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这种代理关系:“英国表面上的统治者是游行队伍里最吸引人的部分,他们影响大众,观众也为他们喝彩。但真正的统治者却偷偷坐在二等马车里,没人理会或谈论他们,但他们的意愿却被那些走在前面、挡住他们光辉的人所遵循。”(Economic:76)这个比喻突出了二等马车里中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难看出,哈罗德已不满足于有名无实的高贵地位,在“托利派已成为太古动物”(Felix:90)的时代,他放弃了传统的乡绅政治,希望以非传统的激进主义者身份进入国家机器的有效部分,获得实权。 哈罗德将自己称为“新人”,企图将历史上的腐败一笔勾销(18),但小说细节却提示,哈罗德的性格又保留“顺从”传统的一面。其实在英国历史上,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历来就不是敌对的两个阶级。早在工业革命以前,中产阶层便已通过通婚、买地等手段与贵族阶级相互交织,第一次改革法案更使中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上层阶级稳固的政治联盟。新兴的中产阶级始终表现出融入旧“封建”制度的意愿,希望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得到尊敬,而不希望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当许多暴发户变得受人尊敬时……他们也就不再是锐利的社会改革派了。”(19)与这些被旧秩序纳入的暴发户不同,哈罗德本来就是上层阶级的一员,他不但在伊顿完成学业,而且继承了本乡最古老的庄园。因此,尽管他在政治上采取“非传统”的立场,却并不如彻底的激进主义者一样,希望唤醒游行中欢呼却无知沉睡的大众,更没有像宪章主义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做出过任何帮助所有男性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哈罗德革新的外表下始终潜藏着对旧秩序顺服的一面,埃丝特的顿悟就是对哈罗德政治立场的深刻总结:“他对自身优势沾沾自喜,他把家庭和地位的骄傲与对变革的支持融合在一块,这些变革将要磨灭传统,将镂刻的金色祖传物销熔并化为‘人民’蛋匙的镀层。”(Felix:379) 在埃丝特看来,哈罗德支持的是加上了引号的“人民”,其中的讽刺意味引人深思。探究激进主义与人民的关系,就需要联系19世纪英国社会的民主风潮。在大多数对“英国民主发展”的记述中,所谓“民主”是“有限制的选举制度”,选举权被刻意限定为“某一群具有资格的人”的权利。通过第一次改革法案,英国选举人数从439000扩大到656000人,涵盖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19)由于担心无地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也许会在政治上形成压倒性力量,英国选举权与财产和赋税情况一直联系得很紧密,如第一次改革法案要求选举人需同时交纳房税和税赋,每户税赋高达十镑(详见《关》:113-114)。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证明,政治问题背后总是隐藏着经济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如果没有财力支撑,竞选人根本不可能参与竞选。爱略特在笔记中摘录道:“我相信弗兰克·劳利在沃威克郡的竞选中花了接近三万镑。”(“Genesis”:583)不难想象,哈罗德15万镑的丰厚财产带给了他“极大的权力”,因为“选举对财产的要求在不断增长”(Felix:98)。纵观整部小说,哈罗德从未提出过任何赋予所有工人选举权的政治主张,作为游行队伍前面和二等马车里的集合体的一员,他代表的绝非那些“在矿井里双膝跪地前行”(Felix:4)的普通工人,他心里的“人民”仅限于刚获得选举资格、用着“镀金蛋匙”的中产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爱略特笔记中提到了一点,即,行贿纵酒的情况在1832年选举中非常普遍。她对当时的《行贿报告》有详细摘录:“甜面包酒馆。给工人们发酒券,引诱他们去竞选日助威。法案公布后,招待就停止了……两个持对立观点的竞选人往往为这笔招待费分账。”(“Genesis”:583-584)小说中1832年竞选日这天,激进主义者哈罗德、托利派迪伯瑞、辉格派加斯丁都在参与这种行贿工人的活动。这也再次证明,第一次改革法案颁布后,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依然是与贵族联姻的激进主义。 二、菲力克斯·霍尔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 爱略特将《激》的故事背景放在1832年,当时“热心的改革者对政治改革疯狂又信心十足”(Felix:179)。小说的发表时间是1866年,此时英国正在经历第二次政治改革高潮,经过二十多年相对稳定后,英国社会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阶级不断要求获得选举权。1864年,自由党领袖W.E.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发表声明,支持将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最终第二次改革法案于1867年正式通过。在这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中,爱略特创作了小说《激》,作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回应。在《随笔》中,爱略特写道:“对历史的诚实想象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现在和未来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设计出达到政治或社会变化的具体步骤。”(21)如果说哈罗德的激进主义更倾向于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联姻,再现了第一次改革法案中的激进主义政治风潮,那么作为小说主人公的菲力克斯则更关心工人阶级的选举权问题,他的激进主义与第二次改革法案及19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结合得更为紧密。可以说,菲力克斯的激进主义立场正是爱略特政治设计的充分体现。但令人狐疑的是,尽管菲力克斯在小说中再三申明自己的激进主义立场比哈罗德的立场更为宏大深邃,希望“比选举权走得更深,一直走到根底”(Felix:247),叙事者对他的评价却是“表面上的激进主义者”(Felix:46)。 要深入理解菲力克斯激进主义的悖论性,我们需要考察19世纪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后,工人阶级仍然没有选举权,进一步改革议会的任务主要由宪章运动者担任,他们常被称为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see Economic:200)。在19世纪30年代成形的宪章运动共有六项目标,即,每位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对议员不设财产限制、向议员付工资以便穷人也能参与政治、同样规模的选区、议会每年选举一次。(22)从宪章主义纲领可以看出,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不仅要求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也要求以经济平等为基础的平等社会地位。(23)对于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而言,政治选举改革只是社会变化的工具,他们的目标是整个民主进程和下层工人的物质富裕,以最终实现英国社会的完全转变。能否赋予大众权利,能否使他们掌握命运、发出声音,这是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需要应对的问题。菲力克斯的回答不但充满矛盾,而且言行之间也体现出极大反差。 小说中,菲力克斯曾两次明确提出过自己的激进主义思想。他对哈罗德坦言:“我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愿意一生反对特权、垄断和压迫。”(Felix:168)在议员提名日演讲中,他告诉集会工人:“我希望工人们享有权利。我自己就是一个工人,不想成为任何其他人。”(Felix:272)然而,紧接着他就告诫工人: 有一种权利是花巨大的代价和劳动来除掉传统,进行浪费和破坏,残暴地对待弱小,欺骗与争吵,讲有毒的废话……这种权利是无知大众的权利……你认为它能管理好一个伟大的国家、制定智慧的法律、给百万群众提供住房、食品和衣物吗?无知的权利最后等同于邪恶的权力,带来苦难……我要强调的是,选举权并不能给你们带来有价值的政治权利。(Felix:272-273)整个演讲过程中,菲力克斯一直使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来指涉工人。与此相对,为哈罗德造势的代理人约翰逊却依靠宪章主义纲领吸引了很多工人听众。他说,“如果没有饥饿感,我们大可以逍遥,但我们的肚子促使我们开工……如果我们工人要享有权利,必须有全民选举权、年度议会、投票权和选区”(Felix:271)。与约翰逊巧妙地将自己扮演成“我们”不同,菲力克斯使用的第二人称模糊了他的阶级身份。如哈罗德一样,菲力克斯的阶级身份其实也充满矛盾。他的父亲是闻名乡里的医生,他本人也曾学医五年,生来就是一名地道的中产阶级,只是出于对药品的效力感到失望,才当上钟表匠。这里,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对立。群体身份意味着群体成员对自身特点具有一种清晰的共识,这种特点形成与其他群体的区分。(24)约翰·特纳提出,群体的形成是主体表现出某种形式的集体行为,成员间相互吸引。(25)很明显,群体身份建立在“我们”这个意象上,与“他们”或“你们”是相对的概念。虽然菲力克斯一开始便强调自己的工人身份,但他的演讲不但缺乏与工人的共识,还透露出一种“你我”之间的差距,显得居高临下,反映出他心中工人激进主义者的形象是破坏者与无知者。可以说,虽然菲力克斯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工作,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属于中产阶级。 菲力克斯的集会演讲发表于1832年。回顾历史,1829至1834年间英国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工会不仅得以合法化,罢工游行运动也此起彼伏(see Economic:229)。尽管菲力克斯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也是激进主义者,他对工人运动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例如,议员提名日这天,他明知有工人集会却不愿前往,还抱怨说:“我没有特别的事要做,但也可以去,就把这当成度假吧。”(Felix:265)在最重要的竞选日,他一直待在家里修钟表,直到工人的喧闹声越来越大,才出门“站在一边看人群缓慢疏散,恢复平静”,接着又奔向埃丝特家告诉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Felix:286)。当工人们涌进托利派的特雷比庄园劫掠时,他更是一马当先,告诉太太们“救星[骑兵]立马就要来了”(Felix:298)。这里的“度假”、“害怕”、“救星”提示读者,无论就言谈还是行为而言,菲力克斯都算不上是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他更像一位与托利派之间存在隐秘关系的局外人。因此,许多评论家都把菲力克斯称为极端保守主义者,早在1890年雅各布斯就曾写道:“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是保守主义者,他甚至算不上托利—民主派。”(26)如哈罗德一样,菲力克斯由于具有中产阶级身份属性,在政治上与保守派形成了联盟关系。从维多利亚时期工人教育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也反映出中产阶级在民主风潮中的自我政治设计,他的“激进主义”表现出爱略特对工人教育和社会责任的思考。 由于惧怕“无知的力量”,菲力克斯最重要的行动是每周到小酒馆去劝说工人参加夜校,试图将那些“混乱、恐慌的羊群”(Felix:299)纳入麾下。在他眼里,“100个工人里有70个不清醒,70个里一半只知道喝酒……另一半无知、卑鄙、愚蠢”(Felix:274)。他对工人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叙述者的态度。在竞选日,叙述者以貌似中立的口气谈到那些“愚蠢的乌合之众”,描述“这群疯人盲目的愤怒”如何使他们爆发出“野蛮的咆哮”(see Felix:292-293)。小说在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在菲力克斯和叙述者眼里,工人只是一群没有人性的暴徒吗?小说的答案是肯定的。菲力克斯认为:“如果情况还是和眼下一样,选票永远不会给你们带来值得拥有的政治权利,如果你们走上正道,就算没选票你们也迟早会得到权利。”(Felix:273)可见,菲力克斯强调的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的前提,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工人“走上正道”。因此,小说的侧重点在这里不再是民主改革本身,而是工人的自我改造。 1868年,爱略特发表了《菲力克斯·霍尔特向工人的致辞》,它既是对小说的发展,又是小说的脚注。在这篇随笔中,菲力克斯向刚刚获取选举权的工人发表演讲,他回顾了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的时代,并重点谈到1832年在特雷比马格纳发生的暴行。他维持了自己在1832年演讲中的看法,认为盲目的工人如同无知的灌溉者,任其发展只会带来和自然灾害一样严重的政治灾难,带来“可怕的不幸”、“内战”、“兽性”与“疯狂”(Essays:283)。在他看来,工人需要文化与秩序的监护人,因为“愤怒是一匹战马,它需要一位骑手”(Essays:278)。他同时将民主改革与国家秩序和精英文化联系起来:“将这些拥有知识财富的阶级推翻,让他们退出公共事务,突然停止他们闲适生活的来源,剥夺他们发挥卓越影响力的机会,你们干的事就和法国那些短见者一样”;“特权……孕育着优秀”(Essays:285);“现在使社会稳步前进并减少邪恶的唯一安全办法,不是直接去掉阶级区分和阶级特权……而是将阶级利益转化为阶级功能或责任”(Essays:281)。最后,他警告说,如果工人不听话,“政府会以枪炮的形式将无知的贱民扫除干净”(Essays:284)。 《致辞》的发表与小说出版时间仅隔两年,表达了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但在内容上从对工人的不信任发展到对拥有特权的中上层阶级的维护,在语气上从对工人的谴责上升到严肃警告。很难想象,《致辞》的演讲者是一名终生以反对特权垄断为目标的激进主义工人代表。这篇随笔以简单直接的笔触将工人教育推向工人运动的反面,明确了小说中语焉不详的工人教育内容。不难看出,菲力克斯倡导的教育是在精英文化庇护下工人“人性”的自我改造,否定以法国大革命式的突变方式改造英国社会。如马修·阿诺德一样,爱略特对工人运动持怀疑态度,希望将权力交给拥有“知识、科技、诗歌、高度思想、感情、习惯、保留伟大记忆”(Essays:285)的最聪慧的阶级。1865年,穆勒当选议员后,爱略特发出欢呼:“一个人完全凭智力出众当选,真是良好的开端,这将创造一个新时代。”(Selections:301)在爱略特心中,智性的力量显然高于无知的力量,工人的自我改造应当先行于政治行动。 但另一方面,爱略特又认为工人教育应当受到限制,这点体现了亚当·斯密对爱略特的影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把人类社会形容成一个大棋盘,棋手尽管希望控制棋局,却因为棋子各怀目的而操控失败(27),爱略特将此比喻引入小说:“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棋子都热情而聪慧,这盘棋会是什么局面……如果马突然狡猾地移动到一个新格子去,如果象哄骗兵换位,或者兵因为仅仅是卒子而憎恶你,自行逃离使你突然被将死……你也许会被自己的棋子打败。”(Felix:259)棋手与棋子的关系正是阶级关系的隐喻,如果说棋手的任务是从高处控制棋局,那么棋子的驯服则是赢得比赛的先决条件。从中上层阶级的角度看,改革进程的顺利发展需要防止工人具有过度的自主性,即避免所谓“疯狂”。在创作笔记里,爱略特曾就民主与驯服的关系提出明确看法:“民主对于恭顺精神是一个不利因素……民主在本质上强迫人平等地对待事物,而不是认为某个人更值得重视,也谈不上尊敬个人地位。”(28)《致辞》里的菲力克斯不仅再度扮演了精神上的领导角色,而且希望将社会等级制保持下去。自我改造被他转化为保留阶级特权的正当理由,阶级差异也变身为文化差异得以延续。如琳达·罗伯特森所言,菲力克斯“没有挑战阶级体系,他希望工人在自身的阶级角色中履行义务”(29)。在这个意义上,“走向根底”与“表面上的激进主义者”不再矛盾,而是高度统一。 1790年,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中曾提到完全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因为民主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群众力量,少数人(特别是拥有大量财产的富人)将会被这种力量压抑(详见《关》:114)。以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为目的的民主政治与私有财产权之间显然存在对立关系,而爱略特对群众力量的具体阐释和对少数人特权的维护,与她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有一定联系。随着声名鹊起,爱略特的财富不断增加,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她的客厅挤满了伦敦最优秀的“知识贵族”,维多利亚女王的公主们也热情邀请她共赴晚宴(see Selections:285)。在给出版商约翰·布莱克伍德的信里,爱略特写道:“你知道金钱的问题对我有多么重要。除了钱以外我不想要这个世界给我任何东西。”(30)1863年,她“以非常奢侈的感觉”购买了摄政公园附近的新家(31);1866年,她将小说《激》以5000镑的高价卖出,并在出版日前与李维斯奔赴德国休养,“那里的温泉真是无与伦比的奢侈”(32)。很明显,“奢侈”与以触动财产权为基础的革命方式相互抵触。在谈及改变世界的方式时,乔治·奥威尔的观点很有见地,他认为有两种方式改变世界,一种是通过重新分配财产的革命方式,另一种是基于教育的道德手段。(33)爱略特在小说与《致辞》中均倡导以工人教育为政治改革手段,将阶级利益转化为阶级责任和普世的社会共同目标。但是,与其说她是天生的道德家,毋宁说她对工人教育的重视乃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大潮中提出的妥协之道。 联系小说与《致辞》,可以看出,菲力克斯的两次演讲表面上都充满信心和权威感,但背后却隐藏着悲观与焦虑。这种不安其实从小说一开始就存在。前言中,叙事者叹息道:“荆棘丛和厚皮树干中隐藏着多少人类的历史,那仿佛无动于衷的树枝间又埋藏着多少难言的呼喊,鲜红的热血浇灌着长夜睡梦里永不平息的记忆和颤抖的神经。”(Felix:8)这些被树林隐藏起来的工人的昏沉与痛苦仿佛一股无声而危险的暗流,成为英国民主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爱略特曾在1866年的书信中感叹:“改革的美在于如果成熟运作,人们将会变成自由体——我希望这种预言是真的,但成熟的操控现在还没有到来。”(Selections:311)将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作为小说标题人物,爱略特实在用心良苦,不仅突出了小说中政治主题的重要性,也暗示了工人问题是小说隐含的重心之一。 爱略特在《激》中将重点落在激进主义政治和在此背景下发展的工人阶级普选权运动两个方面,整部小说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中心困境:阶级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博弈。由于爱略特面对的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是她思考的主要问题。乡绅哈罗德以激进主义为外衣,表达了新男性顺应时代却缺乏原则的政治诉求,以工人形象出现的菲力克斯则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对激进主义的反驳:政治法制的改革与工人的自我改造哪一个应该走在前面?爱略特将菲力克斯与哈罗德放置在不同的阶级空间。在小说结构上形成对位关系,两位主人公恰似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他们看似矛盾的激进主义却几乎同时表达了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与恐惧,对特权的蔑视与崇拜。他们从对激进主义的向往走向理想的幻灭,哈罗德的竞选以失败告终,菲力克斯则由于领导工人运动被投进监狱。在这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激进主义与保守力量的较量中,社会经济的变化带来政治法制改革,民主在表面上意味着人人平等,然而这些变化是正是负?改革到底应该如何领导,由谁来领导?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是否仅有法制改革就能解决个人、阶级、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激》恰恰指出了政治的局限性。 注释: ①See 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London:Chatto & Windus,1948,p.50. ②See Nancy Henry,"George Eliot and Politics",in George Levin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8. ③George Eliot,Felix Holt,the Radical,London:J.M.Dent,1980,p.4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Pauline Nestor,George Eliot:Critical Issues,Basingstoke & New York:Palgrave,2002,p.106. ⑤Pauline Nestor,George Eliot:Critical Issues,p.112. ⑥Nancy Henry,"George Eliot and Politics",p.139. ⑦详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79-38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详见《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70页。 ⑨See Arnold Kettle,"Felix Holt,the Radical",in Barbara Hardy,ed.,Critical Essays on George Elio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p.108. ⑩See D.C.Somerwell,English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Methuen & Co.Ltd.,1960,p.74. (11)George Eliot,Selections from George Eliot's Letter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30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2)See Fred C.Thomson,"The Genesis of Felix Holt",in PMLA,74(1959),p.57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D.C.Somerwell,English Thon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73. (14)See D.C.Somerwell,English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73-74. (15)See Robin Gilmour,The Victorian Period: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1830-1890,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3,p.169. (16)Roger King,The Middle Class,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1,p.52. (17)See Trevor Ma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760-1970,London:Longman,1987,p.7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8)See Lenore Wisney Horowitz,"George Eliot's Vision of Society in Felix Holt,the Radical",in Karen L.Pangallo,ed.,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George Eliot,Westpor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4,p.134. (19)Robin Gilmour,The Victorian Period: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1830-1890,p.14. (20)See Harold Perkin,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1780-1880,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p.313. (21)George Eliot,Essay of George Eliot,Thomas Pinney,ed.,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63,p.446.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2)See Evan Horowitz,"George Eliot:The Conservative",in Victorian Studies,49(2006),p.11. (23)See Evan Horowitz,"George Eliot:The Conservative",p.10. (24)See Craig Calhoun,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4,p.177. (25)See John C.Turner,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Oxford:Basil Blackwell Inc.,1987,p.28. (26)Hilda Hollis,"Felix Holt:Independent Spokesman or Eliot's Mouthpiece?",in ELH,68(2001),p.157. (27)See Imraan Coovadia,"George Eliot's Realism and Adam Smith",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42(2002),p.822. (28)Sally Shuttleworth,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London:Cambridge UP,1984,p.125. (29)Linda K.Robertson,The Power of Knowledge:George Eliot and Education,New York:Peter Lang,1997,p.19. (30)Ina Taylor,George Eliot:Woman of Contradiction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p.165. (31)See Jennifer Uglow,George Eliot,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7,p.175. (32)Jennifer Uglow,George Eliot,p.179. (33)See Linda Bamber,"Self-Defeating Politics in George Eliot's Felix Holt",in Victorian Studies,18(1975),p.428.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选举权论文; 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霍尔特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爱略特论文; felix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