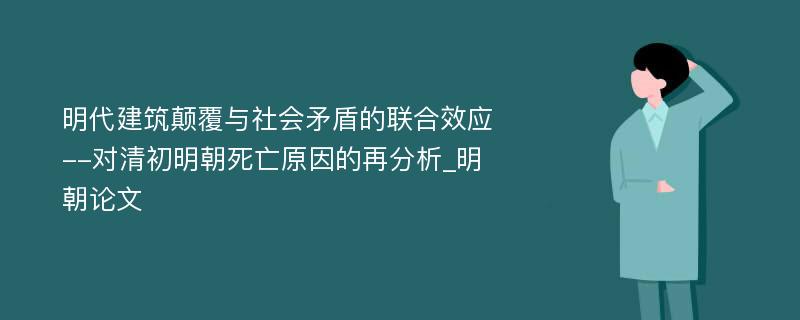
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合力论文,社会矛盾论文,大厦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11-0093-10
大凡改朝换代的初期,前代官僚士大夫等遗民似有一种情节,即痛定思痛,反思本朝兴亡的利弊得失,寄托一种哀思之情。而新朝君臣也格外重视前朝之鉴,以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以维系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明清易代,也不例外,检讨明亡之因仍然是清朝一个较长时期的热门话题。而清人对此关注程度之高,不亚于历代王朝。换句话说,明史对有清一代影响深远。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烈火之中诞生,发展壮大。历时276年之后,这座王朝大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焰里轰然倒塌,化为灰烬。明朝灭亡是一桩历史大事。清前期,人们探索明亡成因已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其中主要有三部分人:(1)思想文化界学人,内含部分明代遗民等。诸如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唐甄等,解析明亡历史,以犀利的笔锋,痛斥君主专制之弊。他们的主张无疑具有民主思想的色彩。不少史家如谈迁、张岱、谷应泰、查继佐、傅维鳞、计六奇、全祖望、赵翼等考订史籍,探研明史,著书立说,多方揭示其亡的经验教训。(2)清代政界名臣。例如,魏象枢、魏裔介、汤斌、陆陇其等进谏之时,多举明朝案例,以便引起皇帝重视,巩固清朝一统天下。(3)清初列帝。他们对明朝历史尤为重视,除了用近百年时间编纂《明史》并钦定之外,圣祖玄烨、高宗弘历多次南巡,均拜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盛赞功德,探析有益治道。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圣祖特别叮嘱纂修《明史》之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史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① 可知此三朝的得失对满洲贵族政权巩固的价值。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弘历在养心殿存贮书内,检得明季寺人所撰的《明朝宫史》一书,认为此书“文义猥鄙,本无足观”,原不堪采登册府,因有明一代,“秕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宦官“生杀予夺,任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乾纲不振”。他每当读到宦官流毒事迹,甚为痛恨,下令将此书交总裁官,照依原本,抄入《四库全书》,“以见前明之败亡,实由宫监之肆横”,以此“为千百世殷鉴”。② 清代君主以明亡为鉴,宗旨明确,就是拨乱反正,兴国安邦。
清前期,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均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明代“社稷沦亡,天下陆沉”之因。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见解:(1)亡于流贼;(2)亡于宦官;(3)亡于朋党;(4)亡于皇帝;(5)亡于民穷;(6)亡于学术。兹就上述之因,再作解析如次。
一、农民军势如破竹,“宗社不守”
明朝覆亡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推翻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起义初期,各路农民军主要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独立地同明军交战。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农民军履冰渡过黄河,将反抗斗争推向河南地区。明朝鱼烂土崩,不可复故。清人吴伟业指出,统治集团惊呼此为“渑池渡”,“此中原之所以溃,国家之所以亡也”③。这也标志着明廷围剿农民起义的失败。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十三家、十八寨、三十六营、七十二营等会聚河南荥阳,各路农民军共商作战大计,由分散的各自为战走上联合行动的道路,史称“荥阳大会”。这是农民起义军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农民军反守为攻,由被动变主动,集中力量重创明军,多次取得大捷。
明末农民战争起于陕西,横扫中原,席卷西南,威震东南。李自成、张献忠率众起义以来,明朝陷入窘境,“材(财)富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于是“瓦解土崩,一蹷而坏”④。清人谷应泰将此事比作犹如一人之死,张献忠絷其手,椹其胸;李自成刺其心,扼其吭。经过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力推翻了明朝。前代遗民多对亡国扼腕叹息,“然则颠覆之祸,固当责之庙算欤”⑤。明朝“宗社不守”,固然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所为。但是,论者却说,明并非亡于“流贼”,而是亡于某某因素。这就表明识者透过历史现象,探究事务变化的本质。亦间接地论证,农民军的胜利正是利用了社会各种矛盾势力,才推翻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
晚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给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上了生动的一课。如何严加防范民众聚集起事,维护整个统治秩序的稳定,这是他们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疏参纵容游民连直、不行查拏的地方官。圣祖指出,出于生计所需,允许小民跨省行医卖药。但对蓄意的奸恶之徒,越省游行,严行禁止。“若令其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即行劫掠,有害地方”。下令有司剪除恶乱之辈,不然“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豫为之计乎”?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地处偏僻山区的闅乡县革退扑役马现龙,抢夺贾世锡银两,因不服县差拘讯,纠约刘建业等,持械拒捕,伤死差役数人。高宗闻知,对聚众滋事,格外重视。他指明,设任地方,庸劣有司,一切姑息,即可酿成事端。所谓涓涓不息,流为江河。“前明李自成等,独非裁汰驿卒乎”!“此所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⑦。民众一有聚事,清朝统治者就敏感地与明末“流贼”造反联系起来,而李自成的名字在他们心中已经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烙印。
二、宦寺操持大柄,“祸国殃民”
明亡于宦官之说,在清初十分流行。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管束十分严格,立铁碑于宫门为戒,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到南京宦官的支持。登基之后,他背离祖训,重用宦官。宣德年间,设立内书堂,由大学士陈山教授宦官识文断字。从明中期起,宦官团伙与官僚集团,交替执政。自英宗到武宗时期,皇帝不理朝政,宦官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专权;从嘉靖至万历时期,系权臣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掌政,他们也要拉拢宦官。例如,张居正入主内阁,得到宦官冯保的支持。万历二年(1574),冯保自建生圹,张居正为之书写《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⑧ 足见二者关系密切。宦官多能掌控内阁,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均握“批红”之权,成为皇权代表,皆力压内阁一头。同时还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打击迫害反对派。
宦官尚拥有监军权,并受钦差出使等。宪宗朱见深时宦官汪直,怙宠立威,大臣皆屈膝。时有谚语曰:“尚书叩头如捣蒜,侍郎折股似栽葱。”⑨ 小太监阿丑擅长于表演相声,讽刺他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言外之意,不知有天子。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六年(1506—1521),依赖宦官刘瑾,北京城内外流传说,当朝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万历年间,四处派出矿监税使,掠夺工商业,激起市民罢市。天启时,熹宗热衷木作,魏忠贤专权达到巅峰。熹宗“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己竟不与”⑩。朝官人等皆称“九千岁”。魏忠贤还设立“武阉”,尽掌内廷兵权。明代内监“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踞窟穴;政府言路,凭借奥援;羽翼腹心,势焰熏灼,驯至不可收拾”(11)。足觇宦官势力的嚣张到何种程度。
清人谷应泰论道,明中叶,宠用宦官,“英、宪、武、熹乱者四世”,“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厂之酷,刘瑾不轨之谋,魏忠贤闇奸之状,而潜窥意旨,驯致败亡者,无他”。(12) 宦官擅权,导致君臣关系日疏,内竖肆虐,加速朝廷衰落。清人张岱指出:“宦官之祸,种毒既潜,国与随尽。可不畏哉!”(13) 正如赵翼所言,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14)。
清入关后,满洲统治者对明代宦官专政尤为重视,从制度层面上对宦官严加限制,“内庭法制,尤为严密”。顺治十年(1653),世祖将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改设十四衙门,再改十三衙门。十二年六月,世祖福临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谕曰:
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板,世世遵守。(15)
十八年(1661),复设准军事组织的内务府,将太监纳入上三旗管辖范围,收缴宦官权力,堵塞了他们擅政的渠道。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圣祖指出:明朝“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16)。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高宗指明,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为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其“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以朝廷大政,付之刑余,“妄窃国柄,奔走天下,卒至流寇四起,社稷为墟”,并强调:“我朝家法,太监止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若听其认识交言,实非善事。”(17) 满洲统治者将此纳入“家法”,告诫子孙世代恪守,以致有清一代没有宦官专权事件发生。
三、朋党相互构陷,“士气浇漓”
万历后期,神宗不问朝政,政务怠荒日甚。朝廷中枢机构官缺,长期不补。内阁只剩方从哲一人,帝以一人足办,不增补;六部堂官仅四五人,五十余员六科给事中止四人,十三道御史祗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朝廷陷入“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窘境。(18) 神宗宠信郑贵妃,专横跋扈的郑氏皇亲充斥朝廷,宦官又多聚集郑氏周围。大臣们既敬畏皇帝,又畏惧国戚和宦官,依违其见,无所建白。部分中下级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对社会现状不满。例如,被革职返乡的吏部郎中顾宪成等,目睹了朝政的黑暗,预感到市民阶层的抗争,农民的反抗,必将威胁朝廷的统治。为了拯救朝政危机,社会名流汇集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被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并与非东林党的齐、楚、浙、昆等党进行论争。
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主要围绕着“争国本”、李三才入阁、京察大计等展开。“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19)。天启初年,“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中外忻忻望治”(20)。四年(1624),时局突发逆转,非东林党麇集在魏忠贤身边,官僚顾秉谦、魏广征等人也献媚迎合,举朝若狂,形成“阉党”。他们宣布“东林榜”,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以致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党而党愈炽,党愈炽而国事不可问矣”(21)。正直的官吏遭到残酷打击,阉寺宵小,浊乱朝纲,政局黑暗。他们将正直官吏撰成《点将录》、《天鉴录》,并将明哲保身、不附逆奄者归入《选佛录》。(22) 世上所谓清流者,则被一网打尽,造成“士气浇漓”,臣心涣散。清人指出:这场党争,“指以朋比,斥为伪学,窜逐禁锢,殆无虚日”(23)。其结果是双方“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坐误不暇顾”(24)。
明末党争蔓延到清初政治舞台,出现所谓陈名夏与冯铨的“南北党争”,明珠与索额图的旗内政争,噶礼与张伯行、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满汉之争”,他们争权夺利,扰乱朝政。满洲统治者格外重视明末党争教训,倾力打击朋党。针对清初官员结党之弊,世祖福临命大学士王永吉纂修《人臣儆心录》八篇,以遏止朋党之乱,并御定其文。他在《御制序》中指出:“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诸一心,心正则为忠为直,众美集焉;不正则为奸为慝,羣恶归焉。是故心者,万事之本,美恶之所由出也。”他历数了谭泰、石汉、陈名夏等横行跋扈、目无纲纪、背德植交、蔑法罔上等罪过,明确地提出:“观诸近事,复炯鉴昭,然足为永戒。”(25) 索额图与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圣祖已有察觉。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斥责党祸危害,指出:
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置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哉!(26)
圣祖力陈朋党之患,以国法不容,训诫廷臣。
世宗即位之初,继续弹压“太子党”等。雍正元年(1723)四月,特谕满汉文武大臣等,以朋党为戒,指出:“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相互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杜绝朋党,他要求“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人人知改其恶而迁于善。君臣一心,国之福也,传之万世,亦有令名”。(27) 次年七月,颁布御制《朋党论》一文,陈述朋党诸种劣迹,指出:“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28) 以此严加防范,重点打击。高宗继承父祖衣钵,严加防范朋党,多次指明,明末党争,“人所痛恨,可为炯鉴”。“将来朋党之渐,其为国家之患甚大”,并将世宗《朋党论》等,“朔望令教官宣讲”(29)。他还果断地解决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各为魁首的满汉之争,稳定朝政。由于清初列帝措施得力,遏止臣僚结党为乱,乃至清朝有“朋党”之名,却无“党祸”之实。
四、皇权旁落,“倒置太阿”
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尔后列帝多平庸缺智,无所作为。宪宗在位二十三年(1465—1487),深居内宫,据说只接见一次朝臣,当大臣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时,皇上已起驾回宫了。他宠恋比之长20岁的万贵妃,致使她肆虐后宫。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1488—1505),接见了几次朝臣,官僚们已颇满意,称之为“有道明君”。武宗朱厚照私自出京,巡游山西大同等地;又出通州,经山东临清,游逛江南,为非作歹,骚扰民间。世宗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执迷道教,炼服丹药。神宗朱翊钧长期不临朝,不会见大臣,不批答奏章,致使大量奏疏“留中”。皇帝深居内宫,贪图安逸享乐,于是将大权交予内廷助手宦官,或外廷的帮手官僚,他们交替掌政,明争暗斗,乃至朝政混乱,局势不稳。张岱以明朝遗民自居,指出:嘉靖、隆庆二十年后,皇帝潜居不出,“百事丛挫”,又“贪呓无厌,矿税内时,四出虐民”。尤其强调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池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他痛感“盖我明亡之征已见之万历末季矣”(30)。
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圣祖明确地指出: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経史”,(31) 不学无术。“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他以前朝为诫,指出:“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岂容假之此辈乎?”(32) 世祖、圣祖皆肯定庄烈帝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非亡国之君”。清人全祖望却认为,其性刚而自用,缺乏应变的灵活性,怙前一往,“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33)。高宗弘历在《国朝宫史·圣论》中云:“论者率谓,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似矣。而朕不谓然。”他阐述道:
宦官之祸,汉唐来已然。顾其使宦官得志擅权,肆毒海内者,伊谁之咎也?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人君所与处者,若辈耳。凡监役、监军、要地、要务,非若辈弗任也,非若辈之言弗信也。导谀纵逸,愈溺愈深。中叶以后,羣臣有数年不得望见颜色者,而鬼蜮之计得行。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置太阿,授之以柄,其失皆由于不与士大夫相接耳。(34)
从中期以来,明朝列帝蜗居内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皇权假借宠信宦官,倒置太阿,以致朝政混乱。高宗明确地提出:“伊谁之咎乎?”他解析道:
胜国洪武,草昧初开,未尝不得之艰苦。而中叶以后,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荡佚,恬不为怪;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民。此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事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至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固,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末造。而宴安酖毒,终于不可救药,自覆厥宗。殷鉴甚近,尤足为炯戒耳。(35)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明帝无作为,将大权假手于人,主要是君主的过失。高宗的论断正中明亡的要害。“干纲独断,乃本朝家法”(36)。清朝列帝事必亲躬,决不将大权假手于人。他们以前明败亡教训为戒,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到军机处,不断强化皇权,也使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未曾出现过皇权旁落的现象。
五、闾阎之匮,“民穷而盗起”
明初的各项制度详严,成祖登基,发生了变故,出现宦官执柄,官僚掌政的局面。明朝礼部尚书冯琦说:“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夷狄。它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阎之匮耳。”(37) 清人计六奇指出:明朝“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38)。明清官员总结所言,农民、市民的贫苦化,是朝廷克扣百姓制度甚繁,人民难于休养生息。随着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盘剥百姓。社会贫富日益悬殊,势必再现“民穷而盗起”的局面。
在北方,主要是皇帝、勋戚、王公、宦官兼并土地。皇帝亲自占田,成为私产,叫皇庄。(39) 成化时期,给事中齐庄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宪宗朱见深不听。(40) 正德年间,皇庄快速地发展到36所。(41) 同时,宦官打着黄龙旗,在北京设店房,招歇商人,征收商税,称“皇店”;放高利贷,谓“皇债”;卖盐谋利,叫“皇盐”;在房山与门头沟开煤窑,曰“皇窑”。此皆内臣提督,“正额进御前”。像明朝列帝这样大肆聚敛私财,在历史上是未曾见到的。上行下效,此时勋戚、功臣等以“请乞”和“投献”的方式,不择手段地侵夺民产,建立庄田300余座。针对这种状况,户科给事中李森率诸同仁揭露道,“畿内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处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42)。
在南方,主要是豪绅地主占田。所谓豪绅地主即以“笔杆子”功名起家的士大夫地主、以“锄头柄”发家的粮长地主以及退居林下的缙绅地主。他们在土地比较集中的江浙、福建、江西地区,广占田土,欺压乡民,为霸一方。正德年间,福建“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嘉靖时期,(43) 严嵩的家乡在袁州分宜,该州四县的土地7/10被严家所占据。徐阶为江南松江人,徐家在松江的土地有4000顷。农民丧失生产资料土地,产生大量的流民;重敛矿税,剥夺工商业者,城镇市民罢市频发,由此造成全国统治秩序的动荡。
商品经济繁荣,白银进入流通领域,更加刺激了统治者贪婪,“溺志货财”。凤阳巡抚李三才已经深感问题的严重,多次上疏,反对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工商业,危害地方。他尖锐地指出:
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闻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阙,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国敌,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44)
李三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晚明财富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加剧,民不堪命,严重地威胁着江山社稷的安危。
万历天启年间,天下灾荒饥馑,疾病频发,“同类相食,人死如乱麻”。任职饷司的杨嗣昌奏报岁饥,指出,淮北居民“食草根树皮至尽,甚或数家村舍,合门妇子,拼命于荳箕菱杆”。江南“灶户之抢食稻,饥民抢漕粮”,所在纷纭。荒歉所致粮价腾贵,苏州、松江等地,斗米长至百三四十钱而未已。从北到南,“顾瞻闾左,民穷财尽”(45)。顾炎武以农商之业,分析了明代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指出:至正德嘉靖初,与以往不同,“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惶”;嘉靖末隆庆间,更加异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益富,贫者愈贫”;及万历中期,“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有九”(46)。天启时期,陕西“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盗由此而始”(47)。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军从者日众,大多数为贫饥之民。
六、思想不清,“亡于学术”
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一批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李颙、唐甄等,深感君主专制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高举批判的旗帜,激烈地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48),平衡君臣和地方权力;要求改善与协调君臣关系,共理天下。明朝后期,在学界内,陆王“心学”异军突起,“士人多皆阴弃朱子而从之”。从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门户水火,相互攻讦,长期不休。一时传统的程朱学术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王阳明一派的“心学”在学术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否定的。而后,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且多出“狂放”之言,在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李贽等人,蔑视孔孟的“绝对权威”,指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矣。”(49) 并强调:“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50) 他还尖刻地抨击尊孔潮流,“犹如一犬吠影,羣犬吠声,可笑之至”(51)。痛斥《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则为“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52)。李贽的“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举动,既不为明廷所容,也难为士人所接纳。
清初一批名臣认为,学术的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正如兵部给事中魏裔介所言,“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53)。因此,他著有《圣学知统录》,极力倡言,大兴圣学:
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为之,圣人之心为之也。今夫衡平则轻重不易,鉴空则妍媸不爽,而况人主之心静乎,天地之大览万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无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终无有得其正者矣……“圣学以正心为要”,此可谓得学之本矣……学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非学不为功焉……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君而国定,正其心之谓也。(54)
熊赐履亦著《学统》等,阐述晚明社会风气衰退与学术不正有关。他们力谏朝廷大力弘扬“圣人之学”,明辨学术,以正人心。这些建策深得圣祖玄烨赏识。
康熙年间,玄烨“崇儒重道”,定程朱理学于一尊。他指出:“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朕必嘉之。即天下万世,亦皆心服矣。”(55) 因玄烨大力倡导理学,汤斌、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应运而生,他们以卫道士自居,将批判陆王“心学”视为己任,把促进皇帝尽心儒学,作为“当今第一要务”,并在“经筵日讲”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护法大师在学术上并无创新之见,但他们从政治上着眼,将学术同政权巩固联系在一起,努力地为稳定清朝统治秩序服务,亦不无成绩。
从学术视角剖析明亡之因的当属名儒李颙和理学名臣陆陇其。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56) 他亲历明清变故,痛感明末“亡国”、“亡天下”是学术思想混淆不清所致。而陆陇其的主张更激进一些,认为,“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他甚至将明亡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滥觞。陆陇其指明: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徧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雎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57)
他认为晚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风俗愈坏,礼义扫地”,是王阳明“心学”弊端造成的。(58) 简而言之,学术的偏颇酿成流寇、朋党祸起,导致明朝衰亡。陆陇其翻检历代注释性理之书不下数十家,认为诸多释义过于枝蔓,去其缪戾,采撷发明章句集注者,陆续纂辑《四书讲义》、《性理大全》、《大学衍义》、《读朱随笔》、《困勉录》,以及《松阳讲义》等书,这些理学著述在当时社会颇具影响。陆陇其站在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立场上,竭力地宣扬程朱理学,批判陆王“心学”。这些作法与满洲贵族为稳定统治秩序、推崇理学的举措,一拍即合。他从学术上总结明亡的教训,观点新颖,而其言词似有过激之嫌。但他确为清朝崇儒重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清廷授予陆陇其殊荣,其死后,雍正二年(1724),从祀文庙。乾隆元年(1736),特谥“清献”,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衔。
七、社会矛盾的合力,大厦倾覆“而莫之救”
明后期,整个统治机制已病入膏肓,即使再下猛药,其病也难以治愈。魏裔介在《书流寇始末后》一文中总括道:
明亡于流寇,非流寇亡之,自亡之也。始以民饥,继以军噪,于是奸宄倡其萌,荷戈者比附,以张其焰。一时之为督抚者,方且优游坐视,调二三武弁,掠得子女玉帛,即以大捷报闻,甚至杀良冒功,滥叼爵赏。非无忠臣义士,欲为国家出死力者,以阻于赇赂,不得进用,徒呕血腐心耳。又况门户相攻,阉人用事,每将阘冗之夫,推为督抚将帅,借以报复私雠。社稷民生,听其荡坏。黠者慧者,袖手旁观。庚辰辛巳间,宇内连岁荒疫,大地为盗,正赋舞出,犹且严征,加派以资边饷。譬如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复委之至庸极愚之医,投以乌砒,绝其饘粥,焉有不死者哉?赫赫上天,知其君臣终不能拨乱为治也,而天命乃去之矣。(59)
他从军事、朝政、经济、灾荒等方面揭示了明亡是社会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自亡之也”。其论极是。
从明中期起,各种社会矛盾就不断地激化。在百万流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冲击下,明朝已初露衰败的征兆。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已经感到危机四伏。他在《京师重建贡院记》一文中,将王朝意喻成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其中则蠹矣”。明兴二百余年,“纲纪法度,且将陵夷而莫之救,有识者忧之”。他们亟待把这座“将坠而未仆”的大厦,“振而举之”(60)。他深知如不扫除“浮言”,改易更张,“元末之事,可为殷鉴”,“衰宋之祸,殆将不远”。张居正通识时变,革故鼎新,以图“富国强兵”,力拯朝政的衰败。然而,其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愈加尖锐复杂,以皇帝、王公、勲戚、宦官和权臣、豪绅为主体的大地主集团更加腐朽。
清人或认为,明之所以失天下,其故有四,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寇,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将相无人,“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而君之失德不与焉。”(61) 事实上,明朝消亡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经济上,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破产,酿成数量庞大的流民队伍,加上肆意掠夺工商业,加深农民、市民贫困化,加速了社会局势动荡。军事上,京营建制涣散,卫所制度遭到破坏,军队丧失战斗力,无法应对“南倭北虏”的挑战,也无力抗击建州女真骑兵的侵扰。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军以及崛起关外的建州女真,明廷战斗策略失当,颓势日趋明显。当然也不能低估导火线,即天灾人祸所产生的颇大作用。
晚明在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尤显突出。这集中表现在“政以贿成”,纲纪无存。先说宦官,王振得势之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当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62)。王振擅权七年,籍没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63)。弘治时宦官李广用事,四方争纳贿赂,查没其家产,得到一本“名簿”,在许多大臣名下,书写“馈黄白米各千余石”。孝宗惊叹:“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侍从说:“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司法究治。(64) 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科道官员出使归,天下巡抚入京受敕,都指挥使以下升迁,边将违律等,均要重金贿赂刘瑾。(65) 其值“一千曰一千,一万曰一万,后渐增至几千几万矣”(66)。他窃柄无过六七年,败没之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67)。
再说权臣,嘉靖初年,世宗将武宗宠臣江彬、钱宁罪磔于市,籍没江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宝不可数计”;查抄钱家,获“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68)。陆炳为世宗乳媪之子,擢都督同知。御史弹劾他不法行为,其恐惧,“行三千金求解不得”(69)。严嵩为相二十年,“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他秘密运输财产南归,“大车数十乘,楼船数十艘”;抄没其家产,“黄金可三百余万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与其妻窑藏于地,“每百万为一窑,凡十数窑”(70)。而侵吞巨资的官僚为数不少。
宦官和权臣将政治权力变为疯狂聚敛钱财的手段,权势越大,贪贿财富愈巨。如同赵翼所说:“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71) “权门贿赂”是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晚明“政以贿成”的腐败之风,导致吏治大坏,纲纪法度废弛,无力应对内忧外患。刚愎自用的朱由检虽力图扭转时弊,但积重难返,已无力回天。已腐朽如此程度的明王朝大厦焉能不坍塌?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人检讨明亡之因,上述六种观点,只是强调在明朝的某一历史时段,其中一种因素曾对该朝的衰落起到促进作用。不过作用力的大小也不是均衡的,最终由某一、二种主要势力来完成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此即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及崛起辽沈的建州女真,这两股势力对明亡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崇祯十三年(1640),明廷修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南北门额题有“顺治”、“永昌”字样。过了四年,门额字迹仍清晰可见,明朝却消亡了。时人论曰:“岂非天哉!”(72) 这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但其中却蕴含着必然的因素。从明朝整体上考察,王朝大厦的倾覆绝非只是某一种力量所为,乃是长期社会各种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4“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7《张献忠之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 《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⑦ 《清高宗实录》卷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⑧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⑨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5《宦官贤奸》。
⑩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圣论》“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3) 张岱:《石匮书》卷15《熹宗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5) 《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1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4《国运盛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0) 《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2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点将录》、《天鉴录》、《选佛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4)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4《门户大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5) 福临:《御定人臣儆心录》,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26)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7)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8) 《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9) 《清高宗实录》卷241“乾隆十年五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0) 张岱:《石匮书》卷13《神宗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1)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3)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9《明庄烈帝论》,载《全祖望集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4)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圣论》“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5)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一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 《清高宗实录》卷32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7) 《清高宗实录》卷32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论流寇乱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9) 皇庄一词,始见于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第7卷《河字·黄垡仓》,其云:“今建仓黄垡等处,葢成祖龙潜时私庄也。永乐改元,有司请庄所属改称皇庄。”
(40) 《明史》卷77《食货一·田制》。
(41) 夏言:《勘报皇庄疏》,载《明经世文编(三)》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2) 《明史》卷180《李森传》。
(43) 《明史》卷230《欧阳铎传》。
(44) 《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4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杨嗣昌奏岁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歙县风土论》,上海涵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
(47)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5年印。
(48) 顾炎武:《日知録》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9) 李贽:《焚书》卷1《答耿中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0)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1) 李贽:《续藏书》卷2《序彚·圣教小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2) 《焚书》卷3《杂述·童心说》。
(53)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1《兴教化正风俗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4)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14《圣学以正心为要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5) 《清圣祖实录》卷15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6)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二曲先生窆石文》,载《全祖望集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7)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2《学术辨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商鸿逵:《清初的理学界》,载《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59)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书流寇始末后》,参见《国朝文会》,乾隆时期选编,平河赵氏清稿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此文中华书局2007年版《兼济堂文集》未录。
(60)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京师重建贡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6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明季致乱之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明季致乱之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3) 《明史》卷304《王振传》。
(64) 《明史》卷304《李广传》。
(65) 《明史》卷304《刘瑾传》。
(6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权奸黩贿》,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8) 《明史》卷307《江彬传》、《钱宁传》。
(69) 《明史》卷307《陆炳传》。
(70) 《明史》卷307《严嵩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2) 查继佐:《罪惟录》卷31《李自成传·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标签:明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宦官专权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魏忠贤论文; 社会矛盾论文; 心学论文; 东林党论文; 太监论文; 专门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