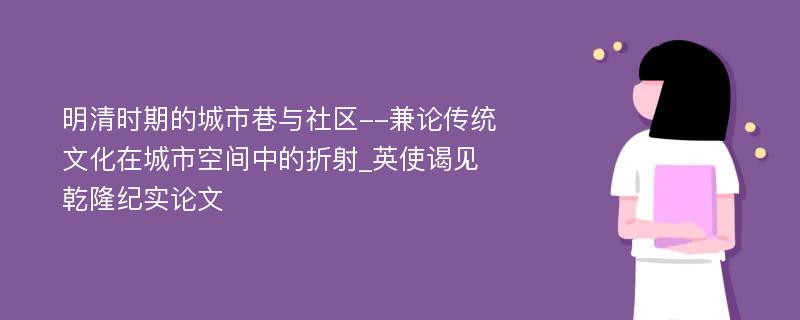
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明清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社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2-0111-07
由坊、街、巷组合而成的地域空间序列,构成了明清城市平面形态的主要元素,在此基础上,行政手段与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许多具有共性的社区,可以说,坊巷与社区是人们从两种不同角度认识城市地域空间分布状态所形成的概念,其中,坊巷是具体的,有形的,而社区则是抽象的,它既具有地理空间的蕴涵,也有着许多不为地域所决定的因素。这里,我们研究坊巷与社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和揭示明清城市布局的主要形态,更主要的是力求探讨融入其中的带着历史沧桑的文化与传统。
一、行政社区——坊的演变
坊巷展示的是一幅城市平面图,它将城市分割成若干个板块。按照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说法,坊代表着一个社区;而在形态上,坊是一个方形块状的地域,巷则是圈画这些社区的一条条顺直的线,坊巷组合便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画面。
棋盘式的坊巷,可谓古今城市中最为普遍的街区规划形态,它不仅被应用于中国的城墙都市、日本的幕藩制都市,同样也被用于西方的古罗马城。然而,中国的棋盘式坊巷就其产生与功能而言,却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的产物。
坊,在古代也称“里”,二者并称“里坊”。“里”的含义主要是指居民聚居的地方,所谓“里,居也。”《汉书·食货志》记载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也就是说,在汉代,里是指城市的社区而言,但在名称的使用上,里的概念却并非城市专属。首先,乡里、里、里闾等称呼无不与农村相关。其次,我国古代自秦朝始,即在郡县之下设乡、亭、里,至明清时期仍以里社为基层组织的命名,表明“里”的最初意义,主要还在于它曾经是对广大农村按地缘进行社区划分的一种行政措施。而后,与“里”相应出现了“坊”。“坊”更近于城市化,或者说专就城市而言。《唐六典》曰:“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食货志》曰:“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唐人苏鄂在《苏氏演义》中则进一步指明:“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这里不仅说明了“坊”由“里”演变而来的事实,而且指出了“里”何以又称作“坊”的原因,以及“坊”的空间形态,即“坊”是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地域空间。清代的地方志中也就“里”与“坊”的关系指出:“邑里之名谓之坊,里中有道谓之巷,……唐制,凡州县皆置乡里,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郭内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者皆有正。”(光绪《宁海县志》卷3)
总之,自汉至唐,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里”与“坊”的设置及其制度化。里坊制,或者称坊制,不仅将城市划分为若干方形的空间,而且对每个空间都做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表现为坊的四周有城墙,设有坊门,坊内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及权贵之家外,余者不得面街私开门向,夜间坊内有宵禁之规,凡鸣鼓警示后,坊门关闭,行人不得出入,违例之人视犯夜禁者而论。这实际上是农村户籍相伍制度在城市的复制,是城市乡村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但限制了城居者的行为自由,而且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居住环境。可见,坊制仍属于自然经济的产物,符合封建专制政治对民众管辖的要求,因而也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同。朱熹就曾经说过:“唐的官街皆用墙,居民在墙内,民出入处在坊门,坊中甚安。”(《朱子语类》卷138,杂类)这也道明了坊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居民,维持社会治安。
此外,坊在划分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空间。《易经》中有“方(坊)之类聚,居必求其类”的论说。可见,坊的另一社会功能就是对城市居民在地域上进行类别的区分,分类的标准自然是反映身份与等级的职业,即官僚、手工业者、商人等。因而,坊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度对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与范围的限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中国城市完全从属于封建政治的特点。
宋代以后,随着坊墙的毁坏、倾圮,坊制已不复存在。在统治阶级倍感“宫殿街巷京城制度……不佳”的忧虑中,城市居民面街而居,沿街建房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坊墙拆除所带来的居住自由是有限的。城居者虽然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但却无法逾越已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类聚”与“群分”的等级观念。在居住上,伴随着坊的名称的延续,坊的“分类”功能仍然制约着城居者对居住地点的选择。它不仅成为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而且以一种惯性持续下去。如南宋杭州的坊,仍是人们划分居住范围与城市社区的一个单位。《都城纪胜》云:“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韋纷纭无数,自融合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皆不以贯万收质。”(《都城纪胜》铺席)这显然是由几个行业相关的坊组成的商业区。
进入明清以后,坊的行政区划作用已大不如从前,但其作为城市社区单位的名称没有变,大小城市多有坊的划分。一般来说,城市的地域布局为:城中为坊,坊的外围为四隅,城门外的城郭为关厢。行政建置则有坊、牌、铺,或者坊、铺。其制以京城最为典型。
明代的北京有五城之划分,城下设坊。所谓“明制,城之下,复分坊铺,坊有专名,铺以数十计”(余启昌:《故都变迁记略》卷1)。如“京师虽设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而地方分属五城,每城有坊”,共计三十六坊,皆有坊名,其中“中城曰南薰坊、澄清坊、仁寿坊、明照坊、保泰坊、大时雍坊、小时雍坊、安福坊、积庆坊。”(吴长垣;《宸垣识略》卷1)连附县宛平亦设坊,且其“城内地方以坊为纲,……每坊铺舍多寡,视廛居有差。”(沈榜:《宛署杂记》卷5)北京的坊铺分布也系根据民居多少而不等。如西城之阜财坊,在“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过象房桥,安仁草场,至都城西南角”,其下“四牌二十铺”。南城正东坊,自“正阳门外东河沿,至崇文门外西河沿”,辖“八牌四十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到了清代,京城有内城与外城的划分,而内外城又各分为五城,坊的作用似不比从前,但仍为城下的一级单位。所谓“清制,于(北京)城下有司坊司,设兵马指挥、副指挥各一员,坊设吏目,俗曰坊官,惟坊名久废。”(余启昌:《故都变迁记略》卷1)其时,坊名虽已逐渐为人们遗忘,但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坊仍然是划分城市社区的一级单位,并有固定的辖区,如“宣南坊,隶西城,凡内城自瞻云坊大街以西,报子街以北,阜成门街以南;外城自宣武门外大街迤南至半截胡同以西,皆属焉。”“灵中坊,隶北城,凡内城自德胜门街以东,地安桥,兵马司胡同,交道口,东直门街以北,皆属焉。”(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这种以坊作为地方布局之纲的做法在外省的小城亦然存在,但坊的数量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广东省潮阳县,“旧有十三坊”,至清末,“县治之坊凡七,城内北曰兴让、南曰南桂、东曰锦缠、西曰归厚,城外自东南隅绕北而稍西曰平和,迤西而南曰临化,正南曰南薰。”(光绪《潮阳县志》卷3)当时,更多的情况为,一些小的县城,坊或者与巷合流,或者已形同虚设,无实际意义,如扬州“城内天宁坊,亦曰天宁街,名起于城外天宁寺也”(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宁海郭内有坊十一而无巷,今志(清朝光绪年间)载巷三十五、坊十。”(光绪《宁海县志》卷3)这里的坊显然已是街巷的代名词。又如,合肥县“城内坊厢……旧志有此十八坊,不分界地。”(嘉庆《合肥县志》卷3)说明在清代,坊所固有的行政社区的划分功能在某些地方已不复存在,坊也越发不被人们重视,其衰落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二、人文社区的形成
坊的存在毕竟为封建政府所设,其社区的划分具有法定的意义,而坊的分类功能所形成的同行业聚居,并不曾限制住坊的外延性,城居者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于若干个坊的基础上自然形成了不同等级与层次的生活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政治区以及娱乐区等。如明代南京,城东是以宫城为标志的政治区、城北是驻扎军队的军营区、城南是世胄官宦的住宅区、而商人与手工业者则集中于城南的旧金陵城区,即“城之南隅,康衢四达,幢幢往来,朝及其夕。”(周诗、李登:《万历重修江宁县志》卷1)又如广州,“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东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故谚云:东村、西俏、南富、北贫。”(同治《广东通志》卷92)这种俗尚的地区性差异,实质上是不同等级与层次的居民在文化上的差异。它告诉人们,当时的广州城,城东为平民区、城西为官僚显贵居住区、城南为商业区和娱乐区,而北贫自然是指城市中的最下层贫民区位于城市北部。
这种居住状况并不止于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边远的小城市亦然。如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齐齐哈尔城,本是一座军事重镇,但城中居民对于居住空间的划分却同样层次分明,其“城中地势……北高南下,夏日南面苦泥淖,北面沙路平坦,仕宦家多据之,东南、西南两隅穷檐蓓屋,如在墟墓间,不免宵小窃处,要皆不如木城中人家稀少,地面宽敞,且有廨舍两府在,可高枕卧焉。”(西清:《黑龙江外纪》卷2)这说明,齐齐哈尔城以南北划分了居民区,官僚达贵居住在城北地势平坦的高地,贫户小民蚁聚于城南的低洼之地。
上述记载表明,居住区域的划分所反映出的身份、等级制度的界限,使人们按照社会地位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空间,而每个生活空间必然有着使人们得以凝聚的共同的文化,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文化是人类得以会集的最大力量。也正因如此,不同的居住空间必然会折射出各自文化的特点及其差异。对于这些反映不同文化内涵的居住空间,我们也姑且借用一下社会学的“社区”概念,而且,如果我们再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它更应该被称作“人文社区”。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城市社区的划分也带有民族的特色,表现为在旗民分治的原则下,对有八旗驻防的一些城市,实行满人城与汉人城并置的制度,满人城多是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或附城,如成都府,“满城在府城西”,“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因而,在成都“城有少城大城”之分,“少城亦名子城,今满城也。大城亦名龟城,今汉城也。”(嘉庆《四川通志》卷42)
这种满汉分城而居的现象,在京城尤为突出。自清军入关,内城便成为满族王公贵族及旗人的居住地。清朝诏令有“顺治元年定鼎建号诏:一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原取两便,万不得已,其中东西三城官民,已经迁徙者,所有田地租赋,准蠲免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田地租赋,准免一年;又顺治五年南郊配享诏:一北城及中东西三城,居住官民商贾,迁移南城,虽原房听其折价,按房给银,然舍其故居别寻栖止,情属可念,有土地者,准免赋税一半,无土地者,准免丁银一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可见,清朝统治者以法令的强制形式,将原有居住在北京内五城的居民,不论身份、不分官民,一律强行迁至外城,迁移过程前后经历了大约五至六年。而内城由此成了满族人的聚居地,故号称“满城”、“鞑靼城”,所谓“内城即正阳门内四隅也,多满洲贵家。”(《金台残泪》卷3,见《清人说荟》)而外城由于全部居住着汉人,所以成为“汉人城”,又称“中国城。”汉人中只有少数高级官僚蒙皇帝恩旨赐宅者方得居住于内城。如奉命入直南书房的张英等人,所谓“张文端英,以谕德赐第西华门后,蒋扬孙、查声山皆赐第西华门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满城与汉城的划分,仍属法定的行政社区。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居住区域的选择仍固守着“同类而聚”的传统惯习,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重新组合着人文社区。
如北京外城,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官僚士绅、商贾、匠人、手工业者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集中居住地。在其居住区域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居民等级的排列与不同文化圈的碰撞较内城更为鲜明和剧烈。夏仁虎于《旧京琐记》中曰:“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直廷枢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夏仁虎:《旧京琐记》卷8)即北京外城东为土著士绅与富商大贾的住宅区,外城西为内城乔迁官僚住宅区。所谓京朝官“所居皆宣武门城南衡守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杨寿枬:《觉花寮杂记》)但北京的这种组合到清末多少有些变化,清人震钧有记载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而今(光绪年间)则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震钧:《天咫偶闻》卷10)
此外,在北京外城于行政上划分为五城之后,由清初而至清末,在百余年、甚至是二百余年的磨合下,五城也相应出现了反应各自文化层次与文化氛围的某些特征,据文献所言,清代官衙中的巡城口号有:“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各举重者为言。”“前门外戏院多在中城,故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语。中部郡尉所治地,或且因缘为利。”(《梦华琐录》,见《清人说荟》二编)
除了上述五个的社区外,在东西两城之间还分割出一块商业区。有记载曰:连接东西城的是一条大街,“大街东边市房后有里街,曰肉市、曰布市、曰瓜子店,迤南至猪市口,其横胡同曰打磨厂。内稍北为东河沿,曰鲜鱼口,内有南北孝顺胡同,长巷上下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曰大蒋家胡同,东南斜出三里河大街,内有小蒋家胡同,冰窖胡同。此皆商贾匠作货栈之地也。”(吴长垣:《宸垣识略》卷9)“大街西边市房后有里街,曰珠宝市、曰粮食店,南至猪市口。又西半里许有里街,曰煤市桥、曰煤市街,南至西猪市口。其横胡同曰西河沿、曰大栅栏,……大栅栏西南斜出虎坊桥大街,此皆市廛、旅店、商贩、优伶业集之所,较东城则繁华矣。”(吴长垣:《宸垣识略》卷10)上述商业区的情形,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只有文化才能对人类产生无形的、趋于自觉的凝聚作用。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人文社区的形成,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组合,但也不排除外来力量的干预。除了满汉分城居住而外,清代有关“内城禁喧嚣”的规定,也将一些“违禁”的社区限制到了外城。如士人流连的会馆区、灯红酒绿的妓院区,以及戏楼曲院区等,均属于这种情况。即所谓“戏园,当年内城被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剧园向聚于大栅栏、肉市一带,旧纪所载方壶斋等处。……外城曲院多集于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小裹沙帽胡同,分大、中、小三级。”(夏仁虎:《旧京琐记》卷10)“正阳门外以西,则改为花柳之窟矣。”(震钧:《天咫偶闻》卷5)而作为士人举子们居邸的会馆,则多设于宣武门外南面的官宦住宅区,故有“士流题咏率属‘宣南’的记载(夏仁虎:《旧京琐记》卷8)
但是,我们在注意文化的凝聚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性。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任何强加的力量,也都抵挡不住文化的撞击和渗透,满族人照样接受了那些原本属于中原文化的东西,而北京内城的变化则完全体现了这一点。清人记载曰:“未几,西四牌楼左近,复变歌吹之林,始只砖塔胡同寥寥数家,继则方以类聚,日变逾多。今则闾阎扑地,歌吹拂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栏也。”(震钧:《天咫偶闻》卷5)除了青楼曲院之外,戏园亦再度出现于内城。清人震钧曰:“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园,西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震钧:《天咫偶闻》卷7)这种变化,其实质是在城市这种人口聚集的特定环境下,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文化在相互撞击中所产生的文化交融现象,它以满汉文化融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三、街巷的形态及其文化的投影
在城市社区中,比坊更小的单位曰街、曰巷。明人沈榜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沈榜:《宛署杂记》卷5)《析津志》曰:“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也就是说,“道”泛指可以行走之路,只有寓意市廛的“街”才是对城市而言,而比街更小的称“巷”。
明清时期的城市,无论大小都由街、巷组成。《儒林外史》记载曰:明朝的南京城,“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里,城内有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而街巷之网最为密集者还属北京。北京内城“其街衢之大者,中曰棋盘街、南北曰崇文门街、宣武门街、大市街、王府街、地安门街、安定门街、德胜门街、南小街、北小街、锦什坊街。东西曰江米巷、长安街、丁字街、马市街、朝阳门街、东直门街、阜成门街、西直门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斜街,”此外,还有巷、胡同等。(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析津志》所谓“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又长街、千步廊、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即是对当时北京街巷的概括性总结。
大城市而外,一般的县级小城则多由四至五条主干街道组成,如江苏省奉贤县“城中街巷由县治前东出者曰东街,西出者曰西街,治之西通南门者曰南街,通北门者曰北街,四街交界处形如十字,俗呼为十字街,大街之北又有一街东西绵亘,曰奉贤街,相传子游曾过此,故名”(光绪《奉贤县志》卷2)又如清代湖南的湘潭县,称街者有“宣化街、大街、攀龙街、新街、河街、半边街、大龙街。”称巷者有“柳丝巷、按察司巷、水门巷、宁乡巷、高步天衢巷、黄龙巷、兴仁巷、铸钟巷。”(乾隆《长沙县志》)一般情况下,“巷皆通十字街”(嘉庆《合肥县志》卷3)。
街巷是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个城市都有其相应的街制,北京城“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吴长垣:《宸垣识略》卷5)南京城的主要街道宽度为九轨相当于今天的22.824米。(《南京古代道路史》,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就连一些县级小城的街道也不例外具有一定的规制。如“平遥街道可分为四种,大街是通向各个城市的主制建设街道的,要道路,宽约四米,可通行两辆马车,两边多为店铺;巷里是次一级道路,为居民的住宅地段,只供人行,宽约1.5米至2米;马道是顺城墙内侧环绕一周,宽约5米,为城防需要,供巡警驰马之用。庙街通向主要庙宇,两侧少有店铺。”(阮仪三编著:《旧城新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又如,广东潮阳“县内之街,一自治前之下至塔右曰新街,一自治东节孝祠之下至塔左曰旧街,各长一百丈,阔一丈二尺,俱由塔前抵南门,是为大街,长二百丈,阔同上。”(光绪《潮阳县志》卷3)
从建筑技术上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许多城市中,以中间高、两侧低的鱼脊型道路最为普遍,而且主要的街道还铺设了人行道,连京城附近的小城市通州“街道两边也有稍高的人行便道”(《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02页)。而从街道的材质来看,主要有两种,一为使用石材铺设,一为以土夯实地面,即为我们常说的土路。石材的街道以南京最多,特别是南京的官街,乃为一条宽阔的石板大道,这与南京曾为明朝建国之地有关。据记载,明朝初年,高祖朱元璋为修建南京的主要街道,不惜拆毁了历代的碑刻。对此,清人“钱大昕金陵石刻记序云,相传明祖营治都城,尽辇碑石作街道之用。窃意六朝三唐世次久远,唐灭残毁,理亦宜然。惟宋元与明相去甚近,自宣圣庙以外,绝无宋元之刻,其为洪武所毁无疑。”(《十二砚斋随录》卷3,见《清人说荟》二编)可见,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碑刻被毁坏,已成为后人引以为憾之事。但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些石碑被用于地下,也使南京的石材街道位列全国之首。
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间有使用石材,如18世纪,英国人访华使团马嘎尔尼等人在经过杭州的主干街道时,看到“中心是板石铺路,两旁是碎石便道”(《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5页)。但在当时,不论城市大小,能够以石铺设的街道实在少得可怜。即使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也不过只在通往城门的主干街道上铺石,以故时人感叹说:“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阙名:《燕京杂记》)。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土质结构的道路给城市居民带来的首先是路途高低不平所造成的行走不便,更令城居者甚感不便的是土质道路在风沙天气、阴雨天气对环境的污染。在明人沈德符笔下有这样的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不免挑浚。然每年应故事而已。”(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遗憾的是,这种以土质道路为主而结成城市交通网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才得以逐步改变。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技术的落后,但更主要的则是政府财政能力的低下所造成的,同时也说明时人对城市街道改造与生存环境的严重忽视。
尽管如此,城市街道、特别是城市主要街道的宽阔,仍已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一大人文特色。在外国人的眼里,“初进北京大门第一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的街道有一百尺宽”(《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3页),与欧洲夹在高楼之间的窄巷形成鲜明的反差。当然,宽阔的街道多建于坐落于北方平原上的城市,而南方多山地多湖泊的地理条件限制了人们对街道宽度的设置,以致像杭州府这样的大中城市,其街道也很狭窄。
街巷的外观建筑展示着时代的风格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状况,而街巷的内里空间却同样折射出带有社区差异的文化特征。这首先表现在那些属于工商社区的街巷,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已由交通功能让位于由居住者所形成的人文功能。如“扬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径甚多。居此者,妇人多以作肚兜为业,而门面又相似,故行人多歧误焉。有作寄江南词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扬州好,年老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误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游。’”(梁章钜:《归田琐记》卷1)又如,天津“估衣街上古衣多,高唱衫裙值几何,檐外行人一回首,不从里坐也来拖。”(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1,直隶,《天津风俗诗》)这些街巷的名称,完全体现出城市的工商业属性,是城市文化在街巷上的直接反映。
其次,街巷的名称也往往反映出城市的属性。传统而又古老的中国城市,其政治的烙印与影响尤为鲜明地反映在街巷上,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城北京,其街巷无处不留有政治的痕迹。如北京外城北城的绳匠胡同,系以“丞相”的谐音而作“绳匠”,据记载,此街曾先后有几位“丞相”浴具于此。《水曹清暇录》曰:“绳匠胡同有休宁会馆,盖前明许相国维桢旧第也。屋宇宏敞,廊房幽雅;有古紫藤二,马缨花一,相传乃相国手植。”(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4,休宁会馆)《宸垣识略》曰:“大学士陈文简元龙邸在绳匠胡同北,有圣祖御书爱日堂额。”(吴长垣:《宸垣识略》卷10)此外北京内城的“石大人胡同”,为明朝大臣石亨赐宅,石亨在景泰年间以武将受于谦所荐,命“总兵十营”,得到重用,又因在反击蒙古瓦剌入侵的京师保卫战中立有大功,封为侯爵。而后,他直接策划并参与了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晋封为忠国公、加官兵部尚书,故有赐第于此。然石亨专横,所营之第亦“壮丽逾制”,终因擅权而致患被诛。
再次,街巷作为历史的产物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然而事实上,作为街巷的“二十四桥”,确曾有过二十四桥。据早于吴趼人一百年左右的清人李斗记载:“廿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熙春台后。平泉涌瀑之水,即金匮山水,由廿四而来者也。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砖墙庋版,围以红栏。直西通新教场,北折入金匮山,桥西吴家瓦屋圩墙上石刻烟花月夜四字,不著书者姓名。扬州鼓吹词序云: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或曰即古之二十四桥。二说皆非。按二十四桥见之沈存中补笔谈,记扬州二十四桥之名。曰:浊河桥、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洗马桥、南桥、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明桥、太平桥、利国桥、万岁桥、青园桥、驿桥、参佐桥、山光桥,实有二十四名。”“程午桥扬州名园记,谓后人因姜白石扬州幔(或作慢)词念桥边红药句,遂以红药名是桥。”(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可见,在清乾隆年间,扬州确曾有二十四桥,但是在历经百余年的岁月变迁之后,二十四桥已不复存在,它以一条街巷的面貌展现给后人,而它的被沿袭下来的名称又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遐想以及对其历史的追忆。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而城市文化是城市文明中的最基本的内涵,它不仅丰富多彩,且有着深厚而浓郁的底蕴。作为明清城市平面布局的坊巷社区,它在绘制出城市空间的分布样态的同时,也展现出其厚重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流传至今的坊巷分布及名称来看,它已经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为了一体。
[收稿日期]200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