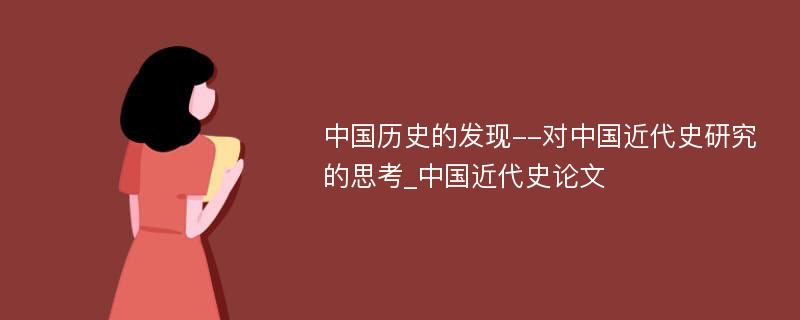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5-0107-06
傅斯年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说,“大凡要把一句话,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彻圆满了,必须于作这言者所处的milieu了晓,否则字面上的意思合起来不成所谓”。换言之,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读其书而不晓得作者的时代背景,“有许多意思要丧失的”。但“milieu是一个各件以分量不等配合的总积”,而古人之所言,本都是随他们的milieu物化的了,“所以后一个时期的人,追查前一个或一、二千年前好几个时期的milieu,是件甚难的事”。(注:本段与下段,参见傅斯年的一份残稿,大概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所写的序言,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该所整理人士代命名为《作者、环境与其他》,并大致确定文章约撰写于1923或1924年。感谢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按Milieu本法语,巳成英语中的外来词,其最接近的指谓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Scene,Background,Surroundings,Situation等义,大致印傅斯年在此文中所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这时空两义的集合。)
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傅先生在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后总结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
该文大约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作者可能是吴稚晖)所写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庄谐并出,然正如傅斯年所说,“这里边的意思也不会不庄重”。其实傅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他所说的“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进而言之,“对手方”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承,它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
特定学术作品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接受者的预设,以及为使其预设接受者“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而做出的有意努力,直接影响到学术作品的构建。而“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例如学术刊物和机构)对双方的影响,在这些与学术的“接受”相关的多因素互动下逐渐形成的有意、无意或下意识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材料的认定和使用、争议的问题、表述的方式技巧,甚至所谓“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制约甚至型塑着学术成品的样态,从而最后影响到“知识”本身的建构,并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注:参见罗志田:《学术的“对手方”》,《历史研究》2004年4期。)
简言之,学术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形成之影响,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今日一般所说的学术作品,大概属于傅斯年所说“对手方”有限而“局促于一种人”的范围,但这是相对于广泛的“人人”而言;实际上,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义的。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至少比台湾地区就所差尚远;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多年前针对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反动,以及近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国斌(R.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注: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三书现在似都有中译本。)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
以“国家民族”(nation)为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不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特别是英国)左派史家那样曾对历史诠释中“国家民族”与“阶级”之间的紧张进行较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也较少在具体层面处理“国家民族”在历史诠释中的地位问题。或可以说,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史学界基本未曾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那样深入探讨马克思未曾处理或“解决”的问题这一阶段,(注: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他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现已有中译本(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缺乏这一反思经历的中国学情与西方相当不同。故“国家民族”观念在西方已渐被视为对历史研究的束缚,最典型的反映当然是前引杜赞奇的书,但在中国内地,根本是以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者未必普遍,遑论控制性的束缚。(注:这个问题牵涉甚广,可能相当一些人不会同意。现试举一例:清季士人曾以历代史书为帝王家谱而反对“断代”,许之衡约在1905年即说,“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受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记》不断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这里可以说有着明确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且从此角度代司马迁立言。许多民国史家也曾继承了“断世”而不“断代”之说,但后来确实无意之中“回归”到新史学之前的“断代”倾向,故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提倡“打破王朝体系”,可知此前并未能真正否定。近年上海一出版社更在重印所谓“经典的”断代史丛书,尤可见非“国家民族”的王朝体系这一传统之有力。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通史与断代史的持续竞争,我会另文详论。)
又如柯文(Paul 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1],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1](《中文版前言》P1-2)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那么乐观。尽管该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2](《再论问题与主义》P230)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便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1](《译者代序》P17-21)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而已。[1](《序言》P1)这大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注: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21-29页。)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难以“沟通”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觉察到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的既存差异。
许多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注: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近年一些的新探索可参见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3-108页。)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注:全文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页。)将此与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为三大高潮,并以之为主线来认识近代中国(据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的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十九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我不能说胡绳等提出“三大高潮”是主观上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本土因素(尽管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倾向),但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当然,这只是就倾向性而言,实则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惟其体现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个案研究。(注: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在晚年指导学生时,就明确提出以研究“如何”或“怎样”来解决一些“是否”的争论,因为,“‘如何’‘怎样’的问题解决了,‘是否’问题也就真正解决了”(刘大年致姜涛信,转引自姜涛:《大年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37页)。但现在不少老中青史学从业者,包括那些学术取向与刘先生接近或不怎么接近的学者,似乎仍更注重“是否”的争论,而相对忽略“如何”或“怎样”的问题。)
“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至少体现出倾向的不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注:这在全国性学会的组成上体现得最明显,1919年后的历史有中国现代史学会,此前的80年过去定为“近代史”,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学会”,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个学会。现代学术机构对研究的推动有目共睹(特别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结果是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无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响到整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国的和外国的)。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提示着中国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所谓“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注: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否“优良”的学术传统一旦中断,学术积累便虽有而亦似无,其实也就失去了今日中国大陆特别凸显的“创新”的基础,最容易造成某种“非驴非马”的后果。)我想,要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这一可能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既存研究关注“半封建”胜于“半殖民地”这一客观后果大体可立,则今后的中国近代史恐怕还要增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研究。由于被侵略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甚或决定着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应更加侧重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特别是侵略与被侵略双方在中国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冲突和互动过程。(注: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对更广义的“西方冲击”亦当类此,不仅是简单陈述中国的“反应”(如所谓“开眼看世界”及引进外来观念体制等),或应更具体地探讨在中国的西方(the Western presence in China)的言与行,对这些的“冲击”有更深入的认识后,必能更易领会中国朝野的各种“反应”。
其实“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指出,对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清廷甚少主动提出修订,这主要反映出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他那时就提出应从提问层面移位到清人方面的主张。(注:John K.Fairban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idem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57-75.)此文可说是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说明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并将其落实到提问层面,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内容仍是受外在预设影响或制约的“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带有异国眼光的“中国史”。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国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自身的“精神错乱”现象,(注:例如,崔述的被“埋没”就是一个“最佳例证”。参见Arthur W.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收入《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442页。)前引柯文所表述的西方史家曾试图从中国学者著述中寻觅“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的现象表明,中国学者自己“忽视中国”的倾向仍长期持续,故美国学者感到他们有责任来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一研究取向产生于外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被“发现”的“中国史”很可能带有异国眼光,毕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受西方整体史学的影响甚大,其具有的“问题意识”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当中国学者转而“引进”并仿效这一取向时,进一步的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史”也带有异国风味。
我这里决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更多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结论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更进一步地与外国同行真正进行“对话”,而不是将国外研究作为“通货”一样进行“流通”。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这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多年来一直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早在1922年,李济就提倡一种“在心理学基础上研究语言学”以认识“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的困难在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有时难以用心理习惯形成于其间的那种语言来描述某些文化现象,若研究者掌握与母语判然不同的第二种语言(这里具体指的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这样具有根本差异者),如用拼音文字描述象形文字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然后对结果进行反向鉴别,则可能认识到特定文化那“心智的起源”,即思想的原初形式(反之,用象形文字描述拼音文字的文明亦然)。这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互证的方法”或许是“以最客观的方式研究最主观的自我的方法”。(注:Chi Li,“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7:4(Feb.1922),pp.325-329,此文承徐亮工先生代向李光谟先生请益,蒙李先生赐赠,特此一并致谢!)
40年后,李济再次对西方学者说,他当年论文的主旨是:“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针对有些西方汉学家以为“无需对中国文字有足够的知识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文明”这一观点,李济提出,像“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这样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参与者“应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须能用中国语言文字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文字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3](《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P286,296,298-299)
我想,李先生对西方中国研究者的要求同样适合于他远更关注的中国自身的中国研究者。由于“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发生、成长、形成和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注: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22),收入其《安阳》,284页。按此文是前引李济文修订本的中译,两者颇有不相同处,关于“双语互证”的问题修订本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3](《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P284)母语研究者应该说有着某些先天的优势。但李济也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这样的“自我意识”对于人文学研究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他在1922年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的普世性问题,即中国学者在剥夺科学之“欧洲籍”的同时,自身也应体认到“超越自己国籍界限的紧迫性”,主动“摆脱国籍的限制”。(注:Chi Li,“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7:4(Feb.1922),p.326.)从这一视角广义地看李先生提出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异国眼光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就更明显了。
进而言之,颜师古早就提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见解。[4](第2册,P2)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央政府在学校教育中正式确立“国语”(即白话文)的地位后,古文在中国已是几乎不再使用的历史文字,今人读古书与学外文实有相类处,读错的可能性几乎是人人均等。在这一点上,中外学人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读“懂”的程度主要靠后天的训练。套用韩愈的一句话:中国人不必不如外国人,反之亦然。(注: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240-241、347页。)
对史学而言,所谓“地方性知识”(注: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或应包括时空两个层面。空间层面似不必论,而时间层面的“地方性知识”主要是说:即使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里,对同一文化系统内的今人来说,古人实际已是“非我”或“他人”(the other)。《庄子》中的师金论世变说:“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庄子·天运》)。其所说的虽是礼仪法度当应时而变,也暗示了古今之间的“断裂”犹如周鲁之为“异国”(当然,先秦“国”的概念未必等同于今日流行的“国家”)。(注:参阅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若本陈寅恪所倡议的“以观空者而观时”的取向,时间层面的“外国”或“他人”亦自有其“地方性知识”。(注:参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164页。并参考William H.Sewell,Jr.,“Geertz,Cultural Systems,and History: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in Sherry B.Ortner,ed.,The Fate of Culture:Geertz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37-38.)
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P693)或者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已逝的往昔其实是无语的,它不能在后人的时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后人表述。
既然西潮早已成为今人面对的近代中国“传统”之一部分,(注: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既然我们过去的研究也未曾离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将“在中国发现历史”落实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注:按柯文原书名为“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本也可译为“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如柯文所说,史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往往决定着在数量无穷而沉默不语的往昔事实中“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注:柯文:《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页。)若能尝试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注:例如,当我们说学术或史学怎样分类甚至是否应当分类时,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考察特定历史阶段或长程历史时段中学术实际是否分类或怎样分类时,我们探讨的是“他们的”问题。这样的人我之分若不在研究者的意识层面充分明确,便很可能会以“我们的”问题替代“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压抑了无语的往昔。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地方性知识”。
收稿日期:2004-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