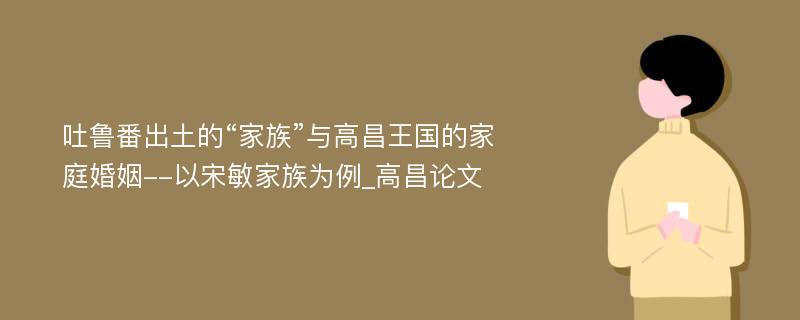
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以宋民家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民家论文,王国论文,为例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4—0084—09
迄今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共有两件族谱,一件是1966年出土于阿斯塔那50号墓的《某氏族谱》,一件是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那113号墓的《某氏残族谱》①。关于这两件族谱,学者们已有一些相关研究,马雍先生认为《某氏族谱》乃麴氏高昌时期之物②。王素先生分别对两件族谱谱主的郡望、姓氏及其生活的时代进行了考证,并将它们分别定为东汉至十六国之间敦煌张氏的族谱及十六国后期至高昌国前期的《西平麴氏族谱》③。李裕民先生认为前者应为北朝遗物,最迟不得晚于隋代,后者当作于北魏后期④。郭锋先生主要从谱牒修撰的角度对二谱的体例、格式及内容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并试图将二谱进行复原,理清其世系脉络,认为二谱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私谱状况,可视为中国家谱世系图的原始形态之一⑤。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其它问题时也曾涉及这两件族谱,不过大多是将其作为门阀政治兴盛的旁证⑥。这两件族谱有一共同的特点,即均出土于谱主姻亲的家族墓中。本文拟以《某氏族谱》为出发点,以谱主的姻亲宋氏家族为例,讨论家族、婚姻、墓葬及族谱等相关问题。
一、谱牒、家族与婚姻
西汉末年,随着平民有姓氏的大体完成,人们的父系、母方并重观念逐渐转变为父系意识占主导。从人们生活的角度看,父系意识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姓氏的变化,即从“妄变姓氏”到子从父姓;二是父系世系意识的强化,即对父系祖先记忆的强化及对父系后代的追求⑦。以父宗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其亲属范围则包括自高祖而下的男系后裔;家的范围则较小,通常指同居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⑧。从服制上来看,则“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⑨。但是对于大族而言,其亲属关系的认定往往超出五服的范围⑩,虽不一定同居共财,但不影响其宗亲关系。尤其汉末以来政治上的选举重阀阅与名声(11),促使谱牒之学兴盛,选官和婚姻成为修撰谱牒最主要的两个目的。《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婚姻目的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是以家族为中心,非个人,也非社会的。为了使祖先能永享血食,故必使家族永久延续不辍。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具有宗教性,成为子孙对祖先的神圣义务(12)。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非个人性的特质,婚姻的缔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因此,这往往成为两个家族间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常常与家族的现实利益相关,受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因素所影响(13)。因此,不同的家族在同一背景下有可能因为其实际利益的类似而做出相同的选择,同样,相同的家族也有可能由于其在不同背景中的现实利益变化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在门户观念兴盛的时代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在北魏高祖至北齐间,博陵崔氏与范阳卢氏都经常选择赵郡李氏作为联姻对象(14)。又如,北魏皇室在道武帝入主中原至孝文帝改革期间,其联姻方针以与宾附之国的上层人物婚配为主;但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至拓跋氏政权分崩离析的北魏后期,其婚姻主要与汉人士族缔结(15)。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举。联姻家族的选择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相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会由于婚姻的选择而发生变化。这种反作用力的大小往往与家族本身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社会上层家族,尤其是皇族及与之有婚姻关系的家族的婚姻常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16)。对一个家族的婚姻对象选择的研究可以折射出该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
二、宋氏与张氏的联姻
北朝时期的宋氏大致有三支:广平郡宋氏、西河郡宋氏及敦煌郡宋氏,他们的具体情况各异,选择的联姻对象也各有差别,如广平郡宋氏曾与赵郡李氏、彭城刘氏联姻,西平郡宋氏曾与京兆韦氏联姻(17)。在敦煌地区,宋氏与张氏均为当地大族。二者的联姻关系从文献史料中可窥其一斑,《魏书》卷五二《宋繇传》云:“(宋繇)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八岁而张氏卒,居丧过礼。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谓妹夫张彦曰:‘门户倾覆,负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遂随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18)宋繇为十六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与同为敦煌大族的张邈等共同辅佐凉武昭王李暠。当暠子恂任敦煌太守时,也曾得到“在郡有惠政”的“郡人宋承、张弘”的协力匡助(19)。在这个时期,宋氏与张氏在敦煌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相似,对于家族利益的考虑也类似,选择对方为本家族的婚姻对象之一,既有当时社会流行的门阀观念及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对双方巩固其在地方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社会声望、地位等的现实考虑。
对于迁居高昌的宋氏来说,在大致同时期仍保持着与张氏的联姻,这在吐鲁番出土的墓砖材料中可以找到痕迹。1930年出土的《大凉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记:
1 河西王通事舍人
2 敦煌张季宗之
3 墓表。夫人敦煌
4 宋氏。(20)
又,1969年出土于哈拉和卓52号墓的《大凉张幼达及夫人宋氏墓表》云:
1 龙骧将军散骑常
2 侍敦煌张幼达之
3 墓表。
4 夫人宋氏。(21)
可见,在十六国时期,宋氏和张氏基本保持着联姻的状态。从《某氏族谱》现存的内容上来看,与谱主婚姻关系最密切的是宋氏家族,共有十例,即金皇适宋重英、提夫人宋氏、需夫人宋氏、缺名妻宋黄头、缺名夫人宋氏、还兴夫人宋苟女、四妃适宋洪施、缺名夫人宋女英、缺名适宋氏、龙训适宋宾,其中以宋氏为妻者六例,适宋氏者四例。该谱中的宋氏为敦煌郡人,根据王素先生的研究,此谱为十六国时期之物,可能是敦煌张氏族谱,谱主的生活时代大致在东汉至十六国之间(22)。那么,宋氏与张氏之间的联姻关系可上溯到东汉,并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期。由于该宋氏家族具体何时迁往高昌地区不得而知,因此,撰谱者可能生活在其家族迁居高昌之前,也有可能在之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个家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对方作为自己婚姻对象的选择之一。
麴氏高昌国末期,宋、张两氏仍保持着婚姻关系,这从2004年出土于木纳尔1号台地的宋氏家族茔院内103墓的《麴氏高昌延寿九年(632年)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张氏墓表》可窥其一斑,其录文如下:
1 兵曹司马宋佛住妻
2 张氏春秋七十四殒
3 塟斯墓。
4 延寿九年壬辰岁
5 五月甲寅朔七日己
6 未题记。(23)
不过,在这段时期,张氏出现在政治生活中的频率开始大大超过宋氏。当然,不能排除两氏在迁往高昌地区的相对人口数上有差别,从而导致其在高昌地区出现频率的相对差距的可能性以及现有材料的有限性。但是,也不能否认这种差距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家族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升降变化。
三、墓葬与家族
从墓葬来看,高昌普遍实行聚族而葬,吐鲁番地区已发掘有各氏家族茔院,并且许多同姓家族茔院分布于不同墓地,以宋氏为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木纳尔等墓地均发现有宋氏家族茔院(24)。就各茔院成员本身来说,他们可能属于同一支系家族。如上文提到的木纳尔1号台地宋氏家族茔院中发现4座墓葬(M101~M104),东西呈“一”字形排列,墓向与茔院方向一致,坐北朝南,年代顺序是由西向东,即M104为最早入葬者(25)。其中M103和M102共出土墓志3方,除前引《麴氏高昌延寿九年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张氏墓表》外,还有编号为2004TMM103:1的《麴氏高昌延寿四年(627年)十月二十九日宋佛住墓志》:
1 延寿四年丁亥岁十
2 月庚辰朔廿九日戊
3 申故宋仏住新除北
4 听散望,中出作永安
5 兵曹参军,转迁内行
6 兵曹司马。春秋有六
7 十六,殡塟斯墓。
及编号为2004TMM102:12《唐显庆元年(656年)二月十六日宋武欢墓志》:
1 君讳武欢,字□,西州永安人也。君,兵
2 曹参军之嫡孙,司马之贵子。生
3 □□下,有反哺之心;长堪强仕,
4 □尽节之志。不骄不贵,出自衽
5 生;行恭行敬,廪(禀)其天性。我君光
6 武王尚其高行,拜从行参军
7 事。计当与金石同固,保守(寿)长
8 年,掩然迁化。春秋六十一。显庆元年
9 二月十六日葬于永安城北。呜呼哀哉(26)。
从这两方墓志可以看出,宋武欢为永安人,兵曹司马宋佛住之子,其祖为兵曹参军,很可能葬于M104。他们属于同一支系家族当无疑议。但是不同宋氏茔院成员间的亲属关系目前尚不能直接证明,不过豪强大族往往举族而迁,对于移民高昌的宋氏来说,也不能否认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宗亲关系的可能性。葬于两处却有明确亲属关系的情况可在中原地区的一些聚葬中找到痕迹。如1968年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南发现博陵崔昂一支的族葬地(27)。1998年在距其约4.5公里的两河乡西岳村北700米处,发掘了博陵崔仲方及其妻李丽仪、子崔大善三座墓葬(28)。学者们根据两地出土墓志所记世系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列出其世系,则崔昂当为崔仲方之从叔(29),属小功亲。二者虽不葬于同一处,但其亲属关系清晰可辨。
此外,木纳尔墓地东距1号台地约600米的2号台地上有张氏家族茔院,坐北朝南,内有12座墓葬(M201~M212),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从出土墓志年代来看,与宋氏家族墓葬属同一时期,年代排列为先里后外,同排的由西向东,M201当为最早入葬者(30)。宋佛住之妻张氏很可能属于该家族。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宋、张两家关系的密切。类似情况还见于哈拉和卓墓群中的张氏茔院和宋氏茔院,其中张氏茔院的M52出土有《大凉张幼达及夫人宋氏墓表》,可为两家婚姻关系之证(31)。
四、宋氏与张氏联姻的变化
比起前述两处墓地,《某氏族谱》出土的宋氏家族墓茔与同地区的张氏墓茔距离稍远(32),并且该张氏家族在高昌王国后期的社会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宋氏,主要与王族麴氏联姻,并在联姻王室的诸姓世族伙伴中,形成了压倒性优势(33)。白须净真先生认为,从5世纪末到7世纪中叶,在高昌地区也存在着一个严格的身份制度(34)。从任官的角度来说,麴氏高昌时期,除了国王外,第一等级的官职令尹只能由王室一族的世子独占。第二、三等级的高级官职除麴氏一族外,也只有世代与之联姻的张氏家族才能拥有。第四、五等级的官职,也为屈指可数的高门望族所据占,而这些家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与麴、张两家有着姻亲关系(35)。而从出土的几个宋氏成员的墓志及文书来看,其在麴氏高昌时期的官职主要有:兵曹主簿(《高昌章和八年(538)宋阿虎墓表》),属于郡府官职的第八等级(36);虎(武)牙将军(《唐永徽六年(655)宋怀憙墓志铭》、《高昌追赠宋怀儿虎牙将军令》),属于将军戎号的第八等级(37);户部参军(《唐龙朔四年(664)宋怀仁墓志》),属于中央的第六等级(38);兵曹司马(《麴氏高昌延寿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宋佛住墓志》),属于郡县官职的第六等级(39),等等,均为第五等级以下,是即便与麴、张两家无婚姻关系的家族的成员也可以担任的(40)。孟宪实先生认为,高昌虽有门阀等级,但并不张扬门阀观念。表现在墓表中,就是宁肯赞扬个人品质甚至长相也不追述家族的荣耀,更不与中原的高门大族攀龙附凤(41)。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使得高昌的各家族地位高低并不以其以前的郡望来衡量,而是以其在实际高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升降为标准。对于同姓各支系家族来说,其婚姻对象的选择也会随其家族地位的升降、利益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就同一时期而言,宋、张两氏的联姻可能更多地维持在埋葬于木纳尔的宋、张两家中,而葬于阿斯塔那的张雄一支,由于其家族地位的耀升,更偏向于与王族等权贵家族联姻。
此外,王素先生根据“该谱书法捺笔较重,隶味较浓,具有十六国时期的书法特点”,判定其应是十六国时期之物(42)。若此,则该谱年代已经较为久远。另外,它被剪成了鞋样随葬,说明已无保存价值。王素先生推测,该谱为宋怀儿的配偶所有,是其从娘家带来的本家族的族谱(43)。笔者认为,它出现在宋氏墓葬中,推测其为宋氏成员的配偶所携来是合理的,但并不一定是墓主的配偶所带来,还有可能是墓主先人的配偶带来。宋氏配偶将其从娘家带来可视为其婚姻方面的表现之一。宋氏将其保存,并传递下来,正反映了其联姻关系的维持。从现实功用出发,迁居高昌的宋、张两氏可能由于其家族地位的升降变迁,已整理修订新的族谱,而将此旧本废弃。
五、谱牒类型及其功能偏重
现存的唐以前谱牒类型除了上述《某氏族谱》的图表式外,还有家传这一叙述形式。后唐赵莹在《论修唐史奏》中记:“古者衣冠之家,书于国籍。中正清议,以定品流。故有家传、族谱、族图。”(44)家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中正清议,以定品流”,即为了选官,因此家传的形式必然与此密切相关。现存的《敦煌氾氏家传残卷》正是这一形式最好的说明(45)。从录文看,该家传共有97行,分为两个部分。第1~24行为总序,叙述氾氏家族的姓氏源流、远祖传承及其迁徙等情况;第25~97行为分传部分,分别介绍氾氏家族中佼佼者的仕宦经历及名望。郭锋认为,晋唐所谓家传,实际上是家族仕宦人物传(46)。有学者认为,将姓氏溯源至三代是敦煌述祖文献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由于敦煌边民的不安主要源自种族层面,因此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将氾氏确确切切地挂附在华夏民族这个族类之中,并通过这种确切具体的描述来强化其种族记忆”(47)。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的追溯现象并不仅见于敦煌地区,而是普遍存在于各地。从侯旭东先生整理的碑铭材料来看,“北到今天的天津(鲜于璜碑),南到四川省卢山县(樊敏碑),东到山东东平(张迁碑),西到青海省乐都县(赵宽碑),说明这种追求不是一时一地的士人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追寻的结果尽管错误百出,但沿着父系寻找祖先的观念已然日益强化,换言之,父系祖先意识已成为促使他们追寻氏族来历的基础”(48)。此外,由于家传的目的是为了选官,在选举重阀阅的时代,追寻姓氏来源,宣扬祖上功德,对于抬高本家族声望、博得名声大有好处。
与家传相比,高昌地区出土的图表式的族谱,虽然内容较为简单,但是其涵盖的信息量却不少,不仅有家族传承的世系,成员的简要仕宦经历,还有各人的婚姻对象,其中包括女性成员的婚姻对象。在当时“士族择偶对于男家女家的门第极为看重,而社会人士也以此来衡量某一氏族的门第,甚至政治上的选举亦以婚姻为考虑条件,与政治经历同样重要”(49)。《某氏族谱》正好符合这种要求,其对女儿所嫁夫婿名字的记载正是女家与婿家同样重要的表现。将这两种类型的谱牒相比较,可以看出其功能偏重上的不同,家传更重视家族成员的仕宦经历及名望,而氏族谱则更偏向于记载家族世系及成员的婚姻状况。可能正是由于这两种类型在功能上的偏重不同导致了其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同,而高昌地区的两件图表式氏族谱均出自谱主的联姻家族则是其在实际使用中婚姻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
六、小 结
本文主要从谱牒与婚姻的角度,对高昌出土的《某氏族谱》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联姻与家族地位问题。主要从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以宋氏与张氏的联姻为例,结合家族墓茔,梳理了宋张两氏婚姻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家族实际地位的变迁而带来的现实利益的变化。
2.《某氏族谱》的出自及其存废问题。该谱被剪为鞋样随葬,为废弃之物,推测可能是宋氏墓主的先人之配偶从娘家带来,由宋氏子孙将其进行保存,并传递下来。这种保存传递的行为反映了谱牒在婚姻方面的作用以及两氏联姻关系的维持。不过迁居高昌的宋、张两氏可能由于其家族地位的升降变迁,已整理修订新的族谱,而将此旧本废弃。
3.谱牒的类型及其功能偏向问题。通过对《某氏族谱》的图表式与《敦煌氾氏家传残卷》的叙述式进行比较,分析了两者在记述内容上的偏重差异反映出其在现实功能上的偏向有所不同,前者重于婚姻,而后者则偏于选官。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以上诸问题的探讨,梳理了《某氏族谱》在婚姻方面反映出的问题及功能,并以婚姻为视角,通过两氏家族婚姻对象选择的变化反映出该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从一件族谱的存废情况折射出家族与时代背景的变化,透过谱牒体例选择的不同看其修撰的目的偏向以及现实功能的偏重,从而观照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情况的变迁。高昌地区出土的《某氏族谱》虽然内容残缺不全,难以窥其全貌,但其中蕴含的信息是很丰富的,值得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发掘其蕴含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意义。有关它的研究不仅对谱牒学的发展颇有裨益,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家族史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
注释:
①《某氏族谱》载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79~184页,图文对照本第壹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82~384页。《某氏残族谱》载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63~64页,图文对照本第壹册,第333页,该文书原本定名为《高昌某氏残谱》,图文对照本中改为《某氏残族谱》,现依后者的定名。
②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原载于《考古》1972年第4期,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3~173页。
③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
④李裕民:《北朝家谱研究》,载《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1~69页。
⑤郭锋:《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⑥如钱伯泉在《从S2828号写经题记看高昌麴氏王朝与敦煌的关系》(《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一文中即以《某氏族谱》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门阀制度、标榜门阀、联络宗亲的谱系之风兴盛的证明。此外,他在该文的注7中根据氐道县的置废时间认为该谱中的“氐道令”至迟也应为东汉时人。(钱文标题之编号当作S2838。)
⑦详见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载《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206页;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载《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107页。
⑧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2~3页。此外,有学者在血缘基础上加入财产因素,认为家庭成员主要是父己子三代,最广推到同出于祖父的人口,这是一个同居共财的社会和经济单位,大功以外至缌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财,算作“家族”,至于五服以外的同姓虽共远祖,疏远无服,只能称为“宗族”。家庭、家族与宗族犹如一串同心圆,其范围因时因地而异,也有重迭部分,但政治社会功能则一脉相通,可以互补。详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780~853页。
⑨《礼记正义》第43卷《大传》,〔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2年。
⑩如《颜氏家训》第2卷《风操》(中华书局,1985年)曰:“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虽然这“于礼未通”,但却反映了即便相隔多世,其宗亲关系仍可辨认。
(11)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提到汉末的选官有“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趋向,之后的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详见作者《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92页,第151~157页。
(1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97页。
(13)中国自古就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之后甚至成为法律条文。《唐律疏议》第14卷《户婚》下记:“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三年。缌麻以上,以奸论。”不过同姓与同宗有别,该条疏议中也有强调“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瞿同祖先生在讨论族内婚时也提示了法律与社会间的距离,实际生活中存在夫妻同姓的例子(《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99页),但其与本文讨论的家族联姻无涉,故在此不论。
(14)参考毛汉光:《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第619~698页。
(15)参考高诗敏:《北朝皇室婚姻关系的嬗变与影响》,载《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
(16)有关中古时期士大夫家族及皇室家族的婚姻关系的研究很多,如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J.Holmgren,Family,Marria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ixth Century China:A Study of the Kao Family of Northern Chi,C.520—55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6(1982),pp.1—50;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长部悦弘:《北朝隋唐时代にぉけゐ胡族の通婚关系》,载《史林》第73卷第4号,1990年,第34~73页;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隋至唐前半期》,收入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87~139页;《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关系为中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1分,1991年,第119~192页;王怡辰:《东魏统治集团的婚媾关系——以高氏和元氏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3年,第83~104页。
(17)长部悦弘:《北朝士大夫通婚关系表》,载《日本东洋文化论集: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纪要》第3号,1997年,第87、98、111页。
(18)同见于《北史》第34卷《宋繇传》。
(19)详见《晋书》第87卷《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20)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7~9页。
(21)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10~12页。
(22)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第67页。
(23)该墓志编号为2004TMM103:2,其录文系荣新江、李肖、孟宪实领导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集体研究成果,在此向小组成员表示感谢。参看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载《考古》2006年第12期,第41页,图20。
(24)如本文所讨论的《某氏族谱》出土的阿斯塔那50号墓葬虽无墓表及随葬衣物疏,但出有高昌重光三年(622年)文书及《高昌追赠宋怀儿虎牙将军令》(《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166、175页),王素先生根据发掘报告所附位置图,认为与该墓同时发掘的阿斯塔那43号、44号、48号三墓相连,为宋氏家族墓园(《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第63页)。上文提到的《麴氏高昌延寿九年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张氏墓表》则出自木纳尔1号台地的宋氏家族茔院。此外,据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可知该地区发掘有宋氏墓茔(载《文物》1978年第6期),其中出土有《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与《龙兴□年宋泮妻翟氏随葬衣物疏》(《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59~63页)。
(25)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第43页。
(26)此两篇录文亦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集体研究成果,新出墓志图版和录文已收入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待刊。参看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第41~42页,图19,21。此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补第18页的《高昌某年洿林道人保训等入酒帐》(见图文对照本第壹册,第261页)中有录文“永安宋佛仕”,笔者据图版辨认,认为此可能为“永安宋佛住”,即上文中M103的墓主。
(27)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载《文物》1973年第11期。
(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载《考古》2001年第2期。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第69页。
(30)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第27~46页。
(31)据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可知该地区发掘有宋氏及张氏墓茔(《文物》1978年第6期),又据《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的《哈拉和卓古墓群平面分布图》,可看出两墓茔相距不远。
(32)伊力:《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墓葬分布图》,载《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33)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4)他将高昌的豪族分为中央豪族和地方豪族,认为其任官与婚姻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详见白须净真《高昌门阀社会の研究——张氏を通じてをその构造の一端》,载《史学杂志》第88编1号,1979年,第25~48页。
(35)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文史》第22辑,1984年,第29~76页。
(36)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29~30页;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第70页。
(37)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80~481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175页。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第62页。
(38)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11~512页;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第66页。
(39)参看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第41页,图19;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第69页。
(40)此“张氏家族”当为以张雄为代表的支系家族。
(41)孟宪实:《唐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以吐鲁番出土墓砖资料为中心》,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第66页。
(43)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第64页。
(44)《全唐文》第854卷《论修唐史奏》。
(45)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4108页。
(46)郭锋:《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第29~39页。
(47)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第303~304页。
(48)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第98页。
(49)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182页。
标签:高昌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吐鲁番出土文书论文;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论文; 考古论文; 宋氏家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