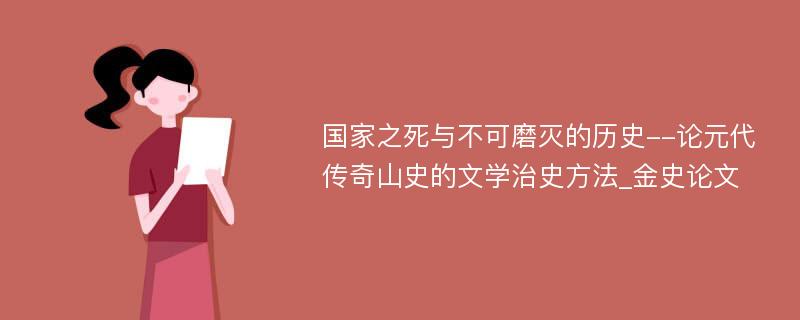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论元遗山治史之文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文学论文,国可亡论文,论元遗山治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拓跋族,①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元之际著名之文学家、史学家。幼年师从陵川郝天挺,淹贯经史百家。后中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第,得时文坛盟主、礼部尚书赵秉文推挽,哀宗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郎中,执北方文坛牛耳。金亡不仕,意“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②又“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③往来晋、冀、鲁、豫之间,遍访故旧,广辑史料,备修一代亡国之史。平生著《遗山集》40卷、《壬辰杂编》;编录金源故老诗作,成《中州集》12卷,余外尚有乐府、《续夷坚志》等作。《金史》卷126有传。《四库提要》谓其:“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至所自作(诗),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末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流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晚年尝以史笔自任,构野史亭,采金源君臣遗言往行,裒集纪录至百余万言。今《壬辰杂编》诸书虽已无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中独称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实用矣。”但于《中州集》尚有所保留,云:“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甚精。”④《四库提要》备加褒扬遗山之著述成就;至于其《中州集》价值之断语当否,有待下文讨论。清翁方纲更称誉“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苏、陆古体诗行墨间尚多排偶,一则以肆其辨博,一则以侈其藻绘,固才人之能事也。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⑤
今所论者,元好问以文学方法修史,借亲撰诗文、辑录他人诗作成集与修纂史书三重手段,以构拟、保存金源一代历史之治史思想与修史方法。其中《壬辰杂编》系记录金朝君臣言行之作,为纯粹之史籍,且早已佚失,故于下文略述而存其目,仅以论其诗文之作为主。
撰著诗文,存感性之国史
遗山一生广为金源贵裔与文臣、武将撰写传、状、铭、诔,其中多金亡后所作,既以彰潜发幽,感念故人,且以探寻故国所致衰亡之迹。《金史》本传谓后世“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⑥即指《金史》传文多采遗山之文,盖不特指《壬辰杂编》之类纯粹史书而言。此简举三例。
一、撰《如庵诗文叙》为完颜璹作传。璹(1171?~1232?)字子瑜,系出金世宗完颜雍,为太祖完颜阿骨打玄孙、(追谥)睿宗宗尧曾孙、世宗孙,《金史》卷85有传。世宗妃张氏生镐王永中、越王永功。璹即功庶长子,爵密国公。但一者其父永功被累于同胞兄弟镐王永中谋大逆案,合族幽囚四十许年;二者金源后期为蒙古南侵势力挤迫,不得已于宣宗贞祐二年(1214)自中都(今北京)迁都汴梁,国势仓皇,大不如前,故其虽贵为皇族,实拮据落魄之甚。
完颜璹为女真贵族中浸染汉文化之最深厚者,诗词风雅清丽,饱含故都故土之思,其家兼饶法书名画之藏,庋集几可与皇家大内一较高下。同时,又因其高贵之身世,不能与金末政治完全绝缘。故一部密国公完颜璹之生活史,实即金源末世之国史缩影。
完颜璹长遗山近20岁,书画之道,于遗山有近乎师弟之谊。遗山日后精于书画品识,悉出璹之提挈指教。因此,遗山撰文,不徒记事,别有一段切身情感在内。据《叙》内言,完颜璹去世于金哀宗天兴壬辰(1232),遗山当时未为之撰写神道碑、墓志铭。此或限于身份地位,无由为之;抑或亡国在即,无暇为之。而《如庵诗文叙》作于其后26年,即1258年,既属书序,且金亡国已久,因较为随便;遗山更于作此文一、二年后即去世,故尔文章本身虽为一通常诗文集序,实则有意在留存金末史实及为作者立传。《金史》卷85“世宗诸子·永功本传”附璹传,几全采《叙》文为之,即此可见遗山叙文之意义。
自文学言之,此叙温文凄惋,信为一绝佳之纪事、抒情散文;而自历史言之,其述完颜璹贵族生活之萧条与对金末高层政治之绝望,则为金代政治之重要文献。如记贞祐二年(1214)金室被迫自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云:
初,燕都迁而南,危急存亡之际,凡车辂、宫县、宝玉、秘器,所以资丕天之奉者,舟车辇运。国力不赡,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诸王公贵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法书名画连箱累箧,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他货一钱不得著身。方迁革仓卒,朝廷止以乏军兴为忧,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岁日所入,大官不能赡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贫无以为资者,其落薄失次为可见矣。
名胜过门,明窗棐几,展玩图籍,商略品第顾、陆、朱、吴,笔虚、笔实之论极幽渺;及论二王笔墨,推明草书,学究之说穷高妙,而一言半辞皆可记录。典衣置酒,或终日不听客去。炉熏茗碗,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时王家故态,……⑦
完颜璹庋藏之富,据元遗山《题樗轩九歌遗音大字后》云,“公家所藏名画,当中秘十分之二”,⑧而据《中州集》所收完颜璹诗前作者小传则云,璹“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秘等”。无论就何而言,完颜璹之书画收藏皆以量巨质精称皇家内廷之外第一人。《诗文叙》之文献价值可自两面观之:一是金源不敌蒙古族之军事迫压,自中都南迁汴梁,时狼狈窘迫,资财辇至者才“千之一耳”,国力尽失,至于“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完颜璹贵为国公,其犒酬亲友,竟须“典衣置酒”,金廷南迁后之国势及其后败亡之结局可以预见矣。二是金源女真族自灭亡北宋,入主中原以来,即以今人难以置想之速度习染汉民族文化,璹即尤著者。其于汉民族文化遗产“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他货一钱不得著身”之钟爱,自身于书画之艺亦擅专长,即汉人或有所不及。所谓“民族融合”,于是见之。
前者则因关涉最高政治之种种避忌,只能曲笔点到即止。今人可以借其它文献,旁证事件之细节。如《叙》云:
自明昌初镐厉二王得罪后,诸王皆置傅与司马、府尉、文学,名为王府官守而实监守之。府门启闭有时,王子若孙及外人不得辄出入。出入皆有籍,诃问甚严。
元光以后,王薨,门禁缓,文士稍遂款谒,然亦不过三数人而止矣。
天兴壬辰,曹王出质。公求见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公奏:“闻孛德虽议和,孛德不甚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者。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丐。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我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⑨
案:《叙》中所谓“镐厉正等二王”,镐厉王即璹诸父永中,与璹父永功同出世宗元妃张氏;另一“王”,即璹诸父、世宗元妃李氏所出郑王永蹈,《金史》卷85“世宗诸子”有二人合传。传叙永蹈谋逆事云:
郑王永蹈本名银术可,初名石狗儿。……初,崔温、郭谏、马太初与永蹈家奴毕庆寿私说忏记灾祥,毕庆寿以告永蹈:“郭谏颇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谏相己及妻子。谏说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贵。”又曰:“大王,元妃长子,不与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马太初论忏记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灾,属兔命者来年春当收兵得位。”郭谏曰:“昨天见赤气犯紫微,白虹贯月,皆注丑后寅前兵戈谮乱事。”永蹈深信其说,乃阴结内侍郑雨儿伺上起居,以崔温为谋主,郭谏、马太初往来游说。河南统军仆散揆尚永蹈妹韩国公主,永蹈谋取河南军以为助,与妹泽国公主长乐谋,使驸马都尉蒲剌覩致书于揆,且先请婚,以观其意。揆拒不许结婚,使者不敢复言不轨事。永蹈家奴董寿谏永蹈,不听。董寿以语同辈奴千家奴,上变。是时,永蹈在京师,诏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鑑鞫问,连引甚众,久不能决。上怒,召守贞等问状。右丞相夹谷清臣奏曰:“事贵速决,以安人心。”于是,赐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长乐自尽。蒲剌覩、崔温、郭谏、马太初等皆伏诛。仆散揆虽不闻问,犹坐除名。董寿免死,隶监籍。千家奴赏钱二千贯,特迁五官杂班叙使。自是,诸王制限防禁密矣。
叙永中事云:
镐王永中,本名实鲁剌,又名万僧。……初,置王傅、府尉官,名为官属,实检制之也。府尉希望风旨,过为苛细。……四年,郑王永蹈以谋逆诛。增置诸王司马一员,检察门户出入,球猎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故尚书张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间画永中母像,奉之甚谨,挟左道为永中求福,希觊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诅咒诛。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发也。会镐王傅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诏同佥大睦亲府事、御史中丞孙即康鞫问,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门所撰词曲有不逊语。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诏遣官覆案,状同。再遣礼部尚书张暐、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覆之。上谓宰臣曰:“镐王秖以语言得罪,与永蹈罪异。”参知政事马琪曰:“永中与永蹈罪状虽异,人臣无将,则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辄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诏以永中罪状宣示百官杂议,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对便殿。皆曰:“请论如律。”惟宫籍监丞卢利用乞贷其死。诏赐永中死,神徒门、阿离合懑等皆弃市。……泰和七年,诏复永中王爵,赐谥曰厉。⑩
此即二王谋逆案始末大略。至于二王族属,遗山有《夹谷公神道碑铭》,作于金亡后八年,即1242年,记曰:
明昌以来,镐厉王、卫绍王族属皆终身禁锢,男女幽闭,绝婚嫁之望。公(案:指墓主夹谷土剌)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贱同匹庶,就有诡谋,谁与同恶?宜释其宿怨,宏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国君不可以仇匹夫;仇之,则通国皆惧。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语虽不即从,其后天兴初元之赦,皆听自便,盖自公发之云。(11)
则镐厉王等罪王家属“终身禁锢,男女幽闭,绝婚嫁之望”起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讫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长达四十年。封建皇室权位之争,惨酷如此。而其罪罚之非人道尚不止于遗山所记。遗山有门弟子名郝经,系遗山业师郝天挺之孙,《元史》卷157有传。郝经著有《陵川集》,卷11《青城行》古歌行有句云:
最苦爱王家两族,二十余年不曾出。朝朝点数到堂前,每向官司求米肉。男哥女妹自夫妇,靦面相看冤更酷。一旦开门见天日,推入行间便诛戮!(12)
它是金末汴梁城破,蒙军屠戮女真贵族之实录。案《金史·镐王本传》:“贞祐三年,太康县人刘全尝为盗,亡入卫真界,诡称爱王。所谓爱王,指石古乃。”(13)石古乃为镐王永中子,故“家两族”云者,或指镐王本支及石古乃之妻族,或别指郑王一支。幽闭期间,族属须逐日集结于厅事前,听点唱到,且穷困潦倒,至于向监守官司乞求米肉充饥。更不堪者,为合族幽闭数十年间,族中少年男女人道已通而与外隔绝,无奈竟于同胞内自择婚配,其羞愤尴尬、毁弃人伦蔑以加矣!至哀宗天兴初年,禁令方开,国已残破,族人“一旦开门见天日,推入行间便诛戮!”狼狈赴死。故本传云:
永中子孙禁锢,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几四十年。天兴初,诏弛禁锢。未几,南京亦不守云。(14)
《金史》卷93“卫绍王子从恪传”之赞语云:
章宗晚年继嗣不立,遂属意卫绍王。卫绍王历年不永,诸子禁锢二十余年;镐厉王诸子禁锢四十余年,长女鳏男皆不得婚嫁。天兴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后可知矣。(15)
案:卫绍王永济出世宗昭德皇后乌林荅氏,同为完颜璹诸父,于1209年至1213年执政,后遭废弑。本纪见《金史》卷13。
《如庵诗文叙》限于时代及撰文体例,虽不能明书事件细节,但行文间已隐约暗示其意。其所述史实,大多为后世修《金史》所采。在此意义而言,遗山著文目的已实现无遗。
二、撰《雷希颜墓铭》为御史雷渊作传,以见金源晚期中、下层社会政治史。渊字希颜,《金史》卷110有传。《墓铭》首称:
南渡(案:指贞祐二年金迁都)以来,天下称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
而高廷玉
卒以高材,为(河南府)尹所忌,瘐死洛阳狱中。
李纯甫则以勘破朝政,
知大事已去,无复仕进意,荡然一放于酒,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至雷渊,则专纪其有关外战、内政两宗大事:
希颜正大初拜监察御史。时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济艰难者为甚力。希颜以为天子富于春秋,有能致之资,乃拜章言五事……
拜章内容涉及关乎当前生死大局之“倒回谷战役”,主张乘胜直逐,聚歼蒙军主力,以解长久之危,
引援深切,灼然易见。而主兵者沮之,策为不行。后京兆、凤翔报北兵狼狈而西,马多不暇入衔。数日后知无追兵,乃聚而攻凤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纵敌,为当国者之恨。
于此可见金廷晚期决策者对外不思长远,唯图苟安一时;内政则吏治败坏,奸蠹横行。雷渊身居监察,肃清吏治,自为本职:
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赃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传“雷御史至”,豪猾望风遁去。蔡下一兵与权贵有连,脱役遁田间,时以药毒杀民家马牛,而以小直胁取之。希颜捕得,数以前后罪,立杖杀之。老幼聚观,万口称快,马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16)
罪案但凡牵涉权贵,法即难行,执法者自身且安危难保,下民更当如何。《金史》雷渊本传特简取以上二事写成传文主体。金朝外战、内政皆如此,可知国政已无可为。
三、撰《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为陈和尚作传。完颜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以小字行。《金史》卷123列“忠义传”,传文几全采《良佐碑》。碑文首以金末朝臣言:
中国(案:指金国)数百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
续纪陈和尚以武夫而喜爱读书,骁勇善战,临难不苟三事,以存金朝英杰之正气。碑文记其师从金末名士王渥读书云:
镇南(案:指陈和尚)得师友之。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仲泽(案:指王渥)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识者知其非吴下阿蒙矣。
后偶以惩戒过犯军官系狱,哀宗予以特赦并加勉励。陈和尚因誓死报国:
镇南泣且拜,悲动左右,竟不得以一言为之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再迁忠孝军提控。
(正大)五年(1228),北兵犯大昌原,势甚张。平章芮国公问谁可为前锋者,镇南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胜兵八千,乘胜逐北,营帐悉迁而西。三军之士为之振奋思战,有必前之勇。盖用兵以来二十年,始有此胜。奏功第一,手诏褒喻,一日名动天下。……所过州邑,常例所给之外,一毫不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
数次战役对金朝安危皆至为关键,其中以倒回谷之战尤为惨烈悲壮,可参上文论雷渊及于此事部分。然而金源覆灭之命运毕竟已大局注定,非一人所能挽回。“三峰山战役”,陈和尚失利,退守钧州。
(天兴)元年(1232),钧州陷,北军下城,即纵兵以防巷战者。镇南避隐处。杀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国大将,欲见合按白事。”北兵以数骑夹之,诣牙帐前。问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大昌原之胜亦我,卫州之胜亦我,倒回谷之胜亦我。死于乱军,则人将以我为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胫,不为屈。胫折,画地大数,语恶不可闻。豁口吻至两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北人义之,有以马湩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17)
遗山撰碑时已值亡国之顷,若不著此碑,往事湮没,后人将无以知前朝尚有此等人物在。
或谓后世修《金史·文艺传》,实多出遗山《中州集》所编之作者小传,言自不虚;但第一,就以上所举而论,遗山为金人撰作碑序之范围已远较文艺传为广,其本意亦不但在纪文艺之事;第二,《文艺传》即或采自《中州集》之小传,实早多有遗山之碑铭记序等本文在先,《中州集》之小传,特多为本文之缩略尔。
至于遗山于金源亡国前后,亲撰大量故国诗,或记录灾难时变,或抒发内心情感,集内多有,此仅举卷12《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为例,它不尽说: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乱似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18)
三诗径以白描记叙哀宗天兴二年(1233)金都汴梁陷落之惨象。至今冯沅君、林庚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中国历代诗歌选》仍选收此诗,以作为一代以诗存史之著例。
编纂《中州集》,以诗存史
自修史书、亲撰诗文固为修史良策,但保存故人文献,令文献“说话”,亦为修史要略。遗山深虑故老遗作经兵燹战乱散佚亡失,起念编辑《中州集》甚早。原书序云:
岁壬辰(1232年),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秋,不暇及也。明年滞留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案:即商衡)之子孟卿(案:即商挺)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19)
据文称,其尚在聊城拘管中即筹备编书,可见内心之急迫。恰金亡臣商衡之子商挺携其父之旧本来访,因合二为一,遂成《中州集》。其体例,金帝以下设“诸相”、“状元”、“异人”、“隐德”、“知己”、“南冠”、“附见”等类,共收前金249位作者之诗,各于名下结撰小序,存其行实,其名类之全意在函盖金源一代之人文。今举三例。
卷五收完颜璹之诗63首。璹,上文已论。《中州集》之完颜璹小传即《如庵诗文序》之节文。其《秋郊雨中》七言绝:
羸骖破盖雨淋浪,一抹烟林覆野塘。不著沙禽闲点缀,只横秋浦更凄凉。(20)
末世王孙之颓唐凄艾灼然可见,又诗笔渲染疏澹,景中寓情,隐约显出诗人之绘画情味。同卷《寓迹》七言绝则云:
寓迹山中记昔年,西溪卜筑欲终焉。飘零何在五株柳,离乱难归二顷田。漫叟未能忘野寺,道人犹解识林泉。吾乡已宅无何有,一笑醯鸡尽瓮天。(21)
又同卷《梁园》七言绝:
一十八里汴堤柳,三十六桥梁苑花。纵使风光都似旧,北人见了也思家!(22)
又同卷《过胥相墓》七言绝云:
亭亭华表暎朱门,始见征西宰相尊。下马读碑人不识,夷山高处望中原。(23)
后三作昭显完颜璹危居南京汴梁之末世心理与急切退归北方女真故土、重过庶民生活之愿望,《梁园》一作尤露身居汴京,心系北国之幽思。《金史》本传记:“天兴初,璹已卧疾,论及时事,叹曰:‘兵势如此,止可以降。全完颜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真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24)两文正可互证。《寓迹》则藉陶渊明乱世归隐典故,表达一种欲追仿而不可得之颓丧。末联似隐含国家将亡,朝士尚争讧不已之怨艾。《过胥相墓》盖深悲名臣已矣,后继无人,徒遗一风雨飘零之国家,栖居无数如完颜璹一般欲北归而不得之民人。案“胥相”,指胥鼎,《金史》卷108有传。鼎为金源晚期名臣,卫绍王永济至宁、宣宗兴定间两拜平章政事,故云“相”。诗内所谓“征西”,当指胥鼎官汾阳军节度使,知平阳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宣抚使等职时,御退蒙军南侵、安集黎庶百姓等善政。鼎晚年连章请老而不获允,终殁于王事。
卷三收赵秉文诗63首。赵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贞祐初尝建言迁都、导(黄)河、封建三事以图存,宣宗兴定中官礼部尚书,为金后期文坛盟主,与遗山有师弟之谊,《金史》卷110有传。诗前小传及《金史》本传皆采遗山《闲闲公墓铭》为多,可参《元好问全集》卷17。《小传》谓周臣“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其《谒北岳》五言长律云:
四大神仪一,群山太茂尊。奠方荒冀宅,视礼配天孙。西送虞渊暮,东瞻碣石暾。宝符临代郡,铁瓮扼并门。控赵襟形壮,包燕气象浑。九河探禹迹,万里叫虞魂。在昔登封始,前驱羽卫繁。千官骈部曲,万骑隘山樊。卜地恒阳曲,移祠泰始元。(旧注:晋移祠曲阳)荒碑刓岁月,飞石宏乾坤。帝秩加黄屋,宫居象紫垣。云楣朽芝瑞,雨砌裂槐根。天业恢弘大,山灵翊卫屯。巫闾归帝制,长白发金源。九庙龙盘接,三邦蛇势吞。云烟浮近甸,日月绕中原。欵谒天香重,封题御署存。银鏐诸产富,电雨万灵奔。神听羞回德,天聪纳正言。负时身九死,去国泪双痕。日近趋天阙,生还托圣恩。许身徒稷契,无术补羲轩。帝箓长桑洞,仙岩张果村。卜居如可近,重整北山辕。(25)
全诗气象浑厚,自谒拜北岳,忆及金源肇建之初,幅员阔大,至于南渡,国势日蹙,内中焦灼惨凄,“负时身九死,去国泪双痕”,“许身徒稷契,无术补羲轩”,衷心盼一日“卜居如可近,重整北山辕”,能尽复失地,回归北国。自此及上文引完颜璹、下文将引雷希颜诸作观之,金朝晚期朝士深明南宋既不能速灭,北方复频遭侵迫,自身日益隔绝于发祥崛起之白山黑水热土,无不忧心忡忡。
卷六收雷渊诗31首。渊小传及《金史》本传均采自《雷希颜墓志铭》,云渊“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然猝亦不能变也。”(26)可见渊正直、略过刚莽之性格。其《河山形胜图》七言绝:
高峰巨堑与天连,中国关防表里全。北岸尘气重回首,不如图上看风烟。(27)
内中“北岸尘气”抑隐指蒙古铁骑之将南下欤?又《刘御史云卿挽词二首》(之二):
少同里闬早知音,投分交情两旧今。乡校联裾春诵学,上庠连榻夜论心。南山松桂愁霜殒,北地乾坤恨日侵。不得生刍躬一奠,西风吹泪满衣襟。(28)
又同卷《赠陈司谏正叔》七言律:
洗兵有志挽天河,补衮刚留谏诤坡。赋出石肠还婉丽,政成铁面却中和。寒侵桃李凄无色,雪压池塘惨不波。急手尊前谋一醉,六街尘土涴人多。(29)
前二首系心蒙、金战事,“北岸尘气重回首,不如图上看风烟”,“南山松桂愁霜殒,北地乾坤恨日侵”,急切忧虑之情跃然纸上。后首既赞友人“赋出石肠还婉丽,政成铁面却中和”之从政心态,叹许为己身所不能,又借“寒侵桃李凄无色,雪压池塘惨不波”,“六街尘土涴人多”交代时、地之辞暗示时局之险恶。三作皆关国事,既饱含深情,又悲凉慷慨,信见希颜个性。
《四库提要》评《中州集》云:“是集录金源一代之诗,……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如斯之类,尤足存一代之公论。……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30)文内称选作“颇极精审”云云,与上文所引同书之《遗山集》提要“去取尚不甚精”语有抵牾。相信是非自有《中州集》读者公断。暌隔五百余年,清人洞察遗山编纂之寓意明犹如此,遗山地下为无遗憾矣。
遗山撰集前朝遗作以存文献史料,此种修史方法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深远之影响。元代著名史学家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元史》卷181有传)为南宋故相虞允文五世孙,尝领总裁衔,修成元朝《经世大典》。伯生极重遗山修史体例。《元史》卷181本传云:
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道)、淳(熙)风烈。尝以江左先贤(案:指南宋故老)甚众,其人皆未易知,其学皆未易言,后生晚进知者鲜矣,欲取太原元好问《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31)
案:如所周知,虞伯生五世祖允文为南宋丞相,曾祖刚简、外祖父杨文仲、父汲均仕宋。伯生身为元清贵官绅,晚年退致,为一官方学者。其尝于文宗朝与平章政事赵世延同领总裁,仿唐、宋两代《会要》体例,采择本朝典故,修纂《经世大典》。后世延去,伯生独任其事,终底于成。又本传称伯生文兼两宋大家风,“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32);叙事议论动中法度,故其为人所撰碑铭行状,后世史官多采入《元史》列传。伯生终其一生又系念南宋故国不置。其为时人蒋易所编《国朝风雅》作《国朝风雅序》一文,内中论及遗山云:
故金进士太原元好问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盖伤夫百十年间中州板荡,人物凋谢,文章不概见于世。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闵其心焉。(33)
伯生所序书为收有元文章之作,起刘静修,讫许衡。其编书要旨异于遗山,故《序》文之政治意义亦有所不同,但其云遗山编《中州集》是欲“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则知遗山深矣。
国亡史存,“借诗以存史”之修史思想至明、清之际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更趋清晰。牧斋为著名史学家,以南明礼部尚书降清,后生怨悔,转而参与东南反清复明运动,清廷恶之,因编入《清史列传·贰臣传》。钱氏于明天启间尝蒐编当朝诗集,未能终事。清顺至初复起手,历三年编讫,作《列朝诗集序》,申说作者之意云:
毛子子晋刻《列朝诗集》成,予抚之,忾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予曰:“有叹乎!予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之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板荡,载籍放失,濒死讼系,复有此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蒐讨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庚寅阳月,融风为灾,插架盈箱,荡为煨烬。此集先付杀青,幸免于秦火汉灰之余。於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积劫。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哲人其萎,流风迢然。惜孟阳之草创斯集,而不能丹铅甲乙,奋笔以溃于成也。翟泉鹅出,天津鹃啼。《海录》、《谷音》,咎征先告。恨余之不前死,从孟阳于九京,而猥以残魂余气,应野史亭之遗谶也。哭泣之不可,叹于何有?故曰:予之叹,叹孟阳也。”
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疆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时强盛之时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明朝,发挥才调,余窃有志焉。……”(34)
案:文内所谓“庚寅阳月,融风为灾,插架盈箱,荡为煨烬”,盖指清顺治四年(1650)钱氏藏书之所绛云楼失火,为近世典籍之一大厄。所幸《列朝诗集》已付剞劂,与祝融错面,否则今人亦无缘识见该书矣。然原书仍流布甚尠。牧斋族裔陆灿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辑各家小传别为一书,名《列朝诗集小传》,更为稀见,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新印本。该书出版说明云:
天启初年,他(案:指牧斋)四十来岁时,就有志于效仿元好问编《中州集》,录有金一代之诗并附列诗家小传的做法,一度着手编次明代的《列朝诗集》,但不久因忙于宦事而将此事耽搁了。二十余年以后,清兵南下,明亡。……从(清)顺至三年起,他又续撰《列朝诗集》,历三年而终于完成。
这部诗集,选录了有明一代二百余年间约两千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写了扼要的小传。其中有些人,照钱氏所说,即使在当时也已“身名俱沉”,很少人知道了,所以他选录了这些作品,“间以借诗以存其人者,姑不深论其工拙”,要“使后之观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独论诗而已也”。《列朝诗集》既保留了有明一代文献,他所写的各家诗集小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且钱氏本人也是著名诗家,所以在这些诗人小传中也时常表露出他对诗作的深刻理解。……这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35)
是书成于清初,竟囊括朱明一朝两千余位诗人之作,规模远过遗山《中州集》,可谓创发性之继承。而人阅此书,不啻眼见一部感性之明朝政治史、文化史,其文献价值如何,不言自明。
编著史书,留存一代国史
留存一代历史遗迹,莫若直接编撰史书为宜。遗山晚年下功最著者,为史书《壬辰杂编》。就书名即可知为金亡国后作。《金史》本传言遗山“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36)约即指《壬辰杂编》而言。遗山盖担心:
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
引文出《元好问全集》卷20《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作于“癸卯”,即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蒙古灭金后十年。墓主历仕金源政、军要职,熟悉金末掌故。金亡不仕,“柴车北归,结庐洹水之上,不以世务萦怀,左右图书,以乱思遣老而已。”(37)此类先朝遗民为元遗山修故国历史之主要采问对象;及故老之身修史,则为遗山之重要史学理念。
观《金史》本传言,知《壬辰杂编》为金源晚期朝政要事、君臣言论之追录,史料价值极大,惜其书佚失甚早,《四库提要》已无著录,今人不得见之,以反证《金史》之正、谬为憾。
元遗山及己身修史,及亡国故老健在修史,以史书,己身及他人诗文,三重文字修史之史学观与史学方法为当时卓绝而后世罕有。清代大史学家赵翼《瓯北集》卷33《题元遗山集》诗称曰: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38)
诗作颔联下句系用楚共王典。案《说苑》卷十四:“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39)依鸥北诗,遗山正反孔子语意,必欲楚弓楚得,谓金源遗民国亡修史,金源亡国之民读之,俾不忘国本。赵瓯北之体察遗山可谓至深至当。陈寅恪先生更于七百年后作《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慨叹:
昔元裕之、危太仆、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40)
以为诸人人格之高尚、卑污,学识之博赡、谫陋不一,但其国亡修史,力存一代文献,皆功在后人。是从学术角度总结遗山等人修史之意义。
元遗山因时势胁迫,参与为叛将崔立撰功德碑;牧斋则变节,屈身降清,二人著有污点,皆为遁世之在野学者,与虞伯生遭际歧异。但三人各以特定之身地位份、特定之著述体例、特定之史学方法为各自之史学宗旨服务,“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此种治史态度与方法对于保存一代文献故实,使民族历史绵亘无阙,意义深远著明。
注释:
①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五,《遗山先生墓铭》,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元好问集》卷二十,《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第460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脱脱:《金史·元德明传》附本传,第274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2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赵翼:《瓯北诗话》,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金史》,第2743页。
⑦《元好问全集》,第757页。
⑧同上,第835页。
⑨《元好问全集》,第756~758页。
⑩《金史》,第1897~1902页。
(11)《元好问全集》,第474页。
(12)《陵川集》卷11,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112页。
(13)《金史》,第1900页。
(14)同上。
(15)《金史》,第2060页。
(16)《元好问全集》,第485~487页。
(17)《元好问全集》,第573~576页。
(18)《元好问全集》,第292页。
(19)《中州集》,卷前。
(20)《中州集》卷五,第65页B。
(21)同上,第70页A。
(22)同上,第71页B。
(23)同上,第72页。
(24)《金史》,第1905页。
(25)《中州集》卷三,第81页A。
(26)《金史》,第2435页。
(27)《中州集》卷六,第60页B。
(28)《中州集》卷六,第59页A。
(29)同上,第56页。
(3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706页。
(31)张廷相:《元史》,第4181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32)《元史》,第4179页。
(3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4)钱谦益:《有学集》,第678~6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新印本书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6)《金史》,第2743页。
(37)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38)《元好问全集》,第464页。
(39)《瓯北集》,第772页。
(40)刘向:《说苑》,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