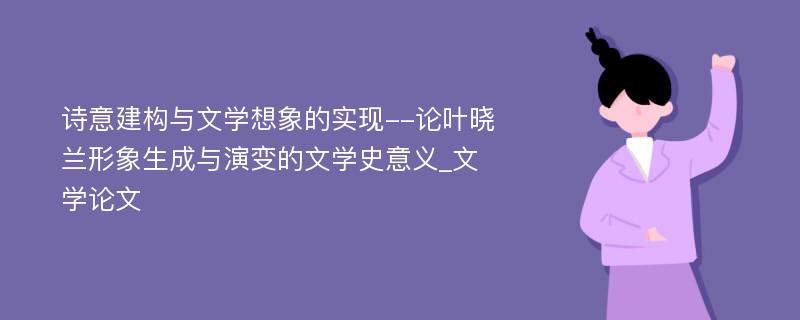
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意义论文,形象论文,文学论文,论叶小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清两代的文学史上,女性占据了文学想象的巨大份额。这不仅因为女性才能的特出,她们的美丽灵慧、超拔不群也给予发现者——男性审美观照的平台,赋子他们诸多寄托情思的机缘。由于男性文人的孜孜创造和乐此不疲,许多真实的、虚构的或二者兼具的女性形象因之进入文学史缤纷的人物画廊,并以才情及与之相生互动的人生传奇激发或者说建构起新的文学想象。苏州吴江叶小鸾(1616-1632)就是其中的一位。其父乃明天启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的叶绍袁(1589-1648),母亲则是出身吴江望族的名媛沈宜修(1590-1635)。叶小鸾幽居闺门17年,婚前五日遽然离世,其《返生香》集存世诗词文总数不过200余篇。但作为文学想象的重要载体和构成因子,她在晚明和清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度却成就了一道独具魅力的文学景观。
一 叶小鸾文学形象的生成
梳理关于叶小鸾一生之种种,发现很多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比如她的超常美丽、婚前夭亡,比如她清空的文学篇什、文学世家的出身,以及一门才媛的生活境遇等等。然仔细分析,这一切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地区并不足为奇。在当时,美丽灵慧且青春夭折的名媛并不少见,《午梦堂集》里就记载有苏州周挹芬等人;婚前几日病逝者如评点《牡丹亭》的三妇之一陈同,也名传一时;至于文学世家的出身、一门才媛的生活状态乃彼时江南一带文化生活的常态,似也不足以切入论题之肯綮。但是,当这一切作为重要构成因素交互作用、彼此激发甚至相互建构、集中于一人之身时,即不同寻常且足以传神了。真实的叶小鸾因之具有了文学想象的基本因子,并借助其父母的先进观念及相应的传播弘扬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由私人语境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晚明江南地区的一个美丽传奇。
作为叶氏的掌门人物,叶绍袁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不仅仅在于其“名父”的身份①。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② 这是其女性观最具时代意义和价值内涵的表白。他不遗余力地推举兼具才、德、色的妻子、女儿,积极鼓励家庭成员包括诸女的创作,“一时闺门之内,父兄妻子,母女姊妹,莫不握铅椠而怡风月,弃针管而事吟哦”③,以至“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④,在家族内部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这是《午梦堂集》形成及流播海内的前提,叶小鸾文学形象的生成因之拥有了最初的载体。据叶绍袁回忆,崇祯五年(1632)叶小鸾离世后,即“为检其遗香零玉,付之梓人”⑤,以免其作“湮没不传”,促其名字“早艳人间”⑥。经过精心编辑呈现出来的叶小鸾已开始显示逸出历史视域的趋向,例如她的美丽和个性因叶绍袁夫妇不遗余力地铺陈叙述,已涵容了文学想象的因子。沈宜修描写叶小鸾:“鬓发素额,修眉玉颊,丹唇皓齿,端鼻媚庸,明眸善睐,秀色可餐,无妖艳之态,无脂粉之气。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清。故名为丰丽,实是逸韵风生”,“真所谓笑笑生芳,步步移妍”⑦,生动可爱,细腻可感;叶绍袁对女儿的“绝世之姿”更为称赏:“倾国殊姿,仙乎独立,倍年灵慧,语亦生香”⑧、“房栊动处,玉女天来,衣带飘时,素娥月下”⑨。在他们的笔下,叶小鸾不仅容貌美,个性亦不同凡俗:“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⑩ 真可谓“才色并茂,德容兼备”(11)。如此修辞色彩浓郁的描写,动用了古典诗词关于女性最美丽的辞藻、最动人的夸张和最明艳的比喻,叶小鸾与现实人生的距离已被悄然拉开,具有了审美对象的意义;而德才色超常与其不幸结局构成的悲剧张力,则凸显了关于才女不幸与人生短暂的文学主题。
叶绍袁夫妇关于叶小鸾形象的建构是最初的,也是诗性的,这与其诗词创作的清空华艳、忧郁哀怨彼此同构,艺术地演绎了她“幼而奇慧”(12) 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叶小鸾卓异才情中透射出的清空气象,凝结为一道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魅惑。“梦里有山堪遁世,醒来无酒可浇愁”、“流光闲去厌繁华,何时骖鹤到仙家”、“三山碧水魂非远,半枕清风梦引长”(13) 等诗句,出自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之手,不免让人尘心震撼、浮想联翩;而“瑶台”、“瑶琴”、“瑶池”一类词语的习见迭出,也为叶绍袁所谓“清冷凄凉之况、超凡出尘之骨”(14)、“其仙风道骨,岂尘凡可以久留得”(15) 等话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蕉窗夜记》中,托名煮梦子的叶小鸾借两位绿衣女郎的歌吟,敷衍自己的“怀仙之志”,叶绍袁在文后记云:“种种仙踪,有不可尽述者。”这种不断出现的评点,引导着阅读过程中关于仙缘与早慧、才情与宿命关系的发现,与叶小鸾不拘一格的文采风流和清奇别致的词格相照应,最终的指向也是她那扑朔迷离的夭逝以及相关的文学想象。
叶绍袁是个钟情之人。崇祯四年(1631),他下定了“永不作长安想”(16) 的决心,一家唱和、其乐融融的美满也弥补了来自仕途的挫折感,以至曾有“生平佳景,斯年为最”(17) 的感慨。然而,接踵而来的家庭灾难乃至最后的国破家亡,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他笔下是大量的回忆悼亡之作,语言清丽婉转,叙事摇曳多姿,感情真挚缠绵。任何悲苦境遇中都不缺失的审美情怀,构成其传神文笔的有力根基,而这恰恰也是《午梦堂集》最令人醉心之处。在其所收叶家大大小小十余人的诗文中,无论稚嫩或成熟,每一篇什都情韵深挚,缠绵悱恻,脉脉动人,蕴含着真挚的感人力量,给人叶氏一门钟情的深刻印象。因死亡事件频发而催生出的大量悼亡之作,更给这种钟情以铺展敷衍的平台,也为叶小鸾进入文学想象提供了丰沛的情感源泉。《鹂吹集》所收沈宜修的悼女之作,多以“哭”字领起,“断肠”之词随处可见,悲怆心声和感伤情绪漫漶无涯;尤其是《夜梦亡女琼章》等作品,多借助对日常场景的细腻描写,彰显亲情的深挚醇厚,呈示了情真意切的亲切自然之美。叶绍袁的伤悼之情则同时体现在编辑《午梦堂集》时留下的那些情不自禁的评语中。如叶小鸾《庚午秋父在都门寄诗归同母暨两姊和韵》后,叶绍袁批曰:“尚欲宽慰父怀,其如一死,使父肝肠寸寸碎也。诗墨犹新,人安往哉?伤哉痛哉!”切切之悲哀,眷眷之深情,一腔慈父悲怀,令人扼腕欷歔。其评语中“伤”、“痛”、“泪”一类字眼尽多,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在他的意念里,并没有以个人悲欢进行宏大叙事的文学追求,却因私人场景的感性呈现演绎了个人命运的无常以及人类悲剧的永恒,契合了时代变动状态中个人对命运的难以把握和扑朔迷离的人生恐惧,进而促成了审美心理的共通性。这种来自午梦堂群体统一的人伦风貌和相似的气质追求,很容易激发审美感动的文学因子。
叶小鸾去世后,叶氏一门表现出空前的震惊和悲痛。从《午梦堂集》本身来看,她的父母、姐弟都有诗文悼亡,篇什近百,如沈自炳《返生香序》所云:“琼章之没,大小皆有诗文祭之,雅丽可观,殆其性然欤。”祭悼诗文皆出于家族中人在特定时间和背景下的主题创作,文学的增殖效应十分突出;以至后来叶绍袁又将名媛亲友及续作的悼念之什汇为《彤奁续些》,不仅“缠绵惋恻”、“惆怅低徊”(18) 之情得到了强化,叶小鸾的才女形象和成仙结局也被进一步凸显。如叶纨纨的《哭琼章妹》云:“辽阳化鹤何时返,仙路无凭总渺茫。”叶小纨的同题诗作则说:“思君才色真如许,一旦空随逝水流。”这些创作应合了叶氏一门“篇章赓和,……闺阁之内,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19) 的家庭酬唱印象,也标识了这一群体创作高峰的来临。而叶小鸾也在叶绍袁“诸儿女中,汝最挺出”(20) 的哀思和惋惜中脱颖而出,成为叶氏子女中最具实际影响力的人物。陈维崧在介绍叶绍袁三个女儿“俱有才调”时,特别指出“琼章尤英徹,如玉山之映人,诗词绝有思致”(21);陈去病则表示小鸾“尤明艳若仙”(22);现代文人周作人也言及“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23)。的确,“早死”是一种机缘,因为这一点,她被过早阅读,过多想象,与文学形象相关的诸元素也借助公众视野的种种中介因素陆续凸显出来。但阅读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不仅是一种审美的创造,首先来自文化上的体认。也就是说,叶小鸾文学形象的生成实际上反映了晚明文化重情写真的时代诉求,是当时文化生态下必然结出的文学之果。
晚明时期,伴随着心学的流行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女性及其生活与创作也浮出历史地表,并逐渐演变为男性话语的“中心”,选色征歌与选文编集在行为本质的相通之处,让许多文人借助这一“中心”获得美感和寄托。研读闺秀诗词、推举女性才情作为一种个性标志,构成士人生活的特殊景观。许多文人有意网罗女性作品成集,通过红颜知己意识的张扬,进行一种文化身份的表达。如清初邹漪“仆本恨人,癖耽奁制”(24) 的表白、王士禄“夙有彤管之嗜”(25)的自述等,均属刻意追求之语。美人易老、佳人早夭,本来容易契合男性文人怀才不遇的感伤心理,何况女性的怀情不遇与男性的怀才不遇在价值结构与审美意义上存有深层认同之处;以才子不遇呼应红颜薄命的忧伤感慨,以“才与命妨”的不幸抒发边缘文人的怨愤不平,既是香草美人文学传统的历史延展,也容易达成文人借助这种文化象征表达对儒家文化价值中心的疏离倾向。如是,叶小鸾的美丽、才情、早逝以及仙化,不仅容易激发女性的自省和人生反思,也打开了男性抒情的文化空间,曹学佺《午梦堂集序》即有“文人多厄,不独须眉,彤管玉台,俱所难免”的感怀;而名媛身份、清空诗笔以及婚前夭逝,又含纳了才情、身份、境遇及人生选择等新的文学元素,很容易激发当下文化语境中关于个体价值、生命体验及情感遇合的审美想象。特别是叶小鸾文字中流动的灵动而忧郁的感伤、对生命无常的失落,总能带给文人难以言说的哀怨和无奈;其人生故事里发散出的那种别致的“哀感顽艳”,隐含的是生离死别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无常,也足以照应挫折感丰盈而边缘意识明确的文人心理,唤起关于自我命运的深长忧思。叶小鸾因之获得文人的格外青睐,成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传奇的价值。
二 金圣叹降乩活动与叶小鸾形象
对于叶小鸾形象的塑造和播扬,当时著名的泐庵大师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泐大师其人,前辈学者如孟森《金圣叹考》、陈登原《金圣叹传》已曾提及;陆林教授有关金圣叹史实研究之文,则通过翔实考证首次将之与吴江叶家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思考有关降乩言行与叶小鸾形象关系提供了史实前提。应该说,如果没有金圣叹的扶乩活动以及叶绍袁的文学记录,叶小鸾的形象肯定会呈现为另一种面貌。
扶乩占卜活动本是市井百姓预测凶吉、禳祸辟邪的重要形式,明清时期则同时成为文人求取试题、预算功名的日常活动(26);尤其在江南地区,乩坛盛设,法事常新,儒释道杂糅其中,敷衍着关于世俗与神圣的种种话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大概从天启七年(1627)到崇祯十一年(1638)间(27),年轻的金圣叹以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538—597)弟子化身的名义,在吴中一带扶箕降坛、广行法事,法名智朗,人称“泐子”,“泐公”、“泐师”、“泐大师”等。金圣叹的扶乩活动具有相当影响,郑敷教即有“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28) 的评论;而叶绍袁与泐师交往的时间也在其道大显、声名鼎盛的崇祯八九年间,《续窈闻》中叶绍袁屡请不至的焦虑、“屏气伫候”的虔诚以及期盼“不朽”(29) 的渴望等,即是这一判断的依据。
事实上,叶小鸾去世后,笃信佛理的叶氏夫妇虽然知道“杳杳泉台,无期再见”,依旧思念之情难抑,或自“拟楚骚而招之”(30),或通过乩师招魂结缘(31)。尤其是崇祯八年叶家接二连三发生的死亡事件:二月,18岁的次子世偁因科考失利抑郁而死;三月,年迈的母亲冯太宜人伤爱孙之殁而去世;四月,5岁的幼子世儴因病夭折;九月,连遭打击的妻子沈宜修亦呕血而逝,令悲哀郁积、无限迷惘的叶绍袁更沉溺于宿命的解释和虚妄的慰藉,求神降乩活动也达到了高峰。在叶绍袁的记载中,幼子世儴患惊风痫疾、沈宜修患咳血之症等,均不止一次地得到泐大师的诊断和指点,而他的睿智评断对叶绍袁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以至在亡国失家之际构成他反思人生的种种回忆(32)。崇祯九年六月初十日,泐师在叶家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扶乩活动。彼时,泐师辨析了叶家的诸多因果,且将已仙化为“月府侍书女”的叶小鸾“招魂来归”,与之联句吟诗、审戒忏悔。其中,泐师与所谓“叶小鸾”进行的一段对话颇为特出:
女云:“愿从大师授记,今不往仙府去矣。”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汝仙子曾犯杀否?”女对云:“曾犯。”师问:“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师又审四口恶业,问:“曾妄言否?”女云:“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曾绮语否?”女云:“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曾两舌否?”女云:“曾 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女云:“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师又审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女云:“曾犯。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鸾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赞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然则子固止一绮语罪耳。”
这段对话经由叶绍袁《续窈闻》的记载而广泛流播,不仅叶小鸾“雾骨烟姿,定人留而不住”(33) 的仙人形象获得了确立,且构成了后来叶小鸾形象最为生动传神的精神内核。晚明乃至有清一代,涉及叶小鸾的各类著述难计其数,人们在惋惜其青春早逝、待嫁而亡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赞美叶小鸾的灵慧、敏捷、才情,所依凭的多是这段精彩绝伦的对答。钱谦益不仅赞赏“叶小鸾”的“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34),且将其呈泐师之诗编入影响深远的《列朝诗集》,所选叶小鸾14首诗中,后二首《仙坛奉呈泐师》、《将授戒再呈泐师》即来自《续窈闻》。实际上,这两首诗不仅于作品集《返生香》中未见,其著作权也不属于已离世三载的叶小鸾,而应归属“卟所冯者”金圣叹。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借助这次天才的降乩,吴江才女叶小鸾由一位真实人物升华为富有文学想象意义的新形象。其灵慧多才、秀丽明艳、机智敏捷、孤高自许等,都在新的载体形式上获得了呈现;尤其是,潜隐于叶小鸾内在世界的多愁善感和弃世求仙倾向,经泐师的强化,生发出具体可感的形象特质和传奇因素,激发了有关离经叛道的审美想象,叶小鸾形象因之具有了丰富的形象结构和传神的艺术魅力。
那么,金圣叹是怎样完成这一艺术蜕变的呢?以叶绍袁《续窈闻》记载而言,扶乩过程中的心理测算和美妙乩文无疑最具实践意义。首先,作为扶乩者,对亡灵的前生来世进行可信的描述最为重要,洞微烛隐的判断能力、细致敏锐的观察能力乃至循循入微的诱导能力都在这一过程中集中呈现,此乃成功之关节所在。金圣叹无疑表现了出色的才能。长期的世俗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民众乐生恶死心理倾向的把握,使他很容易了解叶绍袁夫妇本来就具有的飞天遐想,叶小鸾以一女贞之身于婚前夭亡的题材也非常符合以佛法行冥事的扶乩主题。进入叶家后,他率先阅读了悼念集《彤奁续些》,与叶绍袁等的对话也帮助他进一步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动态,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观察了扶乩活动的现场(这一切很容易在《续窈闯》的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之后才开始进行阐释、分析、判断,最后达成了论说准确、切中关键、为人信服的效果。其次是合适的乩文。一般而言,扶乩咒语具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特点,明清时期则有利用乩文炫示才情、展演学问的倾向;为便于与众多士人酬唱,乩仙也需有即兴赋诗为文的才能,流传至今的乩文多有文人逞才使气之作。金圣叹亦不例外。如同一贯追求不同流俗、卓而不群一样,他设计的乩文也力求摒弃依傍、“自铸伟辞”,体现出超越凡俗的神光霞彩。如他即兴为《彤奁续些》所作题词,即博得叶绍袁“精言丽彩,挥洒错落,笔不停手,应接靡暇。鸿文景烁,灵篇晖耀,真上超沈、谢,下掩庾、徐”(35) 的由衷叹赏。清代王应奎论及金圣叹评点“稗官词曲,手眼独出”时,联想到他“自为卟所冯,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36),从另一面证实了扶乩一类的“神助”活动之于其才华的激发作用。其作为乩仙与叶小鸾亡灵的一连串问答,虽有预先构思设计的因素,即兴创作的成分亦占很大的份额,而这对于才华横溢、口才利捷的金圣叹而言,并非难事。因此,“叶小鸾”的答语不仅约略符合其身份、个性,在意象的构成以及语言风格的精致华美方面亦颇得叶小鸾文笔之神韵和风采,这对于成功地建构一位才华横溢、超尘绝俗的青春少女至关重要。
泐师审戒,“叶小鸾”答戒,基本内容限定在佛家“身”、“口”、“意”三恶业范围内,体现了规定的内容和必要的顺序,也严格遵守了扶乩活动之必要程式,可谓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但因答语出于扶乩者金圣叹基于特定目的的精心设计,所表达的“作者”(金圣叹)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即彰显叶小鸾的才情,所谓“天上天下第一奇才,锦心绣口,铁面剑眉,佛法中未易多见”(37) 也。故全部答语采用七言,选用骈语,多施对偶,造语华丽,意象鲜明,“超郎温润,如其平日所吟”(38),与其诗词作品提供的印象互相映照,凸显了叶小鸾的灵动、机敏、聪慧、才情。故对话一止,金圣叹先致赞语:“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然则子固止一绮语罪耳。”这一引导显然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意图。佛家之“绮语”多指虚妄浮华之言,文笔绚烂归属此罪业。泐大师表面以所谓“绮语罪”让“叶小鸾”忏悔,实际则既迎合了叶绍袁夫妇关于爱女文采英发的先验想象,又以合适的机缘展示了清新流丽的“绮语”,塑造了叶小鸾天真烂漫的神采风流,以至连对降乩行为颇多疑惑的周亮工也不得不表示:“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39)可见“缛丽”之句产生的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一种叙述方式,对话在表现人物的情感活动和心理状态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故在论述金圣叹扶乩活动的戏剧性时,陆林教授对这段答语中“蕴涵的浓郁的戏剧张力”颇为首肯,认为“各组骈语均包含着很强的动作性、表演性,似乎就是专为舞台演出而撰写”(40)。不仅如此,因金圣叹敏锐捕捉到了名媛闺秀的生活特点和心理状态,并借助其日常行为的典型特征进行细腻的表达,拈花、扑蝶、听曲、照镜、读书等都是世家闺中活动之必然,洋溢着清丽、优雅的才女情趣,所以对话式答语虽属发生在时间结构中的历史性叙述,空间意义亦不能忽视。而通过意象的视觉转换所构成的一幅幅美妙的画面,在展示了空间环境的同时,又以景寓人、因景写情,凸现了叶小鸾不同凡俗的美丽和纯真。特别是,为了强调这种人生之常和人性之美,故意采用正话反说的方式,表面是在表现“叶小鸾”的忏悔,实际则是在极力铺写少女对青春、自然和美的眷恋与渴望。这与空间画面引发的由美人和自然花鸟构成的审美体验形成照应,不仅强化了对叶小鸾才情、个性的联想,还伸展到她的日常生活中,激发了关于少女文学形象的深层思考。例如,透过这位花季少女青春的觉醒及对自由的向往,很容易联想到那个为情而生、因情而死的杜丽娘。叶小鸾对青春、自然和美的眷恋追求,以及哀怨无奈的处境,与杜丽娘何其相似乃尔!杜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伤和期冀,又反向昭示了叶小鸾丰盈的精神世界与严酷的现实存在的抵牾。对比叶小鸾阅读《西厢记》、《牡丹亭》后之于“并蒂花枝”、“玉容”、“芳年”等表现出的艺术敏感,所谓“真真有意何人省,毕竟来时花鸟嗔”(41),与金圣叹关于自由、个性和女性情怀的优美阐释如此吻合,这是对一切戕害生命的清规戒律的指责和控诉!叶小鸾形象因之被灌注了新鲜的血脉和灵魂,内在世界更加丰满而可爱,充盈着一种离经叛道的生命律动和眷恋俗世人生的审美情怀。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金圣叹就是一位离经叛道之人。他天性疏宕,高标自许,喜标新立异,厌繁文缛节,生前之悲欢及死后之毁誉均链接着这一词汇。即如扶乩降神这一正统文士眼中的离经叛道行为,金圣叹以十多年时间从事之,还出于“耀于世”的目的请钱谦益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借其文坛领袖的地位进行张目辩解和佛理阐说。有人说:“扶鸾降仙,道家戒之,决不可为,惹魔也,金若采全坏于此。”(42) 实际上,就文化价值而言,不是“扶鸾降仙”活动注定了金圣叹的厄运,而是这种活动因金圣叹而具有了崭新的视界和意义。如在叶绍袁家的扶乩活动,因乩文的缛丽色彩、正话反说的形式,与所谓女性身份彼此自然而有力的结合,不仅突出了叶小鸾的真情、美丽、个性和意趣,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有效的文化表达及与文化权力的对抗,峭拔而凌厉地表达了明清时代文人崇“奇”尚“异”的审美追求。而“叶小鸾”“矢口而答”表现出来的潇洒风致,实际上也是金圣叹自身离经叛道型名士文化人格的反映。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打动周亮工等一代代文人学士的浪漫文心,何止是“绮语”而已!
经由“绮语”塑造而成的叶小鸾形象,与叶绍袁夫妇的诸多记述在逻辑指向上保持了一致,但以“假扮”之叶小鸾对应生活中的叶小鸾,必因与真实的距离而产生张力,促成和扩展这一形象的想象空间,以至真实的叶小鸾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遮蔽,金圣叹建构的叶小鸾反而具有了历史的真实性。清人多有“松陵才女叶小鸾奉以为师”(43) 之语,认为叶小鸾就是泐大师的弟子;王韬《遁窟谰言》卷一《韵卿》也提到她“死后皈依释氏,与衲子谈经,以诗句参禅,甚见慧心”。在文坛名宿袁枚的笔下,叶小鸾的籍贯、经历讹误更多,那些朗朗上口的清词丽句也不免走样:
小鸾,粤人,笄年入道,受戒于月朗大师。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陈平生过恶,方许忏悔。师问:“犯淫否?”曰:“征歌爱唱《求凰曲》,展画羞看《出浴图》。”“犯口过否?”曰:“生怕泥污嗤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犯杀否?”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挂轻纨坏蝶衣。”(44)
这一记述,“叶小鸾”的答语与泐师审戒的顺序已不一致,文辞亦有所改易,所谓“征歌爱唱《求凰曲》,展画羞看《出浴图》”,与《续窈闻》中“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之句已有境界、神韵之殊,这从另一角度昭示了离经叛道取向所导致的理解极致。总之,口才捷利的金圣叹,当他视评点为毕生事业时,万没想到所谓的扶乩作品也能以“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45),给叶小鸾形象的塑造带来无限张力和空间。叶小鸾的形象因为金圣叹的扶乩活动而得到进一步显扬,变得清晰、丰满并更富有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叶小鸾形象的建构和扩展方面,作为“泐大师”的金圣叹扶乩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 叶小鸾的文学影响及文学史意义
叶绍袁夫妇的努力以及金圣叹的扶乩活动促进了叶小鸾故事的传播,这种创造性活动所带来的文学影响和文化增殖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在晚明尤其是清人的日常经验中,时常出现关于叶小鸾的话语,这构成了诸多体类文学想象的来源。人们往往将那些夙根灵慧、时有出尘之思的女性比作叶小鸾,如陈维崧指称吴扣扣即叶小鸾一类人物,并感叹叶与冯小青一样“郁郁以死,兰摧玉折,无乃甚乎”(46);叶观国《序〈薇阁偶存诗草〉毕复题长律一首》有“生天有籍宜忉利,住世无多似小鸾”(47),也情不自禁地将王采薇及其作品比附叶小鸾及其创作;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一《蓟素秋》谈及吴江才女蓟素秋的诗词集,“见者无不称妙,曰:‘诗词清丽,可为《返生香》之继声,而步叶小鸾后尘矣。’”(48) 至于有关叶小鸾及其诗词创作的篇什,更是不胜枚举。明清乃至近现代,许多著名文人如尤侗、龚自珍、柳亚子等写过与之相关的诗词作品,寄托难以言说的情思遐想。其中浸润的关于人生无常、历史变迁的深刻思考,灌注了男性知音者惺惺相惜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的灵感来源,还得自叶小鸾有关传记中提取到的一些文人化表征,如闺房的书房化布置、联吟赋诗的生活方式、“欲博尽今古”(49) 的文人理想,以及《返生香》中那缥缈无痕的“山隐”渴望。这一切很容易跨越地域和时代,与边缘文人关于朝野去留、身份变迁的价值思考发生共鸣,缓解或慰藉了他们确证自我的焦虑心理。也就是说,经过男性文人的艺术想象,叶小鸾形象富有性别意义的文人化特征获得了深具时代意义的延展和丰富。
(一)在叶小鸾所促成的文学想象中,《红楼梦》给今人最深的印象。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联吟赋诗,其中“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之句,多以为取自《续窈闻》中的“戏捐粉盒葬花魂”句;第七十八回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其“弄玉吹笙,寒簧击敔”句中的“寒簧”一词,也有学者指认与叶小鸾故事相关,进而论及到林黛玉与叶小鸾、《红楼梦》与《午梦堂集》存在某种必然的文学接受关系。且不说早在曹雪芹之前,苏州才子尤侗已于传奇《钧天乐》中以“寒簧”为女主人公命名,明确喻指叶小鸾,不能完全排除尤侗作品作为接受中介的可能;至于叶小鸾之于林黛玉的影响,如著名的《葬花辞》与叶小鸾的《莲花瓣》诗表达了似曾相识的情绪与境界等,虽不是空穴来风,但与尤侗《驻云飞·十空曲》被指认可能影响了《好了歌》一样,究竟不能作为可以落实的证据。实际上,阅读面广且杂学旁收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显然依托了广泛的自取,这也是促成其主题多义性进而导致实证研究总是别开宗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叶小鸾一样的才女夭折故事如何激发了曹雪芹关于青春女性的话题,让他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时融入了相关的审美感动,是今天的研究者难以通过精确的细节比对来加以证明的。曹雪芹的时代,《午梦堂集》的各种版本繁多,他没有任何拒绝叶小鸾的理由,何况当时的苏州是女性文化的集结地,叶氏一门的女性唱和足以提供闺中“历历有人”的典型个案呢。
但是,由“花魂”和“寒簧”的著作权均应归属金圣叹而言,进入《红楼梦》的叶小鸾已然是经过历史展开和文学想象的艺术原型了。其气质风神与《红楼梦》中那个“世外仙姝”林黛玉多有同构应属必然,多愁善感、灵慧秀丽、才华出众、孤高自许,的确为林黛玉所禀有,未婚病逝以及神奇的生、仙去的死,也都为同是苏州人的林黛玉所吸纳,但林黛玉式的体弱多病、以还泪传说为神话依托的宝黛恋情却并非叶小鸾的遗传,特别是叶小鸾身上的仙隐梦想,林黛玉非但不具备,且其指向更多的是关乎日常人生的种种诉求。也就是说,在充分展扬清标脱俗之美的同时,林黛玉形象还弥漫着浓重的世俗烟火气。因此,叶小鸾形象的艺术影响之于《红楼梦》而言,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她不能被指认为仅仅是林黛玉的前身,她更多地转换为以林黛玉为代表的一大群青春女性。她将才华和个性遗传给《红楼梦》中的年轻女性群体,又在曹雪芹独特而深邃的艺术观照下发生了深幽别样的拓展。她们无比寻常,“小才微善”、“或情或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们又都是“异样女子”,表现出男性所不及的清纯、超拔和识见。《红楼梦》不断强调的一句话是:“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实际上,这不仅来自对叶小鸾的体认,主要是对晚明以来一种文化共识的艺术总结。如时人众口一词以男性为参照表述的对女性才华的极度赞美:“天地清淑之气,金茎玉露,萃为闺房”(50);“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51)“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52);“乾坤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53),等等。换句话说,林黛玉等大观园女孩的离经叛道因为叶小鸾的精神映照而具有了源头活水,叶小鸾对生命无常的忧郁感伤则借助林黛玉的闲愁哀怨开启了一代文豪的精神端绪,成为曹雪芹演绎“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艺术源泉。一句话,作为女性文学繁荣时期的杰出代表,“叶小鸾”经过曹雪芹的再创造赢得了凤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在新的形象载体中获得了艺术丰富和审美阐扬,并以杰出的形象塑造表达了浪漫而感伤的时代诉求。尽管此“叶小鸾”与叶绍袁、金圣叹建构和扩展的叶小鸾距离更加遥远,却成就了超越其先天内涵和局限的女性的共名。这一形象在逻辑和事实上的归宿,正是其作为丰富的文学共同体在审美合目的性上的必然体现。叶小鸾形象之于林黛玉乃至《红楼梦》的意义也在这里。
(二)与叶小鸾形象直接相关的戏曲作品有《鸳鸯梦》杂剧和《钧天乐》传奇。《鸳鸯梦》出自叶小鸾胞姊叶小纨之手,作为《午梦堂集》作者之一参与了叶小鸾形象的生成;来自苏州才子尤侗笔下的《钧天乐》则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作为一位才子情结始终激荡于心的文人,尤侗对佳人叶小鸾保持了本能的向往和偏爱。其好友汤传楹曾云:“展成自号三中子,人不解其说,予曰:‘心中事,《扬州梦》也,眼中泪,哭途穷也;意中人,《返生香》也。’”(54) 在《西堂全集》中,涉及叶小鸾的诗词作品有多篇,如《戏集返生香句吊叶小鸾》十首、《和叶小鸾梦中作》、《吊返生香》等,一以贯之地表达了对叶小鸾的倾慕和赞赏。《钧天乐》传奇中,作为怀才不遇的男主人公沈白的未婚妻,女主人公寒簧“才色倾城”,婚前而逝,后被瑶池王母召为散花仙史,与被天廷选为状元的沈白在月宫团圆,终成眷属。作品多有取自叶小鸾传记者,如第八出《嫁殇》,当听母亲“拣定今月十五日”成婚后,寒簧问侍儿:“今日几日?”侍儿答:“初十日了。”寒簧又说“如此甚速,如何来得及!”与沈宜修《季女琼章传》所记几乎一样。来自《续窈闻》的例证也不胜枚举,如寒簧的临终绝笔诗:“身非巫女学行云,常对三星簇绛裙。清映声中轻脱去,瑶天笙鹤两行分。”即是泐大师招临时叶小鸾之魂所吟,其中只有三字之改。(《钧天乐》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尤侗“抑郁不得志,因著是编,是以泄不平之气,嬉笑怒骂,无所不至”(55)。此际,佳人的梦想一定发挥了缓解怀才不遇人生苦闷的作用,他才如此扬才露己、少有避讳地表达了对邻邑名媛叶小鸾的热烈向往,以至后来的才女汪端指责他“语多轻薄,文人口孽又过临川”(56)。应该说,作为梦中情人,叶小鸾构成了尤侗才子生活的生动景观。不仅他的三个女儿均以“琼”字命名(叶小鸾字琼章),在审视周边才女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表示:“松陵素称玉台才薮,而叶小鸾《返生香》仙姿独秀。虽使漱玉再生,犹当北面,何况余子?其对泐师语云:‘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词。’请借两言,以弁‘林下’之集。”(57) 评价之高、赞许之诚,均可捕捉到这位才子的白日梦心理,而以“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词”属意叶小鸾,与“寒簧”名字的使用一样,再次证明了金圣叹之于叶小鸾的建构在文学想象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钧天乐》中的“叶小鸾”形象却单薄而欠美感。尤侗为她确立了新的人物谱系:邑令之女、无知者之妹、才子未婚妻;其价值定位则依凭于对世俗功名的态度:一命所系非关真情,而主要是科举功名,未婚夫沈白名落孙山是她忧郁而死的直接触媒。她最具典型意义的宾白是:“咳,古来才子数寄,佳人薄命,同病相怜。世间多少女郎,七香车五花诰,享受荣华,偏我寒簧寂寞深闺,香消粉褪也,似下第秀才一般。好伤感人也。”这位“佳人”与才子同构的形象价值昭然若揭,恰如此段眉评所揭示:“后来做夫人的比官人更加性急,如寒簧十五女郎,一闻儿夫下第,无限感慨,至以死继之,何热中之甚也!”尤侗笔下,寒簧成仙的渴望也来自科举失败的引发,“彩鸾双驾戏蓬壶”(第五出)因之构成了后来情节中人物行动的驱力。尽管具体实践者主要是男性,然佳人寒簧作为男性话语的工具意义依然不彰自显。如是,尤侗仅在仙化的形迹或形象的皮毛上摹写了叶小鸾,这一形象禀有的真情美和丰沛的生命力反被抽取一空。即《钧天乐》中的叶小鸾形象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载体,与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不合生活逻辑的佳人形象一样,只具有确认才子价值的意义,而没有生成与才子形象互相激发的精神之美。在这位著名才媛的身上,尤侗一厢情愿的梦游神恋心理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但这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趣味和手段,除了昭示出他与金圣叹风神与境界的悬隔,还可以推出如是判断:曹雪芹是决不会从尤侗戏剧中获得创作灵感的。
(三)在由历史叙事而为文学想象的进程中,金圣叹扶乩过程中的审戒答吟作为“叶小鸾故事”被不断重写,成为清代小说创作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如沈起凤《谐铎》中的《娇娃皈佛》篇,15岁少女沈绮琴与戒律僧慧公的对话即是模仿泐大师与“叶小鸾”,其中“断六根”一段云:
慧公趺坐蒲团,高声提唱曰:“如何是无眼法?”曰:“帘密厌看花并蒂,楼高怕见燕双栖。”“如何是无耳法?”曰:“休教擫笛惊杨柳,未许吹箫惹凤凰。”
“如何是无鼻法?”曰:“兰草不占王者气,萱花莫辨女儿香。”“如何是无舌法?”曰:“幸我不曾梨黑狱,干卿甚事吐青莲。”“如何是无身法?”曰:“惯将不洁调西子,谩把横陈学小怜。”“如何是无意法?”曰:“只为有情成小劫,却因无碍到灵台。”(58)
作者明言此“与叶小鸾参禅一案,并为词坛佳话”,所采用的亦是骈丽的词语和正话反说的形式,意境和情感却不似“叶小鸾”答戒那样清丽晓畅、明朗如画。王韬《遁窟谰言》卷六《珊珊》提及屈楚香行法事,亦有“因登座为姗来说法,效叶小鸾故事”(59) 云云。在这两位金圣叹苏州后辈的文学创作中,作为小说的有机部分,乩文对于小说文体的参与构成了作品的最大特色,其不仅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丰富了小说文体的形式,也形成了对文体样态的拓展。
但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趋向。即作为叶小鸾形象的表征,扶乩赋诗的话语中心地位导致相关的文学叙事总是借助宗教活动展开,宗教教义的宣传凸显为主题;相应的,形象的工具意义日益明晰,叶小鸾逐渐演变成缺乏尘心的忏情礼佛者,少女丰富的感性世界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娇娃皈佛》中,沈绮琴的对答虽也彰显出文才慧心,并泄露了少女精神世界的感伤和压抑,但冗长的禅语问答除了映射出与“蒲团未破,红粉先埋”结局的悲剧冲突外,关乎女性鲜活生命的塑造却十分薄弱。在某些作者的笔下,叶小鸾本人甚至转换成了一位扶乩者。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二即有“叶小鸾降乩”一文,并云:“小鸾舜华早谢,不无红颜薄命之嗟,今观其诗,当已在灵妃郁嫔之列矣。”(60) 宗教价值的确认,完成了叶小鸾“去”普通人的过程,同时也不免对其形象美感和艺术真实的减损,致其演变成一个负载理念的符号式人物,生命力日益枯萎。叶小鸾形象在另一意义层面被不断解读,体现其形象核心价值的风神笑貌和人生追求必然淡化,平面化和娱乐价值逐渐凸起。如西泠野樵的白话小说《红闺春梦》,第四十九回以所谓的叶小鸾参禅作为酒令嵌入小说叙事,昭示了文化消费过程中的游戏追求给予形象独立精神和艺术品格的消解。此令名“少妇方丈参禅”,得令者“当恭敬在座‘老僧’一杯,拜为师父;须再别其格,以法叶小鸾贪、嗔、淫、杀四说”,于是小儒扮演的“老僧”与五官模仿的“叶小鸾”如是问对:
小儒笑了笑,问道:“你可犯过酒戒么?”五官答道:“犯过,洞房喜饮合欢酒,画阁祥开庆寿筵。”小儒又问道:“可犯过色戒么?”五官答道:“眉黛时教夫婿画,衾裯惯与小星争。”小儒问道:“可犯过财戒么?”五官答道:“姑嫜每赐添妆锦,儿女同分压岁钱。”小儒又问道:“可犯过气戒幺?”五官答道:“嗔婢掐来花带叶,怪郎笑对谑兼嘲。”(61)
同样是对泐大师审戒的模仿,这里的对句呆板平俗,缺乏情韵和灵性。特别是,“叶小鸾”参禅故事与“事实”更加遥远,且俗化、游戏化趋向相当突出。乩文的这种娱乐化倾向,尽管具有消解宗教价值的意义,但以谐俗的感官刺激构造虚拟艺术世界的新奇,不能不过度依赖所谓的成功经验,其结果是造成了想象力的偏执和抑制,致叶小鸾形象渐趋僵化涩滞,最终沦落为苍白的游戏内容。也就是说,一旦失去叶绍袁式的真情倾诉和金圣叹式的诗意建构,叶小鸾形象只能流于猎奇者的述说和游戏式的写作,或者成为演说佛理的工具与载体,不但乏有人文内涵,审美意义也大打折扣。
总之,叶小鸾形象生成于晚明时期流行的追求情本、张扬个性的文化思潮中。其以家族总集《午梦堂集》为展演平台,以容貌言行、诗词创作构成文学想象的最初因子,通过亲友的诗文描述、父亲的真情点评和金圣叹的降乩创设等合力塑造,促进了文学形象核心价值和基本样态的生成。进入清代文学史后,叶小鸾构成了各种体式文学的载体和元素,但多数作品只能在躯壳或形式的意义上模写复制有关的仙话故事和降乩对语,惟有《红楼梦》从人文和审美层面有效吸纳并深刻拓展了叶小鸾的风采神韵和形象内涵,使之创造性地重生于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叶小鸾形象在明清两代文学史上的艺术演变和审美表现,昭示了文学元素的流动路径和构成特征,揭示了作家个性、品味甚或伦理水准之于文学想象层次和形式构架的决定性作用。就这一意义而言,叶小鸾形象的生成演变乃思考文学想象性质、构成的生动个案,其文学史价值应给予重新考量。
注释:
① 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序云:“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即所谓“名父之女”、“才士之妻”和“令子之母”。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② 叶绍袁:《午梦堂集序》,《午梦堂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页。
③(22) 陈去病:《五色脂》,《丹午笔记·吴城笔记·五色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④ 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午梦堂集》第892页。
⑤ 叶绍袁:《愁言序》,《午梦堂集》第237页。
⑥⑨(14)(15) 同叶绍袁:《返生香》评语,《午梦堂集》第356、367、311、330页。
⑦⑩(11)(30)(49) 沈宜修:《鹂吹》,《午梦堂集》第202、202、201、195、202页。
⑧(16)(17)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午梦堂集》第847、846、847页。
(12) 叶燮:《午梦堂诗钞述略》,《午梦堂集》第1093页。
(13)(41) 叶小鸾:《返生香》,《午梦堂集》第329、330、339、316-317页。
(18)(33) 叶绍袁辑:《彤奁续些》,《午梦堂集》第674、673页。
(19) 叶绍顾:《重订午梦堂集序》,《午梦堂集》第1092页。
(20) 叶绍袁:《祭亡女小鸾文》,《返生香》附,《午梦堂集》第367页。
(21) 陈维崧:《妇人集》,《昭代丛书》本。
(23) 周作人:《知堂书话》,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24)(25)(51)(52)(53)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98、909、887、889、897页。
(26) 许地山《扶箕的迷信》:“文人扶箕最流行的时期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几乎每府每县的城市里都有箕坛。尤其是在文风流畅的省份如江浙等省,简直有不信乩仙不能考中的心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页。
(27) 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提及“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并云“其示现以十二年为期,后四年而大显”。见《初学集》卷四十三,《四部丛刊》本。
(28)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乩仙”,《乙亥从编》本。
(29) 《续窈闻》中金圣叹阅完《彤奁续些》后云:“意将欲不朽之邪?”叶绍袁“泣而请之”。见《午梦堂集》第518页。
(31) 如崇祯六年,叶绍袁曾于镇江访“姑布之术,奇中惊人”的异僧普颠,其云:“君男女之宫,煜煜有仙气,然女也且已往矣,必有飞琼上升之事。”崇祯七年春,有仙人称叶小鸾为“谪下散仙女也,不当于尘世作偶,故即去尔……”云云;崇祯九年八月,托名顾太冲的乩仙表示:“令女琼章,前身是许飞琼妹飞玖耳。”分别见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窈闻》等。
(32) 陆林:《〈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3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6页。
(35)(37) 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第518、523页。
(36)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42页。
(38) 查继佐:《闺懿列传》,《罪惟录》列传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
(39) 周亮工:《书影》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40) 陆林:《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42) 冯班:《钝吟杂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43) 章腾龙、陈勰:《贞丰拟乘》卷上《古迹·永庆庵》,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44)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86页。
(45)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页。
(46) 陈维崧:《吴姬扣扣小传》,《陈迦陵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47) 王采薇:《长篱阁集》卷首,《孙渊如诗文集》附,《四部丛刊》本。
(48) 王韬:《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74页。
(50) 卫泳:《悦容编》,《香艳丛书》本。
(54) 汤传楹:《闲余笔话》,《湘中草》卷六,康熙刻本。
(55) 阆峰氏:《钧天乐》题词,《钧天乐》卷首,康熙刻本。
(56)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29页。
(57) 尤侗:《林下词选序》,《西堂杂俎二集》卷三,康熙刻本。
(58) 沈起凤:《谐铎》卷三,岳麓书社,1986年,第31-32页。
(59) 王韬:《遁窟谰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60)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笔记小说大观》第18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88页。
(61) 西泠野樵:《红闺春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