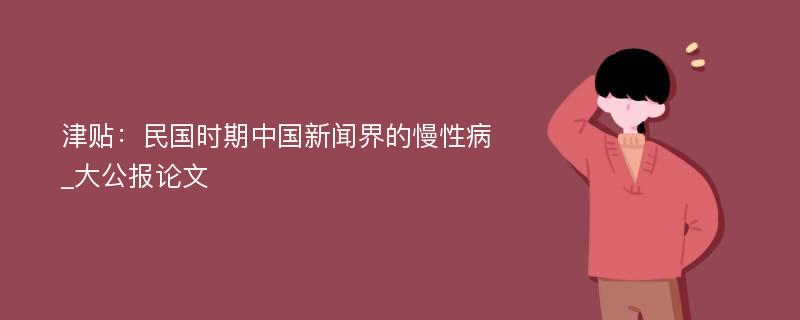
津贴: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的痼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痼疾论文,新闻界论文,津贴论文,中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津贴现象相当普遍,津贴的来源渠道丰富,对新闻业损害很大,也引起了部分有道义的新闻工作者的抵制。从各种迹象看,政治津贴在报纸的创办或发展过程中占重要位置,来源包括政党、政府部门、甚至是政客个人,特别在北方等商业不发达地区。而这种津贴现在除了中国报业不发达的原因外,传统文化也是可探讨的因素。
一、津贴来源多样
1.来自政客个人的资金。政客投资报纸,自清末、民国初即有先例。清末时期,当以开风气为己任的新式报纸出版时,那些和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有关的报纸,基本得到过洋务派的支持,如《中外纪闻》得到过袁世凯的资金支持;《时务报》得到过黄遵宪、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上海《新闻报》在福开森接手前也有张之洞和盛宣怀的股份。
民国以后,这种风气越来越浓。政界、军界名流用各种方式津贴报馆。如同盟会张耀曾(后为国民党中政学系要人)多年为其党派报纸《中华新报》补贴,数额巨大。上世纪20年代,湖南赵恒惕主政,以巨资津贴报馆,金额竟然高达“大报每月2000至3000元,小报每月1000至1500元,通讯社及杂志等每月200至500元不等”,而湖南《大公报》因为名气大,因此私下里得到8000元的支票,但被拒绝①。不过该报在创办时接受过蔡锷的500元,以及湘绅刘人熙等的3000元。从报馆欣然接受津贴的态度上可以推测这种情况在民国、特别是民国初不是个别现象。
2.政党、政府津贴报纸。由于成立党派是各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因此创办或支持报纸宣传自己成为政党活动的重要内容。有资金来源的大党派可以为报纸不断输送给养,使宣传成为日常的开支。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都有一定的预算用于宣传,一份报纸的津贴一般从100元到2000元不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掌握的报刊330种,其中日报有273种,多数都得到各级党部的资金支持,南京《中央日报》月津贴额度更是达到8000元,中央通讯社更是向中央提出月均补贴5万元的请求。
除了本党报纸名正言顺地接受津贴外,政府部门也要对社会上的名记者、报纸进行津贴。李思浩先后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次长、总长,曾回忆说,在他任财长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除《大公报》(由王郅隆出面主办),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政之)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②。
3.津贴现象普遍存在。除了政党报纸,一般以商业报纸为名的民营报纸,也普遍接受津贴,津贴一时泛滥成风。
1925年北京人口仅有100多万,竟然有300多家报社和通讯社,便是政治津贴的畸形作用。这300多家新闻单位中200多家多为见不到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或者与别的报纸合版,换下报头和部分社论,就是另一份报纸。有的仅印刷20余份,到各机关交差,市面上并不见销售,他们都是拿了各大小政党或个人津贴而糊弄出资人的。据1925年11月19日《晨报》报道,其余100多家报社则因有点规模,基本接受过北洋政府六大机关赠送“宣传费”。接受津贴的报馆分四级:1.超等的6家,每家300元;2.最要者39家,每家200元;3.次要者38家,每家100元;4.普通者42家,每家50元。总计15500元,125家媒体,其中日报47家,晚报17家,通讯社61家。③当津贴名单被一些报纸透露后,48家居于次要地位的报纸或不满意排名的报馆聚众要求政府公布名单。当然也有《世界日报》相反,于29日发表声明,否认接受过这笔津贴,一时间舆论界沸沸扬扬。熟悉报业内幕的张季鸾曾断言,“盖华北报纸,除小报尚能经济独立外,鲜有不靠津贴过活者”④。
同时期日本的秘密调查也证实津贴现象普遍存在。据1926年9月5日南满株式会社发行的秘密文件《支那新闻一览表》和1927年11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作的秘密调查《支那新闻及通讯机构调查》显示,在中国稍有影响的报纸都能得到也乐意接受各种津贴。甚至是商业发达的上海地区报业,也有各种名目津贴补助。如《新申报》在1925年左右接受的是李思浩或张学良的津贴,同时与孙传芳关系密切,每月有2500元的补助;而陈布雷所在的《商报》接受的是汤节之、虞洽卿的出资,与奉系军阀关系相当紧密等等。《申报》的史量才也先后接受齐燮元每月捐款2000元,以及一块地皮和一栋住房。当然齐燮元资助的报刊很多,不止一家。
二、津贴的影响与报人的反思
非正常的资金来源,使报业风气恶浊,一味追逐金钱,甚至在政局动荡的时候,敲一笔意外之财,完全忘记媒体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如1925年的金佛郎案发生后,有的报社竟得到几千元到两万元的津贴,几百元的就更多了。上文提到了1925年11月份在《晨报》公布了津贴名录后,竟有报社、通讯社因为没有领到“津贴”,登报质问,使六机关非常尴尬;报社为了津贴的事互相攻讦也是屡见不鲜⑤,不仅影响报业的声誉,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报业客观公正的立身之本。
一些著名报人也接受津贴,拿人钱财,替人说话。如林白水也是生活阔绰,在他的宅子中,佣人最多时有十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就有5个,此外他还酷爱收藏金石和砚台,藏品闻名于世。其卖文、收受津贴和贿赂在报界也并不是秘密。
这种现象引起当时部分报人深刻反思和忏悔,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罪”。时值《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张季鸾曾说“吾尝审思,以为中国报纸无功可论,惟视其罪之大小及性质如何”⑥。此“罪”即接受津贴,它是导致言论偏颇,纪事错误的重大根源。这一点连外国在华的媒体工作者也看得一清二楚,《泰晤士报》总主笔萨雅曾批评中国报纸不能独立,“华字报中,或有受政党之津贴者,有主笔不得其人而致昧于世界之大事者,此吾人之所知,不必为之讳言。”⑦《时事新报》也痛陈此种罪责,“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⑧。因此看来当时报馆的原罪就是接受津贴,由此发生的言论偏颇不当,新闻不实错误甚至捏造,都直接或间接由此而来。
但对此进行抵制的力量,常常源自报人个人的修养。这使得对津贴的抵制缺乏制度、文化、行规等方面的支持,而显得势单力薄。
三、报业津贴泛滥的深层背景
民国初报业津贴泛滥,源自该阶段国家政治腐败、经济不畅、商业不兴。但有两个原因需要细致剖析。
首选,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报业津贴泛滥,实有封建文化遗留风气的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乡绅官士、富庶人家有捐款抄书的习惯,成为中华传承文化与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和社会主流阶层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实际上也是维持统治、延续主流文化的一种做法。只是到清末、民初,这种资金的流向有了新的出路——报刊,特别是党报刊成为救国工具时,其得到官绅的资助就更为普遍,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为宣传本党派的主张,给报界的捐助都很多。除去政治宣传的需要,实际上这里也有文化背景的因素。
第二,商业报纸不发达,盈利不易,很难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这是报业接受津贴的重要原因。董显光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天津《庸报》,是用他辛苦积攒下的几千元开始的;后来拥有《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世界画报》的成舍我,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时,起家资本只有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200块大洋⑨。当时他用如此少的资金涉足报业,也只有办晚报了,因为“晚报成本低,只需用四开大的纸就够了”⑩。新记《大公报》1926年建股份有限公司,5万元的启动资金是四行储蓄会会长吴鼎昌从“经济研究经费”中列支的,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分红极少,这笔钱基本可以看作是“贡献”的启动资金。
民间资本筹集不易,且容易枯竭。《新闻报》老板汪汉溪在世时,为了报社的发展,负责融资,想尽办法。为了得到良好信誉,有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借钱还债,历尽艰辛。直到1921年才还清欠款,给股东发放股息。1923年该报30周年纪念时,他曾痛心地记录下中国民营报纸在资金方面的艰难:
“经济自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至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招集股本一二万,勉强开办,其招足十万八万为基金者,殊未多见。股未齐而先后从事于赁屋、购机、置备器具,延聘编辑、访员,雇佣工役,以沪市物用昂贵,开支浩大,恐在筹备期内,基金业已耗尽。及至出版,销数自难通畅。广告收入甚微,报馆人才,征求延聘,尚难入选,而各股东所荐之人,大都不适于用,人浮于事,办事无人、出版未久,主其事者,支持乏策,乃不得不一再商之股东。加添股本。股东每因所荐之人未能满意。多愿抛弃原有权利,以免屡加股本之忧,股本即难添招,收入亦无把握,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闻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必自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11)。
虽然大家都明白言论独立对报业的重大意义,但前提是经济独立,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如何谈言论的独立。我们从汪汉溪的肺腑之言中体察到民营报纸想通过正常途径融资的艰难。
无论如何,《新闻报》在经济独立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张季鸾曾赞扬它是发挥“在商言商”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还称赞汪汉溪是“不问政治,不兼他业,惟专心一志经营报业,其谨慎精细,久而不懈,全国殆无第二人”(12)。
也许永远无法计算中国报纸接受政治资本的具体数额,但这种捐赠无疑是经常或长期的,成为中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提供给报业最需要的发展资金,一方面又无情地收买了报纸最珍贵的言论自由。一些报人,如《大公报》张季鸾等对此很义愤,“今敢下一断语曰,报纸直接或间接接受党派经济上的补助者,绝不能有光明磊落之气象”(13)。他们在津贴泛滥的环境中,逆流而上,珍视新闻事业,独善其身,在1926年以“四不主义”创立《新记大公报》,发出独立办报的宣言,终于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局面。
注释:
①张季鸾,《新闻报馆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2册附录,1946年7月第三版,大公报馆,第3页。
②萨雅(泰晤士报总主笔),《中国报纸之效用》,《新闻报馆三十年纪念册》,新闻报馆,1923年。
③时事新报同人,《本报五千号纪念辞》,1921年12月10日,《时事新报》,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69页。
④张平子,《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湖南文史资料》2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77页。
⑤徐铸成,《李思浩生前谈北洋财政和金佛郎案》,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233页。
⑥《晨报》1925年11月19日。
⑦张一苇,《华北新闻界》,《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
⑧世界日报史料编写小组,《世界日报初创阶段》,《新闻研究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52页。
⑨成氏接受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贺德霖的3000元,置办机器设备,是在1925年创办世界日报的时候。但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成氏就撇清了与贺以及北洋政府的关系,极力宣称自己的民营独立性质。
⑩《革命报人别记》下,徐詠平著,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73年3月。
(11)汪汉溪,《新闻业困难之原因》,《新闻报三十年纪念》,新闻报馆。
(12)张季鸾,《新闻报馆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2册附录,1946年7月第三版,大公报馆,第3页。
(13)谢福生,《世界新闻事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