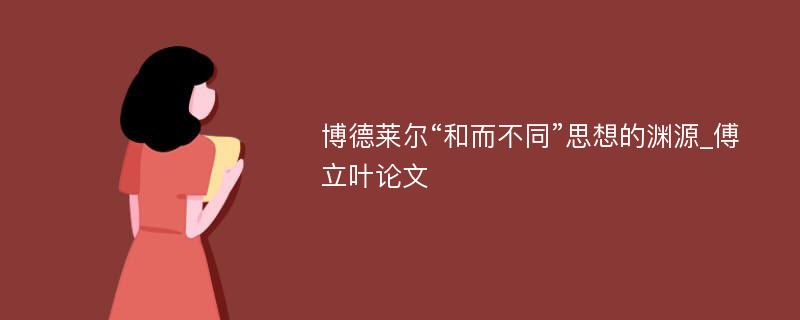
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尔论文,来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4-0022-06
《应和》一诗是表现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重要作品。这首十四行诗在表达一种美学见 解的同时,其本身也是对这种美学见解的具体演示:
自然是座神庙,那里活的廊柱
有时候传出模糊隐约的话音;
人在此经行,穿越象征的深林,
深林注视他,投以亲切的眼目。
如悠长回声遥相应答的和歌
终汇入一个混沌深邃的整体,
如黑夜又如光明般浩漫无际——
芳香、色彩和声音在互相应和。
有些芳香鲜嫩如儿童的肤肌,
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
——还有一些则朽腐、浓烈而神气,
具有着无极无限之物的张扬,
如龙涎香、麝香、安息香和乳香,
歌唱精神与感官交织的热狂。
这首诗中所说的“应和”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即法国批评家让·波米耶在《波德莱 尔的神秘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横向”(sur le plan en largeur)的应和与“纵向” (sur le plan en profondeur)的应和。[1](注:查尔斯·查德威克在名为《象征主义 》(Charles Chadwick,Symbolism,London,Methuen,1971)的专论中,用“水平应和”(
correspondances horizontales)和“垂直应和”(correspondances verticales)来表 示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应和关系。)
所谓“横向应和”是指应和现象在感官层面上的展开,指一种实在的感知和另一种实 在的感知在同一层面的水平应和关系。这种应和关系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隐喻性关联 ,强调人的感官与感官之间的相互沟通。“芳香、色彩和声音”的互相应和就属于“横 向应和”。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应和的关系和“普遍的相似性”,这就 为人的不同感官之间的沟通和应和提供了可能性。嗅觉感受到芳香,可以转移到触觉的 细腻(“有些芳香鲜嫩如儿童的肤肌”),转移到听觉的柔和(“柔和如双簧管”),转移 到视觉的青翠(“青翠如绿草场”)。这种现象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联觉”现象(
synaesthesia),评论界更通常的说法是“通感”,也有人将其称作“感觉挪移”或“ 感觉通联”。
所谓“纵向应和”是指物质客体与观念主体、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等在不同层面上的 垂直应和关系。这种应和关系强调具体之物与抽象之物、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自然之 物与心灵或精神的状态、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等之间的象征关系,是应和现象在象征 层面上的展开。正是通过“纵向应和”,诗人得以“歌唱精神与感官交织的热狂”。纵 向应和关系体现在文学艺术中便是一种象征关系。波德莱尔在一篇文论中写道:“我总 是喜欢在外部的可见的自然中寻找例子和比喻来说明精神上的享受和印象。”[2](P148 )这句话是他对自己建立在应和论基础上的艺术思想所作的经典概括。“纵向应和”在 具体运用中可以表现为具体与抽象、具象与观念、物质现实和心灵状态、事物与人心、 个人与人类、意识与无意识、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现象世界与本体 世界、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世界与神性、显露与隐蔽和表层与深层等象征关系。在这 些应和关系中,前一项是后一项的感性显现形式和手段,后一项是前一项的目的并为其 赋予意义。
如果只有同一层面的“横向应和”,还不能构成艺术的全部。一件作品要成为艺术, 必须在“横向应和”的基础上引出更高层次的“纵向应和”。经由从“通感”到“象征 ”,从“横向应和”到“纵向应和”,波德莱尔逼近了象征的本质,不仅揭示出构成一 切艺术形式基础的象征特质,而且通过揭示事物与人心的沟通,使艺术成为具有哲学和 宗教般价值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显现形式。《应和》一诗充分显示出波德莱尔不仅是一位 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头等的批评家。有论者认为这首诗包含了“创造的逻辑”,应将 其视为“象征主义的宪章”和“高级美学的教理。”[3]
其实,“应和”的观念并不是波德莱尔的个人发明。评论界在论及波德莱尔“应和” 思想的来源时,一般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斯威登堡、霍夫曼、傅立叶和爱伦·坡对他的 影响。这样的说法大致上是不错的,但往往对具体影响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却又语焉不详 ,在论断上给人以流于粗疏之弊。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廓清,并对有些 问题加以必要的补充说明,以期对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有一个更为全面和准确 的把握。
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最早发表于1857年《恶之花》初版。由于波德莱尔本人从未 就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做任何说明,评论界自然也就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最 有可能写成于1855年前后,其依据的理由如下:波德莱尔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到傅立叶的 “相似论”和斯威登堡的“应和论”,同时频繁地将“相似论”和“应和论”的观点运 用于文学和艺术批评的文章中,并且还经常在致友人的书简中对之进行饶有趣味的谈论 。另外,他在这个时期热衷于翻译爱伦·坡的作品,对爱伦·坡作品中关于神秘感应的 文字颇多玩味,视同己出。
“应和”一词出现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一个明确可考的出处是《评1855年世界博览会 美术部分》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发表于1855年5月的《国家》杂志。文中写道:
现代的美学教授……将自己关在他那体系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要塞中,诅咒生活和自然 ,……禁止……用不同于他自己的方式去享受、梦想或思考,……比野蛮人还要野蛮, 他忘记了天空的色彩、植物的形状、动物的动作和气味,他的手指痉挛,被笔弄得瘫痪 ,再不能在应和的广阔键盘上灵活驰骋
在同一篇文章中,波德莱尔还提到不同感觉之间的通感现象:“那些神秘花朵的深邃 色彩不由分说地进入眼帘,而其外形也在挑逗着目光,那些果实的味道令感官错乱,在 味觉上引起嗅觉的印象。”[2](P577)他还指出,不同感觉之间的相通可将人带入一种 具有全新和谐的世界,让人仿佛置身于香薰浴的蒸气之中。次年,即1856年,波德莱尔 在致友人图斯奈尔的信中大谈“普遍的相似性”和“应和”:
长久以来,我都认为诗人是最高的智慧者,是最杰出的智慧,——并且认为想像力是 一切才能中最科学的才能,因为只有它才懂得普遍的相似性或某种神秘宗教所谓的应和 。[4](P336)
“普遍的相似性”的说法自然让人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相似论”。的确 ,波德莱尔在这封信中也提到了傅立叶,而且,这是傅立叶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他的笔下 。不过,有意思的是,波德莱尔在这里似乎并不是要承认傅立叶的影响,相反,他在指 出“自然是一个词语,一个寓托”的同时,强调诗人具有能够勘破其中奥义的才能,认 为真正的诗人自然懂得这一切,无需来自傅立叶的任何教训。[4](P337)波德莱尔在几 年后写的《维克多·雨果》一文中同样用带有几分怀疑的语气谈论傅立叶:
有一天,傅立叶来了,夸夸其谈,向我们昭示相似性的奥秘。我不否认他某些细腻发 现的价值,尽管我认为他的头脑过分热衷于物质方面的准确性,不能不犯错误,不能一 下子达到直觉上的道德确定性。他本来也是可以细心地向我们披露所有那些优秀诗人的 ,人们读他们的作品可以和观照自然一样获得教益。[2](PP132-133)
他在文中用怀疑的口吻谈论傅立叶的同时,确认了更早时候斯威登堡的影响,甚至还 提到了瑞士哲学家、神学家拉瓦特(Lavater):
具有更伟大灵魂的斯威登堡早就教导我们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事物,形式、 运动、数、色彩、香味,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自然中,都是有意味的,交互的,转换的 ,应和的。拉瓦特把普遍真理的表现限定在人的脸上,向我们解说了脸的轮廓、形状和 大小所具有的精神含义。[5](P133)
虽然波德莱尔不止一次表示了对傅立叶的怀疑,但似乎又并未完全否定傅立叶的作用 。他在1860年发表的《人工天堂》中表现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公允的。他在文中将傅立叶 和斯威登堡相提并论:
傅立叶和斯威登堡,一位用他那些“相似”,一位用他那些“应和”,使自己表现在 你眼前的植物和动物之中,他们不用声音来讲授,而是用形式和颜色来宣讲。[5](P430 )
波德莱尔在这里没有提到作为他“应和”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爱伦·坡。不过,他在 论述爱伦·坡的专文中对此有所涉及。
波德莱尔在青年时代发现了美国作家爱伦·坡,并在19世纪50年代大量翻译其作品。1 856年,他翻译的爱伦·坡《奇异故事集》出版,其中的《窃信案》包含有这样的文字 :“物质世界……充满了跟非物质世界的精确相似……”[6]译者在为该书所撰写的前 言《埃德加·坡的生平与著作》中表达了相近的意思:
无生命的自然具有了有生命的自然的性质,并且像那些具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发出超 自然的、过电一般的震颤。[2](P318)
次年,即1857年,波德莱尔借《奇异故事续集》出版之机,写《再论埃德加·坡》, 并将其作为该书序言。他在文中指出:
正是这种奇妙的、永生不死的对于美之本能让我们把大地及其各种景象看作上天的概 览,看作上天的应和。[2](P334)(注:他在两年后所写的《戴奥菲尔·戈蒂耶》一文中 ,引录了这段文字,足见他对这种见解的心仪。)
至此,可以看到,波德莱尔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傅立叶、斯威登堡、爱 伦·坡对其“应和”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认为这便是他“应 和”思想的全部来源,似乎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以上种种证据似乎也并不能够确 证《应和》一诗的创作时间。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宽一点,考察这之前波德莱尔的生平 和创作,就会发现,19世纪40年代中期是《应和》一诗的另一个可能的创作时间。对这 种可能性的考察会帮助我们了解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另外一些来源。
说《应和》写成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主要依据如下理由:波德莱尔在这个时期也许 是通过巴尔扎克同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已经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且在霍夫曼、埃斯基若 (Esquiros)、孔斯当神甫(l'abbé Constant)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对发掘事物间的神秘 相似性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巴尔扎克对斯威登堡的学说情有独钟。据说他的书架上有一层是专门用来摆放《斯威 登堡全集》的。[7]巴尔扎克受斯威登堡“应和论”的启发,不仅强调色彩、声音、气 味的相通,而且还努力发掘面相术和骨相学中可能包含的诗意,认为人的面相和体貌是 其灵魂的镜子,同人的本能、性格、欲望、情感、灵性等有着天然的和深刻的应和关系 。他在《人间喜剧》中大量精细入微的人物描写,既生动活泼,又饶有兴味,能够成为 文学史上人物描写的经典范例,究其原因,是因为作者不是为描写而描写,按他自己在 《<人间喜剧>前言》中的说法,他在写人的同时,特别注意要写出“思想的物质表现” [8]。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同时还应当具有一种“超人的 视力”,也就是他多次提到的“第二视力”。凭借这种视力,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 入常人难以企及的领域,在“公众看到是红色的地方”看到“蓝色”,能够透过观察到 的纷繁表象去洞观事物的内在因由和真谛。[9]由于巴尔扎克的大力推广,一时间,在 作家圈子中,谈论斯威登堡成为时尚,斯威登堡的“应和论”也开始日渐风行。波德莱 尔在结束学生生活的40年代初曾经历了一段“纨绔子”(dandy)时期,仰慕巴尔扎克的 声名。虽然波德莱尔谈论斯威登堡的理论是5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但他很可能受巴尔扎 克影响,在40年代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斯威登堡的学说。尽管波德莱尔本人没有明言,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了解到这点。波德莱尔的好友尚福勒里(Champfleury)在 回忆青年时代生活时写道:“一天,波德莱尔出现在面前,腋下夹着一本斯威登堡的书 ;在他看来,无论哪种文学中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斯威登堡的书一较高下。”[10]另 外,在波德莱尔写成于40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芳法萝》中,笔者偶然提到主人公克拉 梅尔的书桌上有两本书权作烛台使用,其中一本就是斯威登堡的书。[2](P555)评论界 倾向于认为小说主人公身上有波德莱尔本人的影子。
波德莱尔对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作品也可谓耳熟能详。霍夫曼怪诞离奇、交织着 现实与幻想的作品将他引入一个人与自然、天与地、灵与肉相互应和的神秘世界。霍夫 曼短篇小说集《卡洛式的幻想篇》中有部分作品反映作者从事音乐活动时的经历和感受 。在其中《格鲁克骑士》一文中,作者借作品人物之口说道:“特别是当我长时间听音 乐时,我便感到色彩、声音和香味相通了。”[11]霍夫曼在后来的《克莱斯勒传记片段 》(Kreisleriana)中对这句话加以发挥,进一步说明色彩和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波德 莱尔在《1846年沙龙》中援引的《克莱斯勒传记片段》中的以下段落似乎可以作为《应 和》的注脚:
不仅仅在梦中,在入睡前轻微的幻觉中,而且也在醒著的时候,当我听到音乐,我就 会发现色彩、声音和香味之间有一种相似性和内在的融合。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产生于 同一束光线,它们应当汇合成一种美妙的合奏。褐色和红色金盏花的气味会在我身上产 生一种神奇的效果。它使我陷入深深的梦想,于是我就仿佛听见远处响起双簧管舒缓而 深沉的声音。[2](PP425-426)(注:E.T.A.Hoffmann:Saemtliche Werke in sechs Baenden,Bd.2,1:Fantasiedtuecke in Callot's Manier.Werke 1814.Hg.Von Hartmut Steinecke.Frankfurt/M.: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3,S.63.)
这段文字和《应和》不仅有意思上的近似,甚至还包含有“色彩”、“声音”、“香 味”、“双簧管”等一系列相同的字眼。有意思的是,波德莱尔译文中有一处误译,即 他将霍夫曼原文中使用的Bassethorns(低音单簧管)一词误译为hautbois(双簧管)。其 实,前者比后者在音域上要低九个音阶,能更为恰当地配合“舒缓而深沉的声音”。不 管波德莱尔的误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他创作自己的 《应和》和翻译霍夫曼的这段文字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意念上的一致性。
波德莱尔的好友埃斯基若对应和的观点也是情有独钟,将世界看成“神圣的典礼”, 认为一切可见之物都是为“圣事”而设。他在1841年的《歌集》中称森林是“高耸的教 堂”,在那里,树木“向诗人的灵魂言说”。这不禁让人想到波德莱尔笔下将“自然” 喻为“神庙”的表达,以及“廊柱”传出的“话音”。
波德莱尔和埃斯基若还有一位共同的熟人孔斯当神甫。波德莱尔对这位大名鼎鼎的神 甫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敬重,他在1844年的《巴黎梨园风雅秘录》中将其戏称为“一 位五短身材的胖神甫”[2](P1007)。不过孔斯当著作中宣扬的“万物应和”、“言成肉 身”的神秘主义观点却又不能不让波德莱尔感到特别的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斯 当神甫于1845年发表的《三种和谐》一书中恰好也有一首诗题为《应和》(Les
Correspondances),与波德莱尔作品的标题用了同一个词语(波德莱尔作品标题没有定 冠词Les)。在这首诗中,孔斯当神甫从世间万物的“普遍相似性”出发,寻求自然中的 各种表征与灵界真理的关联,要求通过人与自然内在的和谐而达成与圣言的沟通。他在 诗中写道:
如此世界上帝梦幻,
昭然言辞乃其构筑;
象征形式传达圣言,
圣灵似火将其灌注。
自然并不缄默乖张,
符合法度便可通晓;
漫天繁星书写铺陈,
田野百花话音琅琅,
黑夜昏沉圣言闪光,
严词厉语直达幽冥。
先知于此读出奥义;
张开双目慧眼人士
传译宇宙至深奥秘
自然是由象征构筑的大厦,万物讲述着一种生动的语言,圣言是一切和谐的保证,能 读出其中奥义者便成为先知,这是孔斯当神甫所要表达的意思。波德莱尔也许并不全盘 接受这样的宗教信条,但又不排除他会从艺术思想的角度在孔斯当神甫的诗中寻找开启 诗歌世界的钥匙,从中获得启发,甚至获得创作自己《应和》一诗的直接灵感。法国学 者雅克·克雷佩在其权威版本《恶之花》的注释中指出,孔斯当的《应和》也许是波德 莱尔《应和》的一个重要来源。[3](P296)
对《应和》一诗创作时间的考察属于对可能性的推测,对确证文学史上的事实真相也 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又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因为两方面 所提供的证据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和形 成过程,以及波德莱尔在文艺批评活动中对应和论加以运用的一些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巴尔扎克、埃斯基若、孔斯当神甫这些同 波德莱尔有过交往的人士,是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直接启示者,斯威登堡和霍夫曼 的“应和论”、傅立叶的“相似论”则是其“应和”思想的理论根据,爱伦·坡的作品 强化了他对“应和”思想的信念。
不过,以上种种似乎仍然没有揭示出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全部来源。在前文提到 过的致图斯奈尔信中,波德莱尔特别看重诗人天生的秉赋,认为诗人自然懂得万物间存 在着的“普遍相似性”,无需来自别人(傅立叶,也许还应当算上斯威登堡)的任何教训 。他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在强调一种思想的形成绝不仅仅是从外部袭得的,而必须还 要有一种内在的经验作为其基础。
波德莱尔在步入社会之初,曾有一段时间浪迹在以戈蒂耶为首的一群狂放不羁的文学 青年中间。这群人以追欢买笑、纵情声色为乐事,为寻求感官刺激和迷幻状态而不惜大 量饮酒,甚至吸食鸦片、大麻等兴奋剂。戈蒂耶在很多地方谈到梦境、幻觉和某些超日 常的状态往往向人们揭示互不相关的事物或形象之间神秘的应和关系,认为在这样的状 态中,听觉可以感受视觉印象,声音可以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他在1843年发表的《 大麻瘾君子俱乐部》成为当时一帮文学小青年的枕中秘籍。波德莱尔对兴奋剂的兴趣大 概是始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在接触到英国作家德·昆西的《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后更是将这一兴趣加以发挥,成为他写作《人工天堂》的直接动因。他在书中探讨超日 常的精神状态对于感受事物间隐秘关系的作用,并发掘其在美学上的积极意义,把艺术 效果发生作用时带来的沉醉同吸食鸦片等兴奋剂后产生的迷幻状态加以类比,认为两者 的对象都是超灵敏的神经感觉到的自然。说是迷幻也好,说是沉醉也罢,由鸦片引起的 幻觉或错觉用最极端的夸张形式演示着应和现象的特征。在波德莱尔的语境中,所谓幻 觉或错觉,不过是对一种极度敏锐的感觉状态的比喻性说法,与其说是一种反常的精神 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能够进行深入体察的本领。他在《人工天堂》中坦言,所谓“超自 然状态”,其实是对“自然”材料的强化和深化,是对某些微妙感觉的放大,它使人摆 脱常规的束缚,捕捉事物间隐秘的象征关系,进入诗意思维的真境。在这种精神状态中 ,一切最普通的事物披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成为蕴含着某种深意的寓托(allégorie) 或象征。波德莱尔在《人工天堂》中写道:
在精神的这种神秘而临时的状态中,生活的深刻之处连同其各种问题在人们眼前最自 然、最平凡的场景中完全显露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事物一经出现,就成为会 说话的象征。(注:在题为《火花断想》的笔记中有一段表示相同意思的话:“在心灵 的某些近乎超自然的状态中,生活的深刻之处便会通过眼前的场景——哪怕是最平凡的 场景——被彻底揭示出来。那场景便成为象征。”(《全集》,第一卷,第659页)波德 莱尔在《天鹅》一诗中写道:“一切对我来说都成为寓托。”(《全集》,第一卷,第8 6页))[5](P430)
他在《评1855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中称这种状态是“精神上的美好时光”,并指 出,“在这样的时刻,感官的注意力更为集中,体会更为强烈的感觉;蓝天更加透明, 仿佛深渊一样更加深远;一切声响发出乐音,一切色彩说着话语,一切香气讲述着观念 的世界。”[2](P596)这种基于自身感觉状态的神秘体验,可以看成是波德莱尔艺术思 想得以形成的经验基础,也是他接受“应和论”和“相似论”的内在依据。这种基于自 身经验的内在因素在波德莱尔艺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许比他从外部和传统 中袭得的任何体系都更为重要。他从外部和传统中借用的,与其说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 系和教训,不如说是一种能够恰当地表述自己思想的方式,而这种思想的根存在于他自 己的心灵和血肉之中。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用调侃的语气谈论所谓“体系”时,其论述“ 体系”和“感觉”二者关系的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我跟我的朋友们一样,不止一次地尝试着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体系中,以便悠然自得地 进行鼓吹。但是,一种体系就是一种遭罪,迫使我们无休止地发誓弃绝;因为总需要发 明另外一种体系,而这种疲劳是一种残忍的惩罚。……由于我总是被迫经受不断改换门 庭的屈辱,我终于下定决心。为了避免哲学上种种背弃行为的可憎,我骄傲地自甘于谦 逊:我满足于感觉,我重返到完美的天真中寻求庇护。……正是在天真中,我的哲学良 心求得了平静;至少,像一个人可以为他的美德担保一样,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思想 现在具有更多的公正。[2](PP577-578)
如果抛开在这段文字中强调的朴素而本真的感觉经验,对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任 何讨论都会迷失其最基本的对象。
“应和”的观念不是波德莱尔的个人创造,在他进入文坛的19世纪40年代,这已经成 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个观念甚至不可以被看作是斯威登堡、傅立叶或霍夫曼等 人的发明,他们其实是对西方文化传统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观念的解说和发扬。从广 泛的文化背景上看,“应和”的观念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原始思维中就有“万物有灵” 、“天人合一”的观念。宗教里有神性世界(神圣本质)通过现象世界显现自身的观念, 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将世界看作神圣范本的图像或 投射。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得以传承。《圣经新约·罗马人书》写道: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 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无可推诿。”(I,20)斯威登堡关于地上世界、中间世界和天上世界的说法就是从古 老的宗教思想中脱胎出来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除了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外, 也是一个具有表义功能的图像存在。另外,哲学上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紧密关联的 观念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对明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无不包含有“应和”的 思想在其中。
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神秘学说纷呈、神秘教派林立的时期。无论在意识 形态上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都表现出一种对于“应和”、“相似性”和有生命宇宙的 统一性的普遍热衷:如将世界看作是用隐秘或神秘的符号书写的诗歌(谢林);将诗歌看 作一切崇拜的自然语言,认为这种语言可以消弭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界限(斯达尔夫人); 将自然看作上帝的神殿或表达神圣观念的象征符号(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圣-伯 夫)。
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在对传统的“应和”观念进行全面综合的基础上对其作了形 象、明确、精练的格言式表述。这一表述调动图像、音响和嗅觉,让人以最直接的方式 “看到”、“听到”和“闻到”其中包含的精髓,此前还没有任何人达到如此精妙的地 步。不过,复述一个古老的思想,这并不是《应和》一诗的全部意义。其实,当波德莱 尔表述这一古老思想时,他更多的是将其完全作为自己的思想来对待的,他在传统中找 到了同自己内心的观念契合的思想所在。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思想的出现都 不会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必定是某种思想传统和作为思想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才智完 美结合的产物。要准确把握《应和》一诗的精神,显然不能脱离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背 景。当我们把这首诗同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时, 我们就能够理解何以有人会认为这首诗包含了“创造的逻辑”,并将其视为“象征主义 的宪章”和“高级美学的教理”。当我们把《应和》一诗看作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概括 表现时,就会发现,诗中涉及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对传统应和论的简单解说和总结,诗中 其实包含了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基因和关于艺术创作的一系列原则,如对艺术与现实的 关系,艺术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处理,艺术家观察自然和表现自己主观内心境界 的态度和方法,艺术表现形式等问题,都作了理论的规定。波德莱尔自觉地将这种美学 思想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丰富了自己作品中对词语的独特运用和对文学意象的 新颖创造。同时,他还在自己的文艺评论中热烈地捍卫自己的理论,使古老的“应和” 观念成为构建自己具有现代意识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并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探索一种 全新的创作方法,在本体的高度上建立一种对文学艺术本质的全新认识,为文学艺术的 现代转型开启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