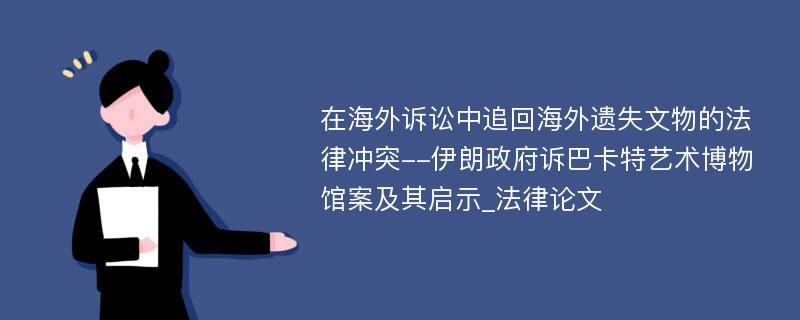
境外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冲突法问题——伊朗政府诉巴拉卡特美术馆案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特论文,伊朗论文,美术馆论文,境外论文,巴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过境外诉讼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背景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即达几十万件,涉及数十个国家。其中一部分是战争情况下被抢走的,另有很大一部分是近年来通过非法走私途径流失海外的。①欧洲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国家就是英国,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为最,该馆收藏有数量极丰的各类中国文物精品,代表性文物有汉代玉雕驭龙、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敦煌绢画和文书等。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国际上兴起了向文物所在国法院起诉并要求有关机构或个人将被非法出口到法院地国的文物返还其来源国的诉讼浪潮。②中国官方和民间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行动也日益高涨。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行宣布将于2009年2月份在法国巴黎举办一场专场拍卖,拍卖品中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鼠首和兔首铜像。不久前,我国一些民间机构和个人远赴法国法院起诉试图追讨该文物,引起了广泛关注。③
英国作为世界文物交易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境外中国文物的主要收藏地和集散地,其对待跨国文物诉讼的态度也最值得关注。英国法院最近审判的伊朗政府诉巴拉卡特案(下文简称巴拉卡特案)非常具有代表性,④反映了国际文物保护诉讼领域的最新趋势,值得我们予以研究。
该案中,英国伦敦的巴拉卡特(Barakat)美术馆从法国、德国和瑞士收购了18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古代雕刻容器。按照伊朗政府的说法,该批容器是从不久前发现的伊朗吉洛夫特小城(Jiroft)的古代墓葬中非法盗掘并偷运到国外的。根据伊朗1979年的一项法令,该批文物的所有权已归属伊朗政府,于是伊朗在伦敦起诉巴拉卡特美术馆,要求其返还该批文物。而巴拉卡特主张它是根据合法的途径收购该批文物并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该案中伊朗政府依照英国法律提起了一项追索被非法占有之物的变更之诉(conversion),其依据是英国1977年侵权(侵犯财物)法。⑤伊朗的诉讼请求是否被法院接受,取决于两个先决问题(preliminary issues):
第一,伊朗政府是否依照伊朗的法律已经获得对该文物的所有权或直接占有权;
第二,假如伊朗根据伊朗法律拥有对该文物的所有权或直接占有权,英国法院是否对其予以承认和/或执行?
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双方当事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也在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对立。一审法官对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回答,判决伊朗政府败诉;而二审法院则驳回了一审判决,改判原告胜诉。
本文将结合该案例,对此类跨国诉讼中涉及到的冲突法问题进行逐一论述,并针对我国可能进行的类似诉讼活动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二、跨国文物诉讼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一)诉讼资格适用法院地法
在跨国民事诉讼中,原告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诉因(cause of action),否则法院不会受理。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对该诉因享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如前所述,巴拉卡特案中,伊朗政府提起的是一项英国侵权法上的变更之诉,那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英国,谁有资格提起一项变更之诉?诉讼资格问题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相对应。在国际私法中,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实体问题适用案件准据法(lex causae)。⑥因此,伊朗政府是否有资格提起英国法上的变更之诉,应当根据英国法律判断。
根据英国1977年侵权(侵犯财物)法,⑦只有对动产享有特定权利的人才可以提起变更之诉。⑧这种特定权利包括占有权(possessory title)和所有权(proprietary title)。⑨普通法中本来不区分占有权(possessory title)和所有权(proprietary title)。占有一项动产即可获得对该财产的权利(title)。但如果占有发生非自愿转移,比如丢失或被盗,则初始占有人对该财产享有的权利优先于后继占有人(subsequent possessor)。后继占有人的权利可以对抗除了初始占有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无论是初始占有人还是后继占有人都可以针对第三人对该财产的侵犯主张直接占有权(an immediate right to possession)。正是由于动产的权利可以分享,才出现了所有权和占有权之间的区分。比如,初始占有人(委托人)将占有权转让给后继占有人(受托人)并声明委托人享有该动产的未来收益,此时,该委托人可以被认为享有所有权,而受托人享有占有权。任何第三人对该财产的侵害都同时损害了所有权人和占有权人双方的权益,故此双方都有诉权。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诉因(causes of action),一种是追还被侵占财产的返还之诉(detinue),它针对的是对原告所有权的侵犯;另一种是所谓的变更之诉(conversion),它针对的是对原告占有权的侵犯;二者可以并存。所以,本案中伊朗是否拥有诉讼资格关键是看伊朗政府是否拥有对所涉文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
(二)先决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伊朗是否对文物拥有所有权或占有权的问题就构成了伊朗政府是否拥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先决问题(preliminary issue)。在国际私法中,普遍的观点认为先决问题应当依据法院地冲突法解决。⑩巴拉卡特案中,伊朗对文物的所有权问题,应根据英国冲突法判断。根据戴西的权威著作:“动产转让的有效性以及转让对有关当事人和其他对该动产主张权利的人所产生的效力,依照该动产在转让时所在地国家的法律(lex situs)确定……动产的转让如果根据该动产被转让时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为有效并具效力,则在英国也为有效并具效力。”(11)因此,本案中伊朗是否享有对文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应当根据伊朗法律判断。
(三)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
本国法院在适用外国法的时候需要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并且在外国法内容有疑义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解释。在英国,外国法被作为事实,通常由当事人提供的专家证人向法官出具对该外国法的证明。(12)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各自聘请的伊朗法律专家当庭出示了对伊朗法律的证明。原告的专家证人为原伊朗德黑兰大学法学教授,被告的专家证人为原伊朗律师,均常年在英国从事伊朗法的服务工作。
双方对伊朗法律的内容并无异议,但对该法律的效力产生了分歧。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伊朗法律尤其是1979年的《法令》是否赋予了伊朗政府对文物的国家所有权。原告的专家证人认为,原来属于伊朗国王并构成国家遗产的文物,根据该项法律都归伊朗共和国所有。而被告的专家证人则认为,根据伊朗民法典,文物的所有权归发现者。一审法官认为,伊朗法对此问题并不存在权威的司法解释或学理解释。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问题提供的证明相互矛盾,法官必须审查双方专家证人所引用的法令条文的效力以便在二者之间确定谁是谁非。一审法官Gray最终接受了被告方专家证人的见解,驳回原告观点。(13)
二审法官对此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本案涉及对伊朗法律的解释问题。对于伊朗法律是否赋予伊朗政府对文物的国家所有权,不能根据英国法或其他外国法对所有权概念的定义,而应当依据伊朗有关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来确定。如果伊朗法律赋予伊朗政府对有关文物的权利相当于英国法中的所有权(ownership),那么从冲突法角度来看,英国法就应当将该权利作为所有权对待。因此,对英国法院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伊朗政府根据伊朗法律所享有的权利能否依据英国法律提起一项变更之诉。二审法院对伊朗的各项法律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虽然伊朗1979年的法令没有明确规定伊朗国家对文物的所有权,但如果对该法令内容进行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对于发现的文物,除了国家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所有权人。(14)
三、外国文物保护法在内国法院的效力
(一)对外国公法的“承认”和“执行”
如果根据文物来源地国家的法律,原告拥有对文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此种所有权或占有权的法律基础,即外国的文物保护法,能否被法院地承认或执行。由于各国文物保护法大都规定有刑事或行政强制措施,往往被认为具有公法性质。所以此类案件就牵涉到冲突法上的外国公法的适用问题。
传统的冲突法理论认为,一国法院不能适用外国的公法。但二战以后,随着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相互融合,公法的域外适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并引起各国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分歧。(15)在英国,戴西著作中的规则3(1)明确规定:“英国法院没有管辖权去受理一项其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执行(enforcement)外国刑法、税法或其他公法的诉讼。”(16)该书认为,一个国家的法院不执行外国的刑法和税法是一项公认的普遍原则。根据基斯(Keith)大法官的观点,执行外国公法上的请求是对外国主权的扩张,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领域内主张主权权力,因此是违反独立主权的概念的。(17)
然而正如戴西在该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该项规则仅涉及对外国刑法、税法或其他公法的“执行(enforcement)”,但并没有禁止英国法院去“承认(recognition)”外国公法。(18)如何区分“执行”和“承认”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法律问题。根据上述规则,执行包括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直接执行是指外国国家或其代理人直接根据其公法获得财产或利益。(19)而间接执行很难定义,只能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它通常是指一个外国国家或其代理人试图获得赔偿,但并非直接基于某项外国公法,而是事实上使得该国公法获得了域外效力;或者某个私人当事人依照某项外国公法提出抗辩从而为该外国的权利开脱或辩护。但是,间接执行与承认也往往难以区分。法官在个案中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外国公法的判断
在英国,法院不能仅仅依据诉讼的性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来判断某项法律是否属于公法,而必须根据所涉及的外国法律本身的实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20)也就是说,一项外国法律即使不属于外国刑法典的一部分,或者是在民事诉讼中所援用的一项外国法律,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刑法、税法或公法。同理,一项包含有刑事制裁条款的法律,并非其所有其他条款都是刑事法律条款。比如在Schemmer v.Property Resources Ltd案中,英国法院拒绝承认根据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指定的一位财产接受人的权利。英国法院认为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一项刑事法律。但实际上该证券交易法虽然规定有刑事制裁措施,但根据该法任命的财产接受人是为了保护和挽回公司财产而规定的,与刑事制裁措施无关。(21)
至于“公法”到底包括哪些法律,英国上院终审法院并没有权威解释,只能根据个案由各法院具体判断。通常,英国法院拒绝执行的外国公法包括外国的进出口管制法、对敌贸易法、外汇管制法、价格管制法、反托拉斯法、国有化和没收充公法等。(22)
(三)外国文物保护法的性质:奥提兹案确立的先例
外国的文物保护法是否属于上面提到的“公法”,这涉及对文物保护法性质的判断。在1984年英国法院审判的新西兰诉奥提兹案(以下简称奥提兹案)(23)已经确立了一项先例,即外国的文物保护法属于公法,在英国不予执行。
该案中,新西兰政府试图追回一件从该国被非法出口的珍贵文物毛利人雕刻。该雕刻被著名收藏家奥提兹(George Ortiz)购买收藏。奥提兹现准备将其委托给索斯比拍卖行进行拍卖以便支付他女儿被绑架的赎金。根据新西兰1962年的历史文物法,(24)未经允许而被出口到外国的历史文物将被没收归国家所有。新西兰政府于是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将该雕刻返还新西兰政府。被告提出两点抗辩:第一,新西兰法律规定的没收并非自动生效的,除非该文物被新西兰政府扣押,而本案中文物并不在新西兰政府控制之下;第二,新西兰的该项法律不能被执行,因为它是一项刑事法律或公法。一审法官施托顿(Staughton)支持新西兰政府的请求,认为:第一,根据新西兰法律没收是自动生效的;第二,该法律并非刑事法律,并且也不存在不执行外国公法的一般标准。
在上诉判决中,施托顿法官的判决被推翻。上诉法官之一丹宁(Denning)爵士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新西兰法律规定的没收并非自动生效;第二,该法律是一项公法,而公法是不能被执行的。丹宁法官重申:“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即我国法院不会去接受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提出的请求,直接或间接地去执行该外国的刑法或税法。我们不会去替外国收税或去替它实施惩罚。”(25)本案中新西兰政府根据其文物保护法主张获得该项雕刻文物,如果满足新西兰政府的主张,就意味着对新西兰公法的“执行”。丹宁法官的结论是:“……如果某国的立法禁止艺术品的出口,并规定如果它们被出口则自动将其没收归国库所有,那么该项立法就属于‘公法’类型,它不会被出口目的地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执行,因为它是一项目的在于执行主权权力的法律,不应在其本国领域外得到执行。”(26)另两位上诉法官艾克那(Ackner)和奥康纳(O'Connor)进一步认为,新西兰的该项法律是刑事法律,因此新西兰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建立在一项刑事请求权基础之上,是不能得到执行的。(27)在终审法院,布莱特曼(Brightman)爵士支持了上诉审判决,并补充说:“我倾向于认为,对于非法出口的历史文物的追索,只有当其所有权不是通过没收的方式归于国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28)
奥提兹案遗留下一个仍待解决的问题,即支持新西兰政府的诉讼请求到底是“执行”了新西兰的文物保护法还是仅属于对新西兰文物保护法的“承认”问题。丹宁和其他上诉法官均将其识别为“执行”,故驳回了新西兰政府的请求。
(四)巴拉卡特案:新规则的诞生
1.承认伊朗的权利不属于执行伊朗的主权权力
伊朗主张其拥有所有权和直接占有权的基础是伊朗1979年的《法令》,而被告认为该《法令》属于刑法和公法,在英国法院不具有可执行性。伊朗政府对此提出两点抗辩:第一,外国某项法律赋予外国对其境内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该项权利应当在英国得到承认,即使该项法律属于刑法或公法;第二,伊朗所依据的法律并非刑法,就算它属于公法,在公共政策上也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它不能在英国执行。(29)
一审法院采纳了被告的观点,裁定伊朗1979年《法令》首先是一项刑事法律,其目的在于保护国家遗产;其次该法令是一项公法,英国无法执行。
对此,伊朗向上诉法庭提出以下几点主张:1.1979年的有关条款并非刑事法律;2.对待外国公法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看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特定的公共政策理由促使该项法律不能在英国得到执行;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不应当被认为是该类公法;4.任何情况下,如果某外国国家根据财产所在地法律获得了财产的所有权或直接占有权,并且该财产不允许被私人所拥有,则其所有权应当得到承认和执行而不管该国家是否占有该项财产。(30)
二审法院分析了戴西著作中的规则3(1),并结合上文提到的奥提兹案,认为一审法官的判断是错误的。二审判决指出,伊朗1979年法案尽管大部分是刑事条款,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其他所有条款都是刑事条款。其他有关文物所有权的规定就不是刑事条款,它们不具有溯及力,不影响此前已经合法存在的文物所有权;它只是修改了法律中有关尚未发现的文物的所有权的规定,将其所有权赋予国家,而给与发现者一定的奖励。这些条款并不是刑事条款,以此为由驳回原告请求权是没有道理的。二审法院接着分析了英美国家和法国的多起案例,(31)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外国政府提起的诉讼请求不能被执行的惟一理由除了刑法和税法的原因之外,仅在于该诉讼请求包含了对外国主权权力的执行或维护。没有任何一项判例显示存在这样一条规则,去禁止所有外国公法的执行。(32)
法院指出,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法院主张其财产的所有权,不属于主张主权权力;在这方面国家和一个私人的地位是一样的。戴西著作中的规则128也强调了这一点:“对任何动产或不动产的私人财产权产生影响的政府行为将会被英国承认为有效,只要该行为根据该行为生效之时的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为有效并具效力,仅此而已。”(33)对于该项规则,戴西著作中进一步解释说:“规则128的效力在于财产所有权的转让将被承认,因此如果外国国家对财产进行了处置,新的所有者的权利将被英国承认以对抗原所有者。但如果原所有者仍占有该财产并将其带往英国,情况则更复杂。此时所涉及的就不是承认问题,而是执行问题。如果外国的该项处置法令具有刑法性质,则无论是该外国政府还是其代理人均不得执行一项依照该法令成立的权利,因为存在着‘一项国际法规则规定,一个国家不能执行……另一个国家的刑法’。但如果该项法令既非刑事法律,也不违反英国的公共政策,情况则更复杂……如果该外国已占有该财产,则毫无疑义应当保护其对该财产的实际占有权,只要它已获得可予承认的权利”。在著名的科威特航空公司诉伊拉克航空公司案中,Nocholls爵士也重申:“根据英国冲突法原则动产财产权利的转让通常取决于财产所在地法:该动产在被转让时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同样,政府影响私有财产权的行为也会被英国法院承认为有效,只要它们根据法律生效时该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为有效。”(34)
但如果外国国家通过没收或查封的方式剥夺私人财产,则该国家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只有在其实际占有该财产的情况下才会被英国承认。在针对Princess Paley Olga v.Weisz案(35)所做的评论中,F.A.Mann发表如下观点:“苏俄政府没收了Paley Olga公主的珠宝首饰。这些珠宝首饰位于俄国境内,根据俄国法律其所有权已经转移。但假设该珠宝首饰仍然被公主占有并被公主带往英国,如果俄国政府在英国提起一项返还之诉,则该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因为俄国的真实目的在于执行其国家的主权权力。相反,假如俄国政府已经占有了该批珠宝首饰,而该批珠宝被盗往英国境内,此时俄国政府在英国提起一项返还之诉则应当获得支持,即使盗窃珠宝的人就是该批珠宝首饰的原始所有人也不例外,因为俄国政府对该批珠宝首饰的所有权因占有而得以成立。此时英国法院支持俄国的诉讼请求并非是执行俄国政府的没收法令,而是执行一项在其后发生并且与其无关的诉因。”(36)
但是在本案中,伊朗政府主张的所有权并非基于它对私人财产的强行征收,而是基于它对伊朗国家文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是基于一项具有30年历史的法令而成立。这是一项财产权之诉,而非执行外国公法或主张国家主权的诉讼。因此它跟上面讲到的那些案例类型都不相同,不能归入任何一类。因此不能说,由于伊朗政府没有实际占有该批文物,所以其权利主张不能被英国法院执行。
2.承认伊朗的权利并不违反公共政策
二审法院最后还探讨了公共政策问题。法院认为,承认伊朗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英国的公共政策。相反,本案中如果驳回伊朗的诉讼请求反倒是违反公共政策的。法院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各国之间应当相互协助以阻止国家文化财产的非法流动。国际上已经缔结了多项有关这方面的公约。2002年,英国也批准了1970年联合国《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并自2002年11月1日起生效。迄今为止该公约已经有100多个成员国,而伊朗早在1975年就已加入。美国则于1983年颁布《文化财产实施法案》将该公约纳入美国法律。英国2003年的《文物(非法)交易法》[The Dealing in Cultural Objects(Offences)Act 2003]规定了对非法转移文物的行为进行刑事惩罚。根据该法,不管盗掘文物的行为是在英国还是在他国进行,也不管该行为触犯的英国法律还是其他国家的法律,都受该法约束(第2(3)条)。欧共体委员会1993年《关于归还从成员国领土非法流失的文物的指令》(37)也已于1994年3月2日经《1994年文物返还条例》(38)转化为英国法律。根据该条例,文物流失国有权针对该非法流失文物的占有人或持有人提起诉讼。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也通过了《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并于1998年生效,伊朗是其缔约国。英联邦也曾于1993年在毛里求斯达成了一项协议,彼此承认对文物的出口管制。(39)尽管上述国际协议对法庭均没有直接约束力,但它们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趋势。
最终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驳回了一审判决,承认了伊朗政府根据其文物保护法所享有的所有权。(40)
四、结论和启示
(一)海外诉讼的方式是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一种有效法律途径
近年来,我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追索流失境外的文物,其中最主要的通过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我国政府积极参加了四个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1月22日加入)、《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89年9月25日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7年3月7日加入)和《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99年10月31日加入)。(41)但是,这些公约都有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文物收藏大国)都不愿意加入这些公约,因此公约对它们没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多数公约都只适用于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非法出口到该国境内的外国文物,对于之前已经存在于该国境内的文物不发生影响。尽管中国加入上述公约时特别声明保留对历史上流失文物的追索权,但该声明仅是单方面的,在国际法上对其他国家不产生效力。从近几年我国政府通过国际公约途径成功追索非法走私文物的案例来看,索回的文物多为近年来因盗墓、盗窃等非法途径走私到国外的文物。通过国际公约的方式很难使那些历史上流失海外的国家文物回归中国。(42)本案例提供了通过在文物被发现地国家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还文物的法律途径。这样一来,即使文物被发现地国家没有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也可以通过该国国内法的途径收回相关文物。
从国际上看,通过海外诉讼方式追索流失文物越来越得到有关国家的配合。在德国柏林高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例中,埃及政府要求德国法院颁发紧急命令,阻止一批埃及文物从德国被出口到美国。(43)埃及政府是根据其本国文物保护法主张自己为该批文物所有者的。虽然法院没有满足埃及提出的请求,但并没有否定埃及文物保护法的效力,而是认为埃及政府无法证明在该文物保护法生效之日,该批文物位于埃及境内。在德国石勒苏益格州高等法院处理的一起与希腊之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案件中,一位定居在德国的希腊籍男子继承了其父位于希腊的房地产,他在该地产上发现了一批古代钱币并将其携往德国。德国法院满足了希腊方面的请求,将该批钱币运往希腊作为在希腊提起的刑事诉讼的证据。根据1959年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的规定,(44)申请刑事司法协助措施的前提之一是,在申请国发生的被诉行为根据被申请国刑事法律也是应当被追究的犯罪行为。因此,德国法院同意希腊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就意味着承认了希腊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希腊政府对该批钱币的所有权资格,而被告发现埋藏物隐瞒不报的行为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46条的规定也是违法的。(45)
美国法院也在多起判例中依据外国文物保护法承认了外国对文物的所有权,并依据美国刑事法律对一些文物贩子施加刑事处罚。根据美国“国家被盗财产法”(National Stolen Property Act)(46)的规定,如果明知某物为被盗财产而仍将其卖往或运往国外,该行为为犯罪行为。在判断某物为“被盗财产”时,如果某物被以违反来源国文物保护法的方式运往境外,则也以被盗财产论处。(47)在United States v.Schultz案中,Schultz是纽约的一位成功的艺术掮客,被控贩卖一批埃及文物。其行为违反了美国国家被盗财产法。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根据埃及法律的规定,所有在1983年之后在埃及被发现的文物均归埃及政府所有,因此埃及政府是该批文物的所有权人。(48)该判例承认了埃及依照其文物保护法享有的文物所有权。
(二)完善国内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是追还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前提
通过巴拉卡特案可以看出,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伊朗法律对文物所有权的规定如何解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所采纳的解释不同,判决结果就完全相反。故此,完善我国国内文物保护法是海外追索流失文物的法律基础。我国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所有权的规定虽然规定得很详细,但仍存在一些模糊之处,比如在修订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把修订草案第5条第3款修改为:“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境内出土的文物;……”,但最后文本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限制,由此引发一个问题:我国国家所拥有的可移动文物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到底如何确定?我国解放前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是否归国家所有?如果法律不做出明确规定,一旦发生类似于本案的跨国诉讼,外国法院在解释我国文物保护法时就会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法理断定我国国家对出土文物的所有权仅限于《文物保护法》生效之日以后出土的文物。
同时,虽然我国法律确立了出土文物的国家所有原则,但如何具体落实国家所有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比如,我国流失海外文物众多,如果需要到海外起诉追回,中国政府出面作为原告是否合适?巴拉卡特案和其他国外类似案例中都是由文物来源国国家政府出面作为原告起诉,而我国政府历来都不愿意接受外国法院的管辖。如果政府不出面起诉,到底应由什么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对文物的所有权和起诉权?是由国家文物保护机关还是有关的博物馆或收藏单位?非政府机关出面向外国法院起诉是否符合外国法律?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近来引起轰动的中国民间人士向法国法院起诉要求禁止拍卖圆明园兽首铜像的诉讼,就因起诉主体资格问题而遭法国法院驳回。(49)
总之,伊朗政府诉巴拉卡特案的胜诉一方面让我们对海外诉讼追讨流失文物的前景抱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一定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法律研究,否则,光凭一腔热情是无法解决法律问题的。
注释:
①王成:“中国文物边抢救边流失”,《法制与社会》,2006年第7期。
②德国:KG Berlin,Urt.v.16.10.2006-10 U 286/05,NJW 2007,705;英国:Iran v.Berend,[2007]2 All E.R.(Comm)132,[2007]EWHC 132,[2007]Bus.L.R.D 65,KunstR Sp 2007,206;在法国,阿根廷政府也起诉Gaia拍卖行,要求其返还一件公元前3世纪的Tafi文化时期的面具,2008年5月27日该诉讼被驳回;参见海尼克:“来源干净也要返还吗?”(Angelika Heinick,Rueckgabe trotz sauberer Provenienz?,FAZ,28.6.2008 Nr.149S.50.)。
③《京华时报》,2009年1月17日第11版报道。
④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the Barakat Galleries Limited,[2007]EWCA Civ1374=[2007]2 C.L.C.994 =[2008]All.E.R.1177.
⑤The Torts(Interference with Goods)Act 1977,Section 7.
⑥帕纳哥珀罗思:“国际私法中的实体与程序”(George Panagopoulos,Substance and Procedur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005,p.69.)。
⑦The Torts(Interference with Goods)Act 1977,Section 7.
⑧变更之诉(Conversion)是相对于返还之诉(Detinue)的一个普通法上的侵权诉因。
⑨《哈斯博瑞论英格兰法》第4版(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4th edition,volume 45,2.);温菲尔德/约洛维奇:《侵权》(Winfield and Jolowicz,Tort,17th ed.2006,p.762)。
⑩科马克:“冲突法中的反致、识别、定位和先决问题”(Joseph M.Cormack,Renvoi,Characterization,Localization and Preliminary Question in the Conflict of Laws,S.Cal.L.Rev.221,1940-1941,p.243.)。
(11)《戴西、莫里斯和柯林斯论冲突法》(Dicey,Morris and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Ed.Lawrence Collins,vol.1,14.Ed.,2006,Rule 18,para.9-001.)。
(12)同注(11)引书,第24R-001段。
(13)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the Barakat Galleries Limited,[2007]EWHC 705(QB),29.3.2007,para.4.
(14)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the Barakat Galleries Limited,[2007]EWCA Civ1374,para.63-79.
(15)麦克科纳海:“国际冲突法中的公法禁忌的复苏”(Philip J.McConnaughay,Reviving the "Public Law Taboo"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f Laws,35 Stan.J.Intl L.1999,p.255.)。
(16)同注(11)引书,第5-020;Dicey规则3(1)中所提到的“其他公法”来源于Keith所修订的该书第四版(1927年),其中的规则54(第224页)提到“政治性法律”(political law),并援引Emperor of Austria v Day and Kossuth案指出政治性法律不应得到执行。在该书第七版中“政治性法律”的概念才被“其他公法”代替;参见《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七版(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7th ed.,ed.Dr J.H.C.Morris et al,1958,Rule21,p 159);修改的主要原因在于F.A.Mann博士以及Parker法官等人对“政治性法律”的概念提出批判,参见曼:“外国国家的特权与冲突法”(F.A.Mann,Prerogative Rights of Foreign States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1955,Tr.Gro.Soc.25,p.40,reprinted in F.A.Mann,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1973,p.492,at p.500); Regazzoni v K.C.Sethia(1944)Ltd[1956]2 QB 490,at 524。
(17)[1955]A.C.491,511.cf.Att-Gen of New Zealand v Ortiz[1984]A.C.1(CA),at pp.20-21,per Lord Denning M.R.,at p.32,per Ackner L.J.
(18)同注(11)引书,第5-023段。
(19)同注(11)引书,第5-023段。
(20)Huntington v Attrill[1893]AC 150,at 155; Att-Gen of New Zealand v Ortiz[1984]AC 1,at 32,per Ackner LJ.
(21)Schemmer v Property Resources Ltd[1975]Ch 273.
(22)同注(11)引书,第5-033段。
(23)Attorney-General of New Zealand v.Ortiz and Others,[1982]Q.B.349,reversed[1984]A.C.1(CA and HL).
(24)Historic Articles Act 1962.
(25)Attorney-General of New Zealand v.Ortiz and Others,[1984]A.C,24.
(26)同注(25)。
(27)同注(25),第1、34、35段。
(28)同注(25),第49段。
(29)同注(25),第88段。
(30)同注(25),第92段。
(31)Att-Gen(UK)v Heinemann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td(1988)165 CLR 30; President of the State of Equatorial Guinea v Royal Bank of Scotland[2006]UKPC 7; Mbasogo v Logo Ltd[2007]2 WLR 1062; Robb Evans of Robb Evans & Associates v.European Bank Ltd[2004]NSWCA 82,(2004)61 NSWLR 75; Etat d' Haiti v.Duvalier,Cass.civ.I,May 29,1990,1991 Clunet 137,1991 Rev.Crit.386.
(32)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the Barakat Galleries Limited,[2007]EWCA Civ1374,para.125.
(33)同注(11)引书,规则128,第25R-001段。
(34)Kuwait Airways Corporation v.Iraq Airways Co[2002]2 AC 883,1077.
(35)Princess Paley Olga v Weisz[1929]1 KB 718.
(36)曼:“外国国家特权与冲突法”(F.A.Mann,Prerogative Rights of Foreign States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i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1973,p.492 at 503-504.)。
(37)Council Directive 93/7 on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Unlawfully Remov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State.
(38)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Regulations 1994,SI 1994/501,as amended by SI 1997/1719 and SI 2001/3972.
(39)O'Keefe(1995)44 ICLQ 147.
(40)同注④。
(41)黄风、马曼:“从丹麦返还文物案谈境外追索文物的法律问题”,《法学》,2008年第8期,第75页。
(42)参见法制日报有关报道:“相关公约不完善,国际法框架下文物追索仍存难题”,《法制日报》2007年9月24日。
(43)KG Berlin,Urt.v.16.10.2006-10 U286/05,NJW2007,705,707.
(44)Europ? ischen? bereinkommen über di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vom 20.4.1959,BGBl.II 1964,1384,1386ff.
(45)OLG Schleswig,Beschl.V.10.2.1989-1 Ausl.2/89,NJW 1989,3105.
(46)18 U.S.C.§§ 2314,2315.
(47)美国的相关判例见United States v.Hollinshead案,495 F.2d 1 154(9th Cir 1974),该案中,危地马拉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为某些文物的所有者;另见United States v.MeClain II,593 F.2d658(5th Cir 1979),该案中,墨西哥文物保护法规定禁止某些文物的出口;另见 United States v.Schultz,333 F.3d 393(2nd Cir 2003),该案涉及对埃及文物保护法的承认;参见格德贝格:“重申麦克克莱恩案:国家被盗财产法与被掠夺文物的持久贸易”(Adam Goldberg,Reaffirming McClain:The National Stolen Property Act and the Abiding Trade in Looted Cultural Objects,53 U.C.L.A.L.Rev.2006,p.1031);克雷德:“被盗文物上述的民事和刑事救济选择”(Jennifer Anglim Kreder,The Choic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Remedies in Stolen Art Litigation,38 Vanderbilt J.Trans'l L.2005,p.1199.)。
(48)Cf R v Tokeley-Parry[1999]Crim LR 578.
(49)尚栩、郑甦春:“法国巴黎法院今晨就中国圆明园文物追索作出裁决,驳回停止拍卖的诉讼请求”,《新民晚报》,2009年2月24日A17版。
标签:法律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文物论文; 纽约公约论文; 非法占有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文物保护法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