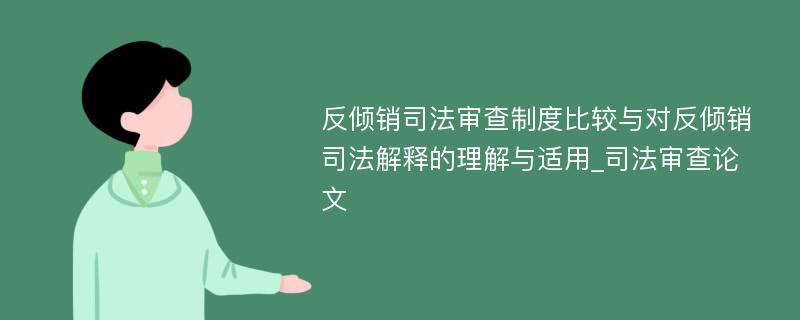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比较 兼谈反倾销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解释论文,司法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法审理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人民法院承担的重要司法审查职责。近期以来,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已受到有关方面较多的关注。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肖扬院长要求“妥善处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等与履行司法审查承诺相关的新类型行政案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姜兴长副院长在总结讲话中对审理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因此,准确地理解适用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搞好反倾销反补贴司法审查工作,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反补贴行政案件与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近似性,本文拟结合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及美国和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仅就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规定》)的理解适用及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审理,谈一些看法。
一、反倾销司法审查概况
由于我国反倾销、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而确立的,在开展此类司法审查时有必要深入了解和密切跟踪世贸组织反倾销裁决以及一些世贸组织主要成员的相应制度的动态。世贸组织有专门的反倾销协定,该协定对司法审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世贸组织成员中,美国、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最为发达和最具影响力。我们在起草《反倾销规定》时,着重研究了反倾销协定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因此,本文以反倾销协定及美国和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对比的对象。
(一)世贸组织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司法审查
反倾销协定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即“国内立法含有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1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种裁决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决或者复审的主管机关。”本条对司法审查的机关、程序等提出了要求。
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职责是由专门法院行使的,即初审法院为国际贸易法院(CIT),上诉法院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国际贸易法院是于1980年创设的专门法院,属于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的法院,对反倾销和反补贴争端和其他国际贸易问题(如进口货物的分类和评估,海关代理人的评估)具有专属管辖权。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判,可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与其他上诉法院一样,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只审查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适当的审查标准问题(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在欧盟(欧共体),对反倾销决定有许多司法救济的途径。首先,可以直接起诉,包括在设在卢森堡的欧盟初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合法性(legality)进行司法审查。其次,可以对成员国为实施欧共体措施而采取的措施提起诉讼。例如,一个进口商请求免除其对征收临时关税的担保,或者返还已支付的最终关税。在这些情况下,起诉人可以按照有关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提起适当的诉讼,并请求国内法院提请欧共体法院对欧共体措施的有效性作出初审裁决。再次,对欧共体主管机关提起诉讼,要求对因非法的反倾销措施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注:"DUMPING AND SUBSIDIES:The Law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Imposi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ird edition),by Clive Stanbrook,O.B.E.,Q.C.and Philip Bentley,Q.C.,Kluwer Law Intemational,p.209.)
(二)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
我国反倾销立法起步较晚。《对外贸易法》(1994年5月12日)率先对反倾销作出原则规定,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1997年3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细化了《对外贸易法》的反倾销规定,但未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实际上对行政决定采取的是行政终局决定制度,排斥了司法介入(尽管行政法规不能设置排斥司法审查介入的行政终局决定制度)。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反倾销条例》第5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即“对依照本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在反倾销条例的起草过程中,有人建议建立独立的复审机关,也曾设想只规定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当时的想法是,反倾销司法审查涉及大量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当一个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决以后,再由另一个独立的、同级的行政机关行使复审权,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反倾销案件利害关系方就裁决起诉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为此另行设立机构、配置人员,有可能导致资源浪费。行政仲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是相对可取的方案。一方面,法院的独立性不容置疑,特别是司法相对于行政的独立性,更能体现公正性;另一方面,如不规定司法审查程序,势必迫使外国企业和政府在对行政裁决不服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还是首先在国内提供这种审查机制为好。但是,《反倾销条例》最后仍然采取了行政复议与司法审查的双轨制。按照我国《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由于相应的反倾销决定都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的,利害关系方不服该决定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的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就只剩下不可兼得的选择,即要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么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而国务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具有可诉性。
由于我国以前缺乏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经历和经验,《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也语焉不详,为适应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反倾销规定》,就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主要问题作出了基本的规定。
二、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
(一)反倾销协定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
反倾销协定第1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1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规定是对成员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范围的最低要求,其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确定为两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如有关倾销和损害的最终裁决;另一类是反倾销协定第1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倾销税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者应利害关系方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者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美国、欧盟等成员的司法审查范围,实际上是广于反倾销协定对司法审查范围的一般规定的。
(二)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范围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又译为商业部)是反倾销的行政主管机关,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决定倾销是否给国内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商务部负责计算因倾销活动造成的损害数量。商务部的程序类似予美国其他行政法领域的行政程序。调查是应有关外国竞争对手的存在倾销的国内生产者的申请而启动的。(注:申请成功的门槛实际上很低,只要求列举生产者的成本和相关的进口数据即可。)确定倾销是否存在以及倾销的幅度是高度复杂的,因为这要求详尽的成本和价格数据,其不仅难以获取和证实,而且还必须转换货币和计算标准。(注:See John H.Jackson,Dump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Its Meaning and Context,in ANTIDUMPING LAW AND PRACTICE2-3(John H.Jackson & Edwin A.Ver mulst.,1989);Thomas v.Vakerics et al.,antidumping,Countervailing Duty,and Other Trade Actions 23-193.)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存在着实质性损害,商务部就提出初步决定,并接受利害关系方的评论。在审查评论和进行现场调查后,商务部发布其最终裁决,该裁决为向外国产品征收反倾销(或者反补贴)税的基础。按照美国法律,当事人可以按照实质性证据标准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上诉。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可对两类裁决提起司法审查:1.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即时裁决,包括下列几种:(1)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2)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者实质性妨碍的合理征象的裁决;(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审查基于情事变迁的裁决的决定。2.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包括以下几种:(1)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者否定性最终裁决;(2)由商务部作出的终止调查的裁决;(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美国法典》第19卷§1671c(h)或者1673c(h)作出的损害影响裁决;(4)由商务部作出的有关货品在反倾销令所规定的一类或者一种货品之内的决定。
(三)欧盟(欧共体)反倾销司法审查范围
按照欧共体条约第173条和第174条规定,可以对反倾销措施提起审查和撤销之诉。从判例看,可以提起的反倾销诉讼包括以下几类:对委员会关于不启动程序的决定;(注:Case 191/82,FEDIOL v Commission,[1983]ECR 276.)对委员会关于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条例;(注:Joined Case 239/82 and 275/82,Allie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1984]ECR 1005.)对理事会命令以临时税的方式担保的最终征收数量的条例;(注:Case 113/77,NTN Toyo Bearing Company Ltd.V Council,[1979]ECR 1185;Case C-305/86,Neotype Techmashexort GabH v Commission and Council,[1990]ECR I-2945.)对理事会关于征收最终税的条例;(注:Case 264/82,Timex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1985]ECR849;Case 53/83,Allie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1985]ECR 1621.)对理事会关于终止程序的决定。(注:Case C-129/86,Hellenic Republic v Council,[1989]ECR 3963;see also Case 121/86,E.M.V.N.a.e.and others v Council,[1989]ECR 3919.)
欧盟委员会启动程序的决定不属于欧共体条约第173条规定的意义上的行为。启动程序仅仅是一种准备步骤,其最终可能导致作出可诉的行为。(注:See Cass 60/81,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v Commission,[1981]ECR 2639.)至于反倾销程序中的其他步骤,利害关系人是否可以提起诉讼,仍然值得探讨。例如,消费者联盟欧洲局对欧共体委员会拒绝提供非保密的文件的函件提起的诉讼。法院认为,该信函属于欧共体条约第173条规定的可诉的“行为”(但在该案中以其他理由驳回了起诉)。(注:Case C-170/89,Burean European des Union de Consommateurs vCommission,[1991]ECR I-5709.)
在欧盟,几乎所有的反倾销司法审查都是按照欧共体条约第173条第2款提起的。根据原告资格的不同,其具体类型可作如下归纳:1.就参与反倾销程序的外国生产者或者出口商而言,可以对下列行为请求司法审查:(1)征收临时的或者最终的反倾销税的条例,或者临时反倾销税的最终征收命令。(2)不启动反倾销程序的决定。没有保护行动而终止程序的决定,因接受承诺而终止调查的决定,不审查承诺或者反倾销税的决定,似乎均可接受司法审查。(3)启动程序的决定不能接受审查。2.就申诉人而言,对下列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1)征收临时的或者最终的反倾销税的条例,或者临时反倾销税的最终征收命令。(2)不启动反倾销程序的决定。没有保护行动而终止程序的决定,因接受承诺而终止调查的决定,不审查承诺或者反倾销税的决定,似乎均可接受司法审查。3.就共同体进口商而言,对下列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1)如果共同体主管机构采取的措施要求国内主管机构采取行动,对这些行动可以在国内法院起诉。后者可以或者必须将案件提请欧洲法院进行初步裁决。(2)如果进口商与外国生产者或者出口商有关,或者从原始设备制造商处进口,其可以直接在欧洲法院起诉。(3)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独立的进口商也可以直接起诉。(注:Stefano Inama,Edwin Vermulst:Customs and Trade Law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P.293-294.)
从WTO反倾销协定和美国、欧盟反倾销法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来看,可以提起司法审查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具有最终效力的行为(裁决或者决定),如不启动反倾销程序的决定、有关最终反倾销税的决定或者复审决定等,而临时的决定或者裁决(如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决定)一般不具有可诉性。其原因可以用行政法上的“问题适宜于法院裁判原理”(即美国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或者成熟标准)进行解释。(注: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第642-651页。)就反倾销司法审查而言,反倾销行政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初裁程序、终裁程序和复审程序。由于初裁程序是中间性程序,初裁决定不适宜司法审查,因而WTO反倾销协定和各国反倾销法一般不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而终裁决定和复审决定均属于最终决定,应当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四)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
按照我国《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1.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反倾销终裁决定。无论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还是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依照《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这些反倾销决定主要有:(1)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国务院主管部门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2)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国务院主管部门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反倾销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国务院主管部门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性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反倾销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下列两种情形并存的,可以对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之前90天内进口的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但立案调查前进口的产品除外:一是倾销进口产品有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倾销历史,或者该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口经营者实施倾销并且倾销对国内产业将造成损害的;二是倾销进口产品在短期内大量进口,并且可能会严重破坏即将实施的反倾销税的补救效果的。(3)是否退税的决定。国务院主管部门终裁决定确定的反倾销税,低于已付或者应付的临时反倾销税或者为担保目的而估计的金额的,差额部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退还或者重新计算税额。终裁决定确定不征收反倾销税,或者终裁决定未确定追溯征收反倾销税的,已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应当予以退还。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已经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超过倾销幅度的,可以向外经贸部提出退税申请;外经贸部经审查、核实并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可以作出退税决定。(4)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进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在调查期间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该产品的新出口经营者,能证明其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经营者无关联的,可以向外经贸部申请单独确定其倾销幅度。外经贸部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并作出终裁决定。
3.国务院主管部门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作出的复审决定。依照《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的决定,或者外经贸部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价格承诺的决定。
从我国《反倾销条例》上述规定来看,有关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决定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像诸如临时反倾销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均不属于司法审查之列。正是基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反倾销条例》的上述规定,《反倾销规定》第1条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反倾销行为规定如下:“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对下列反倾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三)有关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前三类行为显然是与《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相对应的,第(四)项则是留有余地,防止遗漏那些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反倾销行政行为。
三、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
反倾销行政案件当事人的确定,问题较多或者难度较大的主要是原告资格的确定。当然,还存在被告和第三人的确定问题。
(一)反倾销协定及美国和欧盟的原告资格
一般而言,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起诉资格。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1款规定:“就本协定而言,‘利害关系方’应当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外国生产者或者进口商,或者其主要成员为此种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者进口商的贸易或者商业协会;2.出口成员的政府;3.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者在进口成员的领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主要成员的贸易或者商业协会。上列规定并不排除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的其他当事方作为利害关系方。”本条规定了利害关系方的最低范围,且其并不排除成员规定比该范围更宽的利害关系方。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倾销(或者补贴)终裁裁决或者实质性损害终裁裁决时,利害关系人(interested parties)可对这些裁决寻求司法审查。按照美国法典§1677(9)(1994)的界定,利害关系人包括被调查的外国生产者、外国政府、美国同类产品的生产者、被认可的代表生产同类产品的美国工人的联盟以及同类产品生产者的行业协会。
按照欧共体条约第173条规定,成员国具有起诉包括反倾销措施在内的任何措施的原告资格,但迄今只有一个成员国曾就反倾销程序提起诉讼。(注:Case 129/86,Hellenic Republic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1987]ECR 1189.)欧共体委员会和理事会也具有原告资格,但其角色往往是维护其反倾销措施。成员国、理事会和委员会属于“特权原告”(privileged applicants),因为其原告资格来自于其地位,而无需在案件中证明其特别的利益。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订欧共体条约第173条之后,议会和欧洲中央银行也属于特权原告,但其眼下对反倾销案件不会有太大兴趣。
在欧盟,任何其他原告要想具有原告资格,必须证明其为反倾销决定所采取的措施针对的当事人,或者反倾销决定所采取的措施与其有实体上的直接和个人的关系(direct and individual concern,也可以译为“直接的和特殊的关系”)。在确定原告资格时,主要涉及下列问题:
1.生产者和出口商。在Allied案以前,出口商必须证明基于案件的具体事实,存在着出口商与征税条例有直接和个人关系的特定事实。(注:E.g.Case 113/77,NTN Toyo Bearing Company Ltd v Council,[1979]ECR1185.)但是,在Allied案中,法院认为,对于能够确定其与措施相关或者与公共调查(public investigation)有直接关系的当事人,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就会与其有直接的和个人的关系。其法律效果是,完成问卷调查和参加现场调查的任何出口商,都具有原告资格。而且,主管机关采取的做法,就是在条例中将被调查者称为出口商,并决定各个出口商的倾销幅度。其结果是,由于Allied案的判决,出口商提起诉讼的数量有相当大的增加。当然,案件必须由出口商提起,而不能由其他人提起,如不是调查对象而只是真正的出口商与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渠道的中介公司。(注:Case C-75-75/92,Gao Yao v Council,[1994]ECR I3141.)但是,生产者或者出口商不能阻止反倾销程序的终止,因为此种决定不能认为对其法律地位有不利影响。(注:Case C-229/86,Brother Industries Lt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1987]ECR 3757 at 3761.)
2.进口商。就进口商而言,其可以援引Allied案的规则。但是,只有其涉及的商品的零售价格被用作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而与出口商产生联系时,才赋予其原告资格。(注:See also Neotype Techmashexport v Commission and Council,[1990]ECR I-2945 at 2998,recitals(17)and(20).)在Allied案中,进口商Demufert是一家进口商的代理商,在调查之中非常积极。法院认为,这并不足以使其具有原告资格。自此以后,基于独家进口商而主张提起诉讼的地位,一直未获成功。在Neotype Techmashexport GmbH v Commission and Council案中,原告的销售并未被用以确定出口价格,但被作为相关的进口商。法院认为,在该案中它们具有必要的原告资格,因为其与出口商有关,作为其结果,其转售价值被用以评估作为计算反倾销税根据的关税价值。除上述适度的扩展以外,在1991年Extramet案以前,法院拒绝承认独立进口商的原告资格。在Extramet v Council案中,法院深入到“原则的精神的深处”,改变了大多数以前的判例中的严格裁决。在详述严格的条件之后,法院指出:“对特定类型的贸易商提起撤销反倾销条例的权利的此种承认,不能阻止其他贸易商也主张因对其特有的和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定特征,而与其有个人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满足这种标准的因素和特征是:“原告是成为反倾销措施对象的产品的进口商,且同时是该产品的终端使用者。此外,其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进口,并且,因相关产品的制造商的数量有限以及其从唯一的一家共同体生产者获取供应的困难,而受到了被指控的条例的严重影响。”基于该案,很显然非关联的进口商可能有权提起撤销之诉,但必须取决于各个个案的事实。
3.申诉人。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中,申诉人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地位,显然有权对拒绝启动程序提起诉讼。在Fediol v Commission案中,法院裁决认为:“条例承认因非成员国的补贴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对于欧共体启动保护行动具有合法利益(a legitimate interest)。它必须因而承认,它们享有条例赋予它们的法律框架内的诉讼权。”(注:Case 191/82,Fediol v Commission,[1983]ECR 2913,para.31.)在该案中,Fediol寻求撤销欧共体委员会对申请人发出的关于不启动反倾销程序的通知。申诉人也具有挑战欧共体主管机关终裁裁决的地位。但是,这是否可以作为一般原则,并不清楚。申诉人似当然可以提起撤销诉讼,有时单个经营者(an individual undertaking)也可以如此。就单个经营者提起撤销诉讼而言,除其必须在启动申诉中具有重要作用外,似乎还要求条例必须以某种方式基于该单个经营者提供的材料。例如,在Timex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案中,(注:[1985]ECR 849.)机械表行业领头的制造商在反倾销程序中处于重要地位,“反倾销税就是根据对Timex的影响确定的”,因而其具有起诉资格。
4.消费者。消费者在撤销程序中似不具有原告资格。尽管现在的程序允许消费者提供证据,但其地位仍然无足轻重。
(二)我国反倾销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确定
在起草《反倾销条例》过程中,有些草稿曾规定“有关利害关系方如不服本条例范围内具有最终效力的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同时将利害关系方界定如下:“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外国生产商或其大部分成员为该产品生产商、出口商或出口商的贸易或商业团体;2.出口国政府;3.进口国相似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大部分成员生产相似产品的贸易或商业团体。外经贸部尚可根据情况将上述以外的其他当事人作为利害关系方”。但是,最后通过的《反倾销条例》第53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其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出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显然是与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1款的规定相对应的。因此,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概括地说,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享有诉权的人是那些参与反倾销行政程序的利害关系方。例如,按照该条例第13条规定,申请人是指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
根据反倾销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特殊性以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精神,《反倾销规定》第2条对原告资格问题作出了下列规定:“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我国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与第三人
《反倾销规定》第3条对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作出了规定:“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例如,对倾销和倾销幅度的终裁决定提起的诉讼,由作出裁决的外经贸部为被告;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提起的诉讼,由国家经贸委为被告;对征收反倾销税作出的决定提起的诉讼,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为被告。
在起草过程中,对于反倾销行政案件是否涉及第三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诉讼参加人中的第三人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行政诉讼法》规定第三人制度的基本意图或者原因有二,即行政诉讼可能涉及到第三人的权利义务,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前者涉及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后者涉及可以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从反倾销条例的规定看,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时往往涉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部门,如该条例第38条规定:“征收反倾销税,由外经贸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由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必须以外经贸部的建议为根据,在起诉征收反倾销税决定的诉讼中,外经贸部显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让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便于对其建议行为进行审查。何况,《反倾销条例》规定的诸如此类的建议、会商等程序,均属于外化的法定程序,而不是内部程序。据此,《反倾销规定》第4条规定:“与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里规定有关部门可以而不是必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参加诉讼取决于个案之中的必要性。而且,在反倾销行政诉讼中如果还涉及其他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还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认定。
四、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是指法院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和程度。如何界定审查标准,直接涉及如何确定法院对反倾销行为的介入或者干预的程度。因此,审查标准问题是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在起草《反倾销规定》中着重解决的问题。
(一)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
美国将国际贸易案件的审查区分为推倒重来的审查(de novo proceeding)和上诉型司法审查(an appellate-type judicial review)。前者是由法院像审理初审民事案件那样进行司法审查,而后者是像审理上诉案件那样由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案卷记录进行审查,不重新听取证言和收集证据。反倾销司法审查属于后者,且既审查事实问题,又审查法律问题。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的审查标准是,如果行政机关的决定“缺乏记录在卷的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就认定其非法。对于因没有充分调查而终止调查程序的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武断、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或不符合法律规定”。(注:Putrick C.Reed:"The Role of Federal Courts in U.S.Customs & International Trade Law",Oceana Publications.INC,p.252,254.)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516A(b)(1)(B)条对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是:“对于缺乏记录在卷的实质性证据支持,或者违反法律的……任何决定、裁决或者结论,法院应当认定其非法”。(注:美国法典第1516A(b)(1)(B)条(1994)。)这种标准被称为“尊重的法定审查标准”(a deferential statutory standard of review)。该审查标准包括两个部分,即“记录在卷的实质性证据”(substantial evidence on record)和“依照法律”(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前者界定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解释和作出决定的理由的尊重程度;后者界定法院对行政机关解释相关法律的尊重程度。
尽管最高法院在其他行政法领域对这种标准进行过解释,(注:See,e.g.,Chevron,U.S.A.,Inc.V.Natural Resourses Defense Council,467 U.S.837,843(1984)150.Id.at n.11(该案界定了法院对行政机关解释法律的尊重程度);Universal Camera Corp.V.NLRB,340 U.S.474,477(1951)(该案界定了实质性证据标准).)但国际贸易法院对应当给予商务部多大程度的尊重,在做法上并不一致。审查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有两种选择,即要么维持行政机关的决定,要么予以撤销。法院能够告诫行政机关如何行事的程度,取决于审查标准。(注:See,e.g.,KENNETH C.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ES§29(2d ed.1984).)如果法院适用了不正确的审查标准,就会损害判决的实体价值,因为立法机关已决定,法院不适合以其判决取代行政机关的决定。(注:“任何(审查标准的)公平运作,最终都有赖于高度称职的司法、司法人员和对其工作的见多识广的评论。”Universal Camera Cor.V.NLRB,340 U.S.474,489(1951).)
审查事实所适用的实质性证据标准是由经典判例Universal Camera Corp.V.NLRB案界定的。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作出了经常被引用的解释:“(实质性证据)并不是一点点(scintilla)。它是指一个合理的人可以认为其足以支持一项结论的相关证据。”(注:Universal Camera Corp.V.NLRB,340 U.S.474,477(1951).)该解释为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多个判决所引用。按照该标准,国际贸易法院并不以其推理取代行政机关的推理,而是应当尊重行政机关,只有在行政机关不能说明其决定的合理基础时,才对其决定提出质疑。尽管有此界定,国际贸易法院适用该标准时,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和案件事实的不同而采取不同态度。最高法院甚至在Universal Camera案中承认,“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方法可以为形成确信提供根据,但不能确保适用的确定性。”(注:Universal Camera v.NLRB,340 U.S.474,488(1951).)其结果,每当国际贸易法院审理一个新案件时,就必须首先决定其对行政机关的实际尊重程度。
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有关制定法的解释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按照法律开展调查时,商务部必须解释反倾销法律。在Chevron,U.S.A.,Inc.V.Natural Resourses Defense Council,Inc.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在行政机关解释制定法时,“如果对特定问题未作规定或者含糊不清,法院面临的问题就是决定行政机关的回答是否为可允许的制定法解释”,(注:Chevron,U.S.A.,Inc.V.Natural Resourses Defense Council,467 U.S.837,843(1984)150.Id.at.n.11.)并在注脚中另外指出:“法院无需得出结论,行政机关的解释为其可以予以支持的唯一解释,甚至如果最初在司法程序中遇到该问题,也会得出该解释。”简言之,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解释的尊重类似于其对行政机关事实裁决的尊重。(注:See,e.g.,Koyo Seiko v.United States,36 F.3d 1565,1570(Fed.Cir.1994);Smith-Corona Group Consumer Producers Div.,SCM Corp.V.United States 713 F.2d 1568,1571(Fed.Cir.1983).)
(二)欧盟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
在反倾销诉讼中,欧盟法院很注重司法自限,基本上是作法雄审查而不是事实审查。在许多反倾销判决中,欧盟法院就其对反倾销决定所适用的审查标准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在NMB案中作出下列阐述:(注:Case T-162/94,judgment of 5 June 1996,ECR 1996-4/5,p.Ⅱ-456.)“基本的反倾销条例是由理事会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13条采纳的,就是说作为一般商业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的一部分。正如初审法院已指出的……一般商业政策的特征是共同体立法机关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保障其实施所必须的。在本案中这种自由裁量必然扩展这些基本条例的采纳和修改。面对实施反倾销行为的多种选择……,理事会在起草该条例时必须在多种利益之间进行调和。”“就反倾销行为的范围而言,共同体司法机关的审查必然是有限的,其目的是决定共同体立法机关采取的措施就其追求的目标而言是否……显然不适当。”而且,欧洲法院反复指出:“主管机关享有广泛的裁量余地,司法审查必须限制在认定其是否发生显然的评估错误或者滥用其权力。”
在受理案件以后,欧盟法院需要审查欧共体委员会的行为是否非法,或者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实施的行为是否非法。欧共体条约第173条规定的实体审查理由如下:1.没有能力;2.违反基本程序要求;3.违反条约或者有关其适用的任何法律规则;4.滥用权力。例如,在Japanese Ball Bearings案中,法院以超出理事会的立法权限为由,撤销反倾销税。在此案以后,欧盟法院仅仅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3条规定撤销六起反倾销税。在前五起案件中,欧洲法院以程序或者准程序的原因,撤销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例:没有为申诉人提供维护其利益的足够的证据:没有指出理事会已考虑征收更少的税足以消除损害;(注:Case 53/83,Allied and others v Council,[1985]ECR 1621.)没有尊重被告方的权利;(注:Case C49/88,A1-Jubail Fertilizer Company and Saudi Arabian Fertilizer Company v Council,[1991]ECR I3187.)没有确定主要的欧共体生产者遭受的损失是否是因为其拒绝向一家加工进口商供应所导致的;(注:Case C-358/89,Extramet Industries A.A v Council,[1992]ECR I3813.)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启动了审查程序;(注:Case C-216/91,Rima Electrometalurgia v Council,[1993]ECR I-6303.)在第六个案件中,欧盟初审法院撤销了因事实错误而征收的反倾销税,且对其调查期限超过正常的12个月的期限而未说明理由。(注:Cases T-163/94 and T-165/94,NTN Corporation and Koyo Seiko Co.Ltd v Council,[1995]ECR Ⅱ-1381.)
(三)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
1.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审
由于反倾销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倾销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审,存在着不同的做法和认识。例如,欧盟法院基本上采取的是法律审,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司法审查通常都是同时坚持事实审和法律审,只是有时又对事实审与法律审适用了稍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如在事实的审查上对行政机关有更多的尊重,而在法律的审查上有更大的裁量权。而且,法院的审查标准与法院本身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例如,美国等国内法院,其享有的是固有的司法权,即其权力范围是固有的(分权体制当然确定或者自动产生的),只要是案件或者争端(cases and disputes),法院都享有管辖权,或者说都属于法院管辖的范围,而像欧盟法院这样的区域法院,其管辖权来自于区域组织的法律的明示或者默示授权,而不是固有的司法权,因而在司法审查的程度上受更多的限制。例如,欧盟法院就是因为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外贸政策领域,而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司法审查有着很强的自限(自我约束)。
我国有关部门在起草反倾销条例时,曾对法律审还是法律与事实同时审,进行过讨论,如曾在草稿中出现过“诉讼仅限于法律适用和程序问题”。但是,最后通过的《反倾销条例》放弃了这种写法,对审查标准未作明文规定。既然《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标准未作特别规定,这意味着其审查标准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标准。有人认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讲,司法审议仅就反倾销调查与裁决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对实体法方面一般不予涉及”。(注: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知识》,中国经济出版社,第61页。)这种主张显然是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相符的。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其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把该两条结合起来看,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合法性审查,即不但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还要审查事实,而审查事实又是通过审查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和确凿而进行的。这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反倾销司法审查,即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是法律和事实同时审,而不是法律审。而且,这种理解也是与我国法院为国内法院而享有固有的司法权的性质相符合的。正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反倾销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反倾销的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
2.关于对事实的审查标准
由于有关方面对法院的事实审查态度比较关注,《行政诉讼法》对事实审查的规定也不具体,我们在起草过程中着重对事实审查问题作出了规定,这就是第7条、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
首先,确立了案卷审查原则。法院审查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形成的案卷,即“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时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这主要是考虑反倾销行政程序较为复杂和完备,行政机关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时必须形成案卷,而这样规定也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严格遵循“先取证,后裁决”原则。案卷审查原则还意味着法院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类似于上诉审,体现了“复审”的属性,不是对被告认定事实推倒重来,简单地重复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过程,而立足于审查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是否遵守了证据规则。换言之,法院以反倾销主管机关认定的事实为基础进行判断,并以证据规则作为判断的基点。例如,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取证和认定证据的规则和程序,等等。
其次,肯定了最佳证据规则。有关条文规定,“被告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不如实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而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不如实提供证据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能够获得的证据得出的事实结论,可以认定为证据充分”。这些规定主要是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以及我国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相衔接。例如,反倾销协定第6.8条规定:“如任何利害关系方不允许使用或者未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严重妨碍调查,则初步和最终裁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均可在可获得的事实基础上作出。”与该规定相对应,我国《反倾销条例》第21条规定:“调查机关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调查机关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反倾销调查机关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的规则,习惯上被称为最佳证据规则(不同于英美证据法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即作为裁决基础的事实或者证据是不完全的,而这种状况又是由利害关系方妨碍调查导致的,因而反倾销协定和国内法均允许在不完全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裁决。作出此类裁决的证据基础是不确凿的,也即称不上“证据确凿”,但有这些证据就足够了,因而可以称其为“证据充分”。
3.关于法律的审查标准
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应当给予尊重,但尊重的程度可以弱于对事实的尊重。首先,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具有优越性,可以不受行政机关对法律解释的约束。其次,行政机关的解释如果是合理的,法院应当予以尊重。究竟如何把握尊重的程度,可以在个案中通过判例进行探索。
五、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在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对于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一般采取维持或者撤销的判决方式,而并不变更行政机关的决定。对于应当发起反倾销程序而不发起的,责令其发起反倾销程序。
在欧盟,如果能够认定反倾销措施不具有合法性,法院就宣布该措施无效。法院不能修改该措施,因为这将侵犯立法职能。按照欧共体条例第176条规定,对被宣告无效的措施负责的机构,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遵守法院的判决。在撤销一项条例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条例规定某种可以考虑的确定效果(欧共体条例第174条第2款)。在法院撤销反倾销税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认为这只是撤销了调查结果,并未撤销程序。因此,委员会仍然可以继续其程序,获取最新材料并征收新的反倾销税。(注:Case C-16/90,Detlef Nolle v HEA Brewen-Freihafen,[1991]ECR I-5163.See also Case T-21 95R,Industries des Poundres Spheriques v Council,Order of 24 February 1995.)从欧盟法院的判例来看,法院实际上排除了获取中止反倾销税的禁令的可能性。(注:Pierre Didier:"WTO Trade Instruments in EU Law(Commercial Policy Instruments:Dumping Susidies Safeguards Public Procurement)",Cameron May,pp.184.)同样,它实际上还排除了对启动程序的起诉(注:Dyson Magnetics v.Commission,case T-134/95,order of 14.3.1996,ECR 1996-1/2/3,p.Ⅱ-183.)和获取损害赔偿。(注:Blackspur DIY and Others v.Council,case T-168/94,judgement of 18 September 1995,ECR 1995-9,p.Ⅱ-2627,confirmed on appel(case C-362/95 P,judgment of 16 September 1997,ECR 1997-8/9,p.I-4775,Srr also Detlef Nolle[ref.cit].)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反倾销规定》第10条对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判决方式作出下列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三)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作出的其他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