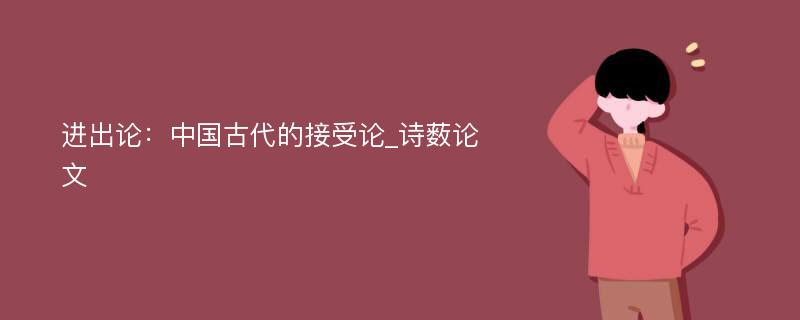
“出入”说——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古代虽然缺乏西方阅读现象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那种系统的文学接受理论,但却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接受思想与接受经验的描述,“出入”说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理论思维的高度对之作出梳理与总结,将不难发现其内在的逻辑与条理。首倡“出入”说的是南宋人陈善,他说: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得读书之法。[1]从陈善论说的思路看,他是将“出”摆在首位的,“出”比“入”更重要,只有善“出”才能用得灵活透脱,融会贯通。而“出”又是以“入”为前提的,无“入”则无“出”。后来王夫之又从创作与接受关系的角度对此作了辨析:“欲除俗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然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涂说耳。”[2]王夫之比陈善的认识进了一步,他并不将“出”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真正的“入”总是与“出”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心入古文中”去悉心体察,感发己心,融贯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是“以古文填入心中”,死记硬背。由此可知,陈善与王夫之所理解的“入”是指读书时要善于进入作品境界,用心体验作品内在神韵与作者为文之用心,缩短与作品和作者的心理距离。“出”是指不被作品所局限,跳出作品的圈子,多方拓展思路,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将作品精神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从而有益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表面字句的相同或相似,就可发现陈善与王夫之倡导的“入”书法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推崇备至的极为普遍的文艺接受方法,它不仅存在于文学阅读领域,而且存在于绘画、音乐等艺术接受领域。首倡“入”书法的虽然是陈善,然其基本思想却源远流长,可以溯至先秦时期。古代文人认为“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艺术素养。文艺素养是接受者在长期的审美实践活动中养成的文艺接受能力,它来源于以前的审美实践活动,又对以后的审美实践活动起制约作用,是影响文艺作品价值能否变成现实的重在条件之一。汉代典籍《淮南子·泰族训》中说:“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存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没有师旷那样能辨识音律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毫无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唐代柳宗元在充分感受自然山水之美的基础上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3]的重要观点。自然山水具备美的属性与条件,当它作为纯客观的存在物未与人发生关系时,尚不成其为美,只有与具备审美能力的人遇合时,其潜在的美质才会彰显出来。柳宗元这里说的是审美主体与自然山水的审美关系问题,但却从侧面肯定了文艺接受活动中接受主体的艺术素养的重要性。
除了一般的艺术素养之外,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更注重接受者的艺术才能,即深通文学创作之道。批评家们有感于经生空凿附会、胶柱鼓瑟的说诗方法,用诗外之物去牵强比附作品,从中发掘出道德政治主题,用繁琐的考据、章句之学去索解作品的微言大义,不知诗而说诗,指出不知诗的根本原因在于不作诗,缺乏作家的创作才能,“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得作诗者之意也。”[4]接受者不懂得对象的特殊性,当然不可能切入作品去体察作者之意。文论史上较早提出接受者要有艺术才能的是曹植,他指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议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也提出“操千曲而后晓声”的著名观点。接受者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成为对象的知音,发现作品的价值。宋代刘克庄直截了当地指明说诗者必须是诗人,“诗必与诗人评之。……不习于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显得大而无当;不得要领。这是因为“作与识原是一家眷属”,[6]作与识作为文学活动的两翼本来就是彼此呼应、互通声气的。作家创作出作品并不是文学活动的终结,他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需要接受者来完成,因而接受者的艺术才能就至关重要了。具体地说,接受者只有具备了与作家基本相等的艺术才能,双方交流的渠道才会更趋畅通,而不会妄加猜度,空华目翳,才会准确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向,“得作诗者之意”。同时,又能通畅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了悟作者实现创作意向的一切艺术手段。金圣叹描绘作者创作苦心时说,作文者“真是将三寸肚肠,直曲折到鬼神犹曲折不到之处,而后成文”,[7]接受者对此若有深切体验,就可能进入作者的创作过程,设身处地,对作品的曲折处与关捩点独有会心,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向。
在具备艺术素养与才能的基础上,接受者的艺术心境与审美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对此论述最为详备的是庄子,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生的艺术化与审美化,人生追求“道”,而“道”必须以“心斋”和“坐忘”的虚静之心才能求得。庄子认为达到虚静之心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对各种生理感官欲念的超越和对个人得失与功名利禄之心的罢黜,获得心灵的自由,达到“游”的艺术境界;二是对知识判断的超越,消除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从一切习惯的圈子中跳出,产生一个虚以待物的开放的“自我”,诞生一片灵虚不昧的审美心境,映照群类,引发万有,对人生世相作审美的自由观照。
庄子的虚静观对中国古代的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澄怀味象”的观点,强调以空明澄澈之心去品味自然之灵趣,畅怀神游,得到精神的超脱。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艺术家观照自然时,凝神结想,情思邈邈,同自然的节奏与生机妙然契合。苏东坡认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8]“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9]作家必须先有如古井水之心,才能了纳群动,映照万象,体验宇宙无穷生机。近代学者林纾在《春觉斋论画》中认为观画的心理应是“神澄气定”,与宗炳等人的观点一绪相承。以上这些说法虽然不是特指文学接受的心态,但那种不疾不徐、悠然从容的心理准备无疑也适合于文学接受。
要达到虚以待物的接受心境,首先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中国古典式的书斋环境,洁净雅致,有名花奇石相伴,清风朗月作陪,很宜于接受心境的形成与培养,接受者独坐其中,暂时脱离尘世的喧闹与纷争,澄思渺虑,达到心灵的自由。其次是接受者面对作品,在作品的初次打动下产生惊奇感,进行自觉的心理调节,将纷繁的思绪收回来,凝聚于作品,形成定向注意。用陆机的话说,就是“收视反听,耽思旁讯”。波兰的罗曼·英伽登将此称为审美活动正式展开前的“预备情绪”,他认为,“预备情绪”的出现“首先中断了关于周围物质世界的事物中的‘正常的’经验和活动。在此之前吸引着我们,对我们十分重要的东西突然失去其重要性,变得无足轻重。我们会停止(虽然这停止可能是短暂的一瞬)正在进行的活动……。”[10]“预备情绪”的产生标志着接受者从现实世界向审美世界的靠拢与过渡,接受者产生特定的审美心境后,人生经验、审美潜能与艺术才能被纷纷激活,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品味与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此时,作品再也不是接受者的异己物,两者的距离逐渐缩小,审美关系已经确立,构成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情感交流关系。
古代文人认为进入作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涵泳”与“玩味”的无声接受方式,注重悉心揣摸与反复咀嚼,如嚼橄榄,如品香茗。“涵泳”这一概念由朱熹率先提出,他认为诗的“语言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诗人话底意思也。”[11]诗的意象是一个活的整体,内部有血脉贯通流转,而读诗之人须反复涵泳感受,才能领悟到贯通整体的内在血脉,如果引外来道理对诗进行分解,必然破坏作品的艺术生命,感受不到诗人的真正意思。与此同时,朱熹认为读诗要“玩味义理,咀嚼滋味。”[12]强调接受者细腻感受的重要性。清代况周颐对此认识更为深入,“读诗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往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13]接受者以空明之心,充分调动艺术想象,通过语言的揣摸去创造作品的意境,沉入其中,思而得之,感而契之。
其二,与“涵泳”和“玩味”的无声接受方式相补充的是“熟读”与“讽咏”的有声接受方式,通过反复的吟咏讽诵逐渐悟入作品。明代胡应麟曾将文学作品分成“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两个层面,他认为,“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14]前者是作品的表层形式,有迹可循,能进行规范化的分析,是进入作品内部的立足点和突破口;后者是形式所暗示的意蕴与旨趣,不可坐实,具有不确定性,它依附于形式而存在。这就决定了读者只能在“熟读”和“讽咏”中通过语言的节奏、声调与韵律去领略它。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方识《离骚》。”“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15]沈德潜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16]都说明了读者按照作品语言的节奏、声调去高吟低唱,紧咏慢吟,从而领会到作品的妙处与味道。桐城派散文家对此有更深入认识,刘大櫆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低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17]读散文之法,重在音节揣摸,摸透了音节,也就把握了作品内在风神;因此桐城派极力标举高声诵读,诚如姚鼐所说:“大抵学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久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
无论是无声的接受方式,还是有声的接受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领会作者的旨趣与作品的神韵,需要接受者以己之心参与作品的创造,为此,古代文人又推出了“以意逆志”的观点。“以意逆志”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一种具体的接受方式,而是贯穿于各种具体方式之中的一般接受原则。“意”是接受者的思想情感,“志”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的体现,“以意逆志”是接受者从自己主观感受出发,通过想象去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正如朱熹《孟子集注》中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中国古代的接受者对此有较深入认识,梅尧臣的“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的观点就强调了要以己之“意”去领会作者之“心”;王夫之说,“读古人文字”须“以心入古文中”,才能得其神髓,他还提出了“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务以其情遇”[18]的文学接受观,高扬了读者的主体性,承认了读者可以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去理解作品,不一定要与作者之意相合。王夫之结合切身体验对其作了阐发,“尝记庚午除夜,兄待先妣拜影堂后,独行步廊下,悲吟‘长安一片月’之诗,宛转欷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谓,及后思之,孺慕之情,同于思妇,当其必发,有不自知者存也。”[19]李白的《子夜吴歌》中“长安一片月”写的本是少妇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了“孤凄忆远之情”,但王夫之长兄却借此抒发对先妣的哀思之情,与作者“一致之思”不尽相合,但却合情合理。
“以意逆志”是以心合心,敞开心胸去接纳作者心胸,达到彼此融洽的接受境界,否则,作者之心就会永远密闭于形式中,成为不可知的神秘之物。清代浦起龙对此感受尤深,他介绍了解读杜诗的经过,堪称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经典表述:
吾读杜十年,索解于疆,弗得;索解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心印杜之心,吾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20]
以杜解杜和于百家诠释中解杜就是在字句上下功夫,不注重心灵契合的感悟。一旦以心入乎其中,思而得之,感而契之,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就会由碰撞而产生交融,作品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
接受者通过对作品的“涵泳”、“玩味”、“熟读”、“讽咏”,以己之“意”迎取作者之“志”,逐渐缩小与作品的距离,达到与作品的深度契合,进入了“妙悟”的境界。首倡“妙悟”说的严羽将它视为一个过程:
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21]
严羽这里本是谈诗歌创作之道,但与文学接受的内在规律相通。“妙悟”是反复“熟读”与“讽咏”后的豁然贯通与心领神会,是悉心酝酿”后的自然融入和审美超越,正所谓“熟读玩味,自见其趣。”[22]“读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将通之,不落言筌,自明妙理。”[23]就像一位攀登者突然发现一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象,又如“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发现,接受者饱览奇观,精神高度自由愉悦。罗曼·英伽登认为这种境界能“使我们产生一阵新的强烈情绪,这种情绪现在真的成了一种快感,由眼前的景象所引起的喜悦和安逸,——一阵‘沉醉’——就像沉醉于浓郁的花香中一样。”[24]“妙悟”又是读者与作品的深度契合,“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25]胡应麟认为,“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机。”[26]从一般的审美玩味突然上升到触发心灵的真髓,读者内在的至情至性被唤醒,他盛赞王维的诗“读之令人身世两忘,万念俱寂,”[27]心灵融入作品,涤尽尘埃。金圣叹谈到自己读《西厢记》时,“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可迷,迷人于此可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28]完全被作品所控制,我之情即作品之情,作品之情即我之情。胡应麟与金圣叹的描述还告诉我们,在强烈的审美经验的后期,读者完全中断了对现实世界的注意,萌发了“忘身”、“忘时”的感受,尤其是缺乏现实时间意识而沉醉于审美时间中,在“妙悟”的霎那间仿佛进入永恒,过去与未来完全消融于现时顷刻的凝神观照中。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了“高峰体验”这一概念,他认为“高峰体验”是一种剧烈的同一性感受,“自我有可能迷醉于对象,或完全‘倾注到’对象中,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29]“在这里,两个极端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30]他并且认为,“在高峰体验时,个人最有此时此地感,在各种意义上最能摆脱过去和未来,最全神贯注于体验。”[31]很显然,胡应麟与金圣叹所说的“忘身”、“忘时”的沉醉正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当读者消除了自身的偏狭与局限,全身心地投入作品的境界时,就会暂时摒除一些陈规陋习,摆脱功利是非的控制,按作品的规定情境重新塑造自己,就能获得精神的超越,创造一个更纯粹更真实的自我。
二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出”和“入”是相互补充、彼此推进的。“入”是立足作品,“进入作品,“出”是跳出作品,善“出”者必善“入”。
“出”要经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基本阶段是“入”中之“出”,接受者在感受和体味作品的过程中从作品中跳出,能使感受与体味更加深邃,它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方法。第一是“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补充,孟子又提出了“知人论世”,前者是“入”书法,后者是“出”书法。中国古人非常注重联系作者人品来考察作品,注重作者人格修养与作品的内在关联,所谓“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中国古人又认为“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32]而要得诗人之心,除“知人”外,还要善于“论世”,知晓作者的创作境遇和创作之心产生的原因。吴乔的认识十分深入,“问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读《着新旧唐书》、《通鉴》、稗史、杂志,乃能于作者知其时事,知其境遇,而后知其诗命意之所在。”[33]作者的创作心境不会孤立产生,而是受到一定客观情境的影响而萌发的,如果接受者知晓这一情境定会对进入作品大有帮助。“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接受方法,并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以意逆志”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清代黄子云的认识比较全面,他说:“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34]推测作者境遇是与审美吟咏彼此加强的,且伴随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如果脱离了对作品的细致体察,专事材料史实的堆积,“知人论世”不但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会破坏作品的艺术特质。
“出”是接受者立足于审美感受向作品之外的辐射,这种辐射不仅要射向作者其人及其创作境遇,而且要射向与读者相关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读者在作品情境的激发下,性情骀荡,思绪万端,从作品的艺术域联想到相关的生活域,其思维程序是“入”——“出”——“入”。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了他接受杜甫诗的心理过程:
余顷年游蒋山,晚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恍然如己语。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
平日读诗,在案头书房,就作品读作品,所“入”不深,一旦走出作品,即景会心,就会豁然开朗。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凝聚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因此古代作家极为注重“诗外”功夫的修炼;同理,读者生活阅历的多少深浅也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感受,脱离生活经验的纯粹字句解读是难以领会作品真谛的,正如清人张潮所说:“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35]读者只有跳出作品,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才能最终进入作品。
“出”的第二阶段是“入”后之“出”。接受者在第一阶段通过“入”与“出”的互补,领悟到作品内在的生气与旨趣,达到物我同一的高峰体验,受到作品的控制,失去了距离感,这就决定了读者不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自己的审美感受,品评作品的高下得失。要对作品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品评,读者必须与作品拉开一定的距离,适当调节自己的接受心境,不为情绪所囿。何坦说得好:“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弈者惑,而旁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置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36]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何坦说的并非特指文学接受,但却恰当揭示了读者走“出”作品,以静观动的心理特征。当读者情绪亢奋,全身心置于作品时,是难以对作品作出公允的判断与分析的。即以金圣叹论,他在“悟入”《西厢记》的妙境时,产生了“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的强烈感受,但如果他不知“出”,是不会有那么多发人深省的评点的。所以王国维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进入作品,才能感受作品源源不断的生命,批评才不会苍白乏力;走出作品,才会有高情至论。
三
“出入”说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既包容了文学接受方法,又体现了文学接受的具体过程。接受者以艺术素养和艺术才能为基础,以特定的接受心境介入作品,通过“涵泳”、“玩味”、“讽吟”、“熟读”以及“知人论世”等接受方法去“以意逆志”,渐次悟入作品,达到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然后又调整情绪,拉开距离,对作品作出艺术的品评,构成了一个自我调节的文学活动系统。这一接受理论同西方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相比,也是独具特色的。第一,在重视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兼顾了作者的地位。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就充分反映了接受者对作者创作意图与创作境遇的重视,这就与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对作者的轻视,孤立接受作品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在重视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没有忽视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对读者的制约。中国古代文人推崇“得意而忘言”、“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接受方法,注重“言外意”、“境外境”、“味外味”的感受与捕捉,读者不能受语言的限制,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去把握那语言文字之外的“意”与“味”;同时又注重对作品语言文字的推敲与品评,认为“言外意”、“境外境”、“味外味”的捕捉须以“言内意”、“境内境”、“味内味”的玩索为基础,相当全面与辩证。而接受美学,尤其是读者反应批评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受作品的语言文字规定,由读者的阅读经验所决定,这就不适当地夸大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第三,“出入”说注重了“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辩证统一,较为科学地认识到了文学欣赏过程中的一系列规律,且将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熔于一炉,这也是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所不及的。总之,“出入”说贯穿了对作者、作品、读者这三者关系的全面认识,不偏执于某一端,洋溢着中国古代以“中和”为主的美学精神,从整体上把握了文学接受中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活动过程。它虽然不及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那种片面的深刻,但却更为全面和辩证,完全可以弥补其不足。
(发稿:解正德)
注释:
[1]陈善《扪虱新语》上集卷四,《读书须知出入法》条。
[2]王夫之《姜斋诗话》上卷。
[3]柳宗元《邕州柳申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4]项世安《项世家说》卷四。
[5]刘克庄《跋刘澜诗集》。
[6]张晋《达观堂诗话》卷四。
[7]金圣叹《第六才子书》。
[8]苏轼《送参廖师》,《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山色》。
[9]苏轼《送参廖师》,《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山色》。
[10]英伽登《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第52页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朱熹《答何叔京》。
[12]魏庆之《诗人玉屑》第267页。
[1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14]胡应麟《诗薮》。
[1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16]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17]刘大櫆《论文偶记》。
[18]王夫之《姜斋诗话》上卷。
[19]王夫之《石崖先生传略》。
[20]浦起龙《读杜心解》。
[21]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22]杨载《诗法家数》。
[23]薛雪《一瓢诗话》。
[24]英伽登《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第52页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5]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26]胡应麟《诗薮》。
[27]胡应麟《诗薮》。
[28]金圣叹《第六才子书》。
[29]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中译本第286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30]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中译本第83页、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中译本第83页、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2]吕东莱《诗话拾遗》。
[33]吴乔《围炉诗话》。
[34]黄子云《野鸿诗的》。
[35]张潮《幽梦影》卷上。
[36]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