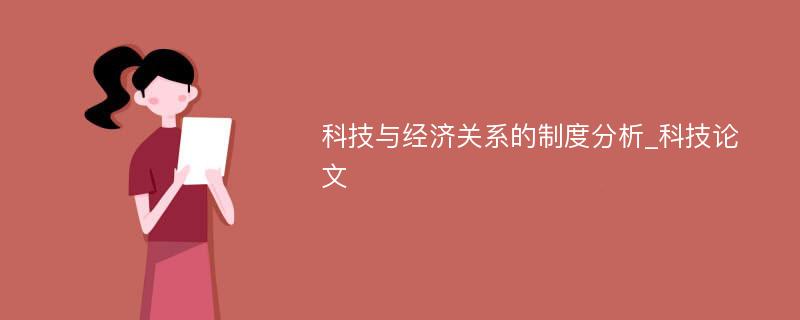
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制度论文,科学论文,经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G301文献标识码:A
1 “科技情结”
技术创新问题在我国被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 是基于下述考虑〔1〕: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在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差,其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的相互分离,因此,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架设连结科技与经济的“桥梁”,以形成“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技术创新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与方法:从“科技”的供给方即“科技界”看,我国创新问题的症结在于科研工作缺乏市场导向,科技的有效供给不足,因而需要使科技工作者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从“科技”的需求方看,企业对科技的需求不足,因而需要增进产业界的有效需求;从科技和经济的结合看,要强化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最终达成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使之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
上述“问题意识”,无疑是对我国国情的真实反映和深刻认识,因而就成为了我国科技与经济体制改革以至技术创新研究的强大推动力量。创新研究已随之成功地把“创新”推向主流话语。但是,在这种认识和“话语”的背后,还暗含着两种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观念:其一,科学与技术不分的观念。关于创新的讨论总是把科学和技术当作一个事物即“科技”加以讨论,很少有人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科学与技术的差别。例如,在西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无疑都是企业,而当人们把“技术进步”一词转换为“科技进步”,把“技术创新”一词转换为“科技创新”,并力求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间作出区分的时候,科学与技术间的关系不见了。其二,总是想从抓科技入手解决创新问题的观念。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然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甚至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只要抓住了科技,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政府要抓第一生产力,抓高科技,要从抓科技入手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同时,掌握科技的“科技界”要发挥特殊作用。基于这种看法,人们最为关注的是“科技界”的科技成果转化,使创新研究往往带有过分浓重的“科技推动型”色彩。
对此,研究者已经或多或少感到了问题的存在〔2〕。应该说, 这两种观念业已沉淀在社会意识的底层而不被质疑,成为一种“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科技情结”。这种情结至今仍在无意识地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力。
于是,上述创新研究的问题意识和两种需要反思的观念,便共同构成了我们创新研究的一种认知图式:在科技不分的观念下试图解决科技与经济分离的问题;以“从抓科技入手”的观念为指导推进体制改革,并试图从整体上追求“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这里,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要突破旧的认识、改革旧的体制时,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不知不觉地沿袭了旧的认知-行为模式?其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科技情结”说到底,是不是还是一种“计划情结”?
本文旨在对科技情结进行反思,试图展示出另一种思考我国创新问题的可能方向。
2 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建构的中西比较
我们看到,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国人对科学与技术的混淆深表痛惜。物理学家吴大猷认为,中国创用“科技”一词是很大的不幸。李慎之深表赞同,也认为混淆科学与技术,害处极大,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3〕。邹承鲁则敏锐地指出, “科技”一词主要是指,有时则完全指的是技术,而很少指科学:在一些场合中,政府领导提到“科技”,几乎一成不变地意指这个词的后半部分。即使在提到基础研究的不多场合中,指的也是基础性的技术科学〔4〕。他们所关切的是,科学与技术的混淆伤害了科学。其实,尽管技术似乎得到了分外的重视,它也并非没有受到这种混淆的伤害。我国技术创新开展不力就是一个明证。
尽管有上述讨论,但从总体上看,相对于西方学者对科学与技术间关系的持久争论,中国学界显得颇为沉寂。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者都不清楚科学与技术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别,而有可能表明,在当下的场合,他们认为辨析这种差异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学术界即使讨论这一关系,也是“对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论述较多,对科学与技术的差别讨论较少”〔5〕。 所谓“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的见解更趋于淹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中西有如此不同的关注方向?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对科学与技术的混淆有着悠久的文化根源。正如李慎之所言:“中国学术从发韧之始起讲的就是求善之学,一切都从应然出发,又归结于应然,实然是不大考虑的;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一切都从实际出发,又验证于实际,其学术原动力乃求知的好奇心。”〔3〕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他所指出的下述现象——本世纪初,国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科学与技术,到本世纪末,反而模糊起来了?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和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不同传统。其实,与中国固有的实用科学(技术)传统相反,西方科学产生于哲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自主于技术-生产活动。近代以来,西方科学逐步成为了独立的知识活动,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即公共科学的出现,标志着自主的科学场域的形成。另一方面,西方的技术传统既然同样是一种工匠传统,它就不能不在经济的“摇篮”里成长。到19世纪后期,伴随着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产业科学体制,它使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拉近了,从而为经济场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持久的动力。随后,公共科学和产业科学体制彼此互补,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走的是不同的路径。近代中国对科学的引进,主要是基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考虑。尽管不乏倡导“求真”的学人,但我们对技术的渴望注定要压倒对科学的追求。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计划体制的形成,面对着威胁民族生存的外部压力,科学技术研究的军事、政治和实用导向进一步增强,几乎所有的科研都成为技术性的了。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关于社会的理性建构观不无关系。我国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原初构想,就是试图通过计划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下述“合理”分工:科学、技术、生产、销售等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分工承担,以实现理想中的专业化经济效益,同时避免市场竞争的无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这样,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生产力”,其投入和产出均由国家统一控制,从而成为独立于企业的一个系统。尽管这一构想正在改变,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条块社会结构依然存在,“计划科学”的观念仍然挥之不去。面对“科技”一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一现实,人们最为关注的首先是如何消除科技与经济间的鸿沟,而非界定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技”一词才应运而生。可以说,人们究竟是否区分科学和技术,不只是认识问题或概念使用的问题,而且也是实践的问题。
就技术与经济的关系而言,西方的技术发展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是具有自主性的经济场域的核心职能。技术史家康斯坦(E.W.Constant)指出,技术共同体和技术传统是技术进步的首要场所,而技术共同体通常所指的就是特定类型的企业群体——“标准工业分类代码是共同体结构的良好指南”,“每一高技术都由几家企业所形成的可辨识的实践者共同体所主宰”〔6〕。 这可以说是西方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研究者的共识之一。相比之下,我们愿意承认企业是或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却似乎不准备承认企业也是或应该是技术知识生产的主体,我们在乎的是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因此,中西的差异不在于技术是否重要以及为什么要发展技术,而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去发展技术,在于谁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体;不在于科学、技术与经济间是否存在某种制度性分工,而在于这种分工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使然,是尊重社会的自然演化,还是理性地对社会进行全盘建构。
总之,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建构具有其观念的和制度的现实背景。正是观念的和制度的因素彼此呼应、相互加强,最终建构出相应的“科技”话语。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西在关于这一论题的“话语”中所体现出的差异,可以进一步揭示出科技情结的制度基础。在西方,这种争论的焦点是科学/技术(经济)的关系;而在中国,争论的焦点在于科技/经济的关系。前者不大在乎技术与经济的差异;而后者不在乎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在西方,争论的制度背景是科学场域中的学术研究和经济场域中的产业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公共科学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争论的制度背景则是“科技界”主导的科技进步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西方,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私有企业越来越愿意投资科学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还要资助公共科学?〔7 〕在中国则只能提出下述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首先发展科技,经济能发展吗?在知识经济时代,若“科技界”没有高效率的知识供给,企业技术创新能有后劲么?我们如何去找到中介性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科技界的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
正因为存在着制度结构/认知图式的差别,对西方社会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中西学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双方所关注的确属不同的问题。
3 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中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间的差异是结构性的,两者确是在质上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活动体系。从科学到技术,也决非一个线性的增长过程,而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跃迁〔5〕。不过, 要真正把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思考。我们认为,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是由社会建构的。只有把科学和技术置于社会诸场域之中,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它们。
布迪厄(P.Bourdieu)最先把场域(field)的视角引入社会分析之中〔8〕。从场域的观点看, 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的争斗空间,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和资本形式,其运行方式与评价尺度迥然异趣。如果说,经济场域的基本要素是商品与货币的话,那么科学场域中的基本要素就是科学发现和承认。如果说科学研究也有“市场”导向的语,那就是面向由科学场域所建构出来的学术需求,而决非经济场域的市场需求。
这样,分别位于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中的公共科学和产业科学遵从的是不同的实践逻辑〔9〕。 公共科学一般由大学以及其他由公共资助的研究组织来从事;产业科学通常由工业实验室来从事。前者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个人职位的获得靠的是体现在著作发表中的对知识的贡献,科学家所受到的惟一约束是其研究结果将受到严格的同行评议;后者受到雇主的明确强制,除少数例外,产业科学家通常不大能够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也不能完全随个人意愿发表研究成果。尽管近年来这两种文化开始走向某种程度的融合,但是西方科学制度的总体构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表1 场域中的科学和技术
科学 技术
科学场域 Ⅰ
Ⅱ
经济场域 Ⅲ
Ⅳ
基于上述考虑,可以把科学和技术置入场域之中加以理解。表1 表明,科学、技术既存在于科学场域之中,又同时存在于经济场域之中。科学(Ⅰ)和技术(Ⅱ)构成所谓的公共科学,而科学(Ⅲ)和技术(Ⅳ)构成所谓的产业科学。但科学(Ⅰ)是科学场域的目标,技术(Ⅱ)是科学场域达成其目标的手段,它或者由科学家自己开发,或者取自经济场域。技术(经济)(Ⅳ)乃是经济场域的目标,科学(Ⅲ)则是其达成目标的手段,它或者来自科学(Ⅰ),或者得自经济场域的R&D活动。如果说在科学场域中所有的技术工作都为了科学,那么在经济场域中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有技术的指向性。所以在特定场域中,区分科学和技术也就不十分必要了。
那么,科学(公共科学)与技术(产业科学)如何关联呢?作为对线性模式的替代,普赖斯表明,科学倾向于建筑在老的科学上,而技术倾向于建筑在老的技术上,其间存在着微弱的相互作用,这主要发生在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接受教育期间。随后他进一步指出,研究工具是科学与技术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10〕。其它研究也证实,科学场域中发现的知识和研究工具,主要是通过教育、出版、非正式交流网络传播到经济场域的。
那么,如何激励知识的生产呢?在经济场域中,知识尤其是明言知识确实具有相当的非独占性,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把其知识基础转化为人工制品或服务,才能赢得经济利润。然而在科学场域中,由于用共同体的学术评价替代了经济场域中的商业计算,知识的非独占性问题消失了〔7〕。
4 结论:走向公共科学与产业科学的分化
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要传达某种真理,毋宁说是要展示另一种思考方式。本文表明,科学、技术和经济间的关系是由社会建构的;我国既定的制度安排参与建构了一种“科技情结”。这种认知图式注意到了社会诸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但并没有意识到社会诸场域之间的可分解性和彼此的不可化约性;这种思路十分契合于在我国扎根已久的“理性建构”观以及凡事诉诸于国家控制的“计划”习性。由此,认知的/制度性的结构形成一个强大的转换机制,它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经济场域履行的功能翻译成中国“科技界”所要履行的职能;倾向于把西方社会的民间行为转换成我国的国家行为。结果,不仅科学受到了伤害,技术创新的期望也屡屡落空。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反思并转换这种思维定式,才可能找到解决我国创新问题的可行的制度解。
我们认为,解决我国创新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在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架设桥梁尤其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架桥,而在于通过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促成产业科学与公共科学的分化。产业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为企业和私人的技术创新服务,而公共科学则为公共目标服务。只有实现两者的分化,才可能一方面保证公共科学的资源投入和研究效率,真正为国家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保证产业科学的效率,使其真正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动机。要走向这种分化,要害问题与其说是靠国家的力量在场域间重新配置研究资源(因为表面上看是技术在场域间的错置),毋宁说是通过制度创新,造就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自主性形成的制度条件,因为只有经济场域具有了自主性,产业科学才能生成并具有活力;只有科学场域赢得自主性,才能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科学发展局面。
收稿日期:200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