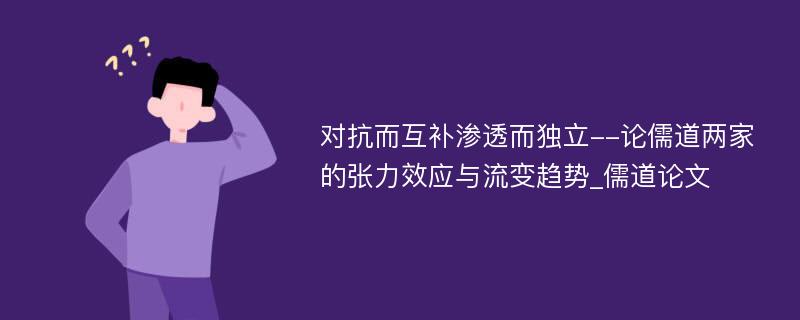
对峙却互补 互渗但独立——论儒道文化的张力效应与流变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态势论文,效应论文,独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作为主流文化,以其两峰对峙、各竞风流与终始衔接,“若环之 无端”的对立而统一的流变态势,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
儒道文化,首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横向并列关系的比较中。儒道文化的对峙 首先是通过在朝的正宗式庙堂文化与在野的异端式山林文化而体现出来的,这渊源于古代中 国特殊的“国情”。
古代中国有两大特点,一是自然型的小农经济,一是血缘宗法纽带,由此决定了必然要建 立一个以自然经济与血缘纽带为支柱的宗法农业社会,这一社会自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按分层隶属原则而构成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学说。
儒家文化以维护宗法关系及其等级秩序、确定和限制封建特权、调节宗族内外矛盾,即维 护“礼教”为其中心内容。儒家文化在其文化流变中,一方面给统治者提供了最佳的“治世 良方”,另一方面又给被统治者巧妙地铸就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为历代的封建统治 集团做了最忠诚的服务,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在朝的正宗式庙堂文化的典范 。
有正宗,就会有异端;有在朝的“庙堂文化”,就必然有在野的“山林文化”。道家文化 便是在野的“山林文化”的杰出代表。据史志记载,道家起源于史官,正是这种职业的博古 通今的历史教养,才使其在深观社会矛盾运动、冷静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对世俗的政 治和权力之争产生厌倦,而自愿或被迫从统治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跳出来,而由史官变为隐 者,再从一部分隐者中发展出道家学者群。[1]由于与现实的权力斗争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隐者——道家们因而有较多机会接触现实,了解民众的疾苦,所以便成为时代忧患意识和社 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并以其超越尘俗、贵己养生、任其自然的仙风道骨,形成了与儒家文 化相对峙的道家文化传统。
作为在朝的“庙堂文化”,儒家文化自然当具大雅之风度;而作为在野的“山林文化”, 道家文化堪称大俗之典范。而二者的旨趣却大相径庭:前者虽为“大雅”之正宗,却不遗余 力地建构面向世俗人生,即注重由雅过渡到俗,实现雅俗共赏的层次效应模型;[2]后者身 为大俗,反以凡俗为大忌,自始至终都强调形下应不断向形上升华、提炼,直至超凡脱俗。 真 可谓,俗到极处便是雅,雅到极处反成俗。
由于儒家文化以“合礼”为最高境界,而“礼”作为社会理知的集中体现,所包含的仁义 礼智,忠孝节义等内容,无一不是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提供所必需的清规戒律。因此,从 学 礼、行礼到合礼,都是为了过好现实的人生,为了与社会理知“合模”。因此就需要也能够 使这种关注现实人生的儒家文化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营造出 最广泛的“过好俗世生活,关注现实人生”的社会共鸣效应,使“天子意识”一步步贴近“ 下民意识”,呈现出上尖下宽的由上而下的“金字塔”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赞 誉儒家思想家,尤其是孔孟之大儒具有“贤人作风”。
相反,由于道家文化以“达道”为其理想境界,而“道”又以超越日常经验,同时又以神 秘地主宰着万事万物的形式而存在着,因此,“达道”只能是在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世界超 越之后才可望完成。也就是说,只有以一种超越世俗生活层面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直觉或智慧 ,才能学“道”,行“道”,而后达“道”。为此,道家文化才建构了“向心式返真系统” , 使“达道”这一理想追求,通过仙话的意象化,环境的建筑化,仪式的氛围化,参与的信奉 化,经典的暗示化,修炼的体悟化等若干环节,一步步深化,一层层提炼,由表及里,由人 及己,从而呈现出结构上的下宽上尖的由下而上的金字塔走向,形象地展示了对日常生活的 超越与作人性异化的逆向运动之形下向形上的运动规律,从而充分体现出以沉思、超脱为主 要形式的“智者气象”。
正是因为关注现实人生与超越世俗生活之旨趣上的“贤人”与“智者”的对立,所以,在 人生态度上才存在着“入世”的积极有为,与“出世”的清静无为之差异。
儒家大师们认为,“修身”、“齐家”,终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通过十年寒 窗之苦读,是为了换取一朝金榜题名之荣耀。为此,人就应积极有为,为了实现“人下人” 向“人上人”的转化就必须不断地拼搏与奋斗。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儒学大师才动用了各种 文化设施,力图在全社会营造出积极有为、与社会理知合模的文化氛围。
道家文化推崇的人生态度则不然。道家大师们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婴儿、赤 子虽柔弱却纯真可爱,且一天天长大,最具有生命的活力;水,看似柔弱,攻坚强者却非它 莫属,且以其处众人之所恶,反而能“几于道”。而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可见,“坚强者 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3]“柔弱胜刚强”。[4]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以“反者 道 之动”为其规律,因此,“弱者道之用”才是为人处世、齐家治国、悟真达道的法宝。这里 所说的“弱”,即指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即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积极有为正相 反对的自然无为,柔弱清静。“弱者”,本是人的原初真实的本性,只是因为人在后天的社 会习俗的包围中逐渐舍弃了它而使其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就表现在人们为了满足 不断膨胀的贪欲(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而变得日益坚强与有为起来,以便能在社会的 激烈竞争中,通过奋力拼搏去达到功成名就,于是离本然之柔弱、清纯的本心就愈来愈远, 直到最终丧失殆尽。因此,欲求“放心”,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绝圣弃智、超凡脱俗 ,直到脱胎换骨的修炼,进入一尘不染、一念不生的境界时,才能返朴归真,复到人性的本 然。可见,“达道”要求人们必须采取清静无为、柔弱不争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只有清 静无为、 柔弱不争的人,天下才莫能与之争,因此也就最有资格“几于道”,以实现“达道”之理想 ,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真谛之所在。
经过严格的“他律”,实现自觉的“自律”,最终达到与社会理知的“合模”,是儒家文 化对人生模式所作的总体设计。因此,儒家文化注重启蒙教育与道德修养,强调“化性起伪 ”,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或渠道,力图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个人要服从社会,个性的 发展要符合社会的统一要求。只有“克己”,才能“为仁”,最终才能“复礼”。所以,“ 分”“别”之后的个体,只有“各得其宜”、“万举不过”的义务,而无自由发展的权利。 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牵一发将动全身,尊卑有序的“使群”局面,必须以个体在 社会整体中的安分守己,即取消个体多样化选择的自由,以服从社会化的统一设计为前提来 作保证,这样,个体的“克己”、“合群”,然后“合模”,永远是维持社会的和谐、平衡 发展的第一需要,社会的“平治”目标始终高于个性发展的要求。
与此相反,道家文化则倡导“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此处“自然”,具有天然,不假 人为而自成的意义,也就是指自然则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强迫的成分。 简言之,“自然”也就是“本然”、“本色”,“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就是指顺应 万物之自然本性而使之自由自在地发展。然而,由于后天环境已使人性发生了“异化”,所 以,保持“自然”又必须首先要经历回归“自然”的曲折。因此,为了帮助“异化”了的人 性“迷途知返”、“归根复命”,就需要“辅之”外力。此“辅”包括两层含义,即“始于 有作”与“终于无为”,或曰“撄而后成”、“雕琢复朴”。之所以要“始于有作”,是因 为原心上积累的层层污垢不会自行消失,必须靠人不断地清扫,才能彻底清除干净。这种“ 清扫”可以理解为引导人们进行刻苦地修炼,因此它是“有为”的;而“有为”只是手段, 目的还是经过“有为”的苦修而进入“无为”,因此“终于无为”。所谓“终于无为”,是 指经过脱胎换骨的修炼之后所达到的“道我相通”、“人天合一”的境界,用道家的话是指 “达道”,用道教的话是指“成仙”,概言之,就是在尘而能超俗的状态。由于这种状态是 经过逆异化之心、顺自然之本而达到的,所以是“不敢”强为、却又能“辅其自然”的“无 为”,目的即在于辅助万物排除干扰、克服“异化”、顺其本性地自由自在地发展。因此, 人的自由自在地“自然”发展,始终是“道化理想”的重要目标,从而从横向比较上与高扬 社会价值和人的社会性的儒家文化形成对峙。
二
儒道文化对峙的客观存在,为其从对立进入统一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契机,这种对立而统一 的辩证法正存在于对以人生为座标的生命旅途的全方位的考察中。
纵观人的一生,一般都会经历“幼稚——成熟——深刻”的思想发展过程,与“童年—— 青年——中老年”的生命进程相吻合。应当指出的是,在人的生命进程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儒道文化发挥了虽相反却相成的作用,共同为生命个体顺利完成生命的全程而勾画了一个 完满的“圆圈”。正是在这个“圆圈”中,儒道文化实现了互补,并由此充分展示了对立统 一的辩证风采。
一个人从其生命旅程的第一站起,就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人或社会的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 之中。也就是说,人不能孤立地存在,作为关系网上的一个“纽结”,与社会和他人息息相 关,所以,首先要“合群”、“入俗”,这就要学习适应群体,乃至社会的规矩。因此,从 呀呀学语,至姗姗学步,无一不是为了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一旦能说能行,成为一个独立 个体了,人便要开始学会做人了。要学会做人,首先就要学会做人的规则或规矩,通过自觉 地践履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或规矩而去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儒家文化就为人们提供了系统而 完整的规范学说。所以,在人的青少年(尤其是童年)时期接受正宗的“儒化教育”,以掌握 做人的规矩,适应社会的要求,便是理所当然的。为此,儒家文化建构起“儒化教育的层次 效应”,以满足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人性发展的需要。
“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率先建构了“角色—秩序—和谐”的经典效应,认为,社会的和 谐以稳定的秩序为前提,而稳定的秩序又必须以社会成员明确自己的角色规范,并严格去履 行为基础。因此,明确角色规范,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第一先决条件。为了使这一儒家经典 意识能深入人心,形成社会的共识,“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相继建构了(1)“蒙学效应” ,以口语化、通俗明了的语言形式,将儒家经典进行了通俗化解说,以便更加生动地向世人 ,尤其是儿童讲述角色规范的道理。由于易懂易记,很受大众的欢迎。(2)“戏曲效应”, 以戏台作“讲台”,通过塑造无数栩栩如生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士,为“实然”之世人 提供了“应然”之角色典范,因其集审表与教化于一身,寓教于乐,所以为儒家经典意识转 变为一般民众的共识,做了独树一帜的贡献;(3)“故事效应”,茶前饭后,讴歌忠烈,贬 斥昏淫,扬善弃恶,使儒家经典意识经过故事情节化的处理后,委婉动听,为民众所喜闻乐 见,促使角色意识深入人心;(4)“建筑效应”,以祠堂的威严,为儒家经典意识的由社会 、国家推行入家族、家庭,创造了异常浓厚的文化氛围;以私塾当“桥梁”,为人们“求生 富贵”的“位移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以(贞节)牌坊作示范,为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的 儒家经典意识深入人心,做了最经济又最艺术的“广告”;乡土建筑以其独特的形式,深刻 的内涵,行无言之教化,将儒家经典意识的“层次效应”推向了高潮,从而为世人如何做人 ,如何扮演好社会一员的角色,即如何与社会理知“合模”,以实现个人的价值,提供了一 份精致、完美的“成熟方案”和切实可行的“实施大纲”。在此意义上,有人称儒家学说是 为童年人和青年人而建立的关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学问,[5]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儒家学说在促使人走向成熟,“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在取得极大成 功的同时,也潜藏了导致人对其自然需求的压抑之趋势。也就是说,成熟同其它任何事物一 样,也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成熟是取得社会承认,实现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另一方 面,日趋成熟也标志着离其自然本心可能愈来愈远。当社会理知以“他律”的形式去塑造人 的性格、心理、灵魂,使人的外在表现趋于统一化、同一化、社会化的时候,社会理知的过 分高扬,也可能成为对人的自然本心构成越来越沉重的束缚、桎梏,即“异化”之威胁,从 而 引发出人的内在需求与其外在表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因此,渴望摆脱束缚,以回归自然的呼声,也将伴随人的成熟日益强烈与明朗,从成熟走 向深刻的“序幕”由此拉开。
对“自然”的“回归”,也就意味着对规则、习俗等社会理知的超越,即对儒家文化作逆 向运动的启动,而能承担此重任的,非崇尚自然的道家文化莫属。为此,道家文化首先在“ 意象”上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空间,人鬼神的三维存在形式,避免了成为社会化的人的 一元选择的绝对论和专断论。人死虽会成鬼,但人经修炼却又可以成仙。当然,所谓“成仙 ”不过是人能自由自在地存在与发展的同义语,这就为人的生活提供了多向度的选择。其次 ,道家文化还为人们提供了观摩“仙境”的“建筑效应”,从洞天福地的“人间仙境化”, 到道观道宫的“仙境人间化”,无一不在向人们展示成仙的妙不可言与现实的可能,在满足 人们向往自然、追求自由的普遍心理的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憧憬无限又切实可行的前景。 第三,道家文化还以斋醮诵吟的宗教仪式或民间风俗,形成强烈的信道、学道、向道、合道 的氛围,用神圣而严肃的音乐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唤起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内在的 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从沉重的社会理知的束缚下解脱片刻,而使心灵得到短暂的静寂,瞬 间享受到人与天、人与“道”的神秘的合一的神仙之妙,其结果必然是促使潜心信道者变“ 旁观者”为“参与者”。那么,怎样才能通过“参与”而实现人的本性回归呢?道家文化认 为“学道首在受戒”,即首先借助“他律”命令的力量,戒除一切陈规陋习,使心灵消除“ 异化”的痕迹,而其中的关键又在其是否虔诚。此“虔诚”可理解为具有脱胎换骨的坚定信 念与“降龙伏虎”的叛逆精神,因为人一生下来面临的就是一个“人我山高”、“是非海阔 ”的世界,世俗的偏见根深蒂固,欲超凡脱俗,不下大功夫,不做大努力,谈何容易?所以 ,尽管目标的实现是求得人的自由自在的发展,手段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严格的 训练或修炼,克制后天的欲心,以发扬先天之本心。而要训练或修炼,就要有一套严格的纪 律或章程,为此,就必须对包括戒律在内的道义精神,树立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在实际行动中 严格践履,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的念头,从而借助“他律”的威力与效力,使无限膨胀的 欲心浊身不断得到遏制、压抑,直至彻底舍弃。一旦“他律”发挥了作用,使“外境勿入” 形成为一种习惯的力量,从而习惯成自然后,外在的命令便可望转化成内心的自觉,则人 向其“回归”的目标便又靠近了一步,于是,“令内境勿出”,人向其自身挺进的号角就可 以吹响了。这时,道家文化便顺势建构了发掘人内在潜力的“经典效应”、“体悟效应”, 以“不言之教”与“绝学”作为两个重要的环节,帮助人们从外在行为方式的“自律”,进 入到内心世界的提炼与升华,在对传统的世俗世界超越之后,再度实现人的心灵世界的净化 ,通过调动潜意识,开启元意识,激发体悟之潜能,最终达到与大道“默契”,实现其“得 道成仙”的终极理想,此谓“归根复命”,也就是回归自然,即“自我”最终回复到其“本 色”、“本位”。此刻,人还是那个人,却能在尘而超尘,脱俗而不离俗,既能过好俗世的 生活,又始终不忘人生的终极追求,即自我的全面实现。在社会群体与个体、凡俗与理想、 规则与超越、应然与实然、他律与自律、形上与形下之间,形成一个“张力场”,在此张力 的效力下,人才最终实现了其人生境界的理想追求:深刻而不失其本真。至此,人生也就划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研究客体与主体在此刻也逻辑地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融合与互 渗:生命的不间断性本身就意味着“互渗”,而始于一源,中于分流的儒道学说,因对立而 互补的需要,也逐渐趋向于归于一源。道家称此为“归根复命”,儒家称此为“和而不同” 。
三
当我们从并列或连续的视角分别去透视儒道理想时,不难看出,二者的对峙恰是形成互补 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二者的互渗正根源于其对峙。这是因为,二者本来就是同源的,即同 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精神的体现。
如果我们把中华古文化精神统称为“道”的话,则“道”的发展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 个“必然”又是通过无数个“偶然”发展的可能性而体现出来的。可见,偶然中有必然,必 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其开辟道路的。这是因为,每种可能性中其实已暗含着与其对应的另一 向度可能性存在的必然意义;每一可能性的性质均取决于与其对立的其他部分的性质。这种 对立的特性,或者说这种双向的可能性的逆反运动,就为必然性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 发展的契机,因为偶然性所包含的可能性的两极的最终统一,就是必然性。同时,由于任何 一种可能性或偶然性又都只是必然性或“道”的某一侧面、某一特性的表现,所以,尽管都 包含有必然性或真理的颗粒,却没有一种可能性或偶然性能穷尽真理之“大全”。这种必须 互补的客观需要,就为必然性的实现创造了从对立走向统一的美好前景。因此,尽管必然性 的发展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但变化万千的多向度的可能性就其本质而论,又都是以双向逆 反运动的对立趋势为其本质特征的。从外部特征上去看,它们是对立的;而就其内部机制或 本质而言,它们则是统一的。
事实上,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儒道文化也正是这样以“一源二流”的方式展现中华古文 化的风采的。这里的“二流”,从横向的水平面透视,是指逆反而行的对峙格局,或谓“百 虑”、“殊途”;从纵向意义上考察,则标志着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连续发展,可谓“一 致”、“同归”。换言之,儒道文化正是在对“合礼”或“达道”的逆向追求中,因相反而 相成,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中庸风范。这种中庸风范,又使二者虽对峙却能互渗,并以其结构 相似,走向相反的“金字塔顺逆效应”模型,揭示出对立而统一的辩证关系。
不难看出,一旦站在兼容、和谐、均衡即“中庸”的立场上去看待儒道理想,则二者在塑 造民族精神、理想人格方面的“殊途”、“百虑”的双重价值,“同归”、“一致”的互补 机制,及其“山穷水尽”而后“柳暗花明”的文化转机及动因,是显而易见的。儒道文化处 处互相衬映,又各尽其妙,从而以其“两峰对峙”但“和而不同”的理想追求,在千岩竞争 、万壑争流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流变中,独领风骚。其中,对峙却互补,互渗但独立的品格, 创造出蕴含巨大张力的文化效应,为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特别是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意义的文化理想,提供了再度超越、前景美好的契机。这一契机就存在于传统的儒 道 文化实现其创造性的转折之中。
应当承认,任何社会的理想之实现首先都要调整好社会性的号召与个体的道德响应之间的 矛盾,而社会性的号召通常以规范体系为基本形式。也就是说,社会性的规范体系只有与个 体的道德响应形成了共识效应,社会的理想才可望实现。在儒道文化那里,此二者的关 系恰好是形成对峙的根本所在。儒家文化倡导共识效应,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选择或自觉的 道德响应为前提的。而道家文化提倡个性自由,又是以对社会规范的超越为条件的。原因则 在于儒道文化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阶级关系的产物,这种不平等的客观社会现实,是造成儒 道文化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的号召与个体的道德响应相协调的真正原因。社会主义现代中国 则不然,其理想的建立是以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克服,即以提倡公民意识和民主国家意 识为基本前提条件的。由于这种民主国家意识是从逾越公民社会每一成员的特殊利益考虑, 即基于平等、公正的“公意”立场或曰社会化的“类意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能得到 公众的普遍认同,从而也就能成为社会性的“共识规范”,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公民所进 行的群体性价值探索的体现,因此,服从“共识规范”,也就等于服从自己的价值理想,而 不是服从任意的外部强制,从而在对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同时,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语),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社会的共识效应的形成,不但不应以牺牲个体的自由选 择 为前提,反而须依赖于个体的自由探索与积极参与。同理,追求个性自由不仅不应以对社会 规范的超越为条件,而且必须在对社会规范的认同与忠诚中才能真正的实现。因为二者关系 一旦建立在平等、公正的意义上,就必然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每个社会成员或公民在成为自我利益的追逐者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 会利益的承载者。在追求个性自由时,更注重热爱祖国、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勤恳工作、 遵纪守法等个性的完善;在对国家、社会忠诚时,并不妨碍个人向政府或决策机构反映意见 ,表达社会变革的要求。至此,社会性与个体性才算真正达到了和谐,理想的中庸境界才 可谓最终实现。当然,这种和谐在现阶段仍旧只是一种理想,但我们坚信,这种理想作为文 化 流变的终极追求与最高境界,必将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而成为现实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