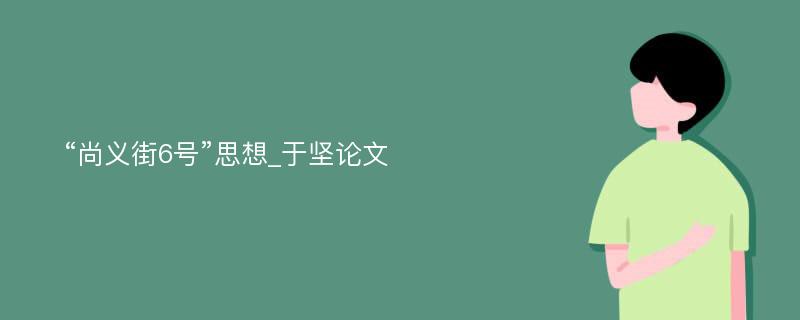
《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尚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02-04
作为已经被纳入文学史经典的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作《尚义街六号》(以下简称《尚》)自它在1986年发表以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粗略统计,关于它的研究文章有近50篇①,这些文章基于80年代初确立的批评方式,要么是围绕“语言”和“形式”进行文本细读分析,要么以宽泛的整体化研究代替细致的文学史梳理②,虽然这些研究对《尚》的意义之阐释和文学史地位之确立功不可没,但由于缺乏一种比较开阔、全面的历史(文学史)眼光,许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廓清,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认识上的混淆。在近20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尚》,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知识气候之中,我们或许要更加谨慎地追问这些问题:在语言与形式的背后,《尚》与朦胧诗的意识形态观念究竟有何区别?这种区别是因为哪些历史因素和个人气质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否意味着“新诗潮”的起源、发生存在着“多元化”的可能?等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并试图在一定的范围内展示80年代初新诗潮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它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缠。
1978年,新诗潮的核心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从刊物名字和它的“致读者”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代诗人对一个时间概念——“今天”的突出强调。在“致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1] 对“今天”的强调并非出于一种简单的要求文学与当下拥抱的渴望,实际上,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文学史背景。日本学者竹内实在1971年的一篇研究中国50-70年代文学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文学中写明天的指向,其本身强调着眼于未来这一关注点,实际上是关于禁止写今天的一种借口,或者是要使人们模糊对写今天的关注。”[2] 竹内实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写明天”的文学,在昨天——今天——明天这一三维时间向度中,“今天”被搁置或者说被“取消”了。所以,当1978年《今天》刊物大声呼吁“今天,只有今天”时,它实际上是在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学写作原则或者说试图引导一种不同于前此的文学写作方向。
在《今天》刊物的“致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老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1] 这段话不仅可以看出“今天”诗人要求与“历史”实现断裂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他们所理解的“今天”的含义,即:新时代的精神。这一所谓“新时代的精神”在后文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阐释——“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将“今天”与生存意义之确立以及自由精神之理解联系起来,必然使“今天”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比较“宏大”的抒情叙事。我们可以分析下列“经典”诗句:“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这也是一切》)。在这些诗句里,“今天”并不是作为一个具体可感的个人生活时间来出现的,它一方面联系着“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和苦难深重的“黑夜”,另一头又指向“新的转机”、“光明”、“希望”和“未来”。实际上,北岛、顾城、舒婷的“今天”是一个抽象的时间观念,它依然处于昨天——今天——明天的三维历史进化中,并在对过去的“苦难叙述”和对未来的“热切渴望”中被“搁置”了。因此在这一点看来,我认为朦胧诗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文学”如竹内实所概括的“写明天”的逻辑,它在内在气质和历史意识上与“社会主义文学”维系着一种血肉模糊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虽然《今天》诗人群在1985、1986年左右就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但“今天”诗人们所想象和写作的“今天”并不能代表80年代初诗歌写作界对“今天”的全部认识,也就是说,对“今天”的认识在80年代初就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至少在1982年的写作中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并在随后的写作中继续扩大。1982年,于坚写作了《罗家生》,1983年写作《尚》,这两首诗歌所叙述的“今天”与北岛、顾城、舒婷等诗歌中的“今天”截然不同。
在《罗家生》里,罗家生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生老病死似乎和历史并没有发生多么尖锐而痛苦的纠缠,“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厂”,这是唯一暗示了历史暴虐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罗家生并没有在这种历史的暴虐中成为一个朦胧诗式的“英雄”或“战士”,他回避了与历史发生冲突的可能,以一种卑微的姿态生活下去。“今天”对于罗家生来说,意味着工作、结婚、生子和死亡。于坚没有叙述罗家生的“过去”,又以突然死亡的方式宣告了他“明天”的不可存在。在《尚》里,于坚给我们呈现了一群小知识分子的“浮世绘”:老吴在尚义街六号的二楼晾裤子,老卡在翻黄色书刊,李勃在讲文坛内幕,朱小羊的手稿乱七八糟,于坚一心想着成名。“尚义街6号”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点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点”里,“历史”消失了,“今天”变成一个既无过去亦无未来的具体“存在”。老吴、朱小羊、老卡、于坚的职业是什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们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尚》对这些都没有作非常清楚的交代。《尚》中的这群人既无“苦难”的过去(如北岛式的),也没有“童话”般的未来(如顾城式的),当“今天”从一种线性进化的矢量中抽离出来时,“历史”似乎告别了朦胧诗提供的关于“确立个体生存的意义”和对“自由精神追求”的宏大抱负。“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恩恩怨怨/吵吵嚷嚷”。[3] 这是一幅琐碎的、物质化的、甚至有些庸俗和自我调侃的“今天”图像。
对“今天”认识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是新时期伊始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的差异。文学史叙述和教育往往使我们认为新时期开始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体验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又被文学史从两个方面予以强化,一方面是将像“伤痕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这样的文学概念予以经典化③,另一方面,就是对作家进行严格的代际划分。这种种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历史叙述声音的“单一化”,抹杀了历史应有的复杂性。比如,将于坚及其作品纳入“第三代诗歌”或“第三代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对新诗潮进行多元叙述的可能。这是下一节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对代际的划分非常热衷,小说界的所谓复出作家、右派作家、先锋作家,诗歌界的复出诗人、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等等都是这种划分的直接结果。与划分结果的明确相比是划分的标准一直相当模糊。以诗人为例,于坚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诗人”,而他的年龄实际上要比其他的第三代诗人要大一些,他出生于1954年,在第三代诗人中,于坚被戏称为“老于坚”,实际上他的年龄更接近顾城(1956)、舒婷(1952年)等朦胧诗人,也就是说,如果以出生年龄来划分代际,于坚应该和舒婷等朦胧诗人属于“同代人”,实际上不仅他们的出生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开始写作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大约都在1970年④,这样一来,于坚和朦胧诗人的“今天观念”的不同似乎就不是一个“代际”就能解释得了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在其起源时刻就存在的差异性问题。
在对朦胧诗最早的推荐以及后来的争论中,对朦胧诗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批评文章都注意到朦胧诗歌中存在着一个“潜文本”,这一“潜文本”就是“文革”十年对一代人的生活写作造成的巨大影响。在《新的课题》这篇文章中,公刘认为:“而不幸客观存在着的,却是被林彪、四人帮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把这一切都搞乱了、破坏了的痛心的事实。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4] 公刘的这段话不仅指出了朦胧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动因,实际上也暗示了朦胧诗的写作上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在和“文革”这样一段历史的辩驳、诘难、抗争和纠缠中,朦胧诗歌才获得了其丰富的社会学含义,可以这么说,没有对“文革”历史的升华、发挥也就不可能有激动人心的朦胧诗歌。顾城在一次访谈中非常自信地说:“为什么许多读者并不是很多的青年,会通过所谓的朦胧诗在遥远的地方共振?完全是超现实的直觉吗?不,更重要的,是一代青年的共同遭遇,共同面临的现实,共同的理想追求。”[5] 480这种所谓的共同的遭遇、现实和理想追求用吴俊在一篇文章中分析的话来说就是“完整地经历过文革的人更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更具有历史的庄严感和严肃性。”[6]
但是,问题果真如此吗?如此统一的关于“文革”的体认和书写没有例外吗?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于坚说“在四十岁之前,我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五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年代,思想解放的年代和市场经济的年代。但是在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却很少影响到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对于“平淡无奇”他在下文中有更具体的解释:“并没有那种九死一生的际遇,我没有被流放、坐牢。”[7] 朦胧诗人所反复书写的苦难似乎在于坚的“文革”中并没有出现,相反,他的“文革”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于坚回忆了1970年发生在他们家大院里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一个干部买了一台电视机,然后每天全院的孩子(于坚其时已经14岁)都搬着小板凳到他家去看电视,并受到了那个干部的热烈欢迎。虽然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但其原因并非来自政治方面,而是那个干部难以忍受孩子们的吵闹。[8] 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平静,生活气息十足的70年代,它确实如于坚所言,相当“平淡无奇”。虽然有人再三提醒于坚关于文革恐怖和苦难的记忆,⑤ 但于坚以没有“看到”过拒绝了关于这方面的书写,他更乐于回忆是他脸上的疯长的青春痘给他带来的烦恼和自卑。[8] 在他的记忆和书写中,“文革”虽然也有恐怖,压力,但更多的是一幅日常生活图景。⑥
这样一种平淡无奇的“文革”体验和记忆使一个高度一致化的关于文革的叙述在《尚》里面遭到了“拒绝”,我们注意到在《罗家生》里有这样一句:“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厂”,在《尚》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他在某某处工作”,这两句都可以认为是关于那段“暴虐”历史的阴影。这是我们注意到这种书写和朦胧诗的书写非常不同,不仅在篇幅上只是一笔带过,更重要的是在情绪上这种文革的记忆和书写并没有带来感情上的升华和叙述上的“戏剧效果”,实际情况是,这种书写即使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仅仅在诗歌中享有同其他故事、人物、感情平等的地位。正是由于这段“历史”的缺席,于坚的“今天”才摆脱了在线性历史中的“升华”,在《尚》里面得到了“空间化”和“具体化”。套用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的一个名词,对“文革”的这样一种体认是《尚》“今天”观念得以形成的一个“认识的装置”。
对文革的认识和体验固然对于坚历史观和现实观(今天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毕竟,对于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诗人而言,其“观念”之形成不仅依赖于具体的经验和实践,也会受到来自包括文本、阅读等以“知识”形态出现的东西的形塑。
吴俊在一篇讨论60、70年代出生作家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由于大学图书馆的开放与否,对这些作家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6] 而贺桂梅在《先锋作家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一文中,干脆就把“阅读书目”作为考察先锋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9] 由此可见,阅读哪些作家,阅读哪些书籍所构成的“阅读接受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讨论于坚的“阅读书目”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话题,到目前为止,于坚仅仅在1998年的一篇访谈录中比较简略地提及了他的阅读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将这段话抄录如下:
早期有惠特曼、罗曼·罗兰、雨果、泰戈尔、莱蒙托夫、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契诃夫我非常喜欢。这些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影响非常大,教我如何看待世界,如何人道地对人,对我的人生观有所影响。[7]
仔细分析这样一段话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信息。虽然于坚列出的作家有近10位之多,但基本上是以惠特曼为代表的19世纪的所谓“浪漫主义”作家群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于坚作为顾城、舒婷的同代人的一致性,比如顾城就在一篇访谈录中谈到惠特曼对他影响至深,[5] 473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的吁求,使那一代人基本上选择了19世纪作家作为阅读的“典范”。但有一点显示了于坚和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于坚特别强调了“契诃夫我非常喜欢”,如果仅仅是从“人道主义”“人性”这个角度,于坚没有必要非得强调契诃夫,契诃夫与上述那些19世纪的“浪漫”作家之间的区别,可能正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卑谦的小人物眼光,冷静而低调的叙述,而这些,正好比较对于坚的“胃口”。
在同一篇文章中,于坚还提到:
到了八十年代,我看的外国书更多了,是跟存在主义、语言学派有关的,如萨特、海德格尔、波普尔等,还有卡夫卡、加缪、罗布-格里耶、乔伊斯、拉金、奥登,这些写作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诗人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不大喜欢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玄学派的诗人。
从这样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拥有“学院”身份的于坚与朦胧诗人的不同。于坚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大学教育的“系统化”和“专业化”使于坚对自己的阅读有更为自觉的选择。在某种专业的“眼光”下,于坚在纷繁复杂的书籍中选择了“写作与日常关系密切的诗人”。这种选择既有早期契诃夫潜在的影响,也有80年代“文化热”的时代驱动。正是从自己的体验(对文革的体验和对80年代的体验)出发,于坚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牢牢锁定在“日常生活诗人”这一块,并直接表达了对浪漫主义、乌托邦等所谓“二十世纪精神倾向”⑦ 的反感和拒绝。虽然不能确定于坚的这些事后“追认”的“阅读史”是否有诗学策略的成分,但从于坚在《尚》等作品中的写作来看,这种“观念”确实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写作。
也许可以这么说,对历史实践本身的体认(尤其是对文革历史的体验)或隐或现地影响着于坚的“阅读”选择,而另一方面,这种“阅读”一旦开始,就逐渐构成一种“知识”,一种“经验”,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正是在历史体认和知识型构等种种合力之中,《尚》的意识形态才得以建构生成,并与朦胧诗人本质区别开来。
在讨论第三代诗歌和朦胧诗的关系时,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部分第三代诗歌的参与者,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看来,“第三代”是在和朦胧诗歌的彻底的“决裂”中获得其诗学合法性的;而在一些更谨慎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眼里,第三代诗歌或许对朦胧诗有着更多的“延续”。“断裂”和“延续”从表面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将第三代诗歌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朦胧诗”的联系或区别的基础之上却是它们一致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新诗诞生以来的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首先是“影响的焦虑”。在一个没有稳固的“经典”可以提供写作范式的历史语境中,每一次诗歌写作都被“叙述”成一种潮流或者范式,其他的写作只有在与它发生“关系”时才能被纳入诗歌谱系中。其次是“发展的焦虑”。出于对更“规范”、更“经典”的诗歌范式的追求,新诗的“当下”总是会遭到质疑甚至反对,只有把新诗叙述成线性进化的矢量过程,这种发展的焦虑才会得到暂时的释放,一种更完美的诗歌图景也得以想象。可能是在这种种历史和非历史的因素影响下,80年代新诗潮的起源被大大简化了,朦胧诗作为唯一起源的地位被“经典化”,在这样的视野之中,“第三代诗歌”只可能对它“延续”或者与之“断裂”。
但是否有另一种可能的叙述存在呢?是否在“延续”和“断裂”之外还有一种更贴近文学史“真相”的叙述呢?对《尚》的意识形态分析(历史观和现实观)正是企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叙述。既然如上文所分析的,认识的差异一开始就存在,并在朦胧诗尚未经典化的1982年就成为写作的实践(如《罗家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以《尚义街6号》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和朦胧诗并不构成一个“等级化”的、前后延续或断裂的诗歌进化链,而实际上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它们源于1980年代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体验,因此“平等”地构成1980年代新诗潮多元化的起源。
需要指出的是,试图“颠覆”已经成为“定论”的第三代诗歌发生学,并重新提出一种新的叙述(“平行”论),仅仅依靠对《尚》的意识形态分析或者是对于坚这样一位诗人的历史考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在朦胧诗经典地位的厘定中,有一项工作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那就是对朦胧诗的“史前史”的发掘和整理⑧。在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中,“白洋淀诗歌群”和诗人食指被“发掘”并叙述成为朦胧诗的先声和起源。在“食指——白洋淀诗歌群——朦胧诗”这样一个诗歌谱系中,朦胧诗的经典地位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巩固。因此,如果要对《尚》以及“第三代诗歌”进行一种新的叙述,对其“史前史”的认定和追溯就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我们能从一些著作中得到一些相关信息,比如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中就认为很多“第三代诗人”完全没有受到朦胧诗影响,其写作是“自成体系的”⑨。但是这些“言论”是否成立却有待考证。它们仅仅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起点”,要真正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将一种“意见”转化为“知识”,必须借助更翔实的“考古学”研究。也许,这种研究会为“第三代”诗歌的研究现状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在中国知网(http:// www.edu.cnki.net)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输入关键词“于坚”,选择时间范围1986-2006,可得到125条记录,其中涉及《尚义街6号》的文章近一半,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中文系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②罗振亚2006年的两篇文章可以说还保持了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见罗振亚:《1980-2004先锋诗歌整体观》、《“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③实际上,历史在其起源的时候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其差异性也是比较明显的。以伤痕文学为例,程光炜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对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它对新时期的“想象”和“叙述”与《班主任》等伤痕“经典”作品有非常大的差异。参见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④见北岛:《失败之书》之北岛创作年表;于坚:《于坚的诗》之于坚文学年表等。
⑤于坚在《人间笔记》中提到一个老干部要求他多写写文革中的“惨痛”,但于坚以“没有看到”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
⑥2005年12月诗人西渡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座谈中说到文革给他留下的主要回忆是“自由”、“没有压迫感”,并说这种体验对他的写作影响很大。笔者当时为座谈者之一。
⑦于坚说:“我实际上更愿意读者把我看成一个后退的诗人,我一直试图在诗歌上从二十世纪的‘精神倾向’中后退……(二十世纪的精神倾向)其基本特征就是‘升华’,用解放者的眼光看待旧世界,看待大地,把日常生活、传统、大地统统视为解放的对象。以抽象的‘终极关怀’否定具体的存在,否定‘日常关怀’。”见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
⑧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程光炜的《一个被发掘的诗人》,《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的《当代诗歌史的写作问题》,见《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⑨参见钟鸣:《旁观者》,第685-695,879-88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标签:于坚论文; 朦胧诗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