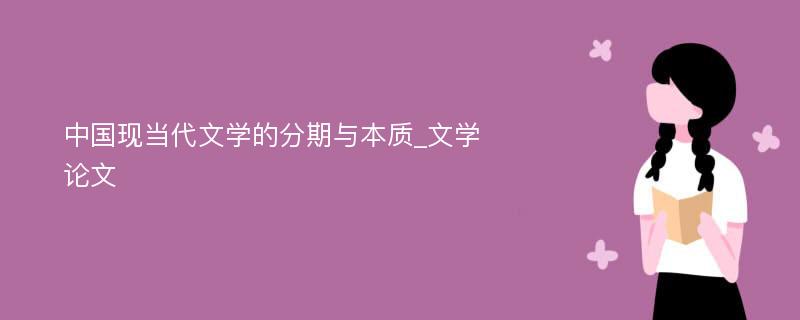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性质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4)02-0143-04
近年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种主要观点:一是传统政治视角的分期方式,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根据和标志;二是从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或审美视角出发,以“20世纪”的概念连接起“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的机械分割,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三是从世界文学格局出发,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作为分期的原则,把1919年五四文学第一次向世界的开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把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第二次向世界的开放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1];四是把五四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把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代文学的终结和当代文学的开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的价值为中心”的潮流取得了主导地位[2]。上述分期原则和分期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传统的政治视角分期方式割裂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也大有问题,正像有人指出的,它“透彻于反封建脉络,而在反帝国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脉络上,其问题意识却相对薄弱”[3]。另外,这一概念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暗含着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来对待的理解[4]。同样,第三种分期方式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它仅仅看到了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抹杀了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力。第四种分期方式则难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和80年代后期的文学有什么不同,也难以确认二者之间的分界点应该在哪里。
对文学进行分期是比较容易的,关键的问题是能够为这种分期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能够根据这种分期对文学本身做出更为恰切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当上述种种分期都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分期原则和标准。在我看来,这种分期原则和标准应当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只要找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上的断裂处,就可以合理地把它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根据这一原则,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当是本世纪初的1902—1905年,而它的终点是新时期的1985年,1985年以后则进入当代文学阶段。
一、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文学史分期的最终根据
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原则和标准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学史断代和分期的最终标准不是这种影响,而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断裂。当中国文学没有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根据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它进行断代和分期。例如,我们之所以把中国古典文学根据朝代分为先秦散文、两汉大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阶段,是因为文学自身的发展具有这种逻辑,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体”。也就是说,上述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主流文学和主流文体,这种主流文学和主流文体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古典文学自身逻辑断裂的结果,因而它能够成为其断代和分期的合理标准。同样,我们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和终结,也必须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找到这种逻辑的断裂处。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的逻辑断裂在于它开始具有了现代意识,不管这种现代意识是来自于西方文学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裂变,我们只要找到了这种现代意识的萌芽,就可以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同样,我们只要找到了这种现代意识的终结点和新的时代意识的萌芽,就可以把它作为现代文学的终结和当代文学的起点。到哪里去寻找这种现代意识的萌芽和终结点?我认为应当到叙事作品的叙事结构中去寻找。这不仅是因为叙事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主流文体,而且是因为这种叙事结构反映了作者的无意识,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文化哲学观念。
叙事结构在这里并不是指叙事作品的倒叙、顺叙、插叙等叙事方法,也不是指烘托、白描等叙事技巧,而是指把一部叙事作品的各个叙事单元和叙事层面贯穿起来的总体结构特征。我们可以说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可能综合运用几种叙事方法和叙事技巧,但是一部叙事作品只有一个总体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它的深层结构是唯一的。这种深层结构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和艺术的领悟和理解,隐含着作者的哲学思想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正像杨义所说:“叙事结构比起某些作者现身说法的唠唠叨叨,更为内在地包含着作者对世界意义的理解,更为内在地作为它的文化哲学模式化展示物而存在。”[5](P114)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结构是文学最为深层的东西,它包含着文学的叙事密码,蕴藏着文学的最根本的意义。不仅如此,由于作品的叙事结构所反映的是时代的思想文化哲学模式,所以一个时代的叙事作品往往具有相同的结构。每个时代都有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哲学模式,所以每个时代都有着特殊的叙事结构。因此,从作品的叙事结构出发就可以把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另一个时代的文学区别开来。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找到了文学叙事结构的断裂点,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叙事结构中找到了现代意识的萌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叙事结构中发现了现代意识的终结和新的思想意识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端和当代文学的起点。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终结
从文学的叙事结构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不是五四文学,而是20世纪初的1903—1905年间的文学变异,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迥异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新的叙事结构,出现了现代意识的萌芽。
从文学的叙事结构来看,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中国古典叙事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按照圆形结构展开叙事。之所以称它为圆形结构,是因为在这种叙事作品中,叙事的终点和起点是重合的。从叙事的起点开始,人物纷纷登场并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叙事的起点,叙事的轨迹最终形成一个圆形。
在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叙事作品《红楼梦》中,叙事的起点是无力补天的石头请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投胎为贾宝玉,贾宝玉在贾府历经滚滚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数年,最终看破红尘出家,这便意味着宝玉尘缘已满,仍由此二人携归大荒山青梗峰下。贾宝玉在尘世的经历只是一种磨难,他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情感纠葛只不过是“金玉良缘”、“木石前盟”那前世命中注定的结果。其他人物也大都是从警幻仙子宫中下凡,历经尘世磨难之后仍要返回宫中。这样,叙事作品的人物从叙事的起点出发,经过种种情节经历,其最终结局仍要无可逃避地回到他们出发的起点;叙事作品的结构同样从叙事起点,划了一个圆形的轨迹,最终仍旧回到叙事的起点。此外,像《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等作品所采用的都是这种圆形叙事结构。主人公都是天上的神圣,只因犯有某种过失,才被打入凡间,一旦他们在凡间修成正果,最终仍要回到天上。人物之间的结构关系只不过是神话人物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而已,它不具有独立现实意义。如果说这些作品叙事的起点和终点都带有某种神话色彩,叙事所遵循的圆形结构是外在于人物的话,那么《金瓶梅》这部市井小说则完全取消了神话色彩,其圆形叙事结构完全内在于人物,是人物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这部作品的起点是玉皇庙,西门庆在这里和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等10人八拜结盟,从而展开了故事情节和西门大官人的市井生活场景;终点是永福寺,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敬济等死后的冤魂孽鬼在这里被超度,西门庆的儿子孝哥儿也在这里剃度出家。虽然玉皇庙和永福寺是不同的地点,但是二者在性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人们祈福禳灾、超度生死的地方,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作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事实上都一样,就像作品中的人物谢希大所说:“咱这里无过只是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这两个去处,随分那里去罢。”即使是《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也遵循着圆形叙事结构,其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从汉末的大一统写起,历经三国割据争斗,最后复归于统一。
上述圆形叙事结构在20世纪初被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所取代。自梁启超于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后,在全国各地迅速涌现出一大批小说刊物,一些新小说最初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这些刊物上。其中,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11月-1903年1月)、李宝嘉的《文明小史》(1903年-1905年)、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年9月-1904年1月)、陈天华的《狮子吼》(1904年-1905年)等作品已经打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圆形叙事结构关系,建立了线性叙事结构。以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例,主人公狄必攘主张进行种族革命,他的对手慈禧集团则坚决反对种族革命,二者是尖锐对立的矛盾关系;宜城愚民既有一定的种族革命要求,同时对慈禧集团又具有妥协性,因此他们是一种中间力量;文明种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对狄必攘、宜城愚民具有重要的启蒙与支持作用,因此,文明种在故事中所承当的是启蒙者角色。这部小说没有写完,我们无法看到它的最终结局如何,但是我们从这些人物关系结构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可以推测,狄必攘的种族革命理想要么得到实现,要么遭到失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结局。
这些人物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作品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决定了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最终的结局,从故事的初始情景到故事的结局之间的逻辑发展就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的命运不是像古典叙事作品那样划一个圆形,而是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故事的叙事结构也不是从叙事的终点再回到叙事的起点,而是沿着自己的逻辑直线向前发展。显然,仅就故事的整体叙事结构而言,上述故事结构属于线性发展的逻辑关系,我在这里把它称之为线性叙事结构。从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几种人物形象、所揭示的人物关系以及它的叙事结构方面来看,它已经迥然不同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
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叙事作品在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上和上述作品完全相同。以鲁迅的《祝福》和《药》为例,祥林嫂和华老栓一家就是作品的主人公,鲁四老爷和康大叔是主人公的对手,知识分子“我”和革命者夏瑜承当启蒙者的角色,柳妈、花白胡子等人则是一群中间人物。这些人物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斗争的结果表明,由于启蒙者自身力量的弱小,他们无法给作品的主人公指明斗争和前进的方向,无法引导大批的中间人物走上正确的道路,使他们被反动力量所利用,最终导致故事的悲剧结局。如果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会发现《祝福》和《药》的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以及故事的悲剧结局在五四叙事文学中具有典范意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叶圣陶的《夜》等作品都与此相似。
萌芽于20世纪初的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经过五四文学的探索,到50—70年代的文学中走向成熟,并取得了在叙事作品中的主导地位。以杨沫的《青春之歌》和柳青的《创业史》为例,前者所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故事的主人公林道静在启蒙者江华姑母和革命导师卢嘉川的引导和帮助下,战胜了阻碍她走向革命道路的对手林伯唐、徐凤英、胡梦安等人,走向了革命道路,由动摇走向坚定的许宁、堕落的白莉萍和自私自利的余永泽则是一群中间人物;柳青的《创业史》描写的蛤蟆滩是中国广大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一个缩影,翻身青年农民梁生宝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在帮手王佐民的帮助下,团结了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物,战胜反对走合作化道路的对手郭振山、姚士杰等人,最终率领大家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人物矩阵关系和叙事结构并没有随着文化革命的终结而终结,而是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再次焕发了生机。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把怀疑和批判的目光指向摧残人性的文化革命和极左政治制度,以高度的真诚和勇气呼唤改革的英雄。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受难的主人公和极左政治制度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关系,在这种冲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主人公的帮手和中间人物。例如《班主任》中的主人公谢惠敏、江青集团、班主任和受害青年宋宝琦就分别在作品中承担了主人公、对手、帮手和中间人物的角色。类似的作品还有《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天云山传奇》等。同样,在改革题材的文学中也是如此,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鲁彦周的《彩虹坪》等作品都具有相同的人物关系与叙事结构,他们都讲述了主人公在其帮手的帮助和支持下,争取中间人物,战胜改革的阻碍,从而把改革推向深入的故事。
综上所述,上述各个阶段的文学之间具有更为内在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是建基于人物关系结构和叙事结构的统一基础之上的。因此,发展到改革文学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各个具体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在性质和外在诉求是一致的。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打破了古典文学的圆形叙事结构,采取线性结构方法进行叙事。叙事的终点不是对于叙事起点的重合,而是对它的推进和超越;作品人物也不再回到他开始所处的地点,而是经过现实的斗争和洗礼之后,获得了思想认识的进步,上升到一个新的人生高度。作品人物丧失了他的神话背景和神性色彩,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的生活中的一切遭遇,他的成功和失败、欢乐和痛苦都是现实生活的产物,都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到解释。如果用一句话对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结构进行概括,那么可以说它们所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主人公在启蒙者或帮手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下,团结中间人物,和敌人或对手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这个故事正是“进化论”、“历史进步论”、“人是万物的主宰”、“理性至上”等现代哲学思想在文学叙事中的体现。所以说,正是现代哲学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决定了它的现代性质。
不仅如此,从上述人物关系中的人物角色要素来看,它具有启蒙性质。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众多,人物众多,但是这些人物不外乎主人公、对手、启蒙者或帮手和中间人物这几种角色。既然中国现代文学所讲述的故事相同,人物角色相同,那么是谁决定着这些故事的启蒙性质?换句话说,是哪一个角色决定着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不同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启蒙性质?答案只有一个:启蒙者。主人公和他的对手以及中间人物都不具备这种功能,因为任何叙事作品所讲述的都是主人公和他的对手之间的斗争,中间人物则是这种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要素。例如《水浒传》所讲述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草莽英雄和官僚统治者的斗争,中间人物则是一些不那么坚定的反叛者,他们在梁山好汉的拉拢和官僚统治者的威逼之下,最后纷纷投奔梁山,才使梁山反叛力量得以壮大;《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在走仕途经济之路还是满足于个人性情之间与对手贾政构成尖锐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贾母、薛宝钗等人扮演了中间人物的角色,正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贾母等人坚决地站在贾政一边,才使宝黛爱情走向了悲剧结局。虽然古典叙事文学也有帮手角色的出现(林黛玉在贾宝玉和贾政的冲突中就扮演了帮手角色,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普罗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也发现民间故事中经常有帮手帮助主人公战胜对手的例子),但是,这些帮手都只是旧世界的一分子,是旧世界的产物,缺乏新的思想和力量,缺乏新的素质,他们不能对主人公进行新思想的启蒙,无法把主人公带到一个新的天地。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国古典叙事作品中看到新思想的曙光和对封建传统的真正有意义有成效的反抗。正是启蒙者或帮手角色的功能决定了中国古典叙事作品无法具备启蒙性质,决定了故事人物最终只能回到他所出发的起点,决定了故事的圆形叙事结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者或帮手则具备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素质。他们最先接受了外来新思想,成为新思想在旧世界的代言人,并且能够为生活于旧世界的人指明新生活的方向,因而他们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使主人公和中间人物都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引导和调遣。文明种、知识分子“我”、革命者夏瑜、卢嘉川、王佐民、林春柱(《改革者》)等人都是这种具有新思想、新素质和意识形态权威的代表,正是他们的出现,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出了历史循环论的怪圈,呈现出不断前进的趋势。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启蒙角色的出现,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启蒙的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因此,具有新思想、新素质的启蒙角色的出现,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性质。
长期以来,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就是,五四文学具有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启蒙性质,新时期文学同样具有反对文化革命中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的启蒙性质,二者都是启蒙文学。相反,50—70年代文学则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背叛,是非启蒙的文学。其实这是对于启蒙的误识。从现代文学叙事结构中人物角色要素来看,启蒙就是启蒙者对于中间人物的思想启蒙,至于启蒙的内容是什么,则依启蒙者所拥有的思想而定。如果启蒙者所拥有的是自由主义思想,那么它就是自由主义启蒙;如果启蒙者所拥有的是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启蒙。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启蒙者卢嘉川、王佐民、陈春柱等人所拥有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主义启蒙思想[6]。但是,无论是自由主义启蒙还是社会主义启蒙,都是作为启蒙者对中间人物的启蒙而存在的,所以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性质和突出特征。
启蒙及其所代表的理性、秩序、结构和意义无疑是现代性的,对启蒙的反叛以及对于理性、秩序、结构和意义的解构与颠覆则是后现代性的。这正是西方思想界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所做出的主要区分。从文学的叙事结构的变迁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结构是圆形的,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结构是线性的,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结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具有后现代性。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20世纪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