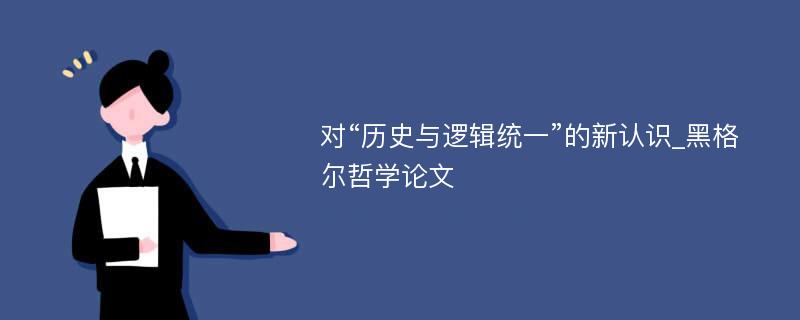
重新认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相统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是黑格尔以降直至当代人们研究精神历史的根本方法。黑格尔认为,“全部哲学史是一个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1〕“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 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也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2〕这其实是告诉人们, 哲学发展历史——抛开其中的偶然性因素——的内在规律,是和正确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演绎相一致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就是被一个固定的逻辑框架整合的历史。
黑格尔所提出的这种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当代美学史家一直将它作为描述美学历史的第一法则。像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就指出,一部成功的美学史著作,既要做到从历史现象的发展中看到逻辑推演的进程,又要让人从逻辑推演中看到历史现象的发展。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合二为一的方法虽然试图照顾到历史的真实性和理论的明晰性,但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却出现了诸多不正常的现象,并一再给人展示出历史的扭曲和变形。
一 是历史修正逻辑,还是逻辑修正历史
作为对精神历史的哲、美学研究,当研究者试图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介入问题之前,他首先不得不面对两种历史:一种是历史的本然状态,一种是预设的逻辑的自动。一般而言,研究者总是对两者之间的契合抱有强烈的自信,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分离却往往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是用历史修正逻辑,还是用逻辑修正历史,就成为检验其研究成果是否真实可信的关键。
就黑格尔本人来讲,他认定,存在和思维的本质都是逻辑的。由于历史性存在是处在受逻辑规律支配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每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在逻辑上都是从前一种状态发展而来。很明显,在这种逻辑化的历史链条中,黑格尔并没有把历史的内容真正还给历史,而是作为他的辩证逻辑的一种证明。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3〕也就是说, 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最终完成的只不过是历史向逻辑的屈服,或逻辑对历史的修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作为方法论原则,那么我们得到完美精神历史的梦想就面临实践的巨大考验。因为研究者为了逻辑的有序和简便,往往会将逻辑无法包容的历史现象看作偶然性加以排斥。他们用逻辑的剪刀对历史内容进行着粗暴的增删、归纳,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部和历史本身大有出入的、被逻辑重塑的变形的历史。这样,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成了一种单色调的逻辑的预谋。
同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也是一种上升的逻辑。他虽然因在其中引入了进步的观念而具有了对历史发展的预见功能, 但他的“绝对精神”、“永恒的善”却为自己的逻辑演绎设置了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终点,并最终使逻辑的历史成为一种走向上帝的天路历程。比如,黑格尔曾经预言,艺术经过东方象征型艺术、古希腊古典型艺术,到18世纪末已发展到“艺术超越了艺术本身”的浪漫型艺术,并从此使艺术消亡;社会形态到了普鲁士的君主政权已达到了终极的完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也达到了顶点。但事实证明,历史却在黑格尔逻辑演绎的终极处一如既往地继续发展,我们今天并没有面临一个没有艺术、没有哲学的暗夜时代。这种历史自身提供的反证说明,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并不能交给我们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胡塞尔说过:“哲学的思维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4〕也即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己的思维方法切中实在, 抛除偏见,达到和实在的统一,这是对某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进行评判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它就明显是一种对历史的有欠精确的描述。首先,就逻辑的自身特性而言,它虽然以数学的公理化和形式科学化的面目出现,但它毕竟是人造的东西,人的局限性和偏见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其中。正如胡塞尔所言:“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只是表现了人种偶然的特性,它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并且会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另一种样子,因而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的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自身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5〕其次,就逻辑的描述功能而言, 对象之物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被领悟。逻辑学家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理性思考,最终提炼出高度抽象的逻辑结构。在描述历史进程时,它要求偶然性服从于必然性,现象服从于本质;在描述社会形态时,它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服从于客观精神。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把握,才能和逻辑设定的历史模型有契合的可能。由这两点来看,逻辑规律描述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功能,就变得可疑起来。在对历史的把握之中——尤其以多变的主观情感和强调个体创造性为内核的艺术的历史,如果坚持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就只可能杜撰出一个个充满主观臆断的逻辑体系,成为以庄严的面孔骗人的东西,或者为了逻辑运动的有序性让生动活泼的历史现象作出牺牲。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逻辑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演进程序自动,才使我们对它的真理性深信不疑,并对它和历史多向度运动之间产生的距离视而不见。也可以这样讲,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可能对描述自然、社会等宏观范畴的发展具有契合性,但对从人的心灵之渊中浮现的文学艺术精神——这一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却显得不那么卓有成效。
二 逻辑规律,19世纪解读历史的典型错误
如果我们想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就不得不认识这种方法所依据、所创造的历史发展规律。致力于发现历史规律性的人们相信,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必然承受因果关系的支配。这种因果关系的历史性表述就是因果决定论,亦即我的明天的部分是由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决定的,我的后天的部分则进一步由我明天所做的事情决定。在这种环环相扣的因果决定之中,历史以合乎规律的方式向前发展。平心而论,这种以客观历史进程为依据的规律,对历史有很强的描述性,它使我们透过一些虚假的表象洞见历史的本质,并使繁杂的历史现象显出内在的有序性。但是,由于我们在对规律的运用过程中,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剔除偶然性因素,用辩证逻辑的自动代替人对历史的能动创造,有时甚至用规律的名义为自己的主观臆断或不切实际的行为辩护,这就使逻辑规律不但不能准确地描述历史,而且有时将人们导向一个永难兑现的未来。
首先,关于偶然性。对于一个善于用各种规律来描述历史的研究者而言,他总是固执地相信,一切事件都是规律性的,不存在偶然性事件。有时他也会承认规律性事件和偶然性事件都是存在的。但这种妥协只是一种语言策略,因为他马上会接着说,偶然事件只是在表面上看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也是被规律必然地决定着。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考虑一些突发性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比如奥匈帝国王子的遇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拉宾遇刺与中东和平进程等。很明显,这种以冷漠的规律观照历史的方法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我们的情感难以接受的。我们一方面在情感上不愿让鲜活的历史都屈服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偶然事件的巨大影响视而不见。按照亚里士多德“偶然性就是反乎常规”的命题,我们似乎可以认定,逻辑规律只能描述常规性的普遍历史,而面对渗透着人的常识、具体行为和情感经验的偶然性历史,它却是显露出惊人的笨拙和无能为力。这又进一步提示人们,在宏观的规律性的历史之外,是否还有一部神秘莫测的偶然性历史存在着?它给人造成的审美惊奇,它给人提供的鲜活的表象和情感的满足,是否正是文学艺术创造最愿意依托的对象,偶然性的历史是否正是艺术历史的本质写照?
其次,关于人对历史的能动创造。像由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创造的历史规律尽量祛除偶然性一样,它也往往用逻辑的自动代替人对历史进程的能动作用。比如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被当作整体来看待,整体的内部矛盾是其自身运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样,历史的规律性运动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人参与历史的机会。就人和历史的关系而言,我们习惯于相信,人只能认识、顺应规律,而不能改变它的进程,如果你想逆潮流而动,那么你将无情地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即使是那些具有无限号召力的英雄人物,他在历史舞台上是否出现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历史规律无论如何都会寻找一个人充当行动的工具,而不管他是何人。这种人面对法力无边的历史规律无可奈何的历史理论,我们不能说对历史进程没有一点描述功能,因为面对着无所不在的自然、社会的钳制,人张扬自由意志的机会远没有被动承受命运打击的时候多。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宿命的结论,那我们就会排除对自身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放弃一切捍卫自身尊严的努力。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对“历史必然性”迫使我们做的事负责任,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徒劳的反抗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观。
正如伯林所言:“那种认为历史服从于自然或超自然的规律,因而人类生活的每一桩事件都是一种必然模式中的一个要素的观点,是有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根源的。”〔6〕这种观点提示人们, 规律作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是传统宗教形而上学在现代的翻版,是上帝死亡之后君临世界的新一轮君王。面对着它,我们除了被动地接受指令别无选择。在这种状况中,我们没有机会谈个体对历史的能动创造,也没有办法为总是渎神的自由艺术家寻找立身的位置。他们也许只有别无选择地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生存于艺术的暗夜之中。
第三,关于规律对未来的预见性。如前所言,哲学家通过理性思辨和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发现了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据此,他们相信,既然历史发展都在预设的逻辑框架中进行,那么这种规律就不但能描述历史,而且更能让人预见未来。于是,他们总爱在遥远的未来为人类设计一个世界末日或集天下之美于一身的乌托邦,并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事实证明,这种貌似科学的理论预设大多经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关于这种让人沮丧的状况,恩格斯曾谈到如下的话:
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来创造他们的历史,那种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也就愈小,而历史和预见确定的目的也就愈加符合。然而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所树立的目的和所达到的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还占统治地位,不能控制的力量远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要强大得多。〔7〕
这种规律的预期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出入无疑让自信的规律制造者大跌眼镜。据此,他们甚至认为,现存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只有理性的世界公民出现之后,人类才能使自己的历史根据预定的计划前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一个规律的信奉者,他并没有能力提着人类的脖颈,让大家变成理想的世界公民,也不能扭住历史的犄角,让它朝着自己设定的规律性方向前进。这样,逻辑规律试图描述、左右人类历史的努力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意义。
面对着这种规律的捍卫者最终被规律遗弃的现象,我们还要从逻辑规律自身找原因。如上所言,规律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个体的理性预见能力面对着漫长而复杂的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它的局限性。同时,理论家总要以规律的名义驱逐偶然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但这两者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盲动无定的力量。令哲学家绝望的偶然性,总是突如其来地取代理性的历史链条;而追求生命自由的人也不愿为规律而活着,他们的非理性激情也总是要将有序前进的世界搅成一锅粥。这样看来,被规律驱逐的偶然性和人的自由意志正是颠覆历史规律的重要力量,如果我们不消灭这两个不合作的“敌人”,逻辑规律就不可能独占历史。但反过来讲,如果消灭了无所不在的偶然性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我们还要规律做什么呢?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相信波普尔的论断:“不存在什么进化规律,而只存在着这些历史事实:植物和动物在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已发生了变化。那种认为规律决定着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19世纪的一种典型错误。”〔8〕
三 在辩证逻辑的框架内,历史与心理相统一的价值发现
以上,我们列述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由此衍生的逻辑规律对描述历史的负面作用。为了修正这种非正常的研究状况,我们的首要任务也许是使历史摆脱逻辑而孤立,“靠对历史无所说这种办法,追求可靠性,使经验命题变硬。”〔9〕但是,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对历史无所言说,那么就意味着因惧怕出现错误阐释而放弃历史研究,像西方现代反历史主义思潮所做的那样,将历史像阑尾一样割掉。这种对历史的回避,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之后,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对艺术史——达到比旧方法更紧密的契合度。
在寻找新的历史方法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对黑格尔说三道四,但他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巨大历史感却是不能被证伪的。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深邃的历史精神必须成为新一轮探索的起点。我们和黑格尔的分歧在于,他是用辩证逻辑去策动历史,而我们则是从历史自身发现其动力和自组织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言:“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史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0〕据此,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在社会内部发现了编织历史的力量。同理,艺术作为人的喜怒哀乐等本质力量的精神表现,它创造自身历史的内驱力,只能是人的生命意志对世界的选择、批判和创造。这种艺术自身的心理动力源,正是美学、艺术发展所凭依的对象。
由此看来,我们和黑格尔在直面历史这一点上是没有矛盾的,只是认为面对不同的历史形态应该有相应的具体方法去解决。也即对待宏观的自然史、社会史与微观的美学、艺术史决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很明显,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要为整个世界的演进历程立法,如他所言:“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个时代里,精神的普遍性已大大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紧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持着并要占有着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11〕黑格尔的这种判断,表现了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们特有的野心和自信。据此看来,既然在黑格尔那里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东西微不足道,那么以人的命运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以虚幻空灵的精神形态为依托的美学史,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式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它的硕大无朋,就成功掩盖了它面对局部历史的软弱无力,尤其对艺术、美学史这些远离经济基础的历史形态,它更像庄子所言的“大瓠”一样大而无当。
作为对人的心灵生活进行历史研究的美学、艺术理论,与人的心路历程相对应的艺术精神嬗变历史应该是它独特的描述对象。艺术精神作为人心理运动的结晶,它虽然避免不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避免不了逻辑规律的宏观规定,但这些决定因素是间接的,它终究是人的微观心理运动的直接结果。因此可以说,起码对于美学、艺术历史的研究,采用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必定比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更恰切。具体言之,人的心理动力可以促使人的审美趣味的形成、审美欲求的变迁,可以引起人理想倾向和理想形态的转换,这一切的变化最终促使艺术精神由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以致构成历史序列。据此,人的心理动力完全可以代替逻辑,去策动、编织、贯穿艺术的历史,使之构成前后相连的脉络。这正是我们用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的方法描述审美历史的立论基础。
总而言之,从心理角度和从逻辑角度看美学、艺术史,形成了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和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两种历史方法。两相对照,前者侧重对审美对象的近距离条分缕析,由此衍生的美学、艺术史显得真实而可亲近;后者则侧重对审美对象的远距离观照,为了追求逻辑的一致性,对美学、艺术史的曲解和强暴在所难免。由此,我们可以返观一些当代的美学史著作,逻辑规律的宏观性逼迫研究者将社会、政治、经济等决定因素充塞其中,大量的内容与美无关;逻辑规律的抽象性又使美学史简单枯燥,除了思想范畴的罗列之外,真正富有生趣的审美风尚、审美趣味研究隐匿不见。很明显,真正的美学史并不是社会政治史的翻版,单单关注美学范畴的逻辑演绎也只能使美学史日益丧失其审美特质。在这种背景下,以心理学的介入为美学史研究恢复活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另外,现代心理学、生命科学的发展,也为重新观照美学、艺术的历史提供了雄厚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我们用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代替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注释:
〔1〕〔2〕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40、34页。
〔3〕〔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第3卷第74页。
〔4〕〔5〕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页。
〔6〕〔8〕转引自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3页。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9〕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177页。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