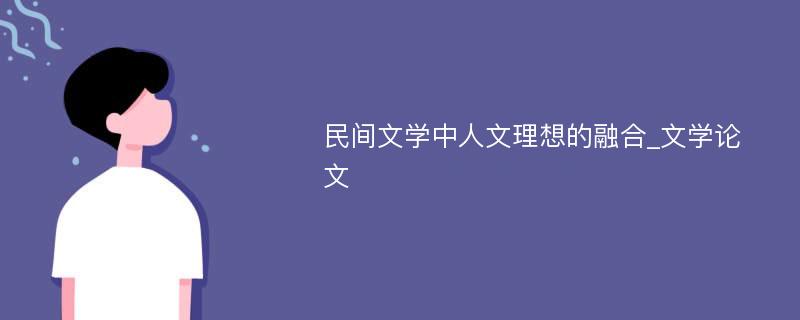
人文理想消融在民间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民间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1)05-0068-03
世纪之交的文学,平民化的创作倾向对小市民的生存状态、苦乐得失给予了某种关注和同情,传达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格调既迎合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的距离。这些小说共同的内涵就是观念消解,建构“社会价值多元”和“个体价值一元”的民间立场。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乃至被抛入到讥笑的荒野之中无人理睬。作家和读者都在世俗的怀抱里过狂欢节,迷失在民间中而无力自拔。
一
中国现代文学以“大叙事”为基点,以一种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姿态,用宏阔的视野表现宏伟的社会文化理想、政治理想,当然包括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理想,是以“人的现代性”为其核心,写作主体是一个以自我标榜为现代意识的代表及其守护神的人文精英分子组成。而“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挫折和疲惫,中国大陆文学出现了一种民间化的倾向。有人‘躲避崇高’,有人‘直面世俗’,有人‘融入野地’,有人为‘民间的还原’而热烈欢呼。一群群作家和评论家放弃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而走向民间,努力获得民间大众话语的同时对‘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精英话语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文学开始寻找所谓‘民间范式’,民间话语成为一种潮流,正迅速地淹没着大陆文学界”。[1]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是知识分子降低文化叙事,转换甚至放弃自己意义立场的开始,方方、池莉率先把笔触伸向世俗的最底层,《风景》再现了汉口“河南棚子”中底层平民辛苦而麻木的生存状态,二哥和七哥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卑贱的命运,但二哥的梦想被“文革”击碎了,七哥虽借助联姻挤入到了上层社会,却也付出了情感的代价,他的奋斗已远离高尚。这里,知识的意义开始消解,作家借此来揭示“生活本身就是个黑洞”的无情事实。方方的“知识分子系列”更是刻划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的窘态,她试图着力探讨知识在民间的人格萎缩究竟是人性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抑或是环境的悲剧?从她的作品里,人们开始感觉到知识在喧闹的社会转型期已逐步丧失其原有的高贵和尊严。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构成“人生三部曲”,不避繁琐地诉说小人物生活的悲苦和欢乐,她忠于生活的原生状态,通过大量琐碎的、平凡的、充满偶然的生活事件表达对生活的感觉和体验。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后,池莉的创作面临着一次潜在的转变契机,是安于世俗,还是超越世俗?在创作视点的选择上,池莉再一次把视点下移,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由认同进而到赞美,《小姐,你早》讲述知识女性戚润物无意间发现丈夫和小保姆私情后,由痛不欲生到伺机复仇,与另一个女人合谋,展开一场阴险的陷害行动。这里,戚润物的知识身份已隐退,泼辣的悍妇骂街,在海鲜城对“美人捞”的观赏,在舞厅里窥视灰暗的人生交易,戚润物已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市侩妇女。作品里不再有“有意义的人”和“有意义的事”,人物和事件的意义取向消融在无休无止的琐碎日常生活和日常场景中,日常感知和日常生活流程淹没了一切理性思考。而到《乌鸦之歌》,池莉则走得更远,融在骨子里的民本态度,使池莉的行文进一步滑向民间化的深处——通俗化,“池莉送给自己、大众一个梦幻的同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纯文学的作家,而滑向了通俗创作。她的小说不再纯粹以作者为本位,进行心灵的求索、苦旅、拷问,而是在创作时预设一个接受对象,根据对象的心理需求照方抓药。阅读时,我们不仅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坐在梦想列车上风驰电掣,一路上处处令人心动的风景悠然而过,还看到一般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东西:高超的武艺、武林秘笈、惊险的打斗、侠骨柔情,甚至,外公成了身怀绝技又忠厚拙朴的郭靖大侠与多情风流的韦小宝的混血儿”。[2]意义溃散之后,“新写实”在文化立场上便下降到日常现实的泥淖中,一反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批判与启蒙精神,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抗性,使自己沉溺于大众实在可感的具象经验中,来逃避意义危机。价值观照和文化批判在这些具象经验面前显得苍白而陌生,任何超越和反抗都被琐碎消解击溃。而自此之后的所谓先锋派文学、新体验小说、新历史小说、平面现实主义,直至到“私人化”、“身体化”写作,一切都心平气和,自顾自怜,历史和人文的思索遁隐了,现代理想精神彻底臣服于民间叙事之中。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民间立场欢呼雀跃,人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很多作家那里同时也日益凸现。“当张承志带着由西方的‘敌意’所激发的民族危机意识与‘被歧视’的怨恨体验回身审视正经历着‘商业化大潮’二度冲击的中国文化现实,便难免会有‘可怕的堕落’这类过激的读解。从而继‘前时期’以来‘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命题之后,提出了‘抗战文学’这一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创作吁求,并与王朔等人的‘痞子文学’构成二元紧张。”[3]张承志选择王朔作自己批判的靶子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因为,王朔在知识分子文化已呈颓败之象的时候,不但不起来拯救,反而落井下石,用最粗鄙的语言挖苦、侮辱自命社会良心、人类希望所在的知识及其分子。王朔最初几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塑造一个市井无赖,肆意地无所顾忌地玩弄、欺辱一个涉世不深却又有点自命清高的女大学生,这在美学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倒不是因为其题材的怪异,而是王朔用一种近乎轻佻的姿态,藐视知识,丑化崇高,以嘲弄嘻戏来解构知识文化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他这只色彩斑烂的毒蜘蛛已是知识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死敌”,自诩为“精神麦地里最后一位守望者”的张承志向其猛烈开火,是试图在文学上保持一种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精神,使其不至于在民间化大潮中迅速沉沦失落。面对张承志们的责难,王朔反唇相讥说:“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4]从这一层涵义上来说,王朔又是民间意义上真正的“英雄”,王朔的“反智”,是通过无情地开涮“知识及其分子”来娱悦大众,为社会底层的民众渲泻心中不满之情,因此他的火力攻击点也集中在知识文化分子的忧患意识、文化批判、启蒙精神等核心价值上。虽然张承志愤怒地谴责王朔“使用一种北京土语作书写的语言,并且一天天推广一种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吃乐喝的哲学”(《无援的思想》)[5],但是,王朔却实实在在地被民众所热爱,其中不乏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价值转换面前陷入价值危机,变得自轻自贱,他们正需借助王朔式的自嘲来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理。所以,人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王朔被嘲弄的对象,即他的“天敌”,却与他一起狂欢,与他一起为“躲避崇高”而喝采,文学的人文精神在民间化进程中不可逆转地消融了。
二
文学为什么会走向民间化?这是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倾向都会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纪之交的民间化倾向便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总的集中的社会化反映。
文学隐入民间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商品机制的生存环境使然,文学的商品化迫使作家必须考虑到社会民众的欣赏口味和兴趣,进入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步入到一个平庸、实利、应顺的金钱拜物教时期,民间化就意味着大众化、商业化。“平民化倾向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哲学基础,理论框架还并不很清晰、系统,然而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潜在的、巨大的、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生活方面,诸如影视、音乐、戏剧等。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经济文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平民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商业社会的一个‘卖点’,是经济得以拓展的手段。”[6]在90年代迅速波及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系列唱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撕破崇高、神圣的面纱之后,人们(特别是新生代)对毛泽东的认识就是和对日本的动画片、美国的麦当劳和崔健的摇滚乐一样充满好奇和逗乐,梁着黄头发大吼毛泽东颂歌只是追逐一种另类感觉的外在表现而已,正如一位音乐制作人所说的:“80年代以前充满神圣和宗教感,那时候唱毛泽东歌曲就像唱圣歌,同教徒唱赞美诗没有什么两样,歌唱的人用圣洁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我们追求的则是今天对毛泽东的理解,注入了许多世俗的东西。”[7]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一旦与经济活动巧妙地联姻,其带有某种空幻的理性思维便被实利行动所取代,魅力无穷的金钱消解了作家对主流话语和贵族精神的迷恋,作品中诗性的生活消失殆尽,庄严的历史使命感成了被嘲弄被冷落的对象,意义成为一个流浪汉,在无人喝彩的世俗旷野中游荡、放逐。人们已习惯去体验那种平面化、欲望化的生活状态,内容完全“还原”于生活本身,所谓“重大题材”已让位于吃喝拉撒睡及七情六欲的日景场面,芸芸众生的小悲小怨、小得小失是作家刻意追求的绝好题材,作家回避外在的判断,使作品获得一种意义的多样性或模糊性,或有时几近于无意义,让作品与现实世界一样实在可感、丰富具体,因而也一样难分彼此、是非泯灭。
文学走向民间的第二个原因是新兴的平民阶层对文学的需求所至,这个阶层要求有自己群体的文化体系。谁都知道,从90年代起,一股“红太阳旋风”在中国大地上突然红红火火地刮起来,它与整个时代的色调似乎格格不入,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感动着人们的心绪,是什么又一次捂热了毛泽东?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民众的一种怀旧情绪使然,而是转型时期一个新兴的平民阶层的心理写照。1993年始,陕北修建了三座“三老庙”,庙里都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塑像,修庙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积极,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因为“由于年龄、经历的关系,他们往往有一种失落感,感觉被时代抛到了一边。某一个人也好,某一群人也好,只要当他的感情、生存与社会的关系等受挫,内心深怀无措、没有依托以及被冷落和遗弃感到难以改变时,往往表现出喜欢采取怀念过去的方式。”[8]
当社会向商业时代转型时,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平民阶层在中国土地上正重新聚合,这个博大庞杂的平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素养和政治权利都与其他阶层不同,这个群体是一个庞大且散乱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的集合群,其派生出来的是某些朴素的反抗情绪和某些不加掩饰的自私、猥琐、庸俗乃至愚昧,其受权力的控制却包含一种对权力的冷漠、疏远、鄙夷、抗拒。他们生活平凡乏味因而追求那种软性的肤浅的文化消费,他们淡漠艺术的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远离历史真实和思想真实。一些敏锐的作家在民间化进程中开始寻找文学新的形式确立文学新的定位,自觉迎合“民间范式”,主动放弃主流地位和启蒙姿态,自觉适应市民、适应市场、反省自己、调整自己。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进行自我否定,其创作基点与世俗化、民间化或者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已处于双重尴尬的境地,相当一部分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的知识分子已经沦落为平民阶层,平民的现实艰难与困苦势必在他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理想上造成一定的迷惘徘徊,于是理想虚无了,英雄淡出了,在“价值判断失语”中生发一种“平民价值”。在这种“平民价值”诱导下的文化世俗化也使得作家们的地位意识发生改变,王朔曾多次戏称自己的作家身份不过是个“码字儿的”,而当有人称何顿为著名作家时,何顿断然否定“作家”这个称谓,辩说自己写字只不过是为油米酱醋养家糊口。这种地位意识的改变,一方面使作家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实践都彻底生发一种“平民意识”,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其创作缺乏内在精神、丧失价值深度。
理想陨落,精神滑坡,一切都原生化到琐屑和平庸,意义在民间中终于消融了。然而,在清算了虚假的理想对大众的愚弄、扫除了道德准则对大众的压迫、嘲讽了精神对人的物质欲望权的剥夺之后,我们是不是有理由冷静下来想一想,中国当代真的就不需要精英文化了吗?利用民间力量来反精英,或利用大众的声音打击知识分子,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民间社会的喧嚣中,或者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化入民间的喧嚣之中,那么,这个时代也肯定是一种病态。”[9]所以,尽管现在所谓走向民间、立足边缘的小说在一片“饿死狗日的诗人”声中异常火爆、产销两旺,我们还是欺盼着文学在民间化的过程中融入一种具有生命气息的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也许,别致的民间经典创作将会凸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
收稿日期:2001-06-04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王朔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张承志论文; 池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