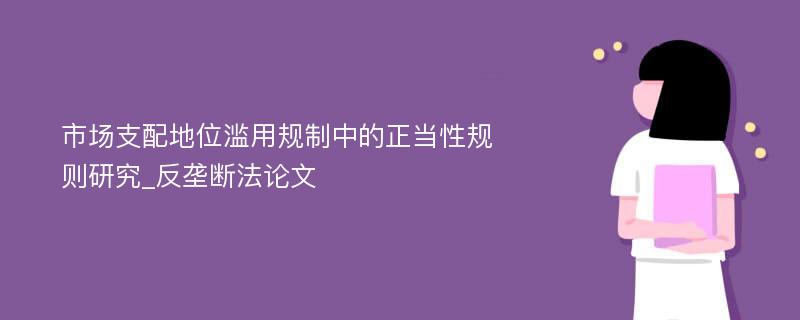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中的正当理由规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当论文,规制论文,地位论文,规则论文,理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75(2015)05~0114~13 自《反垄断法》于2008年起施行,至今已六年有余。在前三年的实施当中,《反垄断法》绵软无力,甚至被称为“无齿之虎”。但从2012年起,伴随一批“垄断”企业被查处,《反垄断法》执法渐成常态化趋势。面对汹涌的公权力机关执法活动,经营者似乎并无招架之功。而在执法机关与经营者围绕垄断行为合法性进行博弈时,双方实际触及到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法律命题: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如何划清边界?也即判断经营者行为在多大限度内是正当的。对此,《反垄断法》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则安排如下:若无正当理由,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的垄断高价或低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限制交易、搭售以及差别待遇等行为应视为违法①。这就是正当理由规则的直接渊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违法性判定必须以排除经营者行为正当理由为前提。在实践中,经营者也基于自身行为具备正当理由而提出抗辩。例如,出于产品整合创新目的②、维护产品品质③、应对对手竞争④等都曾作为经营者行为正当性的抗辩理由。实践中经营者提出的“正当理由”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归纳、论证。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正当理由规则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者们仅在法律价值层面分析正当理由的内涵[1],而并未深入研究正当理由的类型及体系。另外,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对正当理由内容的讨论,而未能将其作规则化分析并深入研究正当理由规则的实施机制,例如正当理由的证明责任、实施程序等。上述理论空白反映在法律实践,就体现为正当理由规则缺乏明确的实施指引。因而,对正当理由规则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成为必要。 一、正当理由规则的规范渊源 法治要求规则的统治,同时,规则必须具备形式规范性和构造合理性才能实现善治。为实现《反垄断法》确定、合乎逻辑的规范经营者行为,正当理由规则应当在形式和内容上具备合理性。当然,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市场环境存在差异,正当理由规则的规范形式也有所不同。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考虑到“不公平”与“没有正当理由”在“非正当”含义上的相似性,可以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离不开对行为正当理由的排除。从结构上讲,正当理由规则体现为“非P,则Q”(P表示正当理由,Q表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逻辑形式。应当说,此种立法例并非我国独有。例如,德国将“无实质正当理由”作为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要件⑤;日本以“不正当”“不公正”“不公平”作为私人垄断行为违法的条件⑥;韩国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以行为“不合理”“无理”“不公平”为条件⑦;其他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瑞典等也都作出了相似规定⑧。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的虽然没有直接以“没有正当理由”(No-Reason)否定滥用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在法律实践中,执法机构仍然需要考虑经营者行为的正当性⑨。欧盟委员会也在《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2条查处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性排他行为的执法重点指南》(以下称《第82条执法指南》)第28段强调经营者行为的客观必要性和实质性效率需要委员会予以评估。 正当理由规则在另外一些国家立法中则表现为“若P,则非Q”的逻辑形式。在美国,经营者实施价格歧视是非法的。但如果价格歧视是由于“制造、销售、运输成本不同”而做出的补贴,或者是因对方交易数量有别而采取的价格差别,抑或是交易涉及私人财产、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易腐烂商品、司法扣押品以及停业中的商品销售,那么该行为就不涉及非法⑩。也就是说,经营者行为满足上述条件(P),则不构成价格歧视(Q)。瑞士《联邦反卡特尔和其他竞争限制法》第8条也规定,若因“有力的公共利益理由”,则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可申请联邦委员会批准。南非《竞争法》第8节也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若能“促进技术、效率或其他有利于竞争的效果”,则该行为不被视为非法。马来西亚《竞争法》第10条第3款也规定,处于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采取的具有合理商业理由的措施或者对竞争者采取的合理商业反应并不受禁止。 正当理由规则的两种逻辑形式规定了不同的事实判断程序,在两种逻辑形式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程序启动、当事人证明责任分配都明显不同。在“非P,则Q”的逻辑形式下,缺乏正当理由是认定经营者违法行为的法律要件,因而必须由指控者证明。而在“若P,则非Q”形式下,正当理由规则则成为经营者抗辩指控的权利妨碍规范。两种逻辑形式,前者使得反垄断法的适用相对审慎,但由于掌握“正当理由”的信息劣势,执法机构很难发现案件事实。后者虽然通过经营者信息上的优势能够使裁判者掌握正当理由事实,但是也“激励”了经营者创造更多于己有利的“理由”。在执法机构或者裁判者处于信息劣势的前提下,经营者提供的正当理由事实也并非真正的案件事实。但好在两种逻辑形式在价值判断上保持了一致,那就是经营者行为在反垄断法价值多元化背景下有可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理由可能源于《反垄断法》内在价值与规则的统一,也可能来自外部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正当理由规则能够在“形式”和“实质”(11)上都满足合理性要求。从而保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不至出现偏颇。 因而通过分析正当理由规则的形式与内容,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澄清。一是为何在传统上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中规定正当理由规则?二是正当理由的内涵是什么,哪些合理因素可以构成正当理由。对于纷繁的合理因素,是否可以结合不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做出类型化分析?三是正当理由规则如何实施,其实施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二、正当理由规则的理论基础 (一)正当理由规则彰显反垄断法价值 从各国立法看,自由毫无疑问是反垄断法所首倡的价值。如果当事人被经济上强势地位者或者社会优越地位者所压迫,在事实上并无决定自由或者缺乏事实上选择被许可之事的可能性,那么自由价值将毫无意义。正如谢尔曼参议员对经济自由的论证:“正如无法臣服于一个君主,我们也不能屈从于一个贸易上享有排除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12)。因而,为维护市场主体意志不受压制、行为不受限制,反垄断法必然通过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来实现市场的整体自由。这就是为何对经营者搭售、任意定价、附加交易条件、实施歧视性待遇等看似符合契约自由的行为予以禁止的原因。但是为防止国家“好心办坏事”,出现干预悖论,反垄断法对自由限制的行为本身也需要“限制”,否则国家干预肆意侵入私法自治的领地必然造成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冲突。为了协调这种冲突,反垄断法一般对执法机构或者裁决机构附加一定的论证负担,也即主张限制个体自由的裁决者必须负担论证自己价值取向正当的责任[2]。换句话说,无正当理由,不得对经营者的自由经营予以限制,这就是正当理由规则的逻辑起点。具体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制度,该规则体现为:无正当理由,反垄断法不得对经营者搭售、任意定价、附加交易条件、实施歧视性待遇的个人自由予以限制。 正当理由规则不仅彰显反垄断法价值内容,而且也体现了反垄断法多元价值的冲突与协调。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都认为,反垄断法存在多元价值(13)。在谢尔曼法生效之初,其主要目的在于分散经济权力,保护竞争秩序。随着保守主义思想对经济政策的渗透,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效率也成为反垄断法实施所重点考虑的价值目标。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反垄断立法中存在博弈,每个主体都要为自己的利益目标寻求价值正当性。因而反垄断法价值多元化必然引起价值冲突,而裁判者也不得不为保护此价值而牺牲彼价值。为了衡平价值冲突,反垄断法必须作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规则安排,否则反垄断法制度将丧失理性。其中这类规则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正当理由规则。正当理由规则强调,为保护某项价值目标而不得不牺牲另一项价值时,必须充分论证这种取舍的合理性。以搭售行为规制为例,反垄断法将搭售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依据就是搭售可能造成经营者在结卖品市场的垄断力量不正当的向搭卖品市场传导,从而在结卖品市场对消费者造成强制,在搭卖品市场造成对竞争者的排他效应。因而搭售行为极有可能损害自由、公平价值。但是,经营者实施搭售也可能基于保证产品品质的要求、互补产品搭配产生配置效率、新产品或新市场的风险公平分担、降低产品销售风险等理由[3]。因此搭售可能存在满足反垄断法上效率、公平以及消费者福利等价值要求。那么正当理由规则就强调在认定搭售违法时要排除其行为合理性,也即在不同的价值冲突中寻求平衡。 (二)正当理由规则体现反垄断法实质理性特征 法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形式指的是法律内在的东西,实质指的是法律外部的世界”[4],实质理性主要强调“(决定的)裁判标准是由法外因素所决定,如基于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宗教的等等其他非法律因素来判断”[5]。由于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导向,国家干预也日益参与到法律的实施,目的在于维护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竞争”“公平”“效率”以及“消费者福利”等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目标很难在立法中给出量化、明确的规定,因而使得反垄断法裁决不得不依赖法外的经济、社会甚至是商业伦理与道德因素进行解释。而正当理由规则也是裁判者寻求反垄断法外裁判标准的重要路径。 1.正当理由规则内容更多标准性 规则的标准性或者标准规则主要指的是规则有关“构成部分(事实状态、权利、义务或后果)是不很具体和明确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或特殊对象加以解释和适用”[6]。按照波斯纳的解释,在“如果X,那么Y”的规则中,标准性指的是要确定X,必须权衡数个非量化因素,或以其它方式作出一种判断的、定性的评价[7]。因而,标准规则与规则构成都明确具体并能直接适用的规范规则有本质区别。正当理由规则就是典型的标准规则,无论是“若P,则非Q”还是“若非P,则Q”的逻辑形式,作为规则构成要件的正当理由(P)都是模糊、复杂的。因而必须对正当理由作出解释、权衡,裁判者才能据此作出相应的判断。并且对正当理由的解释不能完全依赖反垄断法的内在逻辑,还必须衡量经济的、社会的以及商业伦理或道德层面的因素。 2.正当理由规则推理更多实质性 由于无法直接适用正当理由规则作出适当的裁决,因而裁决者在法律推理中不得不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手段。一方面,裁决者求诸目的型法律推理。通过考察正当理由规则确立时的经济环境、社会背景,从而按照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作出立法原义解释。或者考察正当理由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现时的法外环境作出符合法律实施目的的解释。另一方面,实质性的推理不仅要明确规则的构成要件,还需要对规则实施的法律效果进行评估。能否满足反垄断法的价值要求,能否实现增进经济效率、公共利益以及消费者福利等社会效果,这些法律效果都需要在正当理由规则的推理中予以考虑。 正因如此,我们对正当理由规则研究也离不开对其实质理性特点的把握。首先,必须结合经济、社会以及商业伦理道德等法外因素才能对正当理由内涵作出科学界定。其次,对法律效果或者社会效果的评估对于正当理由规则推理至关重要。再次,由于法外因素进入正当理由规则的推理,因而立法者、裁决者的知识构成应更具复合性。在正当理由规则的推理中进行经济分析、社会效果评估等实证考察也将成为必要。 (三)正当理由规则的实施以合理原则为框架 “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上的重要概念,其性质、内涵至今仍众说纷纭。从历史上看,合理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上的米歇尔诉雷诺兹案,在该案中,原告要求被告签订具有限制条件的合同,被告认为限制贸易的合同应当无效。但是法官认为,贸易限制应当分为一般限制(general restraint)和特别限制(particular restraint),一般限制应受谴责,而部分的或从属的特别限制应予以支持[8]。由此衍生出“无正当理由不得禁止合同自由”的普通法原则。后来,在“标准石油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怀特基于普通法上对“限制贸易合同”的解释,认为“如果限制在实施中是公平的,并有其他的合理理由,则合同就是有效的”(14)。按照《谢尔曼法》第1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属于“限制贸易”的行为。因而,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也应当坚持“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正当理由规则与该原则一脉相承,表现为:无正当理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得禁止经营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充分反映了合理原则的精神。 在正当理由规则实施中遵循合理原则还在于二者性质与功能的契合。合理原则是“一种分析模式,一种引导调查和判决的制度”[9]。而正当理由规则由于自身构成要件存在模糊性,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以及判决的作出都离不开合理原则的指引。关于这一点,波斯纳的观点更为明确,他在谈到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的区别时强调,“它们所表示的是法律上的根本区别,是规则与标准的区别”[10]。也就说,如果反垄断法规则属于规范规则,那么依靠严密逻辑和确定性构成就可以将规则适用于具体行为,这种思维被称为本身违法原则(15)。而如果是标准规则,法院的调查和裁判必须依赖法外因素,那么这种思维被称为合理原则。根据上文的分析,正当理由规则具有标准性,必须分析经营者行为的经济、社会以及商业伦理道德正当性,才能判断行为是否违法。因而这种寻求法外裁决因素的逻辑实际是在贯彻合理原则。 三、正当理由的类型分析 正当理由概念高度抽象,从形式上看,符合“正当性”要求的概念都有可能置于正当理由外延之下。按照法律逻辑学的解释,外延过大会导致外延概念间失去共同性,正当理由内涵反而愈见空洞,因而正当理由规则由于抽象过度而缺失规则应具备的“丰满性”。另一方面,经营者在实践中又提出形色各异的“理由”,由于缺乏统一的解释,这可能导致个案各判,使正当理由规则丧失确定、普适的“理性”光彩。由此可见,在正当理由解释问题上存在规范与事实脱节,抽象与具体不符的矛盾。 因而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类型思维方法。德国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研究法律推理时曾提出,在当为与存在之间需要一个“第三者”中介,一个同样代表特殊与普遍,事实与规范的构造物,一个个别中的普遍,一个存在中的当为。按照考夫曼的解释,这个“第三者”就是事实与规范共同表现出的“事物的本质”[11]。因而,寻求抽象与具体联接点的思维实际就是类型思维。没有类型就没有思维,哈特甚至认为,“对具体事物的分类是法律决策的核心”[12]。由此可见,设计法律类型是使法律规则具体化、法律事实抽象化并解决规则抽象性与事实具体性矛盾的重要法律方法论。由于类型处于事实与规范“中介”“中点”位置,因而寻求类型的途径一般也不外乎两种,一是“对贴近生活事实的研究对象予以归纳、抽象,将其共同性方面整构成一个类型”;二是“对接近于一般法理念和非确定的法概念的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化,使其丰满成一整体性类型”[13]。所以正当理由类型的型构也可以通过归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事实并发现经营者行为合理理由的共性,或者依靠反垄断法价值理念并将其具体化而实现。当然,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使我们能把已有的全部知识初步条理化,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知识”[14]。那么所谓“新的知识”其实就是个体的共性或者考夫曼口中的“事物的本质”,这也是将这些正当理由归为一类,而将另一些正当理由归为另一类的原因或标准所在。而通过归纳和具体化途径,我们可以把正当理由划分为效率、公平以及经营需要三种典型类型。 (一)正当理由的效率类型 毫无疑问,效率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在波斯纳法官眼中,效率甚至是反托拉斯法的唯一价值目标[10]2。因而,经营者常以行为具备效率价值作为抗辩的正当理由。欧盟在《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2条执法重点指南》(以下称《指南》)中提出,“执行第82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委员会将对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提出的宣称其行为正当性的主张进行调查”,而正当性主张一般基于行为能够产生“实质性效率”(16)。而根据美国《知识产权许可反托拉斯指南》,主管机构在判断限制行为具有反竞争效果前提下将会考虑该行为是否为达到促进“竞争效率”所必须(17)。由此可见,效率是受到反垄断法重点关注的因素,而经营者也可能基于其“垄断”行为具有效率上的正当性而抗辩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指控。其中,效率概念又包含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两种外延。前者强调经营者必须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后者则要求经营者行为需产生消费者福利。 1.生产效率 如果经营者的生产、营销活动能够提高生产率,带来社会总产出的增加,那么可以认为其行为具备生产效率。以信息产品为例,信息产品研发成本较高,但复制成本却极低,一旦研发成功就可以大规模复制,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也即,信息产品必须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平均成本。因此,即便经营者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也往往采取低价甚至免费策略销售自己的产品。另外,在刚刚面世时,一些产品可能缺乏消费者体验或者生产技艺并不完善。因而这些产品需要在大规模推广中获得生产经验,而经营者推广的方式也可能是低价销售。从形式上讲,上述营销方式很可能被认定为掠夺性定价。但是,由于经营者实际上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生产或销售的规模经济,因而其行为具备效率上的正当性。 除低于成本定价外,搭售也可能具备生产效率。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言,如果多产品生产需要相同的投入要素,不同产品分享相同的知识、技术和工艺[15],或者可以进行共同运输、推销等,那么两种产品搭售可以获得更有效率的生产或销售。例如在Crawford运输公司诉Chrysler公司案中,Chrysler就通过将产品销售与运输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法院也认为,虽然Chrysler通过搭售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成本节约,但这并非垄断汽车运输市场所得(18)。不仅如此,很多搭售产品具有互补性,产品之间产生网络效应,也即伴随结卖品用户增加,与之互补的搭卖品也能获得销售增长,同时搭售产品增加了彼此对消费者的价值。 2.配置效率 如果经营者在生产中的成本节约无法有效地配置给消费者,那么效率作为经营者行为正当性的理由也不会充分。因为,“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是要阻止财富从消费者不公平地转移给拥有市场势力的生产者,即防止其通过垄断剥夺消费者应得的福利”[16]。因而,配置效率作为效率价值的另一层含义也应当成为经营者行为的正当理由类型。 从广义上讲,对商品或服务良好的主观体验以及客观上的消费者剩余都属于消费者福利的范畴。具体而言,它体现在以下类型当中。一是降低价格。这是经营者以最直接的方式将成本节约配置给消费者,无论是掠夺性定价还是搭售,经营者通过明示低价或者暗中折扣的方式使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较好的商品或服务。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经营者的某些行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效率上的正当性。例如,经营者提供技术匹配、功能互补的搭售产品,免去了消费者因自身经验不足而产生的搜寻成本、学习成本。三是保证质量。有时经营者可能为保证产品的品质,维护自身品牌商誉而实施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是因为产品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完整的产品系统或环境,互补的产品、兼容的技术或者统一的标准对于产品功能发挥必不可少。而稳定的产品功能是消费者享受优质服务的基础。因而,经营者可能采取独家交易或者搭售的方式来保证产品品质。在独家交易中,经营者限制交易相对人只能与自己交易,可能是基于自己在提供系统产品、标准产品方面的优势。例如,消费者只能到经销商指定的4S店接受配件服务,原因在于只有这些4S店提供的配件才完全符合整车的质量要求。搭售也有这方面的要求,例如在Kodak案中,Kodak公司要求购买柯达胶卷的顾客要到本公司冲洗。柯达公司的理由是其他公司技术不能达到良好的冲洗效果,因而可能会影响柯达胶卷的品质(19)。 (二)正当理由的公平类型 除了追求效率,反垄断法另一项重要目标就是保护消费者、中小经营者免受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剥削和压迫,防止“巨型公司非人格化的或者其他无耻的行为”“保护商业的轻易进入”“鼓励商业行为的公平性和合道德性”[17]。而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反垄断法往往扮演损害实质公平、应受道德谴责的角色,所以这类经营者似乎不应受到公平价值的关照。但是,公平价值本身强调不同主体利益的恰当协调,并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其适用应具普遍性,不能因为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差别而受到不公平或者泛道德化的苛责。因而,如果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确有对公平价值的诉求,那么也应当将其列为经营者行为正当理由类型。 1.成本抗辩 成本抗辩(cost justification)也称成本合理化抗辩,它是指经营者基于成本差异而给予不同交易对象有差别的待遇,并就此寻求差别待遇行为正当性。差别待遇常被视为违背公平原则的行为。但一些情况下,经营者作出差别待遇的决定也源于对公平价值的追求。这是因为公平概念内涵“不同之人给予不同对待”含义。在经济活动中,公平价值通常体现为收益在买卖双方的合理分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经营者制定的有差别的价格源于不同成本约束,那么这种差别对待也符合公平原则。正如《罗宾逊—帕特曼法》所规定的,如果经营者的制造、销售及运输成本不同,或者经营者销售存在不超过法定数量标准的数量差异,那么,由此造成的价格差异可视为因成本不同所作的合理补贴(20)。因此,经营者可以对自己的价格歧视行为给出成本合理化抗辩的理由,并且成本抗辩是建立在公平分配收益基础之上。 另外,经营者提出成本抗辩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价格差异只取决于与定价有关的成本差异。也即影响定价的因素有多种,直接影响成本差异的因素才能构成成本抗辩。例如,在联合商标公司诉欧委会案(21)中,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认为,由于联合商标公司的定价只存在批发环节,那么这一环节的市场因素,如香蕉产量与市场需求关系、海运成本、装卸费用等与成本直接相关,但发生的零售环节的各国市场供求因素不是合理的成本抗辩。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则就成本范围作出解释:装载和运输成本、目录支出、单独用于一位顾客或一群顾客的销售所使用的设备折旧、佣金全部退还所有的顾客以及制造成本应当计入产品成本范围[18]。也就是说,基于上述因素发生的成本差异属于允许经营者实施价格歧视的正当理由。 2.风险分担 在新产品或新市场的开发过程中,经营者往往面临产品能否成功推广、市场需求能否产生等不确定性,因而经营者承担着新产品、新市场开发的风险。这类风险包括消费者不会使用新产品、新产品无法获得稳定的技术及配件支持、新产品缺乏推广渠道等。一旦风险成为现实,经营者就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甚至失败。因而,经营者往往采取搭售策略使风险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并增加新产品成功的机会。因为将新产品与畅销产品一同销售,能起到类似广告的作用。有的情况下,新产品由可以分别独立的配件产品构成,但是经营者并不认为市场上的其他配件组装可以达到与自己产品同样的效果。例如,在Jerrold Electronics案(22)中,被告较早的开发了一种闭路电视系统,其中使用到天线、增压接收器以及连接到用户家中的电缆。这些配件在物理上是独立的,但被告将其组装售卖,不允许单买。并且法院也认为这种打包销售是合理的。因为,这种闭路系统刚刚兴起,消费者对其构造及运行并不了解。如果强制被告分开销售配件,消费者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而消费者擅自改装造成的损害也很难向经营者主张。因而,允许新产品搭售实则是买卖双方共同分担产品推广风险的公平之举。当然,这种方式必须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如果市场或产品已经成熟,经营者就再无实施搭售的合理性了。 (三)正当理由的经营必要类型 “经营必要”类型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经营者行为既无充分的效率基础,也无明显的公平色彩,而是为了正当的经营需要。并且,产生正当经营需要的原因在于经营者面临恶意竞争、严重的生存危机,或者独特的经营模式使然。例如,美国对价格歧视的规制并不限制市场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以及易腐烂商品、司法扣押品和停业中的商品销售,也不限制经营者善意、平等的适应竞争者价格变化的行为(23)。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也要考虑“有关行为是否为经营者基于自身正常经营活动及正常利益而采取”(24)。欧盟在《指南》中也强调,执法时需要考虑经营者证明其行为是客观必要的主张(25)。由于经营者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活力维系着市场组织系统的健康。因而,一旦经营者失败,必然影响市场整体效率。所以,允许经营者以“经营必要”抗辩垄断指控,也是反垄断法维护市场合理竞争的应有之义。而就内容而言,经营必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应对竞争 竞争对经营者而言也是一种风险,顾客可能因竞争者策略行为而发生转移。因而,经营者通常为应对竞争而采取相应措施,这对企业正常经营非常必要。当然作为正当理由类型,应对竞争也应当具备一定条件。以价格歧视规制为例,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第1条(b)款规定,如果卖者的低价或劳务、设施的提供是善意地,平等地同竞争者的低价,或与竞争者提供的劳务、设施相适应,那么可以推翻认定其价格歧视的初步证据。由此可见,应对竞争的抗辩具备两个条件才能作为正当理由予以适用,一是善意(in good faith),二是应对(meet)。关于“善意”,一般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判断。在Staley案(26)中,法院认定,实施价格歧视的卖方必须证明其给予的更低价格能够应对一个竞争者的同等低价。也即,经营者主观上仅以保护自身经营为目的而无垄断或掠夺企图。经营者客观上面临来自竞争者的压力,且自身采取的价格歧视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仅如此,经营者还需证明“竞争者的低价本身也是合法的”(27)。因为,一个合法的行为不能以违法事实为依据。而关于“应对”,则一般认为经营者是被动的适应竞争而非主动发起竞争,并且实施的价格并非打败对手的低价。那么,经营者的应对就很具有“防御性”“可能仅仅为了留住与老顾客的生意”(28)。但从《罗宾逊—帕特曼法》条文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立法并未就此作进一步解释,实际上,为获得新顾客而实施的价格歧视也能援引应对竞争的抗辩(29)。 2.特殊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是个管理学概念,它是指“做生意的方法,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模式,一种能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商业模式规定了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指导其如何赚钱”[19]。由此可见,商业模式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一个结构,由各种要素组成;第二,商业模式各组成部分紧密相连,离开任一部分,企业也无法创造价值。如果不理解商业模式及其结构要素对于企业经营的必要性,那么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被执法者纳入反垄断法规制。 我们以新经济中常见的平台商业模式为例,它由平台经营者、分属双边市场的两类参与者构成。平台经营者往往给予一边市场参与者价格折扣甚至免费,而对另一边市场参与者制定符合价值规律的定价。但是上述两种定价却极易被认定为掠夺性定价和超高定价,从而招致反垄断规制。应当说,这种观点存在重大误区,没能认识到平台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平台经营者定价的必要性[20]。目前,平台商业模式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应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软件应用平台都是典型的平台商业模式。而平台商业模式的成功源于双边市场间的网络外部性,也即一方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能给另一方参与者带来收益的增加。因此,平台经营者需要设法将用户吸引到平台参加交易。而为激发网络外部性并实现用户规模的增加,平台经营者则需要实施倾斜性定价结构。这就是对需求价格弹性大、单归属性、网络外部性强度高的参与者实施免费定价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反之,则对另一方参与者收费。并且,考虑到双边市场的总价格加成,必须以平台的总成本作为判断价格高低的基准。由此可见,平台经营者的价格策略实在是出于构建平台商业模式的需要。 3.特殊情势 虽然用“特殊情势”来概括该部分经营者行为的正当理由,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上述正当理由类型的兜底。就已有成文法及判例而言,出现下述情形时,经营者往往采取看似具有排他性或者掠夺性的行为。这些情形包括交易抗辩,特殊商品销售以及企业经营困境等。第一种情形主要针对拒绝交易行为,当交易对方涉及严重诚信问题,或者客观上无法完全履行合同,经营者可能基于履行抗辩权拒绝再向对方供货。这种情势下,经营者并非意图排挤对手,而是考虑到对方可能履行不虞。因而为使自身经营不致遭受风险,经营者可据此主张自己的权利。第二种情形主要指的是特殊商品如不采取低价、搭售的方式销售可能会造成生产、销售的浪费。这些特殊商品包括易腐烂、超过时令或者已被新产品替代的老旧产品等。该类商品的销售可能面临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以及搭售指控,但经营者目的并排挤竞争或者掠夺,因而往往可作为行为正当理由。第三种情形则是指,经营者如果面临破产、重整的困境,采取销售上的非常手段基本也能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由于这些特殊情势很容易举证,因而反垄断执法机构一般也都对基于上述理由而采取的行为作出排除。 四、正当理由规则实施程序问题及其解决 正当理由规则的实现需要对正当理由实体内容予以澄析,还需要对实施程序进行合理设计。这是因为,虽然正当理由规则作为一项实体性规范,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和经营者提供了权力(利)基础。但由于正当理由规则高度抽象,可能会带给执法机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对于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执法机构与经营者常常陷入价值选择的冲突。对此,科斯教授强调,“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力工具”。由此可见,将价值判断转化为程序问题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为此,有学者提出,程序化应成为反垄断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21]。 按照《反垄断法》实施中国家公权机关的参与和分工,可以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正当理由规则的实施分为行政模式与司法模式。其中,行政机关具备反垄断知识和技术优势,从而使反垄断法实施呈现“行政中心主义”,但同时也带来人们对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的担忧和诟病。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虽长于程序控制,但在知识生产层面却并未“适应反垄断浓重的专业化底色”[22]。由此可见,无论行政执法还是司法程序,正当理由规则的实施都需要在程序细节上作出适当调整。如果适用行政程序实施正当理由规则,就需要严格限制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适用司法程序,则需要增强司法机关的知识生产能力,提高司法机关解决反垄问题的专业性。 (一)正当理由规则行政实施的程序控制 针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一般要通过调查、证明、听证以及决定等程序进行规制。在此过程,信息不对称导致执法机构难以明确经营者行为目的和效果,因而在适用正当理由规则时存在裁量权失当的情形。为此,加强正当理由规则行政实施的程序控制成为必要。 1.加强经营者参与程序控制 按照《反垄断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正当理由规则采用“非P,则Q”的逻辑形式。也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排除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存在正当理由的可能。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正当理由的信息往往为经营者所独有。因此,正当理由规则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据实际分布不相匹配。为克服这一矛盾,经营者应当积极参与程序控制。按照当前立法,经营者参与程序控制大致有两条途径。 第一,针对执法机构的调查或决定,经营者有权申辩。《反垄断法》第43条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有权陈述意见并提出相关事实、理由和证据,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此予以核实。《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因此,当存在行为正当理由,经营者可以积极申辩、陈述意见并提供充分的证据。为此,执法机构也应当加大调查权,对经营者正当理由事实与证据进行检查。比如执法人员可以进入经营者场所,检查经营者账簿或其他记录,要求经营者对正当理由证据予以解释等。 第二,经营者有权获得听证的权利。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对听证程序有所规定,但实际均为收集意见的“非正式”程序[23]。因为我国听证程序缺乏严格的证据规则,仅为当事人表达意见提供场所,因而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并无实质约束力。为保证经营者听证权利,有必要引入正式的听证程序,也即将听证程序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裁决的必经环节。例如,《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竞争规则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欧盟委员会只能基于相关各方在听证程序中已发表的意见来作出决定。而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556条规定,听证记录是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决策的唯一依据,这一规定也被称为“案卷排他规则”。因此,在正式听证程序,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听取经营者辩护意见,以保证经营者能充分辩护其行为的正当性。 2.加强正当理由规则的经济分析 通过前文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正当理由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因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适用正当理由规则时需进行自由裁量。但若缺乏科学的分析工具,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可能会丧失合理性,自由裁量或张或弛都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而,如果能够事先对经营者行为效应以及执法机构规制后果作出评估,在执法程序中加强对正当理由规则的经济分析,则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进而提高正当理由规则的适用性。加强正当理由规则的经济分析,关键在于对成本收益分析工具的应用。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分析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正当理由与反竞争效应。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因素:经营者行为对自身的不可或缺性,对消费者福利的贡献与损害、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和损害等。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制行为本身也应当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比如,规制造成时间、货币损失以及其他风险。为便于成本收益比较,经济分析应当原则上按照货币化分析到其他量化分析,再到定性分析这样的优先次序进行[24]。然后,执法机构应当对上述评估后果货币化并比较成本收益。 (二)正当理由规则司法实施的知识供给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正当理由规则实施的司法程序指的是在原告提起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诉讼中,经营者提出自己行为具备正当理由,以避免被认定为行为违法的过程。由于司法机关在知识储备上并不具有技术优势,加之司法的被动属性,因而正当理由规则实现的司法通道往往面临信息不充分障碍。法院若进行政策分析,将因信息不充分、能力不足以胜任而导致误判[25]。因此,正当理由规则的司法实现应当在程序设计时着力解决司法机关知识匮乏、专业性不足的劣势。 1.合理分配证明责任 按照学界的通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指的是在诉讼中将提供证据的责任分配给一方当事人,并且该方在举证不能时要承担败诉风险。因此,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必然积极提供证据,抗辩对方的指控,从而为法院查清事实提供信息基础。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分配能够直接决定司法机关的案件事实的查清和对法律后果的判断。那么,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也应当对证明责任予以合理分配,从而激励当事人提供案件信息,“拓展法官采集决策信息的空间”[22]50。 就正当理由规则的证明责任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由被告经营者来承担。一方面,被告经营者承担正当理由事实的证明责任具备规范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被诉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如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理由进行抗辩,则被告应对此承当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被告经营者承担正当理由事实的证明责任也具备法理基础。一是正当理由作为案件积极事实,应当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在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是消极事实:被告“没有正当理由”;而被告主张的则是积极事实:自己具备“正当理由”。从逻辑上讲,原告必须穷尽一切被告具有正当理由的可能性才能完成举证责任,而被告仅需提出些许正当理由即可完成举证责任。两相比较,主张积极事实难度自然要低于消极事实。并且从古罗马时代,就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无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二是正当理由证据距离被告更近,因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更为方便。美国法学家麦考密克曾提出,证明责任的分配取决于对一个或多个因素的衡量,其中“方便”“公平”就是衡量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有关争点的事实独为一当事人所熟知时”,则该当事人应当就此负担证明责任[26]。正当理由事实存在于被告经营者从事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客观因素中,因而由被告证明该事实才是合理的安排。 2.适当引入专家意见 正当理由规则的实施具有强烈的技术色彩,特别是经营者行为效率分析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法院从人员素质到知识构成,显然缺乏对正当理由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的能力。由此,从司法系统外部引入专家意见成为必要。相关领域的专家可以针对经营者行为的经济原理、模型等作出专门的解释或说明,以满足法官对案件判断的知识需求。就法律渊源而言,《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该条规定为法院引入专家意见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由当事人聘请的专家如何保持中立却也一直存在争议[26]24,因而,我国法律规定的专家意见对法院并无实际约束力。对此,英美法系诉讼中的“法庭之友”制度经验可资镜鉴。“法庭之友”在主体上涵盖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法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各个行业技术人员等,因而它具备完整、专业的知识构成。另外,“法庭之友”专家既可以由当事人请求,可以由法院邀请,也可以自己主动申请参与诉讼,因而能够相对保证其中立性。结合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一方面,应当明确专家意见作为专家证据使用,从而强化专家对正当理由解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建议由法院直接指定专家提供相关意见,以维护专家意见的中立性。专家意见的适当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正确判断经营者正当理由提供知识基础。 五、结论 正当理由规则关系到经营者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而该规则成为执法机构与经营者博弈的重要工具。但立法的抽象性使得正当理由规则无法有效实施,因而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正当理由的解释充满分歧。对此可通过类型分析方法对正当理由进行阐释、归纳,划分为效率、公平及经营需要三大类型,从而消弭规范与实践的矛盾,实现反垄断法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根据不同的福利标准,可将效率进一步类型化为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经营者可依此提出效率抗辩。基于对经营者和交易对象利益公平协调的考虑,可将正当理由的公平类型进一步划分为成本抗辩和风险分担。反垄断法不仅保护竞争也保护竞争者,因而经营者维护自身经营的客观需要也具备正当性,这一方面的正当理由可划分为应对竞争、特殊商业模式以及特殊情势等类型。执法机构自由裁量过于宽泛,司法机关裁判又面临专业性不足,上述困境构成正当理由规则实施的主要障碍。为此,一方面加强经营者参与程序控制,加强经济分析,实现对正当理由规则行政实施的程序控制。另一方面,可合理分配证明责任,适当引入专家意见,从而增强司法机关的专业知识生产能力。 注释: ①参见《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 ②See 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253 F.3d(D.C.Cir.2001). ③See Eastman Kodak Co.v.Image Technical Services,Inc.,504 U.S.451(1992). ④参见“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简称:“奇虎诉腾讯案”),(2011)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 ⑤参见: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9、20条。 ⑥参见: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第2条第9款。 ⑦参见:韩国《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第3条之二。 ⑧参见:巴西《反垄断法》第21条、俄罗斯《保护竞争法》第10条、瑞典《竞争法》第19条。 ⑨参见:United Brands v.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ase 27/76[1978]ECR 207,para.184. ⑩参见:美国《克莱顿法》第2条(a)款、《罗宾逊—帕特曼法》第1条(a)款。 (11)这里主要借鉴韦伯关于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按照韦伯及其追随者的解释,人类历史上的法律可以划分为形式的不合理的、实质的不合理的、形式的合理的和实质的合理的四种类型。其中,“形式”可被认为是意味着决定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内在于法律制度之中,“实质”则表明决定的裁判标准来自于经济、社会、伦理道德等法外因素。而“合理性”(rationality)也被称为“理性”意味着决定遵循的某些判断标准适用于所有类似案件,并因此衡量制度所采用的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参见: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60;Dvaid M.Trubek.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J].Wisconsin Law Review,1972,(3):729. (12)Senator Sherman,12 Cong.Rec.2455ff(1890). (13)与反垄断法价值多元论相悖的是“一元论”,而且一元论者多突出效率价值的唯一地位。例如,柏克法官认为,《谢尔曼法》立法者除了考虑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几乎没有考虑什么。See R.Bork.Legislative Intent and the Policy of the Sherman Act[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6,(9):7.那么在福利分配领域,实际也涉及到生产者、消费者两方主体,反垄断法不可能仅关注生产者效率实现而忽视消费者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价值内部本身就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后者衍生出消费者福利价值)的冲突。因此无论多元论还是一元论,反垄断法不可能仅关注一方主体的价值追求。 (14)See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et al.v.the United States,221 U.S.1(1911). (15)由于立法明确了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只要具备某种行为形式,就可以依据法律规则判断行为违法。 (16)See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2009/C 45/02),Para.28. (17)参见:美国《知识产权许可反托拉斯指南》第4章第2节第1段。 (18)See Crawford Transport v.Chrysler Corp.338 F2d 934(6th cir 1964). (19)See Eastman Kodak Co.v.Image Technical Services,Inc.,504 U.S.451(1992). (20)参见《罗宾逊—帕特曼法》第1条(a)款。 (21)See United Brands v.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ase 27/76[1978]ECR 207. (22)See United States v.Jerrold Electronics Corp.,187 F.Supp.545(E.D.Pa.1960). (23)参见: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第1条(b)、(c)款。 (24)参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第8条。 (25)See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2009/C 45/02),Para.28. (26)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A.E.Statley Manufacturing Co.et al.,324 U.S.746,(1945). (27)See Corn Products Refining Co.et al.v.Federal Trade Commission,4 U(1945). (28)See United States v.United States Gypsum Co.et al.,438 U.S.422(1978). (29)See Falls city Industries Inc.v.Vanco Beverage Inc.,460 U.S.428(1983).标签:反垄断法论文;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正当程序论文; 公平原则论文; 经营者集中论文; 竞争法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