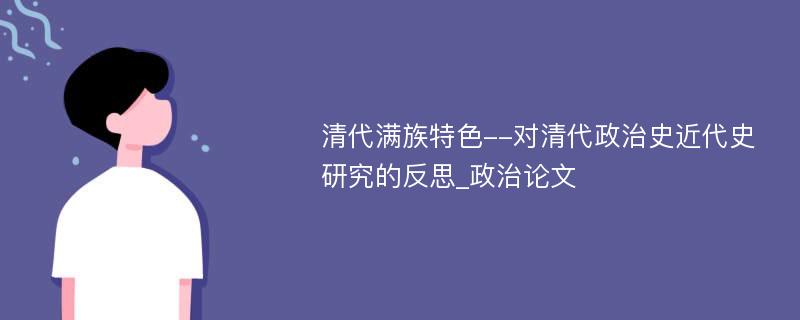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清代论文,清朝论文,史研究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清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崛起于东北一隅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的满族,如何能够问鼎中原,并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特别是构建18世纪的盛世辉煌?“汉化”曾一直是研究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的视角。学界一直把满族的成功、清朝的繁盛定位于对汉文化的倾慕与广泛接受,以此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构建了王朝的合法性,并造就康乾盛世。然而最近一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八旗、旗人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解释清朝入关后的历史方面,角度新颖,方法多样。清朝的满族特色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
一、八旗政治与旗人社会:中国学者的两部著作
杜家骥的《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刘小萌的《北京旗人社会》是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新近组织出版的两部著作,两部书都是关于八旗的研究,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将八旗作为社会组织和政治、军事组织来看待,探讨它对有清一代政治的影响。这两部著作都是集作者多年功力而成,包含着著者长期的学术积累。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它们的出版问世,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视清代的满族民族特色、满汉关系,也暗合了从民族学角度来重新审视清代政治的学术路径,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
重视满族八旗的各种制度、习俗对清朝入关后的政治、社会影响是这两部书的一个共同点。学界以往对16至17世纪满族崛起东北的历史、八旗的形成及其入关前的各种活动,研究很多,这也一直被视为是进行清史研究的一个基础和理解清史的一把钥匙。然而,当研究清朝入关后的历史时,学者们的视野基本上转移到将清朝看作一个汉化的,像汉、唐一样的正统王朝来看待,满族已经主动的去接受儒家文化和传统中央王朝的各种制度,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也已经融入到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清朝如何构建和巩固“大一统”的统治,对满族本身特色的关注则大大减少,八旗这种极具满族特色的军政和社会组织也被冷落一旁。然而,清朝毕竟是满族人建立起的一个王朝,无论其如何汉化,也无论它怎样大力尊崇、推行儒家文化,这一王朝归根结底是要带着强烈的满族特色。具体而言,入关前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八旗制度等都会对入关后二百多年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首崇满洲”的政治原则贯穿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旗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在清代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地位也从未弱化,投身到汪洋大海般的汉族中的八旗子弟无论如何汉化,最终也没有放弃对满族的认同,一直到辛亥革命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清代的满族特色,如何理解清朝入关前的各种制度对入关后的政治社会影响,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清史,杜家骥、刘小萌的两部著作就是做了这样一种尝试。
杜家骥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分上、下两编①,上编主要讨论清朝入关前到顺治朝八旗制度的形成、发展、变革,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即八旗是按照领主分封制组织的,这种领主分封制始自满族早期社会,一直到入关后随着皇权政治的逐渐成熟而归于消亡,但领主分封制的影响则长期存在于清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领主分封制为线索,作者探讨了入关前后领主分封制的形成、八旗领主分封制与后金(清)政权的特性、满族和清政权的统辖关系、共议国政制度、八旗领属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八旗排列序列等。在下编中,作者放眼自顺治至清末八旗领主分封制对政治的影响,包括清代君臣主奴性君臣关系的形成,旗人的内部差异和“抬旗”问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由盛而衰、八旗教育及其政治作用,旗人的任官制度、旗人包衣对政治的影响、旗人婚姻的政治作用等等,并讨论了清朝入关对清代历史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首先以“八旗领主分封制”来概括满族入关前后的政治、社会状况,也是一种极具见解的观点,“八旗”组织下的各种观念是满族人留给入关后的清朝的一种政治文化。其次,对很多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如,他以较长的篇幅和充足的史料考察了从努尔哈赤到顺治时期八旗和旗主的变迁,特别是在皇太极和多尔衮执政初期,正蓝旗两次被分解、换旗,背后隐藏的则是皇权的壮大和八旗领主对八旗私属关系的削弱。这一论述承袭了孟森、阿南惟敬、白新良等人研究之余绪,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解释,是一种学术上的发展。作者还对“入八分”的内涵作了考察和剖析,理清了“入八分”制度具体的历史变迁,以此为基础,他考察了满洲贵族参加议政会议的人员及其资格,对“大贝勒”、“固山贝勒”、“和硕贝勒”、“执政贝勒”的内涵都作了探讨,纠正了过去对八旗贵族议政制度一概而论的缺陷。这种制度将影响到入关后长期存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关注入关前后八旗领主分封制度对清朝政治的影响、从满族自身的八旗政治角度和视野来解释清代历史也是作者在书中极力表现的,这是揭示清朝历史之满族特色的基础。作者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在颁行明朝制度和拉拢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士人阶层的同时,又把“首崇满洲”放在政治的首位,表现在官缺制的实行,对满族人经济利益的保护等制度,对满族人教育的重视,以及翻译、侍卫、笔帖式等满族人特殊的任官制度的实施。作者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探讨包衣制度,清朝入关后,也将八旗的奴仆、包衣制度带入关内,并广泛、长期存在,他们来源广、数量大,可征召为兵,从军出征,亦可借助科举、举荐入仕为官,或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虽很多为汉人,却因为被牢固束缚于八旗主奴关系下,这些都是极具满族特色的制度,都为保证满族人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而制定,也一直影响着清代政治的变革,作者的这些考察和研究能够让我们强烈感受到清朝统治者在接受汉族文化和制度时的另一方面。康雍乾诸帝曾一再强调要保持满族骑射、语言等风俗,视之为“家法”。其实,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能够让满族保持其民族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是自清朝入关以前就确立的这些政治制度。时至清代晚期,当语言、骑射这些“家法”都被八旗子弟丢失殆尽的时候,满族人仍然能够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原因在于此。作者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将自己以往论文的大要收入其中,说明作者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论点鲜明、角度新颖、论证充分的著作,也是多年悉心积累的结果。
刘小萌的《北京旗人社会》②一书洋洋洒洒80余万字,并收集大量的图片。如果说杜著是着重八旗影响下的清代政治的话,刘著则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探讨北京旗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北京作为京师之地,是满族入关后旗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既不同于东北地区的八旗军民,也不同于驻防各地的八旗组织,在各地的旗人聚居地中应该最具特点,但又不乏代表性。作者的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第二章探讨从辽沈到北京旗人社会的形成,第三章“旗民与旗地”和第四章“旗人与民人”阐述旗人的经济生活及与汉人社会的关系;第五章、第六章讲形形色色的旗人、旗人的内部差异及旗人中的世家大族;第七章讲旗人的生活风俗;第八、第九章讲晚清以降旗人生活的艰难、恶化,直至最后在革命的压力下旗人社会走向瓦解;最后一章即第十章则阐述研究旗人社会的史料问题。
刘小萌的著作首先引起我们侧目的是“旗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如何理解满族的历史和民族认同,何谓“满族”,一直是学界极富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作者看来,由“满洲”而“满族”是超出满洲人本身范围的。显然,作者在此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不仅仅是“考虑到历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③,而且是对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回应。其次,此著的重点是揭示入关后八旗军民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他们如何谋生、如何与人交往、如何维系被视为“家法”的骑射和服饰等风俗,晚清时期旗人生活又如何衰败。政治上的特权阻止不了他们生活上的落魄,辛亥以后他们终究抵挡不了革命的洪流淡出历史舞台的核心,这是作者对八旗组织的一种社会史考察。结合大量图片,作者将一个活生生的八旗组织展现在人们眼前,改变了以往那种八旗征伐杀戮无休日的印象;第三,“旗民社会”也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旗民社会”的存在是作者“旗人”概念的延续,是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旗人历史的一种方法,这些概念辨析和使用容易激发我们对满族的民族认同、民族特性等诸问题的思考。
二、马背上的王朝:一部美国学者的著作
同样在2008年,与杜、刘二著在国内面世的同时,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④《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书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张著的研究对象是清帝南巡。南巡一直被清史学界看作满族统治者倾慕汉化、重视汉文化的政治行为,是他们走向汉化的标志,但在张著中,这一行为得到与以往大相径庭的解释。
“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是作者在书中的核心概念。对满族人来说,他们用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的(Ethnic),即对满族质朴、武艺等特质的坚持和弘扬,特别是对马上治天下政治观念的发挥;其次是宗室的(Dynastic),强调八旗组织和政府官僚对爱新觉罗家族及皇帝本人的尊崇和效忠。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满族至上主义”(Exceptionalism),即在清帝国中,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作者的这一概念根源于韦伯的“世袭君主官僚制”。⑤张勉治用这一概念来解释18世纪清朝政治文化的特点,即无论是军人、商人或博学鸿儒,都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统治者要求他们对其个人忠诚、效忠,最终要把所有有自我主体价值的官员变成奴性十足的仆人。然而作者也认为韦伯忽略了民族性的因素。他认为民族性对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非常重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是为了建构群体的共同信仰,是建立和维系世袭统治的基础。民族认同的语境和象征一直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世袭统治历史形成过程中基本要素的构建。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入关前对八旗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将其“世袭家族化”的过程,相对于其军事性而言,纪律性和政治立场更重要。以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野为标志,八旗成为“国中之国”。在1730-1740年代,在完成“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控制之后,清朝统治者又将这种统治扩展到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府。因为与可信赖的集团联盟保持凝聚力和纪律,对清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康雍乾三帝概莫能外。实现政治合法性需要两大基本要素,一方面表现出对汉人政治文化标准和社会利益的包容性,以扼制由商业化和地方精英带来的去中心化倾向(decentralization)。另一方面,他继续强调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特权和满洲统治的军事基础。清朝皇帝在1740和1750年代对巡幸制度的复兴是这种历史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也是张勉治此书的突出特点。他在书中表示,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是从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⑥那里得到启发。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清帝国进行整体研究。中国的汉族地区、满洲、蒙古地区、新疆、西藏,以及西南民族部落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曾经是经济独立(autarkic)的小王国?是什么机制让它们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或减少?帝国亚洲内陆的边疆地区对汉族地区产生什么影响?
(2)中央政府,特别是专制君主的基础。除了那些仆人(包括太监、包衣、旗人,以及学者型官员),皇帝还依靠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政府通过把地主阶级的成员吸收进文官系统,真的就能够控制地主阶级吗?朝廷和商人及其他非官员阶层在什么程度上认可并进行接触?我们对中央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实施缺乏一个清楚的和全面的认识。
(3)满族研究。我们需要对清代早期的历史、对满族自身做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探讨满族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很显然,作者在书中是要以南巡为切入点,来回答弗莱彻的这些问题的,是要对清帝国的性质进行一个全面的界定。
首先,整体性研究视野将南巡与清帝国其他重大事务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南巡和西师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盛衰的两件战略性大事。我们也都能够对西师作出可圈可点的评价,可对于南巡,似乎很难捕捉到它的真正内涵。以往学界对南巡的定位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南巡当作清朝统治者满族倾慕汉化的主要依据,认为它表明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重视江南这个汉人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把南巡看作皇帝安抚江南、控制汉族精英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初以来的很多学者仍然在延续传统士大夫的观点,对乾隆南巡的奢侈进行猛烈批评。现在看来,这些研究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发现和揭示南巡的“战略地位”,没有阐明在统治者自己观念中的南巡,没有发现南巡和帝国其他事件特别是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张勉治在此书中,借助新清史的理路,把南巡当作清朝“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清朝的皇帝在汉文化面前不再被动,而是以主动积极的态度进行改造,构建了南巡与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整体性联系,使我们看到了南巡与西师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其次,作者探讨了皇帝南巡期间如何处理江南汉族商人和士人两大精英集团的关系,也探讨了民间对清帝南巡的反应。乾隆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到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太多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至于民间舆论,或许只是道听途说,但它经常处于一种对朝廷意识形态的反动状态中,正是民间舆论让乾隆帝有了最后两次南巡,也让南巡有了太多的传说。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表面上的繁荣、强盛的多民族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18世纪一直这样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到19世纪也许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清朝结束。在此过程中,它也决定了清朝在政治上总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到底如何确立?
第三,清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如何理解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从清朝建立直至它结束一直是困扰它一个主要问题。显然,乾隆帝通过南巡想要表达的是“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他要通过构建这种政治理念,整合汉族士人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接受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论证满族王朝的合法性。岸本美绪也曾将这样的问题归纳为“十六世纪问题”。即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中,旧的秩序已经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或商品、货币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新政权到17世纪逐渐建立,包括中国的清朝、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是近世国家,都要回答16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这种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美国的阿尔泰学派的研究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特性,主张没有被完全汉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不放弃武艺和质朴。清朝是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不允许其他特权集团的存在。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则极力保持和维系作为战斗集体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控制并整顿八旗组织,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之下。
三、中西研究的对比
以上三部著作的共同点就是非常注重清朝历史的满族特色,杜著以八旗领主分封制为核心概念来窥测它对清代政治的影响,刘著以“旗人社会”为理念,阐释清代北京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满族特色。张著则以清帝南巡这一具体政治行为为对象,揭示了这一行为背后的清朝统治者“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的深邃的意识形态,这些都为研究清代很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纠正了以往中国学界过分强调“汉化”、忽视清朝满族特色的缺陷。郭成康曾撰文讨论满族的汉化问题,他认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汉族文化,不仅表现在极力保持自己的骑射、语言、服饰风俗这些方面,而且表现在重视实践、用人以能、以主奴关系重塑君臣关系、夷夏之辩等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方面。郭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民族都不会被文明先进的民族彻底同化,他们之所以消失,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失败的民族很难留下自己的文字资料,二是即使留下历史记录,而历史记录大多按照胜利者的视角写成,包含着胜利者的立场和理解。所以他认为在清代,占主体地位的是汉文化,而满族的文化则因为满族的统治地位占主导地位。同时清代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和资料,使我们现在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能看到清朝的满族特色,因而仅仅以汉化观来解释中国和清朝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以上学者们的这些观点似乎在回应着国际上一直流行着的“新清史”观念,但新清史走得更远。
如果说把中国历史,包括清代历史仅仅解释为“汉化”的历史有所偏颇的话,那么西方新清史观念下对清代历史的修订则又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观念基本上否定满族的“汉化”,把清朝视为一个完全依靠满族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帝国。例如,柯娇艳、欧立德等人都明确表示,对满族特色的极力保持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⑦张勉治在导言中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这一研究从在清史研究中被称为“阿尔泰”学派(反对汉化观)的观念中受益匪浅,属于“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者简称为“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的、对满、蒙等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忽视。⑧
“新清史”或“新清帝国史”是美国的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一种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对国外的这种研究趋势给与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定宜庄曾撰文指出新清史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的满族因素;二是运用满、蒙、藏、维等民族语言文字材料进行研究,而不是再仅仅依靠汉文材料和汉族人的叙述。这些都表现了这一研究趋势对传统研究的质疑和修订。⑨
十二年前,罗斯基(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Ping-Ti Ho)之间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应该被视为新清史学者将内亚因素注入到清史研究,并向传统的汉化观发起挑战的标志。多年后,司徒琳(Lynn A Struve)在评论这场论争时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⑩尽管有论争,但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清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用以解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认为新清史在民族认同、多元文化、性别和帝国殖民记忆、战争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11)米华健(James Millward)也归纳道:新清史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满族等非汉族人群,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关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而重新审视。对同种同质的“汉化观”下各种命题提出质疑,形成解构。其次,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相对于和汉人的关系,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精英和它的亚洲内陆的臣属(蒙古人、藏族人和突厥穆斯林)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是一个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帝国,“一个在亚洲内陆新的更加伟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清朝的创造。”(12)第三,是对清帝国的整体性研究,新清史的学者认为,以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多指东南沿海一带,忽视了对北部、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清朝的研究实际上缺乏整体性。总之,他们基本上否定了过去的“汉化”观,把清朝定位于一个纯粹的满族王朝,把清朝统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归因于对满洲特质和满洲之道的保持和维护,把清帝国统治重心定位于满、蒙联合和对北部、西北边疆地区(亦称为“内陆亚洲”)的有效治理,甚至在他们那里,满族和清朝成为早在入关前就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权,而不是在统治了广大汉族地区以后才会与世界发生联系。这样,当汉族的思想、文化等等都被排斥出清帝国核心时,西方的很多学者会发现,或许清朝并不等于中国。
“新清史”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新的研究思潮,在很大程度纠正了过去汉化观一统天下、忽略清朝的满族特色的史学观,让我们能够发现满族在清代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特别是大量满文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的使用,也使我们得以认识很多被历史文献掩盖了的历史的真实。然而,将清代历史仅仅归于满族的历史,忽视汉族的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中的主体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于中国的极端上去,显然也有违于历史的真实。这也是国内学者在研究满族历史时与“新清史”学者们不同的一个方面。
从杜家骥和刘小萌的著作可以看出,对于国内的很多学者来说,发现和重视清朝的满族特色将为清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视野,但这和重视清朝入关后接受汉文化的政策并不矛盾。清朝统治者在保证满洲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对于整个帝国来说,接受汉文化,重建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以彰显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同和效忠,仍然是清帝国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虽然有内陆亚洲的因素,甚至不惜以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内陆亚洲各地区的认同,(13)但当乾隆用兵西北后,西域平定,清朝的军队则在西部边境立碑而返,并没有像十三世纪的蒙古人那样继续西进哈萨克大草原,甚至兵锋染指欧洲。如何理解这种行为?郭成康认为这可以表明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很明确,对境外之域缺少认同,他们还是把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作王朝的根本。(14)满族来源于“内亚”,但清朝并没有兴趣在内陆亚洲无限扩张,并没有把它自己打造成一个纯粹的内陆亚洲国家。它的重心在于对汉人的有效统治,这是清朝正统性、合法性的根本所在。首崇满洲固然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入关后的政治重心也应该在如何对待汉族的文化霸权,仅仅向江南地区的汉族精英展示清朝的满族特色是不够的,张勉治在书中也指出,乾隆让汉族人接受其意识形态的做法收效甚微,书中作者借用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人们不会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或者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而总是可能在攻击或否定这些形式和关系,或者对其极尽挖苦和讽刺,或想方设法拒绝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力量。”(15)1780年代乾隆帝重启南巡活动,表明历史发展最终还是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也表明清朝统治者仅仅维护他们的满族特色是远远不够的。
入关后的满族人已经得到一切,已经足够稳定,汉族人对意识形态的把持才是清朝皇帝最顾忌的事情,清朝皇帝在汉族人面前不仅仅是展示什么,而是争夺。清朝皇帝屡下江南,不惜放下万金之尊和汉族士人展开“华夷之辩”,或是不惜背上以文狱杀戮士人的恶名,目的是和汉族士人争夺历史的褒贬权和在道统合法性上的发言权,消除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16)意识形态不统一导致的对满族人统治的挑战将延续,一直影响着清帝国的方方面面,直到清末的革命。这才应该是清帝国的政治核心。
注释:
①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刘小萌:《北京旗人社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刘小萌:《北京旗人社会》,第4页。
④张勉治(Michael G.Chang),200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勉治就一直致力于清帝南巡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为《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2007年,历经十年之功后,张勉治终于将其书稿付梓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⑤韦伯此概念的英文为patrimonial bureaucracy,中国学者在翻译此概念时常有差异。何怀宏在《世袭社会的解体》中将其翻译为“家产官僚制”,黄宗智则在《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2007)一文指出:“韦伯在他的两个理想政府类型“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科层制(“官僚制”)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前者以一个把国家当作统治者个人领地的世袭君主制度为其特色;后者以一个非人格化的,带薪官僚阶层行使专业职能的现代政府为其特色。”
⑥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被认为是唯一在伯希和之后能和伯希和在掌握内陆亚洲研究语言和文献上抗衡的学者,而且也是在史学眼光上超过了伯氏的人。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即伊斯兰在华史,东土耳其史,蒙古史和满清史。Fletcher很早指出满清统治手段的多样和灵活。在他为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所撰写的三章里,他也和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持相反的立场。费氏以为中国近代的主要变迁发生在沿海,而Fletcher则认为晚清以来的情势变化,关键在内陆亚洲部分,只有照顾到满蒙藏突地区的稳定,帝国才得以延续。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出版后受到学界严厉的批评,唯独Fletcher所写的三章受到称许。可他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出版太多成果,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的最大损失。现在美国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新清史的发展受弗莱彻的影响很大。
⑦(美)盖博坚《谁是满洲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罗斯基(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
⑨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见《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1期。
⑩司徒琳著、范威译,《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
(11)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清史研究》2008年1期。原文发表于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
(12)米华健(James Millward)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的形成》),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
(13)这种获取不同民族认同的做法被称为“共时性”,见盖博坚《谁是满洲人?》。
(14)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见《清史研究》2005年4期。
(15)转自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6)杨念群:《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见2009年9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纪念郭影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明清之际历史与人物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标签:政治论文; 满族论文; 清朝论文; 满族服饰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新清史论文; 八旗论文; 满族风俗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八旗子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