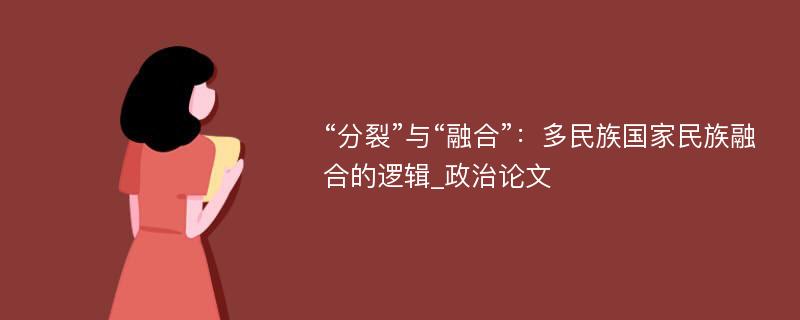
“分”与“合”: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民族论文,多民族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3-0017-005
从民族构成上看,现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比例占到国家总数的95%以上。① 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多元特征,构成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因一国内部民族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而产生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乃至民族分离运动,充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些民族问题不仅阻滞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和谐和社会发展,恶化了国家外部的族际环境,而且还影响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以至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惊呼,“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②
对于多民族国家尤其是一些正处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对待国内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把具有异质性的各个民族成员单位统合到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消除因民族异质性要素带来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进而构建更高层次的政治共同体,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极为重要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终极目标和构建过程。本文从“分”与“合”两个方面出发,认为主导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逻辑展开的是其内在规定性,即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与国家统一性这对特殊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多民族国家产生了结构性张力。围绕这对结构性张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具有现实性、政治性和构建性三个表现方面。
(一)民族整合的内在规定性:分与合的观察视角
探讨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逻辑,首先要弄清楚民族整合的内涵或其内在规定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质是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质的属性和特征则取决于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③ 民族整合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民族整合的内在规定性及民族整合逻辑的展开。
“民族整合”是一个组合词,由“民族”与“整合”共同组成,要理解其内在规定性,需对“整合”及相关概念作一番考察。“整合”作为特定范畴第一次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文章中,是与系统理论联系在一起的④,这并非偶然。在社会研究领域,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最先把“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作为社会行动总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即“一个系统得以确保其内在稳定性的诸因素”⑤。此后,“社会整合”和“整合”便与社会系统的功能分析联系在一起,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社会系统功能分析中的“整合”,其内涵由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加以规定:(1)“分”。社会分化出大量异质性要素,要素重组产生新的结构及功能的专业化,打破了各子系统边界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系统的均衡产生压力;(2)“合”。为了维持系统的均衡,需要协调各异质性要素、使各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的力量或机制。换言之,社会结构分化之“分”与系统功能统一性之“合”构成一对特殊矛盾,两者的关系规定着社会整合的内涵。
从词汇的演变和转借来看,“民族整合”的涵义来自于社会整合的衍生⑥。与社会整合相同,民族整合的内在规定性也取决于一对特殊矛盾,它决定着民族整合的内涵及其逻辑的展开。民族整合的特殊矛盾可以从“分”与“合”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从“分”的方面来看,一国内部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增加了民族之间的区隔及其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从“合”的方面来看,民族国家的构建是运用国家权力实现多重统一性的过程⑦,包括主权领土、经济生活、政治法律规范、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等的统一,是统合各种不同民族成员单位走向统一的趋势。总之,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内涵由这一对特殊矛盾内在规定着,民族整合的实质就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缓解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张力,协调国内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进而构建更高层次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
(二)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现实性:分与合的矛盾运动
从“整合”一词的社会学渊源来看,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整合就可能是分化和交互依存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共性。”⑧ 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现实性来自于民族整合内在规定性中“分”的方面。民族整合“分”的方面,即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存在的时空场景是民族构成多元性的多民族国家。探讨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现实性,有必要追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探究其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普遍国家结构形态的必然性。
“所谓‘多民族国家’,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⑨ 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是从民族结构上对国家所作的一种分类。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源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遵循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两者的演进表现出一定的交叉性。民族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分化和聚合的趋势,具体表现形态为一个民族分裂成或分化出数个民族,或数个民族联合、同化或融合为一个民族。民族共同体以共同的文化为联系纽带,其具体形态的演变本质上体现为文化特征的趋同或变异。国家政治共同体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超越了民族共同体以文化为联系纽带的狭隘性,在共同地缘基础上实现了领土主权、中央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因此,一个国家把各种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或者一个民族由于发展演进的不同趋势分布于数个国家,就造成了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能完全吻合的情形。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民族成员跨国界的迁移和流动,无疑增加了民族与国家交叉互动的复杂性。多民族国家遂成为现代国家结构的普遍存在形态。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只是为民族整合内在规定中“分”的存在提供了时空场景,而由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带来的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与国家统一性的张力,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现实性的根源。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异质性要素是指民族间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差异。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是自然体和社会体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自然体,每个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些自然特征,这些自然特征在斯大林经典民族定义中被规定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⑩。其中,族属意识(民族心理素质的一种深层次体现)和共同文化,是民族自然属性中最为重要的区分性要素,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最稳定、最持久和最直接。“民族共同体的存续是以民族特征(语言、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的存在及其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为前提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特征的集中反映。这些特征作为整体,具有区分性的功能,它们彼此密切交织而组合为稳定的整体。”(11)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存在形式,必然要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社会属性。其中,政治属性可视为民族共同体及其范畴的本质内涵之一(12)。民族在与社会互动关系中表现出政治属性的不同方面,其核心则是围绕公共权力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展开的活动。作为民族构成要素或民族区分性重要特征的政治属性,在社会政治结构上显明地标示出民族之间的差异。
民族间异质性要素具有维持民族边界、实现民族利益的功能,而其力量的过度增长则会打破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均衡状态,增加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摩擦、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甚至会因内部排斥力过强导致某些民族成员单位的分离或多民族国家解体。随着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异质性要素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旺盛、民族文化的发展、政治利益诉求的强烈等倾向,其不适度的发展则会突破民族之间区分性界限,加剧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冲突和矛盾。多民族国家内部这种排斥力沿着利益和价值两条线索展开,具体表现为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国土开发与利益分配、国家的现代化与族体发展等方面的矛盾(13)。多民族国家内部结构性张力中“分”的倾向,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协调和调控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实现各民族成员单位统一之“合”,这就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政治性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政治性:分与合的政治保障
如同在社会体系中,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是两个相生相伴的持续过程,民族构成多元性带来的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决定了把各民族成员单位统合进国家社会生活、实现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是任何多民族国家都必须面临的持久主题。所不同的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历史传统、族际环境及观念意识等不同,决定了在民族整合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机制和标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诸多实现民族整合的手段和机制中,民族政治整合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民族整合的政治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尤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其它整合机制如文化整合、领土整合、经济整合等,都离不开政治整合的权力辅助和一体化保障,“国家克服地方主义的能力及民族主义思想赋予国家以权力的能力,大大地得助于交通、运输、正式的组织科层机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得助于‘主权在于人民’的观念。一个民族社会要有能力达到、甚而只是接近于文化整合,唯一的可能性便在于通过这些机制。”(14)
民族整合的政治性,或者民族整合的政治属性,是指民族整合的主体、客体、实现机制及目标与国家公共权力及其延伸部分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民族整合的主体通常是国家及其实体组织——政府,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和执行者,通过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民族整合,因而这种整合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公共性。民族整合的客体是各民族成员单位间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民族单位要素及其与整体的关系,由于涉及利益调整和价值分配往往会演化或表现为政治关系,“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的核心是政治关系”。(15) 民族整合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制定、制度构建等,其实施和运转都与公共权力密不可分。
对于多民族国家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而言,民族政治整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在17、18世纪西欧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政治体系的统一为民族市场、民族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进而催生了现代民族(Nation)。从民族整合内在规定性的特殊矛盾来看,民族政治整合在民族异质性要素保护和发展及国家合法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了多民族国家因民族构成多元性带来的结构性张力。
从“分”的方面来看,民族政治整合通过针对民族的利益分配和权利保障,有助于民族异质性要素的保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民族作为一种以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人们的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主要围绕维持和发展与其他民族成员单位相区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展开,表现在文化特征的延续和发展、民族成员资格的平等、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分享等方面。诸多民族利益诉求的核心是实现和保障民族集体及其文化的权利,即要求多民族国家对民族作为一种异质性要素(差异性要素)法理上予以肯定和权利上加以保护。可见,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群体”(17)。伊斯顿认为,所谓政治是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8)。对于利益、权利、财富等社会价值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的公共权力,取决于民族整合的政治性。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通过诉诸各种民族政治整合机制,实现社会价值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能够实现和保障民族成员单位作为差异性要素的各项权利。
从“合”的方面来看,民族政治整合通过增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统一性。“民族(人们共同体或者族裔文化集团)与国家的形成以及内聚力的产生遵循不同的逻辑。”(19) 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家族、宗族等原生性纽带联结局限性基础之上,通过地域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联系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民族成员单位的历史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也由魅力型、传统型逐渐转向法理型,而法理型合法性的核心则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自愿践行公共领域的制度规则。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凝聚各民族成员单位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文化传统(通过诉诸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来实现),而且还需要在权利保障和利益公平分配条件下,实现其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保证了民族成员对国家持久的效忠情感,保证了民族成员对国家制度的自愿遵守,进而构建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民族政治整合无疑契合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通过围绕民族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构建一套协调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增长与国家统一性张力的政治机制,从而有助于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为多民族国家合法性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总之,民族整合的政治性来源于多民族国家因民族多元性带来的结构性张力,其核心在于围绕民族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合理引导和保护“分”的同时,加强和凝聚“合”。而如何通过观念导向、制度构建等具体机制实现“分”“合”有序,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构建性所要解决的问题。
(四)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构建性:“分”“合”有序的目标
多民族国家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的整合状态,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政治建构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整合可以看作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过程(20)。民族整合的构建是从政治实践角度对多民族国家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实现过程的抽象概括和描述,它包括运用公共权力缓解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增长与国家统一性之间张力的各种手段和机制的总合。
对于一国民族构成持何种观念,即如何认识多民族国家内部异质性要素的存在,决定了民族整合的不同构建过程。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种对立民族结构观念的斗争。一种是排斥性的民族结构观念,它追求一国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追求以血缘、种族、宗教或民族纽带建立国家,忽视、限制乃至否定民族异质性要素的存在。这种观念在早期欧洲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表现为“民族国家”的理念(即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在现代则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大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泛宗教主义和同化主义。在排斥性民族结构观念支配之下,民族整合往往表现为主体民族垄断国家权力、执行歧视性和不公正的民族政策、忽视弱势民族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等。其结果只能是带来民族异质性要素对国家统一性的排斥力,由此导致的民族矛盾、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另一种则是包容性的民族结构观念。它承认“多元一体”是一国民族结构的普遍存在形态,承认民族异质性力量的存在及其合理发展的要求,国家构建的基础是地缘联系和政治法律纽带。持有这种观念的多民族国家也往往能够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促进各民族成员单位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巩固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最终有助于增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
排斥性民族结构观念,已被证明无益于缓解民族异质性要素及其力量的增长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张力,无益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采取包容性的民族结构观念,通过政治制度构建保障民族权利、公平进行利益分配,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题中之意。在围绕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制度构建上,由于对民族异质性要素或差异性要素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的认识不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展开:一条是个人权利或公民政治的构建路径,另一条是集体权利或民族政治的构建路径。
在个人权利整合路径下,国家的法律实施和制度建设以公民个体为对象,各种制度、法律和规范针对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利益实现展开,不承认针对国内某一民族成员单位的特殊权利。这种构建路径假定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个体,保证个体的公民身份及其权利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任何针对特殊群体的集体权利都是对个人权利公正性的侵犯。这种路径下的制度构建突出表现为西方以政党政治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以及各种以实现民族非集体政治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文化政策,如美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墨西哥的民族一体化政策等等。个人权利的整合路径实质上不承认民族成员单位作为一种异质性要素或差异性要素的存在,忽视、限制乃至否定民族成员单位对于民族集体及其文化的权利诉求。在集体权利整合路径下,民族成员单位的文化延续、社会发展及自我管理等集体权利,被作为民族政治的核心内容加以构建。这种路径下的制度构建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职位的民族比例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联邦制、民族自治,以及一些以实现民族集体权利为目标的民族政策,如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集体权利的整合路径本质上肯定了民族异质性要素的存在,并且通过制度构建保护民族异质性要素,以促进民族异质性要素力量的发展。
从实际的实施效果来看,集体权利的整合路径,由于顺应了“现时还是一个民族发展而不是民族消亡的时代”(21) 的科学论断,符合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更好地缓解了民族多元性带来的结构性张力,实行此种整合方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也较为和谐。
注释:
①(15) 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④ 严庆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相关文章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4期)一文最先使用了“整合”一词,参见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现代性社会学》,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⑥(20) 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⑦ 参见付春:《论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⑧(14) [美]迈克尔·舒德森:《文化与民族社会整合》,李贝贝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5年第1期。
⑨(21) 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
⑩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11)(12) 周星著:《民族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第31页。
(13) 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5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7) Grazer N.,A.P.Moynihan(ed.).Ethni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7-8.
(18)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9) 王建娥:《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