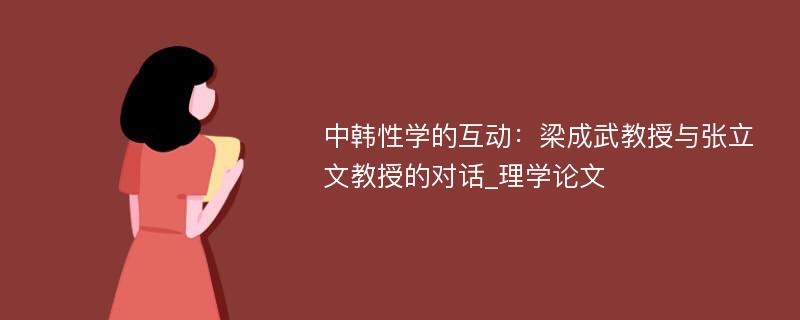
中韩性理学之互动——梁承武教授与张立文教授对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互动论文,理学论文,中韩论文,张立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承武(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问:张教授同意卫满朝鲜时儒教东传韩国,其根据是什么?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答:儒教何时东传韩国?有各种主张:有主箕子东来说,有倡秦汉东传说,有主卫满朝鲜说,或主小兽林王二年说。对此金忠烈教授在其大著《高丽儒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中有精到的分梳。笔者同意卫满朝鲜说,其根据是:(1)箕子东传说,只是传说,且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没有出生:(2)春秋战国东传说,现无足证之资料;(3)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建立太学,儒家思想传入应早于此时;(4)卫满朝鲜,汉时属乐浪郡,随汉建制,导入汉代典章制度和文化思想,汉代尊崇儒术,儒家思想在汉管辖之郡得以传授,当无问题。
梁问:栗谷批评退溪的理气互发论,教授对退栗思想作如何评价?
张答:退溪与栗谷是韩国性理学上的双峰,或称双璧,对韩国性理学都有极大的贡献。退溪作为“朝鲜之朱子”,通过自己的教学、政治活动,在朝鲜传播、研究朱子学,其功可谓大矣;同时,能结合朝鲜朝社会实际和吸收明代朱子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变理“不会自动”为理“自会动静”,提出“理发而气随,气发而理乘之”的主张,使理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与“四端七情”的性情、道心人心、善恶问题联系起来,而更富人性意味;亦使朱子理气“决是二物”与“不可分开”的观念得以协调,兼顾“理气”与“四七”的互发相须的方面。
栗谷根据朱子对于理的“无造作”、“无计度”、“无情意”,“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的规定,否定退溪“理发气随”说,以符合朱子理“却不会造作”的思想的原意,主张“气发而理乘”。指出退溪“互发”二字,是“不能深见理气不相离之妙也”之故。“理气之妙”,含意深刻:“理气元不相离”,又“元不相杂”,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性,以及功能和作用。理气若无此差异,就无所谓不离;由其不离而免于混淆,故有不杂。理气之妙,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此其一;其二,理气体用,显微无间。说明理气体用具有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对性。由于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理气体用一源,一源而各有体用,理有理的体用,气有气的体用。如一理为体,万殊为用;其三,理通气局,本然之妙。“理通气局”是栗谷自得之见,来自对“气发理乘”的体贴,故说:“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栗谷的理通气局说,确有精到之见(请参见拙作《栗谷的理气观》,第3次栗谷思想国际会议论文)。栗谷思想对理、气两方面都有所继承和发挥。因而,在韩国性理学史上具有整合前人、开启后来的作用和意义。就此而言,可谓集大成。
梁问:中韩性理学互动,韩国性理学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其发展前景如何?
张答:学术思想交流,都是互动的。其间只有主次之别,而无仅单向之动;这种有主次之别的互动,可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无永恒不变之理。互动的形式亦多样:有文字记载的文本的传播,有口语相传的耳闻等。譬如说:(1)“死理”与“活理”的论争,影响韩国性理学家,又反馈中国。明清之际的哲学家以理动静之静,是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静者,动静”。(2)“理寓于气”,七情含四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亦以“理寓于气”,“理者,气之理也”。(3)对“情”、“欲”的合理解释,影响明清之际思想提出“体情遂欲”的思想。中韩性理学前景的互补、互动、互济的动态发展,十分喜人。
梁问:主张心本论的阳明学为什么在韩国得不到发展?其理由是什么?
张答:阳明学约于朝鲜前期的明宗代,柳成龙得赴明而返的谢恩使弃置江边的《阳明学》一书,为阳明学传韩记录。然阳明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朱子曾对陆九渊心学进行批判,朱陆之争一直延续到清代,请参见拙著《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其不发展的原因:(1)朝鲜朝的朱子学者,排斥阳明学。退溪于阳明学传来之初,即撰《传习录论辩》,从理论上对阳明学进行批评。以退溪之门人为首的当时学者,在当时朝鲜学术思想界具有崇高地位,他们的批判,使阳明学的传播、接受都受阻;(2)朝鲜朝的阳明学始终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只有少数王学研究者和信念者,如李瑶、崔鸣吉父子、郑齐斗等。在视阳明学为异端的朱子学时代,阳明学很难发展;(3)朝鲜朝没有出现像明中叶后中国社会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求破除朱子学的权威,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要求。所以阳明学在中国下层社会与在野知识分子中得到传播发展。
梁问:韩国性理学中关于人性与物性的论争,教授认为如何?
张答:人性物性论争,是性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它关系着人性的来源、人之所以为人等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的探讨,被称为湖洛之争。这个论争是在湖南(忠南)与洛下(京畿)学者之间展开的。具主理倾向的洛下学者(如李巍严),注重理一,主张“人性物性俱同”,即人性物性同具太极、天命、健顺五常之德的本然之性,其异是由于禀受阴阳五行之气的正偏的不同。具主气倾向的湖南学者,如韩南塘注重气殊,主张“人性物性相异”,认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统一,所谓性即指气质之性,随气质之性的偏全而偏全的理,便成为性的偏全,人与物亦随气(形气)的不同,性亦相殊。梁承武教授您对此已作详尽论述。
梁问:“死理”的含义,以及“死理”的作用是什么?
张答:朱熹自己并没有把理说成“死理”或作为“死理”。所谓“死理”,是明初曹端对于朱熹所说“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的批评。曹端说:“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从曹端的批评来看,“死理”是指理(太极)不会自动静而言。这个批评也仅是曹端对“理”的作用和功能的理解或解释。其实“理”作为朱熹形而上学本体,朱熹认为是“形而上者”,它与会动静气(阴阳)构成对应关系,为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蕴含着“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即无造作的,不自动静的理是会凝聚造作、会动静的气的“所以然”者。理因其为“所以然”者,不仅具有动静的潜能,而且是会动静的气(阴阳)的支配者和制约者。同时,理正因其无造作,而能无不造作;不自会动静,故能无不动静,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思。这就是说,“理”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是理无造作,不自会动静,这是形而上学本体的永恒性、绝对性的需要,而与变动性、相对性形而下气相区别;二是理是“所以然”,无所不能,气的动静以理的“所以然”动静的潜能为根据,无此根据,亦无气的自会动静。退、栗的“理发气随”的互发说与“气发理乘”说,都是对朱熹理气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