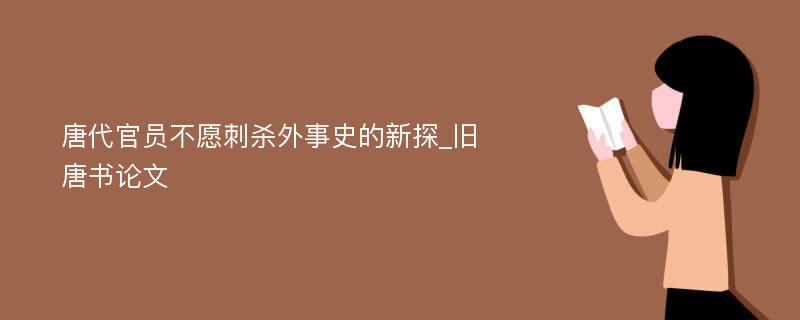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刺史论文,不愿论文,唐代论文,官员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86-06
关于唐代官员不愿担任地方刺史,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京官、轻外职的不良倾向,即使是担任刺史这样的地方大员,他们也颇不情愿。一个著名的例子,“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倪)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①连倪若水这样颇有地方政绩的“良吏”都认为从地方入职中央是“登仙”之事,可见当时人们对京职之热衷。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宰相韦嗣立也说:“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②除牧伯而再三披诉,显然是不愿担任地方长吏。为何不愿担任地方长吏呢?韦嗣立如此说法的立足点旨在说明由于当时官场存在着浓厚的重内轻外的风气,所以朝官不愿担任地方官,并力图纠正此种风气。沿着这一思路,当代许多学者在研究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的问题时,也往往引用以上史料,说明当时朝官不愿外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官场存在着普遍的重内轻外风气。③这当然并无不妥,但并不全面,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当时存在的重内轻外的风气,实际情况并非仅仅如此。
唐代官员轻视外官,韩国学者柳元迪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唐代考察地方官吏的第一标准是户口的增加和均田农民的生活安定,这个目标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于是便造成了轻视地方官和地方官资质低下的结果。轻视地方官的倾向造成了地方行政的低效率,加之缺乏有效的监察,使地方官很难在短暂的任期内实现善政。④概括柳氏的论述,唐代地方官由于在任期内难以完成考课的任务,从而造成轻视地方官的倾向,进而不愿出任地方刺史。考课难以完成是实际情况,对此冻国栋先生曾指出,“从地方官本身来说,由于国家对之政绩的考核标准之一在于户口的增加即‘人丁滋生’,因此这些地方官员出于政绩和升迁的考虑,为了获得较好的评价,有时也不惜在户籍上弄虚作假。地方官员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同时也是重要的考核标准之一是赋税的征纳,为了完成额定的赋税特别是按人丁计额的赋税,某些官吏则出于中饱私囊的考虑,也存在对其治下的人户申报弄虚作假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作者征引了三条史料,证明了地方官在一定程度上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⑤之所以弄虚作假,固然是出于邀射声名进而有利于升迁需要,但也说明“滋生人丁”“赋税征纳”等任务的不易实现。⑥实际上,地方事务极为繁杂,无论是增加户口还是提高赋税额度,均非易与之务,而地方官的任期是固定的,为了取得所谓的“政绩”,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有一定必然性。⑦笔者作上述说明的目的在于,刺史等地方官完成朝廷规定的既定任务存在一定的困难,更遑论有显著的课绩了。由于地方事务的繁难,使不少官员自感难以胜任,进而或不乐意出任刺史等地方长吏。杜牧曾说过:“臣自出身以来,任职使府,虽有官业,不亲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参台阁,优游无事,止奉朝请。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素不更练,兼之昧愚,一自到任,忧惕不胜,动作举止,唯恐罪悔”。⑧从上可见,做京官整日“优游无事”,而地方官则“忧惕不胜”“唯恐得罪”,滋味颇为不同。我们在读了众多刺史的谢上表之后,相信这种因为地方事务的繁杂而产生的担心和疑虑绝非杜牧一人的感受。⑨
综合以上所论,除牧伯而再三披诉的原因:一是重内轻外的官场风气,二是地方事务的繁难而令人望而生畏。以上两种解释其实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基于唐代官员的清浊之别。依唐人说法,职事官分清浊,而州县官例为浊官。“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以下详列所谓清官,全部为京职,地方外职无一入选,可见地方职务基本上都是浊官。⑩唐高祖关于清浊官有明确的解释,李素立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11)地方职位之浊官性质,还有一个更为显明的例子,唐代官场戏称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12)堂堂县令,居然被称为“畜生道”,可见在唐人眼中,地方职位由于事务繁杂,根本不是什么好差事。刺史之职,颇类于县令,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刺史虽属“清望官”之列,但主要是因为其品级较高,并非其事务“清”;若论其事务,毫无疑问当为“浊官”。如果说,唐代前期,称刺史为清官尚可,唐代中后期则殊不可作如是观。(13)论人之常情,其他条件相同或一定时,皆愿就清而避浊。时至今天,情况也是如此。
对除牧伯再三披诉,以上解释笔者并无异议。但除此之外,笔者感兴趣的是,他们“披诉”之内容为何?既然他们不愿赴任,势必要找一些理由与借口,而且这种借口也要符合实际。其实,所谓“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未必是任何外任大家都不愿去,似乎只有那些偏远之地,大家才都不愿去。此种趋利避害之心理,古今不殊。移民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规模宏阔,形式众多,因官移民乃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形态。(14)唐人就官,往往举家前去,人口众多,所谓“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以就一官”;(15)“扶老携幼,尽室而行。”(16)以古代之交通条件,辛苦程度可以想见。更有不幸之人,即因种种原因,而卒于赴任之途,亦足令人叹息。(17)若赴任岭南、剑南、黔中或西北偏荒之地,其路途之远,任所自然人文条件之不尽如人意,皆足令将去赴任之刺史县令或其他之僚佐望而生畏。就人之每个个体而言,都愿意去自然及人文环境优越之地,彼时外遣之官员,何尝不是如此?开元三年(715)七月敕称:“如闻黔州管内州县官员多阙,吏部补人多不肯去。”(18)谅非孤例,实有多端。元和八年(813),吏部称:“比远州县官,请量减选。”减选之原因,乃是由于被任命的官员多不愿意去赴任。(19)大和四年(830),中书门下再次上奏称:“如河北诸道沧、景、德、棣之类,经破荡之后,及灵、夏、邠、宁、麟、坊等州,全无俸料,有出身及正员官,悉不肯去。”(20)边远州县自然条件艰苦,待遇又差,官员多不肯去,是整个唐代一直存在的问题。与此呈鲜明对照的是,自然环境优越的江南之苏(州)杭(州)闽越(州)等地,地理位置也称偏僻,但因自然人文条件较为优越,刺史县令们却乐意之任,甚或有争赴之势。杜牧说:“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21)闽越之地,彼时经济文化虽有较大之发展,但尚不能与北方和江东一带相比,可以暂置不论。(22)但是,天下名士多往吴越之地,似无可置疑,其魅力之大与黔中、剑南、岭南及西北等地之情形适成鲜明对比。
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被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集大成者,他关于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的精彩论述,(23)今天看来,其论述尽管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24)据竹可桢先生研究,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温暖时期,温度普遍较现代高2-3℃。(25)有学者进而据此研究指出,“唐代文明的兴盛,是以当时十分温暖的环境作为基础的。”(26)可见,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之大。唐代广大南方地区是刺史县令阙员最严重的地区,我们认为,所谓“除牧伯而再三披诉”主要应是不愿赴岭南、剑南、黔中等条件艰苦、自然和人文环境“恶劣”的地区就官。就我国唐代广大南方地区来说,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之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尚未大规模开发,生态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原始状态”,经济自然谈不上发达,只能用落后来形容。笔者认为,对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广大刺史群体来说,去南方“蛮荒之地”任职,面临着多种不确定因素。自然环境方面最为明显的是南方的“卑湿”令前去赴任的刺史们颇感不适,特别是可怕的瘴疠更令他们闻之色变。
关于南方“卑湿”的自然环境,是唐人经常感慨的话题。李桐客说:“江南卑湿,地狭州小。”(27)柳公绰出为湖南观察使,“以地卑湿,不可迎养,求分司东都”。(28)柳宗元说:“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29)李轸在为李孟犨所作的墓志铭中说:“出牧泗州,清明简肃,治行第一。而地接吴楚,气候卑湿,因之痁疠,辞以疾归。”(30)张谓(字正言)说:“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31)刘禹锡谪连州刺史说自己:“某一辞朝列,二十三年。虽转郡符,未离谪籍。卑湿生疾,衰迟鲜欢。”(32)白居易在为崔元亮所作的墓志铭中说:“公(崔玄亮)之丁少师(玄亮父崔抗)忧也,退居高邮,其地卑湿”。(33)王彦威(开成中检校礼部尚书,为忠武军、宣武军节度使)说:“江南卑湿,送终者无悬窆封树之制”。(34)总之,在唐人眼中,“卑湿”的江南之地,是不太适合长期居住生存的。最可见的是一个事实是,南方因为“卑湿”的环境而产生的令人谈之色变的瘴疠之害,这对出任南方偏僻州府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唐初卢祖尚乃是一位颇有地方政绩的官员,历蒋州刺史、寿州都督、瀛州刺史,“并有能名”。“贞观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征至京师,临朝谓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远,须贤牧抚之。前后都督皆不称职,卿有安边之略,为我镇边,勿以道远为辞也。’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以旧疾为辞。太宗遣杜如晦谕旨,祖尚固辞。又遣其妻兄周范往谕之曰:‘匹夫相许,犹须存信。卿面许朕,岂得后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对曰:‘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之于朝,时年三十余。”(35)从以上叙述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路途遥远,二是岭南瘴疠。卢祖尚因害怕瘴疠,认为“去无还理”,多半是听说过瘴疠杀人之事,坚决不去。不去赴任之后果,依卢氏之想法,顶多也就是个抗旨之罪,并无死理。然出乎他的预料,太宗逞一时之忿,竟将其杀之。太宗此举,遭魏征之批评,(36)本人也后悔,并促成死刑之罪执行程序的改进,也算是卢氏没有白死。(37)唐人对南方瘴疠的了解十分有限,然颇为害怕,史书多载其事。贞观九年(635),李道兴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厉,恐不得年,颇忽忽忧怅,卒於官”。(38)《新唐书》卷130《宋庆礼传》称其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贞元中,裴耀卿之孙裴佶为黔中观察使,“为瘴毒所侵,坚请入觐,拜同州刺史”。(39)永泰二年(766),陈少游除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他“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泣言之曰:“南方炎瘴,深怆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最终改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40)陆贽贬忠州刺史,“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41)唐人因对染瘴疠者多有死亡的现象历有所见,这对唐人来说普遍产生了较大的心理障碍,将要去南方炎瘴之地赴任的刺史也不能例外,并由此产生了“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排斥行为。
唐人所了解之瘴疠,大致如下:“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残害也”。(42)刘恂的说法,道出了瘴疠产生的部分原因,并将其与蛊相区别,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另外,江南地区的瘴在不同的季节其产生的原因也不相同,以岭南为例,《番禺杂编》载:“岭外二三月为青草瘴,四五月为黄梅瘴,六七月为新水瘴,八九月为黄茅瘴。”(43)关于瘴疠,近世及当代学者多有研究,成果可谓丰硕。(44)但是,大部分学者关于瘴、瘴疠的解释有不准确之处,有时还将瘴、瘴疠、瘴气、疟疾、伤寒、传染病等相互混淆,理解显然是有偏差的。
近年来关于瘴与瘴疠的研究与解读,以周琼的研究最为精审。依她的解释,瘴气并不完全是疟疾或伤寒,而是自然环境中的一种生态现象,瘴气与瘴病的内涵也不同。文献及人们混用的瘴、瘴气、瘴疠,是三个不同层次和内涵的概念。瘴是概括性的称呼,是史籍及人们印象和心理感觉上的瘴气,但在事实上,瘴气是瘴的气体表现形式,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瘴水,人中了瘴气瘴水后的疾病症状,就是瘴疠,瘴气病是瘴疠的普通称呼。历史时期,瘴气或瘴气病只是模糊笼统的称呼。造成这个错误认知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最早认识瘴时,它主要以气体形态存在,最初的认识又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因此,瘴、瘴气、瘴疠常以同一面目、同一概念或同一内涵出现在史籍及有关研究中,被解释为有毒气体、湿热或致病的空气。但是此种解释往往过于简单。
瘴最初产生于偏僻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其自然环境长期保持在原始状态,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空气流通较少,气候或炎热潮湿或极度寒冷,生物多样性特点显著,许多自身含有或分泌毒素的生物生长其间,散发的有毒气体或液体在这种环境中极易发生生物的、物理的或化学的反映,产生一些毒性更大更强的气体或液体。同时,动植物死后,尸体暴露于旷野,在腐败霉变的过程中形成变异有毒的尸胺、腐胺等有毒致病的有机化合物。以液体或气体形式散发、分布在河溪、泉井、河谷、山沟等阴暗潮湿、暑热低洼或高寒阴冷地带,在炎热湿闷或阴寒僵滞的气候及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或成水汽蒸发熏郁,或成气流凝滞郁结,产生了对人体生理机能及生命构成严重危害的气体和水(液)体。由这些气体和水液体构成的自然生态现象,就是瘴。各种有毒矿物质和有毒动植物释放、排泄及经生化反应产生的各种致瘴毒素就是瘴毒素,产生瘴毒素的生物及矿物就是瘴源(原)体。当长期存在于这种环境中的有毒(害)气体、水(液)体对进入者的生理机能乃至生命造成危害时,瘴开始从一种沉闷的自然生态现象和人类产生了联系。
瘴的种类很多,据其表现形式,可分为气体形式的瘴(即瘴气)和水液体形式的瘴(即瘴水)。“瘴疠”是人中了瘴气、瘴水后的疾病的表现症状,以类似并包含疟疾及伤寒为主要疾病表现症状,是包含多种病毒性、传染性疾病的疾病群。开发越少、生态环境越原始的地区,瘴毒素就越浓烈,进入者接触或感染瘴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时期因医疗条件、医药水平及人们对瘴认识的有限,一经感染多无法救治。瘴病患者,在很多情况下会表现出并包括类似诸如疟疾、伤寒等在内的多种传染病的特征,使瘴病又具有某些传染病的性质,从而在人群中引起更大的恐慌。因瘴病的高死亡率,古人笼统将其称之为“瘴疠”,“疠”者,瘟疫也。从人们将瘴病划入瘟疫的行列,我们可以感知当时人们面对瘴疠时的巨大心理恐惧和无助。这种恐慌不仅在古代的文人及民众中普遍存在,在近现代的闽赣、岭南及滇黔等瘴气区也依然存在。(45)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资料,说明唐代普遍存在官员不愿去南方就职的行为。再根据以上关于瘴疠的科学解释,我们相信,南方瘴疠确实对唐代外遣官员的生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至少可以推测他们不愿赴任的部分原因应该是惧怕南方瘴疠之害。实际上,南方瘴疠对不少地方官员的身心都造成了危害。陈子昂《为义兴公陈请终丧第三表》称:“臣自到桂州,病转增剧,更加瘴虐,卧在床枕,两目渐不见物,起动皆须扶引,死在朝夕。”(46)张楚说自己“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从闽适越,染瘴缠疴,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斑鬓,难为壮心。”(47)王焘自称:“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量移大宁郡。提携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痢,十有六七,死生契阔,不可问天。”(48)于卲自述:“前年病热,远视不审:去夏罹瘴,近听不闻。疲惫之余,难于尸素。伏乞曲赐恩波,放归田里。”(49)吕颂为黔中观察使,上表请朝觐:“臣管内素多瘴疠,山峡重深,毒雾蒸云,常在牖户。四时多雨,不识霜雪,终岁阴昏,少见天日。出门无路,举目唯山,猿鸟之心,如在笼槛。臣从去年冬初,忽染脚疾,膝胫顽痹,行步艰难,绝无医人,素乏药物,深山穷谷,无处市求,任重命轻,何可言疾?”(50)“臣从前年六月患脚膝,行立艰难,秋深以来,更染风疾。又从去年六月,直至今日,不见三光,山谷昏昏,终日阴雨,吞茹瘴毒,实所难堪。”“臣伏见近日以来,杨悦、孙诚、李速、裴腆皆以遐裔,相次丧亡”。(51)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称:“伏以南方疠疾,多在夏中。臣自发郴州,便染瘴疟,扶策在道,不敢停留。”(52)杜牧则对任职睦州颇为不快:“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过,不敢率然请告,唯念满岁,得保生还”。(53)还说:“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喑偪塞,行少卧多。”(54)李商隐为王茂元所写陈情表中,茂元叙其为岭南节度使时实不堪瘴疠之害:“盖以久处炎荒,备薰瘴毒,内摇心力,外耗筋骸。”(55)可见,由于瘴对唐代部分地方官员在身体上产生了危害,再经过他们的叙述,无疑对更多将要去瘴区任职的官员在心理上产生了压力,促使他们不愿去偏远地区任职。
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之外,人文因素对官员外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我们知道,唐代文人多喜唱和交游,(56)而南方因知识分子的普遍缺乏,(57)造成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由此而带来的知识孤独的状况也时常令刺史们略感困惑。对此柳宗元有明显的感受,他说:“居永州,刺柳州,所见学者益稀少,常以为今之世无是决也”。(58)甚至还为自己的婚姻问题而发愁:“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自己很想结婚,可惜南方少有知识分子,也就少有“士人女子”,因而颇为苦恼。(59)
总合以上所论,笔者认为,唐代官员不愿任刺史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仅以唐代官场重京官轻外职来解释,似乎并不完备。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度,地区差别明显,偏远地区不尽如人意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对刺史等外任官员均为制约因素。当然,外任牧伯是唐代官员通向更高台阶的必经之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我们也不可夸大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的规模。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716)二月”条。
②《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
③例如,李燕捷:《从内外官迁转规律看唐代内外官之轻重》(《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刘海峰:《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文都探讨了唐代的内外官轻重问题,可以参阅。
④柳元迪:《唐前期州县官小考——以轻视外职倾向为中心》,载《韩国木浦大学论文集(1982)》,转引自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页。
⑤(14)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19-339页。
⑥长安四年(704),武则天以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20人各以本官检校刺史,而其后政迹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鍠两人而已。可见,刺史之职并非易与。参见《资治通鉴》卷207“唐纪则天顺圣皇后长安四年(704)三月”条。
⑦以下是刺史弄虚作假的生动例子:文宗大和七年—开成元年(833-836),刘源为银州刺史,“请置营田,事多不实。或朝廷遣使至边上,源必先令下吏多驱马,皆负布囊,实之以土,声言运粮于屯田,百千驮之中或致粟麦之囊一二。因潜为识认,于使者前私决其囊,以遗之用,取信于人。”(参见《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邪佞》)作假手段可谓老到,结果朝廷被他完全蒙蔽,“大和七年(833),就加简校国子祭酒,旌营田积粟之功也。”后擢为夏州节度使。(参见《册府元龟》卷673《牧守部·褒宠二》)
⑧杜牧撰、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卷15《黄州刺史谢上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⑨《全唐文》卷693载元锡《衢州刺史谢上表》称:“伏以浙东诸州,衢为大郡,……臣自量智力,惧不胜任,守信偷安,踰年受代,当此益重,实昧宠章。”诸如此类,史籍多载。
⑩《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唐代所谓清官如下:太子左右谕德、左右卫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郎将,以上四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赞善大夫、洗马、国子博士、尚书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以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议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以上六品;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太学助教,以上七品;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以上八品。其中并无地方职务。
(11)《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李素立传》。
(12)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5《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7页。
(13)李锦绣指出,唐代后期地方官执掌胥吏化的趋势很明显,自节度使以下,刺史、县令、僚佐无不职掌繁剧,不胜劳碌,疲于奔命。刺史、县令躬亲庶务,案牍繁杂,类似有权的胥吏。参见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第1章第4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107页。
(15)(19)(20)《唐会要》卷74《选部上》。
(16)《全唐文》卷54,唐德宗:《复先减官员敕》。
(17)《太平广记》卷470《水族七·李鹬》(中华书局1960年版)载:“唐敦煌李鹬,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血刃血沙上,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鹬,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鹬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絷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鼍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鹬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鼍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鹬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故事当然荒诞,但“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风俗的形成的背后,必有血的教训在其中,只是人们不能了然而已。实际上,赴任死于途中尤其是江河之中,并非没有其例。《旧唐书》卷75《苏世长传》载,贞观初,世长“出为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
(18)《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二》。
(21)杜牧撰、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22)冻国栋:《唐代闽中进士登场与文化发展管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收入其《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39页。
(2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0-286、334-342页。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但他也认为,除地理因素而外,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对人民的性格形成也有重要作用。可见,孟氏虽然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但并没有绝对化。
(24)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6)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27)《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李桐客传》。
(28)《新唐书》卷163《柳公绰传》。
(29)柳宗元:《柳宗元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0页。
(30)《全唐文》卷371,李轸:《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31)《全唐文》卷375,张谓:《长沙土风碑铭并序》。
(32)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小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18《谢窦相公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3页。
(33)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70《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并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71页。
(34)《全唐文》卷729,王彦威:《赠太保于頔谥议》。
(35)《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
(36)《唐会要》卷52《忠谏》。
(37)《旧唐书》卷50《刑法志》。
(38)《新唐书》卷78《宗室·李道宗传附道兴传》。
(39)《旧唐书》卷98《裴佶传》。
(40)《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41)《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42)刘恂:《岭表异录》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3)《番禺杂编》,转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6页。
(44)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耀南:《云南瘴气(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学杂志》1954年第3期;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文:《地域偏见和种族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等。
(45)周琼:《寻找瘴气之路(上)》,《中国人文田野》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7页。
(46)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补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页。
(47)《全唐文》卷306,张楚:《与达奚侍郎书》。
(48)《全唐文》卷397,王焘:《外台秘要方序》。
(49)《全唐文》卷426,于邵:《与萧相公书》。
(50)《全唐文》卷480,吕颂:《为张侍郎乞入觐表》。按,本表乃是吕颂自请入觐表,非为张侍郎所作也。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51)《全唐文》卷480,吕颂:《再请入觐表》。
(52)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小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谢上连州刺史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3页。
(53)杜牧撰、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卷16《上周相公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54)杜牧撰、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卷14《祭周相公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
(55)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为濮阳公陈情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3页。
(56)柳宗元说:“吾长京师三十三年,……校集贤秘书,出入去来,凡所与言,无非学者,盖不啻百数。”参见《柳宗元集》卷25《送贾山人南游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4页。
(57)《唐摭言》载:“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荆南尚不称十分僻远,尚且如此,岭南、黔中等地则更其落后。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7页。
(58)柳宗元:《柳宗元集》卷25《送贾山人南游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4页。
(59)柳宗元:《柳宗元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