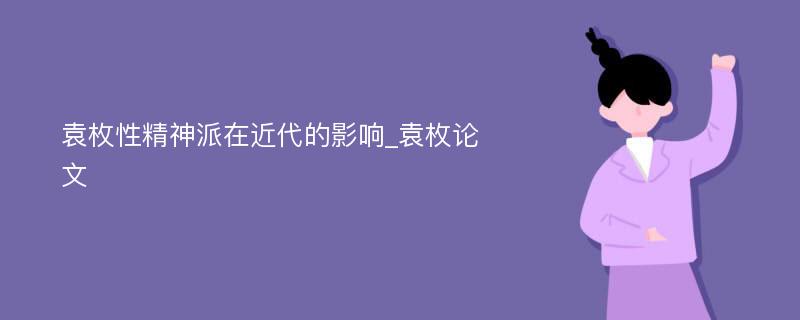
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近代论文,袁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枚性灵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阵容庞大,但真正颇具声望、才情超凡者毕竟是少数,除了主将袁枚、副将赵翼外,其他骨干分子孙原湘、舒位、张问陶等尽管成绩不凡,但诗坛地位不高。至于性灵派的基础,即一般诗弟子与袁氏家族诗人则处于“偏师”地位,人微言轻,而女弟子更难引起广泛的首肯。所以据现存资料考察性灵派的影响,基本上是考察袁枚与赵翼的影响,而主要是袁枚的影响。然袁、赵亦可以代表性灵派了。考察袁枚性灵派的影响,其阶段可分乾嘉时期与近代时期,其性质有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如果说袁枚性灵派于乾嘉时期以正面影响为主的话(另有专文论述),那么其于近代的影响则以负面为主。这其中自有时代的原因。
一
清代自嘉庆朝已渐走下坡路,道光以后更转为衰世,内忧外患,终于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沦为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忧国忧民之士皆欲挽狂澜于既倒,但在思想界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欲以传统的儒家经术为救世药方,一种是欲以改良为强国利器。反映在诗坛上,前者强调“诗言志”的载道观,标举诗的社会功能,反对嘲风雪、弄花月的审美情趣,于是袁枚与性灵派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予以批判,尽管性灵派亦不乏讽谕社会的精神,但并不为他们所重视,他们只看到性灵派的风花雪月的一面。而后者则仍汲取了性灵派思想的精髓,并予以发展。
汲取性灵派思想的人,其代表人物当推“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的近代诗坛开山祖师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身处封建衰世,与魏源等主张变法革新,开康、梁变法维新之先声,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即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以诗而论,或评云:“定庵之诗,拟求之于西洋则浪漫主义文艺,拜伦之俦也。拟求之于中国,则性灵派一流。”(朱杰勤《龚定庵研究》,《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1935年)此评道出龚氏与性灵派的渊源关系,良有见地。事实上,龚氏对同乡性灵派主将袁枚确实十分敬仰。其《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有言:“席中亦复无知者,谁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请读乾隆诗,卅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翕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并自注云:“翕山谓毕尚书沅,仓山谓袁大令枚。”可见在他心目中,袁枚属于“海内文章”之“大师。”另外,龚氏与性灵派女诗人归懋仪有唱和,同袁枚弟子王昙更是忘年之交。当然龚氏经世匡时的新思想,非性灵派可及。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不同于嘉道同代主张复古的经术之士。他对于晚明以来的启蒙文艺思想包括性灵派的诗学思想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并汲取了性灵派主真性情的观点。他明确主张诗“陶写性灵”(《述思古子议》),此“性灵”就是性灵说的真性。但是龚氏是从“尊情”、“宥情”的角度提出,又有新意。龚氏《长短言自序》云:“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氏显然是反对锄情,而主张宥情、尊情的。必须指出的是“锄情”是道学家的观点,即所谓“道学谈性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新1版,第25页),所谓“圣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五经大义终始论》)。龚氏主“尊情”、“宥情”的针对性甚是明确。他认为:“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同上)诗文主情是由人之有情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锄情”则与人本性相悖。“尊情”、“宥情”的另一个说法即是推重“童心”。李贽最早提出“童心说”,袁枚亦标举“赤子之心”,龚氏亦一再标举“童心”,即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梦中作四截句》)。“童心”即是“少年哀乐”,即是“真”性情,与李贽、袁枚的含义一脉相承。性灵派还注重创作个性,表现自我,袁枚《续诗品》专设“著我”。龚氏进而提出“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的观点。与性灵派一样,此为针砭诗坛模拟习气而发,批评“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即“剽掠”、“摹拟”(《述思古子议》)之风;此乃造成缺乏个人的真情、个性,人与诗相分离而“万喙相因”(《与人笺》)、千篇一律的根源。创作只有“诗与人为一”,才能真实无饰地表现自己的全部心灵与个性,达到诗如其人的完美程度,而与性灵派相比,此“人”的思想内涵已具有新的时代精神,是像汤海秋一样有革新思想之人。此外,龚氏追求创作的自然天成,称“文章天然好”(《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皆与性灵派观点相通。
龚氏被诗人称为“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钱吏部遗集序》),就是他尊情的结果。他的诗除了抒发追求理想的强烈感情和壮志难酬的幽怨悱恻之情外,亦颇多类似袁枚的表现艳情之作。龚氏本是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好与声妓来往,不乏红粉知己与风流艳事,因此“花月冶游”之什,是其性情诗之一部分,所谓“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己亥杂诗》),皆可见一斑。而在艺术表现上,不仅有些诗句脱胎于袁枚诗,而且其《破戒草》“瑰丽悱郁之才,未尝无取于瓯北清丽流易之体”(钱钟书《谈艺录》三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清诗之独具面目实自袁枚性灵派始,而龚氏正是继承了性灵派的独创精神,从而达到文学革新潮流的高峰。
性灵派对近代维新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继承性灵派观点与诗风者首推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政治上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文学上则是近代诗界革命之先驱。道光以后的近代诗坛日渐萎靡不振,复古之风甚烈,且派别繁多。黄氏乃作为复古派的对立面崛起其间,而其反对复古派的观点,即他所自称的“别创诗界之论”(《与丘菽园书》),正是性灵派思想的发展。
黄遵宪“别创诗界之论”的核心思想是重视诗歌的时代感与社会意义,倡导表现真情实感,反对复古、拟古,主张艺术表现具有独创性与语言口语化等。其重视诗歌的时代感与社会意义,这与维新派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相关,自然高于性灵派,此处姑且不论,而其余各点皆可视为性灵派思想的再版。黄氏《人境庐诗草·自序》云:“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今世异于古,今之人则不必与古人同的创新思想,即“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与朗山论诗》)的观点,与性灵派“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今不得不变,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等思想同出一辙。而《杂感》一诗更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复古派: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从罪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俗儒”即复古派,他们奉“故纸”、“六经”为圭臬,以“剽盗”、模拟为能事,只能是“妄造丛罪愆”,于世无补,于人无益。黄氏主张打破古人的束缚,语言要口语化,因此他特别赞赏民歌,认为“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而不能,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山歌《题记》)。而袁枚早就认为“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十五《国风》,则皆劳人、思妇、静女、狡童矢口而成者也”(《随园诗话》卷三引欧永孝语),张问陶亦云“天籁自鸣天趣足”(《论诗十二绝句》)。黄氏与袁、张观点一脉相承不言而喻。同时,“我手写我口”亦强调“我”,即“诗之中有人”之“人”,故他又说诗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人境庐诗草·跋》)。这与性灵说倡言“著我”正含义相通。可见,说黄氏之“别创诗界之论”主要是承性灵派观点而来,并非虚言。而黄氏诗歌创作,钱钟书评为“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谈艺录》三),亦可见与性灵派有密切联系。
诗界革命巨子梁启超(1873~1927),对袁枚似乎十分鄙视。《清代学术概论》称:“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按:袁、蒋、赵“三大家”并称时,赵乃专指赵翼,与赵执信无涉。梁氏这一常识性错误,表明他对乾隆诗坛并未深究。但其诗学思想仍不乏与性灵派相关之处。例如,他反对厚古薄今,称:“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平生最恶闻此言。”(《汗漫录》)这自然是其维新思想的反映。此外,他甚推重感情,认为感情“是生活的原动力”(《人生观与科学》),故诗应抒发真性情。他说:
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可以发摅,本难工。况郊庙诸歌,越发庄严,亦越发束缚。无论何时何人,当不能有很好的作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且因其体制之庄严亦束缚性情,故不为梁氏欣赏。反之,对杜甫之寓有真性情之作予以赞美,并以“情圣”誉杜甫(见《情圣杜甫》)。而且他还说谐谑之情,更能感人:“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导之。或故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以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淫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过之。”(《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此思想与性灵派之重诙谐风趣实亦相通。
此外,道光以来诗人、诗论家,还有一些肯定袁枚性灵派者,现择其要者简略论述。
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至四川学政的道州人何绍基(1799~1873),他对袁枚很尊重,称“山水文章儿女缘,此翁真是地行仙。披图不憾余生晚,憾不留公到百年”(《袁简斋先生杖乡图,诗为少兰大令题》)。他论诗言“性灵”,认为诗“能发性灵方近道”(《次韵答梅根居士》),“性情有本斯无穷”(《中丞潍县寄来论诗诗》),都是标举真性情。而且他又重视灵感,称“诗思无端满太空,偶然飞堕酒杯中。来时霅遝纷如雨,去后苍茫渺若风。”(《次韵答梅根居士》)这都与袁枚、张问陶的论述相类似。但他把“‘性灵’与‘明理’统一”,重温柔敦厚的“诗教”,“故没有像袁宏道、袁枚那样带有异端的色彩而步入正统的范围”(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章第6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又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江苏兴化人刘熙载(1813~1881)的《诗概》,亦讲性灵:“性灵光景,自《风》、《雅》肇兴,便不能离。”同时强调“真”:“诗宁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此“真”当然指真性情。另外标举诗中“有我”:“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后一句当然是性灵说思想,前一句主张不废传统亦符合性灵说观点。但刘氏于性情要“辨其归趣之正不正”,则是独到之见。
咸丰五年(1855)举人,安徽定远方濬师对袁枚甚钦慕,不仅撰写了《随园先生年谱》,而且在《蕉轩随录》中批评吴嵩梁“少时依傍随园门墙,希冀一语奖励,以耸动公卿耳目”,而于袁枚身后,“竟尔逞其狂吠”,大肆攻讦;又反驳潘德舆“以‘狭邪’加蒋、袁、王、赵”等,竭力维护袁枚的声誉。咸丰十年(1860)进士,杭州人钟骏声(1828~?)著《养自然斋诗话》,论诗颇服膺袁枚性灵说,故赞赏诗之“自写性灵”、“自写性真”、“自写真趣”等,而标举真性灵及真趣,乃源于性灵说。同治诸生,江西南昌人尚镕著《三家诗话》,专论袁枚、赵翼、蒋士铨,而袁、赵皆性灵派代表人物。尚镕于三人中尤推举袁枚,称“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而子才点化胜之,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而子才简括胜之。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所以喜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应该说尚氏的评价颇中肯綮。另有光绪举人,海澄邱炜萲(1874~1941)著《五百石洞天挥麈》,于袁枚颇为推重,除不满其《新齐谐》为“生平最无聊赖之作”外,于诗文皆予好评,称其“《小仓山房诗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达今人所欲言,是以语妙当时,而传后世”。并赞赏其“论诗偏主性灵”,“立言浅切”,“为诗教开一方便法门,引人入胜,不可废也”,此评言性灵说价值角度颇新。林钧的《樵隐诗话》称“不甚喜随园诗,而独服其论诗之言。盖诗主性灵,此千古不灭之论也”,把性灵说与随园诗区别开来,亦别具只眼,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称袁枚“论诗雅有深识”正相契合。而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曾提到樊增祥“少喜随园,长喜瓯北”;钱钟书称“曲园之于子才行事,几若旷世相师”(《谈艺录》五九),皆可见性灵派诗影响之一斑。
二
与乾嘉诗坛相比,道光以后对袁枚性灵派的批判增多。原因之一是袁枚诗固有的纤佻、轻薄之弊,发展到性灵派末流,已更加明显,而在清诗发展的危机中,便自然潜伏着改变诗风的内在要求。原因之二是时局日益衰败,一批关心时局、胸怀匡世之志的名士,注重道德修养,以气节相尚,于诗则强调其社会功能,欲以文章教化人心,因此以性灵派为批判的对象,自然无可非议。但由于观念的保守性或认识的片面性,他们对性灵派往往存在误解,批判时或夸大其词。另外,也有一些复古派人物,对袁枚性灵派存有偏见而大力攻击,更是十分自然的事。
批判袁枚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潘德舆(1785~1839)。他身处衰世,愿以“一腔热血”匡救时局,但仕途不顺,只能寄希望于文章。鲁一同评之曰:“其宗旨以为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用在有刚直之气,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顽懦鄙薄以复于古。”(《安徽候补知县乡贤潘先生行状》)此“宗旨”决定了其诗学观的根本思想。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批评性灵派云:
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予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媟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于呼!此岂性情也哉!
这段话从三个方面批评性灵诗写“性情”之失,承袭的是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观点,但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对把诗引向脱离社会现实的“嘲风雪、弄花草”乃至“荒淫狎媟”之途,以“挽回世运”,又是发扬他所崇仰的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空谈义理性命之学的理学家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于诗境标举“质实”,反对虚空,亦是为其改变时局的理想服务的,有其积极意义。然正如林昌彝所指出的:“潘四农论诗专取‘质实’二字,亦有偏见,盖诗之品格多门”,“岂得以‘质实’二字遂足以概乎诗,而其余可不必问耶?”(《射鹰楼诗话》)潘氏确有其偏执的一面。由于偏执,他对于不质实,不具有美刺、教化作用的诗一概排斥,根本不提诗的审美作用,这与性灵说不提诗的社会功能一样,皆走向极端而不可取。
与潘德舆具有同样政治思想的张际亮、林昌彝等对性灵派同样持批判态度,是理所当然之事。张际亮(1799~1843)亦具经世之志,忧时伤国,关心社稷民生。他在给潘德舆的一封信中论诗,把汉以下的诗人分为三种: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志士之诗。他以志士自许,故极力推崇志士之诗:
若夫志士,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观万物之理,备四时之气,其心未尝一日忘天下而其身不能信于用也,其情未尝一日忤天下而其遇不能安而处也,其幽忧隐忍慷慨頫印发为咏歌,若自嘲,若自悼,又若自慰,而千百世后读之者,亦若在其身、同其遇而凄然太息怅然流涕也。盖惟其志不欲为诗,故其诗独工,而其传也亦独盛。
志士显然是慷慨悲歌、志在安邦定国的人,其诗抒发幽忧慷慨之情,关乎社稷民生,足以传之千古。他最鄙视的是“才人之诗”:“模范山水,觞咏花月,刻画虫鸟,陶写丝竹,其辞文而其旨未必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必广也,其情往复而其性未必厚也,此所谓才人之诗也。”(上引均见《答潘彦辅书》)“才人之诗”的致命伤即是与匡时济世无涉,远离“风雅”。在他的眼里,乾隆以来的诗人皆不足道,而对袁枚尤其鄙薄:
袁子才辈则又所谓野狐外道也,然皆足以惊众侈俗,取一时之声誉。子才尤甚,盖少年轻薄,其溺于佻滑放荡之习久矣,或犹畏大雅之讥,不敢显以自遂,一旦见当世负重名如子才者,举其佻滑放诞之诗谆谆道之,其乐为依附,犹积薪然火,焰必张矣(《答朱秦洲书》)。
“袁子才辈”指性灵派,而张氏斥其为“野狐外道”,则显然是站在正统立场上说话。他又抨击其首领袁子才更是“佻滑放荡”,关键在于其“无与风雅之旨”(《岭南后三家诗序》)。为针砭性灵派之流弊,他主张“惟进之以积理养气四字”(《答姚石甫明府书》)。“积理养气”是老药方,但张氏亦加入了新的“药剂”,即与关心现实相联系。尽管张氏对袁枚性灵派的批判很难说客观全面,但在当时还是有其针砭现实的意义的。
林昌彝(1803~1876)著有《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等诗话。鉴于鸦片战争后国家危亡的时事,他写诗话乃是“借诗以正风俗,意在维持风化”(温训《射鹰楼诗话序》),可见他亦是恪守“诗教”的传统观念的。但他借他人之言赋予“诗教”以新的含义,包括了“兴革政教”、“化民成俗”、“感发志意而治其性情”(《海天琴思录》)的内容。以这样的诗教观来审视袁枚《随园诗话》与随园诗,就不予好评,如“钱塘袁简斋《随园诗话》,讥孔颖达《五经疏》为郑康成之应声虫,简斋于是乎失言。简斋喜词章,不喜经学,故作此呓语,况所讥未能的切耶!”(《海天琴思录》)此批评《随园诗话》反对经学。又诗云:“诗薮金陵筑小仓,少年绮丽晚颓唐。”(《海天琴思续录》)此批评随园诗有失风雅之旨。但总的看,林氏对袁枚的批评比较温和,而且林氏论诗亦主“有性情”(《二知轩诗钞序》),并且不反对诗写男女之情,这又与袁枚相同。他说:“《诗》三百篇言男女之情者极多,采兰赠芍,私以相谑,圣人亦存之以为鉴戒。魏晋以来,《子夜》、《折杨柳》诸作赓唱者累时不绝。沈归愚选列朝诗,凡缘情绮靡之言皆所不录,钱塘袁简斋非之矣。”(《射鹰楼诗话》)看来他对袁枚批评沈德潜不选情诗一事表示首肯,又可见袁枚对其正面影响的一面。
批判性灵派最严厉的是朱庭珍(1841~1903)。他是同光年间云南诗坛领袖,思想属于守旧派,著有《筱园诗话》。他对袁、赵等攻击之口吻颇近章学诚,基本是从卫道立场出发,与经济之士之批评性灵派并不相同。《筱园诗话》云:
赵云松翼,则与钱塘袁枚同负重名,时称袁、赵。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
朱氏对袁、赵性灵诗予以全面的贬斥,列出诸多罪状,简直一无是处。这样,袁、赵自然成为“风雅”之罪魁;而性灵派之“继起”则成为“纷纷逐臭之夫”。但朱氏所谓“风雅”、“六义”,并无时代意义,这可能与他身处西南一隅,远离政治变革有关。因此这种谩骂式的批评实在不足为训。其实朱氏论诗不乏精义,如反拟古而批评沈德潜“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反肌理派而讥讽翁方纲“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论诗主张“以识为要”,“诗贵真意”,特别是强调“诗中有我在焉,始可谓之真诗”,且解“诗中有我”为“我有我之精神结构,我有我之意境寄托,我有我之气体面目,我有我之材力准绳,决不拾人牙慧,落寻常窠臼蹊径之中”(均见《筱园诗话》),甚是精辟,细究其精神,正与性灵说相通。当然,朱氏最重视的还是“诗教”:“温柔敦厚,诗教之本也。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温柔敦厚之诗。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传后世,轻薄之词,岂能传哉!”(《筱园诗话》)这一保守的立场又表明他与性灵派有根本差异。
晚清批判袁枚性灵派者还有不少。如江西赣县人钟秀(1808~?),其刊于光绪年间的《观我生斋诗话》,论诗推重沈德潜、潘德舆,故亦重“诗教”说,以复古求正的思想品评历代诗歌,目的在于“力矫流弊”,即匡正袁枚《随园诗话》造成的所谓“风雅扫地”的局面,乃是复古派的老调。又如杭州人谭献(1832~1901),乃词论家,颇有建树。在《复堂日记》中斥袁枚为“文妖”,并称他是“东南大乱”即太平天国反清之先兆,“罪名”大得吓人。山阳人周实(1885~1911),为南社诗人,革命烈士。他出于反清斗争的需要,在《无尽庵诗话》中强调诗歌与“世变”、“时政”之关系,认为“若夫守宗派,讲格律,重声调,日役役于揣摩盗窃之中,乃文章诗歌之奴隶,而少陵所谓小技也”,反对复古与形式主义之风,并推重“忧时悯俗”、“陶情淑性”,认为“其外乎此者,盖不足语风雅也”。由于重视诗之“风雅”即“士君子伤时念乱”之情,故再审视性灵派之作,就认为袁枚虽“主张性情,其失也在狎亵”。而倡导新的诗风,以之为反清革命服务,自有其现实意义,其出发点与朱庭珍、钟秀、谭献自然大不相同。近代著名词论家王国维(1877~1927),于中国美学史上有卓著贡献,但亦批评“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人间词话·删稿》),这与其遗老思想的保守性分不开。
综上所述可知,道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由盛转衰,并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盛世文学流派的性灵派,其中一些思想与诗风已不适合时事政治的需要,故无论是欲匡正时弊的志士,还是欲变法维新的仁人,乃至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大多对性灵派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虽亦有少数人出于卫道,但多数人出发点是积极的,亦切中了性灵派末流的一些弊端。不过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对于性灵派愤世嫉俗、关心社稷民生的一面多未认识到。像龚自珍那样真正理解并汲取性灵派思想之精髓,使之发展升华者,则寥若晨星,惟其如此,所以更显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