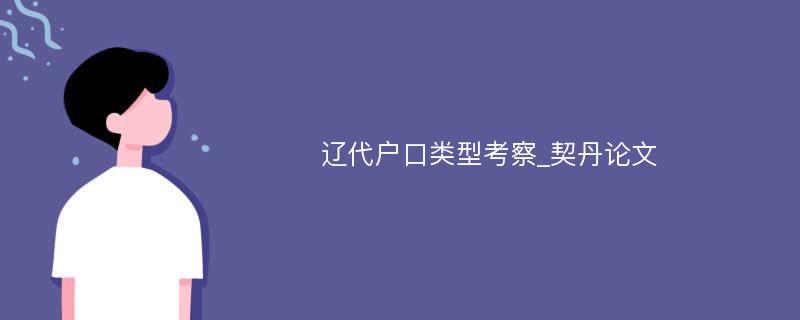
关于辽朝户口类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口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3)03-0071-03
中国历史上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立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宋宣和七年)为金人所灭,统治中国北方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除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量不能计算。”(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54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陈述先生的见解道出了研究辽代户口的高难度。这也是治辽史者少涉及辽代户口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研究辽代户口必须从当时的户籍制度和户口类型等基础问题入手。
据《辽史·地理志》,至五代时期,契丹八部已“辟地东西达三千里”,“属县四十有一”。自辽太宗以迄兴宗,五京渐备。“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头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显然,辽代人口当即生聚于这一广大地域空间的人口。按其户籍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类:州县户口、宫卫户口、头下军州户口、部族户口、属国户口以及属于特殊社会阶层的僧寺户口,他们共同构成了辽代户口。而实际上,辽朝政府经常有效掌握和控制的户口仅限于王朝州县赋役户口和宫卫军户,属国与辽朝之间保持的是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
州县户口 这是辽代封建赋役的承担者,故又称之为赋役户口。辽代早在太宗时,政府即曾命令“籍五京(按太宗时只有上京、东京和南京,中京和西京是圣宗统和与兴宗重熙中置)户丁以定赋税”,只是“户丁之数无所于考”(注:《辽史》卷59《食货志》。),当时户丁的统计资料并未保存下来。但由此可知,辽代赋役是以户丁为征收对象的。契丹统治者为了获取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政治的需要特别注重户丁检括,而置丁外人口于不顾,所以文献所载仅限于户丁资料。辽代200余年间,并未建立定期阅实户口的制度,每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据《辽史》记载,辽代诏括户丁共进行过10次,均在辽圣宗统和纪年之后。这10次户丁检括,州县户与宫卫户显然分别进行,即分属于两个系统。这与“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注:《辽史》卷46《百官志》。)直接相关。故《辽史·兵卫志》论五京乡丁时指出:“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其余蕃汉户丁分隶者,皆不与焉。”(注:《辽史》卷36《兵卫志》。)即隶于宫帐的契丹户丁与蕃汉转户丁,隶于部族的契丹户丁皆不属五京乡丁之列。蕃户即契丹户之外的少数民族,如奚、室韦、女真、渤海等户。因此辽代州县户口乃是州县领属和检括的赋役户口。
宫卫户口 这是独立于州县户口之外的辽代帝王的侍卫兵戎户口。“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注:《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实乃“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猎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注:《辽史》卷31《营卫志》。)的军政一体、军民一体的军事行政组织。其所领属的户口,即宫卫户口来源于部族与州县,原系部族和州县户口的一部分,一旦析出便独立存在;显然已与“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注:《辽史》卷35《兵卫志》。)、“备畋猎之役”的部族户口不同,与前述州县赋役户口亦不同。在这里,太祖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益以渤海俘、锦州户”的事实不容忽视。弘义宫,契丹语谓“算斡鲁朵”,汉语即心腹宫卫(注:《辽史》卷31《营卫志》。)。以后诸帝的宫卫仍以心腹卫及部曲为主,增以降服户口、部族户口、州县户口及罪没者。宫卫(府)下置州县、提辖司、石烈、瓦里、抹里、得里、闸撒等军事与行政组织。终辽一代,共置宫卫(府)13个、属州38、县10,提辖司41、石烈23、瓦里74、抹里98、得里2、闸撒19个(注:《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军户即隶属于这些军事行政组织。每宫卫提辖司除领属一定数量的契丹户口外,还领属诸蕃部及汉人即蕃汉转户。各提辖司共领属正户(契丹户)8万,蕃汉转户12.3万,共计20.3万户(注:《辽史》卷31《营卫志》。)。按《辽史·国语解》,提辖司为诸宫典兵官,因宫卫军户即兵即民,所以提辖司实际上就是管理宫卫户的军事机构,兼管宫卫兵与民之事。
著帐户为宫分“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宫之属,皆充之。”一般说来,“著帐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其户口编入宫卫所属瓦里,领于著帐郎君(注:《辽史》卷31《营卫志》。)。因此著帐户实乃辽代帝王贵族的随身奴仆,系宫卫户口的一部分。
部族户 按《辽史·营卫志》:“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举,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甲兵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实为之爪牙云。”这里不仅指出了部族析置的过程、民族构成、部族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说明了部族成员的义务及隶属关系。显而易见,尽管部分宫卫成员来自部族,但部族和宫卫并不属一个系统。作为爪牙的部族包括大首领在内,地位均在腹心宫卫之下。太祖时包括奚、室韦诸部共置20部,其中二国舅升入帐分。至圣宗时以旧部置16部,增置18部、共计34部。契丹诸部包括奚、室韦、女真、乌古、唐古、回鹘在内,皆分隶于契丹南、北枢密院(注:《辽史》卷45《百官志》。)。以上诸部或“以户口蕃息置”,或以宫分改置,或以数部“民籍数寡,合为一部”(注:《辽史》卷37、38、39《地理志》。)。因此,部族户与宫卫户互为表里。宫卫户乃析部族与州县户组成,直属于诸帝宫卫;而宫卫户蕃息则又可改置或析置部族,直隶于契丹南、北枢密院。诸部使命如前所述,在于备畋猎之役,承担赋役,并戍守四境,以“为之爪牙”。
头下户口 它领属于头下军州,为头下主的私奴。按《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这里不仅指出了头下军州的实质和隶属关系,而且阐述了头下军州户口的来源及其人身依附关系和应尽的义务。考头下户口来源,除以战俘为主外,尚有从部民中分化出来、依附豪强、官僚、贵戚的部曲(注:《辽史·地理志》:“横州,国舅萧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汉故辽阳县地,因置州城……户二百。”),以及朝廷赏赐的头下户口和贵族的食邑封户等。据考证,辽代共创置头下州县达39个(注: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116页,中华书局,1979年。)。《辽史·地理志》记载的16个头下军州所属头下户共计34300户。头下除置州军外,尚建置有头下县、城、堡等,即“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注:《辽史》卷48《百官志》。)。辽代节度使为军政长官,早期头下军州的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自然有监督性质;及至后来不仅节度使之下诸官皆以本主部曲充任,而且连节度使的任命也“往往皆归王府”(注:《辽史》卷48《百官志》。),正说明头下军州隶属关系上的相对独立性。尽管如此,头下军州对朝廷还要尽一定的义务:一、“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或“守卫四边”(注:《辽史》卷35《兵卫志》。);二、“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注:《辽史》卷59《食货志》。)。《金史·食货志》谓头下户“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输租为官实质上是领主头下对辽朝政府应尽的义务。头下户与辽朝政府所属五京州县赋役户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因此,头下户口实乃州县赋役户口之外的户口,不直接隶属于政府,非国家的赋役编户。
属国户口 据《辽史·兵卫志》:“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故《辽史·百官志二》称:“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各自为军,实质即各自作为一类户;宫帐、部族、京州、属国、乃至头下军州分属不同的户籍系统。《辽史·兵卫志》云:“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按上述164.28万兵仅包括中京三韩一县丁,故有下述说法)、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辽代属国户口属于独立的系统,但由于没有统一统计,其户口数不包含在164.28万之中。从属国与辽朝保持军事和朝贡联系来看,属国户口属于辽朝户口。因此,辽朝户口应当主要由州县、宫帐、部族(包括大首领)、头下军州和属国户口组成。
僧尼户口 在辽代,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僧尼应是当时社会人口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据辽代人记述:“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货,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故今海内塔庙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似耆阇之涌出。”(注:《全辽文》卷8。)这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时上自帝王下至士庶的佞佛心理和趋之若鹜的热情。如在辽之南京地区,“诸阿兰若,岩居野处,如鹫峰鹿苑者,比比而是,云之城邑,则又过焉”(注:《全辽文》卷10。)。佛寺尼庙,胜似城邑,比比林立,故僧尼甚众。辽道宗大康四年(1078年)七月甲戌,诸路奏饭僧36万人(注:《辽史》卷23《道宗纪》。),与《辽史·道宗纪》“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记载略有不同。按辽人饭僧一般在有大征伐杀人众多或灾异严重时同时进行,而并非一年中反复进行的特点,推知当时拥有36万僧尼是可信的。对辽代奉佛惟谨、僧尼众多一事,北宋使辽大臣苏辙曾谓:“此盖北界(按指辽朝)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注:苏辙:《栾城集》卷16。)无疑,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辽代佞佛规模之大,危害之深。当时祝发之僧者不仅仅有平民百姓,而且有官宦子女。如广德军节度使王泽,其二子并登进士第,而三女中竟有二女出家受戒(注:《全辽文》卷7。),占子女数的40%。对这众多僧尼,辽朝政府则实行了供养制度。故史称“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注:《金史》卷46《食货志》。)。因此可见,辽代僧尼是一个不属州县编民、不向封建国家承担赋役而由民间供养的庞大寄生阶层。其丁口乃是上述各户籍之外的部分。
综上所述,辽朝户口分属州县、宫分、头下州县、部族、属国、僧寺等不同的户籍类型,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统计和制度,故而《辽史》记录的州县、头下和宫卫户丁均只是辽朝户口的一部分,都不能代表辽朝户口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