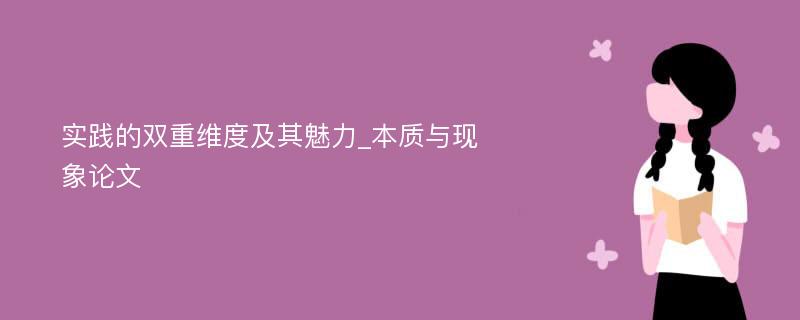
实践的二重维度及其人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其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4)03-0063-07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思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第1卷,p.55)的论断,表明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自始就是外在的“环境的改变”与内在的“自我改变”二重维度的有机统一。人正是在“改变世界”——既改变人外在的环境世界,也改变人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实践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人成其为“人”的历史性生成。因此,无论是“环境的改变”还是人的“自我改变”,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深情眷注,体现出实践所具有的人的价值意韵。 一、实践的外在维度 (一)改变自然的实践 实践是因着人的需要而发生、由人的需要所引起的“人的感性活动”,因此对实践应更多地从“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2](p.297)方面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p.94)这表明,人的纯然动物性的需要并不就是人的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人的真正的需要。只有需要成为“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3](p.126),或实际需要“人性化”,成为属于他的人的本性的那些需要时,才是真正属“人”的需要。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马克思再三致意,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p.514),“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3](p.34)。“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决定着实践行为所当具有的人的品位。在实践中,人把自己的目的意图、价值取向等内在尺度实现在对象中,“物化为对象”,使对象发生适合人的需要的变化,成为确证和实现“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对象”;人则在人化殊多的对象中创造和展现自己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成为他自己。因此,实践是一种人在其中实现自己、肯定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感性活动。 在改变外在世界的实践中,首要的是改变自然的实践。所谓改变自然,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解放自然本身固有的潜力和特性,并“按照美的规律”人化之。马克思认为在人的“需要的体系”中,单“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第1卷,p.79)由生活需要所引起的物质生产,必然诉诸改变自然的实践,从而在实践上把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于,生产实践根源于人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而“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规定着物质生产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处处都把寄托着人之价值的“内在的尺度”体现到“按照美的规律”改变自然的实践中,使自然发生合乎人性及人的发展的变化,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具有“人的本质”。“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p.95)如是,“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3](p.122)可见,正是通过生产实践,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人则在其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中直观自身,直观他的人的本质。由此,马克思说:“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3](p.37)、“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p.127)同时,在改变自然即“解放自然的潜力”的实践中,人自身的自然也人化着,不仅人的肉体的一切感官都是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如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耳朵成为有音乐感的耳朵,而且人的智力也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5](p.574),即人自身的潜力也获得了解放。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p.96)因此,改变自然就是改变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自己,“解放自然的潜力”亦是解放人自身的潜力。这样,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物质生产实践既不意味着“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3](p.118),因为“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1](第4卷,p.179),更不表明物质生产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所进行的生产(因为人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而是自始至终就不曾脱开人的价值寄托。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贯穿马克思整个思想的价值主题。所以,他并不仅从经济效用的角度考察物质生产实践,而是把它提高到“人的高度”,从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发展的高度,把它既看作是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即马克思所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p.368)),又看作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3](p.34)。这样,“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3](p.37)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既是“受动的存在物”,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的受动不同于他物的受动。他物的受动是纯粹的受动;人则能自觉其受动,即他“感到自己是受动的”,因而人的受动是能动的受动。“能动”体现出人的生命是“自由”的。“自由”是人所独有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因而是人的类特性。基于此,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3](p.169)既然人受动于自然,人的活动便不能不遵循自然的律则,这表明了实践的科学取向;既然人能动于自然,人的活动必然赋予自然以人的价值,使之发生适合人的需要的变化,这凸显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人在“受动”而“能动”地改变自然的实践中,须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式,生产“适合人性”需要的产品,创造作为“真正人的生活基础”的物质世界。同时,人因对其“受动”有所自觉而又“能动”于自然和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从而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人也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这样,人才不至于淹没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并在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确证自己,使对象呈现出人的意义。因此,人在改变自然的实践中,不仅获得物质性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则是确证了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成其为人,成为他自己。正如H.马尔库塞所言:“在这种自由活动中,人重新生产了‘整个自然界’,并且通过改造和占有自然界,使自然与他自己的生命一起得以进一步发展”[6](p.108)。为此,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第1卷,p.67)可见,改变自然的实践,既改变着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使自然解放自身的潜力和特性,并呈现对人的意义,也改变着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使人凭借现实的、感性的自然表现自己的生命,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彰明了实践所蕴含的人的价值意韵。 (二)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 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马克思更多属意和强调的显然是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这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是一个“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第1卷,p.287)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4](p.515),以至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7](p.45),导致了“人的完全丧失”——不仅“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7](p.45)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产阶级公开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他们公然“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3](p.57)这就是说,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即“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这样,“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3](p.104)作为资本存在的工人为了生存,便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甚至“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3](p.23)结果,他“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3](p.19),从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另一方面,在资本家眼里,“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3](p.72)资本家所关心的不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而是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和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对他们来说,“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3](p.105)因此,他们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这样,资本家不仅把工人变成了物——能创造价值的机器,而且把自身也变成了物——人格化的资本,导致人的世界被物的世界所淹没,“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p.103)这就既“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又导致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形成了金钱拜物教现象——“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p.194)并且,国家也沦为资本奴役人的工具,“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1](第3卷,p.53)由是,人的现实的世界和关系成了资本或金钱的世界和关系,成了“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和关系。人则被资本或物的世界和关系所支配和奴役,陷入欲求生存外观而不可得的、非人的生存境遇。 出于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关切,马克思提出了必须改变现存的一切以“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的历史任务,从而把改变社会的实践指向了“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现实世界和关系。他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为“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4](p.234)为此,必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第4卷,p.385),反对“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现实的、现存的世界”,“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7](p.45),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样,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把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中解放出来,“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1](第1卷,p.14),“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2](p.521)对既有现实世界和关系的实践地扬弃,还给人的是真正属“人”的世界和关系,是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因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p.189)鉴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p.24)。因而,对既有现实世界和关系的实践地扬弃,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3](pp.123~124),从而使对象性的现实“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或使“真正的人”成为人的整全的现实。 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可现在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需要消灭私有财产。这便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第1卷,p.286)由于“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p.100),即私有财产是“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的生命外化,消灭私有财产也就意味着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地扬弃。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就是“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3](p.369),获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实现“自由个性”,使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现实的人”成为合乎人的本性的“真正的人”,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基于此,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p.121)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地扬弃,建立的共产主义是作为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人类社会“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实现自由”[9](p.215),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由的个人自主联合而成的“真实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人的“现实的自由”。 二、实践的内在维度 倘把“解放”并不仅仅理解为每个人须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的束缚或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解放”也必然意味着每个人须从内在世界的束缚或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身的主人”,即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这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每个人的发展中,来自主观世界的束缚并不比来自客观世界的束缚少,来自自身的阻力并不比来自外界的阻力少。甚至可以说,在同样的外在条件下,每个人发展的程度根本取决于自己从自身的束缚和阻力中解放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2](p.165)的道理所在。人的自我解放提醒着每个人,不仅要从物质的贫困中解放出来,更要从精神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不仅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更要把心灵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不仅从“被名利迷住了心窍”和“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中解放出来,更要从“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解放出来,从“最下流的意念”之“精神堕落”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每个人须直面自身、改变自身的、本己性的解放。所谓“本己”,一方面是说此种解放由己不由人,因而它有赖于每个人自己自觉地做切己的自我改变;另一方面人的自我解放还给人自己的是人所当有的情操、意趣、意志、品格、“头脑”、观念,引向和成就的是人之为人的道德、人格、精神、境界,因而它是每个人为了“人本身”这一“人的根本”的解放。依马克思之见,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理论出发的解放。因此,人的自我解放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解放,是人“向自身的、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生成的本己性的解放。这种本己性的自我解放使“人的自我改变”的实践成为人“内在的必然的需要”,并规定着其价值取向。 依马克思之见,如果人不改变自己而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他就不能真正从自然和社会中解放出来。他这样写道:“如果人们不改变自身,而且如果人们即使要改变自身而在旧的条件下又没有对‘本身的不满’,那末这些条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4](p.440),“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3](pp.24~25)“没有对‘本身的不满’”,意味着人对自身的麻木不仁;“不承认自己是人”的人,则是自甘沉沦于奴隶的人。他们既不愿做有思想的人,也不愿做自由的人,因而没有任何思维和任何人的尊严。基于此,马克思在唤醒人的自尊心以趋向崇高的向度上,发出这样的狮子吼:“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只有这种心理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10](p.409)他也在激起人的耻辱心以奋起改变的意义上诲导着人。针对德国陷入泥坑且越陷越深的现状,他担保:“连最缺乏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这种民族耻辱”,虽然“耻辱代替不了革命。可是我认为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10](p.407)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疾呼:“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1](第1卷,pp.4~5)唤醒人的自尊心、激起人的耻辱心,警醒着每个人,须回向内在世界、直面人本身,力发耻心和勇心,既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当下处境并时刻警醒,又自觉到“人作为人”的需要并内化为自身的需要;既以人的眼光和人的高度把自身当作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使“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又勇于同过去一切束缚、“纠缠”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把“深沉的神圣思想”植入心中,确立“人的观念本性”,发展“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形成“头脑”和“精神武器”,并“变成实践的力量”。这样,就在自我改变的实践中,每个人使自己当下的现实按照“人的自我意识”、向着人成其为人的面貌改变,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自身相协调、相一致,从而凭藉自己的全部历史、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实现“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自我生成。 人的生命本身是感性的活动,并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p.125)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3](p.126),比如同一个“矿物”,在一般人眼里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它的商业价值,只有艺术家才感受到它的美和特性。因此“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3](p.155)而“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3](p.126)这表明,改变自我必须解放、丰富和提升人的感觉。所谓解放人的感觉,就是把“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p.124)中解放出来、从“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使之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马克思曾提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4](p.330)这“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就包含着发展自己的一切感觉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觉地从事一些较高级的活动(如对艺术、科学和创造的追求),使自己“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从事有意义的、感兴趣的活动(如欣赏美景、阅读经典作品、吟诵诗词歌赋等),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感觉能力,提升知、情、意的水平。由于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并且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中,人才形成了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因此马克思指出:“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3](p.169),“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p.126)换言之,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人在展开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中产生的,是人自身实践的结果。随着人自身感觉的丰富和提升,有限的对象才绽放出五彩缤纷的意义,同样的对象才呈现出更加丰富、深刻的意韵。每个人就在感觉的丰富和提升中,自我创生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 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9](p.455)“自己去寻找”或“选择”,在人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因而自己把握和担当自己命运的意蕴上,提示着人的命运的自作主宰——自由而非他由、由己而不由人。既然人的命运须得每个人自己审慎地抉择,自由就绝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而是始终有着自己的价值指向,这便是“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这一取向使自由在内向度上更多地体现为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意味着人类精神的自我规定、自我更生、自我精进和自我实现。“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9](p.119)人正是在由己不由人的自律性提升中,开阔胸襟,纯洁心灵,丰富情感,确立理想信念,提升需要的品位和层次,转变自己的生存态度,贞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9](p.217),不断把生命引向精神的富有和内心的高尚,实现着自身的完美。因此,职业的选择不应仅仅出于谋生的外在效用考虑,而应更多地体现人作为人而成其为人的内在需要。为此,马克思确立了“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9](p.459)“高尚”、“幸福”、“自身的完美”这些字眼所折射出的心灵祈向,澄明着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命运的现实关切,即他眷注的是人所应有的道德人格,冀望的是人所当有的生命境界,要求的是“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因此,每一个神交于马克思的人,都会自觉承担起把自己成全为“有道德的个人”的发展责任,并在躬行于自我改变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心灵的滋养、精神的充盈、人格的成长、境界的提升、意义的绽放,从而让自己作为一个人站立起来。 三、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深化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整体性认识,关键在于把握改变环境的实践与人的“自我改变”实践的二重维度的统一,彰显其现实意义和价值。这种统一体现在:一方面,改变环境的实践,就是改变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建立“合乎人性的环境”,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能认识和体会到自己是人,创造“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实现人在现实世界的解放,获得“现实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人。马克思指出,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第1卷,p.73)因此环境的改变和提升必然改变着生存于此环境中的人,这就是升华人的需要、丰富人的情趣、充实人的精神、提升人的境界。另一方面,人的“自我改变”的实践则是改变人的内在世界,把心灵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到自己本身”,自主地陶冶性情、纯洁心灵、提升审美情趣、增益道德品格,从而在自律性的提升中,趋向精神的富有、内心的高尚和“自身的完美”,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成为“有道德的个人”。这样,“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实现自由”[9](p.215),让自己“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第3卷,p.760)。马克思曾指出:“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3](p.25)因此,改变自身也就意味着改变自己的社会,即改变和提升了的自我“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10](p.651),创造合乎人性的环境,使环境发生适合人性的变化。如是,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第1卷,p.92)、人与自己的环境一变俱变的动态绵延中,人获得了属己的自由和解放,成为“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因此,无论是“环境的改变”还是人的“自我改变”,在究极意趣上,实践皆不在于致取外在的功利,而是归宗于人的历史性生成,即人实现自由和解放、成全自己为人的那一度上。人,才是马克思实践思想的真正价值底蕴。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由于过分注重外在维度的改变环境的实践,且把它唯一化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根本遗忘了其所蕴含的成全自己为人的价值指向,不仅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极大损害,导致了生态危机,而且极度膨胀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造成了“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11](p.24)这必然驱逐着人们贪婪地攫取利益,结果,整个社会似着魔一般,逐利而疯,争利而狂。人完全沦为了实现物质欲望的工具和消费的机器,以至于“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12](pp.79~80),“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第1卷,p.275)这种用精神上的堕落来换取物质上的丰富,已严重危及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导致了人为财而亡的非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危机。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长期忽视甚或根本淡忘了人的“自我改变”这一内在维度的实践,人失却了内在的精神家园、情趣意志、道德品格、良心尊严,结果,生命因缺失崇高、神圣的东西而流于肤浅粗鄙,从而精神毫无生趣,生活因淡去了理想信念而变得浮游无根,从而心灵浮躁不堪,人深陷于心灵危机、精神危机之中。可见,这危机并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人成其为人的那一度的失落,是“人本身”这一“人的根本”的危机,即“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6](p.121)。邓小平曾说:“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13](pp.705~706)因此,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马克思实践思想的二重维度及其蕴含的人的价值意韵,在“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中,既改变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又改变人的内在世界,以人的内在世界的改变引领现实世界的改变,以现实世界的改变促进人的内在世界的改变,实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历史统一,无疑将有助于化解现代人正遭遇着的——“忙”于追求外在之物却“亡”了内在于己的心,结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