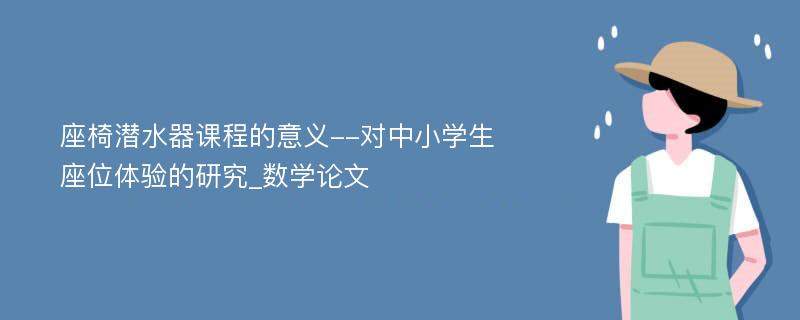
座位的潜课程意义——中小学生座位体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位论文,中小学生论文,意义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6 )06—0022—07
20世纪70年代,派纳(William F.Pinar)和格鲁梅特(Madeleine Grumet)等课程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非常有见解地提出“currere”的概念。这个概念把课程(curriculum)看作是“在跑道上跑”的过程,突出了课程的个人体验性质,从而赋予课程概念以新的理解。这突破了传统对课程的单一理解,即把课程仅仅看作是“一个代表一系列学程的名词”[1]59,为潜课程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潜课程(hidden curriculum)① 这个概念是杰克逊(Philip W.Jackson)在其《Life in Classrooms》(《教室中的生活》)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以区别于现有的“学程”[2]。他认为在学校中,学校生活、教室生活等都是学生成长体验的构成部分,其意义非常重大,所以他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如果他想获得满意的学校生活,就必须要理解学校生活中的潜课程”[3]。座位体验作为学生日常教室生活体验的一部分,不仅伴随着学生的学习、交往以及自我的形成,而且还牵涉到同教师及家长的关系,因此座位体验就构成了他们学校教育的潜课程之一。
为了加深理解座位对学生的意义,笔者访谈了北京、安徽、广东的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及家长。当问他们对学生在学校的座位有什么看法或体验时,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对此的反应表现得似乎都不像语文、数学等“学程”或者考试成绩那么重要,但他们对座位的意义却都有着一种非反思的、潜在的感受和体验。因为当他们进一步反思座位的相关体验时,座位的意义就如同冰山埋藏在水下的某些部分一样,在反思中得到关照。“只有当经验被反思时它才真正成为经验,只有经过反思这个第二阶段才能发现意义。”[1]49 本文正是通过他们,特别是学生的反思而获得座位对学生的成长意义的。
一、座位的空间体验——学生在教室的“家”
每个中小学生在教室里都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座位空间。这小小的地盘是他们学校生活中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虽然说这只是一个“流动的家”——不仅随着年级、学校而变动,即使在同一个教室也是经常变动不居的,但在一定时期,当学生获得了一个固定的座位后,它便成了其在学校的“家”。
“家”是属于自己的。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有些同学会在这里画上一道“三八线”,阻止同桌的“侵犯”。不过划定这个“三八线”也并不容易,往往是在不断的争论,甚至在“战争”的帮助下才可以确定下来。但这样的“三八线”维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会消除;还有些同学,为了加强主人的感觉,就用小刀在这里刻上自己的大名或者“座右铭”,像“××的座位”等。这种行为在上完鲁迅的《三味书屋》后尤为流行,从而构成了“课桌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虽然用刀刻的逐渐减少,但白色修正液和贴画的“装饰效果”似乎也不亚于刀刻。还有一些同学学会了充分“利用”课桌这种资源,把它当作草稿纸用或在考试时为自己做点儿小小的“提示”等。但是当“继任者”接替这样的座位时,往往是怨声载道,特别是那些爱整洁的女生。虽说这是一个流动的“家”,但没有谁会希望“接管”一个“满脸涂鸦”或者“千疮百孔”的“家”。有鉴于此,很多“继任者”希望“前任”要具备一点“座位精神”——爱护公物和对其他同学负责的态度,并提出“换位不换桌子”的应对策略。
“家”的感觉是亲切的。为了给“家”营造一份书香之气,他们会把自己的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课桌左右两边;有时还放一些小花或贴上一些精美的贴画装点自己的“居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总有一种归属或“居家主人”的感觉。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串串门”,到其他好友的座位那儿去坐一坐,聊一聊,但上课铃一响,各自马上又回到自己的“家”;当受到批评或者遇到伤心事时,自己的“家”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地方,“要哭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哭”。上学来时,或路过教室,总会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座位瞟上一眼;一个假期的分别,看到自己的座位会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倍感亲切。
不同的“家”体验也不一样。他们分别冠以“金窝”、“银窝”和“鸡窝”的称号,但却又不是绝对的。“家”在第一排的学生可以听见老师翻动书本的声音,清楚地观看老师如何演示或者做实验,得到老师的“真经”。他们这些特权是其他座位上同学所没有的。而且每次下课,可以“第一个冲出教室”,每次老师发本子或试卷都可以“第一个拿到”。但必须承认这里的不足,因为在这里看黑板和老师“需仰视才可见”,而且这里的同学多数长年笼罩在“沙尘暴”中,饱尝粉尘的侵袭;有时还有老师的口水像“小雨”般“滋润着”他们。也许不坐在前面的同学是无法体验这里的“地理环境”,实属“最糟糕”!另外,由于在“天子脚下”,他们需要格外小心,上课只要稍微“发挥一些想象的空间”就会被老师洞见。前排两边所谓的“南极”和“北极”的座位也会因为黑板反光而看不清老师的板书。
窗户边的学生虽也受到黑板反光的影响,但在这里却能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私事班事学校事,事事关心。”他们除了听课之外,还可以观察、感受教室内外。自习课的时候还可以为同学们站岗、通风报信,为同学们预防老师突然检查立下汗马功劳!当组和组之间进行轮换座位时,他们就享有回到“中心”的权利。有时坐在过道边的同学也会享受一下“把关”的乐趣——不让里面的同学进出。
“家”在教室最后的同学似乎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他们有一种“鸟瞰”的优势,可以“冷眼观世界”的悠然姿态察看课堂的一切举动,不过也有些同学向往“升迁”——往前调动的机会,但也并非容易。坐在后面也罢,不过最好不要是倒数第二、三排。因为这样既没有鸟瞰全体的视角,而且和后排那些更加高大的同学比较起来,自己永远处于“小弟弟”的角色。
前面中间三排的座位一般被公认为是“风水宝地”。坐在这里的同学,常年“沐浴在老师春天般的阳光中”,而且他们多被认为是“种子”,享有特别的关爱。在那些按照成绩排座位的班级里面,能够坐到这里却并不容易。因为能够坐到这里除了身高和视力原因外,其他多属于“班宝”级人物。同样在这里,有些同学是“姜太公钓鱼——稳坐钓鱼台”,而有些同学则“如履薄冰”——毕竟需要努力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位置和声誉。尽管中间的第一、第二、第三排座位被公认是学习的“最有利地形”,但同学们还是为它们排出了一个高下,即“第一排是铜,第二排是金,第三排是银”,不过也有人认为是“金三银四”。这主要视班级规模大小而定。
二、座位的同学关系体验——学生的生活场域
爱因斯坦把场定义为“相互依存的事实整体”。勒温(K.Lewin)把物理场域的概念应用到心理学中,从而建立心理场论。其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这些相互依存的事实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 4] 学生的座位就位于“场域”的中心,和周围的同学形成一种“场”的张力——人际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吸引也有排斥。同学之间的爱恨情仇袒露无遗。
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座位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无论是从学习还是从择友来说,学生对座位的感情都有一个“心理力场”因素在起作用。学生多有这样的感觉:“坐哪儿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同桌、好邻居”。如果老师让学生自己选择座位的话,就会发现同学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这也可以从学生喜欢临时换座位中看出,特别是在新老师或副科老师的课上——因为学生认为他们对固定座位并不熟悉,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们的行为不予干涉。虽说他们喜欢换座,但未必是利用上课时间说话,只是那“新奇的感觉”总让人神往。这样就有人陪伴在身边,上课就不会“孤独”。当然,也只有那些大胆的学生才敢于冒这个险——毕竟有时会面临勒令当场“退回原座”的尴尬。倘若得逞,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利用老师转身向着黑板的时候谈些逸闻趣事。
虽说同在一个班级,但多数同学的活动、交往“力场”往往都会形成一股较为稳定的态势。“坐久了,对座位就产生了感情,离开它,总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因为对同桌以及周围的同学产生了友谊和依恋,所以我不喜欢调换座位,不想因此而与朋友分开”。不过,如果这种“友谊”若影响到学习或班级纪律,老师就会采取一些隔离措施,严重的会把他们“东、西、南、北各派一个,造成隔离的态势”。或对有些同学采取包围政策,形成一道“防护墙”。不过,那些作为“墙”的同学也有自己的苦恼,原来那些同学虽然被隔离了,但是他们“千山万水也会传纸条,或是‘眉目传情’”,而且“不是长途不断,就是短信连连”。所以对他们而言,不但“自己的朋友被隔开,而且有时不得不担当起传递纸条的任务,听不好课。”
同学们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同桌或者邻居。这样不但有了知己朋友,而且还给学习带来帮助和快乐。座位成为结识朋友的途径。通过同桌,他们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管我坐在何处,只要有我的同桌做伴,我都不在乎。我注重的是同伴之间的感情而不是座位。”如果不幸倒霉遇到一个调皮鬼或者死对头,那不啻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坐在第三排,但我的同桌总说我长得丑,还经常妨碍我写作业。有一次,因她的原因,老师命我站起来。虽然满肚子怨气,但我没有说。更让我生气的是,就在我坐下的时候,她把我的板凳给抽掉了,结果可想而知。一气之下,就让老师把我调到后面,免受欺负了。”有时候同桌的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情绪,“他老是吐痰,有一次不小心把试卷掉到他的痰上,别提多难受了。”
有时老师喜欢从搞好男女生之间关系角度出发,让男女生同桌。但也有老师从班级管理角度出发安排男生同桌,“毕竟男女有别,在说话方面会收敛许多”,有利于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无论如何,男女同桌也容易“引起八卦”(“恋爱”的谣言)。“虽然爱说话的少了,但是流言蜚语却开始满天飞,搞得很多无辜的同学天天受到‘炮轰’”。
邻居之间,也会因为教室的“拥挤”而发生摩擦,“同学们经常喜欢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一点点地盘,他们会往前挪一挪,往后挤一挤,结果往往挤出了火花。”这时,老师往往会出面调停。“当我被调到后排,找老师论理的时候,才知道是同桌写信告了我的状。没办法,看着这一群‘陌生人’,想着自己以后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好想念以前座位周围的那些朋友,看他们在一起玩得多开心!不禁顾影自怜起来。”所以有时候,为了搞好同学的关系,需要学会忍。“上课的时候,我经常听到周围的同学说话,想和老师说,可我知道,说完后,同学们会在背后骂我、议论我的,所以我不知如何是好。”
无论如何,学生多数还是喜欢换座位,因为“换座位就是换一种心情”,“换座位给人以新奇”。虽说他们都已习惯了换座位,但是每次换完座位后,总是情态各异。只要站在讲台上往下一看就可以知道“人类的表情凡所应有,皆集于此。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学生只能安慰道“排座位就像人生一样,不可能次次如意,总会遇到不满意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学生多反对“一座定终身的做法”,因为那样要么“日久生情”,要么“相看两厌”。座位不变动的班级“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缺乏流动和交流。”特别是后面的同学,往往会形成固定的交往圈或者小集团,很容易和其他同学造成隔阂,而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和其他“场域”中的同学交往。
三、座位的师生关系体验——民主与关爱的体验
“民主(democracy)”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概念,它的古希腊词由demos 和kratos构成,demos相当于村一级的自治地区或者生活在城邦中的全体市民,kratos则是指“统治”、“权力”。在古希腊城邦中,民主就是指全体市民所行使的统治权。“民主意味着对某些态度的拥有和持续作用,这些态度在各种生活关系中形成个人的性格,并决定个人的愿望和目的。”[5] 杜威则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还是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6] 教育就是要养成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而学生在座位安排中就在直接体验着这种生活方式。
虽然同学关系在座位体验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无论如何,排座位的大权不在我们的手里”,班主任掌握着排座位的大权。多数老师持一种公正的立场:有的按照个子大小排座位、调座位;有些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学生根据抽到的号为顺序先后自由选择座位,老师再作一些微调;也有按照成绩排座位等。北京某中学的一些班级采取一种“对角递退的方式”,即每两周按照斜角往后退一次。比如由第一组的第一排退到第二组的第二排,这样依次往后退,就可以确保每个学生在三年段的初中或高中生活中能够在每个座位上都坐一次。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会造成学生周围的“邻居”变化不大,造成“一座定三年”的情况。同时,教师也失去了主动发挥座位的教育作用。
多数学生支持老师的这些排座方式,也能够认同老师照顾那些因视力或身高等特殊情况的同学,体现出应有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老师也充分利用这种时机教育学生。不过,也有老师和家长把这方面原因作为借口,为个别学生“谋利”。学生对老师和家长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幕后交易”深恶痛绝,“老师平时指责我们学生撒谎、不诚实,可是他们自己却言行不一。带着伪装的面具,显得似乎是很公平、公正的样子。其实,那只是表面工作而已。”
当然,也有在民主方面做得比较“高明”的老师。有位班主任老师,在学生建议自由选择座位的呼声中,为了“顺应民心”,答应自由选择座位,但前提是各任课教师毫无怨言,若有教师抱怨纪律不好,就要按照老师的意愿排座。结果是:两个星期后果然各个老师都反映上课有人说话,于是班主任就借此重新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座位,而且通知家长。大家都无话可说,从此座位全由老师安排。虽然如此,但另一位老师的话却道出了学生的心声“狼吃羊总是会有道理的”。
虽然很多老师对排座的态度不很直接、明确,但一位教师的话代表了一些老师的基本信念:“我把有望能够升学的学生都放到前面几排,他们就像我的儿女,每天都处在各科老师目光所及之处,伸手可以环抱的地方。只要把这些学生抓好了,也就不用担心学校升学的压力了。”学生却不希望老师怀有这样的偏见和独断,他们都希望老师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安排座位。
杜威说过“当前学校的可悲之处在于,它力图培养这种社会制度的未来成员,然而所采用的方式却明显缺乏这种社会精神所需具备的条件。”[7]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爱和希望一样,学生都可以感受到。一位“差生”的话较好地代表了多数学生的看法,“其实坐哪里都没有多大的区别,最重要的是老师要关心我。这样即使在最后一排,我也绝无怨言。”在学校生活中,学生对老师寄以很大希望和依赖,有时他们似乎是在“为老师”而学习,他们都希望得到老师的重视和认可。就像有位同学所说的,他找老师说座位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真正希望解决座位的问题,而是渴望得到老师的重视。而老师的一句“以后再说”则会让他困惑,“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的成绩不是很优秀?不会的,我不希望老师这么想我,这会让我更加伤心的。”“真没有意思,老师根本都不管我了,我还学什么呀!”
从这些体验可以知道,对座位的民主体验与老师的关爱和对学生的尊重不可分离。“虽然我对坐在哪里并不在意,但还是不喜欢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好被老师调到后排。我不想坐在这里,我想这是老师故意冷落我,突然感觉自己很孤单。”所以有学生提出,老师应全面衡量座位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老师调座位的时候应该问一问学生是否满意,若不满意的话,连课都不想上,这样的调换座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例如,“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要求和我同桌。老师便答应了她。我很气愤,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也没有问我同不同意!我不喜欢和她同桌。”
座位安排在老师的眼中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它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却不小。座位及座位上的学生在教师的眼中本应像母鸡羽翼下的卵一样,都应该在母亲的怀抱范围之内,都应该得到母亲的温暖,这样才可以孵化出健康的雏鸡,过热或得不到适度的温暖,都会造成残缺不全。
一位学生的比喻也许可以表达座位对他们的意义:“如果把所有的学生都比喻成为‘宝石’,那么座位有时候会像泥巴一样淹没它的光辉,甚至是永远。”这可以从一个学生的体验中看出“一次数学考试我考得很差,被数学老师调到了最后一排。这一排只有一张桌子,就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我才感受到教室的空旷、寂寞、寒冷。以前的伙伴不再有什么交往,因为他们很快就有了新的同桌和朋友,而我却没有。我恨数学老师,她的课我无法听下去……”
四、座位的认同体验——身份与自识体验
身份(identity)和同一、认同是同义词,既指自我认同也指社会认同。它是由人在集体交往中和反思中逐渐形成的认识。
很小的学生对于座位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座位意识”——座位所代表的学习意义和体现出来的身份的意识。而且面对越小的孩子多数老师往往表现得越公平。随着年级的增长,不仅学生的“座位意识”越来越强,而且也逐渐发现老师的“座位意图”——有意识地以某种标准和关系安排座位——逐渐明显。也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座位意识”的加强,所以才逐渐有了对座位所体现的身份意义和其中的自我意识。
学生在班级中最突出的身份表现为学习成绩。班上的“名人”几乎都是那些学习成绩非常突出或有一技之长的人。当然也不乏老师眼中的“异类分子”,不过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身份地位却因人而异,不像学习成绩那么稳定。“名人”在各个方面似乎都受到优待,排座位时也不例外。学生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谁的成绩好,坐在“好座位”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老师“除了按照个子、视力排座外,还要考虑成绩”。
在明确地或潜在地以成绩排座位的那些班级中,能够坐到前面或中间是一种光荣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座位是个人学习成绩和能力的证明”,“所以座位能够让一个人骄傲,也会使得一个人自卑。座位能够让人奋进,也能够使人丧失学习的动力,甚至自暴自弃。”当学生因成绩原因从前面被调往后面时,他们往往对自我的认识会形成很大的落差。“因为期中考试成绩的原因,我从第三排调到了倒数第二排。巨大的反差让我感受到以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每次月考之后,我都会心惊胆战,害怕老师将我调到后面……在后面就是告诉别人‘我是差生’”。
“从小学到初中,从未为‘座位’担心过,也许那时根本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危机感。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就变了,班级座位是按照成绩排的。高一时还坐在前排,而高二下学期的成绩着实折磨了我一整个暑假。因为这次考得差,整个暑假我都怕见到同班同学,怕在街上遇到老师。突然觉得很丢人。一想到高三开学就要坐到后面,心里就害怕。有时正和朋友聊得开心,思绪会不自觉地被牵到‘换座位’这件事情上来。我倒不是担心坐到后面,而是因为大家已经在‘坐到后面’和‘成绩差’之间画上了等号……”
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很大意义上是老师赋予的。老师是他们的“主宰”、“保护神”。座位的身份标志体现为老师对学生的重视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关系意义,这种关系往往和学生的学习成绩联系在一起。学生都希望在老师心目中最特别、最受重视。如果老师能够按照学生自己的意愿安排座位,或者总是把他们安排在“理想的座位”上,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也标志着自己在班级学生中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们多数还是有自知之明,所以在提出要求时,他们还得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老师还是挺看重我的。不过我的同桌却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家伙。我想让老师把他调走,可是话没有出口就又迟疑了。他的成绩比我好,老师会把他调走还是把我调走呢?还是不要说了,就这样忍下去吧!”
班级中最前面或最后面,或者靠墙的座位有时会具有特殊的身份意义。对于班级那些“异类分子”,老师不是把他们安排在眼皮底下,就是在遥远的“边疆地区”,或者在“隔离地带”。老师甚至为他们设置“专座”:在班级前排的两边分别设置两个“雅座”,专为那些上课爱说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准备。“我在开学的时候就坐在最后一排,今天,又因为上课说话被老师发现,所以又被‘降了一级’,被放在最前面——第一排前面加了一张桌子,是‘手可触黑板(摘星辰)’,只我一个人坐,再也无人可以说话了。”
有时老师也会采取另外的策略,把他们放到不说话的同学旁边,或者包夹在异性周围,从而起到“隔离”的作用。“当站起来环顾四周才发现,周围全是女生。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老师是嫌我上课说话,让她们把我和那些朋友隔开!”“当老师宣布我的新同桌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上课说话过多。因为她是我们班出了名的‘老闷’。”
虽说座位让学生体验出自我的身份和发现,但如果哪位学生想利用社会或者家庭关系享受排座上的“优待”,特别是到了高年级,随着学生“座位意识”的增强,这种身份似乎并不光彩。“她爸爸是我们的校长”,“他妈妈是我们市医院的院长”……在这样的舆论中,即使享受了优待而获得一个好座位,也并不显出荣耀的身份,充其量只是获得了一个好的“学习位置”而已。
五、座位的环境体验——座位的学习意义
很明显,座位体验不限于座位本身,而是处于一个系统中。其中学生和同桌及邻里之间组成一个较为核心的“微系统”,和老师组成一个“中系统”,而和家长及社会又组成一个较远的“宏系统”。这个系统总体形成了学生座位的“氛围”,不同的“氛围”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勒温认为,个人的心理场与周围的环境及情境是不可分离的。他不满心理学中人与环境的孤立的状况,所以他用“心理生活空间”[8] 一词,来指一个人在某一时间内的行为所决定的全部的事实,从而把人与环境和情境理解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
座位几乎就是为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而设定的,所以座位的学习意义在学生和家长的座位意识中居于首要地位。学生也把好座位与学习联系在一起。“昔孟母,择邻处”,说的就是周围环境对成长的重要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同伴对人的影响作用。人是一种非特定化的存在,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做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留下了未确定性[9]。 人的非特定化使得人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向世界开放,学生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非特定化的存在,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而选择座位其实就是选择一种环境。
老师安排座位也会考虑同学之间的“优势互补”或者优秀同学对差一些同学的“一帮一”作用。同伴学习是同桌最大的教育意义所在,这也是老师安排座位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学生就很明显感受到同桌带来的益处,“我的字本来写的很丑,同桌的一手好字真是让我羡慕。和他一起我不但写字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把好讲话的毛病也改掉了。”所以“好座位意味着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能够带动我们学习的兴趣,提高成绩。”而且同伴之间还会形成“比、赶、超”的学习赛势。“每次考完试,我都抢过同桌的卷子来比一比成绩,可几乎每次都是我垂头丧气地把卷子还回去。因为他每次都比我高。但我并不灰心……有一次,成绩下来,我一看,哈哈,我比他高出2分。”所以,多数学生都很珍惜这样的好座位, 也会为此而努力。“我座位可以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可是让我心烦的是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得不好就意味着要失去这块宝地。……为了这块宝地,我要冲刺。”
倘若遇到不理想的同桌也还是非常恼人的。“我的同桌是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女生。每天上课都会唱歌,总以为自己的歌声多么优美,其实在旁人听来,简直跟噪音有得拼。如果哪天她不唱歌了,那一定是找到什么话题了,跟你凑得很近地说个不停,像个机器人似的,会唠叨一节课。有一次老师在背投上投映了一篇作文,让我们默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可她非要读出声音,我周围的人提醒她,可她却越读越响。”看来座位环境不但影响学习,而且还影响心情。不过,对于这些,不少同学还是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如果换到自己不满意的人,也就多了一次锻炼自己交往能力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个朋友,或者多了一块“陶冶情操的砺石”。
对于那些换到新环境的学生,座位也会给他们带来“不确定”的压力。“同桌会不会嫌我把她以前的伙伴给撵走了?我会不会不如她以前的伙伴?这里的环境这么陌生,万一我作业不会做我该问谁呢?”有些学生感到“坐在前面,上课就会过度紧张,但如果坐在后面,我又无法集中精力听讲。所以我只能坐中间。”有一些学生因为喜欢玩或者喜欢自主学习,所以他们往往对座位没有要求或者宁愿调到后面座位上,从而主动地减轻自己的压力。不过坐在这里或长期坐在这些地方对听课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两年半以来,我不是在倒数第三排就是最后一、二排,感觉非常难受,恨不得不上学了。感觉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觉得老师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我。有时老师声音很小,听不清楚,所以就想和其他同学说话。”
学生还观察到,坐在前面的同学被提问的机会更多,特别是新教师的课,当他还不熟悉班级的时候,就在前面任意指点一些学生回答问题,所以后面的同学逐渐就被冷落。时间一长,后面学生对回答问题就不再抱有希望。“据我精密洞察,老师提问检查一般都是到第五排就打道回府。所以越往后面就越不用担心。”有些学生因此就会有挫折感,“老师从来不叫我们回答问题,他只叫前排的同学回答问题,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当然,老师偶尔也会叫到我们,但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结果更加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心。”而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吸引人的注意。”而且,在后面的学生还发现老师也对他们抱有偏见,“数学老师每次讲到有挑战性的题目时,总是把眼光投向前面几排的同学,‘谁能够做出来?’而讲解很一般的题目时,却把眼光抛向后面,‘听懂了没有?’”
结尾
学生的座位体验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本文无意于“还原”学生的座位体验,因为“我们回归不到直接经验。”[10]。本文只是从空间、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自我认识及学习环境等五个方面主题把握学生对座位体验的一般结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小小的座位”蕴含着教育学中许多的矛盾:学习与生活,自由与限制,学生个体与班级集体,理想要求与现实状况……这里没有任何抽象的“理论”或某种规定能够解决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学校教育也不可能消除这些冲突和矛盾。这里的关键是教育者要有“座位的课程意识”——理解座位对学生成长的意义。座位作为一种体验课程,它也是一种文化产物,学生对它的体验与所在班级、学校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它是一种涵盖着学生经历和周围环境的整体体验,它已经成为了学校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知道,不同的学生对座位有着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座位安排或组合方式也具有不同的效应。有人倡导按照成绩来排座,“这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实这只是“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不公平”而已,实质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他们在没有排座之前就已经把成绩作为第一标准了;也有人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例如制定规则,学生自选等安排座位。这其实也只能说是一种“最不坏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失去了教师从教育学角度安排座位的灵活性。康德把教育称为是一种艺术,杜威也持相同的观点。这提醒我们,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教育的问题也不是一种固定程序、规则就可以解决的。这里的关键是教师首先要理解学生,理解座位对学生的可能影响。这是一种教育学理解(pedagogical understanding)。“教育学理解是一种实践性理解, 它总是从形成性上关注孩子的可能性。教育学不是抽象的,教育学的兴趣是要从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生活体验的意义”。[11]
感谢为我提供资料的所有老师和学生;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的指导
收稿日期:2006—10—19
注释:
① 自潜课程一词提出以来,已逐渐得到学界的公认,但是对潜课程的称谓和理解却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潜课程包括了所有的正式课程以外的所有影响学生成长的方面。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范兰丝(Vallance)在《国际课程百科全书》(1991)中把潜课程描述为“那些在课程指导和学校政策中并不明确的学校教育实践和结果……它是学校经验中经常而有效的一部分。”——转引自:靳玉乐:《潜在课程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标签:数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