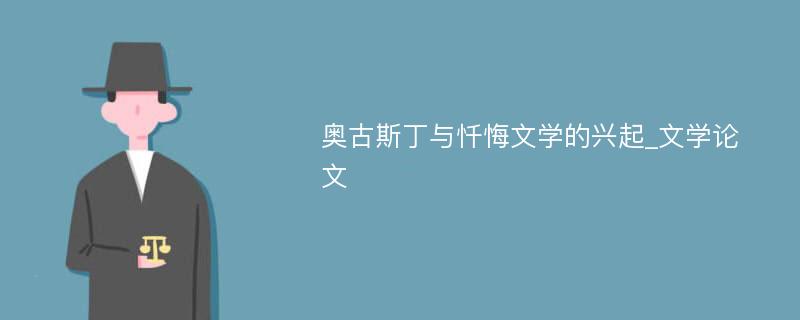
奥古斯丁与忏悔体文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源于宗教活动的忏悔体文学
文学起源的一种重要途径便是通过人类的宗教活动来探索自然和人生的奥秘,吟唱神秘而又美妙的诗篇。在宗教意识的支配下,人类为诸神吟唱和颂赞,讲述诸神的奇迹性故事,构造圣徒的传奇,这一切又在宗教纪念性与仪式性活动中有效地通过心灵记忆和文字保存下来,这些最初的颂神诗和人类信仰神灵奇迹的叙事便是原初的宗教文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即人对神的感恩与赎罪意识,所以,可称为忏悔体文学,它通常被结集编入宗教圣典文本之中。当这些忏悔体文学既构建着纯粹的信仰又满足着人们神秘的好奇心时,因为它既是感性形象的又是理性抒情的,一些富有诗人气质的圣徒在宗教激情的支配之下以此为基础再创新的颂神诗篇,表达内心的虔敬与感激,从而形成新的宗教文学特别是忏悔体文学。忏悔体文学说到底就是企求通过坚贞的信仰来获得神的恩宠从而使灵魂获得极度欢悦的一种抒情方式,它是感恩与自责的统一体,即赞颂神圣生活的超越性而贬斥世俗生活的现实性,力图使人类生活进入一种虚幻的心灵完善境界。这种纯粹的忏悔体文学由于受制于宗教观念,因而,它还不能广泛地探索人性生命的真实。也许是有感于纯粹颂神诗的局限,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一些激进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诗人和艺术家试图用一种非宗教的体验形式来探索宗教性人生问题,从而使宗教领域的忏悔体文学发生了一种演化,构成了一种非宗教意图但又具有深层宗教意识的文学形式。事实上,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抒情主体或叙事主体对原罪和生命沉沦或生命过失的一种反思性忏悔,并力图拯救或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这种独有的精神取向具有宗教原典式忏悔体文学的一般特征,所以,这种文学形式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广义的忏悔体文学。无论是广义的忏悔体文学,还是狭义的忏悔体文学,实质上都与宗教观念有关,涉及到宗教的深刻的人生问题。可以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这种思想信念的典范式表达。
在西方文学乃至文化史上,奥古斯丁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一地位在基督教世界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而在文学界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忏悔体文学的认识不足有关。可以说,奥古斯丁的忏悔体文学不仅是对圣经文学的出色继承,而且也决定了忏悔体文学的新的发展方向。正如皮特布朗所言:忏悔这个词并不限于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意思,即它只是对罪的忏悔,“忏悔这个词来自《圣经·诗篇》,对奥古斯丁来说,这是每一个人与上帝交谈的唯一方式,正如大卫王向他的祈祷者显示的那样。”①他那种独有的诗人气质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使他的《忏悔录》创作具有重大的诗学意义和宗教意义,在忏悔体文学兴起与演变的历史上,奥古斯丁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奥古斯丁的忏悔体文学显示了宗教与文学的独特联系。远古人类历史文化证明,宗教与文学具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性品格,在法术思维或神话思维时代,文学即宗教,宗教亦文学,且不说宗教诗篇是最早被保存下来的诗歌,单就宗教与文学的精神活动方式而言,它们就是以神秘自由的想象与真诚信仰的抒情方式来表现生命的自我理解。原初的文学浸透着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宗教则无法离开文学这种形象化与语言化的传播方式,可以说,任何神秘庄严的仪式所展示出的宗教教谕力量都无法与宗教歌诗和神话的力量相比。因此,宗教很自然地继承或有效地利用了文学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也决定了原初的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说宗教与文学的关联在原初的宗教活动或宗教仪式中还具有特殊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在神学日益壮大之后,宗教的内在本质则与文学渐行渐远,尤其是在基督教教父哲学兴起之后,一些神学家觉得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分析与逻辑证明比圣典的抒情诗篇和历史神话叙事更有价值,或者说,他们对圣典的读解更注重其神学理性的价值,而相对忽略其文学抒情的价值。这种理性神学的兴趣,使原初的忏悔体文学的宗教力量被削弱,其文学价值则仅仅被用于宗教教义的传播之中。奥古斯丁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善于对圣经神话进行神学的解读和证明,而且也很重视个体的独特宗教体验通过诗体形式来进行叙事和抒情传达。事实上,他在基督教传播史上构成巨大影响的不是《上帝之城》,而是《忏悔录》,因为《忏悔录》更适合诵读和体悟,而《上帝之城》则适合作神学的历史反思。《忏悔录》作为公元4世纪末的一部忏悔体文学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一方面使人在宗教领域能够承继古希腊罗马的抒情传统,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极具个性并极具抒情魅力的个人性话语来领悟和体验宗教信仰的神秘和诗性的智慧。
其次,奥古斯丁的忏悔体文学是对圣经文学的一种伟大继承。《圣经》作为一部圣典,其宗教意义无可替代,其文学意义亦不可低估。事实上,西方文学史在叙述公元1世纪后西方文学和欧美各国文学时,都将《圣经》置于一个特殊地位。这不仅因为《圣经》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和文体形式,而且也因为《圣经》的伟大而丰富的思想内容,同时还在于,《圣经》的各种语言的译本直接纯净了其民族语言,使英、法、德、俄、意等国的文学语言具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所以有人直接把《圣经》作为新世纪的文学的一个伟大开端,因而继承圣经文学的传统在西方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而公元4世纪左右,还没有一位文学家和宗教家像奥古斯丁这样热衷于通过个人体验式的抒情话语来表达自己对《圣经》神话和思想的文学理解和诗意想象。《圣经》的文体多样性可以通过神话故事、英雄传奇、历史书、诗篇、先知书、书信、传记和启示录来证明,而且还可以通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形式来证明。对于大多数信徒来说,福音书、书信、圣咏、雅歌、约伯记等的宗教与文学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可以说,《旧约》和《新约》内的每一部作品和每一句重要的话语都与西方近现代文学的精神有一种深刻的渊源关系。奥古斯丁显然最初强化了这一点,并开启了宗教抒情的个人化形式。这种宗教抒情本身不仅激活了文学的想象力,也影响到了宗教的诗性探索。“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忆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②这就是奥古斯丁对待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的一个基本态度。
第三,奥古斯丁的忏悔体文学维持了一种正统的基督教神话观念和神学观念。在《圣经》叙事中,由于叙述者时时刻刻在构拟神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向上帝感恩和向上帝作赎罪的忏悔,因此,忏悔意识是无处不在的,但忏悔意识毕竟不是其核心内容。《圣经》的核心内容在于确立上帝的三位一体形象,在于确立其对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神灵信仰。上帝的三位一体形象不是通过抽象叙述来构造的,我们甚至在《圣经》中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词,但上帝与耶稣的形象鲜明生动,在《旧约》中,神学诗人致力于刻画上帝的形象,上帝用话语创造了世界,又用泥土造了人。在上帝的创世工程中,上帝对人情有独钟,并与人类的远祖订立了契约。上帝许诺亚伯拉罕的子孙繁盛,亚伯拉罕则保证只信惟一神,并行割礼作为与上帝立约的标记。可是,在宗教神话的历史演变中,人们相信,政治争斗的递变和人的堕落使上帝加重了对人的处罚乃至绝望,人类的基本缺陷在于欲望的泛滥,各种各样泛滥的欲望或者背离了上帝之道的一切行为皆被视为罪(sins)。基督教中人的罪感意识具有一种特殊的强化作用,与现代法律意见上的“罪”不同,它似乎相当于汉语中的“过”、“过失”之义。人类的原罪不仅在于性欲,也在于贪欲、权欲和各种各样的非道德欲望。
正是这种罪过、罪感,决定了人的不完满性。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人死后必得进入天国才能永生,其重要保证之一在于灵魂的无垢,而且必须接受真正的审判,公正的审判决定人进入天堂或地狱。因而,基督教中的罪感具有多重意蕴:相对上帝而言,人之罪表现为不虔诚,不纯信;相对于宗教伦理而言,人之罪有悖于灵魂的纯洁;相对于神学目的论而言,罪感人生需要拯救,通过他者拯救与自我拯救,信仰则是拯救的最高准则。这种罪感意识就决定了忏悔的必要性,因为“原罪”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负面回应,面对恩典,人不仅没有感恩,而且背离或遗弃了恩典;没有恩典意识,上帝与人的契约也就不具任何效力。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一旦背离上帝,就不会受到上帝的恩宠,一旦人处于被遗弃和被惩罚之中,灵魂就永远不能安宁,生活就永远没有幸福。所有的圣徒都力图让人明白这一点,先知们以杜鹃啼血的方式在呼号、在冥思、在遐想,在宗教诗篇中表达感恩。这样,先知式的忏悔体文学自身也就成了一种情感呼号与渴望信仰的一种心灵方式。
不仅如此,奥古斯丁还将《新约》神话与神学的内容贯穿到《忏悔录》之中。耶稣神话承继《旧约》中的救世主神话而来,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并强有力地继承且合理地改造了旧约神话的精神,使耶稣作为圣子之身份出现。上帝化身为人子,经历人世的苦难,通过担当苦难自身展示给人们一种启示,并以其亲自关爱的方式将爱的神话推至高峰。三位一体神话的构拟与十字架神话的象征意义,使人类自身更加深刻认识到了“罪恶”与“苦难”之间的关联,表现在忏悔中,则是人对上帝的恩慈的感激,抒情式忏悔显得更具有诗的意境和激情。
由此可见,纯粹的忏悔体文学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由于宗教活动与文学活动都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方式,尽管宗教还要形之于具体的仪式并实施相应的宗教行动,但其精神特性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说到底,宗教与文学都需要激情,需要以一种超越性方式对人生形成一种关爱。文学和宗教正是在自由的精神创造中让人的内心获得一种充实。只不过,文学更偏重感性的生命活动,偏重人的生命存在,它重视人的情感与欲望,重视人的意志与理想,它以人为本,通过人的生命活动来探究人生的意义,因而,文学永远向人生开放。但宗教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纯洁信仰,试图通过信仰来构造独特的生命世界,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人的生命情感和正常的生命欲望,试图通过对灵性生活的夸张想象来控制人的生命欲望和世俗情感。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信仰生活的美丽是通过否定情欲和个人意志来实现的,而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的美丽则是通过展示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和诗性精神生活来实现的。纯粹的忏悔体文学显然以宗教精神为内心的灵魂,以宗教与文学共有的生命激情作为叙事与抒情的动力,以文学的文体方式作为表现形式,达成神圣抒情与生命沉思的宗教艺术目的。这种忏悔体文学消解了宗教的神圣庄严性和刻板淡漠的特性,使之具有一种亲切的信仰体验。与此同时,这种忏悔体文学又因其精神的单一性和对生命情感需要的漠视乃至否定而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局限。因而,狭义的忏悔体文学可以这样来定位:它服务于宗教活动本身,使宗教信仰自身充满诗意与激情,能够展示独特的宗教心理与自由想象的天地,它使生命显得神圣、高贵;与此同时,它又服务于宗教,否定人的正常生命情感,使诗意抒情自身显示出单调的宗教神圣性。
二、《忏悔录》的话语意识与抒情方式
《忏悔录》的诞生,无疑是宗教史、文学史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忏悔虽然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在日常宗教活动中自然地进行,但真正撰写一部《忏悔录》并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典范绝非庸常之辈可为。在湮没无闻和浩如烟海的基督教文献中,释经的作品和讲述信仰奇迹的神话屡见不鲜,但真正将个人的生命信仰旅程作一种体验性与反思性的诗意表述,必须具备许多前提条件:如浪子回头式地投身基督信仰之中,这在基督教宣教上具有特别的号召力;创作者的精神领悟力与创造力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地位,确能对信仰的本真意义和生命的内在秘密形成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奥古斯丁显然具备了这些因素。
他的《忏悔录》首先是一部生命回忆之书,而且它是以基督教精神作为个人生命价值判断的惟一依据。可以说,奥古斯丁的生命旅程是一个正常儿童的自由生命历程。青少年时期酷爱拉丁文,喜欢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等传奇故事,热衷于写诗和戏剧演出并获奖励,与朋友们四处游荡,寻欢作乐,不喜欢荷马史诗,也不喜欢希腊文。也就是说,他对罗马传统充满了热爱,实际上又通过拉丁文间接地接纳了希腊文化和思想传统。这种自由的心性支配着奥古斯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决定了他不崇信他母亲所信奉的基督教,而宁愿在摩尼教等宗教中沉浮。《忏悔录》的前九卷以圣典语式和基督精神为依托,赞美上帝,同时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进行反思与忏悔并叙述自己精神转变的历程。32岁是奥古斯丁信仰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从此,他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纯粹而又高尚的圣徒。这种生命叙述与沉思和基调决定了《忏悔录》的诗学语式的独特性:主体性第一人称叙述与独白式倾诉共同构成一种和声。
主体性第一人称叙述在诗学上是一个具有优势同时又具有局限性的一种文学语式。作为抒情语式,“我”的独白与倾诉是合法的而且具有文学表达的特权。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选择的是“我”的独白语式,这不仅可以保证抒情与叙事的真实性,而且足以使倾诉性的情感内容在表达上不受到拘束。《忏悔录》作于奥古斯丁的信仰转变之后,因而,贯穿作品的是基督教精神以及抒情主体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从宗教方面看,奥古斯丁捍卫了宗教的神圣性与信仰的诚挚性,而从文学方面看,奥古斯丁显然漠视了人的生命情感的正常地位,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了宗教性贬损,这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强化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显然,奥古斯丁通过“我”不仅要树立一个忏悔者形象,同时也试图确立一个坚定的信徒形象,这一方面使“忏悔”的含义泛化,另一方面也使生命被贬合法化。
宗教意义上的“忏悔”是忏悔主体面对神灵的一种倾诉,是自我内心按照基督精神对个人的罪与恶的一种反思与忏悔,是对上帝的一种自觉认同而且对自我的历史形成的一种否定,以信仰为第一要求来否定个体的全部的生命情感活动。所以,忏悔总带有一种强制性和审判性的特质。实质上,从《忏悔录》来看作为主体性的第一人叙述者,并未特别强调真正的罪恶,而是强化了心灵信仰的主体性与纯粹性。一般说来,抒情者强化了主体性内心活动的倾诉式表述所具有的忏悔意义。这样,忏悔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强制性的心灵审判,而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心灵独白与信仰归依。按照法律意义的界定,罪恶主要是对他人和国家的生命财产的一种侵占与不公正掠夺,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施暴与不公正,是一个人对社会公正秩序的背叛,杀人、抢劫、密谋、颠覆、侵占、受贿等是人的社会罪恶。宗教意义上的忏悔虽肯定无疑地否定这些特大罪恶,但它同时又将罪恶观念无限扩张,如奥古斯丁对儿时的偷梨行为反复忏悔,就是将罪恶夸大的一种标志,而将荷马史诗与个人的创作演出也视作一种罪恶,显然是对合法性生命活动的宗教原罪式夸张。因而,忏悔实际不能从法律意义上的罪恶观念上去理解,只能从宗教的心理净化意义上去理解。
这样,忏悔本身就是忏悔主体拼命压抑个人的自然生命情感的活动,是一种否定现实活动而归依于纯粹心灵信仰的活动,是一种极度地夸张信仰的无限真实性和无限神圣性的一种活动。因而,主体性第一人称叙事和独白式倾诉实质上只服务宗教信仰的纯粹性本身,于是,对个人生命活动的极度否定和对上帝的极度赞美以及归依于主的夸张式牺牲就成了奥古斯丁的单一性话语意识。
其次,《忏悔录》标志着心灵的想象与精神世界的充分主体性及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这就是说,奥古斯丁不自觉地维护并开创了心灵化诗学或信仰化诗学的合法地位。如果将西方诗学的两大传统作一比较就可看到,圣经诗学与古希腊诗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主题的惟一性、信仰的中心性和文学的宗教性,即在文学创作的主题上必须以基督教的内容为中心,以圣典为中心,将圣典视作文学创作的母本;在文学想象中,只有上帝的形象,人对上帝的诗情只能是崇拜之情、感恩之情和精神新生的欢悦之情,宗教文学创作的目的必须以基督教的宗教信念作为惟一的价值依据,即文学必须服务于宗教,使宗教精神更能在文体的多样性和文学的抒情性与形象性中深入人心,圣经诗学在文体上的开创性贡献直接影响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的叙述与抒情风格。后者则强调主题的丰富性、生命的神圣性、想象的自由性和文学的审美性,虽然希腊宗教在其文学发展过程中也显示了其历史性影响,但希腊宗教自身的多神信仰和自然主义崇拜的精神决定了希腊宗教对人性的充分尊重,对生命的充分肯定。希腊诗学开创的是对自然、自由和生命、想象的充分重视,它归依于人的生命自由,而不是神圣信仰。
圣经诗学与古希腊神学有着根本上区别,由于奥古斯丁对希腊诗学的否定,他自然归依于基督教诗学,这就使得他在信仰上以基督教精神作为基本依托,在抒情上以赞美生命作为惟一目的,在文体上则取法乎圣典本身。从《忏悔录》的引文来看,奥古斯丁直接引证《诗篇》中的句子161次,引证《创世记》60次,引证《罗马书》等章节20次左右。这说明,《忏悔录》的话语意识和大体意识与圣经诗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圣经》中,《诗篇》共有150章,大多由大卫和所罗门而作。必须承认,《诗篇》的主体性抒情是强烈的,但也应该看到,《诗篇》在主题上相对单一,即赞美上帝;在内容上,比较空洞,因为所有的隐喻和明喻都是为了赞美上帝,表达一种主体性感恩;在宗旨上,则明显具有一种宗教教谕性倾向。奥古斯丁也多少承继了这种文学风格。实事求是地说,从文学的情感与思想表达意义上而言,《忏悔录》的内容显得单一而不丰富。由于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主导目的是为了赞美上帝,表达内心的自然归依的喜悦之情,因而,即使是有关个人生活的回忆性叙述,内容也显得相当空洞。实质上,奥古斯丁在创作上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挣扎,因为按照回忆性的叙事话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应以叙事本身为主导,这样,奥古斯丁本人的生活经历便会显得丰富生动,如他的顽皮,他的颂诗才能,他的演出,他的放浪,他的欧洲和非洲之旅等等,完全可以展示出一个青年的自由活泼的心灵。但这种叙事内容自身同时也给宗教信仰者提出了一种挑战,即叙述得越详细,就越会与宗教精神形成根本性背离,因为这些正常自然的生命活动本身没有罪恶,不需忏悔,按照希腊罗马人的生命观念还值得充分肯定。在奥古斯丁的内心中,他一方面要表达浪子回头归依基督的庆幸,因为他把归依上帝视作节日般的自由生活方式,内心充满感恩般的幸福,另一方面又要表达自我青年时代的迷昏。前者作为一种内心生活,不适宜作叙述,只能进行单调的抒情独白,后者作为一种历史经历,不适宜作抒情,只适合进行生动的叙述。这种不和谐性最终在奥古斯丁宗教理念的支撑下决定了他的《忏悔录》,以抒情压倒叙事,这样,事件本身成了一个抽象的骨架,失去了文学自身的生动活泼性,而抒情又因其思想与语式的单一变得缺乏感染力,想象也变得单调且具抑制性。他说得很明白,“我愿回忆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③
这种挣扎的必然性结果是《忏悔录》在宗教教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文学上则显得地位不高,这在某种程度也决定了西方文学的历史评价原则,即按照希腊诗学原则创作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易于表证丰富的人类生活本身,既能正视现实,又能有表达个体的生命理想;而按照圣经诗学原则创作的文学则是宗教的文学,它服务于宗教本身,在文学想象和情感表达上显示出一种宗教认知的狭隘与单调。所以按照希腊诗学原则创作的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学成了自由的文学,而中世纪文学则由于受到了特殊的宗教观念制约,其思想情感表达和文学想象显示出不可避免地单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诗学的强制作用只可能限制文学的自由发展,当然,这并非指要绝对排斥圣经诗学,实际上,圣经诗学的内涵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圣经》的宗教道德论主题和人性主题的关怀能够深化文学探索自身。
第三,《忏悔录》的积极意义在于确立了神圣体验在圣经诗学乃至西方诗学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体验性并强调神圣体验的精神独特性成了《忏悔录》的一个中心性内容,独白式倾诉性内容就是奥古斯丁对个人生活进行神圣体验和反思的内容,体验性可以无限扩张主体的自由心灵,并使之达成一种深刻的感情与认知。“主啊,请使我得知并理解是否先向你呼吁而后认识,或是先认识然后向你呼吁。但谁能不认识你而向你呼吁?因为不认识你而呼吁,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④这样,关于上帝形象的体验与构拟便成了一种抒情性忏悔的精神出发点。“主,请你俯听我的祈祷,不要听凭我的灵魂受不住你的约束而堕落,也不要听凭我倦于歌颂你救我于迷途的慈力,请你使我感受到你的甘饴胜过我沉醉于种种欢乐时所感受的况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住你的手,使我有生命能从一切诱惑中获得挽救。”⑤“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具有纯洁光辉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灿烂的正义与纯洁,在你左右才是无比的安宁与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当三类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就找不到。过去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的现在便是期望。“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我是看到了三类时间,我也承认时间分三类。”⑥
这样,奥古斯丁的体验观具有独特性内容,即心中只有上帝,上帝的形象可以无限想象,上帝的大能和恩慈和灵魂拯救可以无限夸张。时间只有现在,记忆、感知、期望无不是为了主的恩慈。由于他的宗教信仰至上观,因而,对艺术和审美本身有着本能的信仰排斥,他甚至将音乐歌声战胜信仰理智也视作一种罪。“回忆我恢复信仰的初期,怎样听到圣堂中歌声而感动得流泪,又觉得现在听了清彻和谐的歌曲,激动我的不是曲调,而是歌词,便重新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巨大作用。”“我在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体验之间真是不知如何取舍,我虽不作定论,但更倾向于赞成教会的歌唱习惯,使人听了悦耳的音乐,但使软弱的心灵发出虔诚的情感。”⑦看来,审美与信仰的矛盾,在奥古斯丁那里也始终是一种矛盾,尽管他以体验为支撑,不但充实体验的理性内容与情感内容,但他同时又在极力排斥情感内容。这样,忏悔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显示了诗学的真正缺陷。
三、忏悔体文学逸出宗教语域
奥古斯丁的忏悔体文学创作在西方文学史上对宗教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以其真诚的理想影响到了不信教的文学创作者。事实上,这正是对圣经诗学传统的双重继承,即一方面为了宗教可以牺牲文学,为了信仰可能牺牲情感,同时为了信仰可以利用文学,为了信仰可能进行想象性体验。由于宗教永远属于决定性地位,文学不自觉成了神学的奴仆,正如哲学一样,这种诗学法则使西方近千年的文学除了民间文学遗产和古希腊罗马文学遗产外,再未增加任何独创性的自由内容;另一方面,作家从生存体验本身出发,通过生命的沉思,感应《圣经》中的精神内容或叙事抒情主题,使生命具有一种深沉而又博大的情感。
文艺复兴可能说是对基督教传统的一次有力反击。在基督教主宰千年的体制中,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来得并不容易,但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异教文化和异教思想便开始获得合法性地位。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辩中获得了正常发展,尤其是启蒙主义艺术与启蒙主义思想的合作,它们带来了西方文化的真正革新。主体性精神体验以及对内心生活的高度推重,使作家在创作中把心灵表现放置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基督教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在启蒙思想的反击与吸收中得到了批判继承。18世纪的卢梭也创作了一部《忏悔录》,这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卢梭的《忏悔录》是否有感于奥古斯丁的同名之作而为,虽然作者并未明言,但可以肯定,以卢梭的博学多识,他对奥古斯丁的这部名著应该说不陌生。事实上,他在《忏悔录》中叙述过他曾熟读奥古斯丁等神学家的名作。这样,采取同名著作可以得到两个解释:一是认同是奥古斯丁的心灵独白方式,以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活动的忏悔方式进行心灵表白,对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系统的回顾;二是不满意奥古斯丁的忏悔方式,以更真诚更坦白更自然的方式,以非基督教精神作为思想支撑或者说以自然与自由的人性观念作为价值支撑来评判个人的生命历程,以便与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形成一种对比,告诉人们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前一种理由,那么,卢梭的忏悔体文学可以视作对奥古斯丁的一种继承;如果是后一种理由,那么,卢梭的忏悔体文学可以说是对奥古斯丁的一种解构。
卢梭的《忏悔录》标志着西方忏悔体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自卢梭始,忏悔体文学逸出了宗教语域,所以,从实际效果而言,卢梭的忏悔体可以说是将奥古斯丁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覆过来。卢梭的《忏悔录》确实忠实地记录了主体的心灵性历程,他的坦诚与大胆不能说后无来者,但确属前无古人。尽管人们对卢梭的真诚忏悔程度还表示怀疑,因为按照人们的理解,人的卑劣与卑微心理肯定要比卢梭所叙述出来的一切更可怕,或者说,卢梭在《忏悔录》中还有隐恶倾向,即他肯定还有无法为人道的事实没有叙述出来,但我们应对卢梭所充分表达出来的一切表示敬意。卢梭作为一个日内瓦公民所具有的自然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在其思想的审美自由精神的历史生成过程中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历史线索,因此从卢梭所叙述出来的材料看,他虽直接受惠于基督教教会教育,直接受惠于富有基督仁慈精神的信徒的巨大帮助,但卢梭并不敌视基督教,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首先是一个自由意义上的思想者,一个热衷于自然与自由体验的思想者。
相对奥古斯丁而言,卢梭的忏悔体文学首先是恢复了生命真实与心灵真实的合法意义。卢梭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只把人看作宗教意义上的人,他把人看成一个社会的人,这样,他就恢复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他不漠视人的个性,相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存在的合法性。这表现在忏悔体文学的文体选择上,他选择了自叙传或独白体;表现在话语方式上,以叙事为主体,以抒情作为调节手段;表现在思想主旨上,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历程为主体,偏于客观性叙述。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变显示了文学的独立意义,它不再服从于宗教,也不再屈从于基督教信仰,而是从人自身出发,从个体的生命经历出发,以回忆与体验作为思想核心。卢梭的探索表明,忏悔体文学最适宜的话语方式是主体性叙述,尽管他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主体性抒情,但第一人称叙述无疑是最主要的基调。由于卢梭没有从某种信念出发,而是从自我生活经历出发,因而,他直接将人带入到他的生活世界中。他以一种最亲切最真诚最没有姿态的自然方式将个人生命经历娓娓道来,他假想中的读者是他所信赖的亲密的朋友,他的忏悔式叙述带我们去理解他的生活,他的心理,他的选择,让我们消除对他的种种误解,尤其是那种道德论的指责。卢梭并未过分夸张他的天才,而是平实地叙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忏悔”在卢梭这里显示了与奥古斯丁相似的意义,忏悔即一种真诚的内心独白,奥古斯丁的忏悔是面对上帝的自我内心独白与感恩式抒情,他所忏悔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罪恶,而不是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罪恶,这种忏悔实质上是主体性的内心情感活动。尽管奥古斯丁在忏悔体写作中有“罪”的自责与忏悔,但在接受者那里,这并不是真正的罪,而是一种非纯粹的信仰生活。卢梭的忏悔不是面对上帝的有罪的自责,也不是面对法官与贵族的有罪的自责,而是一种面对自我的内心反思,一种富有理性的个人生活价值判断,超脱了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罪责概念。这样,忏悔可以分成宗教意义上的自我评判活动和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评判活动。卢梭选取的是道德论的自我评判,他的忏悔本身并无过分的道德罪错,但作者对华伦夫人的感恩与背弃,对儿时的亲友的感恩以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意错误的悔悟则多少了体现了他的忏悔论立场,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犯罪者”在卢梭这里获得了一种巧妙的回应。
卢梭的忏悔式独白表明,他在自然主义与自由主义道德论意义上并未重大的罪责与过失,尽管在基督教伦理意义上,他有不少罪错,但这些大多是由环境逼迫而成。卢梭的《忏悔录》主要展示了人的精神崇高与心灵的美丽,这种精神性崇高是由他的自然主义的道德论立场决定的。自然主义的道德论是一种重视人自身的价值立场,即在评判一个人的生活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时,首先看它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只要是自然的合乎人性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而社会上的流俗的道德评价推则是不管你的行为是否合乎人性或是否合乎自然,而在于你的行为是违背宗教伦理和世俗法则,像卢梭与华伦夫人的特殊关系一直被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视之为非道德的,而在卢梭看来,这种合乎自然伦理的人性活动无悖于道德。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都出自天然,出自弱者的选择和高尚者的爱心,出自有信仰者的那种高度同情心。他的生命活动本身纯粹出于自然,不是非道德的,也无损于真正的道德,相反,那些标榜道德之士,以道德法官自居,对他人进行中伤伤害,才是真正的非道德与反道德,因为这些道德卫道士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损害,恰恰是对道德一种嘲弄。
当然,卢梭也对真正的道德归罪表示良心上的不安与真诚忏悔,核心事件则是青年时期的偷窃行为、诬陷玛丽、将自己的婴儿送育婴堂而不承担哺育责任,尤其是诬陷玛丽一事,他的忏悔是沉重的。“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像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每当我生活处于平静状态时,这些回忆带给我的痛苦就比较轻微,如果在动荡多难的生活中,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我可以说,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复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⑧在卢梭的这部忏悔录中也充满了感恩,不过,这份感恩是献给那些心灵高尚的人,那些富于基督爱心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直接献给上帝。
必须承认,这种独白式陈述,尤其是关于自我生活真实的独白式陈述确实需要勇气。事实上,将自我真实地坦露出来,正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那样需要许多前提,否则就没有典范意义。在奥古斯丁和卢梭之后,这种自我忏悔本身受到了挑战,可以说,奥古斯丁式忏悔树立了一个宗教典范,而卢梭式忏悔则树立了一种个人性典范。很难说卢梭之后再无传人,但人们出自对这种忏悔体文学的恐惧与怀疑,于是,将自我隐遁起来,或者通过一个假定者的身份来达成心灵忏悔或表达,也就是说,忏悔体文学在卢梭之后转入了一个新的航道,即通过小说虚拟和假定的方式来达成忏悔体文学的内心独白与真实抒情的个人要求,不再采用自叙传的形式,这就进一步使忏悔体文学溢出宗教语域和道德语域,同时又能很好地介入到宗教论域和道德论域之中。
这种泛化的忏悔性要求,既可以看作是宗教对文学的一种感召,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对宗教的一种回应,因为它们禀有共同的精神使命。事实上,忏悔体文学在近现代小说中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以俄语文学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使忏悔体形式在其小说创作中具有了特殊的位置。应该说,这两位作家本人的生命活动带有宗教或道德意义上的罪错,这种罪错本身使他们心灵焦灼不安,而成为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展示了这个问题,在不平等并充满罪恶的社会中,贫贱的善良者为了生存不得不犯罪,这罪错本身在法律上是无法责怒的,而在道德上又值得忏悔。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都正视了这一问题。以德语文学为例,卡夫卡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也体现了一种凝重的罪责性思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的象征,《城堡》中的罪责源自那种无所不在的制度性的漠然约束,它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甚至用罪错来表示,因为表面上看不到一个施罪者。就他个人的生活而言,他始终充满一种罪责畏惧,由此而形成的宗教道德沉思是:谦卑给每个人(包括孤独的绝望者)以最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惟一的前提是,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言语,同时又有建立崇拜者与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最牢固的关系。人可以从忏悔中或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因此,忏悔体文学不仅标示着一种宗教性力量,也标示着一种道德力量,它是对生存的深入的反思,忏悔自身就是忏悔主体自身把自我推入到心灵的审判台前进行心灵审视,寻找良心的自慰,也通过对责错的忏悔而达成良心的安宁。因为忏悔标志着一种力量,一种深入地探索心灵,探索人性,探索生命存在价值的力量,忏悔作为一种第一人称叙述与抒情,它确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事实上,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这两部《忏悔录》永远标志着一种信仰的尊严、道德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它也是一种评判方式,让我们在心灵的审判台前能够真正地评判自己,从而获取人性进取的力量。
①参见《忏悔录》英译本导言,Confessions,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②③④⑤⑥⑦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51,25,3,18,247,216页。
⑧卢梭:《忏悔录》。
标签:文学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忏悔录论文; 基督教论文; 圣经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神话论文; 旧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