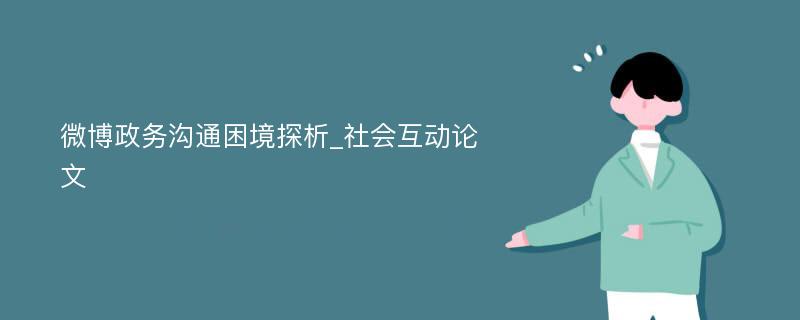
政务微博传播困境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政务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5)04-061-04 政务微博指经过实名认证的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开通运营的以政务传播为主的微博。通过社会化的“共有媒体”进行政务传播和公众沟通是区别于倚重传统媒体的、面向未来的新选择,也是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在社会新结构、媒体新环境、技术新条件和舆论新格局下,适应现实发展、适应“不仅要管理好、服务好还要传播好、沟通好”新要求的主动选择。 《2012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提示,政务微博已经从最初的以信息发布为主,逐渐发展成集信息公开、舆论引导、政民互动、为民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媒体平台。政务微博传播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经验,积累了部分成果,并出现了一些突出个例,如部门微博中的“外交小灵通”“平安北京”,地方微博中的“上海发布”“天津发布”,以及以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云南省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为代表的党政干部微博。 微博是新事物、新工具,政务微博是政务传播的新应用、新尝试,传播实践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的公私不分,有的搞笑装萌,有的谨慎小心、避重就轻,被统称为“气象局”微博(主要发布天气预报和逸闻趣事等不痛不痒的内容);有的只管开通不管维护而沦为“僵尸”微博(不发言、不更新、不回应)。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操作层面看,政务微博是否能够良性运营与党政机构领导的政务传播意识、媒介素养及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工作经验紧密相关。从学理层面看,政务微博试图适应网络的精神实质和微博的技术逻辑,同时必须遵循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造成了明显的双重人格,面临着身份困境、关系困境、表达困境和互动困境等四重传播困境。 一、身份困境 第一,作为实体主体与符号化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开通政务微博的主体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和机关内设机构、其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以及在上述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1]经过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是实体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的媒介延伸和符号化存在,携带着实体社会的身份、角色和等级进入虚拟社会。符号化主体代表实体主体然而并非实体主体的简单复制,政务微博并非既有政务传播的网络搬家;同时符号化主体不能完全脱离实体主体,脱离实体主体性质、定位的政务微博取消了与个人微博的区别,丧失了政务传播的公共性也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既要保持在实体社会中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满足微博用户对符号化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的角色期待,这对矛盾难以解决却始终存在,是政务微博安身立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作为实体社会中绝对的中心与作为虚拟社会中流动的节点之间存在矛盾。党政机构是计划经济时代高度一体化社会的大脑和生产生活的指挥中心,自上而下的文件、命令是主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政务传播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党政机构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作用作出了重大调整,但是仍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无可争议的核心、权威和领导者。转换到虚拟社会,党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一样,均为网络结构中的一个节点,符号互动中的一个ID;失去了在场等级和在场地位的党政机构不再是绝对的中心,中心和边缘在虚拟社会具有了相对性和流动性。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的流动及从边缘化到去边缘化的流动使反传统、反权威、反主流的话语空间空前膨胀,极大地挤压了政务微博的话语空间。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之外的大多数时候,政务微博的消息愔愔无闻,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碎片之中,出现政务微博事实上的传播失灵。 二、关系困境 1.关系重构 党政机构与公众在实体社会中的权威与依从关系重构,此为其一。格雷戈里·贝特森把社会信息传播区分为揭示传播内容的“内容讯息”和揭示传播者之间关系的“关系讯息”。[2]任何传播都是关系传播和内容传播的统一。实体社会中党政机构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往往以党政机构为主,由党政机构决定政务传播发生的时间、场所及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甚至在场等级和在场关系能够直接决定政务传播效果。一句话不仅看说的是什么,关键要看是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在权威与依从的关系框架下,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务传播,即使内心产生了疑虑和不满,或者存在争议甚至持有反对意见,由于受到在场秩序的约束和压制而无法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和释放。对于政务微博来说,权威与依从的在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为彼此平等的非在场关系。政务微博发布的消息、提出的意见不再因为是来自官方的声音就不容置疑、不可辩驳,反而正因为是来自官方的声音往往受到更多的调侃和挑剔,甚至遭到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实体社会中强势、高效和主动的政务传播进入微博空间变得相对弱势、低效和被动。 党政机构与公众在实体社会中依托大众媒体形成的导向与依从关系重构,此为其二。政务微博出现之前,党政机构主要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传统大众媒体即报纸、广播和电视进行政务传播,营造有利于政策过程的舆论环境。具有强大的广泛传播、大量传播、快速传播能力的大众媒体一方面放大了某些事实和意见,一方面制造了其他事实和观点——尤其是冲突性和竞争性的观点的沉寂化,形成了特殊的“地位授予”功能。实体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很少能够得到这种“地位授予”,通常只能被动地依从由党政机构和社会精英控制的大众媒体的导向,缺乏技术意义上的话语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话语权利。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微博等网络应用获取新闻、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生活,倚重传统媒体的沟通成本越来越高,沟通效率则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力不从心。对于伴随网络一同成长起来的90后及21世纪出生的一代,传统媒体对他们父辈的影响模式和影响力很难重新复制,他们更熟悉新媒体,不习惯接触传统媒体,对传统媒体存有天然的生疏感甚至排斥感。导向与依从关系在虚拟社会中依然存在,但是存在方式已不同,不是常态的、稳定的,而是流动的、脆弱的,相对于实体社会而言可控性降低而随机性增大。 党政机构与公众在微博空间中形成关注与被关注关系,此为其三。关注是主动的,被关注是被动的;关注者是政务信息接收者,被关注者是政务信息传播者。是否“关注”政务微博接收政务消息,是否“转发”形成多次多级传播,是否“评论”发起互动讨论等话语权利掌握在政务信息接收者一方。政务信息传播者的影响力直观地表现为关注者的数量、黏度和“转发”“评论”等微博行为。微博媒介的工具理性赋予关注者较高的价值,只存在没有“粉丝”,“粉丝”太少及失去“粉丝”的焦虑,不存在没有微博账号可关注的担心。实体社会政务传播活动中被动、弱势、喑哑无言的不特定的大多数人,转换为虚拟社会中身体缺场的、符号化的、流动的微博用户之后身价倍增,成为政务信息传播者一心以求的关注者。他们掌握着“加关注”这个按钮,掌握着转发和评论的主动权,掌握着哪个微博账号能够上到人气排行榜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关注的投票权。如果说作为新媒体、自媒体的微博也具有传统大众媒体的“地位授予”功能,那么显然这一次得到传播媒介“地位授予”的是实体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传播关系重构过程中最明显、最深刻的变化在于话语权利向政务信息接收者一方转移和倾斜。 2.关系脆弱 政务微博、财经微博、公知微博、媒体微博、明星微博、草根微博……在微博这个消息的集散地和观点的自由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竞争性主体,充斥着太多的竞争性事实和意见。在众多的可替代选择中,有多少微博用户、受什么样的力量驱动、在哪些事件上、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关注政务微博是尚待证实的问题。“人天然是一种政治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假定。公众只能作为民主政治的“局外人”,这是李普曼舆论学的推断。不同的假定和推断反映出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参与民主政治动机的不确定性,以及参与过程和机制的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政务微博关注关系的建立、维系和终止均为关注者自主合意的个人行为,较少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或保护,在场关系、在场秩序对政务微博接收、转发和评论等传播环节、传播活动的控制弱化间接化,移动互联趋势下随时随地可通过手机终端轻易地“关注”或者“取消关注”。关注关系脆弱,此为其一。 微博传播的起点是强调自我价值的个人,虚拟社会中重新构成的权威、导向等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自主认同的基础之上。对于基于符号互动的微博用户而言,实体社会中作为权威消息和主导意见来源的党政机构并不具有达成共识、形成认同的天然特权和优先权。实体社会中观点表达者的身份、地位等因素与观点自身的说服力、影响力的紧密关系在虚拟社会进一步分离。即使在某些公共事件或社会问题上微博用户与政务微博形成某种程度的自主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也具有相对性、流动性和可替代性。强调自我与回归群体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动力,各抒己见与寻求一致是一对彼此转化的矛盾,政务微博有成为虚拟社会意见领袖的成长空间,且可能性极大,但是得到认同和维系认同比实体社会中得来更为艰难,失去则更为容易。认同关系脆弱,此为其二。 三、表达困境 好的表达不仅是表达内容、表达形式的统一,也是表达情境、表达意图、表达者身份、表达接收者需求和表达效果的统一。从实体社会在场表达到虚拟社会非在场表达,表达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仅从表达形式看,由于缺失了基于在场可见的实体身体的身体语言和副语言,补偿性地出现了具有类似功能的各种键盘符号和变体语言。例如“:)”表示一张一般的笑脸,还有相应的符号对应大笑、吐舌头笑、挤眉弄眼笑,“同志”变“筒子”,“同学”变“童鞋”,“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变为“喜大普奔”……与微博内容总体上的碎片化、人际化和情感性相对应的是微博表达形式的个性化、非正式、无厘头、频繁使用语气词及网络流行词汇和流行语体。 政务微博既要保持在场表达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又要适应网络表达的新形式和新要求已成为一种共识。与表达内容的公共性相匹配,与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的身份相适应,兼顾微博用户的接触习惯和使用体验是形成政务微博自身表达方式和独特语言风格的基础。“亲,你大学本科毕业不?办公软件使用熟练不?英语交流顺溜不?驾照有木有?快来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招人啦!有意咨询……不包邮哦。”这是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发布的“淘宝体”招聘信息。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曾用当时最流行的“咆哮体”推荐浙江官员微博群:“真给力啊!浙江军团再现!童鞋们何不一睹为快!有木有!有木有!”在与特定内容要求相一致的前提下适当使用“网言网语”有利于避免官僚化、生硬感,增强亲民性、亲切感。蔡奇在微博上袒露心声:“官员要重新学会说话,不讲官话大话而讲白话,讲百姓听得懂的话,否则谁听你的,最重要的是拉近与网友的距离,毕竟现在不是权势而是粉丝时代。” 官腔官调、空话套话即使在实体社会也不受欢迎,只是处于特定情境的公众迫于在场等级在场秩序的压力而无可奈何。如果不加改进地全盘照搬,那么严肃死板、面目可憎的政务微博根本无法适应网络表达的情境和场合,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政务信息传播受限,政治社会化过程受挫,公众沟通渠道受阻,政务微博形同虚设。当然,政务微博也不能没有原则地模仿,失去自我地赶时髦,为了吸引粉丝而卖萌讨好,毕竟与政务传播内容的公共性相适应的表达是庄重持稳、平实大气,而不是甜腻轻佻、油滑饶舌。“你逃或者不逃,事就在那,不改不变;你跑或者不跑,网就在那,不撤不去;你想或者不想,法就在那,不偏不倚;你自首或者不自首,警察就在那,不舍不弃;早日去投案或者惶惶终日,潜逃无聊,了结真好。”[3]这是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发布的一条官微,可谓在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的矛盾之中寻找平衡的一种探索。 四、互动困境 比照实体社会中的传统大众媒介,微博作为新媒介使得虚拟社会中话语资源重置,话语体系再造,话语关系重构,话语权利重新分配。实体社会中的政务传播,信息由传播者单方面发出,互动只是理论模式图中那条叫做“反馈”的虚线,受众自主发声缺乏技术可能性和社会现实性。微博“评论”按钮的设置,赋予政务信息接收者发起互动的话语权利,实现了即刻反馈的技术可能和便利表达的社会可能,与此同时对政务微博提出了即时响应和人格化互动的要求。 互动的前提是存在对等的主体。在新浪、腾讯等微博平台上,关注数量庞大、互动行为活跃的人气微博多是个人微博。政务微博与个人微博性质、定位不同,内容的吸引力、话题性不同,不宜进行绝对数量的简单对比。不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作为微博平台上的一个账号,政务微博与其他微博用户是对等的、平权的,然而符号化存在带来的对等、平权是相对的、有边界的。虚拟社会不可能脱离实体社会而独立存在,微博世界并非与实体社会隔绝的虚幻世界。实体社会中的党政机构是微博平台上的政务微博账号的根源和基础,政务微博是党政机构在微博世界的镜像和影子。包括消息发布、关注其他账户、转发其他账户消息及与微博用户互动在内的全部微博行为都是公开透明的组织行为,不仅要遵守程序、讲求规范、得到授权,而且要为政务微博上所做的回应与答复等履职行为负全面责任,包括虚拟社会中的言论责任、舆论责任和实体社会中的工作责任、职务责任。不是个人对个人负责,不是为了互动而互动,政务微博的互动行为必然按照组织规章制度行事,追求互动效率和互动导向。 政务微博是社会管理的新思路、公众沟通的新办法,不得不面对制度化响应与人格化互动之间的矛盾,以及夏雨禾所证实的微博互动“以话题的变异性、弥散性、不可知性为主要特征”的事实。[4]适应政务传播实践的迅猛变化,政务传播理念已在宣传思维的基础上发展出传播思维,目前亟待确立的是互动沟通思维。有论者指出:“如果没有网民的热情参与,政务微博功能、目的等所有期待都将归于失败。而吸引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最佳途径就是满足公众的被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5]尊重在线用户,与其进行负责任的平等对话和真诚协商,政务微博传播才能扭转传播困境,克服传播失灵,在虚拟社会中构建政治沟通的新仪式。标签:社会互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