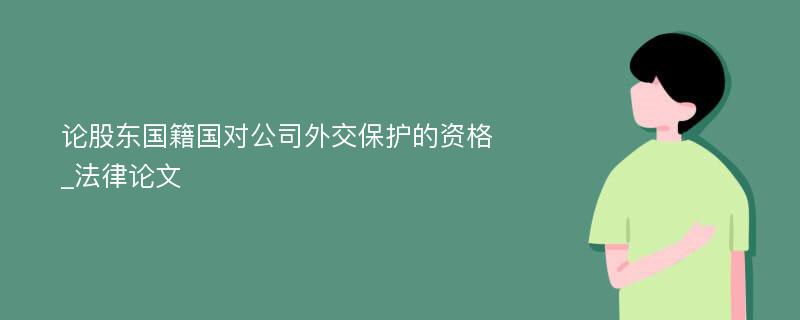
论股东国籍国对公司的外交保护资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籍论文,股东论文,外交论文,资格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司不同于自然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背后存在同样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股东。于是,要求允许股东国籍国在公司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为其实施外交保护的呼声不绝于耳。1970年,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公司案(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中,否定了股东国籍国的外交保护资格,但争议并没有就此平息。
一、对传统原则的改良方案
从法律角度讲,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国际法院之所以否定股东国籍国的外交保护资格,是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独立这一基本原则。①此外,国际法院也有政策上的考虑。②该案之后,公司应得到公司国籍国而不是股东国籍国保护的原则被确立起来。对此,质疑声一直如影随形,归纳起来,要求赋予股东国籍国外交保护资格的方案大致有如下三种。
(一)公司国籍国和股东国籍国实施双重保护
该方案早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就被国际法院的田中(Tanaka)法官提出。他认为,的确没有国际法规则允许分别对公司及其股东行使两种外交保护,但也没有国际法规则禁止双重保护。③
然而,笔者反对双重保护,因为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在传统中,对公司人格独立的维护是应当被肯定和保留的。我们可以追溯公司法的发展历程。公司最早是以无限公司形式出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演化为两合公司。为了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17世纪又出现了股份有限公司,19世纪末产生了有限责任公司。④然而,到了21世纪,假如我们将这种有限责任的基础——公司人格独立彻底抛弃,真不知道这是法律进步了,还是生产力退步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关于该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官方意见颇有道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股东国籍国可对股东行使外交保护,而公司国籍国也可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对于东道国而言,因同一侵害导致要面对两个不同的争议,这无疑将会使争端的解决复杂化,并加重东道国的负担。⑤因此,该方案实在不足取。
(二)股东国籍国取代公司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杜加尔德(John R.Dugard)在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外交保护的第四次报告》中就论及该方案。这个方案是受国际法院1955年做出判决的诺特鲍姆案(Nottebohm)的启发。
笔者认为这种方案比双重保护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如果说双重保护只是否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那么这种则是从根本上否定公司人格本身。虽然诺特鲍姆案启发我们应当重视控制因素,然而对控制因素的考察应当是全面的,不应简单地与股东国籍国画上等号,例如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虽然比利时国民控制了公司88%的股份,但国际法院却认定与该公司建立起密切和永久联系的国家是加拿大。
上述两种方案都主张由股东国籍国直接保护,即不必在公司国籍国无法实施保护的情况下才启动该保护。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股东国籍国直接保护的做法已经成为一项国际习惯。⑥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乐观了。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物质要素(国际惯例的形成)和心理要素(法律确信的建立)两个方面。在他们的论述中,笔者看到的只是对国际惯例的强调,却没有见到对法律确信的证明。除了难以证明法律确信外,一次付清协定的特殊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二战期间由没收财产行为导致的索赔,另外一大部分则是因为战后国有化引发的索赔,而这部分索赔往往是在冷战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的。此外,国际法院2007年在迪亚洛案(Diallo)中依然认为巴塞罗那公司案之后的国际法实践的发展不能赋予股东国籍国直接保护以国际习惯的性质。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股东国籍国直接保护尚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
(三)将股东国籍国保护作为公司国籍国保护的例外
应当承认,即使有种种质疑,但巴塞罗那公司案的权威性在今天尚未根本动摇。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在肯定公司国籍国保护的基础上,将股东国籍国保护作为例外情况。
事实上,当年在宣称应由公司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时,国际法院的确审查过是否存在已知的例外情况。“揭开公司面纱”在该案中显然是不存在的,也未被提及。不过,国际法院却明确提及两种股东国籍国可以实施保护的情况:第一,公司在成立地不复存在;第二,成立地国应对造成损害负责,并且通过国籍国获得保护是外国股东在国际层面的唯一救济渠道。
巴塞罗那公司案没有完整地审查这两种例外,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该案中,但该例外却得到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肯定。国际法委员会在2006年二读通过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以下分别简称《草案》和《草案评注》)。《草案》第11条规定:“在公司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国籍国无权为这些股东行使外交保护,除非(a)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按照成立地国的法律该公司已不存在(ceased to exist);或(b)在受到损害之日,该公司具有被指称对造成损害应负责的国家的国籍,并且在该国成立公司是该国要求在其境内经营的前提条件。”⑧
二、公司已经不复存在情况下的股东国籍国保护
(一)判断“不复存在”的标准
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之前,权威意见赞成一种不那么严格的判断标准,允许国家在公司“实际停业”的情况下为维护股东利益而介入。⑨英美与葡萄牙之间的德拉果阿湾铁路公司案(Delagoa Bay Railway Company)就是一例。葡萄牙于1883年给予美国人麦克默德(Macmurdo)建造一条铁路的特许权。后者根据葡萄牙法律成立了一个公司,并将特许权转给该公司。之后,他又将该公司部分股票出售给一家英国公司。葡萄牙在1899年占有了铁路并废除特许权。英美将此纠纷诉诸仲裁。葡萄牙认为它只能与该公司打交道。而英美则认为该公司实际上已不存在,除了由股东国籍国干涉外,别无他法。仲裁庭支持了英美的主张。⑩本案中的公司虽已停业,但仍保留人格。
巴塞罗那公司案规定了更高的标准。在该案中,公司瘫痪或财政情况危急的标准被视为不适当,实际停业的标准也不被采用,因为这在法律上不十分准确。国际法院认为只有在公司在法律上已消亡时,股东才失去了通过公司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只有失去了这种可能性后,股东国籍国才有独立权利。(11)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即认为消亡是指公司在法律上法人资格的消灭,而不是指公司事实上的瘫痪、财政危机、停业甚至清算等情况,只有公司法律地位的变化才应予以考虑。(12)“法律人格消亡”的判断标准的确可圈可点,不过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判定公司不复存在的准据法。
(二)判断“不复存在”的准据法
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承认涉案公司在西班牙已倒闭,但强调这不影响它在成立地国加拿大的继续存在。《草案》第11条(a)也将不复存在的准据法规定为公司“成立地国的法律”。然而,奥地利则建议将“成立地国”改为“国籍国”。(13)
按照公司国籍的一般理论,即成立地标准,公司国籍国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成立地国。但是随着公司国籍的判定标准越来越强调实际联系因素,因此,在一部分情况下,公司国籍国可能是成立地国以外的、与公司具有实际联系的国家。由此可见,成立地国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籍国。于是,假如公司是否消亡仅仅依据成立地国法律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种尴尬——当公司国籍国不是公司成立地国时,《草案》一方面承认公司应当接受公司国籍国法律的调整,另一方面却认可该公司可能依据另一个国家(成立地国)的法律消亡,而无需参考国籍国的法律。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同意奥地利政府的意见,“不复存在”的准据法应当是公司国籍国,而不是成立地国。这既能够更加适应目前公司国籍判定标准越来越强调实际联系的大趋势,又能够避免将公司成立地国简单地等同于公司国籍国的误区。
(三)将“与损害无关的原因”作为限制条件
笔者注意到,在杜加尔德提交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外交保护的第四次报告》中,并没有写入这一限制条件,但到了《有关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时,“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这一限制出现了,并被最终写入《草案》第11条(a)。如果将《草案》第11条(a)与第10条第3款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委员会将公司不复存在的情况分为两种:由于损害的原因而不复存在;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而不复存在。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对于前者,应由公司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对于后者,可以由股东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然而,笔者认为,即使在公司由于损害的原因而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股东国籍国也应该有可能实施外交保护。笔者主张一种阶梯式保护,即先由公司国籍国保护,如果该国放弃或在合理期限内不保护,股东国籍国仍可以实施保护。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国籍国享有的外交保护权不应当是无期限的。正如美国所主张,允许在公司生命结束后涉及该公司的权利主张无限期地存在,这可能有损这一定局以及相应的资源分配决定。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律只是允许公司在解散后一段有限时间内继续提出和维护公司存在期间产生的要求,也就是说法律人格持续至这段时间终止。(14)换句话讲,公司不复存在后,其法律人格的延续应该是有期限的。当公司人格彻底消散后,股东就应当被允许主张自己的权利。
(四)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利的区分
《草案》第12条特别规定:“在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股东本人的权利,而非公司的权利,造成直接损害的情况下,这些股东的国籍国有权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15)美国认为这项规定是多余的,因为股东如所有其他国民一样,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设立一项单独的条款。(16)中国政府也认为股东个人而非公司的权利,原则上可援引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没有必要做出专门规定。(17)不过,笔者认为单独规定仍有必要,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股东的权利与公司的权利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巴塞罗那公司案中提到股东最明显的权利是:获得已公布红利的权利、出席股东大会并在会上投票的权利以及分享公司清算后剩余财产的权利。然而,正如国际法院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清单并不详尽。《草案》第12条也没有试图提供一个穷尽的列举来区分公司权利与股东权利。事实上,这也没有必要。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确定一个准据法。
《草案评注》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成立地国国内法决定的问题,但如果公司是在做出不法行为的国家成立,那么可能需要援引公司法的一般原则,以确保外国股东的权利不受到歧视待遇。(18)笔者认为,采用公司国籍国法律,取代公司成立地国法律,可能更为妥当,理由与之前讨论“不复存在”的准据法基本相同。需要强调的是,决定哪些是股东的权利,哪些是公司的权利,并不仅仅取决于公司在哪里成立,而更取决于公司受哪个国内法体系的调整。此外,虽然公司在做出不法行为国成立与外国股东是否受到歧视待遇的确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公司法的一般原则的确存在,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就明确列举了股东最明显的权利。因此,不应当排除适用公司法一般原则的可能性。
三、公司具有损害责任国国籍时的股东国籍国保护
(一)《草案》设立第11条(b)的合理性依据
美国反对设立第11条(b)。它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制定这项例外所依据的所有案例中,都存在两国之间的特别协定,给予股东要求赔偿的权利。由于存在这些协定,上述案例不能支持存在一项国际习惯。同时这项例外规定将建立一个可能并不公正的制度,使得相对于外国拥有的公司的股东来说,在某国成立的公司的股东更有权在该国寻求对他们的主张提供外交保护,而外国拥有的公司的股东则必须依靠该公司的国籍国提出主张。(19)国际法委员会所援引的案例的确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著名的1989年西西里电子公司案就比较典型。(20)本案中,国际法院实际上是默许了在公司具有损害责任国国籍时,股东国籍国可以实施外交保护。但国际法院避免声称这是一项所谓的例外,因为它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而是对美意之间的友好通商条约进行解释。(21)所以,国际法委员会在案例方面自然会受到质疑。美国的反对意见看来似乎是有根据的。
笔者认为,第11条(b)是否是国际习惯的确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然而,该例外之所以仍有必要被编入《草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对国际投资环境的政策考虑。正如英国在1938年墨西哥鹰石油公司案(Mexican Eagle Oil Company)的答辩词中所说,如果承认这种理论,即政府能够首先使依照当地法律成立公司成为外国利益方在其境内营运的条件,然后将这一成立作为拒绝外国外交保护的理由,则显然总会有办法阻止外国政府根据国际法行使其不容置疑的权利以保护其海外国民的商业利益。(22)所以,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正常规则,外国股东将听任有关国家摆布,可能蒙受巨大损失且得不到补偿。(23)因此,尽管我们不能毫无争议地称该例外已是国际习惯,但我们却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进行发展。
(二)《草案》将“被迫取得”损害责任国国籍作为限制条件
虽然允许股东国籍国在公司具有损害责任国国籍的情况下实施外交保护,但《草案》第11条(b)却附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即损害责任国要求在其境内成立公司是在该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这实际上是将例外情况进一步限制在所谓“卡尔沃公司”(Calvo company)的情况下。这种公司的建立类似于卡尔沃条款(Calvo clause),旨在保证它不受国际法上有关外交保护规则的制约。此款规定与卡尔沃条款混杂在一起,不能不引起对类似制度表示反感国家的注意。(24)英国就认为,无论在成立地国成立公司的理由为何,都应允许股东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权。(25)但笔者认为,将“被迫”因素考虑进来是明智的。假如在公司自愿取得损害责任国国籍的情况下,也允许股东国籍国保护,一方面,这将极大地扰乱投资东道国的国内秩序——国家不得不担心正常情况下成立的本国公司也会招来别国的干涉;另一方面,大股东完全可能为了寻求股东国籍国保护,而故意使公司具有损害责任国国籍。
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加尔德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有关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中,该限制条件曾经一度被局限为迫于法律因素。然而,在北欧国家的建议下,《草案》最终将之拓展至非法律因素。笔者认为,非法律因素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使得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界定,即使将它纳入被迫因素,也应当在实践中加以明确,否则将导致该例外规则被滥用。
(三)股东国籍国保护导致索赔多边化的问题
允许股东国籍国保护很可能会导致索赔的多边化,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一个股东的国籍国都应该有外交保护的权利。或许有人会建议借鉴国内法上股东代位诉讼制度中对股东资格的限制措施,例如对持股数量的限制。但笔者认为,在外交保护中设置类似门槛是异常困难的。一方面,当国家决定出面干涉时,它实际上已经是在主张国家权益,那么必然会要求各国主权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法律的差异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或许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
于是,有学者对多边索赔可能导致的混乱表示了担心,例如股东往往本身就是公司,而且确认每个股东的过程可能旷日持久,这种过程在任何案例中实际做起来都很困难。(26)巴塞罗那公司案中,田中法官和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法官则不认为这会导致混乱,因为外交保护是斟酌权,而且有关国家可能会联合行动。(27)外交保护通常成本不菲,国家一般不会为小额股份而兴师动众。此外,联合行动不但是一种可能,而且是国家的内在需要,因为它更加符合国家利益。作为具有外交保护丰富经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表态很能说明问题。它在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政府意见中明确表示:“在实践中,而不是由于法律规定,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寻求与其他国家联手提出。我们也尽量避免提出交涉,除非那些持有大部分股份资本的国民的国家支持联合王国提出交涉。”(28)因此,笔者认为,多边索赔的确可能出现,但达到所谓混乱程度的可能性并非像部分学者担心的那样大。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赋予股东国籍国外交保护资格的诸多方案中,比较可行的是将其作为公司国籍国保护的例外情况。虽然这可能导致多边索赔,但出现所谓混乱的可能性不大。在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努力下,相关例外情况已经初现端倪,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尚存争议。
笔者认为,作为例外,股东国籍国起码可以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实施外交保护:第一,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按照公司国籍国的法律,该公司的法律人格已不存在;第二,由于与损害有关的原因,按照公司国籍国的法律,该公司的法律人格已不存在,并且公司国籍国放弃或者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实施外交保护;第三,按照公司国籍国的法律或者公司法一般原则,国际不法行为直接损害的是股东本人的权利,而非公司的权利;第四,在受到损害之日,该公司具有被指称对造成损害应负责的国家的国籍,并且在该国成立公司是该国要求在其境内经营的前提条件,但只有当公司通过其国籍国提供的救济手段主张自身权利因国籍国的严重违法行为而失败后,股东国籍国才有实行外交保护的资格。
注释:
①See I.C.J.Reports 1970,pp.34,35,36.
②See I.C.J.Reports 1970,pp.35,38,46,48-49,50.
③See I.C.J.Reports 1970,p.131.
④参见刘宗胜、张永志:《公司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⑤参见《中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58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的发言》,来源: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3/t530817.htm,2011年6月3日访问。
⑥See Richard B.Lillich,The Rigidity of Barcelon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5,No.3,1971,pp.525,526,531; Round Table:Toward Mote Adequate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Private Claims:"Aris Gloves","Barcelona Traction" and Beyond,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Vol.65,No.7,1971,pp.343-344; Burns H.Weston,Richard B.Lillich,David J.Bederman,International Claim:Their Settlement by Lump Sum Agreements,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5,p.36.
⑦参见肖军:《对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国际法院关于迪亚洛案(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评析》,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8年第2期。
⑧U.N.Doc.A/61/10,p.19.
⑨See U.N.Doc.A/61/10,p.60.
⑩参见王慧:《对跨国公司外交保护问题的分析》,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
(11)See I.C.J.Reports 1970,pp.40-41.
(12)参见《中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58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的发言》,来源: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3/t530817.htm,2011年6月3日访问。
(13)See U.N.Doc.A/CN.4/561,p.32.
(14)See U.N.Doc.A/CN.4/561,pp.30-31.
(15)U.N.Doc.A/61/10,p.19.
(16)See U.N.Doc.A/CN.4/561,p.35.
(17)参见《中国代表段洁龙在第61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中“外交保护”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两项专题的发言》,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283191.htm,2011年6月3日访问。
(18)See U.N.Doc.A/61/10,p.67.
(19)See U.N.Doc.A/CN.4/567,para.63,p.26.
(20)参见梁淑英主编:《国际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20页。
(21)See Chittharanjan F.Amerasinghe,Diplomatic Prote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8.
(22)See Marjorle M.Whiteman,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U.S.Department of State,1967,pp.1273-1274.
(23)See Mervyn Jones,Claims on Behalf of Nationals Who are Shareholders in Foreign Companies,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6,1949,p.236.
(24)参见张琼:《对公司和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以〈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基础之分析》,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25)See U.N.Doc.A/CN.4/561/Add.1,p.10.
(26)See Mervyn Jones,Claims on Behalf of Nationals Who are Shareholders in Foreign Companies,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6,1949,pp.234-235.
(27)See I.C.J.Reports 1970,pp.49,77.
(28)U.N.Doc.A/CN.4/561/Add.1,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