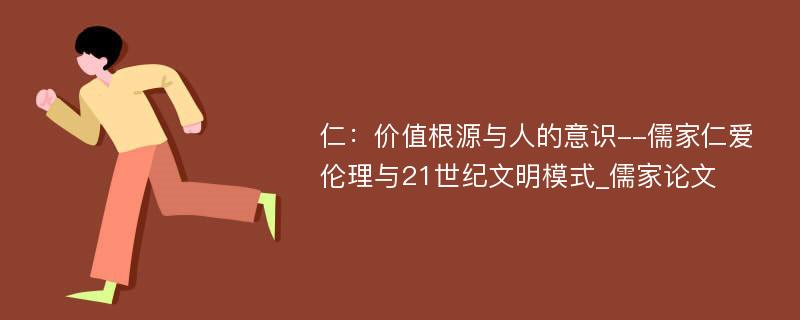
仁性:价值之根与人的自觉——儒家仁性伦理与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与人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伦理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仅有的幸福之一,乃是不得不去认识自己。”
——罗洛·梅(Rollo May)
是否能清醒地生活在二个世纪的边缘,这是一个大问题。
人类生存的危机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引起诸多哲人们的忧虑和思索, 处在世纪末的大变动时代, 历史不可能如马修·阿诺德(MathewArnold)所说的那样,给我们展示出“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的清晰画面,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回过头来反顾对自我的追寻:我们究竟迷失了什么?又迷失在何处?
1
尽管从哲学发展的纵深角度上看,二十世纪正如W ·怀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然而面对社会伦理思潮所展示的内容,文化的诊断者们却忧心忡忡地认定,二十世纪乃是一个充满怀疑、焦虑和虚无的世纪。德国哲人施太格缪勒(W·stegmüller)认为,在当代社会,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两种巨大的分裂正逐步侵袭着人们的心灵,“形而上学的欲望与怀疑论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存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的确,求得永生的要求与价值观上的捉摸不定感困忧着现代人,自由的获得与责任的承诺苦恼着现代人。
二十世纪,一面是科技文明的空前辉煌,一面是资本经济的猛烈冲击;一面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面是人性的毁灭与价值的迷失。面对这样一个良莠相杂、幻化不安的世界,二十世纪的许多圣人贤哲或以重建教堂的情怀,期待神圣的回归,或以鞭辟入理的睿智,梳解人生的死结。虽说这种悲情的呼声不乏仁者的高贵,然而到目前为止,笼罩人们心灵的却依然是驱赶不散的晦黯和阴影, 于是, 雅斯贝尔斯(K ·Jaspers)不得不唉叹:“不可靠的人,替我们这个时代看相。”
二十世纪的气氛,合而为一的感觉销匿了,统一的理想丧失了,共守的价值标准不复存在了。上帝死后,人们很难在现代人笔挺的礼服下面发现宗教的虔诚与笃信,卢梭的“科学与自然”、康德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尖锐和突出,道德判断只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非理性的表现,“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感觉如何,全看什么东西备受赞尝”,在相对主义的另一面便是虚无主义,人生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从普鲁斯特(M·Proust)、 托马斯·曼(Thomas Mann)、艾略特(T·S·Eliot)到纪德(A·Gide)、 乔伊斯(J·Joyce)、卡夫卡(F·Kafka),在他们慎重而深刻的主题中所表现的,大多是人在世界面前的无力感。人生就是梦魇,一切都是轮回,人生在世注定要与生活中的一切作永无止息的斡旋与搏斗,然而究竟对手是谁我们却不知道,因而一切挣扎皆为徒劳。 当你置身于奥尼尔(I·O·Neill)戏剧的情境之中,你会感到生活是一种重负,人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悲剧的宿命;当你站在毕加索(Picasso)的绘画面前, 你会感到传统的、现代的一切准则、规范都扭曲了、变形了、七零八落了,仿佛一切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把我们投置到一个机械般的生活方式之中,结果是逻辑的自律系统把人化约成纯粹的客观对象,找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科学家奥本海默所担忧的“艺术家的孤独学者的失望、科学家的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科学理性的没落。随着科技对人的宰制,“机心”对“人心”的替代,人们很难自觉到人性的价值和心灵中值得开发的富藏,价值和意义被漂白,人失去真正的自我,仅仅成为“残骸的积聚”。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所酿成的求利心态和功利意识普遍蔓延,市场经济已渗透到象征性的行为领域,因而相互关系已变成机械性和不完全性,人生的意义、人性、人情和人格皆跌落在效益的迷宫之中,而且被无情地转化为分工角色,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同时,这种生命世界的殖民化与通过金钱手段而使生命世界系统规则分离的行为一并发生,金钱不仅使相互作用的特殊性非世界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形成一种功能性子系统形式成为可能,这种子系统提倡以金钱的形式处理与周围的关系,因而也影响到行政管理结构。逐渐地,生命世界中的道德实践因素从个人与大众的生活领域中驱逐出来,“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金钱化与官僚化”〔1〕,形成一个无规范的社会。
鉴于理性的丧失,哈贝马斯(J·Habermas )主张以无限的交流和对话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鉴于现代生活的表面化、市场化、匿名化和分裂化,索罗金(P·Sorokin)和弗洛姆(E·Fromm)希望以爱心的力量来熨慰这个世界,价值哲学强调人作为文化的制作者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法兰克福的马尔库塞(H·Marcus )细致地考察了现代社会人的个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并以社会批判的形式寄以深深的幽怨。还有弗洛伊德(S·Freud)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福柯(M ·Foucault)的“情境与角色”;海德格尔(M·Heidegger)关于生命此在的意义;萨特(J·Satre)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与行动的强调等等,似乎一切都旨在于解救覆盖于整个世界的荒谬感、幻灭感和虚无感。的确,社会的剧变,价值的虚无如狂风暴雨般为我们点燃了世纪末危机的讯号,然而在它的深层处,即在于人性的无明和意义的丧失。皮兰德罗(Pirandello)发问:“我真正是谁?我是人吗?”,艾略特(Eliot )回答:“我们都是空心人,形状无形式,色度无色彩。”这也许正是存在主义将身心交迫的苦痛、焦虑和绝望等人的情感上升为哲学本体论的深刻根源。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哲学的思考该怎样延展历史、笼罩现实、指向未来以帮助危机中的人们摆脱困境;重持完整的自我?这是世纪之交向全世界哲人发出的声音。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退隐后,哲学要做的事便是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然而面对人生的危机和意义感的丧失,虽在存在意义上殚精竭虑,对人性的呼唤却也间隔一层,所谓“以智明有”与“以性化诚”方是人性回归的二路正途,亦即中国儒家仁智双彰的过程。未能于人身上发见仁性,哲学家的工作终不能说完全。尤其在现代社会,人性逐乎物、荡乎杂,以致残碎和迷失自我,自当在人性之本源处照察。程伊川说:“观乎圣人,则见天地”,张横渠则言:“大其心者则能体天下之物”,这正是孔儒天地同一的精神旨趣,亦是医治人性迷失的不二法门。据乎此,有的学者将思维转向东方文明,甚至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明的世纪。我们固不能、亦不必陶醉于这种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二十一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将是人的问题,是人性的回归和显发问题。无疑,作为东方文明主干的儒家思想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发生深刻的影响,尽管儒家思想经几千年的演变已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然而即便这些基础全被拆除,儒家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也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固有的人文关切,究其因便在于它所具有的人文睿智及其对人性的洞澈的了解。
2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心、性、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然而,对这些观念所具有的超越而内在、抽象而具体的了解方式却殊不同于西方。不容否定,现代西方学术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注重主体性的研究,主张以人为中心,重铸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以解救时代的的病痛,寻求存在的意义。这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在宏观上,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各个侧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在微观上,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无疑,这种研究方式是有意义的,但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研究方式仅仅把人当作一个纯粹的客观对象,但人的现实性并不一定能穷尽人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人性的伦理价值设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可欲的?什么是可能的?对此三问题的理解自有不同的方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纯外在和纯客观的分析方法既不能解救人性的危机,亦不能医治价值的漫荡无归。根本上,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与自己被“托付”给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神奇力量一样,皆试图以外在超越的方式来安顿自己,其结果是始终与人自身间隔一层。而儒家却通过心、性、仁的观念,把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在人之性根上统一起来,这便是儒家的“为己之学”, 即所谓“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的道德格式(moral schame)。的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儒家伦理之本质决不只是告诉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内怎样扮演一个为人所接受的角色,更不是只讲外表面子建筑在羞辱感上面的社会组织,不论其伦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作用有多大,而其核心的终极关怀却是建筑在对自己本性的理解上,即通过不断的修养功夫以彰显自己的德性,培养出负责的个人,安顿好自己的生命。无疑,这对于纠正当代世界人心放失外驰,价值纷乱迷散的现实具有直接的启悟作用。
在传统儒家看来,人之性根本上不是人所面对的一种客观事物的性质,即某物的普遍性或特殊性。换言之,我们不应当把人性作为一客观事物来研究,人性不是一种预设的客观对象,因而对人性之体认不当从外部构设一概念并假设其如何。儒家言人性,乃克就“人面对天地万物,并面对其内部体验之人生理想,而反省此人性之性之何所是,以及天地万物之性之何所是”,也就是说,人性是通过人的内在理想的实践,日新日成,以至与宇宙万物圆融合一。同理,儒家言心亦不是一客观物,而重心之主宰性、虚灵性。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儒家思想中,心是一个主脑,心之体能容能藏,贯于万物;心之用能住能行,主宰一切。就心性天关系而论,儒家主张心以承性,更以心继天,而天以生物为心,纯然是善,故心性亦无不善。
但是,儒家言心,常常是性情并用,将心、性、情统贯为一,藉此,心之无限性和主宰性便获得了内容上的落实。离性情言心,则心便会脱空悬置,故而性情是心之本,依此自然生命中之崇高价值方能彰显出来,亦即人之善性与生俱来,而对善性的把握了解端赖于当下心情的反省体验,在形式上被动的情中(此情常常为感于物事而生发)见人有自动自发的性显露其中。比如孟子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中,发现人的自然生命并进而认识到人的仁、义、礼、智之性。应当说,从情中见性,是儒家通过对心性观念的规定,把人的自然生命收摄进道德领域并进而提升之,这样,儒家言道德乃根于心,见于性,现乎情,而并非是一个纯然的知识概念。依性而生之情乃一体平铺,直上直下,在每一事件和情境中见其意义和价值。
仁在儒家思想中乃是一切价值之最终基础、源泉和归宿,但仁又不是外加的,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心呈现。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儒家言仁,当在义理上解释成每个人先验而内在地本有,是一普遍的主体性之存在,也是人之生命形态所以异于禽兽之本质,因此,仁不是一抽象的、客观外在的道德律令,仁是心之体,亦是心之用,但是这种体(Substance)又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 即外在的客观的某物。仁体之朗现在于仁之用而显发出来,即在任一具体的情境之中,“道德主体应机而当下本然地呈现”出安不安之感(如《论语》中的宰我三年问丧)和忍不忍之觉(如《孟子》中乍见孺子将入井),因此仁心乃即用而见体,即体而存用。
发于主体之心的仁是情亦是理,说它是情是指仁之觉、仁之感而言;说它是理是就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必然性而言。统合而观,这种道德上的情、意、觉、感便是人之性,故仁心、仁性情理交融,仁之感、仁之觉乃时时处处自作主宰,人之道德践履依仁心而行,便可照耀人的行为方向,并使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客观化。因此,仁心内在,即价值内在,一切德性理想之达成乃内求之于自己,同时一切成德之德目也由内在仁心而导出,是仁心外发的规范,所谓自由自律之道德乃从此出,自格物、致知乃至治国平天下都是仁心内省和推广的过程。仁心的这种内在和谐和价值的统一,奠定了孔儒的人文基础。
当代著名伦理学家A·麦金泰尔(A·MacIntyre)认为, 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普遍性及独立于任何传统的中立性,经审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格式包涵有三个要素:即a.作为现实人;b.人当他实现了他的目的时,将会成为怎样的人;c.一套德性的规则, 这套规则能使人从a过渡到b。但是,启蒙运动及现代道德哲学都拒绝了有关人性的目的论观点。这种道德理论便成了一个抽象、自主的道德主体的人身观和一堆地位不明的道德规条,道德理性却无法显露出来。〔2〕麦氏所说,自然是就西方伦理理论之大势而言。的确, 一种伦理理论若拒斥了“什么是值得人所追寻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道德就可能走向相对主义,而情感却会大发作用。不过,道德是基于主体生命的,生命诚然要理性化才能是客观的,但这种理性又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即对象性的“本体论的存有”(ontological being), 否则道德就仍然只有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 ), 而不具实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儒家言仁心、仁性, 一方面对自然生命有超越义、主宰义,即能防止人一味地“顺躯壳起念”,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生命有顺承义、涵盖义,仁之为仁,便在顺遂人之自然欲望处见。儒家言道德自律是自心上说、性上说,道德意志乃心之本质的作用,自律即是自由心之明觉活动。但是仁心又是知是知非之心,这样道德感与道德理性融合为一,体与用融合为一,形成一理性自觉之境界。
人之精神表现之规格和方向,关涉到人性的圆满和价值的和谐,然其核心处便在于人之终极关怀何所寄、何所系。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的精神方向亦复如此。精神方向专注于自然和物质,即人之心身外驰而黏附其上以至自身被遗忘,所谓精神无归,魂如飘絮者,虽有上帝高悬其上,然人人满眼是自然与物质,无心理会,所以也只成一摆设。无疑,在当今时代,“上帝退隐”的主要表现便是价值脱幅现象,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峙和紧张关系,按韦伯(M·Weber)的说法,整个西方理性化的历史便是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的历史。而科技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量化原则和效率原则又以自我膨胀的规律加强了工具理性的主宰地位,
导致“单面人”(one —dimensionalman )的出现和“生命世界的殖民化”(thecolonization oflifeworld),如此,人性终成一堆“残骸之积聚”。根本上, 西方文化只见“物心”、“机心”,未见“人心”、“仁心”,虽唱出了文明发展的动力和主调,以至鬼斧神工、能人巧匠、繁兴大用,酿成一葱郁澎湃之气象,但其根砥处却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乃是“以气尽理”之路向,换言之,此一文明和文化的精神表现之方向,是顺应自然生命之材质而来,而不是仁心的盈科焕发,不是以“富润屋,德润身”为鹄的,其结果则“不免如济慈之夜莺之啼血以死”(唐君毅《西方文化之根本问题》),而儒家思想以仁心内在为根本,自主体来发生系统,从意义来发生结构,自觉地以文化和精神理想主宰自然生命,涵润人生的各个方面,以避免生命的外在化和分裂化。这种以德性之理内在而独特地实现于个人人格的思维方向,显然具有久远而永恒的价值。
3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的身心和谐问题,人的精神归宿问题,总之,人的生存条件问题,早已不独是哲学、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而成为各门学科必须思考的问题了。人不仅是动物的存在,而且也是社会的存在,还是神圣之体现。因此,如何对人的存在问题进行全面的反省,如何成就人,化人性为德性,这是富有全球意义的跨世纪的问题,无疑,这些问题将重组下世纪文明的格局、样态和走向。
纷繁的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物欲的澎涨,核威胁的笼罩,无一不侵袭着人的生存基础。身处这样一个“利害生而人心动”的时代,如何致力于唤醒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仁心善性,点醒人的道德意识,激发人们对善的企向意志,便成为任何一位思想家义不容辞的职责。知己之可贵,即可使人独立流俗,自作主宰,从人性的疏离和陷溺中超拔出来,这对于今日只知功利可求,不知圣贤可学,只知情意我,不识道德我的风气来说,乃是一正面提撕之功夫,藉此而直下打通人圣(人而神)之途,开出文明之新气象。
孔儒以指点仁性来开掘价值之源,人惟其性善,方有价值意识之自觉,涵养、察识、居敬、致良知皆在开发本源,彰显心中之仁,使人人识得仁德无限,性量无际,乃至身心圆润。故而“中庸”上说:“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民,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以一心之发,觉得此心,便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当恻隐时自恻隐。在孔儒看来,人之仁心不仅是人成圣的基础和根据,而且与天地之德圆融不二,人心之自然流露处便是天理之所在,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者,识得仁心善性深广不竭不可胜用,则理想有所根,价值有所归,所谓“独握天枢以争剥复。”
人之仁心,至虚至灵,恒存恒觉,如何以德性涵养生命,调护人生,其吃紧处便在于存养此仁心,积极的路径是尽心知性而知天,仁心既为仁、义、礼、智之端,出入无定时,即须操存而不令其放失,人若把守得住,它便昭然亭当。人心只是一个心,但其体却甚大,所谓尽之即可与天为一。消极的功夫是存心养性而事天,存养是操存润养之谓,操存仁义礼智之心防其放失,润养自身之性之纯而不被侵害。人乃感性之存在,人之天心真性常与感性之物相接,难免生私心妄念,人若于此一无警觉,心为物役,轻则善端必亏,重则人禽无分。识得此理,并能于此研九谨微,守得牢固,便能真宰常昭,诸惑冥伏。因此,存心尽心,其精神彻上彻下,一无间隔。
孔儒自人性处开掘价值之源,是一种文明的自觉,也是历史发展意识之点醒。就个人言,这种仁性之点醒乃开启以价值理性以化成身心性命,避免物欲之嘈杂及时事之纷繁对人性完整所造成之侵害;就社会和历史言,这种仁性之点醒乃经由仁性体认的理性方式,普行于历史进程,为文明的走向把脉。孔儒主张人性本善,人本身则富有绝对自足之价值标准,“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所性也者,即是无条件的必然的绝对价值之所在,故而,依所性而发,依所性而行,便是无待于外的成德过程。人或八面玲珑或沽横绝港,或升或沉,或进或退,与人之所性不增加一毫。亦不减少一毫,性是根于心的仁义礼智,人无须顾盼于畅达通顺,亦不须计及于穷艰坎坷,顺此心而行,顺此心而动,即可成就一绝对价值之人格,所谓“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故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此所谓生色者,便是心体焕发,四端作育而至德润身之境界,亦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人格气象。
另一方面,仁心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所谓感通润物即是以道德本心和周遭的存在界相对应,把成德的土壤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统一、相一致,并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终极关怀,实现道德理想。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然而,对儒家而言,涵养自身德性生命,寻求超越的精神理想,又不是在教堂的塔顶上,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即直面并接纳人的各种生存条件,把它转化成发展个人仁性的真实根据,所谓“圣人不离人伦日用”。儒家这种独特的路径,一方面把道德生命之成长力量落于个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勇气上,而见出仁者之刚毅与不屈,另一方面即以生命之自觉来润泽存在,如此即不仅化解了自我生命之限制,同时也遍润于一切存在,使有限的自然生命转化成无限的历史生命,以至参天地,赞化育。
“我是谁?我怎样才能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我?”
这是人对自我的寻找,也是一个文明对自身的发问。
《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但丧失(forfeits)了自己的灵魂(soul),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还能拿什么东西赎回他的灵魂?”〔3〕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上帝对我们的警策。上帝是“先知”, 所以他的忧虑不会是多余的。
陆象山则云:“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与曾宅之)。陆象山是儒家,而儒家是仁知、智知,然而他的回答却有一种世纪般的深沉。
注释:
〔1〕Thomas Mc Carthy:"Introduction"to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I Boston,Beacon Press1984,Pxxxii.
〔2〕"After virtue"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and also see,Samuel Scheffer:"Review of After Virtueby A.Maclityr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xxll,No.3.( only 1983),P444.
〔3〕《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