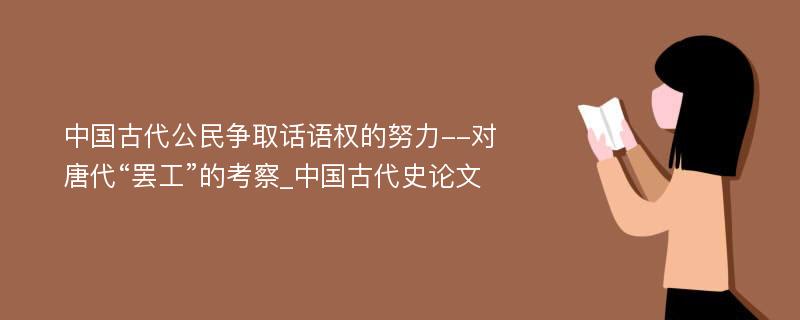
中国古代市民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对唐朝“罢市”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唐朝论文,话语权论文,市民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罢市”,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采取集体行动非正常的终止商业交易活动①。除了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罢市往往还因政治或社会因素所导致,但又通过经济手段而表现意志或意愿的行为。唐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民阶层②逐渐形成,不断壮大,有关“罢市”的记载逐渐增加,从最初的表达意愿转向更多的是为维护权益、争取话语权的有组织的举动,唐朝应该是关键的转变时期。官府的抑制、剥夺等政策和措施激起了他们的群体性抗争,从“罢市”这类非暴力抗争,演变成大规模的民变,往往采取群众性的非武装暴力活动。这一历史过程是商人、市人以及后来形成的市民阶层在维护经济权益中自我意识崛起的表现,也是他们争取更大程度的话语权的体现。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唐朝出现的“罢市”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市人),自秦朝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后,拥有的自主话语权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桑弘羊这样的大商人出身而执掌财政,出任汉武帝朝的大司农,也并非是代表商人群体的利益说话和行事。抑商、限商、轻商、贱商的种种政策和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长期徘徊不升。不过商人群体并没有沉默不语,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意愿以达到维护自身的权益目的,“罢市”正是市(人)民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一、“罢市”:民意的伸展与价值判断
唐朝以前,由于官方规定的商品交易活动被限制在“市”区,因此商人又被称为“市人”。此外,市人也包括在市区内从事手工业生产和销售的亦工亦商的工商业者。工商业者的罢市行为很早就出现了,不过,引起“罢市”的缘由早期很多却与经济权益受损并无直接关系。
《管子》中,已经有关于“罢市”的记载,“(齐)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丝纩之贾贱,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请以令沐途旁之树枝,使无尺寸之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对曰:‘途旁之树未沐之时,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父兄相睹树下,论议玄语,终日不归。是以田不发,五谷不播,麻桑不种,玺(四库本作“蚕”)缕不治。内严一家而三不归,则帛布丝纩之贾安得不贵?’桓公曰:‘善。’”③。《管子》中提到的“罢市”,显然指的是放弃经营与交易活动而沉迷于享乐的行为,与本文准备探讨的主题似乎无涉。但是,也说明,“罢市”举动会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后世对这类的“罢市”有更多的记述,如唐咸通年间(860-874),懿宗为爱女同昌公主送葬,场面奢华,声势浩大,“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④。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周汉国公主得旨,偕驸马都尉杨镇游览杭州西湖,泛舟湖上,“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⑤。这里的“罢市”,目的是为了看热闹,商人和市民都顾不上做买卖了,其实是烘托一种盛大、热闹的场面。
由于“罢市”上升到一种代表民意的价值判断,于是当时很流行的墓志铭、神道碑、祭文、行状等文章中常常用“罢市”一词表达传主深受民众爱戴的程度。如张九龄《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⑥、李邕《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⑦、王勃《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⑧、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⑨、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⑩等,都用“罢市”来歌颂传主。这里用“罢市”作为修饰用语,只是表达一种“民意”,是否市民真的对传主的离世表示惋惜悲痛,是否有“罢市”之举倒是其次了。我们并没有见到史书上对上述文章中的“罢市”有专门记载。《旧唐书》上出现了唯一一次“罢市”的记载,是市民为经济利益受损而举行的“罢市”(11)。《全唐文》中,共计出现22次“罢市”的词语,有21条是使用在为已离世人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中。
唐人的诗歌亦如是。岑参做《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之一》:
盛德资邦杰,嘉谟作世程。门瞻驷马贵,时仰八龙名。
罢市秦人送,还乡绛老迎。莫埋丞相印,留着付玄成。(12)
挽歌是为裴冕而作。
雍陶的《哭饶州吴谏议使君》:
忽闻身谢满朝惊,俄感鄱阳罢市情。(13)
诗中描述的“罢市”场景,我们同样在史书中没有见到相应的记载。从确有其事的行为到被使用为溢美褒扬的修饰词语,说明“市民”一词具有广泛性,成为城市民众的代名词。他们的向背和价值认同已经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
二、“罢市”:表达政治取向与维护经济权益的方式
唐朝以前,记载市人通过集体“罢市”的行为表达某种意愿,与经济利益有关的很少,比较常见的是集体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目前见到比较早的是西晋的一条材料。据《晋书》记载,西晋羊祜,正直忠贞,嫉恶如仇,刚正清廉,“南州(14)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15)。这是用停止正常的交易活动,市民集体表示对他离世的哀悼悲痛之情,而之所以悲痛,似乎没有记载他给市民谋取了什么利益,只是因为他疾恶如仇,刚正廉洁,因此,罢市表达的应该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东魏元悰“以兴和四年(542)十一月廿日薨。工女停机,商人罢市,设祭满道,制服成群”(16)。唐朝史书中,为表示对去世某人的哀悼而举行“罢市”的记载更多了。唐朝陈州人赵珝,世为忠武军牙将,昭宗朝官至检校太傅、右金吾卫上将军,因病去世,“陈人为罢市”(17)。与这种自然死亡而引起的“罢市”相比,非正常死亡采取的“罢市”行为,往往更带有政治倾向性。唐末,盘踞四川的王建因忌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有勇略,得众心”,于是,命亲随“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18)。这是用“罢市”来表示不满与愤懑之情。
唐朝后期,市民阶层(19)逐渐形成,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也日益接触到核心问题——经济权益,集体罢市就成为他们维护经济权益的主要方式。
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叛乱,朝廷连年用兵,财政窘迫,掌理财政的官员“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于是决定通过借富商钱以充军费,约定罢兵后还钱。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但不想远没有达到预定征敛的数额,就“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20)。于是市民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是全城“罢市”,二是成千数万人相率遮宰相卢杞马“哭诉”,迫使德宗停止征收。由于“宿师在野,日须供馈”。不久,又有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请税间架、算除陌(21),主要被征敛的对象仍然是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没过几个月,发生泾原兵变,叛军进入长安,竟然在市区对狼狈奔窜的市民喊话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22),足见民怨之深,这显然是直接指向官府与市民群体矛盾的核心问题。
唐朝普通市民表达意愿的方式,不仅限于“罢市”,史书上还记载了他们采用过“拦邀诉求”、聚众喧嚣、“街议汹汹”、街中传呼、匿名榜贴、集体“巷哭”、“率钱雇百戏”、街衢诟骂、投掷瓦砾等衍生方式。
如,唐懿宗因爱女同昌公主病逝而迁怒于医官,宗族枝蔓300人收于牢狱,宰相刘瞻因进谏获谴贬黜远州,后量移入朝,史载:“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23)。虽然没有“罢市”,却用各商家集资“雇百戏”方式,明确表达了市人的好恶。再如,五代后晋,东京(开封)市民对投降契丹的杜重威,极为不齿,再加上他曾重敛百姓,税外加赋,“既至东京,驻晋军于陈桥,士伍饥冻,不胜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为市民所诟,俛首而巳”(24)。还可以举任延皓的遭遇为例,他因“业数术风云之事”而得宠于后晋高祖,曾在交城文水令任上聚敛财贿,因其诬告,文水县十数族被诛。晋高祖驾崩后,任延皓获罪配流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掷瓦殴骂甚众,吏人救之仅免”(25)。
不可避免,市民也有被利用的时候。唐末,昭宗曾与朝臣谋划很想除掉盘踞陇右的李茂贞,李茂贞遂“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先后拦住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和入朝宰相崔昭纬、郑延昌肩舆,力求彰显“民意”,阻止朝廷发兵,并且采取“乱投瓦石”的过激行为,迫使二宰相仓皇逃匿民家避祸,狼狈的连堂印和朝服都丢失了。(26)
宋朝以后,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继续成长,他们也越来越多的用“罢市”方式表达意愿,维护权益。仅举几例:北宋徽宗朝,童贯宣抚陕西,当时长安物价踊贵,童贯有心抑制物价,负责财经的官员曲意逢迎,规定市场物价一律降低40%,违者重罚。商人被迫以罢市加以抵制。(27)金朝贞祐三年(1215),因军费开支庞大,纸币“交钞”不断贬值,官府实行限价措施,商人为之罢市。元光年间(1222-1223),因钞法紊乱,屡次更改,银贵钞跌,民间交易多用银,官府于是规定买卖在银3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3两以上,三分之一用银,其余用纸币,导致“市肆昼闭,商旅不行”(28)。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以讨伐盗匪为名,江州宣课司“税及民米”,于是米商“避去”,民皆“闭门罢市”(29)。清朝,有些地方官在离任或“蒙冤”被劾时,民众往往借保留为名,“鸣锣聚众,擅行罢市”(30)。
不过,由于没有深入研究,无法展开,只能暂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线索。
三、官府的应对与对策
历朝应对影响到社会稳定“罢市”的对策大概有几种方式:
一是听之任之,回避矛盾。唐宋时期,市民群体很活跃,“罢市”及衍生举动往往能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或起到调整措施的效果。法典中,也没有对“罢市”行为的具体惩治条文和举措。事态激化时,“罢市”的衍生产品“拦邀诉求”、聚众喧嚣、“街议汹汹”、街中传呼、匿名榜贴、集体“巷哭”、“率钱雇百戏”、街衢诟骂、投掷瓦砾等,往往成为市民自己开辟的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但在民情失控的状况下,有可能引发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动乱,也有可能被居心叵测者所操控,或酿成暴乱。其实,被迫“罢市”及衍生举动也损害了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朝廷的统治。
二是禁止、严惩。唐朝的法典中,我们没有看到针对“罢市”行为的律条,不过,《唐律疏议》卷27《杂律》有这样的条文:“诸在市人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31)应该是针对在公共场所闹事惊扰者的律文。清朝则正式将“罢市”及衍生举动列入法律禁止的条文中,据《大清会典则例》载:雍正二年(1724)“议准地方,如有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殴官等事”,都要严惩,否则有关官吏并以“溺职例革职”(32)。清朝政府严禁地方民众借“罢市”等方式对朝廷任免贬黜施加压力,否则“加倍治罪”(33)。按《大清律例》,对“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34)。由此可以推知,“罢市”与它的衍生产品已经到了愈演愈烈的程度,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民的矛盾已经纳入刑事案件的范围了,大概已经按“敌我矛盾”处理了。虽然也有缓解、疏导的举措,但往往多采取回避矛盾的做法,甚至手足无措,于是严禁、严惩成为统治者治理“罢市”的主要手段。从回避、疏导演变为严禁、严惩,政府对应政策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在成长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障碍。
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在城市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政府颁发和施行的很多政策和举措直接关系到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无奈之下的“罢市”,就是一种有形的利益诉求方式。争取能在更大限度上自由表达意愿,争取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力度和意识增强,更积极参与城市社会建设,影响政府政策、决策,表明了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和崛起。
如果说,唐朝的“罢市”还是偶然的现象,明朝大中城市屡屡发生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城市居民为自身利益公开持续抗争的活动,则是社会转型期,官府与市民、商人与工匠矛盾激化的表现。如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爆发的一系列反抗矿监矿使的斗争,酿成全国性的民变。明清两朝手工工匠的“齐行叫歇”,则是“商匠冲突”中,弱势一方——工匠群体,有组织的抗争运动。不仅矛盾和冲突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且具有了行业特点。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力量的成长,商业、手工业行会组织的规模化,“罢市”活动的频繁与激烈反映出市民为了争取话语权,在控制与反控制中,从无序无组织的抗争向有组织转化,从无固定利益群体向形成相关利益群体转化的历史趋势。(35)
同时,从“罢市”到“罢工”,愈演愈烈的市民抗争举动表明原有的社会调节功能其实已经滞后,城市管理体制的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如何走出回避、严禁和镇压的困境,是传统社会的政府面临的难题。
注释:
①中国古代还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举措——“徙市”,即官府为某种目的而做出暂时停止市场交易活动,但如有临时紧急需要,则可在坊里进行交易,称之为“巷市”。也有徙市于“野”的说法。“徙市”的原因:1、丧礼的一种,“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市”(《礼记》);2、天象异常(往往与彗星的变化有关);3、自然灾害发生(主要是旱灾,属于救旱的方法之一);4、火灾;等。“徙市”与“罢市”虽然都是停止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但从性质上显然不同。
②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虽有不同说法,但都不大明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普遍兴起。唐宋时期应该是市民阶层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市民”成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城市居民的统称或泛称,应该是唐朝中叶形成的。“市人”这种称谓,早就出现在各种史籍中,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明清仍在沿用。在拙文《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待发)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凡用“市民”的地方,就不再强调其时间性了。关于中国古代市民研究概况,吴铮强《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有比较系统的综理。有关论著,请参见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江汉论坛》1991年第8期);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涉及了市民的问题。郭正忠在《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一文中认为:市民仅仅是“坊郭户”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成分或职业构成,纯为工商业者,至少绝大多数是工商业者,而不包括工商业者之外的其它城居人口——诸如官绅军吏之家”(《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第36—37页)。其说可以商榷,市民绝大多数是工商业者,或主体成员是工商业者,应该比较妥当。
③黎翔凤:《管子校注》卷24《轻重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97页。
④(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6页。
⑤(宋)周密辑:《武林旧事》卷3《西湖游幸》,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17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9页。
⑥(唐)张九龄:《曲江集》卷17《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36页。
⑦(唐)李邕:《李北海集》卷5《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39页。
⑧(唐)王勃,(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20《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⑨(唐)独孤及:《昆陵集》卷9《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0页。
⑩(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918,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4833页。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15页。
(12)(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0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93页。
(1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518,第5915页。
(14)西晋南州,治南川,今四川綦江。
(1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4《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1页。
(1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东魏《王讳悰(元悰)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89《赵级传附子赵珝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76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3《唐纪七九》“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81页。
(19)关于中国古代市民的定义及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拙文《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待发)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关于中国古代市民的研究还可参见吴铮强《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江汉论坛》1991年第8期);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著和论文也都涉及了市民的问题。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等。
(2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2《食货二》,第1352页。
(2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35《卢杞传》,第3715页。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35《卢杞传》,第3716页。
(2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八》“唐僖宗乾符元年(874)”条,又,“考异曰:《玉泉子·见闻录》曰:初,瞻南迁,无问贤不肖,一口皆为之痛惜。殆将至京,东西市豪侠共率泉帛,募集百戏,将逆于城外。瞻知之,差其期而易路焉。”第8170页。
(2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9《杜重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35页。
(2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8《任延皓传》,第1431页。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唐纪七五》“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条,第8447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卷317《钱惟演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51页。
(28)(元)脱脱等:《金史》卷48《食货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0页。
(29)(明)宋濂:《元史》卷162《史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01页。
(30)《皇朝文献通考》卷197《刑考三·严地方士民保留离任官员之禁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4页。
(31)(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27《杂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4页。
(32)《大清会典则例》卷27《吏部·考功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0页。
(33)《皇朝文献通考》卷197《刑考三·严地方士民保留离任官员之禁奉》,第524页。
(34)马建石等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24《刑律·盗贼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页。
(35)从政治学的视角考察,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往往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纽带,这就是社会。中国古代国家与下层民众之间,缺乏健全完善的“社会”层面,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愈加频繁(某种程度上的“维权意识”),市民的抗争方式也逐渐有组织化,这种“维权”行为势必影响到统治的稳定,于是限制和禁止的法律就相继出台。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话语权论文; 汉朝论文; 旧唐书论文; 社会论文; 工商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