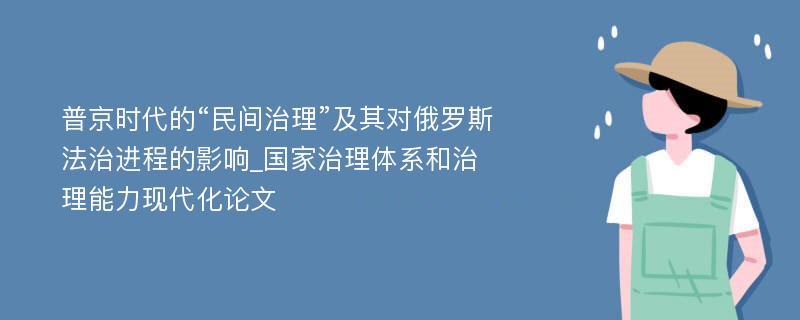
“普京时代”的“民间治理”及其对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其对论文,法治论文,进程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作为多元社会发展核心标志的民间组织,开始在俄罗斯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到2005年已达60万之多,其活动范围日益扩展,能量不断增大,成为当下俄罗斯“民间治理”机制运行的主力军,并对其转型秩序重建和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普京时代”的民间组织勃兴及其问题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力图通过“休克疗法”来加快私有化进程,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私人自由、权利和利益获得了肯定,从而使民间组织开始浮现并与国家相分离,开始了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转型。①政府也开始着手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②在这种政策环境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不断扩大的过程。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宣布继续忠于俄罗斯宪法的各项原则,并逐渐认识到“第三部门”的重要性,他强调民间组织发展对民主的推进是非常重要的,主张在“第三部门”团体和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俄罗斯民间组织也随着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截至2002年1月1日,在俄罗斯至少有589228个在册非营利组织。③2004年普京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他向全国发表致辞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成果将得到保障。而且我们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我们将巩固多党制。我们将巩固公民社会,竭力保证媒体言论自由。”④2006年,俄联邦国家杜马社会部发布了《2006年公民社会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10月1日,在俄罗斯登记注册的非商业组织有665623个,与2001年比,非商业组织数量增加了34%;在俄罗斯平均每1000个居民中,有2.5个人是正式登记的非商业组织的成员。 梅德韦杰夫上台后,也十分重视俄罗斯民间组织的培育,充分认识到它们对社会发展及民主法治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发展民间组织同反腐败、建立透明的司法体系紧密相关,主张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真正的多党制,以实现政治民主化。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将继续支持那些帮助国家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将修订法律旨在简化那些从事公益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非营利组织的注册程序。”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2009年下半年《非营利组织法》再次得以修改,简化了非营利组织的注册程序、减少审查报告、限制执法官员的“胡作非为”,不允许国家部门任意检查他们的税务等有关文件。此外,还于2009年设立总统专项基金,为非营利组织提供120亿卢布资助。2012年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接近尾声,俄罗斯再次出现了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对国家有害的讨论,梅德韦杰夫针对这一情况,在俄罗斯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认为非营利性组织危险,必须加大对其监督力度的想法是不严肃的。这些措施使得非营利组织获得“自由化”发展,在他执政的四年期间,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2012年“王者归来”的普京在对民间组织进行严格执法管理的同时,也重视疏导利用,签发了《关于2013年保障国家支持非营利组织完成社会意义项目和参与发展社会制度》的总统令,向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参与社会制度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注资30亿卢布。 由此可以看出,与西方民间组织的形成壮大历经百年相比,“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罗斯民间组织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瞬间壮大。然而,俄罗斯的现代化、民主化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化。相反,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轨迹,俄罗斯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东方色彩更浓,因此在现代化主导趋势中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与传统、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使它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⑥而客观的分析也会让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同样不可能是西方的翻版,俄国学者К.Г.霍拉德科夫斯基也承认,俄罗斯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公民社会,⑦俄罗斯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也有其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特点。 首先,“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民间组织的成长具有监护性。众所周知,西方民间组织的孕育成长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并最终成为其民主法治体制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石。而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国家被视为“文明的支柱、社会完整及存在的保证、整个生活的组织者”⑧,在俄罗斯更多的是国家吞并社会的状态,并没有民间组织的传统。苏联解体后,民间组织才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到了普京执政阶段,采取了自上而下建立“可控的民主”的策略,倡议组织“公民论坛”,广泛吸收和容纳社会组织,与政府管理部门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颁布《政党法》完善相关机制和法律基础;成立俄罗斯联邦社会院采纳民意,建立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通过《非政府组织法》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树立“俄罗斯新思想”,提倡“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社会互助精神”。可见,俄罗斯民间组织是在国家的积极参与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使得民间组织的成长壮大处于国家权力的监护之中,国家对其干预过强,甚至影响了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民间组织对国家的制衡就难免成为一种奢望。 普京对于发展民间组织所做的努力,似乎证明了俄罗斯政府参与引导民间组织正是发展中国家巩固民主成果、实现其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民间组织的不断壮大,政府就会出于政治稳定的考量而抑制民间组织的自由特性和抗衡权力的内在要求,从而对民间组织的成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普京时代的一系列举措(如整合政党、打击寡头、控制媒体等)在稳定深化秩序和规范公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免产生了一些抑制公民社会自主自治能力的消极影响。”⑨ 其次,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民间组织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俄罗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根据2008年1月的民调显示,俄罗斯31%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添加应季服装鞋帽,16%的家庭缺乏足够的收入购买食品,10%的家庭将3/4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俄罗斯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10%最富裕者的收入高于10%最贫困者15倍”。⑩俄国著名政治家、改革者斯托雷平曾经指出“贫困在我看来比奴隶制更坏……对这些人谈论自由是可笑的。首先要使他们的福利水平达到那种至少是最低的限度,即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所需要的最低的满足”。面对严重的贫富分化,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均表示将继续推进积极的社会政策来缓解严重的社会分化,最大限度地让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但不平等和贫困直接影响到政治文化和民间组织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因为穷人每天都要面临生存问题,很少被纳入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来。这一国情使得民间组织的勃兴主要集中在少数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而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度日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人际关系等还处于“前公民社会”状态。由此,俄罗斯民间组织的成长勃兴由于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 最后,俄罗斯民间组织的价值观具有非主导性。在西方国家,民间组织构成了民主法治的社会根基,契约、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价值诉求也成为其思想文化的源头。而在俄罗斯,特别是普京总统执政阶段,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经济和稳定社会环境,实行了一系列以“强国理念”为核心的执政方针,他强调:“强大的国家政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11)普京的“强国理念”切实地提升了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改善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使民众更加相信,只有强大的国家和强有力的国家控制才能够切实保护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确保国家稳定。因此,人民支持普京的中央集权控制,俄罗斯国家的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国家的集中控制之下,权力本位、国家本位重新抬头,这使得广大公民的自由理性的法观念和现代民主法治的精神信念受到冲击,这恰恰与民间组织的主流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的内在冲突。由于俄罗斯的民间组织是在国家监护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民间组织的价值观受到正统价值观的统领,还处于非主导的状态。 二、俄罗斯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 尽管俄罗斯一直寄予民间组织以很大的法治希望,但是,与西方几百年的民间组织发展历史相比,俄罗斯的民间组织毕竟是“瞬间”出现的,而且是在国家快速转型中自上而下来推动和重建的,又有特殊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纠缠,因而它就必然会形成十分浓重的、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性格”。他们自己也承认,“创造西方文明的,是具有一定性格的民族,这是他们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其他民族创造的,则是符合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存在的历史条件的、其他类型的文明”。(12)正是在这种瞬间出现、快速转型、国家推动、传统文化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发展并不是理想化的,而是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难以承担起人们所过高期望的法治重负。 其一,“西化”的民间组织发展期盼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内在张力。俄罗斯解体后,“西化”的民间组织情结得以快速释放,并致力于“西化”的发展道路探索和推进。然而,今天的西方民间组织是几百年漫长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以来多元权力分割制衡的政治背景下孕育成形的,(13)这一背景是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所不具备的。因此,俄罗斯社会转型期中的民间组织发展,尽管在形式上走的是一条“西化”之路,但承载其民间组织制度体系的基础却无疑是“本土”的,特别是仍然受旧有时代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习惯所支配。传统的村社意识和依附性的个性使得俄罗斯人个体自主独立意识发展得不充分,一直依赖于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缺少民间组织生成的前提——自由的人——制约了俄罗斯民间组织的生成。此外,俄罗斯民族的专制政治、独裁体制的传统较为浓重,从基辅公国到莫斯科公国,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超级大国,国家观念始终以绝对形式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物质是由其‘国民信仰’或宗教决定的。对俄国而言,‘俄罗斯人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种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思想’”。(14)俄罗斯人需要依靠国家观念实现自己的民族理想,“追求强大,志在问鼎地区乃至世界的霸权。在俄国1000多年的历史上,俄国人都在百折不挠地向大国地位冲击,都在努力实现强国之梦”(15),在面对美国等北约力量的威胁时更是如此。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国家主义思想,依然在人们心中具有很大的传统惯性和深刻影响,它与西方那种制衡国家权力、多元自由发展的公民社会理念必然产生严重的内在张力,从而使得俄罗斯“西化”民间组织的期盼受到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层纠缠,甚至发生异变和畸形发展。 其二,“休克疗法”导致了国家控制能力与社会自律能力的双重衰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力图通过“休克疗法”来加快私有化进程,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是,这一瞬间转轨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1999—2000年期间,总犯罪率就增加了2倍,2001年一年记录在案的犯罪就超过300万起,发生32000起谋杀,大约25000起致人重伤的案件,30000多人失踪,每4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有前科。现在,“社会底层”的居民有1400万人:400万人没有固定住所和固定职业,300万乞丐,400万流浪儿童,300万妓女,(16)社会自律水平严重下降。与此同时,国家也面临着具有各自特殊利益主张和要求的诸多利益集团的压力,国家控制能力随之迅速退化。这时,人们便开始反思和怀疑转型国家私有化运动曾做出的承诺,并吁求国家发挥更积极的能动作用。于是,俄罗斯新政府从1996年起,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战略进行调整,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扭转过度经济自由化倾向,放慢私有化速度,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其实质是恢复国家控制能力,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努力。(17)然而,强化国家控制能力,就会使民间组织的自由发展空间受限,而国家控制能力衰微,在社会发育不成熟、自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又会加剧了社会失序。因此,如何建立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成为一个战略难题。面对国内外日益高涨的要求俄罗斯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呼声,普京提出了“可控民主”。而“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建立新形式的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有利于恢复国家控制能力和建立社会秩序,但其中一些措施(如控制媒体和舆论等)客观上会阻碍民间组织的发展。(18) 其三,民间组织发展“空心化”和“依赖性”倾向明显。众所周知,民间组织是多元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对话平台,是多元社会发展状态的核心指标。尽管俄罗斯民间组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其成员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成员的社会阶层分布也不够多样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空心化”状态。另一方面,俄罗斯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特别是很多民间组织常常需要依靠国家的支持以及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援助。事实表明,俄罗斯大多数有名气的民间组织都是依赖于外国的援助,长此以往会使得民间组织附庸于西方势力。面对这一情况,普京曾指出:“一些国家拨巨资支持俄境内某些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动且都涉及敏感方面,我们十分清楚出资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俄政府将严禁外国对俄境内的政治活动进行资助”。为此,为防止西方势力渗透和影响,国家就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先后通过了《社会团体法》和《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19)予以严格规制。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再次对《非营利组织法》进行修正,细化非营利组织类别,明确违法行为罚则,还特别增加了外国代理人类别,以约束和严查一些非政府组织利用外资充当“外国代理人”介入俄罗斯政治。2013年4月9日俄司法部宣布,要求法庭关闭或暂停近9000个非商业组织的活动,另有5610个组织面临罚款。这样,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又会面临国家权力的威胁。可见,民间组织的这种“空心化”和“依赖性”倾向,无疑会对俄罗斯多元社会的自主性和动员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从而抑制多元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其四,不健全的政党体系与民间组织之间形成了难以架通的鸿沟。俄罗斯是在快速转型中建立起民主代议制的,但民主代议制需要政党、民间组织、利益集团等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承担起中介和桥梁功能才能良好运行,从而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诉求的过滤、对话、协商与整合。而俄罗斯多元化的政党体系是在发育不成熟的基础上“瞬间”建立起来的,为了发挥政党效能和实现有序民主,国家通过立法不断加强对选举进程的控制,提高了政党参与国家杜马的门槛和要求,并主动承担起建立联邦议院的责任,其目的是“通过代议机构加强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组织间的联系”。(20)然而,俄罗斯的政党不像西方式政党那样能够代表某一阶层或利益,他们的多数政党都是由既有的政治精英所创建的,他们往往自己在政府内部和经济寡头中寻求支持,并不需要各利益团体太多,因而国家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确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政治思想和决定每位公民的未来生活的政治文化,这不仅使大部分政党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也形成了政党体系与民间组织的重大鸿沟,从而使民间组织很难获得进入联邦议院的途径和渠道。这样,多元社会与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联系就发生了某种“中断”,多元社会的真实诉求也就难以涉足政治对话和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制约多元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功能发挥。 其五,民众参与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足。民意基金会2001年6月对15000名俄罗斯城市和乡村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5%的市民认为民间组织是积极的,73%的市民不愿意为任何民间组织工作,愿意为民间组织工作的只有15%。(21)俄罗斯人对制度的信任度也不高,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参与民间组织工作的人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22)目前,俄罗斯民间组织的覆盖率还不到1%。尽管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努力吸引公众的关注并加强对青年进行社会政治的教育工作,激励年轻人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俄罗斯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法观念同样较为薄弱,公众还没能形成现代的民主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普京时期推行的以“强国理念”为核心的执政方针使俄罗斯的一切又都重新回到了国家的集中控制之下。这就会对自由理性的法观念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孕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不利于俄罗斯民间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制约着俄罗斯的民主法治进程。 三、“民间治理”不足及其对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影响 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发展有其特有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从深层文化来讲,“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23)当前俄罗斯民间组织发展所遭遇的这些困境,无疑和这种深层的文化冲突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民间治理”的动力不足和机制迟滞,进而对俄罗斯的转型秩序重建和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民间治理”与法治发展道路的“俄罗斯化”。伴随着俄罗斯快速的根本性转型,他们认识到,“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必须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和巩固,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的过程”。(24)然而,一些社会问题随之也暴露出来,人们发现原来所期盼的一蹴而就的民主政体,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一种低层次性、不成熟性,甚至导致国家权威失效和民间秩序混乱。于是就开始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困境进行反思,甚至认为“在俄罗斯,既没有‘自由的人’,‘也没有独立于国家制度化的公民社会’”。(25)这样,力图通过多元社会来实现对国家的制衡就难免是一种奢望,走西方式的道路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而,必须探索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和国情的民主法治发展道路。特别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仅仅依靠社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同时,俄罗斯为了实现其经济的持续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并保障国家主权和保证“大国”地位,必将继续奉行国家主导的社会控制模式。正如普京总统所说:“在历史范围最短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但这种模式会暂时性地牺牲以公民自治为依托的社会调控体系的建立,制约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改革的进程。这种激进式改革暗藏的危机是,当自由与民主突然降临时,人们又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运用。也就是说,“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化的发展的可能”。(26)因此,政府只有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适当改造本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规范本国范围内的民间组织发展,健康、良性的多元社会才能产生;也才能遏制国家与社会双重衰弱的趋势,实现二者的“双强”和良性互动发展,从而建立民主基础上的、以法律为支柱的民主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活,建立以公众自治为依托的社会调控体系和“民间治理”目标才能逐步实现。这就是说,建立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码的法律秩序,恢复已丧失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恢复同犯罪尤其是同贪污受贿的斗争,过渡时期更是如此。(27)这样,就决定了当下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形式与民主法治发展道路必然是“俄罗斯化”的。 其次,社会信任缺失和秩序危机。面对俄罗斯民间组织的“空心化”状态,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存在良好的自治组织及组织网络……将严重影响俄罗斯民主的品格”(28),而这一状况并不是今天造成的。其实,“布尔什维克革命早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前爆发,新的苏联政权在落后的文化教育处境中生存,大部分国民缺少相应的政治修养,这必然导致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连家庭内部关系也包括在内的领域的强力干预”。(29)于是,正式的公共领域在苏联时期就被高度政治化,并且处于国家的管控之下。人们不能公开地表达想法,社会生活也基本集中在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圈子中,这样便导致了小网络内部利益整合程度高,成员之间普遍信任、互惠合作、程序规范理性化程度低,正式制度在网络内部问题的处理上常常不被重视、也不起作用。苏联解体后的迅速转型,各类民间组织广泛兴起,也带给人们以很大的动力和希望。然而,它们“空心化”的状态随之出现了,社会整合信任度低、合作精神差的文化传承仍没有太大改观。尤其是使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会非常薄弱,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不足,参与公共生活的水平不高。因此,政府放松管制后,民间组织的自律管理无法顺接,不仅“民主秩序没有出现,相反,经济活动混乱,犯罪猖獗”。(30)这就不仅会危及社会信任和社会秩序,也使得民间组织难以担当起制衡国家权力扩张、保障多元权利诉求、推进“民间治理”、建立社会自律秩序的使命,民间组织的法治功能也自然会受到一定的消解。因此,克服民间组织“空心化”状态,强化其动员能力和参与水平就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 再次,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由于俄罗斯转型后致力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精英和经济寡头,他们对国家的财产、利润再分配过程、政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等都有着很强的操纵能力。而民间组织与政党之间又出现了重大的鸿沟,这样,就使得民间组织无法、也无能力参与太多的政治生活、充分表达民主意愿,致使在对国家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利益主张等方面难以有更大的作为,“民间治理”机制的迟滞、乃至缺位状态就在所难免。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25%的居民属于中等收入阶层,1%的居民属于富有阶层,70-75%左右的居民属于贫困阶层。(31)大多数俄罗斯人变得同样的贫穷,只有高度依赖国家。他们所关心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公共性活动,又无法借助所属的民间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表声音,因而就日益被边缘化、贫困化。这样,表面上颁布了民主化、自由化的宪法,但“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常常被忽略或侵犯。”(32)这样,“民间治理”机制就难以有效形成,法治秩序的建立也就步履维艰了。为此,俄罗斯人曾在几年间就经历了“渴望民主”——“厌倦民主”——“拒绝民主”的心理巨变。(33)这就意味着,弥补民间组织与政党的鸿沟,畅通底层民众的民意表达渠道,将成为俄罗斯民主法治进程的关键。 最后,立法司法难以受到监督和控制。近代法治产生于西方,它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自由主义精神。但是,西方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个人本位的,这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国家观念与追求整体性的特征有本质上的差异。对于习惯了追求整体性的俄罗斯人而言,个人主体性意识是不明确的。因此,俄罗斯人一直依赖于一个集团、一个群体,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外在的国家权力身上,好像没有这个外在权力,就会茫然失措。这种惯性思想构成了俄罗斯人参与意识和法治观念不足的重要根源,并深深制约着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不强,不积极投身公共生活,民间组织就不会发达,“民间治理”也就缺少社会基础。这样,个人及群体自然就很难在庞大的国家权力和经济寡头面前表达、捍卫利益诉求和权利主张,而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强,护法精神不足,立法和司法活动就很难受到民众的监督和控制,民主法治进程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培育民众的参与精神和法治观念,“这不仅是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市场与私有制,也是教育公民增强公民意识,关注正义。”(34)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和控制立法和司法活动,确保法律的正义性和公众性,而不是国家权力和经济寡头的独断专行,从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为此,他们开始强调,“为了形成法治国家,在整体上需要高水平的一般文化,而从局部上则需要高水平的法律文化”。(35)这将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四、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建构及其借鉴意义 俄罗斯民间组织虽然正在积极地发展,但是客观上依然弱小,不能发挥对强大国家系统的制约作用,其“民间治理”功能也较为有限。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俄罗斯现实的分权和制衡体系,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俄罗斯转型中的重大问题。 总的看来,俄罗斯不可能走从“对抗国家”到“与国家合作”的欧式发展道路,而是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形成一种从“国家监护”到“与国家合作”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中,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仅仅依靠社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这种情况下,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现阶段的俄罗斯,依靠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加快培育民间组织是更加可靠的途径。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所说:“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排”。(36)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的民主法治进程更多地体现着价值要求和国家主导价值取向的兼容与互动,而民间组织不断上升的权利和自由诉求自然会为公权力设下行动的边界,但其制约方式和手段并不是对抗性的,很多时候则是妥协式的、平衡性的,渐进性的。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法治秩序必然带有国家规划的影子和相对较多公共利益的考量,一些反映民间组织发展共通性要求的制度设计,还可能会受到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价值判断的限制,至少在当下可能是这样的。这种状况的不足是会对民间组织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形成制约,也限定了其“民间治理”的空间和功能发挥。但它的益处也显而易见,即有利于防范民间组织初期发展的非理性因素泛滥和快速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 民间组织是法治秩序的关键部分和重要基石,它的妥协性与平衡性必然会强化俄罗斯法治秩序的建构取向,从而形成一条有特色的俄罗斯法治道路。这种道路也许并不能过快地实现法治的普世价值和目标,但却能更稳妥、更切实地推进俄罗斯的法治进程,并能够形成俄罗斯的特有模式。换言之,俄罗斯的法治进程固然不能脱离世界法治进程的主流,但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西方法治进程亦步亦趋,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开放的进程;而且传统与现代也是截然分开的。“在今天没有绝对的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模式。美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都有自己所理解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37) 俄罗斯作为一个典型性的转型国家,其民间组织发展困境、“民间治理”的水平及其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影响,对我们无疑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和启发价值。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东方专制主义”历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道路和快速转型等等,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反思的一面镜子。事实上,尽管民主法治产生于西方,但它却是不可能复制的。而诸多西方国家并没形成、也不可能有一条普适的道路,反而呈现的是多样性、动态性、非模式化的发展路径。(38)中国的法治建设同样既要借鉴西方又要立足本土,也需要强化民间组织的公信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需要塑造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法治精神。特别是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更要吸取俄罗斯“西化”的经验教训,着力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而这一根基的培育和构筑又离不开国家的积极作用,需要“注入经验理性和建构理性、本土与移植、承继与创新的双重性”。(39)这在当下“法治中国”建设中更具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俄]别利亚耶娃:《中产阶级寻踪》,叶玉珍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 ②1993年俄罗斯宪法的确立为公民的自由和独立团体的权利提供了保障。1995年俄罗斯联邦杜马通过了政治团体法、慈善活动和组织法、非政府组织法和地方自治法,这些法律确立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③参见张海东、董经政:《俄罗斯社会转型中公民社会发展的困境》,《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2期。 ④人民网:《普京当选总统后向俄公民致词答记者问》,2004年3月16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4549/2392117.html。 ⑤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Федералъ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2 ноября 2009 года.Москва,Болъшой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дворец.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5979。 ⑥[美]亨廷顿·塞:《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0页。 ⑦Холодковский К.Г.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ознание/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8 г.-ст.5-6。 ⑧Баталов Э.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ътура России сквозъ призму civic cultura//Pro et Contra.2002.№3。 ⑨景维民、张慧君:《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 ⑩新华网:《透视“梅普组合”引航下的俄罗斯未来》,2008年3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15/content_7793278.htm。 (11)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Федералъ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Ф.Опубликсвано в“Российской газете”от 17 мая 2003 г.,No 93(3207).(http://www.rg.ru/Anons/arc_2003/0517/1.shtm)。 (12)[俄]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13)参见马长山:《国家、公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61页。 (14)宋德星、许智琴:《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影响》,《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1期。 (15)王宇博等:《骁勇俄国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6)[俄]В·Я·叶利梅耶夫:《还是人类社会》,载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17)马长山:《俄罗斯的公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18)2000年,俄罗斯增持公共电视台股份(达51%),结束了别列佐夫斯基对该台的控制;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也利用债权控制了原属“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卢克石油公司对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另一家电视台TB-6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后者倒闭。目前,国家用直接或间接控股方式控制了俄罗斯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2001年还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罗斯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国公民和公司获得这些机构的控股权。2002年,普京签署总统令,取消了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的特权。参见许志新:《“可控的民主”及其风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 (19)卢冠林、晋勇:《美用金钱拉拢俄政党》,《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4日。 (20)Бахрах Д.Н.Новый щаг в развит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и//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о.2008 г.,№ 2,-С.17。 (21)Александр Домрин.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http://www.promved.ru/dec_2003_04.shtml)。 (22)George E·Hudson,Civil Society in Russia:Models an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The Russian Review,April 2003,Vol·62,Issue2。 (23)[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24)[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徐葵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5)雷丽平:《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苏联现代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3期。 (26)[俄]普京:《普京文集》,张树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7)Мартышин О.В.Несколъко тезисов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прав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Росс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1996 г.№ 5. (28)转引自黄军甫:《社会结构变迁与俄罗斯政治转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 (29)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ндивида,общест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аксизма и 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7 г.,№ 8,-С.79。 (30)[俄]费多托娃:《俄罗斯的改革为什么失败?》,李丽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31)任开蕾:《关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问题》,《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2)杨心宇、[俄]谢尔盖·沙赫赖、[俄]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社会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2页。 (33)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34)Мартышин О.В.Несколъко тезисов о перспекивах прав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Росс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1996 г.№ 5. (35)[俄]В.В.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36)维格尔:《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http://www.wiapp.org/maoshoulong/maopaper03.htm.1。 (37)[俄]А.О.博罗诺耶夫:《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公民社会:基本特征与问题》,徐向梅译,《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9期。 (38)马长山:《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9)马长山:《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标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民主法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