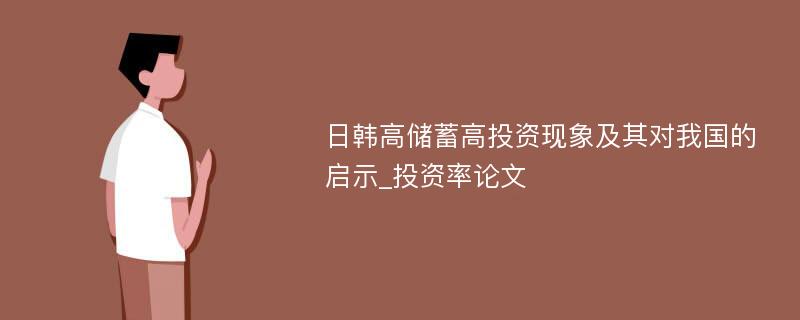
日韩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的判断非常流行,而且对宏观政策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最主要依据是相关比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毋庸置疑,中国的投资率的确比其它国家要高,但我们认为不但应该关心这些现象,也应该关心国际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评价。事实上,国际学术界鲜有直接通过简单国际比较对某一经济体的消费率、投资率高低得出价值判断;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的关系,其结论也充分肯定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注:罗云毅:《消费与投资的若干问题研究》,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表1 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的国际比较
消费率(2003)
资本形成率(1999)
美国 86
20
英国 86
18
意大利79
西班牙76
巴西 78
中国 57
37
日本 73
26
韩国 68
泰国 71
印度 78
资料来源:消费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2005世界发展报告》,资本形成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
本文以日韩两国为对象,以二者工业化进程为重点分析阶段,综合论述日韩学者对本国该时期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的分析以及日韩政府针对该现象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日韩工业化期间,两国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时代。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日韩的研究经验对中国当前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现象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东亚地区高储蓄高投资现象
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很多共同之处。总体而言,他们都倾向于采用政府主导、鼓励投资和利用外国储蓄的政策。
目前研究者对东亚地区的高储蓄—高投资大多持赞赏的态度。Kiseko Hong认为高储蓄反映了消费者出于对将来消费的偏好降低了对当期的消费,因此高储蓄的经济体自然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注:Kiseko Hong, " Korea: Domestic Savings in the Pacific Reg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 1998.)在跨时期和跨地区研究中,Akria Kohsaka也认为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间有强的正相关关系:储蓄率越高,GDP真实增长率越高;并且,各国国内储蓄总体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储蓄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90年代的东亚货币危机也跟储蓄问题紧密相关,危机的产生是过分依赖国外储蓄的结果(而不是投资过高的问题)。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注:Akria Kohusaka, " Overview: Domestic Savings In the Pacific Reg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 Pacific Economic.)亚洲经济增长机制可总结为出口/投资引导的“追赶”型增长,而保持高而稳定的储蓄率以支撑高投资使其与拉美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别。(注:Akira Kojima, " Asia as a Model for Development " , " Catch-up" 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VOL.2 NO.2, Feb., 1997.)拉丁美洲在90年代经济表现不佳,是由于国内储蓄偏低而过分推行吸纳国外储蓄战略的结果。伴随着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这种战略使拉美国家深受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导致了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日益增加的外债和金融危机。(注: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and Yoshiaki Nakano, " Economic Growth With Foreign Savings? " Aug.25, 2003.www.bresserpereira.org.br/index.asp)这个结论间接地反映了国内低储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而对于高储蓄的解释,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与东亚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储蓄率低的原因在于其低下的人均收入、极高的抚养率和大量的外国援助。”(注:Loayza, Schmidt-Hebbel, and Serven, " Sa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Overview, "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4, No: 3 Sep., 2000.)这句话是否也可理解为:高人均收入,低抚养率和较少的外国援助是东亚国家储蓄率高的原因?刘遵义教授认为:东亚地区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获取消费信贷、高房价、低通货膨胀率下正的储蓄回报率、稳定的金融体系、隐性的存款保险和低消费的社会风俗习惯;而高投资率得到高储蓄率的支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也是技术进步的要求。(注:www.stanford.edu/~ljlau/Coumes/Econ216/216Lecture2.pdf)
Makoto Sakura(注:Makoto Sakura,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 Mar., 2003.www.esri.go.jp/en/tie/ea/eal-e.pdf)总结道,东亚国家尽管人口和自然资源差异较大,但这些国家高的增长率都是由高的投资率和劳动要素投入支撑的;其中,生产率提高因素的贡献要低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Young和Krugman认为:东亚经济不是“奇迹”而是“神话”,因为高增长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Arthur J.Alexander总结道:“也许惟一的奇迹是这些国家能够调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这就是东亚与其它国家的不同之处。”(注:Arthur.J.Alexander, "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Asia, " www.sais-jhu.edu/programs/asia/asiaoverview/Publications/Asia% 20Security% 20Policy% 20Fornm/JapaninContext)
二、日本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研究
1.日本高储蓄高投资的基本态势
Richard C.Koo认为,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和公司较高的投资率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私人部门提供的储蓄使得日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使日本经济总量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种投资和储蓄的组合使得日本经济能够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发展起来。(注:Richard C.Koo, 辜朝明, "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 www.icbc.com.tw/chinese/news/news06/news327/doc/327-1.doc)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1973年,这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9%的年均GDP增速使其率先从欠发达国家变为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其最终消费率达到了66%,平均储蓄率为34%,而资本形成率为33.48%。从年度数据看,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一个从低(1952年的26%)到高(1961年的41%)的迅速增长过程,然后又逐年下降,在1967年回落到33%以上。储蓄率变化趋势和资本形成率相似,基本是在30%以上的高位变动,而在30%以下低位变化的年份并不多。投资率连续二十多年保持在30%以上。
表2 日本不同时代的消费投资比例
GDP增长率 最终消费占GDP 资本形成占GDP
的比例 的比例
1952—19739 65.94 33.48
1974—1990
4.2 67.78 30.89
1991—2000
1.46 69.62 28.75
资料来源:Japan Statistics Yearbook 1975, 2001, Statistics Bureau,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Government of Japan.
2.日本经济更依赖于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高增长在于依靠投资与出口,(注:更广泛的原因包括高个人储蓄和高私人部门设备投资,敬业的劳动力,廉价石油的充足供应,技术改良以及政府对私人部门有效的干预等。See, " The High-Growth Era" -japan.org/factsheet/economy/grow.html)但Robert A.Madsen(注:Robert A.Madsen, " Japan' s Incipient Transformation, " www.rieti.go.jp/en/events/bbl/04093001.html)认为,日本出口与名义GDP的比率较低,所以不能说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于依靠出口。而且日本除了在特殊的场合以外,并没把引进外资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这是日本与东亚其它地区的不同之处。同时,进口替代发展型国家从来没有达到30%或更高的投资率,或者没有经历过资本如此快速的增长。所以,他认为日本经济更依赖于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Arthur Alexander(注:Arthur J.Alexander, "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01 Volnme 28, Number 1, Jun., 2003.www.jei.org/Archive/JEIR97/9704f.html)也持类似的观点:投资一直是日本人均收入增长的基本源泉,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快的情况下(落后于美国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人均收入增长更依赖于储蓄和投资的增加。私人部门对设备的强劲投资以高个人储蓄率为基础,既带动了经济增长,也促使产业结构显著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仍以轻工业和农业为主,但后来重工业,如钢铁、造船、汽车、电子设备等成了产业结构中的主要部门。1993年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日本在1960—1985年间的增长同样可基本归功于该时期对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的投资(贡献率达到38%),以及对中学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战后日本的高投资使其资本存量远高于其它工业化国家。Arthur Alexander总结道:“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环境中的高投资导致高回报和生产率的提升,这样反过来刺激了需求,又导致了更多的投资。”
3.日本高储蓄现象的原因及走向
Arthur Alexander的研究发现:日本在利率下降后,储蓄率更高,而这与高利率导致高储蓄的理论相悖。日本储蓄有着特殊的目的,如结婚、上大学、买房子和保障退休生活,而用于赢利目的的储蓄较少。同时,不健康的日本金融体系损害了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的信誉,所以个人觉得必须通过增加储蓄来为未来作更多打算。 Kazoo Ogawa和Kazutomo Abe认为,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前提下和流动性条件的约束下,消费和储蓄是由终生资源和可支配收入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规模也影响家庭部门消费和储蓄。(注:Kazoo Ogawa, Kazutomo Abe, " Japan: Domestic Savings In The Pacific Reg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Horioka(1983)对日本私人储蓄率的研究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日本私人储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抚养率很低的特殊人口结构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未来尽管非成年人口比率将继续下降,但老龄化的加剧将会使得私人储蓄率下降。(注:Charkes Ynji Horioka, " Why Is Japan's Saving Rate So High? " Developments in Japan Economics Edited By Ryuzo Sato Takashi Negishi Academic Press 1989.)Horioka和Watanabe(1997)对日本储蓄动机的经验调查发现,退休和谨慎动机是导致净储蓄增加的最主要的因素。Ohtake和Horioka发现退休和购房动机也很重要,特别是有限的按揭市场和较高的首付比率,使得购买者不得不更少地消费,更多地储蓄。
当然也有人认为日本储蓄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在Horioka的论文中,日本的储蓄率在OECD国家中尽管接近最高,但并不是最高(排在第一的是意大利)。日本家庭储蓄率在1975—1984年为19.3%,私人储蓄率是21.4%。(注:Charkes Ynji Horioka, " Why Is Japan's Saving Rate So High? " Developments in Japan Economics Edited By Ryuzo Sato Takashi Negishi Academic Press 1989.)或者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日本的投资率或储蓄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Hayashi发现,如果日本国民账户按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出概念进行调整的话,两国储蓄率之间的差距将显著缩小。(注:Hayashi, " Japan' s Saving Rate Is Indeed Lower Than Professor Hayashi Revealed, "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8, No.1, March 1996, pp.35-41.)
关于日本储蓄率的走向,Koichi Haji和Yasuhide Yajima认为经济复苏,利率和股利的增加将使家庭资产增多。与此同时,失业率下降、原来过低的利率上升也将增加储蓄。所以从中期看,经济复苏,通货紧缩结束,储蓄率上升和家庭财务盈余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从长期看,老龄化加速后,日本经济将不能再依靠家庭部门创造的丰富的财务盈余。(注:Koichi Haji and Yasuhide Yajima, " The Disappearing Household Financial Surplus-An Analysis of the Recent Plunge in Saving Rate, " www.nli-research, co.jp/eng/resea/econo/eco040603.pdf)Robert Dekle认为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将使日本的整体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假设储蓄下降更快,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将逐渐降低为赤字。也有观点认为: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将逐步下降,但家庭净储蓄率会缓慢上升。除非家庭部门的储蓄被公司和公共部门吸纳。
4.对日本低消费现象的解释和评价
Richard C.Koo认为过量的储蓄意味着总需求不足,将会进一步抑制物价、消费和投资,甚至使经济进入长期的萧条。“在经济潜在全球性衰退的时候,讨论国内储蓄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日本财政部在1998年提出的警句是:“不要储蓄,而要花掉税收减免(省下来的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出现全球经济衰退。假定全球经济增长强劲,而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低迷,该国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来改善经济状况,那么单方面要求刺激国内消费、降低储蓄是否也不合时宜呢?
Arthur J.Alexander(注:Arthur.J.Alexander, "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Asia, " www.sais-jhu.edu/programs/asia/asiaoverview/Publications/Asia% 20Security% 20Policy% 20Fornm/JapaninContext)也注意到持久的低消费问题。他倾向于凯恩斯的观点,赞同低消费会造成萧条,但他同时认为持续上涨的(海外)投资收益是日本持久低消费的主要原因。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浮动汇率的实行,较高的国内储蓄可以流出国外,海外资产利润、利息和红利的回流将使汇率升高,从而减少出口以平衡贸易盈余,国内需求不足则依靠其它国家的需求来弥补。他特别强调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认为如果资本外流的出口被堵塞,经济将会因总消费过低而陷入持久衰退。比较而言,他似乎更担心投资不足:“大于国内投资计划的储蓄将使总需求减少到低于生产能力的水平。”他解决低消费问题的方案是要求更高的资本国内回报。高回报将使公司减少储蓄,减少海外投资,提高国内投资,从而刺激国内需求。
三、韩国高储蓄高投资现象评述
1.韩国高储蓄高投资的基本态势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92年。(注:在制造业飞速发展前,韩国的储蓄和投资率与菲律宾相似,但韩国经历了经济的更快速发展,储蓄率增加,也使得投资率迅速增加。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 Korea: Divergent Growth and a Test of Hypothesis" )1961年5月,韩国开始采用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非均衡发展等战略,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除1980年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外,3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5%左右。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高速增长期,这也是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在此期间,韩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96.8%,下降到1988年的59.7%;储蓄率则处于节节攀升的状态,从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资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运行,1991年甚至达到了39%。从表3可见韩国高储蓄和高投资同时并存的现象非常明显。由于国内储蓄不足韩国采取了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投资率的基本政策。60年代后半期实行了利率改革,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高利率政策提高居民储蓄,(注:金达铉:《韩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2期。)改变了银行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大量利用外资,有些年份海外储蓄甚至超过了国内储蓄,从而保证了年均20%以上的总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确保重化工业战略的实施,韩国的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一般都在30%以上,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高达39.4%。同时国内储蓄增多,使得投资来源更多由国内储蓄解决。
表3 韩国不同时代的消费投资比例
总储蓄率
总投资率 GDP增长率
1970—1980
23.03
28.59
7.61
1981—1990
32.97
31.17
8.67
1991—1997
35.44
36.97
7.01
1998—2002
31.72
25.92
4.58
资料来源: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http: //nso.go.kr/cgi-bin/sws_888.cgi
2.对韩国高储蓄现象的解释和评价
Lam San Ling和Teh Kok Peng对韩国储蓄率的增加持赞成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高储蓄率的国家投资率也高,更高的国民储蓄将使一个国家的投资获得资金,从而导致更高的增长;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储蓄与国内投资无关,但资本全球流动使得这些国家的储蓄者仍将享受全球范围内更高的投资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经常项目平衡都会得到改善。由此可见储蓄增加并非无益。因此,他们建议所有政策的制定者应改变经济中的不利因素以尽力促进储蓄增加:例如,改变因通胀率过高而导致的负真实利率;或者构建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如在农村地区设立更方便可靠的储蓄机构,使储蓄更具流动性。(注:Lam San Ling, Teh Kok Peng, " The Savings and Investment Outlook in Developing East Asia, " www.oecd.org/dataoecd/26/33/17780718.pdf)
Won-Am Park认为:“影响韩国储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人口结构、公共储蓄和经济增长。当国内储蓄相对于国内投资短缺的时候,必须使用外国储蓄。一旦缺乏外国储蓄,投资将难以保持较高水平。”在韩国政府开始刺激国民储蓄之前,国外储蓄一直是韩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民储蓄增长,并成功取代了国外储蓄成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注:Kuwang Suk Sim and Micheal Romer, " Macroec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Korea, "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77.)
Kiseko Hong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收入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年度波动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曾被认为是储蓄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但在解释短期储蓄率时其实也非常合适。第二,尽管抚养率的长期变化能够部分地解释储蓄率上升的趋势,但全部原因却很难明确。第三,韩国异乎寻常的高增长率和低抚养率导致了高储蓄。
未来几年内韩国储蓄率将会下降。韩国人口老龄化也会降低整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尤其是在2025年之后将急剧降低。2025年韩国储蓄率将会稍低于投资率,而早期外部资产积累将带来足够的资本收益。(注:Robert Dekle, " Aging and Capital Flows in Japan and Korea, " Prepared fo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Conference, Apr.2001.)
3.对韩国投资储蓄调控政策的评价
在增长方式的选择上,韩国受经济学家哈士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影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牺牲部分产业和工业部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业。(注: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第211页。)因此韩国选择“倾斜式”的重点投资,采取“先工后农”、“先出口后内需”和“先轻后重”等一系列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注:北京大学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10页。)以达到一种交错的平衡增长。
韩国的五年计划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韩国国民经济计划中曾对投资率和储蓄率进行过规划,在计划中也专门提到了各自的调控比率。
Kuwang Suk Sim和Micheal Romer曾对韩国经济增长做出总结:“由于充分使用了较低的储蓄,韩国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他对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储蓄率的思路非常赞同:“在1977年韩国实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希望GNP年均增长9%,外贸增长16%,进口增长12%。国内储蓄按计划从GNP的21%上升到26%,这样国内储蓄完全能够满足投资需求。而这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难以达到的。储蓄越接近增长目标才有可能使GNP的增长目标更加合理化。”(注:Kuwang Suk Sim and Micheal Romer, " Macroec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Korea, " Working Paper 7705 Korea Modernization Study Series 2.)
Won-Am Park(注:Country Study: Korea.June 2002, ( Hongik University) www.gdnet.org/pdf/draft_country_studies/korea Growth_revised_19June02.pdf)承认韩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资本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资本快速积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没有高储蓄就不可能达到资本快速积累。当储蓄远远低于投资,又没有国外投资时,投资目标和增长目标都无从达到。他认为韩国中央政府为投资设定目标,(注: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并不制定投资率和储蓄率目标,投资不作为最终管理对象,而是服从于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目标,这也是与韩国发展计划的区别。例如1960年日本首相 Ikeda Hayato宣布收入倍增计划,设定未来十年内的年增长目标为7.8%,并没有投资、消费、储蓄等方面的目标。到1968年国民收入倍增,年均增长达到10%,并实现了扩展产业基础的目标。)从而在保持高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间韩国储蓄和投资率均增长了3倍,这是通过执行一系列的五年经济计划而获得的。五年计划中包括一些宏观经济目标,如增长和投资目标,也包括为投资而融资的计划。这些增长和投资的目标预示着对激进的投资政策的采用;并且,政策制定者将采用汇率、税收、信贷配给的措施来为公司投资提供激励。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进口替代的基础产业,并扩大社会一般性的资本积累。出口导向的产业开始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通过促进重化工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在前三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通过坚持高投资战略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
表4 韩国的“五年”计划
时间
背景 计划
措施
效果
汇率改革:韩元几乎贬值了50%,1965年
国内储蓄率从1962年的3.2%
实行了单一浮动汇率制度。上升到1966年的11.8%,1974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7美元,消费
利率改革:1965年9月政府把银行存款
年升到14.5%。税收/GDP比率
一五计划 率96.8%,储蓄率3.2%
计划投资率22.7%,利用国内 和贷款利率提高一倍(定期储蓄的年息
从1966年的10.7%上升到
1962—1966
储蓄率12.9%,海外储蓄率
15%提高到30%,贷款年息从15.7%提高
1971年的15.1%,导致公共储
实行出口导向产业战略和经济增
9.8%到26%)。
蓄增加投资年均增长7.8%,
长战略 提高税收/GDP的比率,成立了国税厅加
但总投资率只达到21.6%,低
强税收征管。
于计划1.1个百分点。
政府实行价格稳定政策,以控制通货膨
投资激增引发了通货膨胀
胀
通过增加税收和引进外资,总
投资率达到25.2%,高于计划
二五计划 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进一步提高 5.3个百分点,所依靠的国内
1967—1971 经济自立度 计划投资率19.9%
储蓄为14.5%,海外储蓄为
10.7%。
经济增长率9.6%,物价上涨
率8%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8美元, 发布了减轻企业负担,改善财务结构的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7∶22.4∶50.6。
《关于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的紧急命令》
三五计划 提出“成长、稳定、均衡相协调”的发
1973年制定重化工业建设计划
经济增长率9.1%,国内储蓄
1972—1976 展方针,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注
推进新村运动的农业投资计划
率23.1%,总投资率达到
意物价稳定以及地区之间的均衡发 制定“关于稳定物价和公正交易的法 26.1%,物价波动明显
展,特别是重点发展重化工业
律”
在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
提出“成长、平衡、效率”的基本方的打击下,韩国经济机构出现
四五计划 针,发展重化工业,建立自立的经
计划经济增长率达到9.2%, 为推进重化工业的进程,对缺乏资金的
失衡,物价上涨,1980年甚至
1977—1982 济结构,促进社会开发、增加科技
总投资率达到26%,并争取
企业提供低息的政策性金融和税收方 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但70年
投资等
全部由国内储蓄解决 面的优惠 代经济增长率达到7.3%,实
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结
构升级
基本目标:以“安定”代替“成长”,
批发物价上涨率0.8%,零售
以数量型增长优先政策转为稳定 首要的措施是稳定物价,在财政、通货、
物价上涨率3.5%。
五五计划 优先政策;随着经济的自由化、开 利率、汇率等方面实行稳定政策,同时
经济增长率达到8.6%,人均
1983—1987 放化的推进,将政府主导转为民间 稳定公共支出。刺激供给,降低需求,增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05美
主导 加储蓄 元,总投资率30.2%,国内储
蓄率27%,海外储蓄率3.2%
拟定经济增长率7.3%,人均
经济自由化
出口增长率下降,但民间消
六五计划 以效率和均衡为基础,走向经济先
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总
努力缓解阶层间、部门间、地区间的不
费、建筑业投资开始主导经
1988—1992 进化和增进国民福利投资率31.6%,国内储蓄率达 平衡,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平均
到33.5%,总固定投资率34% 推进经济国际化、开放化 年增长16.5%,经济增长率
9.9%
尽管政府主导关键投资项目具有很多优势,但是在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对重化工业的大促进(big push)的效果颇为引人争议。大促进虽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但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由于政府不能选择恰当的产业,也不能确定恰当的投资量,出口在促进投资效率方面或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存在局限。第五个五年计划中政策就从政府干预转为依靠市场机制,包括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
Won-Am Park将韩国经验总结为:“持续和纯熟的政策体系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高增长非常重要。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韩国实现了预定的增长与投资目标。韩国政府在计划中明确了投资和增长目标,并兼顾以国内或国外储蓄进行融资。”(注:2000年末韩国金融机构发卡数为5788万张,到2001年末达到 8543万张,15岁以上的持卡人平均每人拥有3.7张信用卡。2001年韩国信用卡购物比上年增长了40%,居民消费额一半以上是通过信用卡结算的。詹小洪:《家庭债务危机困扰韩国》,载《银行家》,2004年第4期。)
4.韩国刺激消费政策的评价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实行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各银行吸取了以前企业贷款易产生坏账的教训,转而把放贷业务放在消费者的身上,大量发展信用卡服务。信用卡大大刺激了消费,但在短期经济增长后,却产生了新的家庭债务问题。低利率和消费信贷政策使得韩国国民少存钱多借钱,韩国家庭经济结构从储蓄型转变为贷款型。从1990年到2001年,韩国储蓄率从37.5%降到27%,,这也是自1986年以来比值最低的一年。2002年末,韩国信用卡公司坏账率达到12%,到2003年,韩国使用信用卡消费的金额比上年减少了30%。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政策并未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为家庭债务爆发性增长、大量家庭资不抵债乃至破产埋下了隐患。
尽管日韩各界对破解高投资高储蓄之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目前几乎没有对此做出精确解释的文献。大部分文献都对高储蓄高投资持积极的评价,持负面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在日韩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两国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时代。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的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
四、日韩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即使到工业化中期,投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较高水平。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投资率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判断,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1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5%,城市化率达到72.1%,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韩国1991年城市化率达到了74.4%,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7.1%,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也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投资率1973年后逐渐下降,2000年下降到26%;韩国1996年后投资率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了26%。
中国较长的工业化进程将使中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结合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观察中国的各项指标;按当期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GDP 1090美元,进入工业化的成熟期;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5∶53∶32,处在工业化成熟期;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49∶22∶29,处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率为41.8%,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综合以上4项指标体系,可以总体判断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投资率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
中国近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将使投资率短期内下降的可能性很小。按照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在人均产出的不同阶段,发展的重点产业是有所区别的。为了更清楚地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将1980年的美元按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折合为美元现价,经折算后中国2003年人均产值1268美元(按1∶8.28汇率价计算)。根据产业结构阶段和发展重心演变的规律,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程度,主要的工业发展方向应该是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建筑业等,所以未来经济增长将由这些重化工产业主导,而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求更高的投资率予以支撑。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公共服务的同质化必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巨大发展。
消费结构的变化将以重化工为基本支撑。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发生变化,以住房、轿车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品成为新的热点。根据测算,中国城镇人口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实际可能达到的人均水平为24.4平方米,而目前仅仅只有18.4平方米,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空间;随着中国自主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关税水平的下降,轿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家庭;而传统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消费周期的更替,升级换代的频率和速度也日益加快,所有这些消费产品都对重化工产品和原料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特别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廉价劳动力和日益成熟的研发能力为支撑的全球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前景,将有着对重化工业产品和材料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
公共服务的同质化目标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本届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施政纲领,通过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地区差别等措施,希望为国民提供同质化、无差异的公共服务产品,这些目标将进一步促进重化工业发展。首先,为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城市化战略将会拉动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城市化必然导致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市政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其次,为了缩小地区差异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将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再次,促进全国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统筹协调的目标也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如跨地区、跨流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等工程的开工和建设也将对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重化工产品和原料形成长期的巨大需求。
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同质化目标将促使工业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对高强度的投资产生内在需求,所以投资率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高位;为了给高投资融资,国内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也会保持较长时间,所以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将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种经济常态。对此我们应该借鉴日韩的相关经验,对高投资高储蓄予以更客观的评价,那种不顾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试图对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进行人为调控的思路是需要商榷的。
标签:投资率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储蓄率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