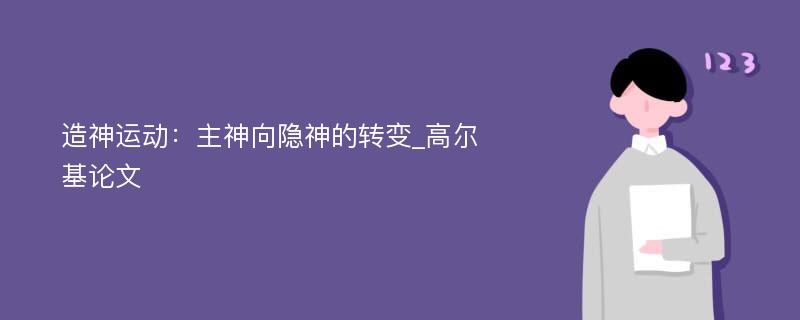
造神运动:显性上帝向隐性上帝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帝论文,显性论文,隐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别尔加耶夫曾说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是宗教的,这是基于俄国文化的宗教性而言。从 这一角度我们最起码可以说,苏联时期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宗教。因为,一种文化 的密码具有永恒的制约性,它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起着构成性 作用。如弗兰克所说:“俄罗斯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就内在本质而言是宗教性的(因为 可以断定每一种创作均是如此),而且宗教性还交织渗透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 ”(注:С.Франк Рус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 рение.СПб.,1996,с.184.)也就是说,这种宗教文化还始终制约着文化的亚形态——文学——的整体构造。即使苏联时期也不例外,尽管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无神论占据重要地位,但宗教特性仍然以隐喻的形态存在着。而20世纪初的造神运动就是这种宗教特性以隐喻状态进入苏联文学的序曲。
一
斯拉夫文化与西欧文化之争是俄国社会19世纪的主要线索性事件,这种论争的结果有 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发生,一是新宗教热潮的兴起。民粹党人的失败使俄国的 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开拓了一条新的革 命之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团体的革命斗争 也经受了种种挫折,即使是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整个俄国仍处于穷困与混 乱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师从霍米亚科夫及索洛维约夫的一批哲学家,其中包括已 成为激进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开始建构他们的新基督教学说——“寻神论”
(богоискателъство)。寻神派(богоискатели)试图通过宗教寻找到新的基督,创立一种基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新精神秩序,从拯救人的灵魂开始为俄国开辟一条根本出路。在他们看来,革命并没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造成了社会精神秩序的崩溃,只有精神的复兴才能拯救灵魂,并进而拯救社会。于是,托尔斯泰相继写出了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格言体著作《哲人思想录》、《阅读圈》、《生活之路》等。而一些宗教哲学家,如谢·布尔加科夫、别尔加耶夫等人,从当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而热衷于创立新派神学、重建基督教精神。上述二人除了撰写大量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之外,还于1905年创办了《生活问题》杂志,专门刊登宗教与社会问题探索的文章,从而使这一杂志成为宗教哲学兴盛的旗帜。此后他们二人又与格尔申宗、司徒卢威等编辑出版了《路标》文集,收集了自由主义和宗教哲学观点的文章,表现出对俄国新生之路的探索。在这一时期,维亚·伊万诺夫、弗洛连斯基、弗兰克、特鲁别茨科依兄弟、罗扎诺夫等,均有多种宗教哲学著作问世,尽管他们的观点、方法都有较大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否定“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建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宗教观。如罗扎诺夫对传统的禁欲主义思想加以弃绝,主张建立新型的性爱伦理,使人回归本性,从而走近上帝。布尔加科夫则试图使新的神学思想科学化,他在其博士论文《经济哲学》中所做的实际上是使人在“将世界感受为经济”的同时,揭示人在世界上的使命和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并从本体论和宇宙论角度对基督教加以论证,他一生所写下的序列性神学著作就是要建立一个由科学、哲学和神学构成的综合体,以完成对人和社会的终极性拯救。
寻神派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抨击。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唯物主义哲学、美学和历史著作,如《论一元论史观 发展问题》、《俄国社会思想史》、《没有地址的信》等。他在探索俄国社会出路问题 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肯定了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经济现状、社 会关系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列宁则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开始确 立自己主流话语的地位。从《路标》出版伊始,他便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他先是在 法国的列日做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讲演,接着在巴黎做了《反革命自由 派的思想体系——路标的成就及其社会意义》的报告,随后便发表了《论<路标>》一文 ,对其“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及立宪民主党立场进行了抨击。在革命的 前夜,列宁必须要对任何危害革命的现实逃避行为加以阻遏,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些宗 教哲学家们的精神探索,他们所试图建立的新宗教意识,即他们的“路标”,在列宁看 来,乃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 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标”。(注:《列宁全集》第19卷(人 民出版社,1989),第168页。)
无论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力图阻遏当时的宗教哲学复兴思潮,但文化符 码的制约性是无法消解的。在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这种制约性便很容易将革命的激情与 宗教热情联系起来。或者说,信仰与崇拜的激情已经成为俄国人心中的一种情结,它将 永远不会在任何外来因素的压抑下缺失,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在 左派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另一种与“寻神派”殊途同归的“造神派”就不足为奇了。 流亡思想家赫克在谈到本世纪初的这种状况时说:
自1905年大革命失败后,一般人更逃入宗教,更想找出一个由智力方面说来比较满意 的宗教。在这时候,甚至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不住了,都往宗教跑,都向教会投 降。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布尔加科夫、别尔加耶夫。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 行动者,如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都想把宗教和革命的目标联合起来。于是他们变成 了“上帝制造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复归于旧日那模糊的正教,但想造出一个新的社会 主义宗教,可以保存宗教的价值,而不需接收教会的信条。(注:赫克:《俄国革命前 后的宗教》,高骅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293页。)
用苏联学者的话说,就是“如果说寻神论是与反动阶级密切相关的话,那么造神论则 是发生于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部”。(注:М.Ласковая
Богоискателъство и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о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ъ.М.,1972,ст.8,62—64.)
二
在“造神派”(богостроители)中,除了巴扎洛夫、尤什凯维奇、鲍格丹诺夫等人以外,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可称代表人物。像当时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对历史的基督教,即由教会所把持的、以政治结构形式存在的宗教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然而这并不说明他对一般性宗教精神的否弃。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在知识界探索俄国精神出路的情势下,卢那察尔斯基基于早年所受阿芬那留斯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重新开始关注宗教的积极意义,他把久已思考的将宗教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的设想在《简论现代俄国文学》(刊于日内瓦俄文报纸《国外周报》1908年第2—3期)、《宗教与社会主义》(1908—1911)等著作中加以完善。他称《宗教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本质性特点是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神话和教义中表现的人类夙愿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在新的世界观中的中心地位”。(注:转引自帕夫洛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陈日山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44页注。)针对当时思想界寻神论的盛行,他在书中力图表明:“神不应去寻找,而必须把它创造出来。世上没有神,但它是可以有的。社会主义的奋斗之路,即人战胜自然的奋斗之路,——这就是造神论
(богостро ителъство)。”(注:А.Луиачар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дискусии 1908—1910гг.//
Об атеизме и религии.М.,1972,стр.439.)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在人类的天性中存在着宗教情感,而这种宗教天性实际上可以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达成一致,他说:“对于伟大的生活斗争来说……必不可少的是人类在一个类乎有机体中的完美融合。不是机械的或化学的联系……而是心理的、智性—感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宗教情感。”“宗教,这就是激情,而没有激情就无法使人创造任何伟大事业!”(注:М.Ласковая Богоискателъство и
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о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ъ.М.,1972,ст.8,62—64)卢那察尔斯基是现实地考虑到如何将社会主义思想与广大民众的心理状态相适应,唤醒对消极的基督教义的沉迷,而又避免重新陷入索洛维约夫以降的宗教哲学家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卢那察尔斯基的思想如他自己所言是“善良的”。
综合而言,所谓“造神论”的主要观点就是:一,否定传统教会及其教义,这一点与 当时盛行的寻神运动有着同样的背景,即对教会权力化、世俗化的弃绝;但可以利用基 督教中有益于凝聚民众的因素,如耶稣这一形象。造神派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但却认为 应当把他视为一个革命领袖和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在《黑暗》一文中说:
如果我们试图将他作为一种个性而加以历史复原,我们将把他视为一个独特的加利利 地区的无产阶级领袖。如果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传奇英雄看待,那么他就是罗马帝国衰败 时期无产阶级大众的典范……尽管他与我们当代精神相比是一个消极的英雄,但无论如 何他也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一个伟大的爱和伟大的恨的导师。(注:С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распад”,кн.I.СПб.,1908,стр.161)
也就是说,把旧有的基督教资源化为己用。二,以神圣事业之名行现世的革命事业。 要使民众接受一种新的社会体制是很难的,而俄国的民众固有一种宗教情愫,将社会主 义加以宗教化就等同于将一种陌生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大众话语,以为他们所接受。如卢 那察尔斯基自己所说,“我们被陷入宗教追问的迷狂之中的广大民众所包围。他们都是 这样一些群体(正如我所想到的,特别是农民的团体),比起别的任何途径来,他们很容 易通过其宗教—哲学的思考来走近社会主义真理。”(注:А.Луначар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дискусии 1908—1910гг .//Об атеизме и религии.М.,1972,стр.438—439.)同时,这种神圣事业不同于传统俄国正教观念中的救赎过程,它放弃了虚幻性、默示性、自虐性,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积极性、现实性的社会行为。三,以宗教热情激发民众的潜力。他认为在民众之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本可以创造任何奇迹,但它被压抑了,因此需要以强烈的宗教热情将它神化,给它加上荣耀的光轮,才能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这种造神论所造的神不是上帝,不是历史基督教的信仰,而是崭新的人类自身、是完美的社会主义的人类自身;以这个神为中心所形成的宗教就是“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他说:“所谓的神,乃是某种永恒之美。在这一形象之中……人类的全部潜能将得到最大的提升。”(注:А.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СПб.,1908,
стр.157.)所谓造物主是不存在的,但存在着一个深植于人人心中的神,人人是神的化身,人人具有创造世界的力量,人人都将是这个美好世界的造物主。
然而,这种带有折衷色彩的革命学说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的批判目标之一就是“造神论”,他称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是“可耻的” ,与寻神派的宗教思想家们站在了同一立场。在列宁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 潜在力的神化”犯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错误,“它把‘心理的东西’跟 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 换整个物理自然界”。(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362页。)
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的批判和直接劝告之下,最终反省并放弃了他的“造神论”主张 。他在晚年所写的《有关1908—1910年的哲学论争问题》一文中做了一个政治检讨:
我如今清楚地认识到,那时我所有的谬见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的产物,这种 倾向迫使我走上了错误的路线——远离由列宁所领导的党的理论和党的批评的坚定而光 明的核心。……当时我所迈出的最错误的一步,是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哲学理论,这就 是所谓的造神论。(注:А.Луначар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дискусии 1908—1190гг.//Об атеизме и религии.М.,1972,стр.443.)
造神论的学说在理论界并未形成一种广泛的思潮,并且在1910年之后逐渐销声匿迹。 但造神论在文学创作领域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应该说,并不是造神论对文学产生 了影响,而是在俄国人的血液之中浸透着对神的向往,这种情愫无论有没有理论的推动 ,它总会通过情感的符号表现出来。
三
1908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忏悔》,这篇小说被认为是造神论文学的代表 作。那么,它是如何体现造神论观念的呢?
主人公马特维是一个弃儿,被教堂助祭拉里翁收养,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性格的宗教性 和原始教徒的求助欲望。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人们的歧视,他以笃信上帝的精神忍受着现 实带给他的一切,并且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他所遭受的一连串打击——岳父逼迫 他作假盘剥农民、妻子和儿子的相继死去——使他渐渐丧失了坚定的信念,尤其是产生 了对上帝的怀疑,他的笃信并没有带给他应得的东西,因此在他成年的时候,发生了信 仰危机,“上帝的尊容在我心目中已经蒙上厚厚的灰尘,我本想擦去时光给它抹上的污 垢,可结果却把上帝从我心里彻底擦掉了,我的心由于恐惧而颤抖起来。”(注:《高 尔基文集》第12卷,孙静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26页。)为了解除精神危机 ,他开始寻求答案。他凭着自身的体验,意识到上帝并不存在,然而又为这一想法感到 恐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遇到了约纳神甫,一个“造神论者”。神甫向他解说了上 帝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上帝不是生活在我们之外,而是生活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被心里的种种难题吓倒了, 才把上帝从我们心里搬了出来,把上帝置于我们之上,企图用他来抑制我们桀骜不驯的 个性,约束我们不安分的心灵。依我看,这是强行阻碍自身力量的发展,把力量变成了 软弱。(注:《高尔基文集》第12卷,孙静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31页。)
因此,人民应该创造自己的上帝,不是与我们对立的、由教会和政权操纵的那个上帝 ,而是与我们自身融为一体的精神力量。但是,马特维不相信生活在他周围的浑浑噩噩 、肮脏愚昧的群氓会成为上帝的创造者。他满腹狐疑地来到约纳神甫所指引的伊谢特工 厂,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个具有圣徒品质的普通人,彼得·亚吉赫、米哈伊拉、科斯佳 等,他们虽然同样生活在苦难之中,但他们以相互扶助、彼此关爱、团结奋斗的行动构 造了一个天堂世界。马特维终于相信:“生活是多么美好啊!俄罗斯人民是多么伟大啊! ”(注:《高尔基文集》第12卷,孙静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90页。)甚至 高尔基为了说明人民就是上帝,还插入了一个完全取自圣经的情节:一个瘫痪3年多的 姑娘在朝圣群众的呼唤下重新站立起来,与大家共同前进。
像宣扬造神论的卢那察尔斯基一样,高尔基的这篇小说也因带有图解造神论的痕迹而 受到列宁的批评。列宁在1913年11月下半月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说:
您想以此来说出“善良和美好的东西”,指出“真理—正义”等等。但是您这种善良 的愿望只是属于您个人的东西,只是您的一种主观的“天真的愿望”。您既然写了这些 东西,它就散布到群众中去了,它的作用就不由您的善良愿望而要由社会力量的对比, 由阶级的客观对比来决定了。由于这种对比,事情的结果(违背了您的意志并且不依从 于您的意识)就成了这样,您粉饰了,美化了教权派、普利什凯维奇分子、尼古拉二世 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观念,因为在事实上神的观念是帮助他们奴役人民的。您美化了 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用来束缚落后的工人和农民的锁链。(注:《列宁全集》 第46卷,第367页。)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未必就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会成为帮助教会和沙皇政府奴役人 民的工具。但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列宁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并 且他真诚地希望像高尔基这样的文学家能够站到他的一方来,他需要的是防止敌人利用 这一点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如他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中所说的 :
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 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 。(注:《列宁全集》第19卷,第168、89页。)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对《忏悔》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哲学理论,它有着自己的生成原则。高尔基作为一个优秀的 作家,在其每一部作品中都蕴蓄着深厚的文化、社会与心理内涵。而《忏悔》也并不是 一个“造神论”所能够说明问题的。即无论作者如何想要使作品接近现实并传达某种显 性的思想,他也无法摆脱文化的制约。也就是说,《忏悔》归根结底要成为文化的代码 ,包容进其宗教文化的精神追求。或者从根本上说,造神观念的出现就是由俄罗斯的宗 教文化规定性所决定的。
《忏悔》想要放弃一般对宗教的理解,试图将宗教现实化,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 起来。但这种造神观念最终仍是宗教性的,即以精神的和谐为最高追求,而不是以形而 下的生存为指归。这一点从造神论者的特征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首先,造神论者生存 的终极价值体现为精神的和谐。马特维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但他绝不是浮士德式的追 求者,浮士德在物质创造中得到了生命的最大满足,而马特维在整个的物质追求过程中 所得到的只有苦难与罪孽。因此,他只有放弃世俗生活到处寻找精神归宿,他来到了19 世纪物质革命的策源地——工厂,但显然物质创造并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幸福。俄国的空 想社会主义思想远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发达,而当时的高尔基尽管已创作过《母亲》,但 仍没有找到真正的生命解放之路,因此他只有选择文化的密码告诉他的方案:于是我们 看到小说最后一个场景仍是祭祀神灵,也只有这样的场面才使马特维像浮士德听到劳动 的音乐那样,最终获得了物质的解脱。其次,不是放弃上帝和耶稣,而是赋予上帝以全 新的内容,并且真正复活耶稣的本源精神。在他们看来,人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早已经过 历史教会所加工过的耶稣,如约纳神甫所说:“他们歪曲了耶稣的精神实质,叛离了耶 稣的教义,因为耶稣是活生生的,耶稣反对他们,反对人对人的统治!”(注:《高尔基 文集》第12卷,第430页。)而在米哈伊拉的书架上既有世俗书,也有圣经、福音书和古 斯拉夫圣诗集。他们要以耶稣的平等和博爱的教义来重建世俗秩序。第三,对上帝的信 仰其实就是对人的信仰,因为他们坚信上帝是照人的模样造出来的。然而他们所信仰的 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人类的大同也正是耶稣的理想。米哈伊拉对马特维说 :
您还没有意识到把您自己的思想与工人群众的思想联系起来的必要性。……您自以为 您是一位英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准备无私地给弱者以帮助。实际上,您不过是一 种特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照您这样,只能是昙花一现,您不可能持久地去完成一 件美好的、伟大的、永恒的事业。(注:《高尔基文集》第12卷,第470页。)
这里的广大民众乃是如上帝一样的抽象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某种事物,这也正是宗教 信仰的特征。
总之,造神论虽然否定的是传统的上帝与基督教,但其内在实质仍是一种新的宗教, 或者说,作者是在以文化的规定性来对抗现实的规定性。由此可见,《忏悔》的根本性 对话是作者的文化人格(集体无意识)与现实人格(意识形态)的对话,或如巴赫金所说的 ,它体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作为现实人格,高尔基试图否弃传统意义上的教会与 上帝,教会已不再是信徒救赎的媒介,而成为借救赎之名行罪孽之实的机构,而上帝则 成为教会控制民众的工具,——这是高尔基自觉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归属。而作为文化人 格,他无法在否弃教会的同时建立一个纯粹世俗的目标,他排除了外在的上帝,但无法 排除心中的上帝。文化的话语告诉作者,仅在物质中生活,或者哪怕是物欲偶或压抑了 信仰,也会使人变得肮脏、猥琐、卑鄙,季托夫、面包师米哈正是这种话语系统中的辅 助符号。生活目的性(精神指归)的确立则会使人在灵魂上由地狱相升华为天堂相,如伊 谢特工厂的工人们,他们满面煤灰,但他们的心灵是由信仰之光所照亮的,他们生活在 一种坚定的信念之中,这种信念就是:在他们的意志中将会产生出神奇的、不可战胜的 力量,上帝将在这种力量之中复活。虽然小说强调此上帝已非彼上帝,但显然,上帝仍 然不是人民大众本身,民众只是造神者,上帝仍然是民众意志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上 帝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仍然是民众的理想的精神归宿,不过是从显性状态 转换为隐性状态而已。
《忏悔》尽管受到列宁的批评,但它与此前创作的《母亲》属于同一类型,它虽然没 有像《母亲》那样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核心描写对象,但就肯定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以及 对沙皇俄国社会的批判而言,它仍应属于革命文学。而就其造神思想来说,《忏悔》将 俄国的上帝文化以隐喻形式带入了新世纪的革命文学。它的出现是一个标志,它预示着 20世纪的俄国文学将创造一种对上帝吁求的隐喻格式,即把19世纪文学中的显性上帝转 变为隐性上帝——带有拯救功能的民众英雄,而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19世纪以来的宏大 叙事,这在20世纪现代主义以私人叙事为主潮的文学中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