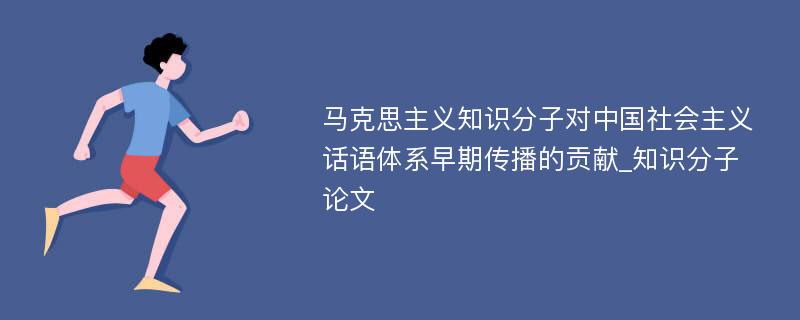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早期传播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话语论文,贡献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7-0061-06 “话语”是言语交际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话语体系建构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福柯指出,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做验证。[1](p.26)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传播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对此。习近平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2]研究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规则和路径能为加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借鉴。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话语符号的形成 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汉语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与西方的对话体系中,于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它们都不能科学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而未能真正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与日本、苏联的对话中逐步引进了科学的、实践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确立了准确的话语表达,并随着历史的前进日益完善,形成了中国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系统。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词源上讲,日本是最重要的来源国。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广泛吸收西方文明,由于日本学者崇尚汉文,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倾向于使用汉字新词或赋予汉语旧词以新意。因此,经由日文翻译的西方文明更快速地传入中国,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大量借用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汉语词汇表达,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封建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劳动力、政治经济学、私有财产、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农民、权力、政权、解放、反动、不断革命、改造、意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产者、无产阶级等。这些基本术语在中国广为流传,很多确立下来保留至今。但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始终保有其对话性的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说,话语的本质在于其对话性,不管我们的话语具有多强的对白性,实际上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回应,都与其他话语处于不同程度的对话关系中。[3](p.59)日语翻译的借用词在中国的具体对话中有些被不断地否定和创新,选用了更为准确的汉语词汇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载体。如“劳动者”原日语表达“工人”之意,后来被“工人”取代。而“劳动者”则表达“劳动的人”。由“垄断”取代了“独占”,“统治”取代“支配”,以“压迫”代替“压制”、“压抑”,以“资产者”、“资产阶级”取代了“有产者”、“有产阶级”,以“专政”取代“独裁”,以“剥削”取代“榨取”,以“觉悟”取代“自觉”,以“群众”取代“民众”与“大众”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形成过程受苏联影响很深。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始于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介绍,其后宋教仁、廖仲恺、戴季陶等都有传播,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广泛传播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刺激了东亚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繁荣起来,研究的对象也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扩展到列宁思想。于是出现了一些新概念,要求新的语言形式与之相适应。日本学术界在对俄国革命的讨论中开始使用“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概念。[4](p.79)而中国,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繁盛起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量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加。1922年光亮翻译了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上所谓的“过渡期”》,在论述列宁、考茨基和马克思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特点时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瞿秋自在留苏回国后撰写的著作中开始系统地介绍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使用了“互辩法的唯物论”这一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由“唯物史观”话语扩展到了辩证法视域。20世纪30年代,受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唯物辩证法开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代表了全新涵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矛盾”、“对立”、“对抗”等词汇进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系统。 话语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处于言语文脉的对话体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也是在中国历史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中国自己的话语符号系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符号话语系统至今依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话语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需要不断吸纳最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符号话语,打造开放融通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二、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 创建马克思主义学术知识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扩散的学理基础和理论依靠。福柯秉持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方法,把知识归结为一种话语体系,他认为每门学科都是一种话语,知识的独一无二的话语结构成为巨大的驱动力,改变着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开始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中心聚集起来,以“社联”、“左联”等学术团体为依托,展开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开始形成。抗日战争开始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在有利的学术环境中潜心研究,创造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成果,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初步成熟和完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李达、艾思奇、鲁迅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融入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创造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 史学领域最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史学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学者德里克谈到:唯物史观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欧洲最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的思想指导下断定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因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发展进程。20世纪30年代,一个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历史倾向的增长导致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优势地位。[5](p.1)事实上,唯物史观被引入史学研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开展和深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侯外庐、吴泽、李平心、华岗等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长起来,出版了一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完成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的建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建构了独特的哲学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之后历经传播、发展、创新的艰辛历程,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出发论证社会的发展规律,凸显唯物史观的批判性,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要旨。此后,瞿秋白开启了中国唯物辩证法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20世纪30年代,李达建构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体系,强调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6](pp.79-80)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和阐发高于同时期苏联的研究水平。艾思奇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趋向,用中国人民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和大众化运动中表现突出,唯物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发现、发展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合理因素。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认为,陈伯达的思想对毛泽东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对中国革命进程的探索中,融合中西两种视界,以实践为基点,创造性地建构了实践的认识论、实践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整体,实现了哲学立场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凸显了实践维度的首要性和重要性,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实质性融合,建构了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将文学创作的主题意蕴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同时也在理论与创作相得益彰的情形下,使革命文学产生空前巨大的磁力和辐射力,既稳定了重心,又加大了影响。[8](p.109)“革命文学”成为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成仿吾、沈雁冰、郭沫若、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是这一转变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的文学主张总是显示出对当下现实的巨大关切,并旗帜鲜明地要求新文学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成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瞿秋白、鲁迅、钱杏邮、林伯修、阳翰笙、蒋光慈等是其杰出代表。文艺大众化则为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学术界对此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他们认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一场有规模,具有理论自觉精神的,不断深化的、民族的、体系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运动。它所力图解决的是革命文学运动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文艺和大众的关系问题。它是后来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9](p.51)1942年,针对当时解放区迅速扩大,需要进一步动员和领导民众起来革命斗争的政治斗争形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批评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的倾向,将文艺大众化推向高潮,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话语由知识分子群体传递和扩散到广大民众中,知识对于革命的向前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逐步建构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厚重的理论支撑,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变得深刻而久远,知识体系的独特话语建构超出了知识学术领域的效果。逐渐地,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如胡秋原、方亦如等。马克思主义成为三四十年代首屈一指的思想潮流,甚至连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10]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要依靠强大的学术理论支撑,通过学术理论研究解读中国实际、中国道路,打造出具有中国灵魂的、系统的、科学的、前沿的学术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体系构建成果不足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式微,甚至在有些领域被边缘化的问题。 三、立足实践,建构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话语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元素,它既是一种力量,又是一种权利,具有认识论和政治效用的双重效果,话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改变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一种话语体系能否确立和产生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话语能否引领时代发展,解决社会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被赋予了唤醒现实,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落实于具体的行动,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实践的武器和革命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仅钻研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更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彰显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莫不如此。他们不但学理论,还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军事,学会打仗,学会做革命的领导与组织工作,使年幼的中共迅速成长起来,担负起救亡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们成为具有丰富实践基础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启在实践中探索理论的研究路径。他们在实际状况中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上升为新的科学理论形态,把中国革命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实践问题上升到理论形态上论证,从中国实际出发,重视事物的特殊性,沿着从特殊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路径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拯救了沉沦的中国和困境中的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创建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在对革命现实问题的解决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革命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日益为人们理解、接受和信仰,中国社会主义话语在实践中日臻成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实效性赢得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确立起来。 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话语体系建构不是封闭的逻辑推演和论证,而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表达。离开社会实践,话语体系建构就变成了无源之水。立足当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切实关注人民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 四、重视受众是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历史经验 巴赫金指出:“言语交际是多方面积极的‘思想交流’的过程,所交流的思想彼此间不是漠不关心的,每一个思想交流也不是独立自足的……他人表述都以语言交流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互联系,并充满对该语言交际领域中其他表述的种种应答性反映。”[11](p.177)任何话语都期望得到回应、理解和聆听,从而形成对话关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大众化颠覆民众落后封闭的思维模式,使马克思主义通达大众内部思维结构。他们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以大众习见常闻的通俗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原生态生命话语。 中共从“左联”时期开始强调走文艺大众化路线。1929年3月,林伯修提出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1931年瞿秋白发表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阐述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鲁迅在1929年指出:“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12](p.148)其后鲁迅在《文艺大众化》一文中对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问题作了独有而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文艺大众化应该为大众所鉴赏,但大众也要有一定的鉴赏基础,应该针对不同文化保有程度的人创作难易不同的文艺。他同时指出大众化不是低俗化和媚俗化,那样的文学作品对大众是无益的。“左联”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对于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影响力还很有限,只围绕着中共中央所在地展开,并没有能够覆盖全国范围的民众。 延安时期,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语言的思维已获得更广范围的实效性。1936年11月22日的中国文协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大众方向。1942年,针对当时解放区迅速扩大,需要进一步动员民众的政治斗争形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批评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的倾向,将文艺大众化推向高潮。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大众化的语言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潮流。除了“文艺大众化”之外,还涌现出“哲学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等。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都从事建构哲学大众语言的工作,并形成了哲学大众化运动。艾思奇撰写了《大众哲学》,陈唯实发表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和《新哲学体系讲话》,胡绳撰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和《哲学漫谈》等,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大众化的认识和态度。他们的著作通俗易懂,力图破除哲学的神秘性,通过比喻等方式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易懂,让一般大众能理解接受,并使话语内化为革命的力量和能力,这对当时热血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树立了大众化的方向,以受众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民众内心的生命话语,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大众化路径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技术路径,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导向,深入考察和研究大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善于把深邃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道理,善于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形象的生活逻辑,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进去的理论学术观点。”[13] 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最切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探索中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早期传播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构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为基础,符合中国文化表达方式,能够解释和回答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在继承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汲取古今中外科学研究成果,加强诠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效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走向世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控制力和引导力,要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严谨治学、大胆创新、通学通识、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要汲取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脉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瞿秋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