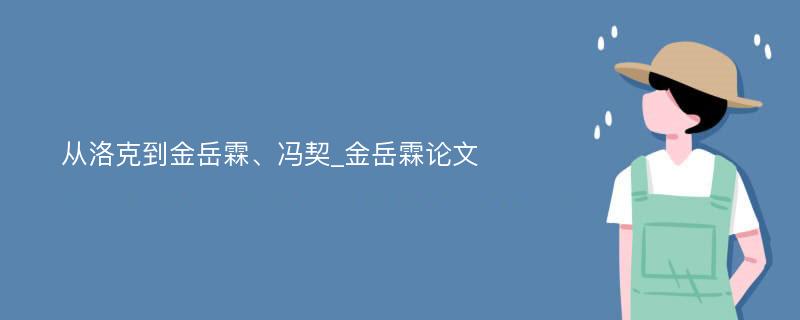
感觉经验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从洛克到金岳霖和冯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克论文,客观论文,感觉论文,经验论文,金岳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感觉论是认识论的基础部分,在这个领域,哲学论著可以说已是汗牛充栋。但已故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在80年代讲授他的“广义认识论”的时候,却仍然说感觉论是他花力最多的部分。这个问题对于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重要,这个问题之确切解决的不容易,由此可见一斑。
感觉论的核心是“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常识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但稍作思考,便能发现对感觉的无条件信赖是不明智的。在古代,哲学家们就开始怀疑感觉的绝对可靠性。庄子、荀子、德谟克利特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感觉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实在论的哲学家在论证认识的客观性的时候既不能摆脱常识,也不能回避常识的局限性。不能摆脱常识,是因为常识是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日常生活是人们所有最根本信念的贮藏场所,哲学论辩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就在于将哲学观点与这个信念库联系起来,或者以直接的方式,或者以间接的方式,也就是说对这个信念库本身进行改造。实在论的一大优点就是同常识一致,也就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致。不能回避常识的局限性,就是说要克服常识对于感觉的盲目信赖,对常识的信念即使不能提供合理的辩护,也要提供合理的解释。从洛克开始的实在论传统的所有工作,说到底就是在常识和实在论理论之间建立这种类似于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反思的平衡”。
从洛克的实在论到贝克莱和休谟传统的实证主义
洛克认为观念的来源有两种,要么来自感觉,要么来自反省。因为对外部事物的感觉是大部分观念的来源,而且只有获得了这样的观念,才可能有心理作用,从而有反省观念,所以,在洛克的两种经验中,感觉要比反省更重要。他的两种物性理论正是在阐述感觉的内容与感觉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不论是第一性质的观念,还是第二性质的观念,都是外部事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也就是说,感觉的内容与感觉的对象是结果和原因之间的关系。但是原因和结果是否相象呢?换言之,我们能否通过感觉而把握对象的本来面目呢?对此洛克这样回答:“第一性质底观念是肖像,第二性质底观念便不是。”(注: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4、102~103页。 )因为,“物体给我们的第一性质底观念是同它们形似的,而且这些性质底原型切实存在于那些物体中。至于由这些第二性质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观念,则完全同它们不相似;在这方面,外物本身中并没有与观念相似的东西。它们只是物体中能产生感觉的一种能力(不过我们在形容物体时,亦以它们为标准)。在观念中所谓甜、蓝或暖,只是所谓甜、蓝或暖的物体中微妙分子底一种体积、形相和运动。”(注: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4、102~103页。)
洛克主张唯物主义感觉论,但他的两种性质学说及其所预设的感觉与其对象的因果关系说和代表说,为贝克莱发展其唯心主义的感觉论提供了依据。为了论证他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观点,贝克莱指责常识,指责力求与常识一致的洛克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在这种指责时,他确实是抓住了洛克的观点的一些漏洞的。首先,贝克莱反对把对象与感觉分析为二,认为只是由于人们错误地运用了抽象,所以才使得对象和感觉由于互相抽象而彼此分离。实际上,任何可感知的事物都不可以离开我们对它所产生的感觉或感知。第二,唯物主义认为,各种观念自身离了心灵虽然不能存在,但是也许有与它们相类似的东西,为它们所模拟,所肖似,而那些东西是可以在心灵之外,存在于一种不能思想的实体之中的。对此贝克莱反驳道:既然感觉和对象是两个不同的项,而对象是在感觉之外的,怎么能比较它们是否相似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贝克莱针对洛克的两种性质理论,强调不仅第二性质(如颜色、声音、滋味等),而且第一性质(广延、大小等)也不是对象的摹本。他认为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是密切联系的,既然第二性质在心灵中存在,那么第一性质也应该在心灵中存在。同时,贝克莱还认为,第一性质,如大、小、快、慢等也是随着感觉器官的组织或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物体在晴朗的天气中看起来要比在雾中大些,远处的运动的物体看起来比近处慢些。这就说明,大、小、快、慢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它们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中。此外,贝克莱还认为,表示广延的单位是由人任意确定的,同一广延可以由人以不同的单位去表示,这就说明广延不在心外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
但是,贝克莱一方面认定人们只能同感觉打交道,另一方面却对感觉之外的领域作出明确的断言。他不仅断言感觉之外物质不存在,而且断言上帝的存在和心灵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独断论。
贝克莱的独断论受到了休谟的怀疑论的批评。与贝克莱的“观念”相当的是休谟的“知觉”。休谟把知觉分为两类,其区别标准是知觉的强力和活力的不同。较不强烈、较不活跃的知觉,叫做观念;较活跃的则是“印象”。观念来自印象。常识认为,印象是人们对于外部对象的感觉。但休谟认为这种对感官的“信托”只是一种“盲目而有力的自然本能”。(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134页。)对这种自然本能,可用怀疑主义来加以反驳:“我们既然假设,心和物是两种十分相反、甚至于相矛盾的实体,所以物体究竟在什么方式下来把它的影像传达到心里,那真是最难解释的一件事。”(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5页。)
如此彻底的经验主义势必不仅取消感觉之外的物质的存在问题,而且取消在贝克莱那里仍然设定的上帝与心灵的存在问题。
休谟的经验主义被现代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实证主义者像休谟一样取消了外物、上帝和心灵的存在问题;他们把这些存在论的问题作为“形而上学”问题加以抛弃。与休谟不同的是,实证主义者认为既然心灵的存在问题被取消了,那么就应当改变原来因为心灵的存在而形成的说话方式,不是只承认感觉或知觉,而是把原来叫做感觉或知觉的东西叫做“要素”、“所与”或“与料”。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所承认的一切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但必须是从这些“要素”、“所与”或“与料”出发演绎出来或构造出来。
金岳霖:从“有效原则”出发综合实证论和实在论
在金岳霖看来,感觉的地位问题或客观性问题和整个知识论的出发方式有关。金岳霖认为决定知识论出发方式的选择原则有两种,一是无可怀疑原则,一是有效原则。所谓“无可怀疑原则”,是以无可怀疑的命题作为知识论的出发点。金岳霖指出,无可怀疑的命题只有两类:逻辑上不能不承认的命题和“自明”的命题。可是,逻辑上不能不承认的命题无积极性(无实证性),考察知识论问题不能从这样的命题出发,而单纯的自明只是主观的、心理的自明。更重要的是,根据“无可怀疑原则”无法对实际存在的知识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说明。要能够对实际存在的知识作出恰当的哲学分析,必须以“有效原则”作为选择知识论出发方式的原则。所谓“有效原则”,就是作为知识论出发前提的一套命题必须能供给知识这一对象的各方面所需要的理论。贝克莱和休谟的知识论的出发原则实际上是“无可怀疑原则”,他们认为惟有感觉才是无可怀疑的知识来源,超出感觉的东西则是可怀疑的、不存在的。但是由这种原则决定的出发方式(金岳霖称为“唯主方式”)不能对知识作出理论上全面的说明。知识论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保证对象(被知)的实在感,一是保证其理论本身的真正感。但在金岳霖看来,贝克莱、休谟以及后来的罗素,所采取的唯主方式无法使我们得到对象的实在感,而“对象上的实在感既得不到,理论底真正感也得不到。得不到理论的真正感的方式就是无效的方式。”(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5页。 )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感觉经验的重视错了。金岳霖事实上也认为感觉是知识论的一个出发点:“知识论底对象既然是知识,知识既复杂而又以官觉为基本,我们底出发题目当然是官觉。”(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页。)但问题是,感觉并不是知识之可能的唯一条件。知识的另外一个基本条件是外物的独立存在(金岳霖认为理论的真正感也是以对象的实在感为基础的)。外物的存在是知识论所必须预设的,这一点甚至连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也无法完全否认——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认识论的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从感觉中推论出人们通常所设定的外物的存在。贝克莱把“物”定义为“观念的复合”,马赫把物定义为“要素的复合”,罗素先是认为可以从感觉材料中推论出作为原因的客观物质事物(在《哲学问题》中),后来又发现这种推论碰到同归纳推论同样的困难(没有必然性),便改变了手段:设法通过构造论从感觉材料演绎出事物来。但正如金岳霖在《罗素哲学》一书中指出的:“构造出来的客观物质事物是有某种组织或某种结构的感觉材料,它不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注:金岳霖:《罗素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既然感觉与外物的存在同为知识论的出发点,而且后者不能从前者推论出来(当然前者也不能从后者推论出来,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存在不被感知的时候),那么就应当把这两者同时包括在知识论的出发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对知识作出有效的说明。金岳霖明确指出他的知识论的出发方式的原则是“有效的原则”:“知识论有一套在前提上我们所承认的命题,这些命题要供给知识这一对象底各方面所需要的理论。如果它们能够供给如上述的所需要的理论,它们有效;如果它们不能够供给如上述所需要的理论,它们无效。”(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3页。)但问题是,这两者的关系如何?
正是对这个问题,金岳霖提出“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观点作为回答。所谓“所与”(the given), 即知识的材料——感觉中所提供的东西。所与有一个双重地位:既是感觉的内容,又是感觉的对象。就内容而言,它是呈现;就对象来说,它是具有对象性的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所与的这种双重地位表明,感觉的内容和感觉的对象并非如因果说和代表说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个体,是两项,而是同一个东西:“呈现就是所与,所与就是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5页。)当然,呈现与所与, 感觉内容与感觉对象,是在金岳霖所谓“正觉”上统一起来的。金岳霖对“正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正常的官能者在官能活动中正常地官能到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即为正觉。”(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5页。)正觉当然是感官的活动, 但不仅仅是感官的活动;它是正常的官能活动,而这“正常”起码有两个含义。其一,它是对外物的官觉。有些官能活动不是与外物有直接接触的活动,假如眼睛有毛病把一张桌子看成两张,官能活动虽有,而两张桌子之中有一张不是外物。这样的官能活动就不是正觉。第二,它是某一类官能者所普遍具有的官能活动。“正常是对于个体所说的,可是,一正常个体底正常是相对于它直接所属的类而说的。”(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 )由于感觉内容与感觉对象是在正觉上统一起来的,这种统一既预设了对象的独立存在,又预设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可共享性、可交往性——即所谓“主体间性”。实际上,用当代哲学的术语来说,知识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两种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由于感觉内容与感觉对象是在正觉上统一起来的,它们虽是同一个东西,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仍有不同的特点:“就所与是内容说,它是随官能活动而来,随官能活动而去的,就所与是外物说,它是独立于官能活动而存在的。”(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页。 )我们可以用“外在关系”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两个方面。所与作为感觉内容,也就是外物处于同感官的关系之中;显然,外物处于这种关系,是外物成为感觉内容的条件,所以金岳霖说“就所与是内容说,它是随官能活动而来,随官能活动而去的。”但外物与感官(及其活动)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即这种活动并不改变外物的性质,所以他又说“就所与是外物说,它是独立于官能活动而存在的。”
冯契:用实在论和智慧说对实证主义作双重超越
冯契对金岳霖的感觉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为解决“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金岳霖的感觉论,冯契作了三个方面的发挥和发展,一是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体”和“用”发挥和发展金岳霖的观点,二是把金岳霖的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基础上,三是从“智慧说”(广义认识论)而不仅仅是“知识论”(狭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感觉的问题。
金岳霖在论述感觉呈现(内容)与对象的关系的时候,用了这些范畴:部分和整体,关系和性质,但他没有用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所谓呈现就是处于同官能个体S[m][,n](N类中的M官能者S )的正觉关系中的外物。冯契的观点与此略有不同:“感觉是外界对象引起的,既是‘引起’,那就有作用。问题在于对因果性作如何的解释,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因和果割裂开来。”(注: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一方面承认感觉内容与外物对象不是彼此分立的两项,另一方面又承认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两种观点如何协调一致呢?冯契正是为此而求助于“体”、“用”这对范畴的。
“体”和“用”这对范畴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提出并一直加以运用和探讨的范畴。魏晋时期的哲学家王弼第一个明确提出这对范畴,并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后为多数中国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所接受的“体用不二”的思想。这里的“体”的范畴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实体”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或事物,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逐步把握了这个事物的各种属性、与其它事物之间和其自身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各种功能和样态,包括种种变化状态。这些属性、关系、功能和样态就相当于“用”的范畴,而所谓“体”或实体,指的就是对象全部多样性的内在统一的根据和源泉。从认识论上讲,正是这种根据和源泉构成了把对象的各种理论规定综合为完整体系的根据。也就是说,当我们达到对于“实体”的把握的时候,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实体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7页。 )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属性”范畴相比,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的特点一是更突出实体的“自己运动”的一面一“用”,这个词本来就含有动态的含义;二是中国哲学历来有强调“体用不二”的传统,认为作用是实体的自己运动,离体别无用,离用别无体。更进一步,哲学家们认识到实体的自己的运动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一切实体自己运动的内在原则。
冯契所做的工作,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解释(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哲学的传统对金岳霖的感觉论作进一步的发展。在他看来,对感觉与感觉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运用“体—用”范畴。首先,从感觉与感觉器官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感觉活动(神)是感觉器官(形)的作用。这就是说,感觉是以感觉器官为实体的,是感觉器官这种物质实体在一定条件下表现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并不能离开感觉器官而独立存在。反过来说,感觉器官之所以为感觉器官,正因为它有感觉活动。这方面,我国南北朝时期哲学家范缜的“形质神用”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由于感觉与感觉器官之间有用之于体的关系,所以,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样的感官对同样的对象就有同样的感觉。作为感觉之标准的是正觉,即正常人的正常的感觉;而与正觉相异的错觉、幻觉,也可以用客观的条件,包括主体感官方面的因素,加以解释。如荀子说:“压目而视者,一以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汹汹,执乱其官也。”(注:《荀子·解蔽》。)
还可以在另一方面运用“体—用”范畴:感觉与感觉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用之于体的关系。感觉确实是感觉对象造成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原因之外的另一个实体,而是实体自身运动的表现,或就是对象的一个方面,并不外在于对象。感觉对象对于感觉来说是“自因”而不是外部原因。从体用不二的观点来看,感觉与感觉对象正是在正觉上直接同一的。外物在同官觉的关系之外仅仅作为外物而存在;在这种关系之中,它表现为感觉(的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其所谓‘能’者即用也,所谓‘所’者即体也。”(注:王夫之:《尚书引义·召诰无逸》)
一方面,感觉是感觉器官的“用”,另一方面,感觉是感觉对象的“用”,这两者之统一的基础就在于感官对于外物的官觉活动。由于感觉器官的关系,感觉具有主观形式,所以是“能”的方面;由于同客观对象的关系,感觉具有客观内容(此内容就是处于同感官的关系中的对象),属于“所”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感觉是一个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矛盾统一体。
用“体—用”范畴刻划的能所关系、感觉与对象的关系,既适用于洛克所谓的“第一性质”,也适用于他所说的“第二性质”。同“第二性质”的感觉一样,第一性质的感觉也具有主观形式。荀子所说的“从山上望牛者若羊”,与“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与贝克莱举的例子,即远处运动的物体看起来比近处的慢些,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贝克莱的第一性质观念象第二性质观念一样仅仅存在于人的心中,而没有外部对应物。因为感官仅仅是感觉的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独立存在的外部事物,在正觉中,这种对象与感觉内容是直接同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同“第一性质”的感觉一样,“第二性质”的感觉的内容与感觉的对象也是直接同一的。冯契写道:“感觉的内容,无非是呈现在感官之前的客观事物,红颜色就是760μω的光波, 紫颜色就是390μω的光波,人尝到咸味就是盐本身的特性, 感觉的内容和对象是一回事。”(注: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可以用科学的手段来确定760 μω的光波呈现为红色光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760 μω的光波一定要呈现为红色光。因此,红颜色本身就是有客观内容的、亦即是客观对象的呈现,而不是由外在于它的实体所造成的与它没有任何相似性的结果。
冯契在金岳霖的感觉论的基础上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把金岳霖的理论放在实践的基础上。能所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既有认识关系,又有实践关系,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作为认识之起源的感觉,与实践有着比其它形式的认识更为密切的关系。人们的感官接触外部事物,总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和改造外物的实践中发生的:“对象的实在感是实践或者感性活动中主体最基本的体验”。(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的实践的成功将是包含在其中的感觉的可靠性的一个标志或标准。由于人的实践是在社会、集体中进行的,所以,感觉之能够给予客观实在,不仅得到感觉层次上的主体间性(“正觉”或“类观”)的担保,而且得到实践中的主体间性的担保:“在集体劳动中,不会产生唯我论,不会有主观唯心主义。”(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一个冯契没有明确提到的方面,来讨论感觉论上的唯物主义出发点与实践的关系。金岳霖在论他选择知识论之出发方式(也是其感觉论的出发方式)时说他所采纳的是有效原则,而“有效”的含义是有助于对知识作出全面的即合乎常识和科学实践的说明。然后他又说他的有效原则不同于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讲的“有效原则”,因为后者所引用的不是知识论,而是知识,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服务于生活,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有效。金岳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唯物主义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很有启发。为唯物主义哲学作论证历来是一项重要但困难的工作。问题在于,仅仅用逻辑论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逻辑论证只能在以下两方面起作用。第一,表明一系统(如唯物主义哲学)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自洽的、无矛盾的。但无矛盾只是一理论之为真的必要条件(从知识发展的眼光来看,连这也不一定),而非它的充分条件。第二,表明一理论确实是建立在已经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或理论上的,但唯物主义作为知识论的出发方式,本身是它的最高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对唯物主义前提作充分的不仅消极(证明其对立观点的矛盾)而且积极的逻辑论证。金岳霖关于出发方式之选择原则的观点给我们以启发,我们可以把“有效”当作唯物主义前提之选择的原则,但对“有效”的含义作进一步的理解——不仅理解为有助于对知识作全面的说明,而且理解为有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人们的科学研究。日常生活实践不加反思地预设了唯物主义前提,因为这个前提有助于人们在环境中的生存,有助于进行人际交往(假定外物存在的同时假定他人的存在)。科学家们在研究时也必须认定对象为实在的,而非虚构的;科学理论的真正感是以对象的实在感为基础的。如实地把握客观真理,也是科学工作最重要的规范性要求。在这双重意义上,唯物主义前提对于实践都是“有效”的。而正是这种有效,胜过无数种别的理论论证,是我们选择唯物主义前提的最重要论据。
同金岳霖一样,在根据实践有效原则选择了唯物主义前提(它承认感觉为外部对象的呈现)之后,要批判实用主义的实践有效原则,因为后者不仅引用于哲学的出发方式,而且引用于知识本身。事实上,正因为把实践有效原则引用于知识,否定知识与实在的关系,实用主义哲学是有害于日常生活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的:不尊重客观现实,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研究中,都是要碰壁的。因此,我们在依照实践有效原则选择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之后,又要进一步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把实践有效原则引用于知识(而非知识论)的实用主义。
在冯契那里,感觉的客观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智慧说的问题。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区别于知识论(或狭义认识论)之处,在于智慧说不仅要考察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关系,而且要考察“性”与“天道”的存在论关系,把认识过程看作是达到对世界最高原理或“道”的全面把握(也就是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的必经之途。在冯契看来,“一切的科学知识,哲学的智慧以及人的才能、德性的培养都离不开感性经验的基础。”(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感觉之所以是智慧的基础,不仅因为智慧以知识为基础,而知识以感觉为基础,而且也是因为智慧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向感觉的回复。首先,智慧的具体性是向感觉的具体性的回复。冯契在讲到智慧时所提到的辩证思维、理性直觉、人的德性、才能、艺术的意境、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具体的东西,因此都是“离不开感性具体或者类似感性具体的。”(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出于对智慧的具体性的强调,冯契认为“始终保持感觉的灵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其次, 同智慧的具体性相联系的是智慧的非语言性,这也是感觉论在冯契的智慧说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们在感觉的层次所把握的,也是种种无法用名言来表达的东西。在冯契看来,恰恰是这种具体的、不可名状的感觉,同实在具有最直接的联系。“我们肯定感性直观给予客观实在感,真正要把握道,不能够离开这种实在感。所以最高的智慧确实需要向这种直观复归。”(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对于感性经验的这种超越和复归,冯契借用“博学”和“心斋”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来说明。知识的基础是“博学”,但仅有“博学”还到达不了“性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要求超越在知识的层次所执著的那些区别和范畴。冯契借用庄子的“心斋”概念来表达这个超越,但并不认为这种“心斋”是冯友兰所理解的那种詹姆斯式的没有知识的纯粹经验,而认为它是一种可以更恰当地用庄子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寓言来表达的状态:“轮扁斫轮得心应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些活动合乎自然的节奏,道就在这样的活动中形象化了,取得了感性形态。”(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这种境界并不是冯友兰所说的经历了“正的方法”之后运用“负的方法”的结果。对于冯友兰来说,重要的是从“说话”向“沉默”的过渡:“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对于冯契来说, 重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哲理境界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而到达,但要求化理论为德性,在理论与实践统一中自证其德性之智,则是共同的。”(注:冯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金岳霖的知识论虽然以其实在论立场而超越了贝克莱、休谟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仍然是一种狭义认识论,就此而言仍然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与金岳霖相比,冯契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实证主义:他不仅捍卫了实在论的立场,而且突破了狭义认识论的眼界。
标签:金岳霖论文; 知识论论文; 冯契论文; 洛克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休谟问题论文; 人类理解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认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