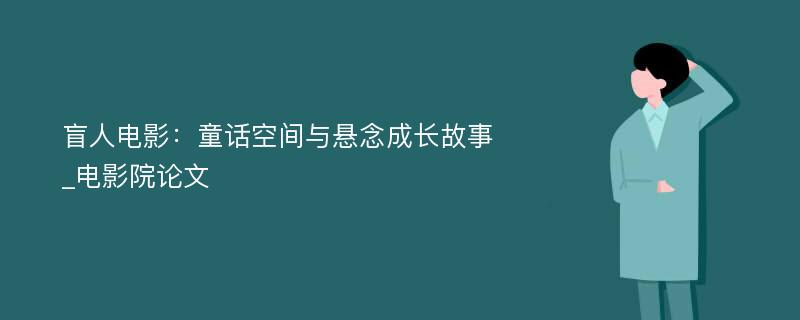
《盲人电影院》:童话空间与被悬置的成长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盲人论文,电影院论文,童话论文,故事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导演路阳自编自导的长篇处女作《盲人电影院》,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盲人电影院里的温情故事:无业青年陈语在贩卖盗版碟时,为了躲避城管的追赶,慌乱中躲入由老高创办的一家专为盲人放映的电影院。在他与老高、刘梅、老横、张航新这些盲人的相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影片在2010年釜山电影节上斩获“最受观众欢迎大奖”,在山寨之风大行其道的当下,本片风格清新自然,情感质朴真诚,显示出年轻创作者“我手写我心”的创作理念。
《盲人电影院》的片名即昭示了影片的叙事空间和主要人物。因此,空间和人物塑造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影片的艺术品质和主题诠释。影片通过对“盲人电影院”这一独特空间的建构,传递出创作者追求质朴传统的个人情怀和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真挚情感。但较为可惜的是,创作者没能在人物塑造上体现出在空间建构上的那种成熟的控制力,大多数主要角色失之于概念化和平面化,这必然影响了整部影片的艺术表现和思想表达。
文化空间与童话叙事
影片绝大部分戏份均发生、发展于盲人电影院及其所在院落这个不大的空间。场景的高度集中,一方面表明青年导演在剧作阶段便具有一种制片意识——考虑到拍摄资金不宽裕,导演在构思故事时有意识地让剧情尽量发生在为数不多的场景内,减少置景费用和转场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杨庆的长篇处女作《夜·店》同样也让剧情集中在一个24小时便利店之中。但在本片中,这一处理方式还有着更深一层叙事表意上的突出作用——构造一个与现代都市相对应的前现代式的生活场域。盲人电影院这个独特的空间场所,成为影片创作者投射其想象与期待的重要载体,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地理空间,而成为一个承载了创作者精神诉求、业已被改写与重构了的文化空间。
影片起始于陈语与城管的一场追逐。在极富动感的运动影像中,陈语一路狂奔至一个古式小院,情急之下闯入了正在放映影片的盲人电影院,一个被清晰交代的关门动作,顿时隔断了屋内与屋外两处空间。从动到静的节奏遽变和从明到暗的光线变换,外化了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转变。自此,陈语开始了他在盲人电影院的放映生活,也开始了一段生活在“他处”的精神体验。那么,之前生活在“此处”的陈语又是何种生存状况与精神面貌?陈语在逃避城管追赶的过程中,有几段升格镜头颇为诗意地传递了这一点。很显然,这是一个被严苛的生活现实苦苦追赶而精疲力竭的都市青年,慢镜头下茫然的面庞是陈语此刻内心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陈语是在躲避城管的追赶,还不如说他是在逃避生活压力的逼催——那个逃进电影院后关门的举动,不只是把城管关在了门外,更是把现实生活的世俗一面推挡在了电影院这个封闭、自足空间之外。至此,在这不长的叙事时间里,创作者已初步交代了两个空间下的不同生活方式,自然而不刻意,殊为不易。
事实上,当创作者把盲人电影院确立为一个与院外空间对立的场所,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代之以更具主观色彩的抒情笔法。盲人电影院由此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空间,而成为寄托作者内心希冀的一处世外桃源。在这一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其乐融融,全然不见世俗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虽然影片的创作起点来自于北京老城区一家真正的盲人电影院,但作为二度创作后的产物,影片中的盲人电影院确实少了一些人间烟火。影片“不合常理”地屏蔽了盲人世界的亲属及其他社会关系,而仅仅维系于盲人与盲人之间;舍弃了他们与亲属之间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这已经接近一种童话式的叙事策略,而对美好如童话的“心向往之”则含蓄地意指在高度物质化的当下,此种空间和生活方式日渐稀缺的无奈现实。
影片中有一段情节处理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两种“空间”的冲突与对立。电视台记者对盲人电影院的采访以及老高不识范冰冰的幽默对答,生活化地定义了本质意义上彼此脱离、互不相通的两种生活。这一来自外来者对“美”的评价在刘梅和其他盲人间产生了化学作用:自幼失明的刘梅无法感知自己的容貌,这种遗憾外化为她回屋后轻触铜镜、若有所思,而其盲人朋友们一一排着队去抚摸她的脸,以感知“什么是美”。在封闭的空间中,间或插入“外来者”形象,同样是为了建构一种并置和对比。这种发生于不同人群之间的观念碰撞,无形中丰满了对盲人电影院这一空间的塑造。
当陈语置身电影院空间中、与老高或盲人生活在一起时,叙事节奏舒缓、摄影机运动缓慢而不明显,营造出温暖、安闲的生活格调,陈语在多数时候也表现得自在和从容。可一旦陈语离开电影院这个空间,如在大公司面试、会见女友时,节奏会相形提速,并使用一些特殊的摄影技术(如升格镜头等)以烘托出陈语此时焦躁、不安的心境和状态。由此可见,创作者有意识地在运用电影化的手法来写人表意和定义空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创作者较为自觉的电影观念和丰富的调度技巧。
未完成的成长故事
影片既不是以高度纪实的手法勾勒一个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以强烈的戏剧冲突来结构全片,而是采取了一种以抒情基调为主、具有一定假定性和设计性的文艺片创作策略。影片叙事部分一个主要的悬念是:陈语最终是否会离开这些盲人的生活圈,重新回到女朋友或都市生活中去?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120分钟的期待视野。虽然有时“空间”也能上升为影片的第一主角(如安东尼奥尼的一些作品),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通过生活于空间中的人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主旨。因此,人物塑造是否立体,细节设置是否精妙,便成为左右影片艺术水准的关键。
陈语是一个刚进入社会、处于价值观迷惘期的无业青年,同时还是介于边缘和主流生活之间的“不稳定”者:一边是女友、爱情、大公司、高额薪水,一边则是盲人、友情、电影院和微薄收入。他的选择或者说他在影片文本内体现的前后变化,无疑最能体现影片的创作目的。但可惜的是,这些并未能在叙事中得以完整、清晰地呈现。
因为与老高都是爱电影的人,所以陈语在老高的游说下,顺理成章地留在了盲人电影院担当放映员和解说员。但陈语在电话里向女友隐瞒了这一点,说他在一个体面的单位上班,之后又数次向老高提出要去大公司面试,因为他并不想因为工作原因和女友分手。这说明在陈语内心里,其实一直没有放弃都市社会的生活观念和生存法则。要让陈语水到渠成地完成生活观/价值观的转变,必然需要通过老高和盲人们的言行举止来对他的内心和观念造成冲荡和影响。由此,影片如何塑造这些盲人群像、进而建构起他们与陈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实为关键。
从人物的功能设置上看,老高最接近于陈语的领路人,陈语也最有可能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完成一段“个人成长故事”。尽管老高和陈语一样是个爱影之人,但他的爱“影”源自于爱“人”——因青年时期的爱人,于是爱屋及乌地爱上电影;而当爱人离去后,电影自然就成了爱人以及过去美好生活的替代者和象征物。从挂满墙的两人合影以及那盒旧胶片不难看出,老高是一个生活在当下但“活”在过去的人,这也与他罹患老年痴呆症,在缓慢失忆过程中只愿意记住他想记住的那些人和事相对应。从中不难看出,在深层次上与老高发生最多对话关系的是“过去”和“爱人”,而不是现实空间中的陈语。影片中两人之间的对手戏不少,但很少有细节能真正深入到影响两人关系的亲疏起伏,大多像油一般浮于水的表层,特别是当陈语提出要去面试、离开电影院时,老高的强力挽留显得不太合情理,也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定位。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意大利导演托纳托雷的那部《天堂电影院》。影片中阿尔弗雷多和托托之间的忘年交,类似于本片中的老高和陈语,亦是影片中的一条叙事主线,但托纳托雷用各种细节铺陈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关系发展,如阿尔弗雷多帮偷拿买牛奶钱看电影的托托解围,托托则帮参加考试不会答题的阿尔弗雷多作弊等。两人之间的情谊不可谓不深,但阿尔弗雷多不希望托托和他一样,把世界局限在放映室里耗尽一生,为此他执意让托托离开,“不准回来,不准想起我们,不准回头,不准写信。”在挽留和劝离之间,在友情和前途之间,阿尔弗雷多的做法令人动容,其人物的丰满和情怀的高尚,通过叙事得到了完美地展现。
正如在童话故事中,如果没有“大灰狼”这类角色,便无法反衬出“小红帽”的纯真一样,影片在构建这一童话式空间时也必然塑造一些对立物,而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要是陈语的女友。女友希望陈语找一份体面、高收入的工作,通过叙事也可以从侧面体现出他们之间的感情还面临着女方家长的阻力。女友是物质社会里为数不少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的化身,她的“他者”形象多少带着创作者否定的意味。在此,女友角色的塑造带有较强的工具性和设计性。为了与陈语女友形成参照,影片还塑造了一位明眸皓齿的漂亮姑娘小鸥。她为了接近意中人陈语,假扮盲人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一个健全人假扮成盲人,这和盲人对健全人“看的能力”的羡慕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比照。小鸥“扮盲”进入电影院这一特定的生活空间,表层动机是接近意中人陈语,但深层动机其实是对这些盲人和他们身上质朴单纯等生活价值观的趋同。可惜的是,影片叙事并未围绕小鸥和陈语的相互关系制造出生动、有趣的情节,两人的关系不温不火,以至于当陈语女友再度现身时,陈语与之重修旧好,徒留门外的小鸥一脸落寞神情。
影片中塑造得比较到位的人物要算张航新。陈语在解说完北野武影片《花火》后与张航新的一段对话,既切合盲人电影院的独特性——观众不是看电影而是听电影,而且对陈语看待“电影”和盲人的观念亦造成了冲击。
通观全片,在人物塑造这点上,创作者还是暴露了一些处理上的问题:一是人物塑造略带脸谱化倾向,不够丰富和立体。老横,单从名字选择上便外化出创作者在设计这一人物时的目的。这在一部以写人为主的文艺片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二是陈语这个外来者与盲人和老高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他们之间欠奉互动,彼此影响便弱了许多。也正因如此,当陈语在片尾进入大公司等待面试时,为了让陈语完成“重回电影院”的封闭性结构,影片特意安排了一个长长的梦,在梦中呈现出他对老高和盲人们的紧张与关切之情。但这个梦既不符合现实逻辑,从叙事文本内部来看也不合情理。这个梦开始的起点颇为模糊,暗合了陈语对盲人电影院感情变化起点的难以确指。由此,陈语最后的“回归”缺乏充分的心理动因,更像是一个带有创作者明显“缝合”意图的虚幻之梦。
《盲人电影院》通过对纯朴/功利、传统/现代的并置,表达了创作者回归质朴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取向。可惜的是,舒缓的影像格调和直白的叙事风格之间形成的裂隙,影响了影片的叙事和表意。影片在空间建构和人物塑造上的得与失也予人颇多启示:电影创作中还是需要通过塑造丰富而立体的人物,用细节表达情感。如果不是依靠情节的层层演进和人物的多维构造,而是直白地表达情感,便有了跳出来言说之感。回头来看《盲人电影院》这个片名,它似乎急于把创作者的诉求呈递,多少缺失了一些含蓄的韵味,若为《老高与陈语》也许反而能多一分想象的空间。
